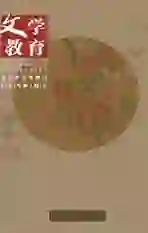浅谈美感与对象的关系层次
2021-02-04江思源
江思源
作为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命题——审美对象(的内容与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感受(即美感)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历代美学家讨论的重点。而在中国古代,审美感受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还突出表现为两个著名的命题之上——“声有哀乐”与“声无哀乐”。这样两种典型的艺术观,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美感”与“对象”关系问题上的两种对立性观点。
一.两种典型的艺术观
一般认为,“声有哀乐”反映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政治)美学思想,而“声无哀乐”更多地体现为道家(或玄学家)的自然(出世)美学思想。i这是主流的研究视角,但本文并不致力于这种主流研究的维度,而是单从艺术观的角度考量“美感”与“对象”关系问题上的美学价值。
“声有哀乐”的艺术美学观大概可以从先秦的“诗有哀乐”的观点说起,而“诗有哀乐”的思想又最终追溯到“诗言志”的观点: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尚书·尧典》中记帝舜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ii再到孔子的感慨:“《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iii一语道破“诗有哀乐”。其后,这种观点继续演变与发展,到了汉魏时期,呈现为两种相辅相成的观点——“声有哀乐”(主要体现在《乐记》当中)与“诗缘情”(主要体现在汉魏五言诗及一些诗论当中)iv。这两种观点虽然是针对两种不同的艺术对象而言,但其本质思想却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认为艺术对象是有“哀乐”的。换句话说,这种“哀乐”的艺术观表现在“诗歌”艺术之上就是“诗缘情”,表现在“音乐”艺术之上,则是“声有哀乐”。
与之相对,“声无哀乐”的发展脉络则不是那么清晰,而且其流传度与接受度也都不及“声有哀乐”,但这似乎并未妨碍其地位与价值。一般认为,“声无哀乐”的思想大概最早见诸于老庄的自然哲学之中,老庄讲的大音希声、大音弃声,所谓“希声”、“弃声”,指的是一种纯粹的“无我”(无情)、“忘我”(忘情)自然的状态;这种观点虽然已经暗示了“声无哀乐”的意味,但毕竟没有明确道破,只是到了嵇康这里,“声无哀乐”的观点才被正式提出来。在嵇康看来,“声音”(音乐)无所谓“哀乐”,“哀乐”只是听“声音”的“人”所具备的情感体验。
二.两种语境的碰撞
“声无哀乐”与“声有哀乐”虽然看似矛盾,但实际只是作为两种不同理论视域下的产物,二者都从各自的语境下阐述了美感与对象的关系问题,也正展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乐记》v开篇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也就是说,先有“人心”后有“音”,“音”是“人心”的产物与结果;后面紧接着又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就是解释“人心”,认为是“物”促使了“人心”的变化。这是一系列反向推导的过程,推到了最初原因——“物”——是“物”促使了“人心”的变化,而“人心”又促使了“音”的产生。这是一个总体的逻辑链条,主要说的是音乐创作过程中的“物”—“心”—“音”的关系,后面在此基础上又继续细化和补充了其他因素,这就是“声”和“乐”。“声”是介于“心”与“音”之间的一个环节,是“人心”在“感于物而动”的基础上“放行于声”得到的。形成了“声”之后,“声”之间相互“应”和产生“变”化,变成“方”(即条理次序)的状态,就“谓之音”了,把这些“音”组合起来并且通过“乐”(即演奏)的方式表现出来(即“比音而乐之”),就是“乐”了。到这里,全部的逻辑链条已经完成。
我们可以表述为:“物”—“心”—“声”—“音”—“乐”。后文紧接着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乐心感者……其喜心感者……其怒心感者……其敬心感者……其爱心感者……: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vi这段话一方面再次重申“心”与“乐”的逻辑关系:“乐”是由“心”“感”于“物”而产生的,本质上是“心”中“感”的产物;另一方面着重强调“乐”“心”关系的逻辑结论:“是故”“乐”就呈现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这六种“感”的状态,也就是——哀心之声、乐心之声、喜心之声、怒心之声、敬心之声、爱心之声——这六种“声”。
《乐记》中反复强调“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成于声”,其实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人心“生”音,情动“成”声。然而,不管是“生音”,还是“成声”,它们又都同时指向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创作”:“声”“音”“哀”“乐”等等,都只是针对音乐“创作过程”而言的,是“创作层”的“声音”的“哀乐”问题,而不是针对“接受层”(受众)而言的;另外《乐记》所谓的“乐”,是在“相应”之声、“生变”之方、“成文”之音、“比音”之乐的基础上,配以“戚羽”舞蹈而形成的,其实质是“乐剧”,也即儒家所谓的“诗舞乐”之于一体的“乐”,因而这里说的“乐”是有“内容”的“乐”,是“内容层”上讲的“乐”。
下面再来看看嵇康的《声无哀乐论》vii。《声无哀乐论》全文是以“‘秦客与‘东野主人两人之间的反复辩驳,来论证‘声无哀乐的命题”viii的,因而把握二者辩论的焦点才是快速切入文章逻辑的关键。通过文章梳理,我们发现《声无哀乐论》文章的前两段分别作为全文的立问与立论段,其中涵盖了所有后文要“辩论”的和要“反驳”的观点。据此,我们只需要梳理清楚这两段的逻辑,就足以把握全文的逻辑结构。
首先是立問段。文章伊始,“秦客”就引经据典来重申“声有哀乐”,这里“秦客”主要举了两个经典的例子,一是《乐记·乐本篇》当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二是提到孔子与季札的故事。这是两个很典型的说明“声有哀乐”的例子,“秦客”据此发难——“声无哀乐,其理何居?”
其后是全文的立论段,在这里,嵇康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说明“声无哀乐”的:其一,“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天地之间……其体自若,而不变也。”也就是说,他认为“音声”犹如“气味”,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东西,它的本体永远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不会(因为“人”的介入)有什么变化;其二,虽然“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名实对应),但是同样的“哀乐”却对应着不同的“声音”,即“声音”与“哀乐”并没有绝对的固定的匹配关系,因而“声音”与“哀乐”并没有对应关系;其三,“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哀乐”是内心深处本就有的,只是遇到了“和声”而表现了出来,因而并不能说“声音”有“哀乐”;其四,审美对象只是唤起主体的“爱”、“憎”、“喜”、“怒”,但并不是对象就具有了“爱”、“憎”、“喜”、“怒”的情感,它从本质上只是唤起了主体“哀乐”的一个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哀乐”。这样,嵇康便通过“音乐的本体不变”、“声音无常”、“先有哀乐而被激发,哀心有主”、“声音只是一种唤起哀乐的工具”这四条细致的分析论证了“声无哀乐”。
由此可见,在嵇康这里,“哀乐”是听众内心的情感,音乐则只是唤起“接受主体”内心已有的“哀乐”,因而“哀乐”只是“接受者”内心的“哀乐”,是从“接受层”(听者角度)来说的,这显然与“声有哀乐”所指向的“创作层”恰恰相反;此外,嵇康多次提及“天地”之“音”、“至和”之“乐”等,是一种没有“文”、没有“诗”、没有“舞”的纯粹的“乐”,“按照儒家的乐观,这个乐其实是属于‘音的层次而非‘乐的层次,”ix因而严格意义上讲,这里的“音乐”(更多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旋律和音符)只能称之为“乐音”,如果是人为的,则约略相当于现在意义上的“纯音乐”。因而从本质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侧重于“形式层”的“乐”,而不是儒家美学所追捧的有内容(质)的“乐”。
三.结语
据上可知,虽然从结论而言,“声无哀乐”与“声有哀乐”看似针锋相对,但它们在各自的理论视域内是有效的,因为它们各自针对的美感与对象的关系层次是相同的:一方面,就“创作层”而言,由于创作“音乐”的人(艺术家)本身是带着情感创作的,因而难免会其情感灌注于作品对象之中,使其存在本身就充满了主体心理中的“哀乐”等情感。而就“接受层”而言,艺术对象只是作为一个召唤我们情感感受的客体,其本身无所谓“哀乐”,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唤起主体内心“哀乐”感受的工具与手段;另一方面,单就审美对象而言,“哀乐”的存在也是分层次的:审美对象的“内容层”由于它们本身就含有“意义”、“意蕴”x,所以往往是存在“哀乐”的。而审美对象的“形式层”,由于它们本身只是承载“内容”与“意义”的客观的“符号”,因而也就无所谓“哀乐”与否。
注 释
i徐文武:《嵇康<声无哀乐论>再识》,《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25卷第2期,第40页。
ii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iii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iv参见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v参见乐本篇(一)、(二)中的部分段落。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50页。
vi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vii此部分后面的引文皆出于嵇康之《声无哀乐论》,故后面不再赘述。参见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120页。
viii车坤:《论心与音乐的关系——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思想初探》,《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總第181期),第71页。
ix杨艳香:《声有哀乐:论音乐的‘情感——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为例》,《安徽文学》,2008年第8期,第139页。
x从内容层面上说,譬如有文字的文本,内容中往往是包含有情感的,中国古代王弼所说的“言”、“象”、“意”,对应到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就是“形式”、“内容”、“意蕴”(即情感意蕴),而“内容”与“意蕴”是同属于广义上的“内容”的,也就是说“情感”本身就作为“内容”的一个层面而存在,所以“内容”中往往必然包含“哀乐”(情感)。参见王宏建主编:《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81—301页。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