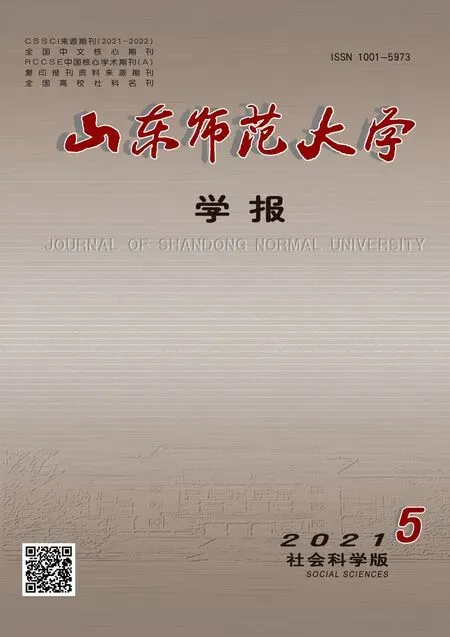论《聊斋志异》与清代侠义主题的温情化*①
2021-02-01王昕
王 昕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1)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自《史记》而下,慕侠心理与任侠行为就成为诗歌、小说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2)张华:《博陵王宫侠曲》,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12页。侠义的本质是以武犯禁,是一种向不公道的命运或体制抗争的精神。每一个时代和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侠义观念的书写。这个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主题,随着时代演进而各有侧重。
李白《侠客行》云:“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禛《侠客行》则说:“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这两首唐代的诗歌,就包含了侠义主题的内在立场和诉求的冲突。李白歌咏的是侠客功成不受报;元稹诗中的侠客则欲求身后名。一面是民间对侠客崇高到没有自我的期许;一面是为侠者本人对事功名誉的渴望。这种张力在后世的侠义故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面向。
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清代文言小说,在侠义书写上呈现出与白话侠义小说不同的进路。在这样一部包含500余篇故事的文言小说集中,侠义主题所占比重虽然不大,却能在众多篇章中别树一帜,是因为蒲松龄赋予了侠义主题以鲜明的温情化民间色彩。《聊斋志异》中的侠者有文言小说中惯有的仙侠;有不具备神奇武艺的普通人;有神秘的书生侠客;有以女性身体拯救绝嗣者的狐魅与侠女;甚至还有老虎、大鸟一类禽兽之属。内容则涉及异类爱情、科举、孤愤、经济、战乱、灾异、报恩、复仇等等。
《聊斋志异》对侠义主题的温情化书写,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古典传奇和志怪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功,是因为蒲松龄在继承前人题材和主题之外增添了新的质素。梳理和描述这些新质,是研究和阐释《聊斋志异》艺术成就的关键点。
一、《聊斋志异》对“侠”的新定义
侠义本是史不绝书的一个主题。侠义本有身份之别与诉求的不同。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就感叹布衣之侠的不可得闻。战国到秦汉,所谓游侠多是政治势力的代表:“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3)司马迁:《史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司马迁所推重的闾巷、匹夫之侠,因其事迹淹没不见,而未能进入正史的书写。其后的时代,直到魏晋时期,张华的《游侠篇》着意的仍然是属于“王者亲属”的战国四公子,歌咏其豪奢与拿云手段:“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名。龙虎相交争,七国并抗衡。食客三千余,门下多豪英。”在那个时代,重诺轻生的侠,指的是豢养门客与私剑的孟尝君、春申君那样的诸侯国公子。他们凭借政治地位和个人财富而招纳剑客,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在唐宋之后的庶民社会中,个体小民逐渐失去了陈子昂所谓“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报国热情,普通人缺少“大人物”那种急公赴义、急国家之难的能量与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小说中,为人们沉湎颂扬的是爱情故事的帮助者,如蒋防的《霍小玉传》中为霍小玉打抱不平、强行挟持负心人李益去见霍小玉的“黄衫客”,薛调的《无双传》中为王仙客救出无双的“古押衙”,许尧佐的《柳氏传》中为韩翊“犯关排闼”,从蕃将沙吒利府中抢回章台柳氏的剑客许俊,裴铏的《昆仑奴》中为崔生盗取红绡的“昆仑奴”;隐身负贩的剑客异人,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一类被藩镇蓄养的游侠刺客,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录的十几位“盗侠”,等等,都算得上司马迁所谓的以武犯禁的“布衣之侠”。
宋明两代小说在侠义主题上没有太多的阐发,也没有形象突出的侠之大者,大多延续唐人故事主题。《夷坚志》的《侠妇人》写北宋末年,南方人董国庆在北方做官,因中原陷落,不能归乡。逆旅主人帮他买一妾成家。妾见董贫,就以治生为己任。“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每得面,自骑驴入城鬻之,至晚负钱以归。率数日一出,如是三年。获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这个善于经营的妇人,知道董国庆是流落在北方的宋朝官员,就找到了一个据称是她兄长的估客,请他带董国庆回家。董害怕漏泄身份,又疑两人欲图谋自己,大悔惧,矢口否认。估客大怒,收走了他的告身文书,临行董妾送给他一件手制衲袍,告诉他返家之后,千万不要接受估客送他的金钱,这样估客欠她的恩情尚不足以回报,就会再次带她回乡。董国庆返乡之际,估客果赠以金银,董举袍相示,估客大惊,称妇人的机智果然在自己之上。董国庆返家后发现妇人赠送的衲袍内缝满箔金,得解缓急。翌年,这个妇人也由估客带归于董。该故事在南北宋乱离的背景之下,写了一位出身下层的女子。她的“侠”并非她有过人的身手,而似乎是指她和江湖暴客一段神秘的恩义,至于江湖暴客为何欠她一段人情则秘而不宣。这位下层女子,虽只是身为人妾 ,但有个人担当,靠负贩经营之才,以及预料世故人情的见识,使丈夫和自己都安然摆脱困境。《志补》卷十四《解洵娶妇》中的解洵夫人的侠义行为与之类似,也是实施于家庭成员内部。她对丈夫解洵的侠义行为,包括在北境成亲时,以其丰厚的妆奁使解洵走出流落饥寒之困境,她自言“非我之力,(解洵)已为饿莩矣”;在解洵思家欲归时,她为解洵备办“川陆之计”,一路水宿山行,防闲营护,全靠妇人之力。后解洵娶妾负心,辱骂妇人,“妇翩然起,灯烛陡暗,冷气袭人有声”,灯光复明的时候,解洵已经变成了一具无头尸首,妇人和她的囊橐都已不见。这个故事和《侠妇人》中董国庆的故事很相似,但更具唐人小说的剑侠色彩。
洪迈以“侠妇人”称呼这些女子,似乎预示了侠义主题在宋代之后某种现实化的转向。
《夷坚志》中较少唐传奇中冷冽神秘的侠者,而将侠义许之于默默生存在市井中的小人物。如护卫家财的婢女(《蓝姐》)、打抱不平的商人等等。明代邹之麟的《女侠传》、冯梦龙的《情史》乃杂取古今人物故事而成的类书,并无多少个人创作的贡献。
回应着明清庶民社会日常困境而生出的期盼,《聊斋志异》为侠义注入新的理想。侠的以武犯禁,就是以法外的手段对付仇家。诗僧贯休写侠客,有“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的咏叹,即是说侠客行踪的神秘。蒲松龄崇拜侠义精神,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中曾提到:“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他感叹,男儿不得志,人生不得行胸怀,“即不游侠,亦何能不曰太阿、龙泉”?(4)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聊斋志异》中的侠义故事,就是蒲松龄口中的太阿、龙泉。这些侠者不是唐前史传和小说中那种侠之大者,而是对小民扶危济困的布衣之侠。其行侠的空间乃在日常生活中,行侠手段则主要是民间的互助。
《乔女》中的穆生之妻乔女,在穆生死后抚孤不嫁。孟生因其品性贤淑,托媒相聘,乔女“虽固拒之,然固以心许之矣”。乔女感念孟生知己之遇,自称因貌丑,“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对孟生许之以心,守之以德,报之以义,在孟生病亡后为其护产抚孤。乔女卒后,孟生之子打算将乔女与父亲合葬,结果“棺重,三十人不能举”(5)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86页。,只得遵乔女意愿,葬于穆生坟侧。乔女对个人意志的坚持,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丁前溪》也是侠义故事的翻新。诸城人丁前溪,富有钱谷,游侠好义,慕古代侠客的为人。在逆旅遇到好客的店主妇人,“莝豆饲畜,给食周至”。时遇大雨,丁盘留数日,主人家贫无以饲畜,店主娘子将房顶上的茅草撤下来,帮丁前溪喂牲口。丁很感动,临行付金酬之,主人妇不受。丁赞叹而别。嘱曰:“我诸城丁某,主人归,宜告之。暇幸见顾。”数年后,因为岁饥,逆旅主人前往丁家求告。丁前溪记起前情,“跴履而出,揖客入,见其衣敝踵决,居之温室,设筵相款,宠礼异常”(6)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并马上派人将钱物送到主人家。这个故事的落脚点在逆旅主人施恩不图报,丁前溪知恩图报。虽然所“施”与所“报”,都是价值有限的钱物一类的交换,并非大侠那样然诺千金、慷慨死生的故事。这类布衣之侠表现的是某种民间的温情,是民间互助道德的具象故事。
二、庶民社会与布衣之侠
《聊斋志异》的侠,依然葆有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果决勇敢和为他人牺牲自我的精神。但其救助的对象则不止于“士”,而是那些无力的人们,其“不爱其躯”的牺牲也不止于个人性命,而是包括了女性身体的奉献与牺牲。由此,引起了侠义主题蕴涵的丰富与变化。在《聊斋志异》中,侠义非只是任侠敢死那么单纯,而是由不爱其躯的慷慨,化为手段多样的民间互助。如为民伸冤、存孤纾困,乃至以性行侠等等。
明清时期重男轻女、婚姻论财的现实,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现象十分普遍。如明代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多鳏旷”,浙江“金衢之民无妻者半”,处州府松阳县 “有逾40不能妻者, 虽其良族亦率以抢婚为常事”(7)常建华:《明代溺婴问题初探》,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7页。;清代浙江温州“十人之中,八无家室”;福建贫家男子多“年逾四五十岁未娶”者等。这种情形带来的后果是后代繁育的困境以及男女大防的松弛,这类现实反映在《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中,就是虚幻想象世界中的“以性行侠”、狐魅鬼婚一类的主题。《红玉》中的冯生丧偶,因为家贫屡空,无力再娶。与狐女红玉交往后,红玉馈赠白金40两助冯生娶妻。他所论嫁娶的吴村卫氏,有一个18岁的女孩儿,因为“高其价,故未售也”。卫氏是居室逼侧的寒门小户人家,女孩荆钗布裙,神情光艳,明显是因为美貌而标高了婚姻的价码,所以拖延到了18岁仍然待字闺中。卫家见冯生“倾囊陈几上”的40两白银而喜形于色,顺利缔结婚姻。虽然40两白银的高价,是因卫家女孩儿貌美的一个特例,但婚姻论财却是明清社会的普遍现象。如果没有狐女红玉的资助,靠书生的家境自是无力再娶的。这样黯淡贫乏的人生,同样是如在陷溺,等待着行侠者的拯救。
王跃生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对18世纪中国社会男性晚婚和不婚群体作过统计。根据他的研究,在18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中,25岁以上未婚者在总样本量中占15.37%,晚婚比例接近六分之一;30岁以上未婚者占总样本数的10.33% ,40岁以上未婚者占总数的比例为3.27%;45岁以上未婚者所占比例为1.25%。这些结果说明,在当时社会晚婚比例是比较高的。在晚婚者中绝大多数为出身社会中下层者。晚婚男性主要集中在贫穷家庭出身者中。经济困难是其婚姻失时的根本原因,男女性别比例在一些地区的严重失调加重了其婚姻的难度。这些问题,对社会中下层家庭的人口增长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正常婚姻秩序的冲击。由此使男女在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禁闭难以形成,至少使严厉的男女“大防”松弛下来。(8)王跃生:《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男性晚婚及不婚群体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义者,宜也。”使物各得其宜,满足了人事应该、基本的公正与需求就是“义”。像狐精霍女(《霍女》)那样:“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用风月手段让吝啬鬼破家,为穷书生“躬操家苦,劬劳过旧室”,又为之谋娶妻室,诞育后代。异史氏总结的这类“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的庶民社会中的侠义,唯花妖狐魅可得而行之。这类女子之侠反映了庶民社会的独特需求。自古以来子孙后代的繁衍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价值。《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赵崎注:“于礼不孝者三事: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中,无后为大。”孟子这句话本是针对先秦的贵族而言,为古代圣王大舜的不告而娶辩护。所谓“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这些“不孝之行”跟平民阶层基本沾不上边。像蒲松龄的父母只是平凡的乡间翁媪,没有什么权威和政治地位,绝不需要“阿意曲从”,事实上蒲松龄妻子刘氏虽然颇得公婆赞许,可在分家析箸之际,却因为老实而在冢妇与众妯娌之间吃了大亏,公婆难以片语主持公道;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蒲松龄虽“家贫亲老”,汲汲禄仕却是求之不可得。所以,孟子之名言对中国社会影响至大的就是“无后为大”。很多的社会组织、家庭伦理和情感的悲欢都是这句圣人之言的实践。《聊斋志异》的很多故事即是这一中心价值观念的演绎。
那些女子之所以被称为“侠”,是因为子孙繁衍的重要性同于先秦“兴灭国,继绝世”之大义,是古老的人本主义伦理精髓的平民化的表现。因骨子里有一个堂皇正大的“义”字存在,故妇人女子可以不爱其躯,以性行侠也。
《论语》认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是从圣王那里建立起的宗法道德。《史记·五帝本纪》:“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夏亡,商汤封夏后,商亡,周封纣王兄微子于宋以奉商祀。吕思勉认为:“所谓兴灭国、继绝世,则同族间之道德也。《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盖古代最重祭祀,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者,则不绝始封之君之祀而已。此义多有行之者。”(9)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不绝封君之祀”,是封建分封时代,国与国或者同族间的道德。在民间社会,存留子嗣就如“兴灭国,继绝世”般的重要。
在近世之民间社会,无财无力的平民之家,子嗣是延续一个家庭的唯一手段,祖宗是他们的神灵,子嗣是这家族崇拜信仰的核心。诞育后嗣,乃是平民社会中,拯救陷溺、兴灭国、继绝世般的崇高。从《史记·游侠列传》所言的侠客“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到明人邓原岳《侠客行》所谓的“壮士借名仍借躯,不似君卿但唇舌”(10)陈田辑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544页。,身体的牺牲,始终是侠客救危扶困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爱其躯”的所指却是有所变化。《聊斋志异》中那些不爱其躯的侠女,反映了平民社会对侠义的新渴求。
三、“不爱其躯”的女性侠义
《史记·游侠列传》太史公赞云:“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游侠救人于困厄,救济人们生活所乏。百姓日常生活中所乏之事甚多,则侠“趋人之急,甚于己私”的施展空间亦甚为宽泛。志怪与传奇的书写传统,为蒲松龄在侠义主题上的想象和尝试提供了掩护和价值依据。《聊斋志异》中的侠女用“不爱其躯”的献身方式来解决贫寒知识分子经济困窘、无子嗣的焦虑。《侠女》中的顾生,家綦贫。年过二十五尚未成婚。跟邻村男子是同性恋的关系。如研究者指出的,同性恋也是部分底层未婚男性满足欲望的重要形式。明清小说中同性恋故事的盛行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现实。有数据显示,明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福建全省男性人口占福建人口总数的74.63%,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量男子无法娶妻,刺激了当地“契兄弟”“契父子”的盛行。(11)吴存存:《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叙略》,《中国文化》2001年第十七、十八期。同性恋这种畸形情感补偿方式,有悖于人伦而又无益于家族的繁殖和延续,自是受到蒲松龄的排斥。顾生的娈童乃是一只白狐,被侠女所杀。侠女受到顾生母子的照顾,她报恩的方式是主动献身,为贫不能婚的顾生诞下子嗣,为顾家延续血脉。之所以称为侠女,是因为她的见识非同寻常女子,她看到男女欢爱的实质是宗祧大计,所以说“相报不在床笫也”,她对贫弱的顾生母子的关切和救助是根本性的。她在诞育子嗣大功告成之后,也如古来的各类侠士一般,“事成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一晚,侠女忽款门而入,声言大仇已报,手提革囊之中的是仇家的头颅。侠女言顾生福薄无寿,叮嘱他要善待儿子,将来光大门楣要靠这个孩子 。说完之后乃 “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12)蒲松龄著 、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聊斋志异》中侠女的女性特征、才干乃至性魅力都成为行侠的资本。蒲松龄第一次把“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坐实在了侠女的生理性别上。小说从侠义行为的原则推演,“感君恩义许君命,泰山一掷鸿毛轻”,牺牲对象从男侠的生命扩大到女侠的身体,似是顺理成章。
《侠女》的原型来自唐人小说《崔慎思妾》和《贾人妻》,故事框架是侠女忍志为亲报仇,其间嫁人生子,报仇之后,弃家远走,绝无消息。这类故事虽相隔几百年,侠女的基本品格几乎没有变化,都是轻儿女之情,无家室之恋。唐代侠女故事的重点在报仇,结婚产子是侠女为在社会托身立足而不可免除的义务和掩护,为了断绝情念,唐代侠女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婴儿。在《聊斋志异》中,故事的关键却是侠女为无力娶妻的穷书生诞下婴儿。女性以自己的贞操、身体来报恩行侠,洋溢着民间道德的温情。在传统的民间社会,子嗣是维系伦理秩序的根本,也是男女之情为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一个母老家贫、无力娶妻的穷书生,固然如在水火之中,妻财子禄,样样悬望空中施来援手,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迫切的还是宗嗣香火。为了报答顾生母子的周济照顾,侠女主动与书生私通,“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聂绀弩称赞侠女的崇高,“在她以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贞操报恩,自己为一个贫不能娶,自己又不与他结婚的恩人生子延祧。这样就是她作了自己的身体、贞操的主人,有了自己的人身的自由”(13)聂绀弩:《侠女、十三妹、水冰心》,《聂绀弩全集》(第7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575页。。这种崇高的“自由”颇有可议之处,侠女的行为体现的是侠者“不爱其躯”地“报”的逻辑,而不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侠义的精髓是知恩必报,而且这种“报”历来就不是等价的。侠者一旦受人恩惠,就有报恩的义务,他的身家性命就不再属于自己。侠客的自由意志只是体现在牺牲的慷慨上,而不在报恩义务的承担与否,更无法选择报恩的对象。在蒲松龄笔下的男性侠客故事中,不得中顾个人之私的被动牺牲,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深层思考。
《田七郎》就在侠义报恩的叙事结构下,揭示了恩义背后的社会不公,以及侠者受报恩义务支配的不由自主。富家子武承休欲用重金结交猎户田七郎,七郎母子力图躲避,但陷于囹圄的田七郎还是靠武公子的钱财脱灾。七郎的母亲声言儿子的一切不再是她“所得而爱惜者矣”。施恩者就如放了一笔高利贷般的喜悦,受恩者则“终不乐”,惟愿恩主“终百年,无灾患”,七郎后来终不免以死报公子之恩。七郎母亲所谓“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实在是蒲松龄看穿了侠义光环之下,施恩者与报恩者关系的实质就是钱财和性命的不等值交易。在女侠报恩的故事中,性命的牺牲转换成性的牺牲。侠女要报答书生是不由她选择的,她因贫困而受顾生家的接济,但她对顾生本人并无好感。这个顾生平庸福薄,还有娈童之癖。顾生之母为儿子提亲时,“女默然,意殊不乐”,对待顾生的试探,侠女始终冷淡乃至厉色相对。侠女所谓“相报不在床笫”,是因为有比以身相报更彻底、更富牺牲精神的报答方式,这便是对伦理道德的根本维护与奉献。在这里,作为侠、作为女性,她的情感和自我都是不存在的,她对妻子这一角色的认识就是操持家务、传宗接代,“枕席焉,提汲焉,非妇伊何也?”侠女不拘于婚姻形式的“私顾”行为,同田七郎颜色惨然地践行报恩义务,其为“义”所驱驰、役使的本质并无分别,因而谈不上女性的自主自由,更罔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位剑侠式的女性之所以“忍小耻而就大计”(14)李贽:《藏书》(卷37),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7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者,在于她对伦理秩序的精髓有着清醒的体认、自觉的维护。当书生的娈童嘲笑她这个“贞洁人”的时候,侠女是“眉竖颊红,默不一语”的。侠女这个以性行侠的人物,同《聊斋志异》中的《红玉》《霍女》《房文淑》诸篇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几位用身体赈济穷书生、延嗣抚孤的女性都算得上自我牺牲。蒲松龄不愿意深究故事蕴含的性别歧视意味,而用修辞技巧使歧视合理化。小说中侠女和《聊斋志异》的花妖狐魅一样,是作为伦理教化之外的异类身份出现的。选择侠女和狐魅作出身体和色相的牺牲,也可以见出作者轻侮的态度。《侠女》篇末异史氏曰:“人必室有侠女,而后可以蓄娈童也。不然,尔爱其艾豭,则彼爱尔娄猪矣!”将侠女与娈童并举,还打个公猪母猪的比方。所谓“鬼可虚情,人须实礼”,这些女性都不需男子付出责任与义务,她们本身也没有自我的意识和要求,侠义就在身体的奉献和情感的付出,结局则是轻身径去。这位侠女缺乏生命的自觉和自主,只是文言小说的侠义主题和片段化的人物叙事方式,保持住了其神龙首尾的神秘感罢了。
《霍女》中的狐精霍女,凭着绝伦的美貌,在三个男人之间辗转来去,让吝啬的朱大兴为她的奢靡倾家荡产,令好色的何生惑于她的手段而不自省。她逃到贫士黄生家里之后,却又安贫耐劳,躬操家苦,劬劳过旧室焉。不但肯为黄生自卖自身,还助黄生娶妻生子,重振家业。这个狐女“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为黄生赚得千金之财,靠的是性魅惑力。异史氏称赞“女非无心者也”,则其诸般放浪、不爱其躯的行为,也可以视为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手段。此种侠女、狐女在《聊斋志异》中的出现,可视为侠义主题在志怪题材中的发展,也是庶民社会心理的反映与迎合。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食与色、生殖和繁衍层面的问题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救赎了,其意义不下于存亡继绝,救危扶倾。
《聊斋志异》将游侠元素加入志怪题材,塑造了新的侠形象——动物侠,如禽侠(《禽侠》)、狐侠(《红玉》)、虎侠(《赵城虎》)等。通过对这些动物侠的人格化描写,拓展了侠主题。鹤鸟巢于某寺鸱尾,三年中“每至鹤雏团翼时”,殿藏大蛇“辄出吞食尽净”。第四年,同样的悲剧即将再次发生时,大鸟应邀而至,只见它“翼蔽天日,从空疾下,骤如风雨,以爪击蛇,蛇首立堕,连摧殿角数十尺,振翼而去”,真是痛快淋漓,难怪作者大加赞赏:“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飙然而来,一击而去,妙手空空儿何以加此?”妙手空空儿为唐传奇中的侠客,剑术神妙,作者以大鸟与之相比,可以说是无上的褒扬。《聊斋志异》著名评点家但明伦更认为“禽鸟中有志士,有侠仙,人有自愧不如者矣”。这个故事来自杜甫的《义鹘行》。杜甫借“义鹘”为苍鹰报仇的故事,激发人类的道德感,所谓“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洪迈《夷坚志》就有一篇“义鹘”,将杜甫诗歌变成一篇志怪故事。《聊斋志异》乃是这一传统“禽侠”主题的延续。
《赵城虎》里,赵城有个老妪的儿子为虎所食,她告到县衙,请求杀虎给儿子偿命。隶卒李能因无法完成任务,“受杖数百,冤苦罔控。遂诣东郭岳庙,跪而祝之,哭无声。无何,一虎自外来”,“贴耳受缚”。这只为了不连累无辜而自投罗网的老虎,可称为虎侠了。
传播神奇怪异的事情,固然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但这只虎侠,塑造得失于夸张,完全没有老虎的野性和兽性。不但听得懂人言,领了县宰的命令,用捕获的野物赡养老妪,还“时衔金帛掷庭中”。更奇特的是,老妪死后,老虎吼于堂中,招来族人为其营葬。这分明就是一只谙识人间事理、熟知风俗礼节的“山中王者”。
老虎是古代中原地区最令人畏怖的野兽,关于老虎被人类教化的传说早已有之。《搜神记》中,汉和帝时荆州刺史王业,敬天爱民,“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山无豺狼”,常“有二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王业死后,老虎就离开了荆州,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神异故事用老虎的低头曳尾,宿卫在王业身旁的恭顺,衬托出王业作为刺史的道德感化力。此种“猛虎渡河”式的良吏书写,在《风俗通义》《洛阳伽蓝记》《后汉书》等书中就有记载(15)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搜神记》中,有母虎为报答人类的助产之恩,再三送野兽肉到人类家门的故事。但像《聊斋志异》这样被完全教化为谙识世俗人情的“虎侠”鲜有其匹。
侠义出于伟大的同情,是向不公正的命运或体制的抗争,在民间一直广受欢迎。《聊斋志异》中这些世俗化、人情化的动物侠士,显示了蒲松龄被温情所控制的立场和想象。
历来对侠义主题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水浒传》《水浒后传》《荡寇志》《三侠五义》《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一类的白话小说。如鲁迅所说:“遂亦特有‘演说’流风”,“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年而再兴者也”(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9页。。从明代金圣叹、清代蔡元放,到现代鲁迅、范烟桥、叶洪生乃至当代学者,关注的大都是绿林豪侠纵横天下的英雄传奇,是隶属于忠义之下的侠义主题。(17)王昕:《论〈水浒传〉的忠义冲突及近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而无论是名教中人对侠客形象的改塑,还是揄扬侠勇、赞美粗豪,处处显示着侠义精神的中衰与扭曲。
在宋元话本江湖化的侠义之外,蒲松龄将侠义主题与志怪传统结合起来,表达了无声无息的沉默的大众所想象的日常生活中的救赎与温情,为侠义人物序列增添了新质素。在《聊斋志异》的侠义故事中,行侠仗义者,是弱小的普通人或者异类。诚如墨子所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18)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8页。所谓“兼爱”,乃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对等互利的民间社会的正义观。《聊斋志异》中的布衣之侠,是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在“施”与“报”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使贫瘠困乏的生活得以延续,也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构建《聊斋志异》神异世界的根本性的情感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