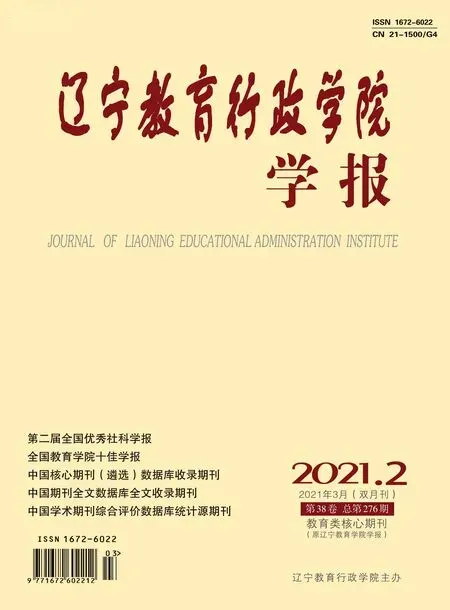论《诗经·郑风》的戏剧表现手法
——以《西厢记》为参照
2021-02-01张野
张 野
《诗经·郑风》是《诗经·国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根植于郑地民间广袤的土壤之中,体现出鲜明的平民性、世俗性、娱乐性的特点。《诗经·郑风》中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常见于后世戏剧作品当中。本文以元杂剧中代表作品《西厢记》作为主要参照依据,试从戏剧创作理论的视角,重新观照《诗经·郑风》的艺术特质。
一、俚俗诙谐的“遣词造语”
戏曲的源头之一是先秦宫廷俳优的艺术表演,滑稽诙谐的戏曲语言特征和审美风貌是对先秦以来俳优语言的继承和发展。元人胡祇遹在《幼龄赵文益诗·序》中提出“教坊本色”这一概念,强调戏剧应具有浅显易懂、诙谐风趣、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1]。明代剧作家和剧论家多强调戏曲的语言应来源于日常的口语当中,如徐渭虽然认为除了《琵琶记》以及《翫江楼》《江流儿》等一些“稍有可观”[2]243的南戏以外,“其余皆俚俗语也”[2]243,但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些作品,即“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2]243。可见,即使是在“崇雅”戏剧观出现以后,强调戏曲语言通俗本色的“尚俗”戏剧观依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观点之一[3]。
“俏骂之辞”的运用是“尚俗”戏剧观的常见表现手法之一。所谓“俏骂之辞”,指的是剧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某些“另类称呼”,亦即以“绰号”称之,往往具有一定的揶揄调侃之意和喜剧色彩。《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在墙角吟诗,红娘说:“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4]25“傻角”这一称呼,旧注释作“轻慧貌”,是“风流蕴藉的排调语”,实际上“傻角”就是“不懂世故的傻子,正是张生不同流俗的喜剧性格的形象概括”[5]30。这类“俏骂之辞”有时也用作爱极的反语,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生唱词:“你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4]13。“可憎才”指的是莺莺,即“讨厌的人”。金圣叹评点云:“‘可憎’者,爱极之反辞也。”[4]13反语的使用,极其传神地表现出张生对崔莺莺“亲昵和极爱的感情”[6]——“不说可爱,偏说可憎,就像称爱的人为冤家一样”[5]20。
明人凌濛初在《谭曲杂札》提出“俏语”的概念:“盖传奇初时本自教坊供应,此外止有上台勾栏,故曲白皆不为深奥。其间用诙谐曰‘俏语’,其妙出奇拗曰‘俊语’。自成一家言,谓之‘本色’,使上而御前、下而愚民,取其一听而无不了然快意。”[2]259“俏语”即指戏剧语言呈现出“滑稽诙谐”的整体艺术特征和审美风貌。上文所举的《西厢记》中的“俏骂之辞”便属于典型的“俏语”。根植于民间的《诗经·郑风》,同样具有鲜明的平民性、世俗性、娱乐性特征。试看《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7]207-208。
李山认为该诗当为“男女相会时节女子对男子的俏骂之辞”[7]208,诗歌先以高大的扶苏、乔松,色彩艳丽的荷花和红蓼作为起兴,奠定了全诗奔放而烂漫的基调。《毛传》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8]言外之意是女子感叹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本想遇到如“子都”“子充”一般的美男子,不料竟遇到疯狂愚笨的家伙。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且当为伹字之省借,……狂且,谓狂行拙钝之人。”[9]方玉润《诗经原始》:“狡童,狡狯小儿也。”[10]214可见“狂且”“狡童”都非什么好话。但细读本诗便可察觉,诗歌并非真的是说该女子厌恶所谓的“狂且”“狡童”,而是对中意自己的男子的揶揄之语,是佯装嗔怒,实则爱慕的打情骂俏之辞。由此可见,朱熹在《诗集传》中斥之为“淫女戏其所私者”[11],虽然带有一定封建卫道士的偏见,但相较《毛诗序》解诗而言,还是触及到了诗歌本义。而清人崔述在《读风偶识》中称本诗实为“男女媟洽之词”[12]240,对诗旨的把握可谓十分精到了。再看《诗经·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7]211-212
李山认为,本诗“应该是溱洧河畔男女相会打情骂俏的风情诗”[7]212。此诗风格明快,程俊英在《诗经注析》中说本诗“每章前四句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活脱一个泼辣女子的声口,读来如见其人。末句忽然放慢声调,以戏谑的口吻作结。寓反抗于嘲讽之中,完全是一种优胜者的姿态,……”[12]245诗中女子因为嗔怒而骂男子为“狂童”,泼辣且果决,同为典型的“俏骂之辞”。又如《诗经·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7]210。
“闻一多《风诗类钞》将《狡童》一诗归入‘女词’,解曰‘恨不见答也。’”[12]241诗中女子因不得中意的男子而颇有怨怼之意:“那个坏小子啊,你不与我一起说话、吃饭,都是因为你的原因,我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虽是牢骚语,但仍然以戏谑的口吻发之,泼辣明快的风格溢于言表。
《诗经·郑风》对“俏骂之辞”的使用,于嬉笑怒骂之中凸显了俗文学所独有的诙谐俚俗的色彩。
二、复杂激烈的“心理冲突”
日本学者河竹登志夫在《戏剧概论》中认为:“‘劇’这个字眼是由‘虎’‘豕’及表示利器的‘刂’复合而成的,表示两匹猛兽或猛兽那样凶猛的对立双方龇牙格斗的情景。即相继表现出人类同其他事物——命运、神灵、境遇、社会邪恶势力、他者、潜藏在自身之中相反的特性等——的矛盾和对立,一面相互交锋,一面不断地产生出种种行动,直至到达结局。”[13]6剧本的二重性使然,不仅要求剧本具有“文学性”,还要求具有“戏剧性”。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戏剧就被限制在不大的舞台空间,一出戏只许演出三四个小时,……正由于有这类制约,剧作家才不得不加以提炼,把含量极大的‘戏剧因素’浓缩在那个狭小的时空之中,使其朝着在高温中熊熊燃烧的方向前进。”[13]68为了达到必要的表演效果,必然要求剧本的创作凝练而概括,同时迅速而集中地表现出矛盾与冲突,以唤起观众的审美注意力。由此可以说,“没有集中的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这已成为一条公认的定理。”[14]
中国戏剧当中,心理冲突是矛盾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与西方戏剧截然不同。王立言在《西厢记选译》的前言中认为:“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它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曲词继承诗词传统,不求每字每句与生活中的‘形似’,而要求‘神似’,贵在构成意境。在《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共有十九个唱段,但真正是舞台上对话的很少,大多是写她的心理活动,以曲词写心理唱给广大观众听,演给广大观众看。虽然把莺莺心中的隐秘宣泄无遗,但莺莺仍不失其温柔矜持的外貌。如不少唱段,若当作话剧台词说出,那莺莺便不成为莺莺了。中国戏曲是透过演员的主观世界,表现客观世界的。”[6]
《西厢记》中,崔莺莺“自见了张君瑞神魂荡漾,心情不快,茶饭少进,已是非常感伤,况且又恰恰逢暮春天气,真让人烦恼。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4]36爱情在心中悄悄地生根发芽,她对母亲平日的管教亦愈发不满起来,“老夫人拘系得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4]38。当张生献计挽救了崔莺莺一家以后,她对张生的感情又进了一步。然而,当崔老夫人赖婚以后,她内心之中又表现出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愈发思念张生,埋怨“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地,虚名儿误赚了我”[4]60;另一方面,又“畏我父母”“畏人之多言”——“怕人家调犯,早共晚夫人见些破绽,你我何安”[4]81。所以当见到张生的简帖时,却又莫名地发起脾气来,声称看望张生只是“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4]81;她约张生到花园相会,但见面后又责问张生:“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4]96可以说,《西厢记》正是通过她内心“追求爱情”和“恪守礼教”的冲突与矛盾,揭示了她青春的觉醒,对爱情的追求,以及成为封建礼教叛逆者的过程。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的恋爱的经过与他们的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15]这种“婉曲的细腻”的“恋爱心境”的描写,早已见于《诗经·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也[7]189-190。(第二三段相似,略)
该诗生动地展现出主人公思想上的一波三折,而《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思想冲突的刻画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歌是女子以拒绝的口吻写给心上人的诗篇,诗中巧妙地表达了恋爱少女曲婉而复杂的心态。女主人公拒绝男子逾墙攀树来相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集中表现出女主内心复杂的矛盾冲突。诚如程俊英分析的这样:“首句‘将仲子兮’,一声呼告,十分亲密,已透露出那姑娘爱仲子的心情。后两句‘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是要求仲子不要再来会面。然而这不是无情的拒绝,她心里还是爱仲子的,虽然回绝了仲子,却又恐怕他误解,所以急急乎解释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解释了还嫌不足,她索性袒露了自己的心迹,‘仲可怀也’,然而她又摄于家庭和舆论的压力,因为‘父母之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至此,整个心事和盘托出,希冀求得情人的谅解。短短八句,一波三折,曲尽女子爱和畏的矛盾心理。姚际恒在‘岂敢爱之’和‘仲可怀也’二句下分别评以一个‘宕’字,点出了诗人婉委曲折心理的微妙。”[12]222
概言之,复杂激烈的“心理冲突”是《诗经·郑风》的又一个戏剧表现手法。后世包括戏剧在内的叙事性作品中,常常以人物心理活动的展开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烘托气氛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可见,《诗经·郑风》对人物幽微细腻的心理冲突的把握和描摹,无疑标志着文学自身演进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三、以对话推动“情节发展”
《西厢记》中“惊艳”“寺警”“赖婚”“赖简”“拷艳”等主要事件构成了剧中波澜起伏的艺术情节。戏剧学中,“情节”一词通常是与“故事”相对举的一个概念。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我们已经给故事下过了定义:对一系列按时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情节同样是对桩桩事件的一种叙述,不过重点放在了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是个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死于心碎’就是个情节了。时间的顺序仍然保留,可是已经被因果关系盖了过去。”[16]按照这一定义,则情节是由因果关系串联的多个事件的总和。考察《诗经·郑风》某些诗歌作品,其描述的事件与事件之间已经初步具备了这种“因果关系”——或者说,《诗经·郑风》中的一些诗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情节。更为难得的是,后来戏剧作品往往与这些诗歌类似,都是以语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不难发现,《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该诗可看作由三个不同的“事件”构成,即“催起猎雁”“烹雁设酒”“赠物示爱”;其次,该诗的三个“事件”按照一定因果逻辑关系相连结,彼此并非孤立,由此可以说,三个事件串联构成了该诗的“情节”;最后,“情节”的发展是由人物的语言推动的。如诗歌开篇,通过男女的对话,将“女子催促男子起床”和“男子赖床不起”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出来。从戏剧视角观之,整首诗无一不是“剧”中人物的对话。又如《诗经·郑风·溱洧》第一章: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
士 曰:“既且。”(女 曰:)“且 往 观乎?”[7]224
当女子邀请男子同去河边时,男子竟然不解风情地说他已经去过了,女子不肯罢休,坚持要求男子陪她再去一遍。以对话上的冲突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将男子的憨直和女子的坚持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自然而富有生活气息,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爱情作为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在不同时空背景之下均具有某种内在的共通性。《西厢记》中的一些唱白受《诗经·郑风》中关于恋爱心理的某些细腻幽微的表达之影响痕迹明显。如《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隔墙联吟”的桥段:
(张生:)“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莺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4]25
二人虽然只一墙之隔,但是于彼此而言却可望而不可即,当真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而《诗经·郑风》之中早已有极其相似的场景,请看《诗经·郑风·东门之墠》:
(男曰:)“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女曰:)“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7]215
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就首章节而观,曰室迩人远者,男求女之词也。就次章而论,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以诗中自为赠答。”[10]219诗歌前后两章,可看作戏剧中某种特定情景之下,男女间互表思慕之情的唱词。“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同样表达出相隔不远,但却未能与所爱之人相恋的期盼又惆怅、热烈又焦灼的恋爱心理。两相对比不难发现,《诗经·郑风·东门之墠》实可作为戏剧中一段表白心迹、推动情节发展的“唱词”。
又如《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送别”一段,面对莺莺“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的叮嘱,张生“忍泪佯低面,含情假放眉”[4]133,恰好可用《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中“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7]220-221作为注脚。《诗经·郑风·风雨》中“即见君子,云胡不喜。”[7]216写的是妻子与丈夫久别重逢的表白之辞,而《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崔张二人团圆之际,崔莺莺的唱词:“不见时准备千言万语,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觎。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则道个‘先生万福’。”[4]163恰似此诗。
显然,《诗经·郑风》中以语言来推动情节发展的艺术手法,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四、独具匠心的“剧本体制”
元杂剧通常是一本四折。有学者认为,元杂剧中常见的四折结构,是受到中国古代诗文创造中讲究“起、承、转、合”的影响而形成的,“元杂剧剧本之所以由四个部分组成,正是因为它用以概括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发展过程,从开头、小高潮、大高潮直到结尾。”[17]如此看来,则唐代律诗分为“首、颔、颈、尾”四联,应是元杂剧中“四折结构”最为明显的来源。而中国古代诗歌的发轫之作《诗经》,已初步显示出这种情节上“起、承、转、合”的布局安排了。现将《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的三章按照剧本的形式加以重新排列:
第一折 催起猎雁
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
(女曰:)“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第二折 烹雁设酒
(女曰:)“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合唱:)“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第三折 赠物示爱
(女曰:)“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如此,则整首诗歌便可看作是由男女之间对话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戏剧作品。诗歌开篇仅通过寥寥数字,便将“女子催促起床猎雁”和“男子的赖床”的冲突推向极致,极具戏剧中的某种喜剧色彩,男女的幸福生活已经初步表现出来(此为第一折)。诗歌这种体裁囿于篇幅,无法像小说一样进行细致的铺展,因此务求凝练,这种要求与剧本创作本是相通的。第一幕结束以后,将“男子最终起床猎雁”这一不能直接反映男女恋爱的场景移至幕后,直接切换到猎雁后女子将雁烹制成佳肴的场景,男女之间琴瑟相谐的美满生活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此为第二折)。通过前两个场景的铺垫,女子的爱慕之言已然呼之欲出。最后一折,通过截取“女子将搜集来的玉石制成饰物赠与男子”这一场景,将彼此深厚的爱慕之情推向高潮。
剧本是一种侧重以人物台词为手段,集中反映矛盾冲突的文学体裁,由于其体裁的特殊性和舞台的表演性质,因此应具有一些基本要求。一是对现实的反映具有高度的浓缩性。这是出于舞台表演的实践和空间的限制。二是集中地表现矛盾冲突。作为一种舞台艺术,为了唤起观众的审美注意力,必然要求达到尖锐、剧烈的程度。三是“人物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展示。”[18]由此可见,尽管不具备舞台提示等常见的剧本组成要素,但仅从剧本的三个基本要求来看,《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实可看作一部原始的戏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