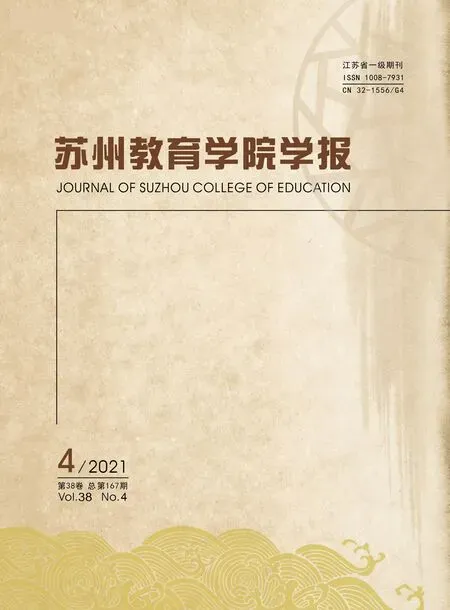从“天问”到“心问”—论小海对传统诗歌精神的再发现与重启
2021-01-31罗小凤
罗小凤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小海虽为第三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但他并未如第三代诗人般秉持解构传统的写作立场,而是一直保持着与传统的密切关联。尤其近年来,他返身古典诗歌传统,重新发现了古典诗歌传统中的“天问”精神。不唯如此,他还在诗歌创作中发出历史之问和“心问”,以此叩问历史、探寻自我并思考人之存在,形成对“天问”精神的重启。
一、“天问”精神的再发现
小海在分析杜涯的诗歌时认为其“质朴、典雅、宏阔,有国士之风”[1]88,可见,小海在杜涯的诗歌中发现了古代文人所崇尚的“国士之风”。所谓“国士之风”中的“国士”乃指国内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国士之风”则指国士的作风或风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便有“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2]之语,用以赞美人才难得。古代常以是否有“国士之风”评判人品,小海用之评论杜涯之诗,无疑是对古代“国士之风”的认同。小海还颇为认同古代“士”的精神,曾撰文《史的传统与士的精神—兼评简雄〈浮世的晚风〉》专门研究“士的精神”。[3]在不少评论中,小海亦善于引入这种“士的精神”来阐释诗歌,如他在评论韩东新世纪以来的诗《扫墓兼带郊游》《冬至节》《天气真好》时援引曹操《短歌行》和苏轼《前赤壁赋》中的诗句作为参照,认为可从韩诗中读出“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的喟叹和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前赤壁赋》)的旷达”[4],曹操对于人生、生命的感叹和苏轼的旷达无疑都是小海在古代诗人身上所找到的传统诗歌精神。
虽然小海在其文中对何为“国士之风”一直语焉不详,未曾作出细致明确的界定,但他阐释杜涯的诗主要是从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角度展开的,认为杜涯是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温新古典主义的艺术之梦”,从诗歌主题、风骨和精神等层面可看出其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是中国古典诗歌,其抒情诗“与《诗经》以降的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一脉相承”。[1]88可见小海对杜涯的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重视。而更为关键的是,小海在对杜涯诗歌的具体阐释中,他将杜涯写山川、草木、村落等题材的诗视为“《国风》中《召南》《卫风》的现代版”,而认为“另一些抒写个人爱情、命运、时序推演的哀怨诗章”则可以“追溯到屈子《天问》、蔡文姬《悲愤诗》、杜工部《旅夜书怀》《秋兴》,以及李清照南渡后的词风那里,何其相似,可谓入其堂奥,是接续传统诗歌精神的写作”。[1]90虽然小海对这种传统诗歌精神未作具体明确的进一步阐述,但由他所追溯并参照的这些诗词便不难推知其主要指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对于杜涯诗中的自问、追问、反问、诘问等各种形式的发问,小海则追溯至屈原在《天问》中的发问传统,他指出:“从屈原的《天问》用振聋发聩的一百七十三个发问开始,就已经将可贵的质疑精神引入了中国诗歌。”[1]92并引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苏轼《临江仙》等诗中的发问进行论证:“这种种发问,携带着古风古意”,由此他发现杜涯“将传统的、屈原式的从人世法则回到自然法则的天问,融汇到她的现实世界和诗歌天地中”,呈现出小海对传统诗歌中的质疑精神、天问精神的认同与欣赏。[1]92因此,笔者认为,小海话语中的“国士之风”实指一种囊括了担当、质疑等内涵的传统诗歌精神,是小海对传统诗歌精神的重新发现。
在这些传统诗歌精神中,小海最为激赏的无疑是“天问精神”,这种精神源自屈原的《天问》[5]。在《天问》这首370多句、1500多字的诗中,屈原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涵盖天地万物,涉及自然、社会、神话、传说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屈原对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的求知欲及存在的困惑、怀疑和探索精神,由此形成“天问精神”,其所指涉的是一种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得到后世不少诗人—如曹植、杜甫、柳宗元、苏东坡、辛弃疾等—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一种可贵的传统诗歌精神,是传统文化和古典诗学传统的重要内容。
二、历史之问:“天问”精神的现代回响
小海颇认同“天问”精神、质疑精神,这不仅构成了他评判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尺度,他还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如《大秦帝国》[6]、《影子之歌》[7]等诗中发出历史之问,构成其“天问”精神的现代回响。
小海的《大秦帝国》面世后,不少评论认为《大秦帝国》是对历史进行重构与还原,但事实上,小海的创作意图并不在此,而是以“历史”为基石发出历史之问,提出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帝国”、帝国为什么坍塌、人民的命运如何等系列问题,这也是一种“天问”,小海所问的“天”是“大秦帝国”及其历史,无疑是对传统诗歌精神,尤其是质疑精神的延续。这种质疑精神是一种屈原式的“天问”“发问”精神,是对权威、主流的质疑,也是一种在野的民间姿态,与小海作为第三代诗人成员所秉持的“民间”姿态具有一致性,亦是小海为自己的“民间”姿态从古典诗歌传统中寻找的合法性依据。
海马曾敏锐地意识到小海“根本无心去完整叙述这段历史”,“更不是为了站在历史的废墟前,发一回感慨”,但他认为小海“试图重新还原历史”,同时也是对历史进行“重构或再造”。[8]窃以为此观点有偏颇之处。小海在《大秦帝国》中并不是对大秦帝国那段历史进行缅怀,亦不是要还原历史或重构历史,而是借这段历史发出自己内心的“天问”,小海想如屈原一样对历史进行“天问”式的发问,因此他在诗中不仅写了赢政、李斯、赵高、吕不韦、赵姬等帝王将相,还写了荆轲、陈胜、吴广、孟姜女等人物以及那些无名者。诗中最打动人的不是秦始皇的诞生,亦非秦国将士的英勇善战,而是秦国底层民众的悲苦,小海勾画了大秦帝国的辉煌,但随后在《咸阳宫的骊歌》中呈现了大秦帝国坍塌的原因在于秦王专制暴政、权欲、情欲和宫廷争斗。《帝国回音壁》中的各种“歌”与“吟唱”之诗都形成对历史的“天问”。小海仿佛化身大秦帝国时代的一个人,在回音壁面前叩问大秦帝国何以会坍塌。在《秦俑颂》等作品中发出历史之问,“明月,你说出的秘密/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身世”[6]45,透露出小海在《大秦帝国》中所追问的华夏民族的精神秘密,所谓的“秘密”正是风骨、担当等华夏民族的传统精神。
小海创作《大秦帝国》之时也恰是2009年11月至该年年底的《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热播之际。《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是根据孙皓晖于2008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分为《大秦帝国之裂变》《大秦帝国之纵横》《大秦帝国之崛起》《大秦帝国之天下》四部。作者孙皓晖在其小说《大秦帝国》自序中指出:“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9]由此,不难见出孙皓晖对于大秦帝国的情有独钟。因此,这套书及据此拍摄的电视剧都对大秦帝国持歌颂褒扬的姿态,呈现了大秦帝国如何于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在列强环伺之下崛起,并扫六合而一统天下,从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的悲壮历程,小说和电视剧都重构了一个大秦帝国形象,并试图还原其辉煌历史。小海或许受到电视剧热播的影响而关注“大秦帝国”,然而小海的态度却与孙皓晖迥然有别,他虽亦以此为题,诗中却主要对“大秦帝国”进行解构和反讽,正如小海在《大秦帝国》的《序诗》中所写的:“战争,七国的霸业;地球,太阳烤箱里的一块香面馍。”[6]2将地球比喻成“太阳烤箱里的一块香面馍”,“七国的霸业”所寓之讽意就更加不言自明了。他看到的不是大秦帝国的辉煌霸业,而是大秦帝国坍塌的悲剧,在他看来,即使是大秦帝国,即使是地球,都不过如烤箱中的一块香面馍。因此,小海并未去还原历史或重构历史,事实上任何还原和重构都只是“拼贴”,无法真正还原或重构历史本身,故而小海在其诗中所做的不过是捡起历史废墟上的一些碎片叩问历史。曾一果曾指出,小海是要通过《大秦帝国》去探索“宏大历史背后,探索神话、巫术和传说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一个看似毫无缝隙的庞大帝国为何瞬间就土崩瓦解?固若金汤的帝国为何会出现一道道致命的‘裂缝’?”[10]显然,曾一果的发现是敏锐的,或许这正是小海创作《大秦帝国》的初衷,亦是这部诗剧的历史意义所在。这是小海发出的历史之问,是永恒之问。小海对于霸权持解构态度,他更关注普通人,如陈胜、吴广、孟姜女、皮影艺人、无名小卒,这些人物既是构成帝国的基座,亦是瓦解帝国的“裂缝”所在。小海在诗中揭露出暴政、权欲、情欲和普通人的悲苦正是导致帝国瓦解的“裂缝”,他在诗中写道:“‘我很好!’荆轲说/我就是秦帝国天空中的第一道裂纹/为什么好?在我之后/高渐离将会为我高歌一曲/后世必将失传的《广陵散》……”[6]78在小海笔下,“帝国永远在颁布法令/帝国永远在说‘今天’/可每一天都在被划掉/当我说今天将讨伐赵国时/昨天的桑田已灌浆成熟/当我向明日的楚国下达战书时/昨天的三闾大夫已自沉汨罗江”[6]5。可见,小海的着力点不在于呈现帝国的辉煌,而是呈现其专制、暴政与霸权。对此,小海在《大秦帝国》自序中有所透露,他在简要介绍大秦帝国在政治、经济、法制、建筑等各方面的举措及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影响后,笔锋一转,用一个“所幸的是”指出“大秦帝国延续几千年的所谓先进政治制度、政治设计已成行尸走肉,所迎来的只是其逐渐冷却的过程”。[6]序言可见小海对大秦帝国主要持否定、解构姿态,其聚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大秦帝国的“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上。因此,虽然小海的《大秦帝国》被不少学者阐释为关于大秦帝国的史诗,而窃以为其实质是对“大秦帝国”形象的解构。在《大秦帝国》中,小海对于大秦帝国不是还原与重构历史,而是根据自己的志趣和喜好选取一些历史的碎片,以此为基点追问历史,质疑权力、专制、爱欲等。他重构大秦帝国形象是为了将其解构得更为彻底,从而揭示其轰然坍塌的残酷性,这是小海发出的历史之问,是其质疑精神的典型体现。
正是由于秉持质疑精神,小海对于大秦帝国以及嬴政、赵姬、李斯、吕不韦、嫪毐、赵高等帝王将相的态度一直是带着嘲讽、解构的。如嬴政是“有的人即便到老/都会有啃食手指和脚趾的习惯”[6]17;对赵姬则用“真是见鬼”“爱欲,也是我个人神圣的仪式/不可剥夺啊”[5]54,对她爱欲上瘾而将爱欲变成信仰的丑陋行为进行嘲讽;嫪毐是“为秦帝国营造了那么多新坟”[6]55,对吕不韦、李斯、赵高的咏唱都充满嘲讽,所谓“咏唱”都不是歌颂帝国辉煌,而属于一种正话反说。如《蜂的咏唱》中 “战争、暴行、劳作/富贵、体面、优雅/蛮荒之国也是真与善的国度/耻辱说:我们应当懂得生活”[6]24,显然是以“咏唱”之名直接揭露帝国之恶。《咸阳宫的合唱》中将咸阳宫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四个声部的咏唱中所透露的是历史的无情和苍凉之感,小海用一句“神像腾出它的位置/麻雀们可以吃早饭了/啾啾声响彻云霄之上”[6]27对咸阳宫见证的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进行了彻底解构。这种解构正是小海质疑精神的体现和天问精神的现代回响。此外,小海在《大秦帝国》中突出了荆轲的英雄形象和孟姜女的凄苦境况,究其因由,关键在于荆轲刺秦王和孟姜女哭长城均可视为人民对苛政的一种反抗或控诉,小海借此表达了对大秦帝国的控诉。因此,小海的《大秦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对电视剧《大秦帝国》的反讽,是一种质疑精神、国士风骨的体现。
三、“心问”:自我存在之思
小海获得“2012年度天问诗人奖”时,唐晓渡在颁奖词中将小海早期的诗歌写作视为“地问”,即“谦卑地叩问土地”;而将《影子之歌》视为“心问”,即“沉思地逼问自心”。[11]唐晓渡敏锐地发现了小海诗歌创作路向的转变。确实,新世纪以来,小海已从他前期的“乡村”“田园”书写所发出的“地问”转向“心问”。李文娟亦发现小海是个“勇于发问”的诗人,认为他常“自我发问、自我思考,并以诗的语言叙述出来”[12]。小海不仅逼问自心,更是对自我的存在之问,通过心问抵达自我之问和存在之问,均是质疑精神的体现,属于小海从古典诗歌传统中重启的“天问”精神之一。
小海的《影子之歌》是对古代诗歌中“影”意象的重启。小海曾坦言其对“影子”意象的着迷和喜爱最初乃源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李白的《月下独酌》,他指出:“诗中时空穿越折射出的空灵哲思也如透明的影子王国,神话般美妙,让我迷惑又迷恋。”[7]1此言道出了小海对于影子的着迷。在古代诗歌中,“影”是重要意象,不仅有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13],苏轼的“起舞弄清影”(《水调歌头》)[14],张先则因经常写影入诗词而被称为“张三影”,曾写下“隔墙送过秋千影”[15]等诗句。“影”既指光线直射或反射而形成的虚像,亦被赋予孤独寂寥等隐喻内涵。“影”作为实体的对应物,属于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虚像”。小海将其作为诗歌的母题,赋予其“文化的毒性、地下的起义和反叛的图式”与“差异性、创伤、权力意志甚至阶级分化”的意涵[6]2,但事实上,小海笔下的“影子”已构成人的另一种存在,小海的“影子之歌”是为了追问人存在的意义,属于自我之问,即唐晓渡所言的“心问”。在《影子之歌》的开篇第一节,小海便对“影子”作了一个诗性界定:“影子在向地下生长/影子是附着于我们身上的祖先/影子是肉身的盔甲……”[7]3实际上是对影子所存在的意义及其与肉身的关系、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思考。小海对影子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诗中将影子视为“我们有形的养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凸显了影子的重要性;小海意识到影子“既无名姓,也无面孔/像无声的节拍/追击着歌声”[7]14,并认为“影子需要被当作一件乐器来对待/影子需要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乐队来对待/影子需要被当作壮阔宏大的细节来对待”[7]14,是对影子属性的深刻认识;小海还发现影子对于人的特别意义:“影子意味着来世/意味着丢失/变化和无常”,“影子常常一分为二,/影子是一种实际发生的世界”,“影子改造肉体和世界/完成我们的使命”。[6]204由此可见,小海笔下的“影子”并非仅仅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虚像”,实际上已被小海视为人的另一种存在,视为物质世界中现实存在的一种可以替代人去完成使命的特殊存在。不仅如此,小海还意识到影子对于人的支配作用:“影子把我变成我们,/影子把他们变成我们。/影子还原我们”,“影子伸手一指/人直接变成了猎物/飞奔的猎物/又在瞬间成为烤肉”。[7]214可见在小海眼中,影子不是人的附属体,而是掌握着人的支配主权,显然是小海对“影子”这一意象的独特发现。古代诗歌中的“影”只是作为一个抒情支点,用以支撑诗人想要抒发的情感或思绪,而小海笔下的“影”已作为人的另一种存在成为诗的主体,无疑是小海对人之存在的本体思考。
在《大秦帝国》中,小海亦有对人之存在的思考,他并不着力于塑造大秦帝国的辉煌形象,而是要探寻帝国形象背后人的存在意义,思考个体存在对于大秦帝国的意义。他那句“地球,太阳烤箱里的一块香面馍”,不仅看到了大秦帝国的悲剧,还意识到在浩瀚宇宙中,地球不过是太阳烤箱里的一块香面馍,而人的存在则更像一块香面馍,呈现出人类的卑微,是他对人的存在之思。小海在对大秦帝国坍塌的思考中突出呈现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如《工匠的咏唱》中呈现了工匠们的生存环境是异常艰苦的:“炎热的工地”,“巨石阵上有捕食的野兽”,“黎明时睡去的奴隶/脑袋开裂,爬满蚊蝇”;[6]22他在《秦俑复活》中不是着力于塑造秦俑形象,而是刺秦王的荆轲,将个体存在与大国辉煌对比映衬,他认为历史最后留下的只是孟姜女、《吕氏春秋》、荆轲等个体存在的印记。在第二章《将士一去不复返》中小海不是歌颂将士们的英勇善战精神,而是思考这些将士在无休止的战争中遭受的命运:“死亡是我终生的学业”,“从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讲/我们只是搬运一小撮泥土而已”,“我们知道死亡才是故乡”,[6]13-14可见小海对于将士命运的感叹与悲戚。尤其是小海在结尾插入两个插曲,即《插曲·战后的皮影艺人》和《插曲·孩子们的合唱》,更是感叹将士命运如皮影艺人手中的皮影,被人摆弄:“带上那一具具头颅/一只只手臂/一条条断腿”,“摆动他们的手臂双腿/让他们回到戏剧深处”。[6]15-16这无疑是对战争中牺牲的人的一种隐喻,同时,是对帝国辉煌的一种抨击、质疑和解构,而通过“孩子们的合唱”,更增加了悲剧性。在诗中,小海一直在思考“我是谁”的终极命题。这是一个关涉人之存在的话题,如在《术士的咏唱》中他发出疑问:“你是谁,谁是我,谁是谁……”[6]23这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人的存在之问;而《陈胜、吴广的咏唱》中则以“我们来,我们走,本该如此”[6]25对人的存在进行思考;在《众将士的吟唱》中小海则不无悲凉地感慨:“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证明/他们像动物在大地上驰骋/他们是没有记录也不存在的人/他们生来就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的历史只有神话可以追溯”[6]32,显然是对战争中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与思考。因此,历史只是小海发出历史之问、存在之问的支点。
小海善于在诗中发出人的存在之问,对此他曾自陈:“我的写作本身,就是寻求另一种存在,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可能性的努力”,“对自己的不断反省,以及对个人身处其间的现实生活所保持的一种当下的领悟与觉知”。[16]小海在他的诗中总对人的来去存在发出追问与思考。
小海还喜欢对人的命运进行思考与追问,这是他对人的存在之思的延伸。如他在《士卒的吟唱》中发出命运之问:“谁在高空/摆布我们的命运……”[6]32在《稻草人之歌》中则用“皮影”和“稻草人”将人受摆弄、无法自我控制的命运呈现出来,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人就像稻草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人最后都像“回音”,“只活在空中,无脚”。[5]115这属于典型的命运之思。《大秦帝国》《大秦帝国人物志》《古今人物志》等篇章更多指向的是人,这也是终极指向。小海认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大秦帝国辉煌时代的人都不过是烟尘,留下的只是碎片。[6]2他即使在思考大秦帝国何以坍塌时,也在思考相对于历史,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他在对大秦帝国兴衰历史的重新审视中思考的是人的命运。对此,李德武指出:“不是试图为一个消失的帝国招魂,他是想通过对历史的反观呼唤并发现人性的光辉,复苏并延传民族的气脉。”[17]李德武注意到小海在《将士一去不复还》中隐喻了士兵如皮影一样被操纵。确实,小海所质疑的是人的命运。李德武还由此看到了小海的人性悲悯和历史情怀:“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之后,长盛不衰的竟然是一部《吕氏春秋》,竟是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竟是墓葬礼被埋藏千年的陶俑。”[17]因此,小海在诗中所要着重塑造的不是秦始皇的帝王形象,也不是秦俑形象,而是荆轲、孟姜女及底层劳动人民等所代表的个体存在。小海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他认为是荆轲那种,而不是秦始皇那种。历史留下的是什么?他认为是孟姜女,是荆轲刺秦王,是《吕氏春秋》,事实上这都是在对人存在的意义进行追问,亦属于人的存在之思。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历史之问,还是探寻自我、思考人之存在的“心问”,小海的终极追问在于“本真”,如他在《秦俑颂》中所言的“从咸阳宫里苦苦寻觅战争的本真”[6]45。他在《大秦帝国》中探寻战争的本真意义何在,在发出系列历史之问和人的存在之问后,呈现出华夏民族的精神,这便是小海所探寻的“本真”。如《秦俑颂》颂的不是秦始皇墓里的秦俑,而将目光投注于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儿女身上,借“秦俑”歌颂华夏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他们是坚不可摧的/就像黄河上的波浪”[6]46,这种精神正是小海所追寻的“本真”。而《秦俑复活》所呈现的是小海对一种真正英雄的渴慕与敬仰,他在此诗中所塑造的复活的“秦俑”是一个只身刺杀帝王的刺客形象,对此李德武指出,所谓“秦俑复活”,“复活的不是征服者骨子里的贪婪和残忍,而是人性中不畏强权的忠肝义胆,是不惧生死的大义凛然,是勇担大任的豪侠与壮烈”[17]。确实,小海对复活的秦俑和“刺客”形象的塑造事实上是对不甘屈辱选择反抗的精神的认同,这种精神是小海所探寻的一种“本真”,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传统之一。正如曾一果指出的:“《大秦帝国》不是一部大秦帝国的史诗,而是一部华夏民族的史诗。”[18]确实,小海在其诗中所着力呈现的正是华夏民族自屈原“天问”精神以来的一种精神传统,正是这种精神传统,使小海的诗具有不同凡响的深度、厚度与高度,既形成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亦建构出其诗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