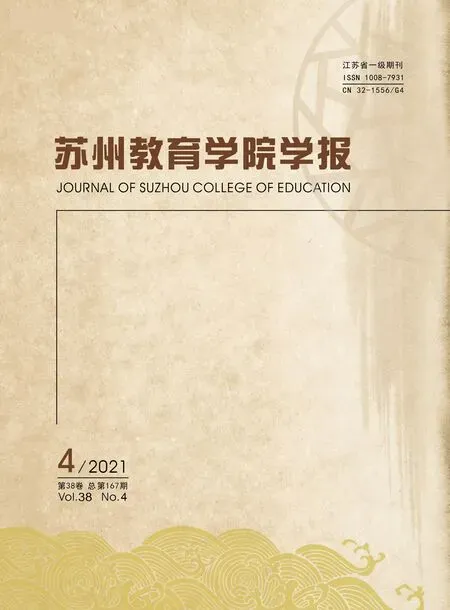小海与新时期江苏诗歌
2021-01-31罗振亚
罗振亚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谈论小海与新时期江苏诗歌这个话题,并非想象的那么轻松。一方面江苏乃中国新诗重镇,数度引发人们的关注,这里走出的卞之琳、辛笛、杭约赫、唐祈等大师曾经领衔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1930年代,程千帆、沈祖棻、吴奔星、孙望等的新古典主义尝试,促成了南京与上海、北京在诗坛的三足鼎立;1980年代,“他们”诗派靠语言和生命意识的双重自觉,进入了“第三代诗”的最前列;进入21世纪,阵营愈加壮观,个体间姚黄魏紫,“和平共处”,众语喧哗,也就是说,新诗的每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江苏诗人的介入。另一方面,作为诗坛三十多年的“长跑者”,小海经历了第三代诗、中年写作、个人化等浪潮的流变与冲击,同时,小海本人又善于自省,不断在“常”中求“变”,探索诗歌存在的诸种可能性,他有过乡土雕塑,还有过经验书写,更有过长诗探险,风格多元,不易把握。尤其是本文题目是一个“与”字结构,小海与新时期江苏诗歌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完全重合,还是若即若离,抑或是异同均有,比较复杂。我想从三个层面接近这个话题。
首先,我想到的是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影响与塑造,也即谈谈小海诗歌和苏州诗歌、江苏诗歌同声相应的地方。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在丹纳《艺术哲学》中,论及决定文学发展的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等三要素里,地域和种族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更为内在和持久①参见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阅读小海的作品,感觉“江南”诗歌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一是以日常化方式的选择,走了一条“及物”的路线。无须多论,只要检索一下小海诗歌的题目,或是心理复杂地看孩子的《走稳了—送涂画》[1]92,或是见到精神病老人每天早晨起来找女儿所见所思的《养老院》[2]189,或是凄凉惨淡从病到死的《空巢老人之歌》[2]190-191,就会发现小海恪守了接受访谈时所说的“我不赞同技术至上”[3],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却从不炫耀充满文化的“知识气候”,对意识形态叙事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不大关注绝对、抽象之“在”,而是在“此岸”世界的抚摸中,以普通人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建构着自己的形象美学。如《谈话—送涂画》:
“要过马路,要转车
她们约好在一个便利店碰头—”
“她的同学中有那么多静
坐她前面的有张静
后排的有陈静,不扎辫子的严静—”
我摘下耳机,听两个老人谈孙女
这样细致的关怀和文雅
她们坐在对面茶室敞开的阳台上
外面是中饭前阳光下的云朵
分别叫苏苏和画画的主角
这只是小名
而不是她俩在各自学校里用的名字[2]163
诗乃具体、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里绽放的精神花朵,从二人对孙女上学路线的了如指掌,对孙女同学信息的熟悉程度和对孙女的昵称等细节中,不难体会到人间温情的淌动,那种对孙女的牵挂和爱,普遍平凡却又令人动容。即便是关注宏大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史诗型作品《大秦帝国》,仍然不忘关注“日常的、卑微的生命”[4],并且一切关于历史的洞见皆从日常卑微的生命里滋生。客观地说,1980年代后期以来诗坛上大词和圣词流行,在很多诗歌远离读者、远离生活的时候,与大量悬置生活、站在人群之上或之外写诗的诗人相比,小海是站在人群之中写诗,这种“及物”策略,仿佛每个语词都是为着当下的存在而生,无疑恢复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性。
二是精心打磨技巧,保持了文本的艺术品位。经历过“第三代诗歌”运动和“盘峰论战”,小海愈加清楚无论到什么时候,诗都是寂寞的个人化行为,在诗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所以他能够沉潜写作,从诗的活动层面回到写作自身,致力于诗歌各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也因此他的创作从不大起大落,而相对沉稳,不同时期的文本均能做到质量上乘、均齐。如《放生的鸟儿》:“放生的鸟儿/又飞回来/天暗了黑了/能说这灯光是假的吗//你们只在外面假装/呆到天黑/白天的林子呢/此刻的你们/翅膀上沾着灰尘/好像山腰/那步行者的脚。”[2]197看似只是对放生的鸟儿飞出去、再飞回来的状态恢复,实则寓意遥深,你可理解为鸟即人,鸟的状态正是人之生存情境的曲现。而“翅膀”与“脚”的链接,也可理解为对一种理想、信仰反复持续的追索,甚至它的开放性结构还可能引发更多的联想和思考。一首小诗有如此丰厚的意涵,自然源于结构感、象征意识的渗入。这种打造技巧和思想深度的纯正作风,与苏州诗歌、江苏诗歌是一致的。新时期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江苏诗人不像广东、四川包括甘肃等省诗人那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他们好像对诗歌创作和文本之外的唇舌之战、意气之争不感兴趣,而从“第三代诗歌”之后更是努力淡化流派意识,转而钟情于艺术品位的精雕细琢,所以如今在江苏虽然再也找不出“他们”那样耀眼的群落,却有胡弦、小海、李德武、庞培、黄梵、马永波、育邦等优秀个体不断涌现。
三是在风格上对苏州诗歌、江苏诗歌的整体认同。一个有趣的现象提醒人们注意,无须阅读小海的全部诗集,仅仅在他的诗集《男孩和男孩—小海诗集(1980—2012)》中,以题目方式出现的和“水”有关的就有《春雨》《河堤》《冥想—降雪》《初雪—浅浮雕》《清明上河图》《北凌河》等[2]89-180,至于以文本镶嵌的方式频繁出现的和“水”有关的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如果按照西方新批评那种“主题语象”理论,“水”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海诗歌的固定词根之一,这和江苏诗人中海的《听雨,断续对白(节选)》、张维的《雪落无声》、杨隐的《在太湖》、许强的《江水》、许军的《大泽》、柳袁照的《渡口的桃花》、老铁的《雨打在窗户上》、李德武的《夕阳与湖光》和车前子的《大运河》等①参见苏州市作家协会:《苏州诗歌选(2003—2013)》,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一道,构成了苏州乃至江苏特有的诗意取向。对“水”这种意象高频、大量的启用,即是江南地理、文化特质的自然折射,苏州、江苏平原、水乡结构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丰富悠久的文化历史,以及它们在人心理、情感中的投影、反馈、遇合,自然决定了其诗魂一直不绝如缕,并且有着水一般的浪漫、优雅、精致与灵动;同时又是偏于柔逸诗歌风格的一种凝聚和凸显,因为虽然说取境是柔是刚,是幽深还是阔达,说起来似乎只是“写什么”的题材问题,但它实际上也在制约着诗人“怎么写”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地域文化对小海的塑造可谓深入骨髓。
其次,我想说一个文学群落或者流派的形成绝非是每个个体求同的过程,正如诸多诗人和苏州、江苏诗歌之间应该成为浪花和海洋的关系一样,只有每个诗人个人化的色彩展示到位,苏州、江苏诗坛才能增加肌体活力和绚烂的美感;或者说,苏州、江苏诗歌的整体取向,也没以共性去规约每个诗人的创作自由。小海就始终以很强的方向感,秉承独立的精神立场,最大限度地拒绝外在写作风气的同化和裹挟,其创作上自觉超离苏州、江苏诗歌的个人化追求正是他在诗坛的安身立命之本。表现有三:
一是小海出道起点很高,但他不喜欢重复自己,所以三十余年从没躺在功劳簿上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地左冲右突,找寻诗歌的艺术可能性,进行自我超越,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诗歌本体观念的内涵和疆域。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小海经历了从《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北凌河》到《大秦帝国》《影子之歌》《男孩和男孩》的变化②参见小海:《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村庄与田园—小海和他的诗歌》,惠特曼出版社2006年出版;《北凌河》,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出版;《大秦帝国》,文汇出版社2010年出版;《影子之歌》,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其实这种变化不只是从乡土到历史、自我表现到客观呈现的位移和转换,其背后更有对诗歌本体的多方探寻。如果说早期的《咖啡馆》《搭车》等[2]8-11诗中不乏情绪的舞蹈,但它们对咖啡馆的位置、形状、招待员的理想和美丽母亲,对“我”和搭车来看“我”的非诗人交流的情境的观照,已经让位于普通生活场景、细节的瞬间捕捉和自动敞开,絮絮叨叨的调式和平庸、琐屑的生命本质达成了同构,零散又温馨;而只有五行的《蜜蜂》:“蜜蜂又出现了/河谷知道/这不是同一只蜜蜂//而春风中的油菜花不知道/野荠花也不知道”[2]198,和长诗《影子之歌》里,内世界观照中理性思考已占较大比重,前者对时空相对关系的辩证把握,后者对“人和影子”随时可以转换的哲学抽象,几近人类经验和智性看法的揭示,感悟和思考的融入,似乎已使诗歌变成了一种心物契合的情感哲学,至于像《有赠》这样的诗歌:“一列火车孤零零/跑出山,却没有铁轨/这是一所房子的葬礼/一群天堂的孩子/梦中下山找司机/我要开着这列火车/去华沙,去西藏/弹琴唱歌,在你醒来前/把你放下/没有铁轨,把你放在我/枕头般的灰烬上。”[2]188因为梦、潜意识的未知视域的涉入,恐怕已经进入思维的博弈层面,内涵艰涩得无法确定当然也就无法避免了。在小海诗歌的多元探索面前,诗是情感流露或生活表现的传统本体观念似乎已经逐渐被击破,在他的诗里,诗有时可能是生活和情感回味的一种经验,有时甚至是思维透明或晦涩的展开。
二是自觉克服新诗的文体局限,通过“反诗”的方式处理诗和叙述的关系,为日常诗意的表达找到了更为切近的理想状态。我曾多次提及诗和其他文体的比较,新诗的优长明显,但缺点也不容忽视,它对“此在”经验的占有、对复杂事体的处理能力等方面,绝对逊色于其他文类,新诗如想继续发展就只能吸收叙事文体的长处,以缓解自身文体的压力。对这一点很多诗人有所察觉,只是小海克服新诗弊端的意识来得更早,更自觉。早在“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那些创作中,他就不满于直抒胸臆的浪漫气息,有意识地避开朦胧诗依仗的意象、象征艺术,而讲究事态的呈现,让对话、场景、细节、人物等叙事因子纷纷进入诗的抒情空间,到后来更加注意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的能量,把叙述作为改变、维系诗和世界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如《周末》即将诗化的抒情让位于事态的流动,“楼下有人叫你/大门上有人留言/孤独的周末/阿山走了/开始的那辆车停在窗前/一只网球拍遮住了山口百惠的脸/留学生从后门溜上了大街/三下唿哨/像跟人约定的暗号/似乎又回到夜晚/黑暗中人人凝重而忧郁……”[2]53,诗中没有寂寞无聊的感情抒发,甚至也没有直接表达痛苦意向的字句,就是车、楼下、唿哨等稀疏的意象存在,似乎已引不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而网球拍遮住山口百惠的脸的具事,留学生从后门溜上大街的动作细节和“舞会结束了/大厅里只有一只脑袋还架在大腿上”等“事态”或行为事象,却成了结构诗歌的主角,由此,诗获得了一定的叙事长度和过程。长诗《大秦帝国》更尝试将诗、歌剧和史诗等多种形式汇通,将散文式的哲学话语与简练抽象的诗歌语言组合,复现宏阔的历史场景。当然,小海诗歌整个抒情空间的细节或事件的铺展中仍渗透着诗人的情感与思考,其叙述仍是一种情绪叙述、诗性叙述,这种叙事化探索、拓展了诗的生长空间,也表现出小海介入、把握、处理复杂生活的能力之强。
三是为诗坛提供了沉静、睿智而自然的个人化风格。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若想在文坛立足,必须提供一种特殊的个性品质,具有鲜明的风格辨识度。小海在暗合苏州、江苏诗歌潮流的写作过程中,更清楚诗歌创作乃是高度个人化的精神作业,所以作为一个纯粹、独立的南方诗人个体精神存在,其诗蕴含着至柔的水性,表现出精巧、飘逸之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要有自己个性追求的“太阳”,属于自己的创作路线,以体验、体验转化方式和话语方式上的殊异性在题材、情感与风格方面烙印上个人化的痕迹。事实上,他诗里机智的情思经验、偏于客观的呈现方式和质感自然的话语感觉,的确为诗坛输送了一种新的品质。他的《老家,老家》《偷钓》《北凌河》[1]66-86等系列村庄建构,就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精神意义,他对乡村世界执着抚摸的诗性情怀,在1990年代乃至当下的很多人看来是背时的,但我以为那恰是他的价值所在,他守住了现代异化社会里的精神清洁,其宁静、恬淡、本色与沉稳,对诗界也不无启迪。至于《大秦帝国》《影子之歌》等长诗,那种包容、大气、高远,则昭示出一个精神个体的多面性和高贵厚重的品质,这对中年写作至关重要。
最后,我还想说小海的确像一些人所说的,其偏于内向性的优雅写作旨趣,异于“功夫在诗外”的低调沉静的写作姿态,与居于苏州的非中心写作地带这几点聚合,造成了诗坛对小海诗歌价值和意义的低估、小视。其实,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小海诗歌的启示都将逐渐超越其自身,并且其价值将客观地回复到应有的文学史地位的序列之中。
一是小海对“他们”诗派的开拓之功与具体贡献将会被人们郑重地记取,并被文学史重新书写。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文学史对一个优秀作家或诗人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滞后现象。速荣者亦容易速朽,那些时过境迁即被淘汰的文本绝对构不成真正意义的经典;那些拉开时空乃至心理距离后还能被人记起的,才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存在。说到小海诗歌,1998年5月发生的一个文学事件应该注意,那就是小海与杨克编选的《他们:〈他们〉十年诗歌选(1986—1996)》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如果说,杨克是因其连续数年编辑《中国诗歌年鉴》获得编选资格,而小海则因其是跨越“他们”诗派整个历史过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并且成绩突出,才成为诗选编选的合适人选。经过三十多年的淘洗和沉淀,历史证明在旌旗招展、宣言大于文本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最终能够在诗坛留下痕迹的恐怕只有“他们”诗派、非非主义诗群和莽汉主义诗群。而小海非但是内部交流刊物《他们》的创始人,还是坚持最久的卓尔不群的写作者,其“在寂寞中倾听自己的声音比无所适从去应和更加接近诗”①参见苏野:《苏野专访小海:诗歌寂寞的力量》,《华东旅游报》2006年1月5日。的意识和实践,与韩东要摆脱文化动物、政治动物、历史动物等三种世俗角色的主张就完全不同,这也造就了小海诗歌独特的个性风貌,使他的诗歌内涵越到流派发展的后期越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流派的影响。相信随着历史的深度打开和渐次细化,小海诗歌必然会冲破“他们”诗派中于坚、韩东两位领袖人物光辉的遮蔽,在当代诗歌的历史脉络中显露出自身的魅力。
二是小海和诗坛保持“距离”的沉潜态度,安静写诗,是对诗坛喧嚣的抗衡和比照,对诗歌写作者充满着启示作用。小海曾说:“‘九叶诗派’的陈敬容先生在我少年时代曾跟我说过,要和自己的同代人、甚至和自己的写作都要保持一点距离。”[5]在小海的诗歌创作中,很难具体辨析陈敬容的艺术与思想影响痕迹,但是其“保持距离”的忠告,却始终敦促着小海时时葆有一种精神独立的清醒,心气平和,自觉淡化“第三代诗歌”的群体意识和运动情结,而敛心静气地探索如何提升诗歌的艺术品位,如何进行诗歌本体的打磨和完善,所以这些年小海很少加入诗坛的各种民间组织,在各种热闹的诗歌会议上基本见不到他的身影,更不愿别人将流派、群落的标签贴在他身上。甚至1990年代后他还有意识地做和文学“场”保持距离的半隐逸者,所以在新世纪接二连三的诗歌“事件”中,他非但做“缺席”者,甚至对时尚和流行的写作风气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从没有搞过带有轰动性的大动作、大举措,只是静默地为诗坛输送品质优良的文本。置身于当下活动大于文本、活动多于文本的诗歌时代,人们肯定会从他这种沉潜的风度中参悟出一些重要的东西。
三是小海在处理诗歌的内与外、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注意。不知从何时开始,诗人的地位和诗歌一起在贬值,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诗人是精神病,是疯子。这种贬损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却道出了诗人的精神结构中有许多病态因子的事实。实际上这和当年指认徐志摩过分诗化生活、顾城是孤僻自恋的抑郁症、海子精神分裂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很多诗人的精神是有问题的。而小海却完全不是这样,作为诗人,他在创作上可谓风生水起,小高潮不断;作为公务员,他的工作有条不紊,有声有色,不但本职的分内之事做得很好,而且写了大量推介、宣传苏州诗歌、文学与文化的文章,个中意义自不待言。记得苏州大学文学院徐国源教授说过:“小海是最不像诗人的一个真诗人。”[6]不愧为知音之论。在诗歌仍处于边缘化的今天,一个诗人太像诗人是可疑的,至少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诗人。从这个向度来说,小海是诗坛上平衡诗与生活的典范,他也许并不自知中的生活与写作态度,对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内在统一、对日常生活和写作活动的有效调配、对诗人角色和普通人身份的合理对接,均值得人们耐心揣摩,甚至从中借鉴一些因子,至少它恢复了社会上对诗人形象的正常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