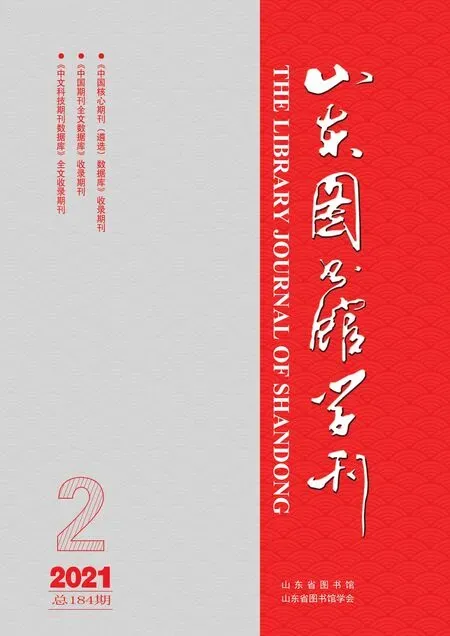从《汉书艺文志举例》的得失论史志目录的体例
2021-01-30马庆辉王承略
马庆辉 王承略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其自诞生起便广为关注。而有关《汉书·艺文志》[1](以下简称“《汉志》”)的研究文献更是为数甚多,细究起来,这些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考察《汉志》内容的,如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与《汉书艺文志拾补》、姚明辉的《汉书艺文志注解》、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通释》等;另一类则是主要考察《汉志》体例的,如孙德谦的《汉书艺文志举例》、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释例》等。相较而言,研究《汉志》体例的专著较少,而单独成篇的文章虽多,却比较零碎化,不能系统全面地阐述《汉志》的体例。鉴于此,本文拟从孙德谦的《汉书艺文志举例》出发,对《汉志》的体例进行重新思考与整合,希望能够为书目编纂与目录学史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与方法上的参考。
孙德谦所撰《汉书艺文志举例》(以下简称“《汉志举例》”)是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汉志》体例的专著,其归纳《汉志》体例为46例,可谓详尽至极。张尔田为《汉书艺文志举例》作序云:“班《志》之例定,而后族史之得失定,即一省、一府、一县征文考献之书,亦莫不定。”[2]5其言可谓一语道明了《汉志》体例研究的重要性。《汉志》开创了“艺文”入史的先例,其编撰方法与体例亦为后世所袭,影响极大,而解决《汉志》的体例问题无疑可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古典目录对《汉志》的继承与发展,亦可为现代目录编纂工作提供更为明晰的方法与范例。孙德谦的《汉志举例》无疑导夫先路,尽管对《汉志》体例的归纳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瑕不掩瑜,《汉志举例》仍是我们研究《汉志》体例所绕不开的著作。《汉志举例》自撰成距今已近百年,但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而目前所能找到的有关孙德谦《汉志举例》的研究文献甚至屈指可数,显然,《汉志举例》的学术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1 《汉书艺文志举例》研究现状
《汉志举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前辈学者还是做出了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他们或揭示《汉志举例》存在的问题,或考察《汉志举例》的编撰过程,或对《汉志举例》作出更为合理的改造,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在《汉志举例》撰成之后,雁晴曾写过《汉书艺文志举例(书评)》一书,主要指出了《汉志举例》存在的一些弊病,他认为古书举例工作要达到“古人虽不必有此意,以此释之亦不为诬妄古人”[3]66的境界,切忌“穿凿”“附会”“牵强”“偏颇”等。雁晴在书评中将《汉志举例》存在的弊病归纳为矛盾例、偏执例、歧讹例、游移例、冗赘例、名误例、证乖例等七例。其中,矛盾例指孙氏所举二例相互龃龉,彼此矛盾之处,比如第六条为“一类中分子目例”,而第七条又列为“分类不尽立子目例”。偏执例指只就一方立例,如雁晴所举第三十七条“记书中起讫例”,实际上除《世本》外,其他如《春秋》《国语》《国策》皆未记书中起讫。歧讹例指出了孙氏举例中的界限不明、分类混乱的问题,如第二十三条“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例”,其中孙德谦对于“学派”的划分便含糊不清,不能令人信服。第四例为游移例,即不确定之例,如第三十条“互著例”,对于《汉志》是否存在互著例历来众说纷纭,对此将在下文着重讨论。雁晴所举第五例为冗赘例,这是针对本来不须立例而强为立例而言的,而这也是我们在归纳古书体例中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例”,怎样划分“例”,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思考的。第六例为名误例,指出了孙氏举例中例名的性质舛错与例名不可通之处,如“称等例”“称各例”等,其实此例与冗赘例相似,均是探讨孙氏举例中不成例之例,涉及到了“例”的标准问题。最后一例为证乖例,一方面指举例之证与例不合,雁晴称之为“失例”,另一方面指孙氏对于恰当之证遗而不举,即孙氏“失证”之处。此外,除了指出孙氏举例存在的问题,雁晴还给出了改造《汉志举例》的注意事项,如在“形式”方面,各例要以类相从,在“名称”方面,例的名称须清晰,切忌标准歧异等,但是他没有对《汉志举例》进行具体的改造,可谓遗憾。
张舜徽苦于《汉志举例》杂沓繁冗而多有疏漏,于是“取《汉志》重加温绎,融会勾稽,得三十事,区以五门写定”[4]173,著成《汉书艺文志释例》(下文简称“《汉志释例》”)一书。《汉志释例》将《汉志》体例分为五类,分别为甄审第一、著录第二、叙次第三、标题第四、注记第五。其中,甄审第一包括不录见存人书例、不录祖先书例、未成之书依类著录例、《七略》类例不明者重为厘定例、书名下不录解题例等五例。著录第二包括彼此互著例、单篇别行例、数书合列例、每类之末用总结例、每略之尾用总论例等五例。叙次第三包括依时代先后例、帝王著作各冠当代之首例、以类相从例、每类中分标子目例、钞纂之书各归本类例、于叙次中寓微旨例等六例。标题第四包括经典不标作者主名例、姓字上署职官例、书出于众手者署名例、书名从后人所定者标题例等四例。注记第五则包括标注书中大旨例、标注书中篇章例、标注作者姓名例、标注作者行事例、标注作者时世例一、标注作者时世例二、人名易混者加注例、书名易混者加注例、书系依托者加注例、疑不能明者加注例等十例。以上是张舜徽《汉志释例》所举之例与基本分类情况,而将其与孙德谦《汉志举例》相比,不难发现前者实际上是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两者既不乏共通之处,而又各具特色。张舜徽以《汉志举例》为参考,虽继承了《汉志举例》的部分说法,但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甄审第一所举之例,多为孙德谦所不及。就分类而言,《汉志释例》更是一改孙氏举例的杂沓与冗赘,更为简明系统。《汉志释例》对于《汉志举例》的改造与创新,颇有可借鉴与学习之处,但其本身亦非尽善尽美,如其所举互著例与单篇别行例,几乎是沿袭孙氏的说法,而这两者仍是存在争议的问题。胡楚生曾撰《张氏〈汉书艺文志释例〉商榷》[5]一文,探讨了张舜徽《汉志释例》的诸多问题,可供参考。
除上述专著,还有几篇关于《汉志举例》的文章值得关注。柯平曾撰《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6]一文,在文章中,柯平首先简要介绍了孙德谦其人与著述成果,接着论述了孙德谦的目录学指导思想、目录学研究以及目录学思想。在关于《汉志举例》的叙述中,柯平认为《汉志举例》在分类、提要、收录范围、排列等方面对《汉志》作了详细的研究,认为《汉志举例》能够为目录学提供工作方法的参考,颇有见地。需要注意的是,《汉志》本身是没有提要的,此乃可商之处。
其次,杜志勇对孙德谦的《汉志举例》亦颇多研究,其撰有《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7]、《〈汉书艺文志举例〉与〈汉志艺文略〉的关系》[8]两篇文章。在《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一文中,杜志勇对《汉志举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不同于以往《汉志》研究中所采用的的随文注解形式,而是专门划分为46例来探讨《汉志》体例特点,对《汉志》体例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称其为“《汉书·艺文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体例的专著”。他对《汉志举例》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汉志举例》宗主“史志”,体现为简要有法以及但挈大旨、别论异同;二是彰明《汉志》,独尊班固,体现为凸显《汉志》体例以及对班固的推崇;三是垂范后世,即孙德谦编撰《汉志举例》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研究,而是为后人编纂目录提供示范与参考。在第二篇文章中,杜志勇指出,《汉志艺文略》乃是《汉志举例》的原稿,而他对于这两部书的比较无疑可为我们了解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形成过程提供依据和参考。
此外,傅荣贤对《汉志举例》的研究亦不能为我们所忽视,其撰有《孙德谦〈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9]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傅荣贤首先对《汉志举例》和《刘向校雠学纂微》这两部著述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指出了《汉志举例》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孙德谦一味高标班固、分类混乱等。但他同时也对《汉志举例》的思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进一步肯定了《汉志举例》的学术价值。
以上主要介绍了前辈学者对于《汉志举例》的研究成果,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汉志举例》存在的问题,也能看到学者对其进行的改造,但其中仍存在不少争议之处,亟待解决。
2 《汉志举例》存在的问题
孙德谦《汉志举例》旨在探讨《汉志》的体例,为后人修撰史志、编纂目录提供范例,即王国维所谓“示后人以史法者”,其本身不乏创新与令人称道之处,如“称省例”“称出入例”等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王国维赞叹曰:“其中‘称出入’‘称省’二例,乃洞见刘《略》与班《志》之异同,自来读《汉志》者,均未颂言及此。”[10]60虽然《汉志举例》在《汉志》的体例总结上具有独树一帜的开创性意义,但对于其存在的客观问题,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
首先,探讨古书体例贵在简练有法,孙氏所举之例分为46条,实在是过于繁冗杂沓,混乱无章,并多有矛盾之处。比如,单是分类例,孙氏便举有“一类中分子目例”“分类中不尽立子目例”“分别标题例”“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例”“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例”等五例,其中,“一类中分子目例”与“分类不尽立子目例”还相互龃龉,如果前者成立,则“不尽立子目例”单独列出就在无形中抵消了前例,而实际上孙氏在“不尽立子目例”所举《诗赋略》的分类问题本身便是存在争议的。傅荣贤在《孙德谦〈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一文中认为孙氏所举条目之间并非杂乱无章、一盘散沙,而是有一条理论总纲统摄,即《汉志》区别于藏书家和读书家的目录而必须接受《汉书》作为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整体规范[9]。窃以为傅荣贤所言有理,孙氏举例中往往对此有所透露,但这并非他举例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不能掩盖《汉志举例》本身冗杂的事实。
其次,孙德谦所举之例有不少所谓不成例之例,比如第一条“所据书不用条注例”,班固在序中既已说明《汉志》是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自然不必再作标注,并且班固对于自己所修改之处都已标出,如果再特意注明何为刘歆所作,岂不过于繁琐。当然,从当今学术规范的角度,对他人成果的引用是一定要注释标明的,但不必以此去评判古人。再如“称等例”“称各例”“称所续例”三例,亦是不能成例的。“称等例”指省略著者名字,若一部书为多人所撰,则不必一一列出,可用“等”来省略。“称各例”指一人之书而卷数相同者,可并列合言,如“《章句》施、孟、梁邱各二篇”。我认为,言“各”言“等”当属于用语习惯问题,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往往也这么用,而将其归纳为体例似乎不妥,对此,杜志勇在《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一文中亦持同样观点,可备参考。而“称所续例”中“所续”二字本就属于书名,孙氏所举此例亦不足以单独成例。其他诸如“称并时例”“书有别名称一曰例”“此书与彼书同称相似例”“书中篇章须注明例”等等皆属于注释的范畴,单独成例未免繁琐,不如将这样的相近之例合并为“注释例”。孙德谦所举其他体例亦可如此进行归纳整理,一来可摆脱杂乱拖沓之弊病,二来更为简练有法,容易为人理解接受。
此外,对于《汉志》是否有“互著”“别裁”二例,历来颇多争议,孙德谦认为《汉志》既有互著,又有别裁之例。孙德谦云:“今考之班《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鬻子》,兵家亦有《力牧》《孙子》……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此其重复互见。”[11]42张舜徽在《汉志释例》中亦持相同的观点,由于其书在《汉志举例》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我认为张氏之说大概是直接承自孙氏。雁晴在《汉书艺文志举例(书评)》中则将互著例列入游移例,而胡楚生在《张氏〈汉书艺文志释例〉商榷》中更是直接持反对的观点,窃亦认为《汉志》中“互著”“别裁”二例缺乏确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何为互著例。互著例最早为章学诚提出,所谓“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12]15,即同一著作可归于不同类者,可分别著录而不避重复,这样可称之为“互著”。因此,如果不同类所著之书不是同一著作,那么便不能称之为互著了,而孙德谦所举恰恰不能断定是否为同一书。《汉志》所载之书,大部分是以著者之名作为书名,比如《孟子》即为孟子及弟子所作,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汉志》不同类中的书若书名相同,则可能为同一作者所著,但并不能因此断定就是同一部书。此外,孙氏所举之书在卷数上亦有出入,比如儒家《孟子》有十一篇,兵家《孟子》则仅有一篇,再如儒家《景子》仅有三篇,兵家《景子》却有十三篇,而其他同名之书卷数也大都不同,因此孙氏所举之书虽同名,实则并不能断定为一书。而事实上,章学诚自己也认为《汉志》中并无互著之例。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列举了《七略》中十家“一书两载”的例子,认为此是“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但是“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12]17可见,章学诚认为刘歆《七略》中本存互著之例,但是班固删除重复之后所撰《汉志》就不存在互著了。而对于这一点,孙德谦则有相同的看法,其言:“盖如《伊尹》《太公》诸书,本重列兵家,今为班氏省去之。或谓自班氏删并刘《略》,后人遂不知有互著之法,其说是矣。”在后文中,孙氏又言“班氏虽于六略中,以其分析太甚或有称省者,然于诸家之学术兼通,仍不废互著之例。若是编艺文者,苟知一人所著书可互载他类,则宜率而行之矣。”[11]42班固删除不同部次中的重复之书,即是客观上否认了互著之例,孙德谦此言强为之说,既与事实不合,而又与章学诚所言互著之本意相去甚远。由上可知,言《汉志》存“互著”之例是不能成立的。王重民在《校雠通义通解》一书中,认为“互著法”在汉代尚未被发现,而刘向父子所作乃是著录现实藏书的藏书目录,更不容易使用互著法,并进而认为互著法“暂可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滥觞,到祁承爜才纯熟的使用,到章学诚才提到一个较高的理论程度。”[12]20王重民此说可备参考。
章学诚所谓“裁篇”,指将一书中可自为一类的篇目单独裁出归于另一门类,即其所言“其所採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12]24孙德谦承章氏之说,认为《汉志》自有裁篇别出之例。如《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汉志》于礼家则载有《中庸说》二篇;又如《弟子职》今在《管子》一书中,而《汉志》则载《弟子职》于孝经家;再如《孔子三朝记》今属于《大戴礼》中的一篇,《汉志》则于论语家载《孔子三朝》七篇。张舜徽《汉志释例》承孙氏之说,亦认为《汉志》中有裁篇之例,而胡楚生《张氏〈汉书艺文志释例〉商榷》则坚决表明《汉志》中不存“裁篇”之说。首先,胡楚生认为《中庸说》并非《中庸》,而是关于《中庸》的训诂解释之作,对此,王鸣盛在《蛾术编·说录》中也认为《中庸说》乃是《中庸》之解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亦以为《中庸说》乃是解说《中庸》之书,而非《中庸》本篇。并且按章学诚所言,《中庸说》若属于裁篇,当不会与《礼记》著录于同类之下,可见这并不符合裁篇之例。此外,据胡楚生考证,《孔子三朝记》及《弟子职》等,本是先有单行之本流传于世,后来编《大戴礼》《管子》时才分别并入其中。如《三国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13]580再如王先谦《汉书补注》在“艺文志”《弟子职》一书下引沈钦韩云:“今为《管子》第五十五篇,郑《曲礼注》引之,盖汉时单行。”[14]2942胡氏所考,窃以为可信,而《汉志》中无裁篇之例亦可由此而证实。
以上简要说明了《汉志举例》的弊病以及颇具争议之例,而对于孙氏具体论述中的一些不当细节则没有展开论述。推其弊病之缘由,主要在于孙德谦对于《汉志》“体例”的确立缺乏一个明晰的标准,见一处文字便立一例,难免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再者,孙德谦对班固推崇太过,多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孙氏《汉志举例》并非尽善尽美,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其存在的问题,以免踏入误区。
3 从《汉志举例》总结史志目录的体例
对孙德谦《汉志举例》的思考,不能止步于探究其存在的问题,还应当针对其问题进行整合与改造。对此,张舜徽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所撰《汉志释例》即是改造《汉志举例》的成果。虽然张氏《汉志释例》颇有见地,但其沿袭孙氏之处亦不在少数,无形间也难免继承了《汉志举例》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我们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志举例》重新进行归纳改造,希望能更清晰明了地揭示《汉志》的体例,能够切实为书目编纂工作提供范例和参考。
孙德谦《汉志举例》共举46例,除去不成例之例,我们认为可将其合并归纳为六例,分别为著录例、序言例、分类例、编次例、注释例、增删例。如孙氏所举,书为后人编定者可并载例、书名与篇数可从后人所定著录例、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例、书名上署职官例、自著书不列入例、书名省称例、篇卷并列例、用总结例等可归为著录例。辨章得失见后论例、每类后用总论例等可归为序言例。分别标题例、一类中分子目例、分类不尽立子目例、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例等可合并为分类例。前后序次不拘例可归为编次例。一书下挈大旨例、称并时例、称所加例、书有别名称一曰例、此书与彼书同称相似例、尊师承例、重家学例、书有传例、书无撰人定名可言似例、书中篇章须注明例、书有图者须注出例、引古人称说以见重例、引或说以存疑例、其书后出言依托例、不知作者例、不知何世例、传言例、记书中起讫例、一人事略先后不复注例、书缺标注例、人名易混者加注例等二十一例可归纳为注释例,并且可细分为关于著作本身的注释和关于著者的注释。再如删要例、称出入例、称省例可归为增删例。除此以外,本文还增加了依据例。现将七例分别论述如下:
3.1 依据例
所谓依据例,指史志目录的编纂并非凭空而出,而是以官修目录或私家目录作为参考依据。班固所撰《汉志》即是依据刘歆《七略》撰成,“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3由此可见,《汉志》乃是删减《七略》而成,并且保留了《七略》的基本书籍和分类体系,《七略》虽已亡佚,从《汉志》中我们仍可看到其大体面貌。
自《汉志》开创纪传体史书“艺文志”体例,后世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比如唐有《隋书·经籍志》,五代有《旧唐书·经籍志》,宋有《新唐书·艺文志》,元有《宋史·艺文志》等等,而它们的编订亦是以官修目录或私家目录作参考依据。比如《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唐时国家藏书目录,并参考它以前的有关私家目录书编成的,其序言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15]7可见其编纂既受到了《汉志》的影响,又曾参考王俭的《七志》以及阮孝绪的《七录》。再如《旧唐书·经籍志》是刘昫依据毋煚的《古今书录》撰成,而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艺文志》更是兼采众书,据马楠《〈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艺文志〉的三种文献来源》[16]可知,《新唐书·艺文志》的编撰不仅参考了《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和《旧唐书·经籍志》等书目,还包括了《崇文总目》以及史传所载,其文献依据甚为丰富。
由上可知,史志目录的编纂必当有所依据,或官修目录,或私家目录,或兼而有之。既然历代编纂史志目录必有依据,故今归纳为依据例。
3.2 著录例
著录例主要是就图书著录的内容和形式而言的,包括书名、卷数、篇数、著者等。首先,《汉志》著录图书大多数只著录图书的书名以及篇卷数,其形式一般为“书名+篇数”或“书名+卷数”,如《六艺略》中书类,便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欧阳说义二篇”两种不同的著录形式。究其原因,其中“篇”“卷”的区别大概在于图书的载体不同,言“卷”者其载体一般为竹简,言“篇”者其载体则为帛。由于汉代以前的著作多以作者之名为书名,所以著者之名在书名中往往会有所体现,如“服氏二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等等。但也有一些条目是专门的“著者+书名+篇/卷数”的著录形式,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许商五行传记一篇”等等。而班固在注释中也偶尔会注释著者之名,比如“易传周氏二篇”之后便有“字王孙也”的注释。不过,我们认为注释之中的姓名应属于注释的内容,当不在著录例的讨论范围之内。其次,《汉志》所载图书有少数会同时著录作者职位与姓名,比如《六艺略》儒家类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道家类有“郎中婴齐十二篇”等。此外,孙德谦《汉志举例》中有一例为“用总结例”,指《汉志》于每一类后,必书若干家、若干篇,如在书类之后又“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在《六艺略》末尾有“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当归于著录例。
除了以上所举著录内容和形式,窃认为著录例还应当包括著录范围,即史志目录的收书范围。《汉志》删自《七略》,创立了以记“一代所藏”为主要特点的正史艺文志的体例,并且为《隋书·经籍志》所继承,之后的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皆沿用此法。但自《明史·艺文志》开始,正史艺文志的记载方式有了变化,仅录有明“一代所著”,《清史稿·艺文志》亦沿其例,仅收录清人著述。我们以为,史志目录记载“一代所藏”,抑或“一代所著”,固然有学术文献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编制目录时一定要明确收书范围,建立明确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执行。
3.3 序言例
所谓序言例是就《汉志》的大小序而言的,《汉志》开头有总序,各略之后有大序,除《诗赋略》外,每略之中各类之后又有小序。《汉志》的总序介绍了汉代之前的学术源流以及汉兴以来对典籍的收藏与整理状况,从中我们可大体了解到先秦到汉代的学术发展状况以及汉代所做的文献整理工作。《汉志》的大小序主要论述本类的学术大旨,介绍历代学术源流和演变以及师说授受之情状,从中我们可辨别先秦至汉代学术的源流派别,明确学术的传承关系,考证学术渊源与得失,彰显学术史的发展轨迹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主要就是通过大小序来实现的。如《六艺略》中诗家类的小序既论述了《诗》的功用以及编订情况,“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1]7又简要介绍了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基本情况及授受源流状况,“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1]7
对于《诗赋略》为什么只有大序而无小序这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其观点大体有二,一是《七略》中本有小序,但是为班固所删,我们觉得此说并不成立,其他五略中皆存大小序,何以单删掉《诗赋略》中的小序呢?二是认为《七略》中《诗赋略》本来便无小序,但由于《七略》早已亡佚,此说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后者较前者可信,赋体是汉代的主流文学体裁,年代较近并且为人所共知,不单独为其作小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自《隋志》以下,序言例被史志目录广泛采用。即便有的目录缺少部类之序,但总序一直是不可或缺的。
3.4 分类例
《汉志》在分类上基本继承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略,所不同的是班固删掉《七略》中原有的《辑略》,而将其内容分散到了大小序之中。而“六略”各略又各有分类。其中,《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类。《诸子略》著录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的著作,各家自成一类。《诗赋略》虽也已分类,但关于其标准历来众说纷纭,多着眼于内容与风格,不一而论。《兵书略》主要分为权谋、形式、阴阳、技巧等四类。《数术略》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类。《方技略》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四类。
《汉志》的分类沿袭了《七略》的“六分法”,之后阮孝绪《七录》所采用的“七分法”以及《隋书·经籍志》所采用的“四分法”皆是以此为基础演变而成。如“四分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相当于《六艺略》,子部相当于《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合并,集部则相当于《诗赋略》。东汉时期史书篇目较少,所以没有单独设置史书的分类,而是将其附在了《春秋》类之中。
3.5 编次例
编次例是就《汉志》的书目排列顺序而言的。首先,无论是每略的编次,还是各类的顺序,都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的。比如,在六略的顺序中,《六艺略》作为儒家经典,位居首位,《诸子略》作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紧随其后,其他《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依次展开。再如在《诸子略》中,儒家类著作亦是排在道家、法家等之前。其次,每一类中之下的具体书目排列,其顺序一般按照时代先后,先秦古籍在前,汉代著述在后,即便是伪托之作,也按所伪托之人的時代著录。如《六艺略》易家类中,丁宽传易本在服生之前,但“丁氏八篇”却在“服氏二篇”之后,此即是按照成书先后排列。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一书中亦对此有所提及,“按以传《易》先后言之,则丁宽当在服生之前,然详究类例,又似以成书先后为次,此则非见本书不能定。”[17]28此外,在各类的图书排列中,各条目往往前后相属,如易家类中,“易传周氏二篇”之后为“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氏二篇”等,后者当是相承前者,皆省略了“易传”二字。姚振宗言:“联写与分条,似乎无大出入,可以互通,而不知各有体例也。如此篇‘易传’二字,唯联写可以包下文七家之书,若改为分条,便不相属矣。”[17]7这些排列体例,在后世史志目录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兹不赘述。
张舜徽在《汉志释例》中有一例为“帝王著作各冠当代之首例”,窃以为此例有待商榷,如《诸子略》儒家类有“孝文传十一篇”,若帝王著作当冠当代之首,则“孝文传”当置于“高祖传”之后,而非陆贾、刘敬之后。再如《诗赋略》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曰:“武帝也。”如张氏所言,此赋当置于本类之前,但其在贾谊赋、司马相如赋之后,显然于例不合。
3.6 注释例
班固在《汉志》各书之后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注释,或关于著者,或关于著作,或关于师承,不一而足。如《汉志举例》中的“称所加例”“尊师承例”等,皆属于注释的内容,可将其归于注释例之中,而无单独立例之必要。就《汉志》注体而言,有注著者的,或为著者之名,或为著者之时代,或注师承及太史公有无列传等,如易家类“杨氏二篇”之下注“名何,字叔元,菑川人”,道家“文子九篇”之后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讬者也”,儒家“孟子十一篇”后注“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除了对著者的注释,还有一些是关于著作本身的,有注书之内容的,如“古五子十八篇”之后注“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有注书之篇章的,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后注“为五十七篇”,再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后注“十篇有录无书”。有注释著作之异名的,如儒家“王孙子一篇”后注“一曰《巧心》”。有注释图书之存亡的,如《六艺略》小学类中“史籀十五篇”后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有注释图书之真伪的,如《诸子略》道家类“力牧二十二篇”后注“六国时所作,讬之力牧。”有注书之附录的,如《兵书略》权谋类“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后注“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之后注“图四卷”,等等。
由上可见,《汉志》的注释内容非常丰富,虽然比较简练,但包含一些重要信息,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过程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以注释的形式对图书或作者作简要的补充说明,显然是比较灵活实用的,为后世的书目编纂家广为采用。
3.7 增删例
增删例是就《汉志》相对《七略》的改动而言的。《汉志》虽是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但并非仅仅是删节本,而是做了有意识的改造,主要表现为删改和增补两部分。
《汉志》作为《汉书》十志之一,势必要受到“史志”体裁及篇幅的限制,不能像官修目录或私家目录那样容纳更多的内容,因此删减是十分必要的,孙德谦言:“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覆推详;若史家者,其于此书之义理,祗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11]12其说甚是。首先,班固虽然基本继承了《七略》的分类体系,但是删掉了《七略》中本有的《辑略》及著录中“一切无关要义者”,需要注意的是,班固删《辑略》之名,而将其内容有所改造地分散到各类的序言中,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对此有所考证。其次,班固删除了《七略》中重复著录的图书,并用“省”字注明。如《六艺略》春秋类中“省《太史公》四篇”,所谓省即是删除之意。再如在《兵书略》之后有“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也是删除重复之意。
除了删重,班固还做了增补的工作,并重新调整了一些图书的类别,这种情况一般用“入”“出入”等字样来标明。如《六艺略》书类云:“入刘向《稽疑》一篇。”小学类云:“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诸子略》儒家类云:“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所谓“入”即是补入,将原来所缺之书进行增补或移入。“出入”则是就调整图书类别而言的,“出”乃是移出之意。如《兵书略》云:“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此即是将《司马法》从兵书类之中移出而将其移入礼类。此外,《汉志》中还有图书只有“出”的字样,而不知补入何处,不知是班固疏忽了,还是《汉书》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脱误,如《六艺略》乐类云:“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此处《琴颂》即是被移出,但未知移入何处。
《汉志》的增补体例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很有必要的,后世修撰史志目录对此亦多有借鉴,甚至还创生了正史艺文志的增补体系,如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艺文志》便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之缺漏,而刘昫所撰《旧唐书·经籍志》之所以备受诟病,就在于其完全依据《古今书录》撰成,仅著录了唐开元时的国家图书,而未曾对开元之后的图书进行增补。
4 结语
自古至今,前辈学者从未间断对于《汉志》的研究,一方面,《汉志》保存了大量的汉代以及先秦文献,是我们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所不可或缺的著作。另一方面,《汉志》开创了“史志目录”之体,开启了艺文入史的滥觞,后世史家纷纷仿效其例,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孙德谦《汉志举例》作为研究《汉志》体例的专著,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书中对于《汉志》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书目编纂的方法总结,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漠然视之。本文对《汉志举例》以及史志目录体例的探索与思考,实乃浅薄之见,惟愿抛砖引玉,大家一起致力于古典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推动古典目录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