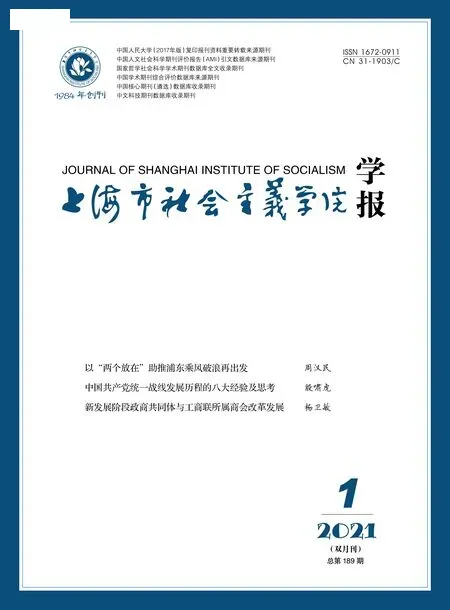海外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研究
2021-01-28龙晨
龙 晨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一、引言
(一)海外视域下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均指出,要“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华侨华人的活动一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同样,中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中国提出的各种有国际影响力的政策,也一直影响着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旨在借助辉煌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记忆,高举和平发展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华侨华人已超过6 000万人,分布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章节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桥梁纽带作用”[1]。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发展背景下,促进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党的侨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沿线国家共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理想,但却受到了一些海外学者、媒体等的污名化解读。“一带一路”与华侨华人的联系更成为了众矢之的,被当作“华人威胁论”“统战干涉论”的现实依据,从而给“一带一路”的落地和建设制造了堵点和难点。了解海外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侨务工作、如何解读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动,有助于了解海外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认知格局、关注焦点和成因。而广大华侨华人生活在海外,海外学者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研究也会影响到广大华侨华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反击一些涉及中国的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了解当地侨情及舆论状况。我国要让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也需要了解海外学者的观点。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综述海外学者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研究,为新时代侨务工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二)研究简介
从研究内容上看,由于“一带一路”提出到现在才七年,时间并不长,因此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这一议题暂时还没有在海外形成热潮,但近些年,海外有关华侨华人与中国互动的议论一直是热门话题。2018年8月24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美国安全和外国事务政策分析师亚历山大·鲍(Alexander Bowe)的调查报告《中国的统战工作——背景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指责中国通过一系列海外附属组织对海外华人个人及团体进行招揽和吸纳,通过强调“血肉”联系争取海外华人,维系他们在政治、道德、经济上对中国的支持[2]。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负责中美经济安全研究的机构审查和研究中国的统一战线,这本身就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从经济领域扩散至其他领域。2019年7月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发布现任环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其(Russell Hsiao)名为《中共在新加坡政治影响力运作的初步调查》的报告。该报告诬称中国政府在新加坡宣传“所有华人无论国籍都属于大中华圈”的观点,通过新加坡商会、宗乡会馆等四大组织要求海外华人效忠中国[3]。这两份报告在海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互动被恶意解读。此外,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成果也受到了质疑,2019年4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有多难?》一文,文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五年以来,受到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和参与,但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只有量,没有质”。
近年来,不断有海外学者关注中共的统一战线,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有:
廖建裕(Leo Suryadinata),曾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2006年接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出版中、英、印尼文著作多部,代表作有《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他是研究东南亚华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专家。
萧良其(Russell Hsiao),现任环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东京大学亚洲高等研究所访问学者。他曾在 《中国简报》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Japan》《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Singapore》),炮制针对中国政府的“侨务干涉论”,而《中国简报》则属于反共色彩的右翼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旗下[4]。他还曾于2018年4月5日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发表报告《美国的欧洲、亚太盟友与中国的关系》,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开展对台统一战线,将统战工作等同于间谍活动。
亚历山大·鲍(Alexander Bowe)是美国安全和外国事务政策分析师,他曾于2018年8月24日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国的统战工作——背景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直指诸如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绝大多数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中国组织都不可避免地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受官方指导抑或避免背离官方的方针。
华人物理学家冯达旋出生于印度,成长于新加坡,而后求学于欧美,是澳门大学对外事务办公室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助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曾多次到访中国,并积极推动中美科学和人文交流。2013年,他开始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内外发表有关“一带一路”的文章。从2016年开始,他与香港经济学家梁海明就“一带一路”做了许多调研,深度访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商界领袖、意见领袖,并在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提出善意的建议。
二、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研究
众多海外学者从华侨华人的特点、优势、作用和立场角度赞扬了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互动。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意识到仅仅依靠国家间的同盟关系是有局限性的、脆弱的,因此,为了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稳定实施,中国需要寻求建立更加持久可靠的伙伴关系。又因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关系、重同胞思想,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广泛寻求海外侨民经济和道义支持,将中国梦与华侨华人事务联系起来,使华侨华人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坚定的支持者之一[5]。
(一)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具有很大优势
华侨华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并且长期存在的侨民群体之一。其一,华侨华人在东道国的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服务业方面都有很强的优势,也与中国企业在高铁、道路、港口建设上开展广泛合作,尤其在东南亚各国,华人主宰着各个东盟国的私营部门,成为中国的重要投资者和业务中间人①。其二,华侨华人基于血缘认同,还有着其他散居于海外侨民所不具备的优势——以中国血统为支撑的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关系网络,华侨华人相互之间较为轻松地建立了认同与信任[6],加之长期积累下来的巨额资本,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华侨华人企业也有两大特点:一是比较注重由地缘和血缘等组成的关系网络,中国传统观念里认为非正式的、自愿的、基于地缘或血缘的信赖将会带来双赢的关系,从而有助于信用担保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华侨华人企业与其他中国企业建立跨国或区域性业务,即便有时会遇到反华情绪的冲击,但也不足以阻碍华侨华人回归本源的经济本能;二是善于通过各种关系网(如家庭、血缘、地缘)等获得中国政府信任,这种良好信赖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自身企业运营,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竞争公司难以模仿的一个特点[6]。这些特点使得海外的华侨华人企业比中国本土企业、外国企业更能够助力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海外建设。
(二)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经济繁荣和频繁的国际交流,也带来了华侨华人在东道国地位的上升。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及情感上中国同胞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之中,也在其中承担了许多独特作用。其一,华侨华人发挥的主要是商业合作上的“桥梁”作用,他们将自己定位为金融家和中间人角色[6]。其二,华侨华人还承担“公共外交官”作用,华侨华人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宣传中国制度与政策,协助提升中国国际形象[7]。
(三)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项目互惠互利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密切,极大地影响了东道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海外学者非常了解华侨华人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举出大量现实合作印证华侨华人非常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他们的主要参与方式有:对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投资,提供沿线国家信息服务、政策建议和法律咨询服务,以及沿线各国城市发展和港口基础设施开发合作。例如2017年12月,泰国最大中国商会——泰国中华总商会——计划投资100亿元,在中国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内为中国企业建造办公大楼。印度尼西亚华人陈江和(Tanoto)家族提供7亿人民币基金给“一带一路”培训和发展项目,2016年北京-陈江和(Tanoto)基金会捐赠1亿元人民币,用于在未来十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培训项目[5]。
中国政府也积极引领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建立华侨城吸引华侨华人建厂投资,组织华侨华人创建地方团体,定期举办华商会加强交流并实现协会制度化发展,等等。例如2014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引进商业和产业平台“侨梦苑”,帮助海外华人在中国开展业务,到2017年,这些平台已经分布在17个地区。2014年12月,广东省汕头市成立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属于国家级的试验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中国组织和动员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政策的主要机构之一[8]。
三、对“一带一路”动员华侨华人的研究
一些海外学者在解读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互动关系时,带有很深的误读与偏见,他们大多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认为动员华侨华人是一种对中国海外力量的再组织,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中国政府和华侨华人的合作,更倾向于认为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反而是对东道国的不忠诚。以下几种观点是比较普遍的一些观点,其中一些学者也是鼓吹“中国威胁论”“统战干涉论”的常客。
(一)所谓“合作需求说”
一部分海外学者认为华侨华人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商业合作是一种双方互利行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合作积极融入华人关系网,华侨华人企业也通过这种投资,在中国树立了企业形象,成为中国政府的牵线人,并且其中一些成果,如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设立,切实维护了华侨华人自身权益[6]。冯达旋、梁海明指出,在大多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华侨华人都占据该国经济的金字塔上层,如马来西亚年富豪榜的前10大富豪中,有8名是华人,因而不少中国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首选合作伙伴便是所在国也有丰富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华侨华人[9]。
(二)所谓“跨国主义民族政策论”
海外华人研究专家廖建裕(Leo Suryadinata)指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待华侨华人政策有了很大调整,华侨华人被认为是一种可利用资本,但他认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多民族国家内部种族冲突[10]。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侨办由中央统战部管辖更加引发了西方政府与学界的进一步批评,他们认为这将为中国国家议程提供更加协调、有组织的推动力量[11]。亚历山大·鲍认为,中国愈加重视海外华人工作,致力于通过种族、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来动员同情中共的海外华人团体,一系列中共领导下的军事和平民组织积极地加入统一战线,其中一部分直接归统战部领导,一部分归政协领导[2]。美国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11月发布了题为《锋利的权力:不断增进的威权主义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绝大部分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中国组织都不可避免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和党的目标,它们要么遵从官方或非官方的指导方针,要么避免背离中共的方针或国家的目标。”这些观点完全忽视了“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及人民带来的共同利益,单单聚焦于中国的侨务工作,抹黑中国政府与华侨华人的公开、正常往来,鼓吹华侨华人的不“忠诚”。实际上,反华仇华情绪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思想土壤,更多是所在国的别有用心人士鼓吹“华人威胁论”所致,单论中国政府与华侨华人的合作导致反华难以成立。
(三)所谓“治外法权论”
美特·图恩(Mette Thunø)教授认为将全球散居华人联结为一种复杂互惠关系网络的战略规划打破了以往领土、主权、人口和政治权威的一致性原则,属于国家空间的重新配置,也是在不放弃国家主权情况下获得治外法权的一种尝试[7]。亚历山大·鲍认为,在澳大利亚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影响华裔澳洲人社区,一些在澳大利亚有影响力的华人同样担任统战部下属海外机构的会长,并试图影响政治[2]。独立分析师和统一战线专家Jichang Lulu认为,对新西兰的统战是统一战线“统治”中国侨民的成功典范[2]。这种观点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忽视华侨华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将一些富裕的华侨华人的立场与中国的互动解读为已“忠诚”于中国、背叛本国的表现,夸张中国的战略影响,并试图为反华言论造势。
(四)所谓“人口扩张论”
部分别有用心人士将华侨华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迁移解读为中国人口扩张论。例如在西方媒体的恶意扭曲下,不少哈萨克斯坦学者都相信,鼓励中国人向哈国迁移是中国政府解决国内人口过剩的一种手段,还认为中国人以低价收购的形式从哈国掠夺了大量战略资源[12]。东英格兰大学地理学和国际发展领域高级讲师拉娅·玛塔拉克(Raya Muttarak)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沿线国家的人口迁移流,这些迁移人口包括雇员、企业家、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东道国居民对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反应取决于中国的投资性质、东道国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华侨华人的异质性和定居模式仍旧有待关注[13]。冯达旋、梁海明借助文献分析法,研究了巴基斯坦历史最为悠久、传播广泛的《黎明报》,其中也存在少量的负面报道。例如2016年10月18日有一篇报道以“中巴经济走廊将变成下一家东印度公司”为标题,表示“从中方获得的借款将由巴基斯坦的穷人来偿还”,而中方在巴基斯坦投资的项目也仅会使中国人和巴基斯坦政府获益,而非当地社区,2017年3月2日的社论《CPEC claims and doubts》也发出了类似的质疑[14]。
(五)新型国际关系形态
在一次“一带一路”国际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推进陆、海、空、网络四位一体的流通,构建“和谐共存的大家庭”,“大家庭”的论述被部分海外学者解读为特指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合华侨华人群体在海外扩大的现象,他们认为中国正意图构造以华侨华人为中心的世界共同体理论,既往意义的国境将不复存在,国际关系也将产生新的形态设计,将产生大中国框架内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就有类似的国际法解释,如周王朝时代的国际法指城市国家和城市国家间关系、以及周王朝与城市国家的国家间关系。
四、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互动关系的研究
(一)海外恶意解读中国与华侨华人关系,激化族群冲突
“同胞情谊”是中华独有的文化产物,历史上也有华侨华人向祖国慷慨捐款捐物、投资建厂以助力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但部分海外学者对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反应激烈,出现了许多恶意解读。
其一是抹黑华侨华人立场与贡献,抹黑“同胞情谊”的情感价值。海外华人研究专家廖建裕(Leo Suryadinata)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企业中,生于东南亚的二代、三代经营者们大多不会说中文,也没有身份认同,和中国联系也比较单薄[10]。聂周斌(Ngeow Chow-Bing)与唐哲本(Tan Chee-Beng)教授在《文化纽带与国家利益——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国的崛起》一文中举出马来西亚穆斯林利用双重文化(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例子,认为如今海外华人凭借同胞之谊获得了经济利益[15]。
其二是抨击中国灌输民族主义话语,制造中国与华侨华人之间的嫌隙。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每当中国致力于海外扩展中国民族主义时,海外华人社会将会从分裂转向一体化,针对此次话题,他们认为华侨华人被分离为一个亚种族群体;更有学者讽刺性地挑出无论华侨华人多么慷慨地支持中国海外事业,都无法与本土的中国人相提并论[16]。这些话题触及华侨华人的敏感点,挑拨华侨华人与祖国的信任度,增大嫌隙,从而使得一些华侨华人迟疑或拖延参与“一带一路”,可谓其心可诛其行可鄙。
其三是将华侨华人的商业参与解读为政治含义的合作,并认为华侨华人是政治工具。海外认为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华侨华人与中国、东道国之间归属关系的变化[6]。长期从事种族和侨民政治研究的奥胡斯大学美特·图恩(Mette Thunø)教授甚至偏激地认为华侨华人是中国实现全球扩张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工具[7]。但实际上,这种指责是毫无依据的,他们无法拿出证明中国“利用”华侨华人的直接证据,也忽视了华侨华人自发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心。
其四是宣扬反华言论,危言耸听华侨华人参与中国事务将导致反华浪潮。许多海外学者在海外宣扬“华人威胁论”“统战干涉论”,使海外对华侨华人、海外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等的好感度降低,反过来鼓吹中国的侨务工作导致了反华情绪。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坚持以中国血统为基础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建立关系会加深东南亚对当地华人社区的怀疑,反过来危及中国与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17],从而劝说中国不要组织和动员华侨华人。学者阿米·弗里德曼(Amyl Freedman)通过历史研究试图说明中国政府过少的干涉有利于华裔自由生长[18]。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存在与流动反而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19],他们的理由是在很多曾经有过反华历史的土地上,如果最高领导人对华侨华人与中国交往密切的行为表示宽容,反而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可信度[20]。但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因果倒置,东南亚国家的反华浪潮归因于深厚的历史土壤和长期的偏见认知,无论中国如何地谨言慎行,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以及华侨华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威胁论”等偏激言论依旧盛行,对华侨华人的敌视也从来只增不减,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能将东南亚反华情绪高涨、民族冲突加剧归因为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行为。
(二)宣扬双方合作的局限性
一些海外学者夸大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局限性,部分学者唱衰“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发展,抹黑中国的海外项目实施能力,抹黑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实际效果,从而打击华侨华人的积极性。
其一是夸大项目合作的风险。一些人认为很多华侨华人企业很难与中国企业合作,列举了一些合作被迫中断、投资过剩的案例,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东南亚国家极度依赖对中国的贸易,一旦贸易不均衡导致两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华侨华人企业将进退两难。
其二是抹黑华侨华人的参与行为,认为仅有少量华侨华人能真正参与其中,从而降低项目的互惠互利性,也打击了华侨华人投资的热情。一是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的分布并不平衡,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数量很少,并且不富裕,也没有很高地位[6];二是华侨华人与中国政府的商业合作只涉及中小型华侨华人企业,需要大量资本和专业知识的大型项目只能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形式,华侨华人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②;三是“一带一路”更多时候是少数极富裕华商的“专利”,但他们由于政治资源和能量存在短板,只能眼看回报可观的投资项目被本土企业获得,无法“分一杯羹”[21];四是年轻一代的东南亚华裔资本家因为对中国商业和政治环境不熟悉,因而在华投资阻力较大。
其三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还不足够吸引华侨华人。学者梁海明和冯达旋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有多难?》一文说,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华商已担当“桥梁”作用,积极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向东道国介绍中国的招商引资项目;在“一带一路”提出后,仅仅多了一个由头继续充当相关角色,改变的“只有量而没有质”,目前的参与并不能够更大程度、更有效地发挥出华侨华人的作用[21]。
五、简要评析
(一)海外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研究的总体分析及特点
纵观海外学者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误读和负面言论,他们质疑中国动员华侨华人的背后动机,唱衰“一带一路”发展前景、抹黑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如华人物理学家冯达旋所述,“不是所有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而外界往往将其一概而论;‘一带一路’项目中早有不少西方跨国企业参与,而且获利颇丰”[22],最重要的是,海外并没有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反映的经济规律。
出现这些认知差异的原因,一是源于文化差异,对中国传统与思维方式不了解,无法理解根植于中华文化中的基于血缘、乡缘、地缘的同胞情谊,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团体观和家国观,更多从自由主义、利己主义视角考虑问题;二是有些学者更多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角度看待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忽视其背后的“人类
海外学者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研究动态基本与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现实过程相吻合,学者们密切关注诸如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北京华商大会、“华裔卡”等各种“一带一路”与华侨华人互动的动态,对各种数据、政策变动都十分了解。
从研究内容上看,海外学者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立场与行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侨情分析也有很确切的资料支撑,但他们更多关注华侨华人与中国政府商业合作方面,而较少关注“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
从研究对象上看,海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富裕的海外华侨华人及其二代,更多是以华侨华人企业代表、富裕华商指代所有华侨华人。对华侨华人社团、有华侨华人身份的其他从业者关注不多,对华侨华人群体的分布、分类及生存状况等具体研究也相对较少。
从研究的学术背景上看,海外学者的背景多元,他们既有国际关系学教授、政策分析师,也有人口学家、华人研究专家。这就导致了研究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侨情文献和研究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文献非常多,但却较少有学者单纯从“一带一路”政策视角解读华侨华人的参与行为。
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关注更多侧重于比较务实的行动性议题,认为“一带一路”潜力巨大,将改变国际社会的格局,而华侨华人的参与更是“画龙点睛”,必将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更上一层楼。有一些学者根据亲身经历和相关经验,客观地表达了“一带一路”与华侨华人互动存在的风险和不合理之处,这对国家的侨务工作起到了提醒的作用,也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国家政策的关注和支持。
(二)海外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研究的误读
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更多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夸大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威胁;三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一些政策分析师恶意解读中国政府的行动,炮制“华人威胁论”和“统战干涉论”。我们应根据不同情况分析误读观点的产生缘由,属于文化差异的部分,应加强对话和交流,回应他们的疑问,尽可能增加各项目合作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以辩证的思维对待不同的观点。
对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恶意解读是海外炮制“统战干涉论”“华人威胁论”的缩影。一些海外学者出于所在国的利益需要,故意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质疑华侨华人对所在国的忠诚度,他们以阴谋论的视角审视中国政府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企图将语境放入中共的海外侨务工作这一话语背景之下,将华侨华人看成中共布局海外的一颗棋子。最终,在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等反华制华浪潮面前,多数有官方背景的海外华人社团都被无根据地视为“间谍机构”,成功的华人企业家也因为与中国合作过密而被过度“消费”。这些无中生有的话语极大地影响了“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许多亚裔变成“哑裔”、避免与中国官方机构有联系。大量海外孔子学院被关停,甚至连日裔钢琴家在海外也因被认成中国人而惨遭殴打。他们鼓吹“统战干涉论”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压制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分裂中国,以加剧各国对中国政府、华侨华人甚至华裔的仇视心理,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对这些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观点,我们应该积极回应争议问题、揭示真相,加大“一带一路”建设实效和意义的海外宣传力度,占领海外舆论阵地。
(三)海外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认知的启示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项目落地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沿线国家也大多有比较强烈的合作意愿,但国际舆论对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仍旧持有较多的认知差异,这些误读与国内对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成果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也与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初衷存在较大偏差。面对这些误读与偏见,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以往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缺漏,也要更新对外宣传的工作方式方法。
首先,要以有利于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情况为优先目标,仔细研究侨务工作的方式方法。一是要优先考虑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融合程度、个人发展需求及团体利益,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华侨华人合作;二是尊重华侨华人的国际属性,研究政策与现实的结合点,构建更能适应所在国语境的话语体系,鼓励海外侨团在宣传有关中国的话语时更具灵活性;三是要探索爱国主义等能激起情感共鸣的工作方法,改善以经济利益为吸引力的单一工作方式;四是侨务工作要突出温情的软实力,探索“以小见大”的工作方针,避免过度宣扬国家硬实力;五是侨务工作要理解当地文化,以当地居民更能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
其次,以更适度、温和的工作方法开展海外侨务工作。一是更加公开、透明地开展海外侨务工作,尤其是与华侨合作的部分,遵守驻在国的法律;二是探索以商业化的方式开启海外工作,涉及互惠互利的商业合作可签订协议,扎实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的海外落地与建设,以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才”与“财”;三是海外侨务工作需要把握好度,避免过度灌输意识形态等内容。
最后,要透彻研究海外宣传工作,加强同海外的沟通与交流。冯达旋曾说道,“中国的传播界过去倾向于将国家的形象视为一个已经写作完成,只需要在海外传播中讲清楚的‘故事’”[22]。但实际上,国家政策的海外宣传不仅在于单向度的向外输出,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密切交流和互动。一方面,中国不仅要让项目走出去,也要让中国人“同胞情谊”的文化传统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研究海外、了解海外的思维方式,加强与海外学者的沟通工作,及时地对一些误读开展解释工作,并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愿景。
注释:
①例如,据有关学者统计,在中国与印尼的商业贸易中,90%的合作都有印尼华人华侨参与,广泛分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数据摘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ne-china-beijing-and-its-diaspora-opportunities-responsibilities-and-challenges.
②学者指出例如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新加坡-四川高科技创新园项目、南京生态高科技岛项目,都是中新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近期的雅加达-万隆高速列车项目也表明没有海外华人公司参与其中,项目在印尼方面的主要推动者均是爪哇人,反而持强烈保留态度的印尼交通部长是一位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