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1-01-23张金尧
张金尧 张 峥
【内容提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如何做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仍旧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既与日常生活同频共振,又伴随电子技术进步不断创新制作方式,从而成为文化之体走向致用的重要中介。本文通过对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体、相、用”的分析,进一步阐明此类节目的文化之体、中介之相、目的之用,从而在三者互相成就、制约的基础上,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获得符合时代特征的具体意义。
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数千年积淀而来的文化精魂在当代如何完成契合时代精神的书写一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影视艺术复合的连接属性使其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当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核衍生出来的电视节目已有许多。从《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到《故事里的中国》,此类文化节目之相已蔚为大观。但本应内蕴其中的文化之体是否恰切得建,体相旨归之致用又能否生出效果,这已然是关涉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艺术欣赏的重要问题。于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而言,如何真正做到“建体致用不舍相”——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电视节目中的传播效果而非空有文化之相,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一、文化类电视节目“体相用”之辨
广义的文化类节目在中国电视领域并非新鲜事物,毕竟我们对“电视散文”这一节目的记忆还不曾散去。但是近几年,文化类节目又以一种新的姿态和形式重新回到主流视线空间内,收获着众多观众的好评。借助一种更容易被当下接受的形式把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出来,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这样一个生命意味浓厚的整体而言,仅仅展现是远远不够的。在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当下的文化类节目似乎一直都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甘心做那“得意忘言”之“言”,借助节目的种种传播形式把作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传达出去,传达的过程就是节目的形式与外在逐渐消隐的过程;另一种则是把文化视为节目的众多元素之一,参与到节目创作和编排的排列组合之中,借此让节目凸显出来。很难说这两种节目创作的取向孰是孰非,毕竟二者创作的出发点本就不一致。但是,面对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问题,是时候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文化类节目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清末时候,冯桂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算得上是中国传统体用思想的延续。在这里,“体”是根本、原本,“用”是应用,二者泾渭分明,但又相互联系。具体到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中,什么才能成为立身根本的“体”?是节目,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相伴而生的中华美学精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在具体的论述中,他谈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谈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绵延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去珍视和传承。这才是文化类电视节目应当秉承的“体”。我们无需给文化类电视节目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因为观众和从业者似乎都有着难得的默契,将荧屏上一系列的节目视为一类。这恰是文化之体带来的一种规约和共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并非指信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它强调的是观众被内容所营造的认同感所吸引,节目成为一场情感与信仰的盛宴[1]。由此出发,传播并非一定要在信息层面有实质的收获,而是有可能借助整个传播过程所营造的情景和氛围使受众获得一种文化性的群体认同。换言之,无论是寄于书信的《见字如面》,还是聚焦于文物的《国家宝藏》,甚至是探索文创之路的《上新了·故宫》,都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本之体的观照下才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类节目。观众除了在节目中获取存在于表层的信息以外,更多的是以此为路径进入一种共有文化的场域,获取认同。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认同永远是无法舍去的第一步,也只有从认同开始,才有可能觉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灵韵。
觅得根本之“体”,“相”与“用”自然清晰明了。就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而言,各种层出不穷的形式和重新组合的元素构成了节目呈现出来的样态,或者不如说这是文化之体经中介之后的一种外在显现。而这正是文化类节目的芸芸之相。《经典咏流传》将诗词谱新曲,完成了历史与当下、古典与潮流,甚至中国与西方的对话;《中国诗词大会》则是将古时雅集的竞争因素予以凸显,你来我往的“飞花令”营造的是足够紧张的氛围;相较之下,《国家宝藏》更加综合,舞台剧、文物点评在故事化的呈现中都更加便于接受。但,这些都是“相”。所有的节目,究其根本都是在构建一种情境,让人跟随情境的内在变动而逐渐进入其中,国宝是如此,书信也是如此,核心问题在于,情境构建只是第一步。如同每年上映的数量巨大的电影一般,每一部电影都各不相同,可能够留下印记、被人们真正记住的总是少之又少。乱花渐欲迷人眼,却总有人囿于这些文化之相中。

《见字如面》海报

《上新了·故宫》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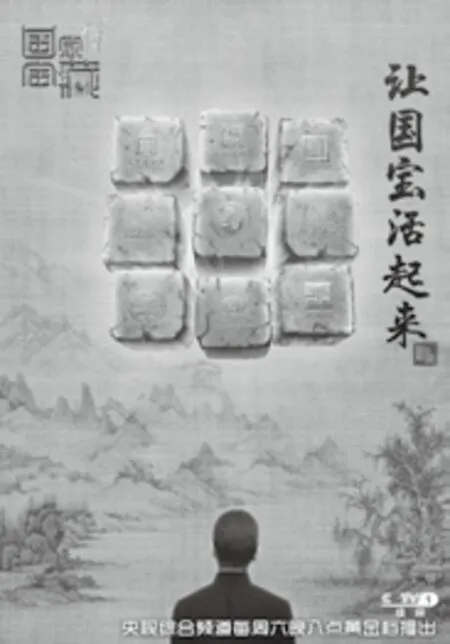
《国家宝藏》海报
如果我们认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其在当代中国完成生意盎然的继承与发展,那么这就是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最为根本的“用”。无论是艺术欣赏还是信息传播,受众总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缺少了受众,艺术作品就没有真正得以完成;信息传播也没有形成完整的通路。文化也不例外,无论体、相多么深入与繁复,总要落到地上才能生长。于是,“体、相、用”在文化内在动力的驱动之下,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的平衡。在文化类节目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需经过节目的形式与设计完成显现,进而与受众产生关联、发挥作用。反过来,受众对于节目的认知决定了文化本身的展现程度,从而影响着文化与节目的传播。但三者间的平衡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平衡的存在有赖于周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当这些发生了变化,平衡会不断被打破,然后在三者共同的作用下重新形成平衡。这也是为什么文化类节目在近几年重新“翻红”的重要原因。可见,想要通过文化类节目的传播,将中华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从“体、相、用”三者着力是可取之道。
二、建体与致用
如前所言,文化类电视节目之体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之前加上的诸多修饰,显然完成了一种对于文化的提炼,而这种提炼的过程正是建体。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华文明史,使众多文化得以存续。只是,这文化无法也不能被全盘继承,因为中华文化某些部分是应被舍弃的,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扬弃。建体的核心在于建怎样的体。传统文化的命名显然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但这二者都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并不是说存在某一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的统称为传统,在此之后的定义为现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别。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向工业社会过渡,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人类活动产生了现代文化。而现代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某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进程是不同的,其所呈现的特殊性与差异性无不深植于本国的传统文化之中[2]。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像是一桥相连的大河两岸,二者始终连接、并不割裂,只是更多地在对岸互相观审。回归传统文化透视现代文化,通过现代文化反观传统文化,进而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到传统文化的位置,使之发挥重要的作用,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最好的相处模式。可见,文化的发展永远是“接着讲”的。我们是无法确定一个稳定的时间点,并以此为界限开始对之前的文化“照着讲”的。文化与时间的流淌始终同向而行,只要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曾断绝,那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也只不过是人为添加了一种限制,让文化本身呈现出更加规律的状态。因此,不论是通过提炼,还是借助现代文化的观审,最终都是要锚定一个具有相对稳定内核和动态发展外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在当代语境中完成再书写,而这就是建体。从这一点看,文化类节目并非只是被动承载着文化,而是参与到了建体的整个过程中。因为如果缺少了显现的载体,建构的“体”永远只能是空洞的存在,而无法与实际生活产生联系。借用英伽登的说法,文化本身也充满着未定点,需要继承文化的人予以填补和连接才能真正得以完成。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总要通过中介或者载体才能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文化类电视节目恰好满足了这种中介和载体的需要。加之电视媒体与生活同频共振的传播特性,此类节目受到关注就顺理成章了。
建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致用。对于文化类节目而言,致用的最终归宿应该是让中华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发芽,产生持续和长久的影响。而当这种追求与诸如收视率、点击率等因素产生冲突时,孰轻孰重就显而易见。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3]。无法否认,在市场的大潮中,电视节目实现经济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经济价值永远不应该成为决定节目创作的根本性因素。否则,无论出发点多么的正确,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被经济大潮带动偏离方向。尤其是当节目的创作开始偏向单纯为了获取关注与点击的时候,节目的根本和样态就不再遵从文化和艺术的规律,而是开始从属于经济。当一些节目把“竞争性”“利益最大化”等语汇反复提及时,就已经有滑向唯利益泥沼的风险。体现在节目中,就是为了迎合市场的关注,将各种所谓流行元素堆砌起来,在环节设定和嘉宾人设上着墨甚多,俨然将一档节目变成了一场闹剧。
纵观我国电视节目的现状,优秀的节目时常有之,但恶劣的重复却也挥之不去。当对文化之体的关注降至谷底,创新的根本动力就不复存在,剩下的除了为创新而变化的表面,就只有一场空虚的展演。事实上,所谓某一阶段的潮流类型节目,更像是吃腻了大餐之后的乡间野味,慢而美只是特定时间中的美好假象,当更多的相似甚至重复不断冲击着观众的视觉神经,慢而美就变成腻且烦了。所以,我国的许多电视节目常常在三五季之后悄无声息地退出电视舞台。这似乎是我国电视节目一个无法逃离的诅咒。就文化类节目而言,其原因就在于,一些节目只是空有文化之壳,而无文化之本。它们不是在文化的指导下完成节目的创作,而是在节目创作中把文化视为其众多元素之一而加以组合、转换、变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类节目立身之本就是“体相用”中最为根本的“体”。缺了这环,“相”“用”两废是必然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简单借用而非融合借鉴,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本身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梁漱溟说:“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4]对待这种“活东西”,我们显然不能将之视为砖瓦石墙,粗暴地添加减损,而是应以一种身在其中的体认来保留文化的生命性。当文化成了元素,有机整体的生命意味就再难被察觉;而此时,在文化类节目中呈现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三、著相与舍相
“相”在中国佛教的“体相用”论中举足轻重,因为“相”是从“体”生“用”的一个中介。但紧接着佛家又讲,“相”也只是中介,远非目的;而且作为实践层面上的“体相用”,其中的“相”都是虚幻的,都是不能执著的,因为一著相便违背了佛教的不执著精神[5]。换言之,“相”最终可以舍去。但是,佛教的“体、相、用”论的出发点是万法皆空的前提。就文化类电视节目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节目立身之“体”,而节目实际存在中经编排、设计呈现出来的种种节目样态与形式就是节目之“相”了。在“体、相、用”三者的关系中,相是指假相,只是这里的假并不是虚假之意,而是取假借意。丁福保解释“假”,“假者,借之义,诸法各无实体,借他而有,故名假”[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必须经过中介才能得以与当代发生关联,进而产生影响。因此,文化在节目中的呈现,颇有种借道而行的意味。只是这道路通畅而行,有赖诸“相”的努力。所幸,以《见字如面》《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故事里的中国》等为代表的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已经开始了探索。
以往很多节目聚焦于中华传统文化时,总是选择从十分宏大的视角概观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长河,多仰观而少俯察。这当然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概观和仰视总是少了血脉相连的亲近之意,平白堆起了崖岸,观众获得的只是抽象的文化概念,而缺少真正的连接。而在当下,日常叙事凸显。日常叙事之为日常,就在于其关注平常状态下的个体的生存,换言之,这是一种个性化叙事。这种个性化叙事可能缺少恢弘的气势,但它将视线聚焦于个体之上,尝试展现出小人物的离合悲欢,宏大历史背景所掩盖的个体层面的内容被日常叙事重新发掘。体现在节目创作中,日常叙事表现为更加注重故事化的表达、更加努力营造仪式感的空间。
故事化是电视节目内容呈现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在文化类节目中,追求故事化是为了获取文化意义,而非单纯通过故事来获取娱乐。这种文化意义无论如何得以实现,观众的认同是前提。“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的一句宣传语。所谓“活起来”就是让隐于玻璃窗之后的文物冲出历史的迷雾,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当代人们的注目。节目中历史剧演出的形式,也是让文物重回当时的情景,从而让文物摘下古老的面具,揭示出本真的状态,以今观古的同时也拉近了古与今的距离。文物之所以为文物,不仅在于其物质性地记载了工艺,更在于其精神性地传承了文化。故事让文物有了温度,由此激发观众的兴趣,才有可能进一步产生影响。古诗词同样不例外,除却部分耳熟能详的诗词外,很大一部分诗词既少被接触,又很难接触,毕竟古诗词的语汇、语法和用典与当今的表述习惯已经相差甚多。但是,在《经典咏流传》中,诗词以一种新的形式进行了转换。和诗以歌,不仅仅是让古诗词借流行音乐传唱开来,更是让似乎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诗意语言与当下的情景重新建立了关联。节目环节的设定,结合了音乐点评与诗词背景的介绍。流行音乐的编配理念与古诗词的内在韵味在拉平的历史空间中产生新的碰撞,看似不搭调的组合方式,在故事化的展示之下,有了一种异样的协调。古诗词不再是“背诵全文”的晦涩对象,而变得充满新奇感与亲近感。正是故事化的呈现,给了古诗词以贴近生活的温度。
广义的仪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中。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仪式阐述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社会不仅成就个体,还依赖并内在于个体。一方面,社会超越于个体意识,但另一方面,它只有在构成它的个体意识中、并通过个体意识才能存在。”[7]换言之,除却法律方面的规约,社会的维持还有赖于每一个个体意识中的共有约定。当个体在实际生活中触及到这种共有约定时,仪式感就产生了。当《见字如面》中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书信被展开时,观众心中由中华文化孕育的家书、情书与友人书的集体记忆就被唤醒了。信件本是私密的,这一判断的隐含意义就是对信件内容真实性的确证。因此,将这种私密的真实在“围炉夜话”式的小剧场进行展现时,情景的参与程度得以最大程度的建立。加上节目对于书信主题的整体把握,生死、爱恨、成长、相思、不舍等一系列人类共通情感带来了强烈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的影响下,各不相同的书信才能将不同的观众凝聚在一起,进而参与到文化的当代书写之中。“展信佳”,本就是一个仪式感具足的开场。当观众随着信件的展开而参与其中时,原本私密的信件就被转变为公共空间对集体记忆的缅怀与反思,从而形成了一种仪式化的狂欢。这种集体记忆更像是种子。初始时只是潜藏在人们意识之中,当经过不断的复现和时间作用下的沉淀、凝结后,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文化的继承自然就完成了。
故事与仪式都是在努力塑造一个凸显“体”的“相”;有了“相”作为中介,才能将中华传统文化以一种真实可感的方式延续下去,而非仅仅留存于概念化的表面。由此来看,“相”当然不应舍去,但也大可不必将所有的重心都置于“相”上,因为一旦过于着力于某方面,节目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刻板与僵化,那个逃不过三五季的“诅咒”就会出现。一些节目视热点为核心,把流行元素不假思索地移植到节目中,看似样态丰富,实则缺少内在的统一性,最终呈现出来的只能是一个个相互疏离的切片。这恰是因为过于重视“相”。面对纷繁复杂的相时,心中仍需有一线清明,知晓哪里才是根本,毕竟形式总是要为内容服务。著相也好,舍相也罢,凡相都只是过程,最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凸显,才是目的。
结语
对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的探讨很难单纯局限在艺术或传播的领域。因为究其根本,提及文化的艺术创作和信息传播都只是表象而已。本质上,应探讨的是如何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再书写,亦或是更为直接地称为转译。冯友兰曾提出“抽象继承法”,并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底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8]何为具体、何为抽象,冯友兰举例说:“《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来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9]哲学命题是如此,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具体意义当然需要被关注,只是这种在具体情境之下的意义在当代也许会水土不服,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抽象继承并不是将有机整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抽离成为概念化的、限定性的表述,放在楼台之上枯等人们凭吊瞻仰;而是将原本情境中合理、有益的传统文化之精神内核总结出来,根据当前时代的发展重新赋予其符合时代特征的具体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影视艺术领域的传承大抵都是如此——“建体”通过中介的“相”达到“致用”。近几年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是明确文化之体后,在寻“相”之路上的更新的探索,也是对文化之体进行当代书写的更新的尝试。而这些节目所依托的电视媒体毫无疑问是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作用”[10],能够结合新的技术手段,在多平台进行内容传播,如此多方合力的推动下,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节目形式本身的局限,开始向着营造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氛围转变。建体致用不舍相,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在连接“体”与“用”之间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引领大众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世界。
【注 释】
[1]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J].国际新闻界,2008(8):46-51.
[2]徐小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25.
[5]陈坚.不是“体用”,而是“体相用”——中国佛教中的“体用”论再思[J].佛学研究,2006:329-344.
[6]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1599.
[7]〔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1.
[8][9]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259,259-260.
[10]仲呈祥.自厚天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