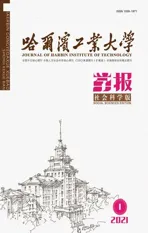进功与遗权:南朝谢氏家族性格与贬谪
2021-01-21孙雅洁
孙雅洁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陈郡谢氏于东晋一朝逐渐步入政治舞台,并在朝堂中谋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家族门户发展达到顶点。至南朝,身为高门望族,他们在政治上依旧活跃。但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时期的贬谪情况,谢氏一族有贬谪经历的人数远超其他同时的士族大姓。考察个体的被贬原因,表面上缘由各异,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与家族内成员相似的性格特征有直接关联。因此,探究家族整体性格,对研究谢氏的群体性贬谪十分必要。
以宋武帝即位改元至陈后主降魏为界,依据史料,陈郡谢氏族中在宋、齐、梁、陈四朝可考的贬谪共计28人次,其中谢灵运、谢超宗各五次,谢几卿四次,谢庄三次,谢朏、谢览各两次,谢晦、谢纬、谢元、谢颢、谢举、谢谖、谢嘏各一次。基于现有文献统计结果,陈郡谢氏族人之贬约占南朝贬谪总人次的5%。再参考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一书确认文人身份,谢氏一族中的文人贬谪共计25人次(除却上文中谢纬、谢元、谢谖三人),约占南朝文人贬谪总人次的15%。以上数据足以说明谢氏家族在整个南朝贬谪与贬谪文学中的重要位置,而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研究有相当必要。
一、“进功”与“遗权”性格特征的界定
《南史》列传第九、第十中,称赞谢氏后辈多用与族内前贤相较的方式:
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儿何为不及我。”[1]538
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1]542
年十二,召补国子生。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王俭曰:“几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几卿辩释无滞,文惠大称赏焉。俭谓人曰:“谢超宗为不死矣。”[1]544
朏谒退,粲曰:“谢令不死矣。”[1]558
以上材料综合起来,可以理出这样两条人物线索:谢玄—谢灵运—谢超宗—谢几卿、谢庄—谢朏。都是或以为祖孙相肖,或以为父子相承。虽然时人的关注点偏重于他们玄理文思的造诣,但这只是谢氏家族言传身教的一个方面。《世说新语·德行》载,“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2]“谢公”即谢安,对后辈的教导方式是言传身教、以身为则。相肖不仅仅局限于文章学识,从深处着眼,更在于家族代代相传的人格风貌。前辈与后辈的相肖,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精神走向,呈现出一种相谐的价值追求,在外表现为具有整体性的家族性格特征。
谢氏家族性格的整体性之中,又有二重性。《宋书·谢瞻传》的一则材料指出两个方向:“(瞻)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3]1557又据《南史》载,谢瞻尝裁止谢晦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 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1]526谢晦、谢瞻兄弟二人不一样的处世之道,恰可以代表谢氏家族的两种行为趣向:一是干预时事、进取权遇,二是素退为业、处贵遗权。进一步可归纳为“进功”与“遗权”两种性格特征。
这两种精神特质看似相互背离,实则出于一源,都形成于谢氏先辈真实的政治遭际,与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确认过程密切相关。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将陈郡谢氏在东晋一朝的门户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谢鲲、谢尚、谢安三个人物为代表。谢鲲跻身玄学名士,谢尚取得方镇实力,谢安屡建内外事功。”[4]202提倡玄学使谢氏一族获得了跻身士族行列的资格,而追求事功则是稳固其门户地位的必要手段,也就是《晋书》论及的“计门资”与“论势位”二途[5]2382。谈玄旨归于遗权隐退,而论事功则指向进功成名。两者在谢氏家族中的融合共生,始自谢安、谢玄。谢安高卧东山、渔弋山水为乐,当天下多难时挺身而出,淝水之战大破秦军。在建此不世功勋后他又自请出镇、营墅土山,是一个退—进—退的回环。谢玄跟从谢安取得淝水之胜后亦屡次上疏、表请解职。
“进功”与“遗权”在谢氏家族的心中,又有着高下之别。由于“遗权”源于精神层的高蹈,“进功”源于现实层的追求,二者并非并重:“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6]根据谢灵运此言,虽对“爱物之情”和“救物之能”皆予以标榜,但进功是屈志,遗权才是志趣所在。然而这只是言语上的自作高标,事实恰恰相反:进功乃是第一追求,是遗权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探究谢安、谢玄政治上选择隐退的本质原因,可以予以佐证。谢安“始有仕进志”的起因是“(谢)万黜废”[5]2073,迫使他不得不站出来承担家族门户的重担。且田余庆犀利地指出,谢安“屡辞征辟的同时,已在观察政局,随时准备出山。所谓高卧东山,只不过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4]198。他在建立淝水之功后的自退,也并非表面上的“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而是“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加以会稽王道子“奸谄颇相扇构”[5]2075-2076,退居是他在猜忌与排挤之中不得已作出的选择。谢安“退—进—退”的回环之中,“进”是建立家族门户的需求,“退”实质上是在政治压力下的权退。谢玄的进与退亦是如此,先“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又因“太傅既薨,远图已辍”[7]解驾东归,在谢安死后以避祸。
此时,对谢氏家族的“进功”与“遗权”两种性格特征作一个界定。“进功”顾名思义,是为了确认及维护家族门户地位而主动追求功业。淝水之战是谢氏门户发展的重要拐点,牢牢抓住了抗击前秦入侵的历史机遇扶摇而上,依靠不世功业确立了家族地位。在此之后,为了维系家族门户,谢氏族人依然不断努力向政治中心靠近。“遗权”的产生则稍显复杂,其内涵有二:向内源于玄学思想,向外源于政治压迫。玄学的物外之趣既是他们精神层面形而上的追求,也是承受政治压力时的退路。淝水之战后,随着外部矛盾消解,内部矛盾激增。谢氏与桓氏、司马氏的权势彼此消长,又加之失信于皇权,谢安、谢玄不得不选择淡出全身。谢氏家族性格的二重性形成于门户与皇权的对抗性压力,且始终也不可能走出这两重压力的倾轧。
至南朝,谢氏“进功”与“遗权”的家族性格被延续。这两重性格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后辈的政治际遇,与这一时期谢氏族人多遭贬斥的政治经历有直接关系。朝代更迭,谢氏一族的命运并未有所改变。在南朝他们既以门第自矜,要在谈玄的时风中引领潮流,也同时高标物外之情。但对“进功”的追求是高于“遗权”的,谢氏家族地位的稳固需要持续争取政治权力以支撑,不肯真正走向归隐山川一途。可是政治始终在皇权的主导之下,皇族对士族的态度仅是用以巩固皇权而已。追求事功和为门户谋取利益,必将受到皇权忌惮。因为“进功”的性格,谢氏一门屡遭贬斥,难以步入政治上流。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不同的个体身上,演化出了与形成期不完全一致的具体精神特质,但士权和皇权的始终不平衡,框定了谢氏家族性格与政治命运的总体走向。
二、“进功”性格的表现与对贬谪命运的作用
“进功”的家族性格在后辈身上的主要走向有二方面:一是和先辈一样积极追求功名,二是因崇敬祖先建立事功之举、以此为则,形成效力皇权的“忠”的人格。虽然具体表现不同,但都直接作用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命运。
谢氏前贤建立的功勋极大地激励了后人博取功名的信心,故入仕者众多。但步入新朝,客观上已不具备建立功业的历史条件,主观上族人又大多缺乏政治嗅觉与政治才能。南朝统治者对士族的整体政策是打击高门旧姓,扶持新兴士族。他们对前朝的门阀士族加以笼络安抚,目的仅是利用他们的势位巩固皇权。同时作为上位者,宗室始终保有戒备之心,对士权加以限制和打压。如谢灵运虽在宋国初建就已仕于彼,但一直在政治上失意。宋文帝对他再三召起,亦唯以文义见接,就是显然一例。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8]这句话几乎是谢灵运的心理写照。谢灵运心中一直怀抱着像先祖一般成就功名之志,在作品中反复提及鲁仲连、范蠡等人。他首先追求的并非归隐曳游,而是建立功名、刊刻史籍。但上位者对他的定位并非拯救时世,而仅是锦上添花,即利用其士权与文名稳固统治。谢灵运因此“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3]1772,这种反抗和不合作的姿态直接挑战了皇权的权威,故受到铁腕压制。而压制的手段,无外乎减降流放。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谢晦虽位为辅国,武帝刘裕临终前却诫太子曰:“谢晦屡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1]27,告诫继位之君对他保持警惕,并建议出之会稽、江州以为防备。齐武帝时,谢超宗娶张敬儿女为子妇,上已疑之。至永明元年敬儿诛,超宗仅因与丹阳尹李安民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君欲何计”[1]543一言,就被徙越州①按,《南齐书》本传作“徙越州”,而《南史》言“徙越嶲”,越州位于今广东一带,越嶲郡属益州、位于今四川境内,两地相隔甚远。依照谢超宗行至豫章(属江州,今江西境内)时,赐于彼地自尽,若徙于越嶲而取道豫章过于枉道,而徙于越州途经豫章则情理之内,故从《南齐书》,作徙于越州。,更当其行至豫章时赐自尽。皇权对士族利用之余,始终保有防备之心。谢氏对建功的追求,或许恰是自毁之途的开端。谢晦在临终前作《悲人道》文及《连句诗》,实已点出自身悲剧性命运根结所在:“绩无赏而震主,将何方以自牧”“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3]1360-1361,把握不好进退之度而一味进功,必不能为上位者所容。加之没有退保之力,就只能沦为权力相衡的祭品。
从个人的自身能力来说,谢氏后辈中亦缺少真正具备政治才干之人,所以在权力的博弈中难谋出位:谢晦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而误封他人;尚书左丞谢元与御史中丞何承天不善、累相纠奏而被禁锢至死;谢灵运见赏于庐陵王义真,而为拥立少帝的徐羡之、傅亮所患,与刘义真、颜延之、慧琳一同被出。如此种种,可见谢氏族人虽留连宦场,但欠缺实际政治才能。如果说是宦场权谋的波诡云谲,使得谢氏应对无力,那么退一步而言,他们更连引以为傲的祖辈军事才干都未能承继。谢览不敌山贼吴承伯,弃郡奔会稽;谢几卿自请从战北伐,退败于涡阳。一味追求比肩先祖功业,以军功谋声名。他们自己却有志而无能,终归挫败。谢几卿求从战北伐前“与仆射徐勉别,勉云:‘淮、淝之役,前谢已著奇功,未知今谢何如?’几卿应声曰:‘已见今徐胜于前徐,后谢何必愧于前谢。’勉默然。”[1]544-545谢几卿此言颇有几分豪壮之气,但徐勉闻罢此语惟有“默然”,实是对谢几卿此去的命运已有洞悉。谢氏的族中先辈为后辈步入仕途提供了平台,也鼓舞了他们的信心。但既非其时,亦乏其才,对功成的追求只能夭折于贬斥的泥沼。
谢氏先祖曾经建立不世功勋,族人钦慕向往,在心中随之衍生出了一种品格:“忠”。但是“忠”对立功名的作用,则具有双向性:在朝廷政权稳固的情况下起到的是正面作用;而在权力频繁更迭的南朝,对进功却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易代之际,士族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新旧朝更迭时的自我定位与心态认同。一朝之末,家族及个人已在旧朝经营多年,根基趋于稳定。心理定式使他们选择忠于旧朝,而不去攀附新朝。忠于旧朝更是将损失降到最低的守成之法,原因有三:其一,规避了举事失败、动辄会遭致灭门之祸的政治风险;其二,即使新朝成功建立,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对前朝旧臣往往会采取笼络的怀柔政策;其三,新朝的建立也意味着士权与皇权新一轮的平衡,即利用与打压。所以“忠”成为这部分人的选择。但忠于旧朝不与新朝合作,尤其是在新政权主动示好之后依然不能见风转舵,则与新朝政权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如当宋齐易代之时,谢朏劝说后来的齐高帝萧道成放弃图谋禅代,并在齐萧新政确立时依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钦属。论魏、晋故事,因曰:“晋革命时事久兆,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帝不悦。更引王俭为左长史,以朏侍中,领秘书监。及齐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9]262
萧道成以石苞痛哭晋文只能用人臣之礼下葬,与冯异助刘秀登上帝位终成大业对举,暗示谢朏助他图谋大业。但谢朏以魏武帝不肯即帝位事答之,来证明自己忠于刘宋正统的决心。萧道成看重谢朏的原因,在于其“祖弘微,宋太常卿,父庄,右光禄大夫,并有名前代”[9]261,谢朏也自幼以聪慧闻名。萧道成想要利用谢朏家世的显赫名望和自身的当时重名,给图划大事以支持。但谢朏不愿意合作,更当宋齐禅代已为定局时拒绝行解玺之仪。其弟豫章太守谢颢,当齐侵宋地时也作出了与兄朏一样的选择,白服登烽火楼以示抗衡。他们的行为举止固“之于宋代,盖忠义者”[9]266,然触怒了已掌决断权威的萧道成,被免废、不许位列官场。新的政权上位者拥有政治霸权,可行黜免以惩戒不合作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可资利用的替代品。“忠”是他们求仕进的衍生品,但此时却反成为利刃、自伤于仕进之途。若他们想要重新获得进功的机会,终须与新政权妥协。谢朏后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得以复起,与一变对宋的“忠”而服从于新朝的心理变化亦有密切关联。
三、“遗权”性格的走向与对贬谪命运的作用
谢氏“遗权”家族性格的形成,大致可归因于两个方面:其一,吸收玄道思想中的归隐幽居、无用全身的成分;其二,因政治压力选择退保自守。基于这两个成因,谢氏家族在“遗权”一途分裂出了三个走向:一是由于身病及玄学思想的影响而选择退处;二是以“遗权”作为政治失意的退路;三是因玄道推崇的任性而步入过度的纵性一途。三者似殊途而同归,其终点都可能对政治生涯产生不利影响,在此仅着眼于考察被贬谪的案例。
南朝虽只有约一百七十年,却不乏隐士。这一部分选择坚守不仕的人,见诸《宋书·隐逸传》《齐书·高逸传》《梁书·处士传》《南史·隐逸传》等。虽仅少量载入史籍,应还有相当一批没有步入仕途而不显于时、未能留名的。这种隐逸之风的盛行,与玄道思想有紧密联系。谢氏家族有一部分人确实选择了真正的归隐,全身于政治之外。按常理推断,这种遗权应当与贬谪不会产生关联。但谢庄于南朝宋孝建三年因辞疾多被免官,这是诸多被贬情况中极为特殊的案例。虽然是特例,但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原因及其与贬谪的直接关系不容忽视。谢庄的被贬表面看来是由于主观请辞的行为。他的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己身之多病,以疾辞应非矫饰:“况今绵痼,百志俱沦”[10](《让中书令表》)、“禀生多病,天下 所悉”[3]2171(《与江夏王义恭笺》)……其实并非仅谢庄如此,谢氏一门的本传中亦多见“疾”“病”字眼:谢安“雅志未就,遂遇疾笃”“有鼻疾”;谢玄“既还,遇疾”“于道疾笃”;谢灵运“卧疾山顶”“谢病京师”;谢瞻“疾笃还都”。疾病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不寿,“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3]2172,程章灿考六朝史传,知“谢氏一门中享年五十以上者罕见”[11]。在家族普遍多疾不寿的现实情况下,谢庄主动辞官以养生是合乎情理的,似乎不应当被贬。但加入政治背景和政治地位的考量,就能够理解个中原因。谢庄并非一介乡村渔隐之人,而是少年即入宦场、名声已然远布。他除了是一个朝堂宦者,更是皇权手中运筹帷幄的一枚棋子。再三请辞打乱了上位者的排布,挑战了上位者的耐性,故用免官的方式予以警告。谢庄并没有和皇权发生正面的冲突和抵牾,这种贬谪起到仅是小惩大诫的作用,在免官次年即重新启用。
也有一部分人虽有思隐、慕隐的行为,却和真正的隐士有本质不同。他们的退隐只是一种权退、暂退,是在政治压迫下不得已的退保自守。这种情况也纳入贬谪的考察范围,是因为往往这种退避大多是贬官之后的延续性行为。且与贬官相似,都是一种在霸权下的被动政治疏离。谢灵运也曾以身疾不堪吏事,辞去永嘉太守之任,于景平元年(423)秋末至元嘉三年(426)长期归隐始宁。这与谢庄的请辞缘由,有一定的相似性。谢康乐在永嘉任上时,曾反复书写己身之病:
卧痾对空林。 (《登池上楼》)[12]95
偃仰倦芳褥,顾步忧新阴。(《读书斋》)[12]113-114
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游南亭》)[12]121
卧病同淮阳。 (《命学士讲书》)[12]136
矧乃卧沉疴,针石苦微身。(《北亭与吏民别》)[12]140
正因卧病日久,更生故园之思。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谢灵运在永嘉、始宁期间对山中草药予以了格外关注:
石室药多黄精。石室紫苑。(《游名山志·石室山》)[12]391
泉山竹际及金州多麦门冬。(《游名山志·泉山》)[12]392
此境出药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药。医缓,古之良工,故曰别悉。参核者,双核桃杏仁也。……二冬者,天门、麦门冬。三建者,附子、天雄、乌头。水香,兰草。林兰,支子。卷栢、伏苓,并皆仙物。凡此众药,事悉见于《神农》。 (《山居赋》自注)[12]456
对这些草药的关注,有一个直接原因:“欲以消病也。”或可推测,谢氏旧宅始宁一地多出草药,谢氏族人聚居于此或辞归故里,很有可能是方便以此地盛产的草药疗疾、延年。因身体衰病选择退身是谢氏家族“遗权”的动因之一,家园故土一方面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另一方面也能疗养身体疾痛。但将谢灵运辞官归始宁纳入贬谪的考察之列,是因为不能仅凭表面所见,认为出于他真实心志的驱动。谢灵运的归隐并不仅是言语层面透露的身体原因或对隐居的向往,其实际更是为了政治避祸。这种情况应当视作贬谪的一种特殊形式——政治失意后暂时的自我放逐。
谢氏家族先辈对始宁的经营,给后人政治受压抑时以退路。“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3]1754,谢灵运亦在归始宁期间对旧居加以开拓。因为有庄园经济的基础,谢氏一族在遭政治挫折时,可以选择表面的“遗权”来作自保之途。考量谢灵运出贬永嘉的政治背景,可探知他从永嘉任上辞官归隐的心路历程。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相友善,而在少帝即位后并为徐羡之、傅亮黜出。刘义真是谢灵运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期望,他曾云得志之日,当以灵运为宰相。可这个希望很快幻灭,谢灵运也被政治边缘化。他选择了主动请退、弃官返乡。通过在家乡恣意行游,试图缓解淡化政治上的失意与苦痛。虽然谢康乐在文字间自云辞归乃是本心,山水游历更是适意。但这其实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失望之后短暂的自我放逐。他虽身在山光水色之中,实从未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是用山水和玄理来掩盖浓浓的寂寞之意。此外,虽然谢氏家族性格中幽居全身的思想本于玄学,但是当南朝之时,佛教逐渐兴盛。上层社会已不满足于谈玄说理,对佛家思想亦涉猎钻研。以玄解佛的玄佛共通性为“遗权”赋予了新的思想源泉,谢灵运在始宁时也常与僧人游处。归隐田居给他以喘息的缝隙,用玄学佛思抚平政治上的伤痕。主动选择更退一步,是他在政治压迫下寻求的自我出路。至文帝时,徐、傅伏诛,谢灵运方才重新出仕。这种归隐与上述因疾自退有交叉,外在表现都是自己主动选择退隐遗权,但其内涵则有深切的不同。其本质是压力下的被迫抉择,貌似豁达惬意,实则无奈沉痛。类似还有谢朏的“拂衣东山,眇绝尘轨”,与当年谢玄的表请解职实出一路,都是在恶劣政治环境下的主动退避。 “虽解组昌运,实避昏时”[9]263。 谢朏为了避齐明帝、东昏时政治波荡,屡召而不屈,至梁武帝时方才再度出仕。修史者姚察论,其“当齐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难,确然独善,其疏、蒋之流乎。洎高祖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9]266。 对谢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9]262,终得以善身的政治选择给予了高度肯定。谢朏也是南朝谢氏一族中为数不多的得以善终、享有哀荣者之一。这种遗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权退,身在江海而心系庙堂,是为了保存自身、伺时而动。
“遗权”这一家族性格的思想来源是玄学,玄学思想中包含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观念,至极端则归于纵性放浪一途,直接决定了一部分人的贬谪命运。加之谢氏作为高门望族,足以自矜门第,族内子弟性格发展出放浪简傲的一面。或触犯礼法秩序,或懈怠政务、玩忽职守,这些情形都是依照法度应当被贬谪的。如谢灵运“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3]1772,当觉得政治上任命不遂其志时便怠慢公职。他以这种行为表示、发泄内心的不满,在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任上无不如此,因此往往被表奏弹劾。即使有宋文帝爱才,也难以宽容他屡屡不改,任性游牧。结果只能是仕与隐两难全,谢灵运既不能够实现自己参与时政的政治理想,又不能够真正放迹于江海。谢灵运屡改骤迁,是他自己高自标榜和恣意纵性的性格直接所致。又如谢超宗、谢几卿,他们行动上承袭了东晋饮酒之风,精神上继承了玄学不为礼法束缚、随性纵情的一面:
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之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1]543
(谢几卿)以在省署,夜著犊鼻裈,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嘑,为有司纠奏,坐免官。[9]708-709
仆射省尝议集公卿,几卿外还,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无人。又尝于阁省裸袒酣饮,及醉小遗,下沾令史,为南司所弹,几卿亦不介意。[1]545
对于魏晋年间一些饮酒高士而言,酒是纵情恣意的媒介,更是对现实逃避与遮蔽的良剂。他们用以全身的做法,到了谢氏这里发展成为了一种故作姿态。谢氏一门有着骨子里的骄傲,纵性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不群与高标。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追求功名权位,违背礼数法度的行为与他们公职人员身份相冲突,故而受到相应的惩戒。
六朝之际,门户之见依然根深蒂固,这也是谢氏自矜之处。谢灵运曾经与谢晦讨论潘安、陆机和贾充三人优劣,“晦曰:‘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他们二人都认为贾充高出潘安、陆机远甚。表面上似乎着眼点在人品,但据下文谢瞻的回答,所谓“不得为并”“本自辽绝”更有其他内涵。“瞻敛容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1]525-526。 潘安、陆机和贾充高下之分的关键点应当落于“处贵”二字上。所谓“处贵”是指身份门第而非个人努力,潘、陆为谢氏轻视的原因更在于门户出身。贾充承袭了父亲阳里亭侯爵位,后又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其地位之显赫远非寒士潘安、陆机可以比肩。谢氏的纵性并非真正遗权外物,否则何必沉浮宦海、为其拘束。谢几卿在《答湘东王书》中说,“因事罢归,岂云栖息”[9]709,他们纵情任性不过是故作高标别蹈,心实系于魏阙之下。当身处其位时,他们又不能放下姿态安心政事。因此,在思想与行动上互相依违,两处落空。风流随性影响到了政治体系的运行秩序,他们在体制内必然被强力规范,故致贬谪。
四、士权与皇权的抗衡与失衡
进功与遗权是南朝谢氏家族的两大性格特征,形成于东晋家族地位的确认过程,与家族在南朝的发展脉络亦息息相关。性格的这两端在后辈身上,内涵有一定的延伸与分化。谢氏家族多有贬谪的政治处境和政治悲剧,与他们的延续而下的家族性格都有直接因果关系。其逻辑线索可用图1(见下页)来表示。
南朝谢氏家族的人物性格,终可归源于“进功”与“遗权”二端。家族呈现出群体性被贬的现象,与其整体性格特征关系密切。可以说,“进功”“遗权”与谢氏贬谪有直接关联。“进功”性格作用下的努力仕进威胁了皇权地位,且他们自身缺乏皇族所需要的真正政治才能,故而屡遭贬黜。“遗权”性格与贬谪的直接关联则稍显复杂。“遗权”看似主动疏离政治权力,但实则往往身不由己。一种情况是皇权需要利用谢氏族人的士权和名望,而“遗权”不能够加以配合,因此被贬;另一种情况是谢氏一族在政治压迫下的自我放逐、权退全身。透过现象掩盖寻求本质,后者绝非自主选择,也符合贬谪被动疏离权力的特征。还有一种情形是纵情任性的“遗权”,此类被贬者有政治身份,却故作对权势的疏离与高蹈。不可否认,谢氏家族的每个被贬者,也有自身的性格特性。每个人在某个性格层面可能会更为突出,譬如谢灵运的任性游牧、谢几卿的自负放纵,等等。但是从个性中见出共性,大约都可以从“进功”与“遗权”这两个性格特征加以归因。

图1 谢氏家族性格与政治处境逻辑线索
“进功”与“遗权”看似是相反的处世之道,但根本出发点都是为家族门户计。不过是在不同政治际遇下,为达到相同目的而做出的具体选择。谢氏家族贬谪的政治悲剧究其根底,是由于皇权与士权的必然冲突,“进功”与“遗权”实是在二者夹缝中努力维持平衡的方式手段。谢氏作为高门望族,进入南朝之时便坐拥先辈的政治根基,这对于门户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提供了进入政治的平台,另一方面靠近权力中心则更有倾危的风险。皇权利用士权稳固自身,却不容自身权威有一丝撼动。唐代史家李延寿评谢晦先以辅国之重、后英年被诛之事说:“向令徐、傅不亡,道济居外,四权制命,力足相侔,刘氏之危,则有逾累卵。以此论罚,岂曰妄诛”[1]545-546。 谢晦是谢氏家族中一度最为权势煊赫之人,又有废少帝迎立文帝之功,他诚然是有政治嗅觉和政治能力的。但百尺竿头不堪更进一步,虽没有事实上的逾矩,对刘宋政权已构成威胁。谢晦最后的凄惨结局,正是王权对士权冒头的打压。
谢氏一族虽然长期承受着皇权的警惕与压抑,却也不能真正地遗权。即使有祖辈留下的基业,远离权力中心也会立刻没落。“论势位”是能够长久地“计门资”的基础,所以高门士族不得不为了维系门户,而不断追求功名。一旦超过士权的阈值,就会与皇权产生矛盾冲突。身在其中的谢氏族人没有办法清晰地认知这一点,当政治中遇挫时,往往仅流于感士不遇的历史悲叹。谢灵运是谢氏族人中文名最高的,也是被贬次数最多、政治生涯最为坎坷的。在他心里,唯庐陵王刘义真对他有赏遇之情,在贬谪期间感怀及追思尤甚,如“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12]54;“心欢赏兮岁易沦,隐玉藏彩畴识真”(《鞠歌行》)[12]310;“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12]183。 似乎他的不幸,仅是因为知音刘义真未能掌权。但事实并非如是,刘义真身为皇室一员,对谢灵运具有审视和利用的本能。他对谢灵运的赏识仅仅局限在相游处,《宋书》记载一事:“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3]1772他对谢灵运的评价多是贬抑,认为不过曹丕笔下“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13]1772的文人之流。可以想见,即使刘义真的掌大权,又何尝会安心将权势交到这样的文人手中。所云得志之日以谢灵运为宰相,也大抵不过是一时戏言罢了。究其根本,谢灵运政治生涯的悲剧,并不在于赏遇,而是皇权对士族始终存在的警惕与戒备。
谢氏家族性格,形成于士族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平衡与倾轧。虽然每个人所处的具体政治背景有所不同,也影响到了个人的黜与用。谢氏族内一些文名较高、声名较显的文人,往往各有际遇、几经沉浮。但因为大环境并未改变,故而在宗室与宗族权力制衡下形成的性格也一直在家族中保存延续。美国心理治疗师萨提亚指出,家庭对一个人有着第一位影响:“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首先在家庭中形成它的雏形。……在众多由我们参与构成的体系当中,它既是最先接纳我们的,同时也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家长通过赞赏与惩罚,使孩子“最终他们将家庭规矩作为尺度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如果他们遵从了这些规矩,他们会感到更可能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照此发展下去,他们就培养了或是约束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独特本质。”[14]新生个体的人格形成过程中,不断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而一个家族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家庭,最终使家族性格呈现整体性和存续性。谢氏祖辈在士权与皇权冲突抗衡下形成的性格特征,被后辈延续,成为群体性贬斥政治悲剧的诱因。皇权与士权的制衡与冲突,是谢氏家族性格与贬谪经历关联的大背景。就皇族利益而言,对士人一方面要加以笼络利用以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又要时时保有警惕。对谢氏一族来说,支撑和维系家族门户地位则必须进功,但又不得不以遗权作为皇权压制下的自保手段。把握拿捏“进功”与“遗权”之间的进退尺度,是为了应对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条件。可惜这注定是徒劳无助的,士族之于皇权,永远处在劣势地位。皇权与士权的不对等,使得谢氏族人疲于应对,亦不免始终在政治的深渊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