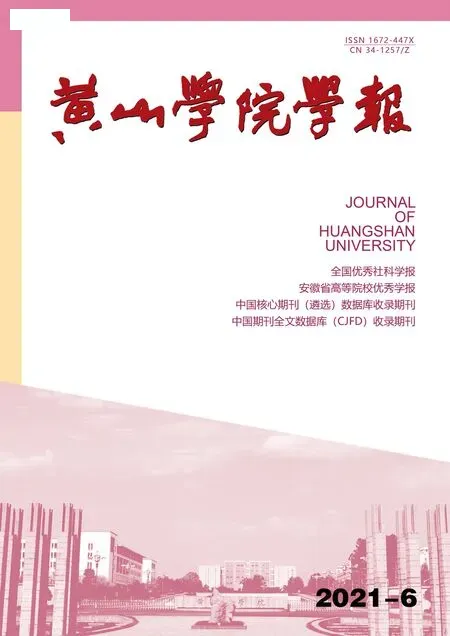莫里森展现黑人困境的空间书写中媒介的隐喻功能
2021-01-17金立
金 立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245041)
一、“媒介”一词的源起及定义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1]在这里,“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其中“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1]《文中子·魏相》:“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1]“介”字一直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英语中的“媒介”一词“media”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义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这里所研究的媒介是指在文本叙事中系连不同空间的中介体,或是使两个空间发生关系的介质。这样的“中介体”或“介质”在莫里森展现黑人困境的空间书写中轮番出现:从《最蓝的眼睛》以“目光”为媒介系连现实空间和视觉暴力空间,《孩子的愤怒》以“肤色”为媒介系连现实空间和权力空间,再到《爵士乐》首次以模仿爵士乐结构的“音乐化的语言”为媒介,将读者从现实空间引入“音乐空间”。“媒介”在莫里森展现黑人困境的空间书写中不仅具有系连不同空间的表层作用,还隐喻着作者对某个空间的态度、认知和对其本质的探索。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认知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参照自己熟知的、具体的、有形的概念来认知陌生的、抽象的、无形的概念,而隐喻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经历和理解另一种事物,是以一个易于理解、比较熟悉的源域映射到一个难于理解、不太熟悉的目标域。[2]在对“空间”的认知过程中,“空间的本质”是一个非具象的难以被认清的目标域,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不是“纯粹的”“静止的”“客观的”“独立的”和“刻板的”,空间的背后总是暗含着政治性、阶级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3]暗含在空间中的这一切由于其“非显性”的抽象特质总是难以被察觉,所以莫里森试图用具象化、易于理解的媒介(目光、肤色、音乐等)作为源域引导读者和她一起探索目标域,即空间的本质,这也是列斐伏尔试图探究的空间运作规律。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在本质上同时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空间与社会的互动中生产出的意识形态塑造了空间里人们的实际行为,并影响了个人命运。[3]26对黑人族群来说,了解这样的空间本质才有可能解构他们在空间里遭遇的困境,这也正是莫里森试图通过媒介的隐喻功能传达给黑人族群的关于空间的认知和态度。
二、以媒介之喻揭示黑人困境的本质
莫里森在展现黑人困境的空间书写中,通过“媒介”的隐喻功能引导人们反思空间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并深入探索黑人族群如何通过解构不合理的空间摆脱困境。
(一)展现黑人困境的“权力空间”书写中媒介的隐喻功能
“种族等级,种族之间的差别,某些种族优秀而其它种族劣等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是将权力控制的生物场碎片化的手段”。[4]在《孩子的愤怒》中,莫里森就书写了以“肤色”为媒介系连的“权力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以“肤色”深浅为标准建构出差异化“权力空间”。有色人种随着肤色的不断加深,被赋予的“权力空间”也越发逼仄,居于“权力空间”最底层的黑人族群对空间和物品的使用权都受到严苛限制,并因此陷入生存困境:他们在公交车站“被推推搡搡”,在排水沟里走而“把整个人行道让给白人”,必须去黑人专用的饮水处和厕所,就连结婚时都得把手放在黑人专用的《圣经》上,被辱骂和吐口水更是家常便饭。[5]
列斐伏尔曾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统治地位的阶层来决定的,他们拥有规范社会成员的“空间实践”的权力。[3]30黑人族群为了进入更高等级的“权力空间”,逐渐失去了正确的自我认知和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在种族社会的人生困境中居然开始认同白人规训自己的行为并积极地进行自我规训,并且这一切“空间实践”都是建立在外在“肤色”的基础上的,比如:浅色黑人会伪装成白人来避免被歧视的惨痛遭遇;浅色黑人排斥深色黑人并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优越感;黑人父母甚至根据自己孩子的“肤色”来进行“爱”的配给——“黑的要命,就像午夜”的婴儿卢拉·安就无法得到浅肤色父母的爱,父亲骂骂咧咧“他妈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母亲不愿用母乳喂养她,甚至一度想把她丢给孤儿院。黑人族群种种被异化的“空间实践”显然与“肤色”背后的“权力空间”密切关联。[5]5而莫里森以“肤色”为媒介系连“权力空间”,显然隐喻着黑人族群基于“肤色”进行的“空间实践”的扭曲和荒谬,因为“肤色”是不可改变的外在基因特征,厌弃并试图改变它无异于“自我绞杀”。尤其荒谬至极的事实是:一个孩子在自我认知都未建立之前,就因肤色被披着“文明”外衣的人们“理所当然”地剥夺了爱和关怀,并且这种剥夺还被集体默许为“理所当然”。在《孩子的愤怒》中,“肤色”作为媒介引领我们认知了种族社会差异化的“权力空间”建构的过程,还在更深层次上隐喻着种族制度下不公正的权力控制法则对人们身心“无形的异化”。同时也暗示着我们:空间从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政治性、工具性和意识形态性,生活于其中的民众总是被空间所蕴含的准则和价值观所迷惑。[6]而在莫里森看来,基于种族特征建构的权力空间是不合理的,顺应和屈从永远不是在权力空间里摆脱困境的有效手段。
(二)展现黑人困境的“暴力空间”书写中媒介的隐喻功能
在种族社会中,某些维持统治和剥削关系的“空间”以非常隐秘的方式存在着,令人难以察觉。比如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书写的以“目光”为媒介建构的“暴力空间”。在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人生经历里,白人老师、白人同学、白人移民杂货店老板乃至所有白人投向她的目光是“带有某种锋利棱角”“完全没有人类应有的认同情感”的嫌恶。[7]这种由白人“目光”凝视黑人而形成的“暴力空间”使小女孩佩科拉产生了难以言说的自卑感和羞耻感。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曾指出,因为“人总是试图以另一个人的视角定义自我”,所以“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己的眼睛在另一个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时,才能在他人眼睛里赋予自己身份”。[8]这种定义自我的惯性方式使视觉“暴力空间”具有了更大的杀伤力。而投向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白人“目光”在本质上隐喻着白人对黑人自我身份构建的主导和控制。当佩科拉开始对自身黑人特征产生极度厌弃并力求摒弃自己的“黑色眼睛”而代之以“蓝色眼睛”时,一个因无法抵挡来自视觉“暴力空间”的白人规训力量而陷入困境的悲剧人生就此拉开序幕。
甚至佩科拉的父亲乔利也曾受困于白人“目光”所开启的“暴力空间”:还是青少年的乔利在某个夜晚的郊外初尝禁果时被两个白人发现,并被迫在他们鄙视、嘲弄的目光形成的“暴力空间”中继续交媾。投向乔利的“目光”隐喻着白人对黑人人格尊严的践踏和对黑人身体支配的企图。种族社会中,被白人目光注视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活动,而是充满规训力量的视觉暴力。[9]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对黑人的规训已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可怕的是,在白人主流文化的霸权空间里,黑人投向自己和本族群其他黑人个体的目光也开始复刻白人视线下的“暴力空间”。《最蓝的眼睛》里黑人女孩佩科拉在学校操场上被一群黑人男孩围追捉弄,他们用嫌弃的目光注视着她,大喊“小黑鬼,小黑鬼”的打油诗。莫里森在此处用“苦心设计的绝望、用心学到的自我憎恶、潜心培育的愚昧”的排比结构来描述这群无意识下以“目光”为媒介对本族群施加视觉暴力的黑人孩子。[7]218他们用来开启“暴力空间”的“目光”隐喻着白人意识形态已内化为黑人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不自觉地通过白人视角看待自我,并最终沦为白人主体注视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客体。种族社会中被“目光”背后的白人意识形态所规训的黑人最终陷入看不到本族群的价值并与本族文化传统疏离的困境中。莫里森以“目光”为媒介书写“暴力空间”,期待人们反思“我们看得见谁,又看不见谁?目光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三)展现黑人困境的“死亡空间”中媒介的隐喻功能
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死亡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10]对“死亡空间”的书写折射出作家对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莫里森在《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都涉及了对“死亡空间”的书写,但书写的重点在于“死亡空间”对“现实空间”中黑人生存困境的映射。
《秀拉》中的黑人族群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受到极其不平等的对待,黑人从孩提时期就被疏于照顾和教养,总是由于被剥夺受教育机会和良好成长环境而陷于困境。黑人男孩“小鸡”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四处游荡,“一直用手掏着鼻孔,穿着十分肥大的灯笼裤”,这也是黑人儿童普遍的生存境遇。[11]可是“小鸡”和他身边的人早已对“被剥夺权力和尊严的命运”习以为常,似乎默认了白人所建构的“黑肤色”是原罪的意识形态。男孩“小鸡”有一次在与秀拉玩闹时被秀拉失手甩入水中而溺死,男孩以“水”作为媒介进入“死亡空间”。继而莫里森着力描写了进入“死亡空间”后的男孩依然被视作草芥的命运:黑人男孩“小鸡”的尸体被发现后,当地的白人法官竟然以“县城里没有黑鬼居住”为由让人“把尸体扔进水里算了”。[11]60因为“水”具有洁净的功能,所以,“死亡空间”以“水”为媒介向“现实空间”的男孩敞开大门,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一场象征着“重生”的洗礼,但其中更暗藏着“黑肤色”被白人强加的原罪是无法“涤净”的隐喻,黑人族群在“现实空间”无法获得的尊严和权力在“死亡空间”必然也不可得,获得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现实空间”里奋起抗争。雅斯贝尔斯认为,死亡才能使人“真正体悟世界和人生的本质”。[12]莫里森期待用“死亡空间”里黑人依然缺失的尊严和权力唤醒现实困境中黑人族群麻木的心灵。通过黑人李子的母亲夏娃的所为,莫里森再次通过“死亡空间”的书写映射黑人生存的现实困境。在李子追求“体面且有尊严地活着”而不可得时,母亲夏娃竟然以“火”为媒介将李子送入“死亡空间”以求重生。而李子在烈火焚身时感受到的也不是痛苦、恐惧,反而觉得周身的亮光是“一种洗礼,一种祝福”。[11]44贝尔克认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永远是居于首位的。[10]可是黑人李子却对“火”所系连的“死亡空间”充满了向往,这种异于常态的感受越发反衬出黑人在“现实空间”的不堪遭遇——李子由于严重的战争创伤罹患心理疾病,精神恍惚,加剧了他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白人主流社会”的人生困境,无法摆脱困境的李子成为只会喝酒、吸毒的行尸走肉。火光隐喻着李子及其母亲对理想、信仰和人格尊严的炽热向往。莫里森以“水”和“火”为媒介把读者导入肉体的“死亡空间”,还隐喻着对现实世界中黑人族群肉体虽生、精神已死的生存状态的看法。莫里森认为,失去精神支撑的肉体是没有价值的,黑人族群与其在虽生犹死的状态之中苟活,不如努力奋战以改变自己在以白人规范为准则的空间里所遭遇的不公待遇。
《所罗门之歌》中,以主人公奶娃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黑人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困惑,面对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他们不知所措,继而开始自我否定。而莫里森在该文本中所书写的“死亡空间”的老一辈人能为“现实空间”陷入自我认知困境的年轻一代黑人提供光明的指引,使他们走出否定自我的泥潭。所以不同于大多数文化中泾渭分明的“死亡空间”和“现实空间”,莫里森笔下以“超能力”为媒介相衔接的两个空间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例如,黑人妇女派拉特具有“超能力听觉”,能听见“死亡空间”父亲的教诲,但父亲的声音并不是在某个固定时刻通过某种特定仪式才能出现,而是在女儿派拉特“现实空间”中任何迷惘的时刻都会出现在她耳畔,给予她人生的指引,以“超能力”为媒介系连的“死亡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显然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还体现在老太太瑟斯身上。瑟斯年近200岁,“老得已经看不出颜色了”,人们看见她的第一眼就会联想到“死亡空间”,觉得没牙的嘴和布满皱纹的脸“不可能是活人的”。[13]可是瑟斯却发出犹如20岁年轻姑娘般“有力而流畅”的声音,将人们瞬间导入朝气蓬勃有生命力的“现实空间”。[13]269“生死”两种空间意象在老太太瑟斯身上以“超能力声音”为媒介交叠轮转,具象化地彰显出与死亡逆向而行的强大意志力。而正是从以派拉特父亲和老太太瑟斯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的口中,年轻一代黑人了解到本族群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身份价值,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莫里森运用“超能力”作为媒介系连并模糊了“死亡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界限,显然隐喻着对黑人文化传统超越生死永远传承的期望。在白人种族社会中,未能传承传统精神文化内核的年轻一代黑人成为丧失身份认同和思想意识的隐形人,黑人族群只有继续传承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自信,才能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莫里森也曾说过:“一个人如果扼杀了祖先,就等同于扼杀了自己。”[8]73以“超能力”作为媒介系连“死亡空间”和“现实空间”也是莫里森对黑人族群以何种方式才能摆脱自我认知困境的探索。
(四)展现黑人困境的“音乐空间”书写中媒介的隐喻功能
《爵士乐》中黑人夫妇乔和维奥莱特满怀着激情和憧憬追随美国20世纪初的移民大潮离开南部农村到北方大都市寻求庇护和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遭遇了新的困境:多年来他们从未被任何企业或公司接纳过,维奥莱特是收入不稳定的美发师,乔成了地位低下的化妆品推销商。而他们曾经的创伤记忆使他们在城市里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维奥莱特因为潜意识里拒绝成为像自己母亲那样“未尽养育职责”的人导致在婚姻生活中不断流产;从未获得母爱的乔试图用情人多卡丝的依恋来弥补这一切,甚至因为怀疑多卡丝移情他人而枪杀了她。经济困窘、种族问题、遭受歧视以及暴力是他们的生活常态。莫里森在《爵士乐》中描述黑人移民在北方城市的上述生存困境时,首次尝试用模仿爵士乐结构的“音乐化的语言”作为媒介,将读者直接引入爵士乐的“音乐空间”,读者在阅读时仿佛沉浸在爵士乐时而低沉、时而激昂的旋律中。这是一种对“音乐空间”进行书写的全新方式,在莫里森的匠心安排下,爵士乐的独奏、和声以及呼唤应答等内在特点通过文本语言得以呈现: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恰如爵士乐中的独奏,叙述者的讲述犹如爵士乐中的和声;主要人物在独白中的自问自答构成独奏内部的呼应,叙述者在讲述中的自我问答构成爵士乐中和声内部的呼应。首先,莫里森以“音乐化的语言”作为媒介在文本中书写爵士乐的“音乐空间”,隐喻着对身陷困境的黑人移民拥有和爵士乐一样的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20世纪初的美国黑人移民与同一时期兴起的爵士乐在发展轨迹上有着诸多的重合,当时发源于美国南部黑人族群的爵士乐开始将发展中心向北方大都市挪移,在挪移的过程中,爵士乐不拘泥于美国黑人族群的经验,不断变革,最后成为几种不同历史、音乐、文化的因素融合在一起的产物。尤其是非洲音乐元素和欧洲音乐元素在爵士乐中相互渗透、相互兼容,为美国黑人移民和白人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镜像化”的未来。[14]爵士乐对新旧世界和黑白种族的二元对立状态的解构,正是莫里森期待黑人族群在未来可实现的一切。其次,莫里森在挪用爵士乐元素、模仿爵士乐技巧的同时,还试图使作为媒介书写“音乐空间”的“音乐化的语言”具有爵士乐的“即兴”灵魂。所以文本中叙述者的讲述里充斥着对当下感受和判断的随性阐发,恰如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我在想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他想象得那么糟?”“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还会有别的想法。”“我发现自己是有多么不可靠。”[14]33由于叙述者在探索事件真相的过程中通过“即兴阐发”频繁地推翻之前的判断,所以叙述者“我”的声音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再是不可质疑的。[14]47莫里森试图用具有“即兴”灵魂的“音乐化的语言”解构叙述者“我”的权威性,从而身体力行地示范“既定概念中的权威思想和见解也并不代表绝对正确,一切都有待实践的检验”。继而隐喻黑人族群要有勇气和信心解构在权威的白人意识形态下被建构的旧身份。最后,爵士乐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流行度和被接受的广泛性,而在于它的可塑性。莫里森以“音乐化的语言”为媒介书写“音乐空间”,模拟爵士乐的旋律表达黑人族群的悲伤、喜悦、梦想和期待,还隐喻着黑人族群应该坚信他们的未来也是具有可塑性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个人命运和种族的前景如何,无论过去的记忆多么折磨我们,都不能妨碍我们要求一个未来。”[15]
结 语
美国黑人族群作为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促使莫里森一再对空间的本质进行思考和探索。莫里森的空间书写在展现黑人困境的同时,通过“媒介”将读者从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空间导入在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生产出的隐秘空间,并借助“媒介”的隐喻功能促使人们意识到代表白人话语和权力的空间对黑人所实行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迫害,以期激发黑人族群有意识地积极反抗,最终基于本族群的文化传统重构差异化空间。正如莫里森在谈及创作动机时认为,文本对读者认知世界应具有“启迪性”,应能“开启一扇门,指出一条路”,这样的文本才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