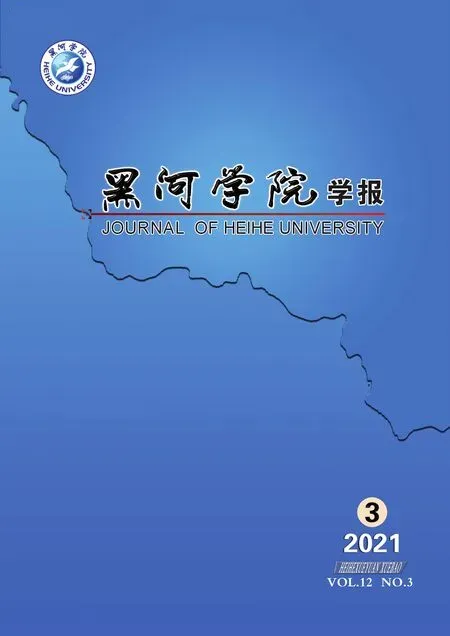文化分层视域下民间文化的再创作
——以《白蛇:缘起》再创作为例
2021-01-16向俊
向 俊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21)
民间文化是“一定群体内自发流传并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产品,又被称为民俗文化、乡土文化、口承文化。”[1]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化在整个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里,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影响,始终进行着不断再创作的过程。2017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阐释了民间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中应起到积极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戏曲、谚语等是民间文化的重要代表。近年来,不少民间文化在再创作过程中,以现代化的艺术形式,并将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呈现出来,产生了很强的社会影响,如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民间文化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达和艺术呈现,民间文化在这一传承和再创作过程中,口头与书面、讲述者与受众、个体与群体等各个层面的关系动态交融。那么以影视作品为代表,在民间文化再创作过程中,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各个层次的交互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对民间文化再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民间文化再创作怎样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现代化技术如何实现民间文化再创作的多样化表达和呈现?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民间文化再创作中的文化层次关系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和社会阶层密切相连,在阶级社会里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主流文化形态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文化的群体差异日益显现。关于文化分层理论,美国的人类学家罗伯特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的理论,认为“乡民社会存在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由知识阶层掌握的书面文化传统,一种是由底层民众创造的口头文化传统”[2]中国近代文人将中国文化分为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和底层民众的俗文化,与之相似,李亦园先生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层的士绅文化”和“下层的民间文化”,认为两者互动互补;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上层的士绅文化可看作是精英文化,下层的民间文化即为底层文化。钟敬文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讲,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中层社会文化,即城市人民的文化;底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3]高丙中先生按照群体差异划分,将文化分层表述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并认为各文化层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区别主要在于创作规律和目的,“精英文化是自律性文化,强调创作者的反思和自觉,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教化和集体规范;大众文化是他律性文化,遵从市场规律的作用,目的在于盈利。”[4]而民间文化是自发的口头文化,具有自给自足的非功利性。
民间文化在再创作过程中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从历史发展来看,民间文化汇集了底层民众的集体意识,经由传播,部分优秀文化渐渐被更为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进入大众文化层,之后经过精英阶层吸收、提炼、完善、再创作,成为原创性文本,进入精英文化层,再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再创作后的文化有意识地去引导、规范广大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化原有的意识内容与再创作后的文化意识内容必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同,而最终决定民间文化原有意识内容存在与否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的规范与引导,以及大众文化的认同与接受程度。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虽有互通融合的一面,但社会阶层的差异,使得各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引发了文化内在冲突,也影响着不同文化的生命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生命力一般最为持久;大众文化受众较广,与精英文化联系与融合更为密切,能够形成书面文本,所以,也具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而民间文化的文本形式和创作特点使其生命力较为短暂,并更易受精英文化规范与主导影响,精英文化甚至直接决定着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当前,精英阶层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民间文化的价值也得到了极大的肯定;随着全民教育普及、现代化技术发展、网络技术应用,尤其是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民间文化创作也呈现出个体化、自觉化的一面,由感性呈现到理性表达,民间文化既自觉地向精英文化融入,也直接被精英文化肯定、接纳、吸收、再创作,然后反馈给广大民众,这既有助于民间文化的保护和生存,也使得民间文化在再创作的过程中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发展。
在当前的影视作品再创作过程中,民间文化是其再创作的重要来源,民间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戏曲等为影视作品再创作提供素材和资源,如《白蛇:缘起》的叙事文本来源于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白蛇传》。然而在影视作品再创作过程中,精英文化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当前,因制作成本高、流程复杂等原因,影视作品的开发和运作,一般都是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影视作品再创作时,精英文化的价值理念引导、聚合、规范着民间文化意识内容,不仅区别于民间文化原生状态,甚至内在的核心价值理念完全是精英文化的意识内容。大众文化虽然有广大的创作主体来源,但从影视作品再创作来看,大众文化更多地是作为受体和反馈层,既要接受精英文化的引导和规范,又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规律的制约。民间文化内容经由市民改编、再创作形成小说、戏剧等大众文本,发展为大众文化,被广大民众接受,其中一些优秀的大众文本被广大民众接受,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此大众文化源于民间文化,对其再创作的过程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对已经有广大受众基础的民间文化进行再创作后,受众对其再创作的影视作品内容更能产生认同感。这种不同层次文化互通、交融和再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广大受众基础的差别,使得对再创作后的影视作品接受程度有显著差别,在不考虑作品本身制作质量、发行推广力度等情况下,参照豆瓣、猫眼等评分,可以看出同样是对民间文化再创作的作品,受众对《小门神》《大鱼海棠》等接受和认同程度较低,而对《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接受和认同程度明显更高。
因此,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网络发展和电子媒介的参与,在民间文化表达和呈现更为丰富的同时,影视作品再创作,由精英文化为主导和规范,可以更为直接地吸纳、改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在其中既可以作为创作主体对民间文化进行改编、再创作为精英文化的再创作提供素材和支持,而更多的是作为受体对其再创作进行反馈和评价;精英文化层直接主导了与大众文化层、民间文化层的互动,并使大众文化层与民间文化层原有的自发互动,渐渐转变为由精英文化层主导和规范下的受控互动。
二、《白蛇:缘起》中民间文化再创作
基于影视作品再创作中文化层的互动关系,以2019年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为例,分析典型影视作品中文化层互动对民间文化再创作的影响,以及民间文化再创作的发展路径,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影视作品中对民间文化的再创作。
从影视作品所选取的民间文化历史溯源来看,民间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经由大众文化层、精英文化层的再创作,民间文化内容往往是大众文化层、精英文化层再创作的基础。《白蛇:缘起》中白蛇的民间传说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唐代《博异志·李黄》中已有关于白蛇女妖的文本记载;明末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一叙事文本,奠定了后世白蛇故事的雏形,冯梦龙本身就很推崇“民间性情之响”的民间文化,搜集整理大量民间白话小说,以文学实践彰显了民间文化价值,这既反映出文化精英对民间文化的接纳和再创作,也可见民间文化在大众文化层、精英文化层再创作中的基础作用;近来年,影视作品中白蛇爱情传说的叙事文本内容是以20世纪50年代田汉改编的京剧《白蛇传》为基础的,白蛇的形象历经了由妖怪到女性的转变,其叙事文本也不断丰富,由妖怪纯粹地给人带来灾祸到女妖魅惑男子的志怪故事,再到白蛇与许仙真挚的爱情传说。《白蛇:缘起》中的白蛇传说本身是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内容的,而白蛇这一民间传说,在后世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其的再创作过程中,不仅增添了许多新的故事文本内容,也融入了在社会变化发展中大众文化层与精英文化层的价值理念,有大众对纯真爱情的渴求,也有精英文化阶层对挣脱封建束缚的思考,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具有资本、技术密集型特点的影视产业,影视作品的开发与运作一般是由精英阶层主导。《白蛇:缘起》的整个开发运作过程资本投入巨大,涉及制片、编剧、导演等专业人士众多,由精英阶层有意识地主导,远非民间文化创作可比。从现代媒介技术的运用来看,《白蛇:缘起》能够得到广大受众接受和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影视作品艺术效果的高水平呈现。相对于传统的口头与文本内容,影视内容通过视听结合更富有表现力,更容易吸引受众,对受众的参与度要求也更低。而且相对于普通民众,精英文化层引领现代媒介技术,能够调动更充足的资源,创作更具有艺术表现效果的作品。
《白蛇:缘起》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大众文化层与民间文化并未直接互动,而是在精英文化层主导下的间接互动,大众的观影体验实际上只是对创作完成后的影视作品所建构的文化内容的把握,而这种已完成建构的文化内容,本身就是精英文化层对民间文化再创作后的新的内容,而且《白蛇:缘起》能够得到广大受众接受和认同的根本原因则是“创作者在动画改编过程中对故事主体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现代性的重构”[5],这也正是精英文化层主导的对民间文化再创作中价值理念的引领与规范。影视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作品的价值生成,当前精英阶层关于文艺工作的政策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再创作本身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被广大民众接受和认同为前提,并以弘扬民族和时代精神、引领文化发展方向为目标的。
白蛇这一民间传说的长期流传为白蛇故事本身积累了大量受众,在大众文化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如何将故事文本受众转化为影视作品受众,一直是精英文化层进行再创作的关键,《白蛇:缘起》以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原型意象,以《捕蛇者说》为故事背景,创作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文本。20世纪50年代以来,白蛇传说改编的多部爱情主题影视作品,大多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追求和对封建专制势力压迫的反抗,这种主题表达背后就有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白蛇:缘起》在再创作过程中,结合当前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层关切的意识内容,在精神内核上进行新的价值呈现,发掘神话传说的现代意义。从爱情主体的叙事表达来看,《白蛇:缘起》诠释了精英文化层对新时代女性意识和价值的思考,在传统白蛇故事中,白蛇作为妖,是与人对立的存在,其与法海斗法,人妖爱情不为天地所容,隐含着自由与抗争的价值内涵,《白蛇:缘起》则明确表达了自由与抗争的主题,白蛇多次提到“不想做但是又不得不做”,与国师等对抗,人妖冲突等,而阿宣表示“就算人生命数有定,也要活得自在”,可见,其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作品在探讨自由、人性的过程中,借由对白蛇形象的重构,表达了新时代的女性意识和对女性价值的思考。不同于传统白蛇故事中的形象,《白蛇:缘起》中白蛇是失去记忆对人怀有戒备的女子,没有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一直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在与阿宣的互动中很长时间都处于被动的一方,而阿宣则表现出诸多优秀品质,在感情中主动向其靠近,甚至奉献和牺牲,这种叙事安排,“更多注入了现代女性关于爱情的某种期待。”[6]现代女性在爱情自由的价值理念基础上,对与男性地位平等、权益对等有了一定要求,尤其是在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要求男性在感情中也要有一定的付出和牺牲,所以,多次拯救白蛇的阿宣是带有这种女性主义要求的男性符号,而影片全部叙事视角都是以白蛇为主体,更反映出这种现代女性意识。这种新的价值呈现既有精英阶层对文化发展方向的自觉引领,也是对大众文化层时代精神与价值追求的客观反映。
从对民间文化再创作的价值引领与规范、构筑现代性精神内核看,《白蛇:缘起》在明确表达人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追求和面对压迫时的反抗同时,更进一步地探讨了个体的成长和自我实现,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现代社会个体自我意识增强,大众文化层、民间文化层中有了越来越多对个体自我发展、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思想意识,《白蛇:缘起》中的价值呈现是精英文化适应当前大众追求个性解放、个体自由,以及个体实现自我的思想需要的。影片通过叙事主体白蛇的失忆到恢复记忆,个体意识复苏、觉醒到冲破束缚的过程,去表现白蛇的成长与自我实现。故事开始时白蛇就遇到成长难题,历经五百年修炼而不能得道,不能得道意味其作为妖始终在天道的束缚下不得自由,无法实现自我,而后白蛇刺杀国师,是因蛇王命令被迫执行,被打伤失忆后,失去对自我的正确认知,被动接受阿宣和命运的引导。在阿宣的帮助和影响下,失忆后的白蛇渐渐有了新的自我意识,对人与妖、自我与天道等都有了新的认识。恢复记忆后,这种新的自我意识促使其做出不同于以往的自我选择,比如,相信人类,对感情开始主动等。之后白蛇因走火入魔化为巨蟒造成灾难,此时白蛇又再次陷于无法自主的困境,在阿宣的帮助下,才又恢复理性,找回自我意识,最终战胜国师、蛇王,在阿宣自我牺牲的激励下,勇敢地冲破对天道束缚的畏惧,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确立了要去找到阿宣转世的目标,努力去追寻、实现自我价值。白蛇由畏惧天道、屈从于命运到最后战胜自我、勇于抗争,不畏天道而寻求自在、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了个体的成长和自我实现。
《白蛇:缘起》在表达个体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觉醒、自我肯定、抗争与追求自由的同时,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以精英文化中主流价值理念进行引领和规范的。影片开始旁白背景介绍:“晚唐末年,天下将乱,妖魔鬼怪,出没人间”,预设了人与妖的矛盾,两者是完全对立的状态,而在天道的立场,人是善的代表,而妖是恶的代表,随着叙事的进展,借由阿宣的话可见,善恶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族群并非一概而论,“人间多的是长了两只脚的恶人”,甚至像善与恶可以互相转化一样,人与妖之间本身就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种价值理念就是精英文化所引导并规范的,也符合现代主流价值范式,无论出身、样貌、外在评判等,只要有主观从善的意识,并为之付出努力去行善事,皆可为善。在这种预设下,真正的矛盾主体其实是善与恶的矛盾,而影片中恶的代表妖族是蛇王以及为恶之妖怪,人族是国师及其手下,白蛇和阿宣可以看作与恶抗争的善的个体,这为他们后来行为选择过程中产生的与本族群表面的矛盾冲突奠定了逻辑自洽,比如,白蛇接受并献身给人类阿宣,以及阿宣主动选择变成妖怪。叙事中内在的善与恶二元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善战胜恶的价值倾向本身就是民间文化中一直所具有并倡导的。影片中所展现的外在矛盾冲突包括大范畴的人与妖,妖与天道;中范畴的蛇族与村民,蛇族与人族统治阶层,村民与人族统治阶层;小范畴的白蛇与国师,白蛇与蛇王,白蛇与蛇族,阿宣与国师,阿宣与村民,阿宣与蛇族,白蛇内心挣扎等,这些繁杂的矛盾冲突通过内在善与恶的矛盾串联在一起,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以此价值内核展开的。在族群内部,国师与其手下不仅有恶与更恶的矛盾,影片还展示了这种恶在族群内部对族群其他成员的吞噬与毁灭,比如,蛇王毁灭蛇族,国师压迫下属与村民,以此反衬善的价值和可贵,阿宣拯救村民,为善的个体才可能促进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与白蛇由妖到拥有人性之善复杂的内心冲突转变不同,阿宣无论人或妖始终是善的个体代表,也是在阿宣的鼓励下,白蛇才坚定了为善的本心,勇于向本族群内为恶的蛇王抗争。作为善的个体代表白蛇与阿宣,对本族群不为恶的成员是想要去帮助和拯救的,比起阿宣对待自我身份更加豁达自在的态度,白蛇对待自己为恶的族群在很长时间仍是不愿抗争和背弃的,蛇王毁灭族群的举动,使得白蛇不用进行两难的抉择,直接与蛇王抗争,其实是将善与恶的冲突直接化、简单化了,而阿宣为妖后面对村民的抵触与苛责仍对其怀善意,尽力拯救,才是影片主题的诠释与表达,人与妖看似矛盾,实质却不然,善与恶、人与妖可以转化,天道则可以看作是自然规律,为恶则有天道所罚,所以,影片最后,村民冲破原有旧的意识和族群所限,选择帮助作为妖怪的白蛇和阿宣,使其没有神形俱灭,得以继续存在,这也正是天道对为善的肯定。阿宣自己的理想追求是希望和白蛇一起远离族群、世俗纷争,寻找到其自在逍遥之地长相厮守“八荒四海,总有容身之地……做一对逍遥妖怪”,但在饱受压迫的无辜村民陷于危难之时,阿宣仍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我,这才是在繁杂的矛盾冲突下影片要肯定的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个体的利他意识,个体为他人为社会群体奉献和牺牲,社会群体以及天道对个体为善的肯定与回馈,既是民间文化一直倡导的价值理念,也通过精英文化的接纳、吸收、再创作对社会主流价值理念进行引领和规范。
《白蛇:缘起》不仅在叙事文本、人物形象、主题价值等方面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作,赋予了其全新的内容,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可以看到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整合、吸收和再创作。电影是一项综合性艺术,通过光影、色彩、画面、音乐等来呈现,专业技术要求较高,并且需要专业人才共同协作,才能呈现出好的艺术效果,这是民间文化层创作所不易达到的,而《白蛇:缘起》在艺术表现方面,明显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更为关注,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影片在光影、色彩、画面方面,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并将道家思想融入到这种艺术呈现中。影片开篇以黑白为主色,用水墨来渲染人物,用黑白两色表现白蛇内心的隐秘,这种水墨渲染的画面,与道家崇尚朴素自然的理念“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相合,而与蛇王、国师等反派浓墨重彩的形象塑造不同,白蛇黑发白衣,装扮也是在朴素无华中尽显清丽秀美。
影片还运用了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中的留白手法,白而不空,虚中有实,形成空灵的境界。影片中大量空镜头,比如,阿宣采药的山峦,云雾缭绕;白蛇与阿宣乘舟途中,水天清碧;二人数百年后重逢的西湖,山色空蒙,风光迤逦等,光影交错中的留白可以激发人的无限想象,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道经·第十一章》)。可见,其空无的价值。水墨朴素之美与留白空无之意境都暗含道家美学,这种道家的美学观既蕴含着对不拘于世俗繁华、寻求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也是将传统民间文化艺术融入到现代影视艺术的再创作。影片还通过具有特定符号与意象的道具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进行再创作,贯穿叙事文本始终的碧玉簪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发簪自古以来是女子用来固定发髻,并加以装饰的一种饰品,但随着时代发展,发簪本身被赋予了许多文化内涵,不同材质,不同纹饰的发簪反映了不同的民间传统文化。韩愈称赞桂林山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送桂州严大夫》),可见,碧玉簪本就是美的象征;白居易《长恨歌》中发簪是象征爱情的定情信物;影片中白蛇所用的碧玉簪则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在故事设定中,碧玉簪是能够吸收法力的宝器,在叙事过程中多次推动影响着情节发展,影片最后既发挥了拯救阿宣并保留其魂魄与记忆作用,也成为数百年后二人再次相逢的道具。碧玉簪刺杀过国师等恶徒,伴随白蛇的成长,见证了白蛇与阿宣的爱情,既展现了白蛇外在之美,也通过白蛇的成长表现出其内在坚毅、善良、忠贞的品质,还成为白蛇与阿宣忠贞不渝爱情的象征,这种丰富的意象表达正是对民间文化再创作的体现。
以《白蛇:缘起》为代表,可以看到当前影视作品在对民间文化的再创作中,仍是由精英文化层从文本叙事、人物塑造、主体价值选择、艺术效果呈现等方面对民间文化吸收、规范和再创作的。大众文化层为白蛇传说故事积累了大量受众,形成潜在的市场,这也是作为影视创作主体的精英文化层所考虑和选择的,虽然影视作品为大众认同和接受是由作品本身创作的品质决定的,但为了取得更多受众关注与接受,影视作品往往也会运作和营销,吸引市场关注。从民间白蛇传说故事来看,经过历史发展,故事丰富,甚至有多次的影视改编创作,其叙事文本早已完成了从民间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为了打破广大受众的刻板印象,使人们对此民间故事有新颖的体验,在对民间文化再创作中,影片建构了新的时空背景、人物形象,融入了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在迎合又引领大众审美趣味与价值追求中进行影视创作。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变迁极大地加速了民间叙事现代传承的进程,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多样化表达”[7]。影视技术作为一项现代技术,在民间文化再创作中发挥极大的优势和作用,相对于口头与书面表达,表现力更强,并能够使民间文化以多元化的形式展现给人们,使受众对民间文化有更真切的感受。但影视创作过程也存在创作主体与受众之间互动不足,即使在当前网络、多媒体等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受众可以通过线上弹幕直接对观映的影视作品评论,反馈仍有滞后性,往往无法对已完成的作品产生影响,而市场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续作品创作,所以,影视作品创作更多的是从民间传统文化已被大众知晓和接受的范畴中汲取资源,对当下在现代技术促使下愈加个体化的丰富的民间文化仍有一个不断认识、接纳、删选、再创作的过程。“民俗学范畴要寻找的首要问题,是特定的文化财富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生成出来的精神互动的特殊形式”[8],现代技术丰富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促进了各层次文化的融合交互,借助短视频、新媒介等技术,越来越多的民间影视创作涌现出来,展现出民间文化个体化创作的自我表达,而精英文化在民间传统文化的再创作与现代传承方面仍起重要作用,对现代价值理念进行引领和规范。
从《白蛇:缘起》中,可以看到民间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可以看到民间文化再创作所展示的更多精彩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与现代技术更加广泛的应用,民间文化能够在精英文化的引领与规范下迅速吸收时代精神,创作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并渐渐成为国家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层次文化一起构筑当代中国文化,并在时代发展中通过不断的再创作焕发新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