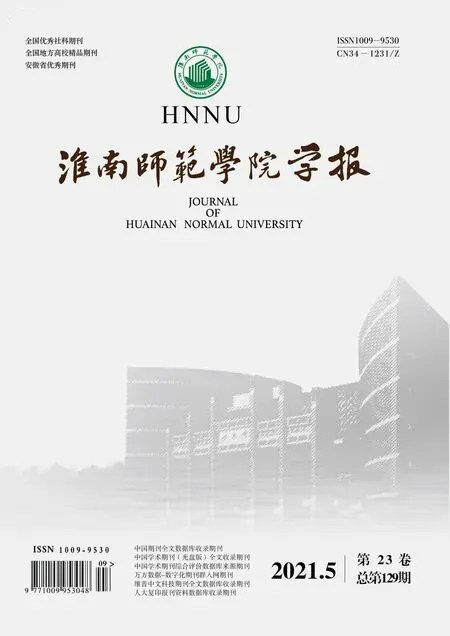《沂蒙山小调》的播布:文本价值的稳定、耗散及敞开
2021-01-16王文营
王文营
(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任何符号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是“发出者自我意图的抛出物”。符号文本形成了一定的意义形态,具备了文本身份,文本就有了意义的多种指向可能。“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仪式/文化领域的符号表意,能指并不需要明确指向所指,而是独立形成价值”[1](P93),也就是说,能指的意义隐含着自身的规范性,尤其是一定的约定俗成,所以任何文本的出现往往都会不自觉地与自身存在的文化连接起来,形成意义的文化构型,也就是“型文本”。“型文本”是指符号的文化背景的显性文化框架,比如《沂蒙山小调》凸显的民歌小调的文化符码,随着身份、历史、文化、地域的诸多变化,文本本身意义有定式,耗散和衍生,符号文本的播布自然在“型文本”之上出现了伴随文本:前文本、生成文本、解释文本等诸多变化。当前,关于《沂蒙山小调》民歌原型、艺术演奏风格与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取得不少成果。本文欲从符号文化学和口头诗学视角探讨下其文本意义的固定、耗散、创生及仍然存在的敞开性问题。
一、《沂蒙山小调》文本的定式来源
《沂蒙山小调》的出现有很强的意图命意,是抗大文艺战士李林、阮若姗在沂蒙山区为进行抗日宣传针对封建道门会黄沙会而创作的,有去巫化和对民众进行精神启蒙的价值内涵:“当时歌的名字叫《反对黄沙会》。歌词分八段,内容主要是控诉黄沙会的罪行,揭露黄沙会的阴谋。曲调是李林根据山东逃荒到东北的卖唱人所唱的曲子加工整理而成的。”[2](P198)黄沙会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迷信色彩很浓厚的民间结社组织,他们自立主神、烧香跪拜,念经吞符、学功习武,甚至为恶势力所利用,用暴力和共产党对抗,蚕食抗日根据地,而歌曲的指向是分化蒙昧群众,影响百姓,命意指向较强,故形成歌曲的召唤结构。民歌原型是“卖唱人所唱曲子”,符合民众的期待视野;其地域域境为“沂蒙山”,为当地群众的栖息安居之所;直指命意,是用科学求真精神宣谕黄沙会的荒诞不经:“硬说俺那个身子能挡枪炮”“烧香那个磕头哎骗钱财。”《沂蒙山小调》的播布在解放区觉悟了的民众中流传深远,文字也多有变迁,如添加“光吃军粮不打仗,一心一意要投降”“勾结鬼子来‘扫荡’,奸淫烧杀丧天良”等语。音乐有自己的基质,音乐的形式一旦完成,基本乐章会统御艺术的全部内容。正如苏珊·朗格所言,“当词进入音乐之后,他们便不复是散文与诗,而成为音乐的元素”[3](P155),音乐的旋律、情感、节奏在声音的复播中造成强大的构想力,承载着艺术共有的生命意蕴和情感体验。音乐原则统治了歌曲的全部,应该说,符合音乐基质的歌词内容可以自如地进入演唱之中。在口头音乐的传布中,演唱文本和文本以外的现实语境构成了文本的真正意义。
《沂蒙山小调》文本的产生是偶然性的存在,但它的播布我们不可忽视其文本的定式。所谓定式是指文本隐含的固定程式,虽然《沂蒙山小调》的原型并没有确指,但是据民间小调的整理创作无疑这种程式构成了《沂蒙山小调》的定式:很强的民间音乐调式。民间音乐调式的播布,是“艺人与听众,共同生活在特定的传统之中,共享着特定的知识,以使传播能够顺利地完成”[4](P20)。《沂蒙山小调》体现了口头诗学的互动性、共时态的美学意味。定式属于传统,当地人用这种习惯了的小调传唱自己日常的劳动、生活与情感,“程式的宝库给传统的歌赋予了同质性”,这既嵌合了民众心理,也确证了其生存习惯,地域、民族、文化、方言、社会政治等存在会体现于定式中。当创作人对定式的积累不同,定式会有一定的更新性,“程式和细胞一样有再生的能力”“一个活态的口头传统,完全可以吸收新的时代的内容”[5](P110)。在民间小调的定式下,歌词其实同样存在定式,那就是民歌意味,也就是表达的起兴和重章叠唱式样。沂蒙山小调的播布,“反黄沙会”和“反伪军”意义的删减和自然耗散并非是因其事件的具体化和暂时性,而是违背了口头诗学的规则:“掌握着‘程式’的词汇,便能够运用口头传统习语流畅地讲述故事”[4](P65),“反对黄沙会”的传唱仅仅保留了两段,只剩下了开始的“山”“景”起兴的句子,就是因为它符合民间传统,属于当地自然风物;而后面的“在”,是政治性话语明显的“在”,而非“民间性人”(确指为“百姓”或“当地劳动人民”)之“在”,并没有体现出普通百姓民间生活的日常存在。定式允许更新,但脱离了语境化的存在会自然受到制约;不符合定式,其价值性的播布就会被耗散掉,而无法恒久性地存在与播布。变化是限度之内的变化,不能脱离定式,也就是必须延续高度类型化、程式化了的定式。
《沂蒙山小调》的内涵整体是作为政治的工具——“音乐武器”而存在的,这是战争域境形成的,无法绕开;从口头美学的角度思考,《沂蒙山小调》在民间音乐定式下,其价值内容应是民间的“山”“水”“人”的融汇,但“民间事”缺失,在起兴之后,没有“我”(民间人)主动的“在”;而是“你”,一个指令性的被动行为:“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说,《反对黄沙会》强大的生命力来自民间音乐的定式,地域性的山水风情起兴,让歌词有了基本的格局,有了闪亮的开始,但因为强大的政治命意,无法在“民间事”上作更好的挪移,意义的流布受到了制约。
二、《沂蒙山小调》文本的播布和耗散
约翰·迈尔斯·弗里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一书中曾谈到,一个歌曲的程式化程度越高,作品越具有口头性,流传性会越广;程式来自传统,“口头诗人并不追求我们通常认为是文艺作品的必要属性的所谓‘独创性’或是‘新颖性’,而观众也并不作这样的要求”[4](P1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沂蒙山小调》歌词定式的残缺性和演唱中的修复功能。所谓“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事,也就是由“物”兴“事”,有所“兴寄”。所谓“事”必须是和“物”(“蒙山沂水”)密切攸关的“民间事”,沂蒙山小调起兴于“好山”“好水”,但“民间事”缺失。“黄沙会”或者“伪军”可以作为“民间事”,但歌词中“百姓”均非“主动者”,而是受动者,自然“民间事”也必须和兴“物”匹配;《反对黄沙会》的施动者是政治性符码:“革命者”,是超越“民间”的意义存在。写物与附意、兴言与切事是意义对称结构中的自然关联,“‘兴’通过所命名或指涉之物,来完成人与神之间的往来,亲证了世界‘看不见’的部分”[6](P36),它是“物”“事”的自然匹配,和谐无间。
《沂蒙山小调》的内容缺少和谐的“兴事”,这也是其内容由“打黄沙会”向“成熟”“丰收”迁移的内在原因。“事”是并不显豁的“劳动物事”:“高粱红了”“谷子归仓”。但已经隐含了一个主动的“我”的“在”:农人劳作丰收。虽然这个景观有些陈旧,但符合定式,甚至修复了起兴。其命意意图从“启蒙价值”向“赞美风情”转化,但转化并不淹没政治性的话语存在,这既是历史的存在命意,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弥漫:“共产党好”,当然后来歌颂伟人的符码更为明显:“毛主席领导的好”。在文本定式修复的同时,也带来了命意的潜在的耗散:其一是好山好水好幸福,这是韦有琴的演唱指向的价值选择;其二是好山好水喜洋洋,源于一种精神价值的引领:共产党好。这是后来较为普遍的价值指向。自然意图的过于明显会造成情感的虚空和意义的不自然拔高,这是文本价值无法绕开的话题。歌词的无限衍义也会淘空文本的真实存在,它是革命歌曲,意图命意是:“抗日”。歌颂伟人的符码一方面让歌词直白化,同时也在耗散它的真实命意和民歌精神。抗日性的历史存在被过于强大的颂圣意图所遮蔽,这也造成了历史真实命意的变迁。
后来的演唱者郑绪岚、彭丽媛保持了歌词的起兴完整性,也保持了民歌精神:好山好水喜丰收,体现出沂蒙山的山、水、人自然融合的品质,去掉了过强的政治性话语,强化了民歌的乡土气息。但文本应该存在的人事命意也被消解了,无法寻觅歌词存在的实在空间与时间,甚至前文本的“抗日”符码也了无痕迹。《沂蒙山小调》的文本成了可以放在从远古到今天任何一个时段的共时性存在,仿佛成了永恒的民谣。另外,虽然说修复了民歌口头传唱的托物兴事,但其“事”,更大程度上,并非“事”,更靠近“象”,甚至它就是“象”:“高粱红”“豆花香”“万担谷子”,和前边的“青山”“绿水”“牛羊”保持了“象”的一致性。而“叙事”并不存在,因为叙事最基本的存在是。“叙述的对象是有人物参与的变化”[1](P324),更何况“象”意,从美学演变看,不仅仅指自然景物和其它实物,也涵括民俗风情和生活景观。这样看来,“山水美”和“大丰收”虽然契合了民歌调式和民俗场景,但“人事”或者说“民间事”仍然是缺失的,内容全部只是起“象”,没有兴“事”,情感的真实性和具体化存在仍然大受制约。音乐的情感是借助简单的经验,在重复和变化中迸发出内在的力量,歌词“作为一种符号,或依循经验的状态、事物活动的态势来组合结构,或依循经验显形现象的过程进行,使我们在一瞬间瞥见实境,或一步步被带入经验生成的情状”[7](P211),虽然大规模或过于具体化的事件叙述并不适于歌词,但口头诗学的“民事”或者说“民间经验”却不能不存在,否则听众无法体验和接纳。
陈伯海先生认为,“感兴”体现了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和审美体验方式,它是一种生命论的美学观念,审美感兴是基于现实生活感受之上的,“是人的现实生命感受的转形与超越”[8](P101),所以具有民歌意味的歌曲往往透出很强的本然情趣和本真意蕴。故《沂蒙山小调》价值的欠缺修复并未达到言象尽意,既然无“民间事”,也就无法呈现来自民间的生命感受和当地本真的生活意趣。
三、《沂蒙山小调》本意的被遮蔽和未定性
《沂蒙山小调》目前的定稿是由当地政府确定的,在赞美“沂蒙风情”三段之后,恢复了“咱们共产党领导的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嗨哎喜洋洋”之句,在突出沂蒙山美之后,恢复其红色品质。这种定稿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存在意味:昭示沂蒙自然的“美丽景观”和历史中的“红色品性”。实际上《沂蒙山小调》的歌词文本并未呈现出完全的封闭性,还带有很强的未定性意味,它敞开着,期待着符合口头诗学的自然修复。
我们不妨抛开以上的艺术分析,从沂蒙“红嫂”的演变探讨《沂蒙山小调》应该作何种延伸和变化。沂蒙红嫂也是当地历史性的存在符码,“乳汁救伤员”为典型意符,最早的刘知侠的《红嫂》小说文本体现出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结合的状态;京剧《红嫂》则主题鲜明,把“红嫂”凸显为正面英雄形象;而新时期《沂蒙六姐妹》和《沂蒙》中的“红嫂”开始去魅,让“红嫂”复归日常,从平民视角呈现红嫂的人性化、生活化,地理景观和家庭存在都呈现出原生态的本真域境,在贫困化生活和残酷性战争的背景下,重叙“乳汁救伤员”“为亲人熬鸡汤”的场景,让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百姓生活的自然和沂蒙人人性中日常存在的仁义和温情,更体会到沂蒙女性在经受战争的精神洗礼之后所迸发出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牺牲精神,那是对和平的期待,更是母亲对炮火中儿子情感的自然挪移,也是妻子对山那边丈夫的深情凝视。红嫂的叙述从政治功利性的表演叙述回归日常精神的事实性叙述,让人复归精神的本源性和可靠性。有学者指出红嫂传播的存在价值:“不仅是新中国的符号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是“重塑集体记忆的”红色文化资产[9](P190)。从“红嫂”符号体察审视《沂蒙山小调》的价值缺憾:政治性的宣谕过于靠前,没有复归沂蒙日常精神的普通存在,没有还原抗日域境里沂蒙人真正的抗日情怀和抗日实相。真实的叙事依旧没有存在,其观念意识也不免有落伍于现实的陈腐气息。
首先,历史的存在叙述不能被淹没,仅仅把主题复归于对沂蒙山风土民情的赞美,未免让人有遮蔽历史的丰富和深度之感;仅仅把“共产党好”作为历史的“红色”意符,歌曲整体的价值则没有现实的落脚点,政教本位的刻意化游离了文本叙述的基本品格,也疏离了歌词本身的审美趣味。“抗日”的符码不能缺失,叙述应从政治性符码“党”向日常性符码“民”落脚,叙述在“党”之下“民”的抗日存在,这不是降低政治性的历史存在,而是恢复沂蒙人真实抗日历史的原初性和对其生活的认同感。洛德曾经谈到口头歌谣主题的基本特征:“程式化的叙述故事时,有规律的使用一组意义”,这一组意义是“个人的和文化的”[5](P35)。回归“民事”既符合民歌定式,也让主题有“一组意义”,这“一组意义”因是民间的存在而更符合民间的身份。“沂蒙民众的抗日”意符会像《沂蒙》中的红嫂价值一样,更能贴近日常的人心和场域,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惯性是特别关注现实的,即使是超越性的追求也往往不尽脱离现实人生”[8](P103),不考虑这一点就不能复归叙述的原生态,自然也无法摆脱真实历史的被遮蔽,叙述自然暴露出皮相化、表面化的演示性症结,美学意味也无法摆脱政治在前、历史在后的尴尬。
其次,叙述视角应转为百姓视角,应是“民”之情怀的抗日叙述。这种叙述是民间化的叙述,是日常存在的言说,“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却不去时时努力地表达他的生活”[10](P233),要恢复“民”的话语存在。过去的叙述是别人的叙述,甚至是被训教的叙述,自己的故事被无限搁置,甚至被别人代言,现在要恢复自己的叙述,就像电视剧《沂蒙》的叙述一样,恢复历史的真相。后来对《沂蒙山小调》的调式使用有了悲情和悲壮的意味,这是音乐情感的自然挪移;文本叙事的价值挪移则有待于后来演唱者的自然填充。从这个角度来看,《沂蒙山小调》还不能定稿,它应该继续敞开着,等待着后来者对文本价值的继续丰富。学人武装对《沂蒙山小调》传播的历史分析,也确证了这一点:“《沂蒙山小调》存在着不同的变体,至今仍尚难有一个‘定稿’。”[11](P34)
四、《沂蒙山小调》文本言说创生的可能性
《沂蒙山小调》文本的敞开是基于歌词非自足的言语品性,是交流性的叙说,隐含着“我对你说”的潜在结构。它的流传就是不断衍义的意指过程,有学者称是“块茎式传播”:虽然诞生在特定的时空,“却因在不同的语境中,被不同的歌众‘传唱’而复活,不同的时空会给它带来不同的语义场,会使它不断产生意义变异”[12](P197),文本在不同的时空被敞开,文本意义自然就不断地被挪移、耗散、变化和创生。
《沂蒙山小调》即使是沂蒙民众抗日情怀的叙事,也未必就成了封闭性的言说构型。“革命性”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沂蒙根据地解放区文化的特点,也是各种文艺叙述的主要目标。它是宏大的革命精神和民间审美趣味耦合的产物,但历史叙事从来不是机械单一的干巴言说,它受限于叙述人、叙述方式、叙述结构的各种变化,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隐含着话语的转义成分,虽然“转义是所有实在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阴影”[13](P1),但转义无疑就是对敞开文本的丰富和重新释意。首先是叙述者所处时代会让自己的叙事有了多种观念陈述的可能性:切合战争的首次创作演唱命意就是指用民间话语言说宏大的政治话语,指向民众启蒙和政治斗争;第二代的演唱,既指向社会新时代,又包含对领袖的崇敬赞美,有高蹈的意味;第三代演唱则指向了民间趣味和沂蒙风情,向现实化进行回归;今天的演唱更多是从现实视角回视地域独特性意味和历史的红色品格,这种意义转移是历史不同阶段的文化观念变迁形成的。演唱者不断解构既定意义的硬质化,标示出文本意义的可能性发展方向,保持着文本始终敞开的可能性。《沂蒙山小调》是以民间小调为根基的创作歌曲,但在更多的意义上,它被看作是山东民歌,它符合了民歌被不断演唱、改写、衍义的民间品性,“阐释的合理性力量就来源于事实在话语中被呈现的秩序和方式”[13](P115)。海登·怀特曾以不同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来思考文本的敞开性和文本意义因阐释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历史事件作为客观发生的存在似乎会保持陈述的客观稳定性,然而不同人的言说却使历史事件不断转义:米什莱把1789年的巴黎革命事件言说为具有浪漫情怀的罗曼司模式,是人神合一的梦想显现;伯克认为其是彻头彻尾的民族灾难,是一种悲剧式的堕落过程;托克维尔则将旧政权的衰退视为悲剧的衰退,幸存者从中获利。对历史存在的陈述似乎有多种可能性,仿佛有多少叙述者就有多少类型的阐释。但海登·怀特认为,无论多少陈述只是罗曼司、喜剧、悲剧、讽刺等四种结构模式的反复出现,这就是文本的固有定式。它们用隐喻、换喻、提喻、反讽的转移策略对文本意义进行解释、情节编织和意识形态还原,不同的叙述模式,就会造成意义的不同方向性[13](P80-83)。《沂蒙山小调》在情调上有了悲喜哀乐的不同挪移也是因为这种叙述模式的变化,其文本格局也在不断腾转挪移。最初的《沂蒙山小调》文本是呼唤“差异中的共性”,召唤和经验现实相匹配的真理性存在;崇敬性话语则是用再现方式呈现激越的英雄主义格调;民间话语的诉求是在恢复民间的话语本相,却消弭了文本的历史真理性。今天是在寻求历史语境、现实格局和历史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型,不同阐释策略和结构组合的偏向也造成了阐释意义的多向性和开放性格局。
《沂蒙山小调》的音乐诠释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唱法上涵盖童声、民族、美声、通俗和原生态;形式上涉及独唱、重唱与合唱;风格上更是遍及原生态、民族传统、西方古典、现代摇滚、爵士蓝调乃至说唱”[14],但其内涵价值的播布还存在着欠缺和滞后,如何恢复其历史的真实面目和促进文本意义的合理性、丰富性,尚仍在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