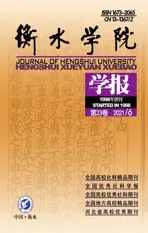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创建略论——以儒释道为中心
2021-01-16黄仕坤
黄仕坤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创建略论——以儒释道为中心
黄仕坤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哲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西化的对象化学术话语难以很好地诠释儒释道的精义,故亟待创建新的中国哲学诠释话语体系。首先,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新创的基础在于对道的体证,因为唯有明悟儒释道之本体才能给出恰当的诠释。其次,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创设应秉持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方向,即学者应深入把握中西哲学思想和话语的分际并会通彼此,从而既避免话语的误用又丰富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与话语。最后,新创的中国哲学诠释话语,应当虽具有逻辑的区分但又相融相即而为“诗言”,即应通过对“道”与“心物一体”存在的描绘而非简单的逻辑定义给出话语。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体证;中西会通;创建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建立起来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始终是建立在“以西释中”基础上的。发展至今,中国哲学研究的概念与思维方式都已深受西方哲学概念与思维的影响,以至于当我们自认为没有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思维或理论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时,也仍难以逃避“以西释中”的命运。借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西方的概念语言及概念背后的思维皆已成为我们研究、理解中国哲学时无法逃避的前视域。然而,中国儒释道之“道”及其开显的“心物一体”存在,皆难以被西化的对象化语言所定义,故以对立二分的概念诠释中国儒释道的智慧,无疑会造成“削足适履”之弊病。因此,为使中国古代哲思在当今被世人所理解,创建一种适合阐发中国哲学精髓的话语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而有意义。不过,这种话语体系的创建,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摒弃西方哲学话语,回归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这在当代的生存境域中已无法做到,而且难以达到阐发儒释道精义以为当代人理解的目的。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研究范式下,转动中国古代经典语词与当代学术话语,以创造一种适合阐发中国哲学儒释道智慧的话语体系。
一、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创建的基础
学界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创建已有不少探讨,其中以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1]和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2]最具启发性。与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作为方法论侧重操作性不同,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则强调,诠释话语源出于对儒释道本体的体验或领会。因为,主客二分的概念认知,难以把握作为非对象物的中国儒释道之“道”,所以关于道的言说须是基于对道的体证而进行的“诠释”。这意味着不仅中国古代儒释道的话语系统是非概念化的体系,而是先贤通过“体道”显示的“迹”,即是对道的揭示或拟议;而且还意味着中国哲学阐释话语体系在当代的重新建立,也须以对中国儒释道之本体的体悟为基础。
诠释话语的不同,根源于诠释对象的不同。中国儒释道之“道”皆超言绝相,所以三家皆强调通过体证来获得“道”的消息,进而才能对之有所言说。例如道家强调通过“虚静”功夫而明“道”,儒家强调“寂感”功夫以通“道”,佛家则强调“觉悟”功夫以明法性实相。其中,各家又因对“道”的体证不同,故所诠之“道”也不尽相同:道家突出道之“虚静”,儒家强调道之“刚健创生”,佛家则以“空寂”明真如涅槃。可见,儒释道皆是基于对作为本体之道的体悟给出诠释话语,而非本主客二分的理智认知进行对象化的语词制作。
就儒释道思想的发展史而言,三家话语的衰败与重建,亦与对道的体知、领会紧密相关。以儒家为例,先秦儒家通过天人合一的“观悟”,将《周易》之“天”体认为“道德之天”。发展至汉代,两汉思想家主要并非通过内在体证的方式冥契“天道”,而是选择通过知识的路径理解“天”,结果使“天”或“天道”被自然客观化了。至唐代李翱提出“复性说”,标志着内在“体证”之学在儒学的重新复归。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等承之,主张复归人之心性以体证天道,从而将天道贞定在人之“诚”“性”“心”中而重新贯通天人,最终建立起全新的诠释话语体系而开启了道学时代。具体而言,二程与朱熹通过体证将“道”诠释为“理”,建立了理学的话语体系;陆象山与王阳明等则将“道”收摄于“心”建立心学的话语体系,其中王阳明基于自身心体的明觉自证,对传统话语的转动与新诠尤其引人注目。同时,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的话语体系,皆体现在其对《周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文本的重新诠释中,并引发或表现为经典的转变①杨儒宾深入讨论了唐宋明儒者对部分先秦文本的重新诠释,及《四书》因此上升为新经典而与《易经》并称“新五经”的发生史。参见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版)。。清代,朴学的兴起虽有各种原因,但其重字义考据而轻义理体贴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儒学思想与话语在清代的僵化与失落。
近现代,中国思想话语体系的重新建立,亦与体道之学的重拾有关。如话语体系建立最成功的学者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皆对中国古代哲思有着真切的体认,从而获得了贯穿其话语体系的“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之道②此处论说参考了王中江的说法。参见王中江《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因此,这些现代新儒家学者都极强调体道功夫:熊十力强调“内省”而明“真性”道体[3];牟宗三以“逆觉体证”论良知心体的自知自证[4];唐君毅强调人基于自身的灵觉“感通”方能通达真实的生命存在或世界[5]。正因为有着对道的真切体悟,所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自觉地将儒释道的智慧与科学知识区别开来,以避免其话语叙述落入主客二分的知识范畴,而能蕴藏并传承着中国儒释道的哲思。
时至今日,中国学人已处在被西方思想革新的话语体系中久矣,因为“百年来已形成了一套新的中文学术语系,其中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方学术的概念语词,大大丰富了中文学术语言,成为当代中国人思考、论述的基本工具”[6]。然而,就西化的当代中国哲学学术话语而言,其主要是一种对象化的诠释体系。相应地,语言的对象化,其实又源自人之思想与存在世界的对象化。因此,语言的革新与存在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这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须获得对道体的领悟并抵达道开显的心物融通一体的存在,如此才能转动凝固的对象化语言,进而重建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正如温海明所说:“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体验就没有表达,或者说,哲学家只有有了体验,才可以说不可说之秘密。”[7]因此,没有对儒释道三家之“本”的体证作为根基,所有的言说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总之,对道的体证,是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在当代重新创立的基础。因此,当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须致力于在现实的生存中体证道并开显道,而非只专注于语词概念的逻辑解析,如此中国哲学的诠释话语体系在当代的创建才能获得基点与源泉。相较而言,加强中国哲学研究者字词考证的小学功夫,以为中国古代文本的解读打下文字学基础,或增强中国哲学学者对西方哲学思想与语言的把握能力,以避免西方哲学语词概念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误用等,皆是重要但属末节的问题。
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创建的方向
百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一直是“以西释中”,因此主要建立起了对象化的诠释话语体系。然而,与对象化的概念体系不同,中国古代儒释道的话语主要是非对象化的,即语词间不存在凝固的区隔,如道与物或心与物之间是相融相即而一体不分的。因此,若不加考察地运用西化的概念诠释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语词,将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程度的曲解。这在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建立至今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屡见不鲜。不过,虽然这种“反向格义”[8]的“以西释中”研究范式存在严重的问题,却并不意味着要拒斥中西哲学的比较会通。因为,犹如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的势所必然,在中西哲学合流已然深入实行并发展成为时势或大方向的当代,拒绝中西哲学的比较会通不仅无法做到且是背潮流的做法③陈俊民对中西融合之势有更多讨论。参见陈俊民《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定位与重构——〈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自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温海明则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可能离开比较哲学的视域和方法。”参见温海明《意哲学与当代作为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孔学堂》,2020年第4期)。。这会使中国哲学既不能补其旧弊并与世界学术话语接轨以更好地显发自身精义,又难以解决时代问题与挑战而立足于当世。因此,中西哲学的比较会通仍应是中国哲学话语建设的方向,但不应是单向且无自觉的“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而是以对道的明觉体证为基,通过深入的中西哲学比较会通明了了中西思想与语言的分际与相通处,而后“融合中西”、创造性地重建可以被世界学术界理解并认可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虽然明末清初因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中国已引发了中国思想与语词的变化,但是中国思想话语整个体系的转变,则始于20世纪初西方思想的概念与方法被大量引入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中作为分析或诠释的工具,这一过程同时与白话文运动相呼应。时至今日,无论日常语言还是学术话语,皆已充斥着西方的文化思想与语词。当代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可以说也已经转变为“英语式”的了。反之,这套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借用福柯的话说,就将无时无刻不规训着当代中国人。因此,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当代西化的中国语言体系,已成为我们言语、运思乃至整个日常生活不可逃避的前视域。以此之故,要想完全回到“以中释中”的话语体系,或建立“以中释中”的话语体系已不再可能。换言之,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在当代的重建,必然是通过承继已然存在的话语体系,并对之予以转化而开出新的话语体系,而非将两者直接截断。这既不可能,又无助于让中国哲学在当今为世人所理解。因此,当代中国哲学话语的重建,必然要走中西哲学思想与话语比较会通的道路。
另一方面,只有保持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交流,中国哲学才能更好地发现自身的价值、优势与不足并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发展自身④李承贵讨论了“西方话语”或“以西释中”对中国哲学研究及中国话语形成的利弊,并主张积极学习消化“西方话语”或西方哲学思想。此处之言受其论启发并有借鉴参考。参见李承贵《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及《“以西释中”衡论》(《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从而有效回应当世的存在问题以重新获得普世之价值。如宋代儒家受佛学刺激,而兼容佛道两家的思想与话语,取长补短并回应时代的需求,才开出道学的话语体系而重新确立儒学存世的地位与价值。就近现代而言,中国哲学话语建立成功者,莫不得益于西方哲学的思想视域,并反过来应对西方思想的挑战。如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学者,在各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建立起原创性话语体系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并拥有一套‘系统的方法’”[9]。这种系统的方法,即是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形成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西方哲学不仅在研究方法而且在思想上,对现代新儒家话语体系的建立都有极大功劳。这在“道德形上学、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外在超越、人生境界”[10]等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皆可寻得踪迹。
然而,由于以上诸位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选择比较会通的西方哲学对象与中国儒释道之哲思并不非常契合,致使西方哲学概念或研究方法在中国哲学话语的创建中被误用。如冯友兰以新实在论作为剪裁、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材料的视域;熊十力直接以西方哲学理性推定的实体界定儒家天道而使道对象化、抽象化或经验化以致有失落真道之危;牟宗三以康德哲学为比较会通的对象而主儒家道德主体说;唐君毅受黑格尔等人哲思的影响言心为道德理性而倾向主体化之心⑤金小方对此等有所论说。参见金小方《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其中关于熊十力对中国道体与西方实体概念的混谈与问题,进一步参见金小方文中提到的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及张汝伦另一篇文章《近代中国形而上学的困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这些做法或说法虽确有明晰中国古代思想之功,但又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以“西”代“中”的结果。因此,中西哲学会通要求中国哲学研究者,对中西哲学思想传统与概念谱系都要有深入的把握,从而才能准确选择适合与儒释道哲思进行深层对话的对象,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并深化中国哲学思想与话语的发展。
这意味着有志于创立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学者,既要精通中国古代哲思与字义疏证等小学功夫,又要精通西方诸家哲学思想,并找到真正适合与中国哲学进行深入对话的西方哲学思想,方具备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在当代重建的学术素养。因为,学者只具有对“道”的真切体悟,而缺少对西方思想的了解与语言技艺的掌握,就无法做到既丰富中国儒释道之哲思而回应当世最前沿的思想问题,又无法做到将体悟与哲思诠释出来以为世人所理解。换言之,因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既是思想的发生史与概念演化史,又是哲学问题的发展史,所以学者们只有精通并准确选择与中国儒释道哲思会通的西方哲学思想,才能在回应当代哲学问题中,既恰当地深入把握与丰富中国儒释道思想,又能明晰当今中国哲学学术话语体系中许多概念的渊源、分际与误用之处,从而为运化并创造恰当的诠释话语清理出干净、稳固而开阔的地基;同时,学者们对字义疏证等小学功夫具有切实的功底,才能既不在字义上对中国古代哲思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又能为古代儒释道术语与当代学术话语的融合打下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因此,中西哲学的比较会通,尤其正确而深入的中西会通,对推进中国哲学思想与话语的创新和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至于与中国哲学会通的合适对象,海德格尔现象学是当今最大的热门。张祥龙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同有一种“非现成的识度”,同以“人间体验为理解之根”、以“终极即构成境域”,且二者的“时间”思想亦相通[11]。与之不同,刘小枫与韩潮从伦理视角对海德格尔思想进行了深入辨析,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是将存在或伦理掷入时间的历史主义,进而对其能否与中国古代思想会通深表疑虑⑥刘小枫《海德格尔与中国》是与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对谈之作,二者皆基于伦理视角论析海德格尔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承继与转变,从而界定海氏思想的性质,以明其是否与中国古代哲思相通同。参见刘小枫《海德格尔与中国——与韩潮的<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一同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如此,张祥龙将儒释道之“道体”与海德格尔作为本有的“Ereignis”皆直接论断为“终极的缘构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古代“天道”确实有着非可时间化的一面。然而,不可否认:海德格尔主张非对象化存在的观点与儒释道的心物融通的存在观相通;而且海氏关于存在、时间、语言等问题的论说,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亦皆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此,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比较会通,无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还是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创建都极具价值。
总之,在中国哲学话语的创建中,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不仅不能摆脱中西融合的大趋势,而且要在对儒释道精髓深入体证的前提下更加深入这一潮流,从而把握中西哲思的精神,并明了二者的边界与相会通处,才能更好地进行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创建。如熊十力、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话语体系的创立,就归功于他们既对儒释道之“本”有体悟和对传统语言有深入的掌握,又与他们对西方哲学思想视域的获得有关;虽然一定程度上由于他们缺乏对西方哲学的精准理解,而未能选择合适的会通对象,导致其话语体系的不圆满。因此,只有基于体证,坚持中西哲学的比较会通,进而选择合适的比较会通对象,才能事半功倍地对中西哲学思想、语言、问题等进行深入消化与磨合,从而建立既通达中国古代哲思又融入世界思想潮流,并为世人理解的中国哲学诠释话语体系。
三、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特征
通过这种磨炼新建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应具有什么特征,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要与世界接轨,就必须改变中国古代语词的模糊性,而使之清晰化。然而,清晰化的概念语言,往往意味着语言的对象化,故其既难以通达超言绝相的“道”,又难以真正地揭示出道开显的“心物一体”存在。相反,源出于对超言绝相之“道”与“心物一体”存在领会的诠释话语,是非对象化的语言。如此,虽然中国哲学的发展要适应中西哲学会通的大潮流,但是中国哲学话语的创立却不能走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诠释路径。不过,话语的非对象化并不意指新建的中国哲学话语是完全反逻辑的,否则就无法辨明道理。因此,恰当地说,重新创建的中国哲学诠释话语,虽有语词的逻辑区分,但又不至于限入凝固化的区隔中,而是成为相融相即的非对象化之“诗言”。
中国古代儒释道哲人通过体证所抵达之域,不仅是天人贯通之道而且是诗化般的生命存在,故其中有“天乐”(《庄子·天道》)。因此,由这种存在体会而生发的中国古代儒释道经典,实际上都是诗性的话语体系。海德格尔即认为诠释“乃是对此在的在此之在的揭示”[12],故诠释“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13]。非对象化的存在与非对象化的诗性语言是互相给出的。因此,基于对道的领会而给出的中国哲学诠释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是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语言体系,而是喻示着道与心物融通一体存在的诗性话语。相对地,主客二分的概念化语言,会将道与一体未分的存在封死并肢解,如《庄子·应帝王》“浑沌之死”的寓言所示。
不过,话语的“诗化”,并不意味着话语不存在逻辑的区分,只是话语可以实现分与不分之间的转化,从而保持住通达生命存在的管道。具体而言,名言的产生是意识参与存在进行逻辑区分的结果,所以名词总是带有对象化的特质,但若又能以一体性存在的体证为基则可相融相即。如《庄子·齐物论》论述存在的分化与名言的产生历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名言”的产生总是对应着存在的分裂与对象化,故即使如“道”“气”之名也是理智对未分化之存在进行逻辑区分的产物。《庄子·齐物论》将这种对象化的名言称为“小言”并贬抑之;与此不同,文中又给出了“大言”,即悬解语言的分际而指向一体未分存在的语言,若《庄子·知北游》的道物无际之论。这意味着庄子主张不应执着于“言”之分,而应把握言语分合之“道枢”(《庄子·齐物论》),以免得小言而忘意,失落心物一体存在之真。因此,虽然当代学术话语更强调逻辑的清晰性,但是重建的中国哲学诠释话语,不应走向分化存在的“小言”,而应成为指向真实存在的“大言”或“诗言”⑦关于“大言”与“小言”或“道言”“诗言”的讨论,亦可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327页)。。换言之,中国哲学诠释话语,应首先基于对道或生命理性的体会并通过对一体性存在的描绘给出,而非只进行逻辑理性的对象化定义,从而使语词虽内含逻辑区分又可相融一体,成为揭示真实存在的诗化言说。
总之,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的重建,首先应当遵循体道之明觉,而非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从而使话语成为揭示“道”与“心物一体”真实存在的非对象性的诗性话语。否则,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比喻,话语将会失去存在的根基成为空转的轮子,而对诠释儒释道的智慧起不到真正的价值。不过,话语的诗化又不代表话语不存在逻辑的区分,因为名言的产生必然是逻辑区分的产物,只是话语因逻辑而来的条理与分际不能被凝固化,而必须保持住话语间的相即相融性。因此,我们在以逻辑区分存在而命名时,应是基于道对心物一体存在进行描绘给出语词。只要能使“道”及其开显的“心物一体”存在居留于话语中,那么话语就既可以包含逻辑又不被逻辑所限,而成为融通一体的话语体系并随缘生发或开显其意。
四、结语
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难以通过西化的对象化语言,对中国古代儒释道之精髓做有效阐发。因此,为了使当代人能通过话语契接中国古代儒释道哲思,重新创造中国哲学的诠释话语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然而,诠释话语的给出,总是源自对道与非对象化的真实存在的领会,故只有摆脱现代中文学术语言或存在方式的规训,体悟儒释道的精义,才能使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重新建立获得根基。不过,只有对道与真实存在的领会并不足以重建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因为还需要掌握运化语言的艺术。这就要求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在中西深入融合的时代,秉持中西比较会通的研究方向,对中西哲学的思想和语言有深入的把握,从而既了然当代中西方思想与话语的渊源与分际,又深识中西哲学思想与话语会通的可能。只有通过中西思想、语言、哲学问题的不断激发碰撞,并基于体证对中西哲学的思想和语词进行反复的消化与磨炼而提炼出一个核心概念,然后将之发展为能贯通整个中西哲学史并回应当代哲学问题的叙事话语体系,一套既适合阐发儒释道奥义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才能真正新创成功。如此,这种兼涉生命明觉与逻辑理性的话语,就成了既内含逻辑的区分,又相融相即而为“诗言”的话语体系。
当然,上述所论只是就个人创建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而言。如果要形成整个中国哲学界学术话语系统,单靠个人是不够的,而需要整个中国哲学界学人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另外,中国哲学界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亦要求创新学术研究、交流的体制,并变革学术话语主导权的产生机制,从而更加包容并激励学术思想与话语的创新。总之,中国哲学界话语体系的重新创立,既需要学者们个人的努力,又须整个学术思想与话语产生机制的进一步转变。这无疑是一件困难,而须众学人持之以恒的事情。
[1]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体系的建立: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252-264,272.
[2] 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J].时代与思潮.1990(2):239-257.
[3] 熊十力.原儒[M].长沙:岳麓书社,2013:7.
[4]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戢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146.
[5]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45-546.
[6] 陈来.中国哲学话语的近代转变[J].文史哲, 2010(1):5-7.
[7] 温海明.儒家实意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31.
[8] 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6(2):76-90.
[9] 王中江.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J].中国社会科学, 2004(4):45-52,206.
[10] 金小方.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J].孔子研究, 2016(6):139-147.
[11]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7-293.
[12] R.E.帕尔默.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J].彭启福,译.潘德荣,校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265-272.
[13]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7.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System——Focusing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HUANG Shiku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at the westernized object discourse cannot interpret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First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e experience of Dao, for only by experiencing Dao can we interpret it. Secondly, its cre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means scholars should deeply grasp the distinction and limit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discourses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ell, so that they can not only avoid the misuse of discourses, but also enrich the thought and discours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tself. Finally, the new created hermeneutic discours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be able to blended with each other although they have logical distinction. In other words, the discourse should be give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Dao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inuity of mind and matter” rather than a simple logical definition.
Chinese philosophy; discourse system;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establishment
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09
黄仕坤(1990-),男,广西贵港人,在读博士。
B014
A
1673-2065(2021)06-0071-06
2021-04-16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