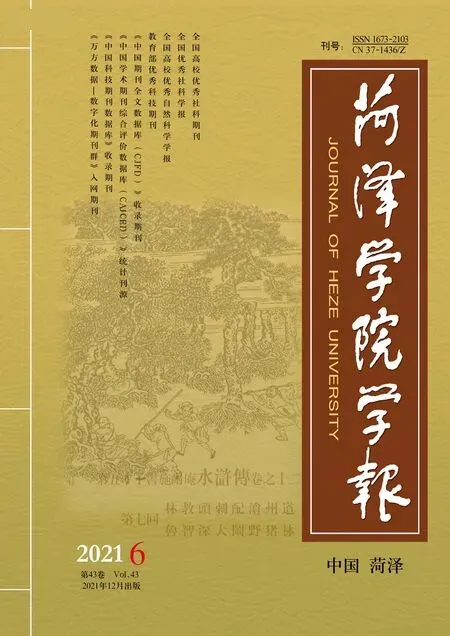论宋江的人生悲剧
2021-01-15盛志梅
盛志梅,吴 娅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一、“夹起尾巴做人”的宋江
在《水浒传》小说中,宋江的人设是最高的。上梁山以前,人人“久仰大名”,渴望与他交个朋友。落草为寇之后,又有许多人闻名而来,投靠他的麾下,心甘情愿地受他领导。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何以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论文才,比不上智多星;论武功,更要甘拜众好汉的下风;论权势,他不过是一区区小押司,能在江湖上立住脚跟的几样看家本领他都拿不出手,他靠什么闯荡江湖?其实,宋江只有一样好处,那就是能收拾人心,会“夹起尾巴来做人”。
英雄好汉大多数都是吃软不吃硬,他们行走江湖“专打硬汉”。宋江却从不充硬汉,而是一个慈悲为怀的菩萨。他大把地撒钱,对那些落难英雄好言相慰,笑脸相迎,临走还有大把银子相送。这样,哪个好汉会对他举起拳头呢?宋江就这样以柔克刚地征服了天下的英雄,使无数好汉对他心向往之。武松在柴进那儿受冷遇了,想去投奔他;李逵在江州过得挺舒服,也想去投奔他。在武松的心目中,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在李逵眼里,则“难得宋江哥哥……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几乎每个好汉对宋江的“仗义疏财”都钦佩得不得了,因为这正是大多数好汉做不到的。
梁山好汉大多缺钱、爱钱,仗义帮助金老父女的鲁智深,在桃花山上还踩扁了李忠等人的银酒器,偷了滚下山去了呢。类似的“勾当”武松也干过,他在杀了张团练一家之后,还不忘收拾一下酒桌上的银器,踩扁了揣在怀里。好汉爱钱,仍不失英雄本色;但这不爱钱的宋江,却说不得是好汉。他用钱收买人心,以他“仗义疏财”的“突出优点”掩盖了他老谋深算、自私自利的名利之心。使众人只知他不爱财,却看不到他有比爱财还厉害的“爱名”,就是这爱名之心把梁山众英雄一步步引入死地的。
宋江收拾人心的另一招就是自谦,从来不自我宣扬。梁山上的好汉大多喜欢吹嘘,如武松,因在景阳冈上打死了一只老虎,走到哪儿,他都要在自己的名字前挂“打虎”二字,甚至杀了人也要在墙壁上留言“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但宋江从来不这么招摇,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名字在江湖上如雷贯耳,对人作自我介绍时却总是说“小可姓宋名江,祖贯郓城县人氏”,人家再追问一句“莫非山东及时雨宋江?”他才说:“小可便是,何足道哉。”类似这样的话宋江好象背熟了一般,见了武松、薛永、李逵等几乎所有的好汉,他都是这么自我介绍的。给人的印象就是“宋江哥哥”真了不起,这么大的名气一点也不拿架子,由此更加敬重他。
宋江的这种过分谦虚还表现在他上山后的屡次让位上。本来,自从他上山以来,就已经在暗地里收拢人心,把晁盖的头领地位给架空了。梁山上的每次军事活动,他都以“哥哥是一寨之主,不可轻举妄动”为理由不让晁盖去。他带队出去,每得胜一次,他的军事威望就高一次。渐渐地,好汉们眼中只知有宋大哥,不知有晁大哥了。所以晁盖一死,在大家的心目中,他自然就成了一把手,这也是宋江盼望已久的了。但晁盖好象看透了他的心思,偏偏不让他的野心得逞。临终留了遗言,要活捉史文恭为他报仇之人做接班人。然而素以“忠义”自命的宋江此时却忘记了“哥哥”的遗嘱,屡屡以老大自居,活捉了呼延灼,他说“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俘虏了董平,他又说“倘蒙将军不弃微贱,就为山寨之主”;请了卢俊义来,他先是假模假式地让位,后来又假仁假义地安排了卢俊义攻打曾头市。没想到卢俊义果然活捉了史文恭。此时本该让位,他却又以众怒难犯为由,再安排卢俊义去打东昌府,他率队去打东平府。以吴用为首的心腹暗地里都希望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所以从调兵遣将到行军打仗都偏向着宋江,这一点宋江非常清楚。然而这场戏他还是演了下去,就为了给大家一个印象:他宋江无意争这头领之衔,是众人推的,“天命”逼的。这样以退为进,把梁山上的人心收拾得服服贴贴。然后又与公孙胜等人合计出了那个遮人耳目的天赐石碣,彻底坐稳了第一把交椅。
宋江收拾人心的第三招,那就是以眼泪赢人。在一百单八将齐聚梁山的庆功宴上,刚刚坐稳了头领之位的宋江,便开始驱使这些好汉为他的功名前程服务了。他在酒席上让乐和唱他写的“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曲子。好汉们一听就炸了营,武松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便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跳起,攧做粉碎”;鲁智深发牢骚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吧”,当然,大多数的弟兄是敢怒不敢言。此时的宋江大权在握,已经不是那个“鄙猥小吏”“小可宋江”了,谁不听他的话,便以“乱了法度”处治。但他用的依然是软法子,先以处置李逵作例子,大喝一声:“这黑厮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斩讫报来”。在众人的求情下,他便将计就计地假装醒了酒,“忽然发悲,道:‘我在江州,醉后误吟了反诗,……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如骨肉一般,因此潸然泪下’”。宋江这一番话是说给武松、鲁智深及其他众好汉听的。意思很清楚,李逵对我这么重的情分,不听话我都要杀了他,何况你们?
俗话说日久知人心,宋江尽用软话收买人心,时间久了众好汉也有些不买帐了。宋江张罗了几次招安,都被好汉们齐心协力地破坏了,三阮偷换了御酒,李逵扯了招安圣旨。后来众好汉虽然勉强随着宋江受了招安,但仍“反心不死”。征辽回来以后,因为没有得着应有的奖赏,大家私下里议论着要打回梁山,托吴用向宋江转达这个意见。宋江听了大惊,第二天在军机会议上就以死相威胁说:“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赖你众弟兄扶持,尊我为头……你们众人苦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不然,我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这些话是软中带硬,意思是说当初我不想做这个头,是你们逼着我做的。既做了,就要听我指挥。你们不按我的指挥行事,我也丢不起这个人,一死了之,你们爱咋地咋地吧,我是管不了了。宋江当初那么处心积虑地让位,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众好汉至此才明白上了宋江的当,“俱各垂泪,设誓而去”。没什么好说的了,既上了招安这条贼船,只得为那个“鸟皇帝”卖命、为这个“义士哥哥”挣个“封妻荫子”的前程了。
后来打方腊,人心已经有些散了,混江龙李俊在战斗中与费保等人结为兄弟,战争一结束就借故退出了队伍,往海外发展去了。而燕青、武松等人也在回京的路上就告辞了,这说明他们早就有这个打算了,只不过为了义气,才善始善终地为宋江打完了这一仗。此时的及时雨已经“黔驴计穷”,除了哭什么本事也没有了。每死一个弟兄,他都要哭得昏了过去,以示伤心,这样别的弟兄也就没法埋怨他张罗招安的罪过了。这是他推脱责任的好伎俩,更是他“夹起尾巴来做人”艺术的最高峰,然而他的威信也就此降到最低谷了。除了李逵还是那么死心眼,一点没看出他为人的自私自利来,其他人或多或少的都明白了“宋江哥哥”是个什么人了。所以战争一结束,一个个都拜辞而去,再也不众星捧月般地追随他了。
细读小说中关于宋江的描写,虽一力标举忠义的李卓吾,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宋江下的这个结论实在有些自欺欺人,名不副实。他在小说的回批里多次指出宋江为人的假道学、真强盗底色。如第十八回回批“李生曰:梁山泊贼首,当以何涛、宋江为魁,朱仝、雷横次之。一边问个走漏消息,一边问个故放贼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1]“李和尚曰:宋公明凡遇败将,只是一个以恩结之,所云知雄守雄也,的是黄老派头。吾尝谓他假道学,真强盗。这六个字实录也。即公明知之,定以为然”[2]……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也就是说,其实早在李卓吾不遗余力为宋公明唱赞歌的同时,他早就看破了小说作者的真实态度。
作者对宋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似褒实贬。在正面塑造宋江“一心只向朝廷”的忠臣义士面貌的同时,总是不忘背面敷粉,把他不忠、不孝、不义的一面以影子的方式涂写出来。因此,小说正面看,是一曲“我忠心不负朝廷”的烈士之歌,背面看,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可怖可叹的人生写照。宋江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终其一生,都在做着成名的美梦。为了成名、扬名,不惜切断亲情,断送兄弟,出卖朋友,比如他的上梁山,就是经过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从一开始的埋怨江湖弟兄们坏了他的清名,到最后积极给别的朝廷命官挖坑,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成名梦而做的。甚至对于他有过命交情的忠实粉丝李逵,坑起来也是绝不含糊,绝不手软。李逵是怎么也想不到宋江会有那么多的心计,一方面要利用兄弟们的情谊来为他讨一个“封妻荫子”的功名,一方面还要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来安抚众弟兄的情绪。李逵到死都以为宋江是个要造反的人,当宋江对他说朝廷赐了药酒时,他还大叫一声“哥哥,反了吧”,并计划着“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临走还天真地问:“哥哥几时起义兵,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却不料宋江利用他对自己的信任,暗暗地让他吃了药酒。宋江为了自己的“忠义”之名,亲手杀死了这个他曾称“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如骨肉一般”的铁牛兄弟。而李逵却是梁山上第一尊活佛,“为善为恶,彼俱无意。宋江用之便知有宋江而已”[3],对于宋大哥对自己的处置,虽然惊讶却无怨恨,只是垂泪道:“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相形之下,更见宋江之贼。诚如明代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所言:“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4]
宋江自始至终不肯翘翘尾巴,在众人面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在小说中,他还是不小心两次露出了他的“豪杰”本色:一次是杀阎婆惜,一次是江州酒楼上醉题反诗。但这两次的坦露,都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前一次让他丢了官,沦为囚犯;后一次则几乎掉了脑袋,直接把他送上了“不忠不孝”的草寇头头的位置。这对他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总结起来,还是带上面具,“夹起尾巴来做人”稳便,所以他便一路做下去,直到最后实现其“生当鼎食死封侯”的夙愿。虽然这与他当年“血染浔阳江口”“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凌云之志有些距离,“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之人也”[5]。以一人之智糊弄了一百单七位江湖豪杰为他卖命,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位“英雄好汉”了。
二、为求最大利益而甘冒风险
说宋江低调做人,有目的性,好像是贬低了他的人格,很多人肯定不服。人们可能会说,他收养阎婆惜母女,给市井老婆婆棺材本难道也是有什么目的不成?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宋江自然也不例外。宋江性格中除了邀名的虚荣之外,还有怜贫惜老,行侠仗义的一面,也有他桀骜不驯、喜爱冒险的一面。所以他一方面投身刀笔小吏,为朝廷效力,一方面又心羡行走如风的江湖,结交草野之臣,甚至不惜担着血海也似的风险去给晁盖等人送信,这种做法明显是渎职,知法犯法,是对皇帝的不忠,对儒家修齐治平信仰的背叛。
宋江性格中有桀骜不驯的因子。当初他执意投身刀笔小吏,为此甚至不惜与父亲兄弟从律法上割断关系,一方面可以看作精通世道,深谋远虑,知道从政之艰难险阻,为了保护家人而有此看似无情实有情之举;另一个角度来看,宋江此举也实在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父亲告他忤逆之罪,孝道有亏,这在从政的人那里,就是终生一大污点,他以后无论如何积极进取,也很难被提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的从政,并不像他后来劝杨志、武松等人那样正能量满满,踌躇满志地想封妻荫子。他一开始就是剑走偏锋,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想着巴结正途。另外,从他出道之初,就早早让父亲兄弟在家中挖下暗道来看,他对自己的这份差事从一开始就深怀警惕,唯恐哪天大祸临头,无路可退。也就是说,宋江其实还是很了解自己的,他深知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循规蹈矩的公务员工作,也深知自己这样身在朝廷心在江湖,终究有一天会奇祸降临。
他的桀骜不驯,不仅仅表现在这样反常的从政行为中,也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包括他对女人的态度。给他惹来大麻烦的阎婆惜,其实是个替罪羊。阎婆惜之死,表面上是因为阎婆惜不知道惜福,惹恼了宋江,让他痛下杀手,实际上正是宋江本人性格使然。如果不是他一味的心向江湖,怎么会如此不在意男女之事,逼得阎婆惜勾搭张文远?试看后来他在攻打祝家庄时,因为俘获扈三娘而惹起李逵的不满,讥讽他想霸占扈三娘做压寨夫人的酸话,就可以明白,宋江并非铁板一块,不贪女色,而是彼时他的野心不允许他有妻室之累。阎婆惜来的不是时候而已!于是,宋江性格中最大的不仁,让我们看到了,杀了阎婆惜,就暴露了他杀人放火的强盗真面目。放眼小说,在后来的梁山队伍扩招的过程中,他把徐宁、花荣、卢俊义等人一个个赚上山,哪一次不是杀人放火不眨眼,只要达到目的即可,何曾为招收对象考虑半毫分?这一点,连一力抬举他的李卓吾也看不下去了,直言“宋江、吴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的要好人做强盗?最可恨是赚玉麒麟上山也。”[6]刚把人家赚上山,切断了别人的后路,就张罗着“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如此心机,如此出尔反尔,也怨不得李逵掀了桌子!
正因为宋江性格中有喜欢冒险,厌倦成规的一面,他才私下里不断的在江湖、民间邀买人心,才在关键时刻,藐视王纪国法,忘了自己的身份,在得知晁盖等人命悬一线时,惺惺相惜,利用其职位身份做出了反叛朝廷之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这句话本身就是江湖规矩,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标准。如果以王法论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反叛朝廷,暗通贼寇;若以儒家伦理处之,则是欺君大罪,不忠不孝之人。所以,从朝廷角度看,宋江的被缉捕、被刺配都是合律合法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儒者,是一个真心报效国家的忠臣,即便一时糊涂做了对不起朝廷的事,也应该引颈待捕,而不是慌慌张从地道逃走,连累父兄家人,更不应该在刺配江州之后,还要醉酒题诗,豪情满怀地说什么“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尽管很多人为他平反,说这不是反诗,但从宋江的性格逻辑去分析,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酒后吐真言!宋江志在凌云,又不想走科甲正途,更不甘心庸庸碌碌做一辈子刀笔小吏,他敏锐地觉察到,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能,连接江湖,刀笔小吏也可以有大作为!他后来在梁山上改旗易帜,招兵买马,要挟朝廷招安等一系列看似冒险的举动,都是他喜欢走钢丝的性格使然,决非时势使然。19世纪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和作家Tyron Edwards(泰龙·爱德华兹)曾经说过:“Thought leads to actions,Actions lead to habits,Habits become your character,Character determines destiny。”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行为绝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是受着思想支配的,是一种内在的使然,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内在逻辑。
宋江的人生具有传奇性和命定色彩,在变与不变之中,似乎一切都是早已注定,悲剧结局只是早晚,一切的变数也仅仅是过程而已。因为从早年间做刀笔小吏开始,他就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不安全感。结交江湖,知法犯法,虽然不排除他谙熟世故,为自己谋退路的思考在内,但此举也恰是他偏好冒险的隐形性格的表现。同时,作者在塑造宋江忠臣义士形象的同时,在他的身边安放了一个“真佛”——李逵。以李逵的至诚无私、天真烂漫来衬托宋江的城府心机,塑造了他虚伪、矛盾、挣扎的多面形象,揭示了其人生悲剧的必然性。李逵的如影随形,恰好说明作者塑造宋江形象似褒实贬的良苦用心。纵观小说中关于宋江的描写,他几次在困顿中入梦求助九天玄女娘娘,清醒之时又拜谒道士、高僧,足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于忠君报国之路的犹疑。因此,作者明面上是在谱一曲“我忠心不负朝廷”的烈士之歌,背面看,却是对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怖可叹的人生写照。
宋江性格中好奇冒险的因素,虽然一直掩藏在儒家温柔敦厚的面具之下,但偶露狰狞,即可看出他伪儒的一面。借梁山大旗为自己的未来筹划,不惜毁掉众弟兄的人生梦想,表面上看是宋江笃行儒家的忠君安邦理念,实际上是写他洞察人心为己牟利的处世之道。马克思·韦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儒教徒并不希望通过弃绝生命而获得拯救,……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实的救赎……只想通过自制,机智地掌握住此世的种种机遇。”[7]也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尽善尽美,追求利益、效果的最大化。这无形中走向了价值追求的反面,培养了虚伪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正是儒家文化的弊端所在。
三、宋江形象的反儒本质
两千多年的帝制,造就了中国文化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并身体力行之。什么是儒家文化呢?被称为“伟大的外行”的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曾非常准确的总结道“儒教的本质……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8]它要求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要自制、内省、谨慎,所谓的克己复礼,君子慎独。作为高调宣扬忠义的《水浒传》,自然也是带有浓重的崇儒尊儒色彩。一百单八将的人生,就是走了一条“忠心不负朝廷”的报国之路,头领宋江更是作者极力塑造的儒家典范人物。表面上看,宋江从修身处事,到保国安邦,无不是秉持着儒家居处恭、出处敬,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儒家求仁之道。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这样评价宋江:“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9]
然而细读《水浒传》,我们又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作者热情高歌背后的悲凉失落。作者对于宋江的最后结局充满了批判和反思。对于其悲剧结局,虽然也同情他参不透名利关,迷恋“成名无数,图形无数”的儒家神话,痛心他不能“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但他对宋江的形象塑造和人格评价,并没有因为同情、感慨而笔下留情,而是尖锐地指出宋江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同时也利用儒家文化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实质。
可以说,宋江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信徒,更是儒家文化的叛徒,背离了儒家“向善、重义、轻利”的价值追求。如此首鼠两端,中心摇摇,其人生悲剧焉能避免?儒家信仰岂能不危?这也许才是作者著书的终极目的所在。他撰写这部小说,通过罗真人、九天玄女娘娘的信仰之争,通过一百单八将悲壮的人生结局,提出了一个令所有读书人都迷茫的问题,人生在世,如何才是结局?是成名还是逃名?在迟疑与恍惚中,作者其实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小说的最后,一百单八将冤魂不散,夜夜鬼哭,这难道不是对儒家提倡的“求名”之路最有力的质疑吗?宋江形象的反儒本质也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