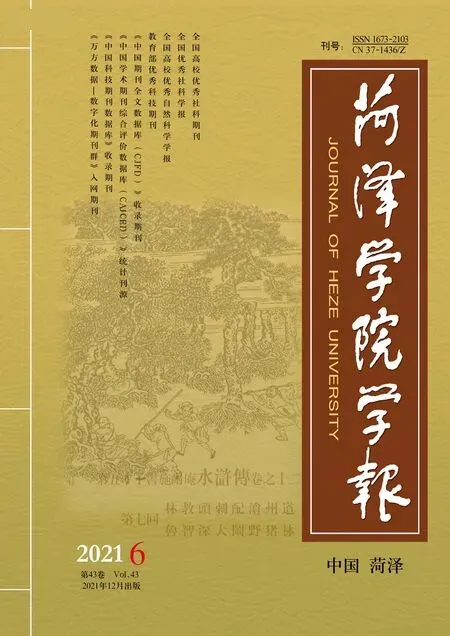《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种族文化创伤叙事分析
2021-01-15戴文疾
戴文疾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杰丝米妮·瓦德继2011年的《拾骨》后再一次让她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作品。小说聚焦当代美国黑人家庭,以诗意的语言吟唱出他们心中难以言说的伤痛,揭开美国南方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在小说中,作者将男孩乔乔、他的母亲莉奥妮、亡灵鬼魂瑞奇设为小说故事的叙事者,在母亲莉奥妮带着儿子乔乔和小女儿离开家乡,前往密西西比州去接男朋友迈克尔出狱这一两天的旅程中,通过几位讲述者的穿插叙述,展示了美国黑人家庭所遭受的沉重创痛。乔乔一家人的苦难史也是美国黑人种族的苦难史,民族的创伤深植于美国黑人种族的集体意识中代际相传。小说既有揭露现实的目的,也有安置历史的意图。
文化创伤是指当某一群体遭受过可怕的事件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那么这一可怕遭遇将永远存在于这一群体的记忆里,并让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发生彻底的改变。文化创伤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他认为文化创伤的形成过程是可以通过言语行为完成的,言语行为的言说者是创伤体验的生产者,听者就是创伤文化意义的接受者,与言说行为相关的历史、环境、文化等则是言说的情境。在小说《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中,乔乔的祖父里弗、亡灵瑞奇、母亲莉奥妮都是文化创伤体验的言说者,乔乔则是文化创伤的聆听者,言说的情境除了小说中的介绍外,作者还在扉页引言部分通过副文本的形式强化了小说的背景,为小说故事中的人物言说创设了更丰满的历史文化情境。
一、文化创伤叙事的情境创设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了叙事学中的“副文本”概念。他将书籍正文之外的一切与作品相关的元素称为“副文本”。“副文本”又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在书籍主体内容之外,与书籍装订在一起的元素为内副文本,如书本封面的书名、出版社等信息,书中的前言、题词、注释等都是;而不与书籍装订出版,但与之有关的作家访谈、书信、日记等属于外副文本,这些元素也有利于读者加深对书籍的理解。在《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中,小说扉页的引言属于小说的内副文本,它起到创设文化创伤言说情境的作用,为小说主题的讲述铺设了历史文化背景。
小说扉页中的第一条引言是一首歌谣:“我们在寻找谁,我们在寻找谁?我们在寻找艾奎亚诺。他去溪边了吗?快让他回来……”这首歌谣中的艾奎亚诺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黑人,他幼时被绑架贩卖至英国。在15至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非洲黑人被当成奴隶贩卖,形成了规模甚大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比其他黑人奴隶幸运的是,艾奎亚诺后来赎回了自由,并出版了自传《非洲人奥拉达·艾奎亚诺或古斯塔夫斯·瓦萨自我撰写的有趣的生活叙事》。这本自传成为畅销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对后来英国政府废除奴隶贸易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奴隶贩子从欧洲出发,并带着廉价的商品当做换取非洲奴隶的成本,之后他们再将奴隶运到至美洲,交换成一些欧洲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人们把奴隶从非洲运到欧洲的这段航程称作是“中间航程”。在这段航程中,被贩卖的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一旦有人染病就会被奴隶贩子直接扔进大海。这段奴隶贸易的历史是黑人种族的伤痛印记,这在《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中有所体现。乔乔的祖父里弗讲给乔乔听的家族史正是源于这段历史。在里弗的讲述中,里弗的曾祖母就是经过海上被贩卖至美国。在海上的航程中,曾祖母被捆着铁链,罩着口套,像“牲口”一样。作者让这段关于家族史的叙事与副文本中的歌谣相对应,回答了人们寻找失踪的“艾奎亚诺”的原因,也给出了这些黑人失踪的去向。
小说扉页的第二条引言表达了时间与记忆的主题。“记忆是有生命的——也是流转更迭的。但就在记忆那一刻,所有想起的事都关联在一起,变得鲜活——年老时和年青时,过去和现在,活着的和已故的。”这段引言来自尤多拉·韦尔蒂的散文集《一个作家的开端》,这部自传性质的作品由倾听、学会观察、找到声音三个部分讲述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分别对应的是韦尔蒂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童年岁月、她去看望祖父辈的旅程、自己的大学时光以及如何成为作家。韦尔蒂的成长三部曲与小说中乔乔的三段经历十分相似,乔乔的第一段经历是与外祖父母及母亲一起生活的经历,第二段是他随母亲前往密西西比州的旅程,第三段则是从密西西比回来后,他成长为家中顶梁柱的过程。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韦尔蒂还是乔乔,单从他们成长角度来看,文本表面看似是线性叙事,但同时又有回溯性的叙述,这形成了时间的交叉。小说扉页所摘录的话更是表达了这一点,让读者意识到,线性时间是虚假性的,过去与未来并无绝对的顺序,过去总是影响着现在与未来,而现在和未来也会让过去产生新的意义。作者借由亡魂瑞奇表达了自己的时间观:时间是汪洋大海,所有的事情都在同时发生。具体到美国的黑人群体,他们并不会因为奴隶贸易和受歧视的经历成为历史而忘记,每一代人都会背负过去,践行现在,并也将影响到未来。
这些扉页的引言成为小说的副文本,加深了正文故事的历史铺垫,让小说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从而让小说中的个体经历和表征具有了种族代表性。
二、文化创伤的言说见证
在《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小说中,作家采用了集体叙事的方式来表明美国黑人群体曾经经历的文化创伤。在小说中里弗、瑞奇、莉奥妮作为三位创伤经历者轮流讲述了他们曾遭受的创伤体验。
里弗作为乔乔的爷爷,经常将个人的经历和家族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讲给乔乔听,其中有祖辈被从非洲贩卖到美国的经历,也有自己曾遭受歧视的体验。里弗讲述自身最经常提到的就是在帕奇曼监狱的经历。帕奇曼监狱里白人罪犯与黑人罪犯隔离监管,但其中白人罪犯大都是杀人越货的重刑犯,而黑人罪犯仅仅是因为贫穷而偷窃这样的犯罪。里弗和哥哥在十五岁时被关进了帕奇曼,起因是他和哥哥与白人打架,白人以袭击罪和窝藏罪将哥哥与里弗送入了监狱。在监狱里,黑人遭受着非人的虐待。当时里弗在监狱中认识了瑞奇,并与他成为好友。瑞奇在劳动中仅因不小心弄断锄头,就差点被打死。里弗在讲述他和瑞奇在监狱中的故事时,从来不提瑞奇的结局,直到有一次乔乔坚持追问,里弗才说出了瑞奇人生的最后故事。瑞奇在狱中与一名黑人布鲁一同策划越狱逃跑,而布鲁想越狱是因为他在狱中奸杀了一名女性。结果在逃跑过程中,布鲁无意碰触了一名白人女性,这让他们遭到了周遭所有白人男性的围攻。被监狱警察抓住的布鲁没有被送回监狱,而是受到凌迟活剥的私刑。里弗当时在监狱里负责看管猎狗,所以也被要求去追捕逃犯。在狱警围困布鲁时,里弗发现了躲藏的瑞奇,为了不让瑞奇免受同布鲁一样的私刑,里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好友瑞奇。这段记忆也让里弗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亡灵瑞奇的言说让里弗的叙事更加完整,且成为美国黑人文化创伤的表征。瑞奇在12岁时就被关进了帕奇曼监狱,但他决定越狱并非是因为无法忍受狱中毫无人性的苦役与惩罚,而是当时在南方黑人随时可能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殒命。在监狱里瑞奇和里弗曾听过一个叫“阳光女人”的黑人女犯讲到监狱外一对黑人夫妇被处以私刑的悲惨故事:一对黑人夫妇在道路上行走,黑人丈夫因无意中挨近了一名白人女性,就被白人女性诬告其骚扰,继而遭到上百名白人的围攻,最后被吊到树上备受折磨而死。“阳光女人”认为北方对黑人的施暴行为要比南方收敛,因此决定出狱后去北方。这也让瑞奇萌生了逃去北方的想法。在偶然看到布鲁犯罪并遭到他胁迫后,瑞奇决定跟着布鲁越狱逃到北方去。瑞奇死后亡灵在人间飘荡,并不是为了找杀死自己的里弗报仇,而是想弄明白自己的好友为什么杀死自己。在乔乔告诉他里弗的动机后,瑞奇内心对里弗是感激的。在小说中,瑞奇并非是简单的创伤言说者,他的存在还证明美国黑人群体的创伤并没有得到疗愈。作为亡灵,他意识到帕奇曼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和未来”,所以他也从个人的经历中看到了黑人的种族历史。他称乔乔的外婆是“盐水女人”,这正好与乔乔外婆通过海运航道被贩卖至美国的遭遇相印证,同时也说明美国黑人的这段血泪史已经融入到种族血脉中。在小说中,像瑞奇一样游荡在人间亡灵很多,瑞奇只是一个未葬者的代表,成为那些因为种族歧视而丧命的美国黑人的言说者。
乔乔的母亲莉奥妮在小说中是黑人种族创伤的当下言说者。她的存在表明美国当下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消失。莉奥妮在成长中时刻感受着黑人与白人的不同,不论是在学校还是生活中,白人总是享有更多特权。尽管她和白人米丝蒂成为朋友,但她却明白“我是黑人,她是白人。如果有人听见我俩扭打在一起而报警,进监狱的人是我,而不是她”。这样的认知使她养成了在白人面前隐忍的性格,因为只有这样,她才可能有更多的生存空间。莉奥妮弟弟的经历就是一个证明,莉奥妮的弟弟吉恩曾经是学校的橄榄球明星,他天真地认为不论肤色如何,所有的队友都是自己的朋友,但当他与白人队友打赌并且赢了时,白人队友却恼羞成怒开枪将吉恩打死。事后在其家人及警察的包庇下,白人队友仅受到了轻微的处罚。莉奥妮从男友迈克尔那里得知了白人队友逃脱惩罚的真相,那位杀死吉恩的白人队友是迈克尔的亲戚,而包庇杀人犯的警察正是迈克尔的父亲。吉恩的死给莉奥妮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她因此靠吸毒麻痹自己,也无法照料两个孩子。
在小说中,里弗、瑞奇、莉奥妮作为黑人种族文化创伤的经历者和言说者,他们所表征的文化创伤贯穿了历史与现实日常,成为美国种族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痕迹。乔乔作为这种创伤文化的倾听者和承受者,开始在其中寻求治愈的道路。
三、寻找创伤疗愈的路径
在小说中乔乔是个刚过13岁生日的男孩,而这部小说也可看做是乔乔成长历程的书写。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观察乔乔的成长:一是乔乔具备与亡灵交流和听懂动物言语的能力;二是他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母亲莉奥妮基本没有担负起母亲的责任。为此,我们可以从黑人种族的文化和家庭亲缘关系分析乔乔这一创伤倾听者的形象。
乔乔的通灵能力与非洲文化的伏都教有关。伏都教的众神之主名为丹巴拉,蛇是他的象征。在美国的黑人群体中,伏都教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伏都教相信亡灵的存在,并认为人能够与亡灵交流。因此,在小说中,引导亡灵瑞奇来到乔乔身边的正是由蛇羽化而成的鸟,乔乔能够看见亡灵并与之沟通,这些特异的能力都是黑人文化语境所特有的,这也表明乔乔的自我认知深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
从亲缘关系来看,父亲迈克尔和母亲莉奥妮很少关心乔乔和妹妹,尤其是在父亲入狱后,莉奥妮更是深陷毒瘾,对兄妹俩恶语相向。乔乔成长的家庭温暖主要来自外公外婆,他沿袭了他们坚强善良的品质,并听到了家族的苦难史。随着祖父母年迈渐衰,乔乔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职责,体现了他关爱他人和坚韧的品质。与莉奥妮企图用毒品麻醉让自己遗忘种族歧视带来的伤害不同,乔乔选择直面自己的文化和种族身份,他既是文化创伤的聆听者和承载者,也在不断寻找治愈文化创伤的路径。
乔乔前往帕奇曼的旅程对于他自身的成长至关重要。在旅途中,母亲莉奥妮对他们的漠视让乔乔快速成长,主动担起照顾妹妹的家庭责任。而到了帕奇曼之后,他恍惚看到了以前祖父辈在帕奇曼劳作的场景,这表明外公里弗讲述的家族苦难史对他产生了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次旅行让乔乔和亡灵瑞奇相遇,瑞奇在乔乔身上闻到了“比底层乌黑的淤泥还浓的味道:那是海里的盐的味道,发出浓浓的卤水味。在他的静脉之中搏动”,这是来自家乡的味道,瑞奇相信可以跟随乔乔找到回家的路。小说通过瑞奇的判断强化了乔乔身份的文化隐喻。
在亡灵瑞奇栖息的树林,乔乔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亡灵,听到了他们对自己悲惨遭遇的诉说:“他强奸我,把我扼死”“我举起双手,他朝我射击了八枪”“她把我锁进牛棚将我饿死”……亡灵的控诉让乔乔感到自己的皮肤在灼烧,他身临其境般感受着自己种族的创伤。但与祖辈们不同的是,乔乔在自己种族文化的创伤中依然抱有探索美好生活的希望,并不断尝试去治愈。作为白人和黑人结合家庭的孩子,乔乔也感受到黑人所遭遇的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已经扭曲了白人自身的人性,因为喜欢莉奥妮,迈克尔被白人看作是异类,迈克尔的父母不能接受迈克尔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当迈克尔的父亲看到莉奥妮和乔乔及妹妹时,厌恶地说那是“该死的皮肤”。
妹妹凯拉的一次无意之举,让乔乔最终有了顿悟。凯拉来到树林找乔乔,天生通灵的她看到了满树亡灵,这时她忽然“将一只手臂举起,手掌向上”,并唱起了一首乔乔听不懂意思的歌。她好像是伏都教的巫师,通过歌曲和手势帮助亡灵们找到回家的路。树上的亡灵们在凯拉的引导下,似乎回忆起“家园”的方向。乔乔目睹着凯拉所做的一切,凯拉的歌声让乔乔意识到,认同自己种族的文化创伤并不意味着自己要被其困住,可以在行动中改变现状寻找安宁,去迎接新的未来。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通过小说的副文本来强化种族创伤言说者的言说情境,让亲历者以集体言说的方式呈现了美国黑人的种族创伤史。乔乔既是种族文化创伤的倾听者也是传递者,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他在铭记自己民族历史的同时,又以坚韧、善良的品质去探索未来生活的希望。作者在小说中以深沉的人文关怀去审视黑人群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试图通过梳理和安置历史来为解决当下的种族冲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