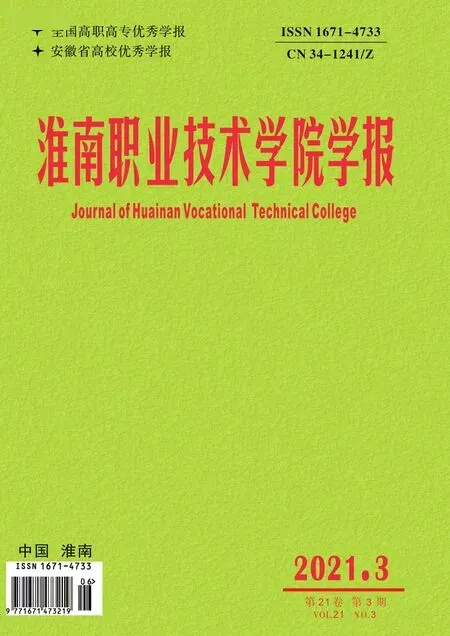网络空间信息生态治理的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2021-01-14阮清峰
阮清峰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永安 366000)
一、网络空间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 治理主体公共性缺失
1.治理主体权责不清晰。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网络主体共同协作治理,界定“权力边界”。首先,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或企业“履职边界”界定不清。当前,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和发布者自我规范的“边界意识”薄弱,在以市场逻辑的驱动下,为了提高信息使用者的注意力,某些网站完全抛弃了网络公共性,利用网络公共热点事件为自己创收或者提升品牌知名度。其次,社会监督力量自我角色定位缺失。随着网络阅读碎片化、快餐化,相当多的网民成为了“标题党”,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博取眼球,满足某些“标题党”的低级趣味,刻意扩大标签效应,截取事件中一些敏感词或者争议点来做片面报道,辅以煽情的语言和浮夸的描述,彻底成为了变成谣言制造者,而非真相报道者,混淆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边界”。
2.主体人格呈现非生态化。首先,意志自律缺位。当前,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系统中的部分行为主体缺乏“慎独”的道德意志,他们为了博取眼球,为了提高点击率,发布了暴走漫画、黄继光砸缸、办公室的董存瑞和张广红的歪曲“狼牙山五壮士”等扭曲信息;甚至出现“香港暴徒好帮手”APP的匪夷所思的反人类软件。其次,网络信息群落呈现极化现象。一方面,是网络信息主体沉默化,由于网络信息的不对等和网络资源的失衡,处于网络空间中的“弱势群体”常常处于缺席和“隐身”状态,他们对网络信息的甄别和选择无法自主,也不愿表达治理网络污染信息的意愿,无法为网络信息治理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是信息主体的非理性化或者“暴力化”,它实质上起到了网络信息污染化的推波助澜作用,呈现巨大的破坏力。
(二) 客体场域建设不足
1.舆论场建设不足。官方舆论场的建设满足不了日益高涨的舆论洪荒,出现了官方引导和疏浚与非官方“不在场”的背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网络舆论工作责任机制、运行机制、应急机制上的制定还不够完善,同时没有抓住舆论的时效性,没有抓住信息受众的心理特征,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什么都管,造成政府的一厢情愿与网络公众自我认同的冲突的“监督悖论”,引导力呈现衰减。其次,“江湖舆论场”的自我约束失序。媒介专业舆论场的自我约束失序,一些无良媒体无视舆论事实,刻意制造“歪曲的共识”,媒体发生异化,失去了媒体的公信力。
2.文化场建设不足。首先,正能量的网络文化精品建设不足。出现了一些以丑为美,以俗为荣的媚俗文化;出现拜金炫富,追星炒星,误导青少年的拜金主义文化;出现宣传违法正义,混淆是非的暴力文化。其次,网络文化综合治理体系不完善。缺乏网络文化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共享,在制度设计和统筹安排上,协作配合度低。最后,网络文化的融合度不够。缺乏融媒体的文化建设理念和融合机制,县域级的融媒体文化建设尚未完善,县域级网络融媒体文化管理上资金投入与管理效应出现比例失调,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化不够,网络文化转化率不高。
(三) 载体支撑性建设不足
1.载体安全环境建设不足。首先,安全技术环境面临巨大风险。近几年,我国在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网络信息技术细分领域表现良好。但在维护网络安全的核心技术存在短板,例如GPU、DSP等计算芯片研究缓慢,射频芯片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存储芯片尚未形成大规模产业,芯片制程工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两代[1]。其次,网络技术安全制度环境不完善。忽视安全防护和安全等级评估动态调整的重要性,没有进行重新优化评估指标权重,网络安全风险动向和趋势研判失真。
2.载体的法制建设不足。一个体系的完善是内在的自动力和外在的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我国加大了对网络立法工作的推进,但总体上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立法较迟。1994才产生中国第一部互联网的法律文件。直至2000年,政府才大量出台了互联网的管理法规。二是立法形式散零乱,各类网络行为准则散落在不同的治理决定、治理条例和治理办法中,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立法格局;三是立法精细度低,立法大部分暂处于规章的层面,不够精细化,可操作性不强。网络立法重“规范”“轻发展”,对新阶段网络发展变化中的网络监督、网络暴力和网络监管等立法规制暂显滞后。
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现实路径
(一) 建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主体公共性
1.协同治理,推进治理主体权责清晰化。首先,政府监管职责清晰化。一是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管网水平。构筑网络内容、网络传播“防火墙”,加强对网络平台的风险审查,积极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明确网络安全事件分级、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调查评估、预防保障等工作流程。二要统筹兼顾,整体规划。监管部门要明确属地管理责任和治理主体责任,建立网络生态治理督查机制;明确网络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联合执法、案件督办等责任主体和责任客体。其次,加强行业治理自律。建立相关行业自律组织。不仅需要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如中国网络社会联合会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还需要更多的行业自律组织共同参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综合治理,共同维护互联网行业秩序。
2.加强自律,实现网络人格生态化。首先,推进网民自律,要廓清网络中的“自由边界”。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但自由不是任性的,而是有“边界”,“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2]”。网络中的“自由边界”指的是人们在从事网络活动中要分清楚哪些行为是可为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为。其次,涵育网络道德。网络道德伦理与传统道德伦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网络空间的“面具性”让传统的道德舆论评论与监督难以进行,网络主体要有责任意识,主动意识到自我责任,不主动滥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
(二) 加强客体的场域建设
1.加强“网络舆论场”建设,优化网络舆论环境。第一,坚持党管网络舆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3]要有阵地意识,壮大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第二,做好网络舆论的疏浚工作。网络舆论反映社会舆情的“晴雨表”,网络舆论治理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不能靠以前的“捂或盖”的老办法。第三,创新网络传播手段,提高网络舆论传播力。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创新网络传播手段,认真研判网络传播的分众化和差异化趋势,精准定位受众;要创新舆论宣传的报道方法和手段,把握网民的心理需求和阅读特点,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增强网络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加强“网络文化场建设”,培育健康土壤。首先,要开辟传播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网络三个地带”实质上就是不让充斥着谩骂和互相攻击的网络不文明行为和非主流文化挤占主流阵地。因此,要开发激扬正能量的网络文化精品,发挥其正向引导作用。其次,加强网络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整合一些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突出传统文化特色,比如围绕春节民俗文化策划网络节目,采取短视频、电影、微电影、系列报道、专题片等多形式、多平台联动传播等创新的综艺网络节目。因此,要积极挖掘网络文化与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红色基因的共振点,推动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三) 完善载体的支撑性建设
1.突破核心技术,强化平台安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4]网络平台的核心关键是安全保障技术的突破。因此,要做好如下事情。第一,总体规划,整体推进。要坚持网络强国战略,要制定总体战略纲要,明确路线图、时间表、任务,规划要有中长期和近期规划,要在核心技术方面整体推进,要遵循科学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要加快核心技术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第二,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走出“围墙”。建构完整的核心技术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技术成果转化体系,突破理论与技术应用的“两张皮”现象,让技术报告、论文、实验试验品走出“围墙”,走向市场。推动“政、企、校、行”“四位一体”技术协同攻关联盟,推动产学研联动发展,形成核心技术产业联盟的协同效应。
2.逐步完善升级载体的安全体制机制。网络安全不仅需要“硬支撑”——核心技术支撑,还需要“软支撑”。首先,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体制机制。健全和完善网络信息平台生态治理负责人制度,明确负责人的履责、管理、年度报告等职责范畴;完善网络不良信息的审核、管理、处置和人工干预机制,及时处理不良信息;完善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分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加快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机制建设,建立适应网络人才特点的人事、薪酬、引进、评价制度,为网络安全保障优秀人才营造宽松环境。其次,完善网络空间的法治建设。网络法制建设应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兼顾安全与发展,以法治保安全,促进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