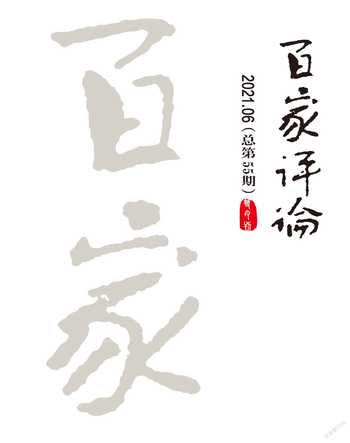走向东北与走出东北
2021-01-13刘晓航
刘晓航
内容提要:从处女作《翅鬼》到小说集《猎人》,双雪涛的小说呈现出由走向东北故事到走出东北故事的主题衍变轨迹。在走向东北中,前期小说为他的东北下岗工人故事提供了写作上的形式训练和基本母题。由东北下岗工人故事到都市生活写作的转变,其内因在于东北故事中犯罪、悬疑叙事体式的僵化。转入都市生活写作后,碎片化和偶然性情节的凸显以及奇幻性的复现,使小说丧失了以往东北故事的可读性和现实感,显露出作家创作上的危机。
关键词:双雪涛 走向东北 走出东北 转变 都市写作
双雪涛可谓当下最受关注的80后小说家之一,不仅是因为其出色的小说创作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刺杀小说家》和《平原上的摩西》业已进入影视化环节,还将引发更大的跨媒介效应,更指评论家可谓“激动”的研究热情,并逐渐产生出“东北文艺复兴”“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新东北作家群”等具有文学史节点意义的概念。由此可见,在纯文学似乎早已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优秀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借助各种媒介的触角引起公众的共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双雪涛创作中最为读者、评论者关注的仍旧是他的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中收录的部分作品。其实,如果深入到作家的小说创作中会发现,当读者仍旧为90年代“下岗潮”中的底层工人艰难生活唏嘘不已,评论者仍旧在“艳粉街”“铁西区”上构建分析王国时,双雪涛却开始逃离批评家的“把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转型。他在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中建立的以底层工人生活为中心的具有高度互文性的故事在小说集《猎人》中不再延续,故事地点也从东北转向了北京、上海,主角由工人变为“作家”和“编剧”,小说的故事情节也随之碎片化,初期写作中的奇幻性重新显现。置诸双雪涛的创作历程,我的疑惑在于作家因何而变,其作品又有怎样的延续和更新?应当如何评价其转变后的作品?以及这样的转变又预示着作家怎样的创作走向?
一、前期写作与走向东北
2018年11月,双雪涛在一次对谈中谈及自己写作上的变化:“开始的时候,我确实调用了东北的历史,包括我写的时间点比较明确,但之后,包括《飞行家》这本书里,我觉得历史感和那种特别准确的时间在减少,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尝试和趋向。当你开始起步的时候,更多地使用自己熟悉的材料,但越往后写越会尝试新的方法”,①这其中道明了作家的早期写作历程及转变之路。
虽然作家自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调用了东北的历史”,但统观双雪涛的创作历程,他的前期创作中并没有将东北故事置于小说中心。处女作《翅鬼》明显受到网络奇幻文学的影响,以完全架空的叙事构建了“雪国”世界,而占据小说大半篇幅的对“雪国”冰天雪地的描述,可谓唯一的东北印记。在稍后的《天吾手记》中,依然以架空的奇幻故事为依托,分两头讲述“李天吾”与“小久”的台北之行,和“李天吾”与警察“蒋不凡”、同学“安歌”、妻子“穆天宁”、死亡世界操控者“老板”交往的人生片段。或许由于受台北文学基金的资助而必须要写有关台北的故事,小说中的“台北之行”远没有第二条线索精彩。纵览其后的写作,双雪涛小说的多种主题已在《天吾手记》第二条线索中展露,警察“蒋不凡”与犯罪人员的彼此扶持以及小说对罪犯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掘预示着他后来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犯罪情节②,由郁郁寡欢的“安歌”部分开始,他又不断进行压抑、略显病态的中学生活描写③,妻子“穆天宁”与“我”的交往,则展露出他后来都市爱情生活描写的影子④,而“老板”这一来自异质空间的奇幻角色以及《天吾手记》的奇幻框架,都显示出作家此后对奇幻性的偏爱⑤。另外,警察“蒋不凡”论说警察虽然不易,但较工人要好得多,以及蒋面对“下岗潮”中的动荡治安的情节,都使双雪涛后来被广泛提及的东北故事首次呈露在小说中,但这样的讲述并没有将东北置于故事焦点,仅是小说的一个片段。
在长篇《聋哑时代》里,双雪涛从中学时代挖掘创作资源,将主题聚焦于教育对人性的压制。虽然小说起始就以极为疏离而戏谑的语气讲述下岗工人生活的艰难处境,但仍是故事的朦胧背景,“东北性”被压抑、痛苦的学生生活推到幕后。同样,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前期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跛人》《长眠》《冷枪》依然在《聋哑时代》的延长线上进行学生时代的故事书写,只有《大师》中消失的母亲和当工厂仓库管理员的父亲的角色设定出现了后来东北故事的人物框架,但故事聚焦的是“大师”“和尚”的生存苦难与精神超越,而非工人生活。所以,在双雪涛前期创作中,虽然东北故事不断隐现,但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不愿进入故事的舞台中央。有鉴于此,作者或是如艾略特所说在“逃避情感”,又或是在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题材,从双雪涛的创作之路看,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前期作品中的题材类型变动不居,明显带有童年视角,还有对经典作品的模仿⑥。童年视角隐含作家从童年经验中寻找文学资源的企图,这是许多作家初入写作之门的自觉选择,而变动的类型和对经典的模仿则表明作家在找寻自己写作根基并走向严肃文学写作的努力。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双雪涛始终还没有找到自己独具特色、摇撼人心的写作方式。
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双雪涛说虽然自己发表了许多短篇,“但我感觉好些东西没有达到我心里想要的标准,所以从2014年夏天开始着手写《平原上的摩西》”⑦,经过长时间的修改——“从2014年六七月份开始,一直改到2015年1月份……改稿量达到一个小长篇的量”⑧——《平原上的摩西》终于完成。
《平原上的摩西》采取將各个人物故事组合成篇的叙述策略,经过《天吾手记》,尤其是《聋哑时代》相似写作体例的训练,双雪涛早已轻车熟路,而小说中警察“蒋不凡”的故事也直接挪用了《天吾手记》中的人物姓名和部分内容,“庄树”的人生经历也有“李天吾”与“蒋不凡”交往片段的影子。不过,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东北故事不再身居幕后,而在小说中爆裂开来。双雪涛感觉创作没有达到自己的创作标准,这不仅是他对写作质量的自我考量,更表露出作家难以阐尽所欲之言的苦闷状态。在《平原上的摩西》中,不仅是作家的道义关怀即他所说的——“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没别的出发点”⑨——真正在小说中成为叙述中心,而且从《平原上的摩西》开始,作家找到了表达这一故事空间的独有方式,即以犯罪情节和悬疑结构构建起的独特文体。在后来的小说《起夜》中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曾说:“小说宜做多线叙事,全知视角,铺向案犯和受害人,在中部汇集,下半部进入侦破和受审”⑩,除“全知视角”外,其余可谓双雪涛的夫子自道,作家的东北故事大多是建立在这样的故事线索之上的。
二、东北故事的叙事困境
王晓明曾说:“文体并不单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句格式,甚至也主要不是指孕育这格式的一种特别的叙述结构:在我看来,说一个小说家创造了自己的文体,那更是指他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对于双雪涛来说,借由这样的叙事体例,东北“下岗潮”中的童年情感经验在小说中形塑为一种独特风格:这些小说往往带着客观甚至冰冷的叙述语调,下岗工人的困顿生活与犯罪等社会问题作为现象进入小说而很少被解释,作者尽量以零度写作的方式将日常生活纳入悬疑结构之中,并以突然而至的犯罪事件给读者以猝然一击。小说中的冰冷感往往是由犯罪事件和童年转述视角带来的,而平淡叙述中给人“致命一击”的阅读快感则主要依靠悬疑结构的延宕。这样的风格首先浮现在《平原的摩西》中,小说以各个人物为叙述中心,虽然都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故事,但语言冷静客观,除“李斐”外几乎无心理描写。在故事线索上,“李斐”和“李守廉”是“犯罪者”一方,“庄树”和“蒋不凡”是破获罪案的警察,最终小说将两条线索集会。从此出发,《跷跷板》《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一直延续这样的写作方式,这些小说皆以凶杀的犯罪事件作为故事推进的重要功能性情节,并在对案件的剥离和复原中完成故事的叙述。
正是这一系列具有鲜明东北风格的小说为其赢得极高评价,那作家为何在小说《北方化为乌有》之后陡然一变呢?双雪涛自言是要脱离评论家的设限:“我觉得好多媒体和专家朋友,也努力在抓我小说中的核心点。就像我去评论别人的创作时,我也愿意马上抓到一个‘把手’……但我是一个创作者,所以看到别人需要‘把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警惕的”。而黄平则将这种转变视为作家走出东北色彩浓重的地方风格,“变成成熟的‘职业’作家”的尝试。
除此两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作家的转变还源于其写作体式的内部危机。双雪涛依靠犯罪情节和悬疑结构建立起的独特文体的确支撑起了他所要表达的东北故事,不过在后来的小说《跷跷板》《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中,这样的文体越来越走向同质化的写作套路。《平原上的摩西》中犯罪情节和悬疑结构,被故事中的偶然性、复杂性以及各人物绵长的生活经历的讲述延宕开来,作家细腻绵密地讲述“庄德增”“李守廉”“蒋不凡”“孙育新”几家的不同遭遇,在一个漫长而充满细节的故事中,将犯罪情节嵌入当中。正如双雪涛对自我的写作要求:“写的是中篇,则希望它有长篇的密度”。
《跷跷板》中,短篇的体量本身很难使悬疑结构包裹于情节之内,所以双雪涛选择在结尾处完成犯罪情节的展露,小说前半部分在“我”与“刘一朵”的爱情讲述,以及与其父“刘庆革”的交往中制造日常生活的“庸常”情景,小说结尾处由“刘庆革”道出自己的杀人事件,情节斗转,给读者以猛击,应当说这样的写作体例依旧有效。而在《光明堂》中,虽然依靠众多的人物和历史书写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将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割为“受害者”和“犯罪者”两条线索,最终在第三节进行故事的交汇讲述,还是将小说的悬疑结构展露得过于明显。如果说,《平原上的摩西》和《跷跷板》中的情节设计仍能让故事的悬疑性得到保持,并在解谜时给予读者阅读的撞击感的话,有了以往阅读经验的读者,在《光明堂》中就很容易识破其中的谜团。《北方化为乌有》依靠“刘泳”和“米粒”的对谈复盘出“刘泳”父亲被厂长买凶杀死的故事,两个人物的对谈有类于两条叙述线索的齐头并进,并最终交融。短篇的体量,使得复盘的故事紧张而仓促,而窥探“刘泳”之父被杀隐秘的关键竟是“米粒”的姐姐藏在工厂柜子里看到了暗杀的过程,这篇小说更像一则悬疑探案故事,而不再是一篇讲述工人下岗之后“北方化为乌有”的历史现实,再诗性和具有抽象概括力的主题也难掩故事中悬疑情节的苍白化,难怪作家说“这个小说写得还是紧了一点”。
在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中,作者用一系列的偶然性情节,将“李守廉”一家推入犯罪深渊:“李斐”为了去和“庄树”一起放烟火而携带了汽油,而正是汽油让警察“蒋不凡”确认了“李守廉”是出租车抢劫杀人案的元凶,同时也由于另一个偶然性情节即有车撞上了“蒋不凡”的出租车导致“李斐”受伤,使得双方误会加深,“李守廉”才逐渐陷入犯罪的泥淖。对于注重以故事性支撑小说的双雪涛来说,他后来的写作难以再现《平原上的摩西》中偶然性与必然性合一的情节架构。可以说,《平原上的摩西》的成功,使双雪涛既找到了一个表述经验的独特文体,但因这一文体过于结构化和功能化,又越来越成为叙述的枷锁,悬疑讲述越来越难以为继。
所以,在后来讲述东北故事的短篇《杨广义》中,小说不再用分线索叙事的悬疑结构,而将故事线索向下岗工人“杨广义”辐辏,同时也不再像以往东北故事那样直击现实,而将主角塑造成带有武侠气息的杀人高手,小说转为一则传奇故事。于是,在这种与现实和主人公拉开距离,故而显得轻松的传奇性讲述中,可以发现作家对以往写作体式的逃离。或许正是这样的写作危机,使作家开始寻找自己的转变之路。
三、走出东北与都市写作的危机
其间,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双雪涛由辽宁进入北京,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习,如果细察这一时期的写作,仍可看到作家叙事的微调。此间,双雪涛创作了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中篇《光明堂》和《飞行家》出现了大量50—70年代的历史。前者围绕“光明堂”中的人物讲述建国后至90年代中期的历史,后者也围绕“高立宽”与“李正道”两家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今的家族史,对80后小说家来说,讲述50—70年代的故事必然是脱离切身经验的历史想象,为何作家要在独具个性的90年代东北个人经验之外加入大量改开前历史呢?此需注意双雪涛在人大接受的教育:“有些对我影响很大,比如余英时的书,比如重读了一些鲁迅先生的东西……阎老师的课是根据作品作家来讲,着重一些流派和小说的趋势,重视道义和形式……梁鸿老师……对当代中国有非常介入式的思考,她提倡一个作家不但要用写作丈量大地,也要用双脚丈量大地,实话说我是一个喜欢呆坐的人,她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被震动的,这确实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关怀,有时候人是需要行动的”。其中“余英时”“鲁迅”“道义”“知识分子的关怀”其实已经勾勒出了一个既抽象而又丰富的教育内容,文学对当代中国的介入性(至少在双雪涛的经验中)是创意写作班教育的重要部分。或许,正是因为经典文学史的重读,和注重“道义”,强调“介入式思考”的前辈影响,雙雪涛才在小说中加重了当代历史书写的比例。但这种受文学教育影响的历史书写却容易丢失以往东北故事中的切身经验,而陷入一定的叙事陈规。
文学是如此的敏感易变,周围环境和阅读经验总能在细微处撬动作家的创作轨迹。不过,三年的学院教育总比不上都市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剧烈。2015年后,双雪涛定居北京,辽宁的童年氛围转为北京的都市繁华,《刺杀小说家》和《平原上的摩西》已被文化资本看中,进入影视化流程,从东北经验的纯文学写作走向呼应都市经验,向大众媒介靠拢的职业作家写作似乎已是必然之举。既然东北叙事已难以建立足以征服读者的叙述体式,历史书写也缺乏独有的个人体验,于是作家在创作方式上回到了原点——《翅鬼》和《天吾手记》中的奇幻书写,主题则转入都市写作。正如黄平所说:“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都市传奇’有可能取代‘东北往事’成为他的主要的文学方向”。
重新回到双雪涛访谈中的那段话,他说:“包括《飞行家》这本书里”,其语锋暗示《飞行家》正处于双雪涛的转变阶段。小说集《飞行家》中从《跷跷板》到《北方化为乌有》,明确的历史时间依然存在,而后《白鸟》《间距》《宽吻》则历史感大为削减。鉴于这次访谈的时间“2018年11月”和国内期刊的发刊规律,因而可以猜测在这次访谈时,收入小说集《猎人》中的小说《女儿》(《作家》2018年第4期)、《起夜》(《收获》2019年第1期)、《预感》(《作家》2019年第1期)、《剧场》(《作家》2019年第1期)、《松鼠》(《小说界》2019年第1期、《收获》2019年第1期)应该已在写作之中或已完成。双雪涛在访谈之时,或许正是以这些作品为基底阐述自己的写作变化的。
在这些约2017年后创作的小说中,双雪涛一变“东北叙事”中冷峻、严酷的风格,转以荒诞、空洞的笔触描绘都市人虚无、压抑的生存困境。《间距》中编剧“马峰”和《猎人》中的“五流演员”“吕东”都尽职于自己的编剧与演艺事业,但作家在故事结尾将其努力化为乌有:“马峰”参与的剧本因投资人被抓而中止,“吕东”的剧组因导演病逝而解散,顿显生活的偶然与荒诞;《宽吻》中讲述的海洋馆中海豚不断自杀的故事,正是主人公遭遇的灰色生活的隐喻,《平原上的摩西》中“李守廉”也曾将在主席像下静坐的老人比作海豚,他说,“新闻上报过,海水污染了,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杀,直挺挺地,一死一片”“懦弱的人都这样,其实海豚也有牙,七十多岁,一把刀也拿得住”。在“李守廉”那里自杀的“海豚”对应着清晰可见的社会问题——对静坐的老人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伦理秩序随“主席像”的推倒而改换,对“李守廉”来说是下岗后的贫困生活,而在《宽吻》中,“海豚”之死更像都市人在莫可名状的都市之网中孤独、消沉的象征,于是展现出后现代意味;《心脏》通篇以心脏病复发的父亲乘救护车前往北京治疗为叙述主干,小说的故事空间始终局限在救护车狭小的车厢之内,司机在高速行驶中的长久昏睡,“我”因内急尿在父亲的尿不湿上的情节都使小说耽于荒谬与压抑的氛围中。此外,《女儿》中失去生活激情,自言“我的悲剧是我的能量,我的差劲是我精神上的鸦片”的作家;《起夜》中因不堪妻子精神疾病的困扰,失手打晕妻子的“岳小旗”;《剧场》中躲在旧剧场,在与盲人排戏中试图获得自我救赎的“曹西雪”;《火星》中在名利场中丢失自我的女明星“高红”,都显示双雪涛将目光转向了都市人的悲欢命运。
不仅主题书写大为改换,在这些作品中,以往东北叙事中清晰的故事线索和完整情节消退,小说往往将多个场景进行并置讲述而使故事走向碎片化。《白鸟》以故事组合将七段人生经历以记忆碎片的形式呈现出来;《宽吻》中的故事不断在大学授课、写作小说、家庭生活、海洋馆经历等场景中切换,以推迟我获知海豚自杀的消息;《起夜》一面是“岳小旗”向“我”诉说杀妻之事,另一面是身为作家的妻子微信和我讨论长篇小说素材,小说同样在这两个线索中不断转换;《心脏》中故事情节几乎消隐不见,以“我”在救护车中的观察和对父亲过往生活的意识流回忆中结构全篇,故事在“我”細致入微的观察和“呓语”般的回忆中切换,使小说更像一篇沉闷的散文。这样的策略使读者容易联想到作家以往惯用的多线索叙事结构,不过,不断转换的场景相较于多线索叙事而言,只是统摄于主题之下的故事片段,而非前后连接的情节,于是故事显得漫漶不堪。
同时,偶然性细节大量出现,雅克布逊曾说:“如果一本18世纪的冒险小说的主人公遭遇一个路人,那么这个路人对于主人公的或至少是对于情节的重要性很可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果戈理或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让主人公首先遭遇一位无关紧要的并且(从故事的角度来看是)多余的路人,让他们的随之而来的交谈与故事无关,却成了一种义务”。《间距》里“柳飘飘”回忆自己几乎被同学强奸的经历时,小说插入“我”看到“楼底下有两辆车撞在了一起,一辆车把另一辆车的屁股撞歪了,道路迅速地变成泥淖,所有车都陷在里面”;《宽吻》中描述的海洋馆出现的意外状况:食人鱼跳出来咬伤小男孩的事件;《起夜》中不断出现的身体不协调但仍执着尝试的“颠球者”;《心脏》中“我”看到的“不知被谁砍了一刀,鼻子和眼睛中间冒着血”,在冷风中跑进医院的“年轻女人”等片段都很难与主体情节推进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叙述手法不仅试图“把日常生活所持有的那些无意义的或偶然的细节包括进来成为表明故事‘真正地发生过’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将包含整体诗性的碎片化细节组织进故事的情感表达中去。
在出版的《聋哑时代》《飞行家》中双雪涛都特意标注“献给K”,如卡夫卡一般,从《聋哑时代》中的学生群像、“东北叙事”中的下岗工人生存困境,到小说集《猎人》中压抑的都市生活,双雪涛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是其小说中潜伏的主线。不过,与东北故事相比,双雪涛“走出东北”的小说抽离了特定时段的历史——“下岗潮”而转为目下普遍的都市生活危机,在脱离“大叙事”之后,双雪涛越来越“向内转”。小说集《飞行家》后期和小说集《猎人》中的作品难以再现以往东北故事的充沛元气,如果说在东北故事中,作家是从生活中跳脱出来冷眼相对的“看着写”,如今的都市书写则变为缠绕其中的“混着写”。另外,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碎片化也给小说叙事的整体性制造了难题,当作家开始用细碎的生活片段直接转义为现代生活的象征,就必然失却对事物整体把握的能力。昆德拉的告诫言犹在耳:“要抓住在现代世界存在的复杂性,在我看来,需要有一种简洁凝练的技巧。不然的话,您就会堕入没完没了的冗长的陷阱”。
从叙述手法上看,这些小说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传奇和奇幻性的复活。小说集《猎人》中,下岗之后成为杀人高手的“杨广义”(《杨广义》),刺杀日本军官失败身亡的“英千里”(《Sen》)都有明显的传奇色彩。《预感》中“李晓兵”与来自外星球的“安德鲁”的对谈;《火星》中情书里的记忆化为现实呈现在“高红”面前;《武术家》中诡异的日本武术以及将邪术与中国近现代政治相勾连,最终修炼邪术的“影人”化为“江青”的情节则奇幻横生。
在最近的小说《不间断的人》中,奇幻色彩依然延续,科学家“陆丝丝”研制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子君”和“涓生”因误杀一条小龙饱受噩梦之苦,于是他们向编剧“安东”索要一部可以让龙头按上龙身的虚构剧本,以完成自我救赎。小说最后一节,“子君”与“涓生”的救赎转为“安东”的童年自赎:在“安东”与好友“M”破裂的关系得以和解、重塑之后,两人友谊的信物——“鸟骨”也成为小龙重生的关键。这是《预感》之后,双雪涛又一篇科幻与奇幻交织的小说,故事更加跳跃,奇幻性也更为明显。这一作品也难言成功,小说的玄幻情节压倒了救赎过程中的人性表现,情节逻辑也略显含糊不清。
值得期待之处则是面对科技的发展和网络文艺的包围,双雪涛科幻感与奇幻性相交织的书写似乎也提供了一种纯文学的新样态,如果说《长眠》和《光明堂》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丰富了现实和历史的表达深度的话,那双雪涛将奇幻与人性书写紧密结合的小说是否也会诞生一种“奇幻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呢?这似乎是双雪涛创作的新走向,并展露出新媒介环境中小说创作新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新形态尚处萌芽状态,仍需拭目以待。
结语
双雪涛在初期作品《翅鬼》和《天吾手记》中展现了出色的故事讲述能力,但尚未自成一格,自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到小说集《飞行家》,他讲述东北下岗潮的叙事开始表现出独异的情感经验和写作气质,不过在《飞行家》后期的小说中,这种写作经验开始有模式化的倾向,而到小说集《猎人》,作家似乎开始丧失对生活的掌控力,具体而言即丧失了面对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矛盾感,他不再将现实的苦难编织进一个具有对抗性的历史故事中,而沾染了80后写作者普遍存在的自恋自艾和都市颓废感。
对双雪涛而言,面对都市生活困境的围剿,仍须跳脱出来,像看待90年代工人生活一样视察社会生活的隐疾,从而避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他需要尝试用一种更加整体、更加具有矛盾性的方式去结构小说,而不能在碎片化的叙事中迷失自我,丧失以往历史书写带给读者的广泛共鸣。而奇幻手法的使用虽然把握住了新媒介环境的时代特性,但需提防流入单纯的叙事乐趣和蹈虚的故事想象的危险,仍需对人性和现实进行深入的开掘。正如作家在《不间断的人》中借人物之口所道出的:“艺术若不能冲进生活里炸开,就不算真正的艺术”。
注释:
①⑦⑧⑨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藝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②如《无赖》《冷枪》《大路》《大师》《平原上的摩西》《跷跷板》《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起夜》《杨广义》《松鼠》。
③如《聋哑时代》《我的朋友安德烈》《自由落体》《松鼠》。
④如《自由落体》中“我”与“张舒雅”,《跷跷板》中“我”与“刘一朵”的爱情故事。
⑤如《翅鬼》《刺杀小说家》《武术家》《火星》。
⑥如《大师》对《棋王》以及《跛人》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致敬。
⑩双雪涛:《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版,第39页,第12页,第123页。
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李德南、双雪涛:《小说:问题与方法(五)玩具,匠人以及通往内宇宙的小径——谈小说的调性与时代性》,《青年文学》2016年第10期。
何平、双雪涛:《访谈:“这三年发生的事情肯定超乎我的想象”》,《花城》2019年第4期。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双雪涛:《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双雪涛:《不间断的人》,《收获》202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