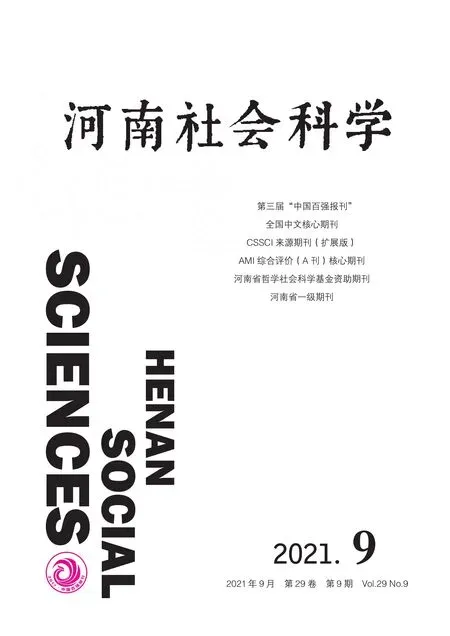哲学中的恒久贡献
2021-01-12威廉莱肯
威廉·G.莱肯 著
(康涅狄格大学 哲学系,美国 康涅狄格州 斯托尔斯 06269)
胡兰双,刘叶涛 译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有没有哪个流派或哪场运动曾经做出过一种恒久贡献呢?这里的“恒久”指的是它像哲学本身一样持续长存。
一
答案是肯定的,古希腊哲学就做出过这样的贡献,它做出的恒久贡献就是哲学本身。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人们提出了我们认定其属于哲学命题的东西,苏格拉底则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苏格拉底发明了辩证方法。但是,说这些贡献属于恒久性贡献,只是一种同语反复。这就像在提问:“哲学会像哲学那样持续长存吗?”“嗯,那当然!”
亚里士多德也给我们提供了形式的或准形式的逻辑学。
二
进一步明确一下这个问题吧。我在这里所说的“恒久贡献”并不仅仅是指一种关切、一种方法、一个概念或是一种新奇的想法,而是指一种论题,关于它人们自始至终都拥有共识。例如,一些陈述或命题依据其形式从其他陈述或命题演绎地推出,而这些演绎推导关系可以被有效地系统化。蒯因甚至书面认可了这个论题。
三
那么,自雅典以来还有什么恒久贡献吗?从某个方面来看,以下说法是没有争议的:每一门科学都源自哲学,在得到某种方法论奠基之后便从哲学分离出去,从而获得一个新的名字。先有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然后是经济学,20世纪之交出现的心理学,以及1957年出现的理论语言学。就像康明斯(R. Cummins)曾在私人通信中所说的,科学是成型的哲学。所以无疑,哲学化(philosophzing)最终会导致知识,而且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一旦哲学的某一领域看起来适合产生实际的知识,我们就不再称其为哲学,而是给它取一个新名字。
哈灵顿(J. Harington)爵士曾写道:“叛国绝不会盛行。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盛行,也就没人敢称之为叛国了。”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考虑把这些哲学成就称为“哈灵顿现象”。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术语使用上的技巧。是什么使得哲学的一个领域发展成为一门基础科学呢?我在前面提到过,这是由方法论奠基促成的,但是每一门科学之所以可以独立成为“科学”,更具体和显著的原因是对经验事实形式的证据给出了系统的回应。(这里我只是较为宽泛地使用了“经验”一词,更多内容见下面的十四)
我在使用“恒久贡献”这个词的时候,对它有一个相关的要求:它应该毫无争议并且要一直这样保持下去。这样就会确保针对我关于持续存在的共识问题的默认答案是“没有”变得无可否认。如果说西方哲学还有一件事是人所未知的,那一定就是共识了。仿照哈灵顿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说,要是真有共识的话,那就不是哲学了。但是关于“共识”和“有争议”这两个词,我们需要说得再精确些。
四
显然,若局限在特定时空,围绕某个特定论题是可以形成共识的,例如在我们大学持续一个完整学期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同样明显的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包括欧洲大陆,以及在持续数年的时间跨度当中,都曾有过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时代”这个词有时被用得有点过于宏大,就像“欧陆理性主义时代”(Continental Rationalist Era)那样。但是,“主导”与“达成一致”甚至都不沾边儿。它更接近的一个观点是:作为一个历史事实问题,广泛一致的周期很短,而且仅存在于特定区域内。就拿我的有生之年来看,仅以说英语国家为例,我们看到,感觉材料理论在40年间从统治地位沦落到后来遭到贬斥;心-身关系唯物论(materialism)从被奉为圭臬到广受抨击,如此等等。我可以蛮有自信地预测,完全有可能就在我的有生之年,理念论(idealism)将会回归。哲学共识要通过检证式论证(probative argument)的累积而达成,这远不及时代思潮、潮流风尚、同僚关系等领域——有一种感觉在哲学家那里心照不宣,即自己所属流派之外的任何哲学观点都是不重要的①。
五
现在,对于认可“共识”的归属来说,什么东西是必需的呢?很显然,它不是所有人的普遍认同。它甚至不能让所有职业哲学家普遍认同。无论是多么令人信服的主流观点,也都会存在一些反常或异议。
这里我就来举个例子,从各个方面看,它都属于边界的边界事例,但在我看来它甚至都算不上边界事例②。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英美认识论家都会同意,事实性知识就是被证成的真信念再加上另外某个条件。若不提及任何异议,则认识论的整个发展进程都是基于这个假定完成的。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针对这个假定的异议。(1)“简约论者”(minimalists)。萨特威尔(Sartwell,1991)、马丁斯(Martens,2006)坚持认为,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对于知道(knowing)来说,只有“真信念”就已经足够了(说明:可以这样回应,即“知道”这个词是在一种略有不同的因果意义上使用的)。(2)有一个老旧的观点,它肇始于奥斯汀(Austin,1961),盛行于雷德福(Radford,1966)和温德勒(Vendler,1972)。基于令人十分信服的论证,这个观点否认相信是知道的必要条件(说明:据我所知,这个观点现在已经完全被认识论家们忘掉了)。(3)威瑟森(B. Weatherson)在其著作(Weatherson,2003)中认定,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第四个条件”,因为盖梯尔的信众事实上的确是知道的(说明:他的论文并不是一篇认识论文章,而是一篇关于如何使用假设性案例去构造反例的一般方法论作品,因而其所关注的并不是对“知识”进行分析③)。
正是上面三个“说明”促使这个例子成为边界事例的候选。但是,我不认为它们是成功的。第一个有争议并且会一直争议下去。第二个在我看来则是无关的。如果反信念论证因为得到决定性反驳而被准确地搁置一旁,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据我所知,它们从没有被真正驳倒。威瑟森的例子尽管能够单独成立,但可能仅仅算作边界性分歧,因为那仅仅是他的个人观点,而且他的哲学关注和动机也不在认识论上。但他是个十分可敬的践行者,我相信他是非常真诚地坚持自己的非正统立场的。
一个更好、也许更真实的边界事例应该是对唯我论(solipsism)的拒斥,也就是宣称在一个人自身的心智状态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存在。有哪位哲学家曾经认真地为唯我论做过辩护吗?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有一些对于唯我论的论证,它们的前提并不愚蠢,而且已经被用于论证一些不那么激进的论题。我也同样不知道曾经有哪一个反对唯我论的论证,它的前提会是毫无争议的。
为了让“无争议”和“共识”这两个词(我将互换地使用它们)具有可操作性,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粗略的规定:P是无争议的和有共识的,当且仅当几乎每个职业哲学家都接受P,而那些声称质疑P 的人,或者(a)他们没有严肃地反对P,而只是探寻这种可能性,或者(b)只是在讨论一项不同话题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例子,或者(c)他们只不过就是一些怪人而已(不管人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或者(d)他们只是刻意地标新立异(同上),或者(e)他们只是为了逗趣,或者(f)否则,他们就不是真的相信非P④。
六
对于“哲学论题”,我设定的是一种日常的专业理解:在历史上一直被某个哲学家关心和捍卫着的那类主张,因为它至少会让人觉得有意思,而且至少需要一点动机(重言式显然不可能是这样)⑤。这样的主张是自然产生的,而绝不是人为造作的。因此,“根本就没有总是穿着小丑服饰的上帝”“物理宇宙不是由一堆无穷深的沙袋鼠支撑着的”等说法,我并不把它们算作“哲学论题”。此外,我主要考虑的是一些肯定性论题(关于这一点的更多说明见下面的十五)⑥。
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时遵守我在前面给出的操作性定义,哲学论题不会因为有人辩护如下观点而被表明是有争议的:“从来就不曾有过哲学这样的东西”“没有哲学论题是真的”甚至“无物存在”⑦。
那么自古希腊以来,有没有什么哲学论题达成了(就目前我们所能预测的而言)持久性共识呢⑧?
七
在之后的2000 年里我没有听说过任何这样的贡献。要是能想到一些候选,我会感到非常高兴⑨。不过我认为,在20 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做出过一些这样的贡献。
我在如下严格且确切的意义上使用“分析哲学”这个称谓:它是兴盛于1890—1960 年间的哲学学派,主要分布在英格兰和奥地利,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我对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几乎没有任何同情,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只承认它过去取得的一些成就。
八
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论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弗雷格和罗素量化逻辑的在先发展。但那只是逻辑-数学的发展,其本身并不是分析哲学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分析哲学存在一个基本(但并非核心)的观点,那就是对语言的考察会对解决哲学问题有所帮助⑩。当然,任何一个分析哲学家所用的措辞都会比“有所帮助”更强一些,但是没有哪一个更强的主张会毫无争议;而这个观点若这样表述的话就太弱了,不足以作为恒久贡献被人们提到。但有一个观点却具有足够的资格,那就是我们可能会被语言的表层语法大大误导。
罗素和其他人把句子的“表层语法”和句子(真正的)“逻辑形式”进行了比较。但是“逻辑形式”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事实上,这个概念几乎立刻就引发了争议:维特根斯坦毫不客气地否认了它的存在,而后分析时代的蒯因在1960 年也拒斥了它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结构的形式分析发展成了一门独立于哲学的完整学科:由哈里斯(Z.Harris)和乔姆斯基(N. Chomsky)创立的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 linguistics),说明关于逻辑形式或至少是底层形式的一种或多种观点已然存在,并且可能永远都会存在。可见,哲学对一门重要的学科做出了恒久贡献——只是对自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维特根斯坦甚至蒯因都同意,哲学家们有时会被句子的表层语法所误导,不过他们都基于各自的理由而拒绝将其与句子的真正的底层性质进行比较。
九
逻辑实证主义。有时候问清楚一些哲学主张或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很重要的。罗素当然会同意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把这个观点进行特别的强调。也许是因为这个观点过于明显,而且这个断言太弱了,并不足以作为一个新贡献,但可以肯定,实证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强化。
一些听起来可能很深刻的言述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和错误的,是不言自明或毫无用处的组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我想起了布拉纳(K. Branagh)1995年的电影《演艺事业》(A Midwinter’s Tale)中的精彩场景,其中自命不凡的自恋型演员汤姆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哈姆雷特不仅仅是哈姆雷特,哦,不,不……哈姆雷特就是那空气……哈姆雷特就是我的祖母……哈姆雷特就是你曾想到的有关性的一切……哈姆雷特就是……地质学。”这时,导演乔的反应是:“地质学?”(Branagh,1996)
当然,实证主义者打算因为其“在认知上没有意义”而加以排除的大部分句子或断言,比如像“一切东西在体积上都膨胀了一倍”“地球在五分钟之前突然诞生了,充斥着错误的记忆和记录”这样的句子并不包括在内,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哲学家的声明却十分模糊或者只是泛泛的比喻,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汤姆的台词。
十
日常语言哲学在哲学上提出的重要见解异常丰富。首先是维特根斯坦关于多个概念之结构的“家族相似论”,还有他的这个重要见解:有关苏格拉底型定义的研究方案具有普遍误导性。很少有概念具有必要且充分条件这样强的结构,这一点,已经得到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证实⑫。
有意思的是,现在你可能会想到,一旦维特根斯坦如此英明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概念上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的探索也就停止了,但众所周知,这种探索并没有停止。事实上,就对“知道”的分析来说,整个“JTB+”研究方案甚至直到盖梯尔年,也就是1963年才开始,而这个时候分析哲学已经可以看出有结束的迹象了⑬。但盖梯尔问题可以置入形而上学框架内讨论,而不是作为一个苏格拉底型概念问题,并且有一点也许会出人意料,那就是,“知道”最后被证明并不是一个家族相似概念(Lycan,2006)。
十一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在数学之外根本就没有绝对精确性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足够实现当前目标的精确性。维特根斯坦认为,就连数学内部也不存在绝对精确性,但至少可以说,这仍旧还是少数人的观点。
十二
奥斯汀认为,语言言述(linguistic utterances)在哲学上具有一种很重要的意义——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
维特根斯坦教导我们,事实上,语言表达式有无穷多个用法(这不仅仅是说,它们并不总是帮助陈述真理,或者它们并不总是能表达思想,或者它们并不总是被用于交流。倘若维特根斯坦当时已经了解到了奥斯汀的后期研究,他就会补充说,它们并不总是会具有行事语力)。同样,奥斯汀表明,
语言言述面临种类繁多的不恰当表达,它们属于极不相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类型的后果。
格莱斯给我们提出了那个不可或缺的概念——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一种语言言述通常会清楚而明确地蕴含该句子字面含义之外的其他某种内容,不过这种被蕴含的内容并不能从句子的字面含义中衍推出来(其中所蕴含的内容也很容易被该说话者取消掉,只要在结尾加上一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行了)⑭。实际上,格莱斯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反对以前的分析哲学家、反对奥斯汀的感知(perception)理论,以及反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个习惯,即提醒人们,某个言述听起来很有趣,并直接推断说这个言述是“无稽之谈”或者至少不是真的。(当然奥斯汀本人曾指出,一个言述,不管是不是有用,可能具有严重缺陷但仍然是真的⑮)
十三
在美国实用主义者未被承认的帮助下,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都坚持认为,在哲学争论中起作用的许多词项都是相对目的或相对语境的⑯。(这为哲学家们总是简单地假定为绝对或极端的那些概念提供了语境主义方案——“知道”一例再次凸显出来——尽管每一个这种方案本身都充满了争议)
十四
我相信,我在八到十三中列出的就是前文我所界定的“恒久贡献”。
但是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然,它们都和语言与概念有关,这在分析哲学中是很自然的预期,但此外它们还有两个让他们和我们都感到沮丧的共同特征。首先,它们的影响主要是否定性的。尽管在澄清概念和差别方面这些观点对我们帮助很大,但它们主要用于警告我们去警惕含混不清、坏的推理和一般意义的坏的论证,以及错误的预设及其引发的坏的研究方案:苏格拉底型定义、不负责任的本体论、若干类型的绝对主义。
其次,当你思考它们时,持续存在的论题实际上都是关于语言的工作原理和概念的结构方面的经验性主张。诚然,对它们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研究,但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得使用概念和语言,并且都能辨别关于它们的事实,哪怕是以前从未被(正式)注意到的事实。它们也不是那种强意义上的经验,需要诸如观察指针读数或进行物理测量之类的数据。但是,无论在该词项的哪一种标准意义上,它们也不可能被先验地知道,而且它们是主体间可确证的。
我注意到,即使是在分析哲学时期,价值理论也没有做出过(我所理解的)任何恒久性贡献:伦理学、社会哲学或美学。但由此并不能将这些领域与形而上学、认识论或心灵哲学区分开。
十五
哲学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呢?如果特别考虑分析哲学的贡献的话,至少已经取得了否定性进展⑰。
或许有人会问,科学和其他领域的“否定性进展”是什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要表明某种被认为有前景的东西并不管用,并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东西不管用。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了哲学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发现一种被认为可靠的论证实际上并不合理的时候⑱。
这是一个语言哲学上充满戏剧性的例子。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被罗素说服,他给出的几个理由促使我们认为日常专名在语义上等价于限定摹状词。最为明显而且看似无可辩驳的论证是,只有通过生成某个摹状词或另一个经由摹状词而“追溯”到的名称,我们才能学习、教授和解释一个给定的名称的用法和它的指称对象。但克里普克认为,指称的“固定”(fixing)绝不意味含义(sense)的固定。他的这种观点顷刻间就颠覆了罗素看似无可辩驳的论证(克里普克进而区分了“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从而只要相关联摹状词是非严格的,这样的区分就可以把认为名称等同于摹状词的另一组理由消除掉)。罗素的观点曾在70多年间屹立不倒——如今这叫作群体控制——但是它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把克里普克的这些见解看作我所定义的那种恒久贡献,不过,尽管它在社会哲学上是重要的,但纯粹作为一个逻辑事实,非衍推性(nonentailment)主张只是哲学论题的一种边界事例。
克里普克确实取得了三个段落前我所指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否定性进展,因为他表明,一个重要论题的几乎无法克服的案例完全就是失败的。但是当我们思考科学上的否定性进展时,我们通常会有多一些的期待:只要能搞清楚为什么先前失败的想法没有用,尤其是搞清楚一个完整的研究规划是何以崩溃的,我们就能指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或者至少指明一个更好的理论。
对某些人来说,克里普克的成就似乎恰恰产生了上面这样的结果,因为它指明了实际上是恢复了直觉上合理的“直接指称”型(DR)名称理论,而罗素最初根据他的亲知原则拒绝了这一理论⑲。但DR并未被广泛接受,更谈不上达成共识了,仍然还有太多的反常之处⑳。
结论:存在着某种否定性进展。但它不是那种导致肯定性进展的进展。
十六
尽管如此,哲学上是否有肯定性进展呢?并没有。按照知识积累乃至公认意见的通常理解,在哲学上并没有肯定性进展。
那么在方法论上呢?那倒是有一点肯定性进展:我相信我们确实比一个世纪前的前辈更加了解下面这些:如何阐发问题,如何明确差异,如何通过诸如判定举证责任等方式对哲学争论进行阶段性管理,如何对诸如此类的论证进行评估,以及如何应用批判性思维的规则。但是,这里的操作性词语是“如何”。一旦我们试图阐明论题,阐明那些支配这些方法论问题的一般性原则,共识便会消散掉。例如,当我们发现乞题谬误发生时,我们(通常)是在别人或自己身上发现它,并阻止它的发生,但对于乞题是怎么发生的,并不存在任何毫无争议的一般性描述,或者对于这样做究竟错在了哪里并不存在一种没有争议的解释。
十七
我的结论:洛克说的是对的,我们只不过是“哲学小工”,而且永远不会比这多出多少。尽管是出于错误的理由,但实证主义者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哲学的有用之处在于:它对概念的澄清,用逻辑去评估论证的有效性,发现和识别逻辑上的可能性,或许还有某种认识论上的排序。但是,基于整个学科史的归纳,我想说的是,哲学并没有建构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也许在“纯”哲学和物理学、哲学和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之间的那些非常有趣的边界区域内,情况有所例外。
为什么说没有呢?这篇论文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存在各种反实在论的答案,包括实证主义自身的答案。我坚定持有的实在论回答是这样的:我们的哲学认识论[于我而言就是解释上融贯的(explanatory-coherentist)那个认识论理论]是十分脆弱的,因为与科学理论相比,我们的理论如此抽象和笼统,以至于它们只能远远地面对经验法庭。在假说和数据之间存在着过大的鸿沟。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论题,要是说在这个论题上也永远不能达成共识,让人情何以堪!
致谢:同夏皮罗(L. Shapiro)的一次简短对话激发了这篇论文的灵感。
附录:应该指出,除了我在正文列出的那些哲学论题,分析哲学也为几个新的分支学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第一,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尽管20 世纪之前也存在关于语言的零零碎碎的哲学化处理,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Cratylus)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那里的论述还很幼稚,未能阐明真正的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中世纪有些人最擅长这个方面,他们尽可能精巧地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多亏了奥斯汀,语言哲学如今包括了所有言语行动理论(Speech-act theory),为行事语力提供了全部哲学上的诉求。不用说语言语用学和语言学其他分支全部诉诸行事语力,就连语法也受到了行事语力的影响。
第二,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为辩解进言》(A Plea for Excuses)是该理论的创始文献。行动理论的第一本权威著作是安斯康姆(E. Anscombe)的《意向》(Intention),该书受到维特根斯坦的直接启发,但更加系统,影响也更为深远。
第三,当然是元哲学,也就是关于哲学本身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本文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第一本矢志于此的专业期刊,也就是本文所在的期刊,直到1970 年才出现。在《元哲学》首期序言中我们可以读到这句话:“它的首要目标是对无可争议的哲学主张和论证的缺乏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Lazerowitz,1970)
注释:
①我在我的2019年文献中扩展了这个主题,其中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案例研究,第六章则给出了更多的案例。我不禁要引用自己得出的结论:“哲学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团乱麻,充斥着争吵、不确定、教条和反教条、时髦用语、吸睛但实际毫无根据的假定、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摇摆不定、纯粹的推测以及十足的滥用。”(Lycan,2019)
②这是约翰逊(D. Johnson)给我的建议。
③他的观点是哲学家对于“直觉”所具有的十分普遍的态度:关于个案的直觉应该被推翻,就像在伦理学中直觉经常会被一个系统且连贯的相反理 论 推 翻 一 样。 可 参 见(Goldberg,2013)(Lycan,2019)。
④这里我忽略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哲学家们会在何种意义上“相信”那些他们真诚地加以捍卫的主张。
⑤但是,不要以为“明显的”重言式在我们的解释下就是没有争议的。根据普利斯特(G. Priest)和他的双面真理论(dialetheism)追随者的观点,不矛盾律就肯定不是没有争议的。
⑥人们可以通过大量添加条件的方式来促使肯定性论题成为共识:“如果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如果其中包含物理对象,如果存在着具有命题态度的东西,如果……”但是,即便这样可以得到一个非同义反复的命题,从而可以算作没有争议的,那也不符合我对“哲学论题”这个词的用法。
⑦尽管公开这样说听上去很疯狂,但坚称人类(人)是存在的仍然有争议。可以说,取消论唯物主义(eliminative materialism)就得出了人类(人)不存在的结论,可参见昂格尔(P. Unger)1979 年的文章《我不存在》(I Do Not Exist),这个标题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⑧这里显然还需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在理性范围内”(within reason)。对于任何一个论题来说,这种情况总是可能出现的:也许正是因为天空中突然爆发出奇特的Q辐射,这些哲学家便开始否认这个论题;或者,也许是考虑到奇异的不可预见的社会变化,尽管名义上哲学仍在继续,但哲学的整个制度和观念将会发生变化。
⑨就像他的著作《哲学家知道什么》(What Philosophers Know)的标题所强调的,加丁(G.Gutting)曾经提出过一些,确切地说是六个话题,它们与我在本文中讨论的内容有交叉。这些话题已经在我的书中讨论过。其中只有两个是我所理解的哲学论题,但在这里没有讨论它们,而就现在的标准来说,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没有争议的。
⑩分析哲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在先验和经验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区分,相应地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也存在严格的分隔。这种观点得到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家特别的强调,而我却主张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拒斥。
⑪有时人们说,维特根斯坦的反对是用一个不雅的意大利手势传达的,但根据马尔科姆(N.Malcolm)在1958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手势实际是经济学家斯拉法(P.Sraffa)做的,并且还伴着他的一种轻蔑——“它的逻辑形式是什么呢?”而那个手势的确切性质也是有争议的,具体大家可以去咨询谷歌教授。
⑫有关评论可参见福多等人的Against Definitions。
⑬在10 年之内,它的确得到了某种负面评价,认识论家们(比如阿姆斯特朗的Belief,Truth,and knowledge)就直言不讳地写了更加一般性的作品,竭力淡化盖梯尔问题,而且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它,不过他们可不想让我们错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
⑭要把这也称为分析哲学就有点骗人了,因为格莱斯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发展出这个概念以及关于这个概念的理论,而他的发展几乎不是依照日常语言哲学的精神做的。
⑮格莱斯在1975 年和1978 年提出了一种关于会话含意由以产生之机制的理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而且很吸引人,但该理论本身也远非无可争议。事实上在我看来,它已经基本上被驳倒并被代以相干理论的其他版本。比如,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⑯或许“未被承认的帮助”是一种诋毁,而我也必须服从于学术共同体,但是我相信,通过罗素尤其是莱姆塞(F. Ramsey),维特根斯坦对杜威的观点是很熟悉的。
⑰感谢凯伦(N. Kellen)提出了这一点。
⑱我将引用起先是摩尔(Moore)在元伦理学中使用、后来又被艾耶尔(Ayer)用来反驳摩尔本人的“开放问题”(open question)论证。但“开放问题”论证有一种奇异的挥之不去的吸引力,令我惊讶的是,当代元伦理学家试图重新启用该论证的更新且更加详细的版本。
⑲不过克里普克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DR,例如在他1979年的文章A Duzzle About Belief中。
⑳实际上,我在其他地方(The Paradox of Naming)已经称名称的语义学是悖论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