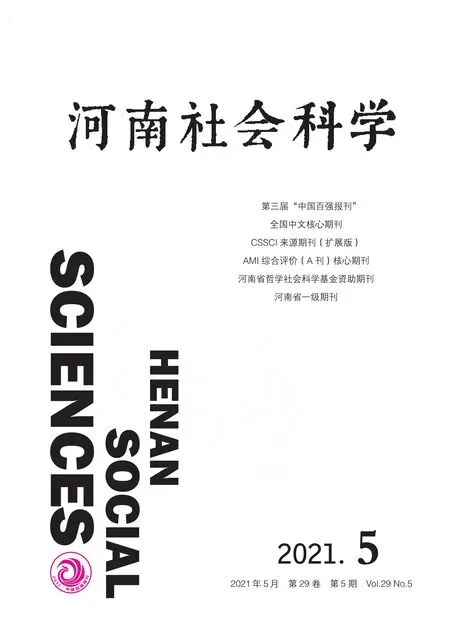论《中庸》的逻辑特征及其内在原因
2021-01-12张红翠
张红翠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作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经典的代表,《中庸》体现了儒家精神的核心与精髓,其精神一直延续到当下时代。但是,现代人在阅读《中庸》时往往会感受到阅读的“困难”,这个“困难”可以描述为:难以迅速获得清晰的“逻辑”线索和内容脉络,难以对文本内容快速做出清晰准确的整体性把握,并最终获得《中庸》文本“杂乱无章”的印象。这种阅读的陌生体验有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地方:这种陌生是来自现代白话文与古文言文之间语言方面的障碍,还是来自现代人对被称为“逻辑”的思维方式与特质的偏好?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先在地有一种意愿或者倾向,总是试图在今天的逻辑框架中理解《中庸》,而结果则是我们又很难在《中庸》中找到当下熟悉的逻辑方式,以至于我们很难“适应”叙事形式上“缺乏”清晰线索的《中庸》。仔细分析,这种阅读感受似乎又隐含着一个前提性判断:我们是逻辑清晰的,而《中庸》则是缺乏逻辑的。那么,当我们本能地以今天的逻辑归纳的方式阅读和理解《中庸》文本的时候,这种做法是否合理,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进而,被现代人接受为理所当然的思维经验是否需要检视和探讨呢?即现代人所谓的“逻辑”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具体指谓究竟是什么?是《中庸》真的缺乏逻辑,还是《中庸》的逻辑另有隐情?这些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在正文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题目所涉及的核心概念——逻辑做一个考察。汉语中,“逻辑”一词由英语logic音译而来,导源于希腊文λογοσ,原意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逻辑”一词最早出现于著名作家严复在1902年翻译的著作《穆勒名学》,这本著作也是传入我国的第一部归纳逻辑的著作。这本书原名《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是19世纪后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中归纳逻辑的总结。书中所阐述的理则学,通称逻辑。1902年,严复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以意译的方式把它翻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一路向前。目前大多数的逻辑学著作在讨论“逻辑”内涵和特质的时候,基本都是偏重于现代逻辑特征,即以演绎归纳为特征的理性思维方式。但“逻辑”的本义还包含着事件内在的关系以及事件发生的方式与状态,不必然以现代理性为特征。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倾向于描述事件(事物、文本)内在的关系与状态,而不专门以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思维方式为唯一标准,并希望在关系性的整体状态和大框架中,同时观照《中庸》文本的逻辑状态及其与现代逻辑之间的差异性关系。
一、离散——《中庸》的逻辑特征
相对于现代以演绎归纳为特征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中庸》的文本状态给我们离散性的逻辑印象。《中庸》文本中的很多段落和细节之间都是“散乱无章”的,《中庸》展开叙事的方式也不是线性顺序的,而是立体发散的,这就形成了《中庸》叙事离散性的结构局面和逻辑特征。具体而言,这种局面和特征表现为多样化和异质化的词汇聚集、说理的反复回环以及《诗经》的不断“闪回”的叙事行为。
(一)词汇的多层系统——世界的基本构成
《中庸》的语汇是非常丰富的,具有多层次特征。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语汇方式提示的恰恰是古人的世界经验。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①。人用语言为世界命名,建立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性关系。因而人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抱世界的。语言本身的结构、样式和元素表明存在者的在世状态,即存在者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安居状态。因而,以什么样的语言自我呈现,本质上表明了存在者当下所体验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状态,也就是说,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同时也指示出人是否在家的现实状况。所以,现代语言哲学看重语言之于世界呈现方式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同样适用于古代人经验表达的语言秘密。在叙事中,词汇是重要的叙事参与要素,也是我们研究《中庸》逻辑方式过程中首先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在考察《中庸》的词汇表现时,我们以名词性词汇为主。因为,名词性词汇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最核心与基本的构成元素,能够最直接地呈现出人的生活世界的外观和特质。《中庸》文本的名词性词汇构成了《中庸》叙事非常突出的一种表现,其词汇使用和选择与我们今天的叙事词汇有很大的不同。《中庸》的名词词汇是实在具体的,《中庸》文本的名词性语汇丰富驳杂、多样具体,包含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和不同性质的语汇,也对应着不同层次的世界事物。《中庸》中的名词性词汇,首先以社会人事一类词汇为主导,如圣人、君子、舜、文王、武王,道、德,礼、乐;父母、兄弟、夫妇、妻子,朋友,子孙,宗器,裳衣、琴瑟;富、贵、贫、贱等,同时围绕以生活具体现象的细化,如货、财等。其次是大量的自然界事物,如天、地、星、辰、日、月,山、川、水、土、草、木、石、华岳河海;动物如鼋、鼍、蛟龙、鸢、鱼、鳖、尺蠖……这些词汇都是非常具体的,显示了古人世界丰富的世界事物,这些世界事物是古人的所感所见所闻以及所念。这样的世界环绕着古人的生命,在他们生命的叙事言说中也自然而然被聚合呈现。中国古人的生命感知就栖居在这些生动的词汇以及与这些词汇相对应的世界中,《中庸》的叙事也栖居在这里。这种词汇方式至少显示了《中庸》世界的两个特质:一个是感性的、具体而非抽象的特质,一个是多元维度的开阔包容的特征。
首先,《中庸》文本中出现的词汇,都是具体感性的词汇。这些名词性词汇共同呈现了可以感知的、细节化的生活情景,充满了万事万物的具体形象。这些词汇的汇集形成了《中庸》世界具象的、感性的而非抽象的特征。古人太熟悉这些活生生的事物,他们时刻与这些生存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在一起,以可感可触的生活经验构建对生活的理解和领悟。而且,这些具体的事物本身就是宇宙深层的“道”: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②。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③。因而,这些名词词汇的涌现便意味着古人能够随时潜入世界存在的深层,亲证无限。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在《亲证无限》中曾描述过类似的经验和观念:“宇宙之根本统一对印度人来说不是简单的哲学思辨,而是要在感情上和行动上亲证这种伟大和谐的生活目标。用冥想和礼拜,用对生活的调整,去培养他们的意识,任何东西在印度人看来都具有精神意义。地、水和光,花和果,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物理现象,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它们正像每一个音符对于完成和音是必要的一样,也是获得完美理想的需要。印度人直观地感到这个世界上现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我们得充分考虑到它,和它建立一种自觉的关系,这不仅是受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对物质利益的贪婪所驱使,而且是以欢乐、平和的伟大情操,以同情的精神去亲证它。”④泰戈尔此中所展示的印度哲学精神与《中庸》精神有相通之处。“无限”“大我”以及“道”一定是以具体的形式呈现于万物之间,因而,按照《中庸》“道在日用伦常”的信念,“道”必须被转化为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的具体行动,道是遍及一切的精神和力量。“道”能转化为宇宙无限形式的活力动力,因此,为了寻求“道”,人类必须拥抱万物,潜心生活。这并不是古人面向世界的自我奴役和盲从,而是通过对“道”的体悟,进入世界万物、触摸万物,与万物同呼吸,从而进入宁静祥和的境界。这个与万物合一而非对抗分离的过程进而引导出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生存状态。
其次,异质词汇是代表多样化事物和不同的世界维度,它们被吸附在《中庸》文本中,呈现了《中庸》文本世界也即古人世界的多样丰富、多维度、庞杂而包容的景象。《中庸》多层次多维度的世界,是“人—万物—天地—宇宙”的世界,其中,不同空间和维度中的事物互通感应、相互沟通。这是宇宙生命系统内部的生命的融合,而融合的前提是生命的开放和生命的包容性。《中庸》的世界同时涵盖了自然万物、人类社会以及天地宇宙不同维度的存在。这种共存的状态表明《中庸》的世界中,万物联系贯通、相互嵌套、相互支持、层层展开。这个开阔通达的世界以宇宙生命为本位,人类生命包裹其中。其间,不同维度的事物不是靠人为的理性逻辑牢牢地锁定、秩序地排列,而是依循世界自然自在的样子存在着,每个生命自由地悬浮在世界中,飘逸但又确定,都安在于自己的位置上,有秩序但是没有贵贱之分。可以说,《中庸》这种词汇系统呈现了古人基本的世界图像,它是具有广延性、多层次性和开放包容性、整体性的多元世界,也是离散性的自在世界。
再次,天地万物与人事的同时共存表明古人生存视野极其高远,所及极其广阔。这种理想暗含着古人面向万物的普世胸襟——万物都有价值,万物并行而不悖的原则。而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及自然万物的生动涌现,又使古人的世界视野始终不离“大地”,形而上与形而下、有形与无形,以及天、地、人始终在同构性生命关系中得以关联。所以,《中庸》的世界非常丰富,天上地下、山川花草、虫鱼鸟兽,都出现在古人的叙事当中,出现在古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中,构成古人的思想本身。因而,生存世界的各种事物对于存在者而言都具有世界性、哲学性和启示性。多种性质以及多种类型事物在《中庸》中同时并列出现在一起,这种叙事方式在现代说理表达中几乎很难出现。正是这一点的不同,显示了《中庸》的世界与现代世界倾向之间的差异性意义。这种差异在于《中庸》词汇所显示的世界方式是一种包容性、整体性存在哲学的显现,它展示的是人类生命与万物同在的生存情感。天地宇宙向人类存在着,这是古人深刻体验和面对的生存世界,这个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从四面八方拥向存在者,人类也迎向宇宙而存在。这种生存判断和体验决定《中庸》叙事展开的逻辑状态是立体发散的,而不是线性顺序的。
(二)说理的并列叠加方式
作为一篇说理文,《中庸》在说理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并列与反复的方式,这主要是通过语录体的运用而实现的。按照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的批注,《中庸》共分为33章,大部分章节都是以语录转述的方式展开的,且不加论证分析和说明。其中,从第2章到第11章,以及第13章、第20章全部由“子曰”起始,引出孔子的语录,以此说理。在这些段落中,孔子语录成为《中庸》说理的主体部分,这使《中庸》呈现出典型的语录体行文方式。语录体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叙说文体,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先秦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行的《论语》及宋代记载程颢、程颐言行的《二程遗书》,都是古代语录体的文本典范。其中《论语》简明深刻、语约义丰,往往在一两句话里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生经验,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警句和格言。作为一种文体,语录体有自己的特点,它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采,不讲篇章结构,不讲篇与篇之间甚至段与段之间内容上的必然联系。而《中庸》对语录的采用则表明《中庸》在结构叙事的时候与语录体的结构方式是一致的。以对话式的语录体为主的叙事方式与逻辑严密的推理论证方式截然不同,呈现为片段叠加、罗列行进的结构方式,在逻辑特征上则是离散性的和非线性的。与现代以推理归纳为特征的逻辑方式迥然不同。
(三)《诗经》片段的反复出现
在《中庸》的叙事说理中,有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诗经》的反复出现,每当作者说明一个道理时,便相应地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表面看,这些诗句是以举例子、打比方以及类比的方式被引入的,但是,《诗经》在《中庸》的叙事中的作用却远不止于文献支撑材料。基于《中庸》文本的整体考量,《诗经》的反复出现,构成《中庸》叙事的结构性动力,是《中庸》叙事中具有独立性意义的存在性部分,之于《中庸》文本的说理层面而言,《诗经》更像是“箴言”和“训示”,是一种永恒的记忆形式,成为《中庸》叙事组织当下生命经验的有效方式。因而,《中庸》整个文本不断回复到《诗经》本身,反复地、习惯性地引证《诗经》。这种叙事行为循环往复,形成不断回到一个源头、一个经典的文本过程,这种做法使得《诗经》在《中庸》中的存在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叙事的意义,而具有了存在层面的象征性和符号性意义。也就是说,《诗经》在《中庸》中被呈现为一个历史传统和理解世界的重要形态与可能,一个中华文化生命的法则和“训示”——“诗经”之意也是一种“天命”之意。就叙事形式而言,对《诗经》的不断引证,使《中庸》的整个文本被收摄在以《诗经》为具体符号的磁力场中,结构上则呈现出非线性的、盘旋辐射的运动倾向和回环往复的逻辑趋势。同时,文本中的“引证”性特征也内在地分离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即《中庸》文本及其意义与《诗经》文本及其意义之间的映照性的互文性结构。
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者茱莉亚·克利斯蒂娃在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时候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⑤。这意在提示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和互为指涉性关系(关于《诗经》在《中庸》中的结构性意义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过)。当我们启用当代叙事学理论观照《中庸》文本结构的时候,我们能够建构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中庸》的结构性图示。也就是说,《诗经》在《中庸》文本中的反复出现,客观上造成了《中庸》文本叙事的结构性分层:相应于《中庸》叙事的文本表达层面而言,《诗经》构成《中庸》文本的阐释性层面。这两个层面构成一种后者不断向前者回访的关系,即现代叙事学理论意义上的“互文性”结构关系。互文性理论所揭示的现实,恰恰是从现代归纳演绎逻辑绕开去、不经过推理演绎的中介环节直接与生命乃至世界源头相连接的叙事现实。或许,现代叙事学理论有关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从反向的意义上正说明了古代叙事逻辑的合理性与文化自在性。
作为《中庸》的互文部分,《诗经》为《中庸》的世界提供了源头性的意义符码,使得《中庸》文本在不断回访《诗经》的过程中得到阐释,这种文本结构体现了《中庸》思想哲学背后的历史观念和生命观念,即大历史观和大生命系统观。因为,《诗经》在《中庸》中的闪回意味着《中庸》将生命乃至文化以及思想,理解为一个由过去到未来的时间的绵延和展开;后来生命的意义需要在先在的历史性生命链条中得到理解和实现,因而需要不断回到源头,回到生命的典范、法则之处。这就是叙事中回环往复形式的内在根源,这种叙事方式不同于现代理性逻辑框架下演绎前行、不断脱壳的运思方式。就像罗兰·巴特在《文本的意趣》中对“互文性”所作的解释那样:“我体会着这些套式的无处不在,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我明白,至少于我而言,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直接就是参考书,是全然的体系,是整个文学天地的曼陀罗。普鲁斯特的作品不是权威,它只是一段周而复始的记忆。互文正是如此:在绵延不绝的文本之外,并无生活可言——无论是普鲁斯特的著作,是报刊文本,还是电视节目:有书就有了意义,有了意义就有了生活。”⑥罗兰巴特在互文世界中体会到一种诗意的秘密——生命(文本)之间相互连接的隐秘。同样,在“互文性”的文本关系里,《诗经》与《中庸》文本层之间构成意义的衍生与互释性关系。这就在客观上阻断线性逻辑生成的可能,从而使《中庸》文本呈现出回环往复的逻辑特质,这种特质也强化了《中庸》文本的离散性特征。
二、离散逻辑的内在动因
在分析了《中庸》离散逻辑的具体表现之后,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中庸》说理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逻辑方式?我们试图从中国文化基因以及口语文化特质两个方面给出解释。首先,在中华文化基因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庸》的叙事,一个是天人合一思想,另一个是崇古宗经思想。如前所述,不同性质、不同维度的事物的并存使得《中庸》行文的表层状态呈现松散的、发散的、片段的、平列的,甚至是“混乱”的状态。这种非线性、“非理性”的逻辑特征与中国古人领悟自然万物及生存世界的无限开放与圆融态度有关,与中国古人领悟生命内涵的灵感方式有关,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其中,“气论”便是古人天人合一灵感方式的重要体现,“气”是游动的、流散的、飘浮的,它无形弥散而无处不在。同时,《诗经》的反复出现,又体现了古人“述古而不作”、崇古宗经的历史观念和生命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素有追源溯流、崇古宗经的思想传统。《隋书·经籍志(二)》曾指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⑦这段话指出刘向、刘歆父子剖析条流是则古之制,并将此古上推至史官和孔子,道破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在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又占据重要位置。就孔子对古代学术史的贡献与影响而言,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性格。《中庸》中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崇古宗经的一种表现,而《诗经》又是儒家经典之一。这种性格使得孔子更多地沉浸在历史往事中,以其内心的敏感,从人类善的美的行为中,形成其道德律和价值观,并择善而固执之。这必然影响后来的学术传统和习惯。同时,孔子奠定了中国古代尊师重教的传统,其所引发的师承关系又影响了思想表达的宗经立场与传统。这一传统的基本特色是思想家通过注释经典表达思想,建立体系,使得他们的思想成果,总是含蕴着旧学与新知两方面,尤其强调新知对旧学的继承关系⑧。刘勰《文心雕龙》亦表达了这种崇古宗经的思想观念。其中《宗经》《原道》所表达的也是这个道理。于是,不断回到《诗经》便成为一种《中庸》自我呈现的极其自然但又不自觉的言说方式。
其次,口语文化时期的表达气质和技术习惯也促成了《中庸》文本的逻辑状态。客观上而言,《中庸》叙事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我们所分析的逻辑状况,还与《中庸》文本所产生的口语文化特质有关系。口语文化时期的表达有特定的习惯性方式,《中庸》的逻辑表现正是这种叙事“技术”和习惯的表现。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对口语文化进行了界定,并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逻辑性差异做了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和非常有价值的探讨,这也是我们探寻《中庸》文本逻辑特质的另一个有效切入点。通过对无文字或者印刷术浸染的“原生口语文化”的全面细致的分析,沃尔特·翁反复强调,口语文化时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与书面文化、印刷文化的线性以及理性方式不同,并对比总结出口语文化时期的九个方面的表达特征。其中以下六条特征尤其为我们理解《中庸》离散性逻辑特质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现代理论视角:一是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口语文化经常用“和”(and)来连接上下文,而不是书面话语经常使用的“然后”(then)、“当什么时候”(when)、“因此”(thus)等线性顺承的连接词,若此,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逻辑方式就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并列关系的,后者是线性螺旋向前的⑨。《中庸》文本的“子曰”在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和”(and)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二是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文化喜欢说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事物而是具体的事物。因此,口语文化里承载着大量的具体称号(这些称号也是事物的呈现)⑩。《中庸》中大量具体事物的出现和列举就是这种聚合特征的体现。三是冗余的或“丰裕”的。口语文化中的冗余,是因为没有文字的固定,言说者要想保证前后内容的连贯并被记住,就需要不断提起之前刚刚说过的话⑪。《中庸》中《诗经》以及“子曰”的内容都是传统沉淀下来的不断被说起的“话”,不断提起之前的“话”就成为说理的一种套式——冗余的套式。四是保守的或者传统的。这不仅是观念上的还是技术上的,因为,在原生口语文化里,如果不用口诵的办法重复,观念化的知识很快就会消亡。所以,口语文化里的人必然花费很大的精力,反复吟诵世世代代辛辛苦苦学到的东西。这就慢慢确立了一种高度传统或者保守的心态⑫。所以,《中庸》对于《诗经》和“子曰”语录的重复,既是以套话方式对文化知识与观念进行技术保存的过程,又是传统保守的文化体现。总之,“子曰”语录以及《诗经》在《中庸》中的出现方式是口语文化表达技术的一种综合性体现。五是贴近人生世界的。繁复抽象的范畴依赖文字给知识提供结构,使之和实际的生活经验拉开距离。口语文化里没有这样的范畴,也缺乏广泛使用的文字工具提供支持,所以口语文化在使知识概念化、用口语表达一切知识时,不得不多多少少贴近人生世界,以便使陌生的客观世界近似于更为即时的、人们熟悉的、人际互动的世界。所以,口语文化中几乎不存在脱离人的活动的统计数字或者事实。相反,书面文化能够使人疏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人失去自然的天性⑬。而口语文化则相反,能让我们看到驳杂的世界物象。《中庸》以具体感性的词汇来表达思想信念的方式恰好体现了这一特征。六是原著中为第9条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式的。一切概念性思维都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而口语文化则往往把概念放进情景的、操作性的框架里,这些框架只有最低限度的抽象性,就是说它们贴近活生生的人生世界⑭。《中庸》词汇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如伐柯,如登高必自卑等)也体现了这样的文化特征。
以上六点特征,不仅符合《中庸》的文本方式,也可以解释《中庸》文本逻辑的深层动因,因此也更确证了《中庸》文本逻辑的内在合理性。
三、离散——古老生命经验的文化呈现
与现代理性逻辑相比较,离散性的逻辑是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的,是立体性而非直线性的,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而这种逻辑特征与整齐简洁明晰的现代理性逻辑特征构成经验的反差,从而促生现代阅读者的接受“障碍”。然而,这种“障碍”的阅读感受恰恰能够提醒我们反思两种文化经验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背后价值观念的不同,并以此为契机对现代文化经验进行检视。在检视的过程中,一个认识越来越清晰,即今天的人们在理解或者是对《中庸》进行“翻译”的时候一定嵌入逻辑归纳的意志,这其实是现代人的理性“偏执”,这种“偏执”背后则是现代生命与古代生命之间经验的巨大隔阂。这种逻辑差异让我们看到,现代逻辑在更加清晰和更加明确的同时,在理性获得的同时,也失落了许多丰富而难以规约的存在状态,最重要的在于失落了一种生存的整体性,失落了一个本可以向人类敞开的“世界”。相反,《中庸》离散性的逻辑方式,对应着深层本质的“整体性”。因为,离散力与整体的收摄力是相对应的:“离散”也对应着世界的整体、生命的整体。这种整体性包含了社会人事、自然万物和哲学理念的各个层面。
厘清这些问题,开篇提出的问题似乎应该作如下修正:不能说《中庸》没有逻辑(如果此处我们一定要用“逻辑”这个概念来谈论问题),只能说,《中庸》的逻辑与我们今天的逻辑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背后隐藏着的,则是《中庸》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生命感受方式、文化表达方式乃至世界观的本质性差异。
与口语文化相反,书面文化时期的叙事表现大相径庭。由于印刷术以及印刷书籍的兴起与普及,文字的阅读开始逐渐改变人类的诸多习惯:文字阅读逐渐促进和养成人们的理性思维方式,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⑮。印刷书籍的线性编辑方式、阅读的自前至后的循序展开方式养成了现代社会时间性的逻辑爱好与习惯,“在18—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⑯。所以,现代人的逻辑偏好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这种逻辑偏好既构建了强大的人类的自我世界,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人类生活感知的范围。因为,理性逻辑具有自恰的特质,但也具有封闭的特点,清晰但往往缺乏包容。美国作家沃尔克·珀西——经常被看作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在《作为错误的隐喻》中记录了一段童年的往事: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和父亲在原始森林里长途狩猎,当时他看见过一种奇妙的鸟,十分惊奇,于是问土著向导那鸟的名字,土著向导告诉他,那是蓝美元鹰。但是父亲纠正了他——那根本不是什么蓝美元鹰,而是蓝鱼鹰。珀西记述说,他仍然记得面对纠正时的失望心情。这种失望在于孩子想要的是面对世界震惊体验的唯一性,而父亲的纠正以及在现代理性标准判断下的“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则在标准化的归类中破坏了这种唯一性的生命体验⑰。
所以,当今天的我们试图用逻辑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避免将世界简化和机械化的危险。正如沃特尔·翁所言,“不论是再现自然的必要性还是自然本身获得再生的力量,都意味着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通过改造,它可以变得容易理解和控制”⑱。我们可以把这种“控制”理解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力量的体现,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种“控制”看成人类对世界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丧失,进而人类生命的可能性也因此极大地被限制。
最后,口语文化时期的文化特点就不具有理性分析能力吗?如果有理性的分析能力,它们是如何表现的呢?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认为,“并不是说书面文字之前分析思维是不可能的,它指的不是个人的潜力,而是一种文化气质的倾向。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⑲。而口语文化则不同,它对世界理解的呈现则是以上沃特尔·翁所总结出来的九种特质为表达方式的。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庸》文本叙事不是没有逻辑,而是其逻辑方式与今天不同,《中庸》的逻辑方式契合的是口语文化时期的表达特征,与书面文化表达逻辑完全不同,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进而,口语文化时期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书面文化、印刷文化的线性以及理性方式的差异,表面是特定文化场域中的表达技术和语言习惯,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如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⑳
注释:
①海德格尔:《通向语言的途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②③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6—27、27页。
④[印度]泰戈尔:《人生的亲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6页。
⑤[法]克莉斯蒂娃:《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Seuil出版社1969年版,第115页、133页。
⑥[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⑦⑧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5页、155—119页。
⑨⑩⑪⑫⑬⑭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8、29、29—31、31—32、31—32、37—43页。
⑮⑯⑱⑲⑳[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62、62—63、87、62、11页。
⑰冯俊等著:《后现代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