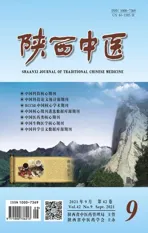孙思邈关于麻风病诊治探讨
2021-01-11卢芬萍呼兴华李耀辉范增慧王晓琳周永学
卢芬萍,呼兴华,李耀辉,高 原,范增慧,王晓琳,周永学
(1.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03;2.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在我国医学史上,唐代医家孙思邈被称为第1位麻风病专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总称《千金方》)中总结了唐代以前有效治疗麻风病的经验,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主要是由体虚外感风邪疠毒,治疗用药以解毒杀虫、祛风、清热除湿为主,根据病情采用口服、外涂、洗浴、浸汤等多种治疗方法,强调服药后饮食禁忌的重要性,并且注重生活方式调摄、传染病的预防,率先在山中设置病床对麻风病患者进行隔离治疗,不仅使患者远离世俗的歧视和排斥,还防止了麻风病的传染。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医家对麻风病的定义和解释略有不同,有“疠、厉、大风、癞疾、恶疾”等,因其描述的症状与现代医学所定义的麻风病类似,后世学者大多将其归为麻风病范畴[1]。自《战国策》中记载殷商时“箕子漆身为厉,以避杀身之祸”始[2],《论语》《黄帝内经》《山海经》《神农本草经》中渐有对麻风病症状、病因病机和治疗的论述,隋以后的中医典籍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解围元薮》《疯门全书》等,对麻风病的认识则更加系统和全面化。但如果从学术地位、理论水平、临床技术的高度审视,我国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对于治疗麻风病所做出的贡献较大。笔者通过汇集孙思邈《千金方》中相关章节,结合后世医家的认识与理解,揣其中要点归纳如下,供临床应用参考。
1 论病名,以恶疾为著
麻风病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大量的史学、医学典籍皆对其有记载。《五十二病方》将麻风病称为“冥病”,一曰麻风病人如活死人一般,二曰麻风病变表现如虫噬植物一般[3-4]。《内经》称麻风病为“癞风”“大风”“疠”,原文记载“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癞风”。《长刺节篇》曰:“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风论篇第四十二》:“疠者,荣气热跗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也,皮肤疡溃”[5]。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一则麻风病诊断的医案: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 伍) 丙,告曰:“疑癘,来诣”,将麻风病称为“癘”[4]。《神农本草经》记载了麻风病治疗相关药物,如“锻石主癞疾,天雄主大风,巴戟天、姑活主大风邪气,枳实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兰茹除大风”,将麻风病称为“癞疾”“大风”[6]。巢元方则将其记载为“大风、恶风、癞”。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将麻风称为“恶疾”“大风”。直到宋朝官修《太平圣惠方》, 正式提出麻风病一词,曰:“治大风癞、顽麻风病、紫点、白癜,宜服此方”[4]。由此可见,麻风的病名由“疠”“冥病”“癞风”到“恶疾、大风”,包含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对其每一阶段所蕴含的真实意义,需结合历史进一步考证辨析。
2 论病因,沿用风邪致病
麻风最早在《黄帝内经》中被称为“疠风”,《素问·风论》有言:“疠者,有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5]。《黄帝内经》中关于风病的记载约50余种,认为“风为百病之长,风之伤人,其病各异,其名不同”[7],如《素问·骨空论》说:“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素问·风论》篇又提及五脏六腑之风状,如“疠风、漏风、首风、肝风、心风、脾风、胃风、泄风”等,所论风病多以外风为主,兼及内风[8]。《内经》之后,医家对于内风外风皆有争论,唐宋以前医家多以“外风、内虚邪中”立论,唐宋以后,则以“内风、本虚自中”学说为主[9]。孙思邈遵循《内经》“风病”的概念,提出“风为人体之常气、风气不调,百病丛生”,既强调外风,又注重内风,但也未明显分别外风、内风[10]。《千金方》中孙思邈将麻风病论为“恶疾大风”,并在“耆婆篇”指出疾风有404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根据脏腑辨证分为“青、赤、黄、白、黑”五风[11],《说文解字》释:“风,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由此延伸出麻风的病因病机以“风虫”学说为主[12]。
3 论病机,虚风夹湿,和合生虫
《内经》认为麻风的病因病机以“疠风,风寒之邪客于血脉卫气”为主[5],隋代巢元方在《内经》基础上,提出“毒虫”之说,认为“五风化五虫”,指其症状变化多端。孙思邈继承前人关于“疠风”的认识,从“风、虫”之说,强调麻风病系“热湿”致病,设“恶疾大风”与“耆婆治恶病”篇对麻风病进行专门的论述。
孙思邈所处的时代内外交流频繁,印度医学随佛教传入我国,引用印度医学“地水火风 ,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13],汇通《黄帝内经》中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皮部、经脉理论认为“风合五脏,五风即黄风、青风、白风、赤风、黑风,五风生五虫,若食人脾,语变声散;若食人肝,眉脱坠落;若食人心,满身生疮;若食人肺,鼻柱崩倒,鼻中生息肉;若食人肾,耳鸣啾瞅,或如车行雷鼓之声;若食人皮、皮肤顽痹;若食人筋,肢节坠落”[14],生动形象的描述了“虫”邪侵袭人体不同部位的临床表现。黄风即脾风,脾发声为歌,虫袭脾脏则说话声音嘶哑;青风即肝风,足厥阴肝经上行连接于目出于额,若虫袭肝脏,则眉毛脱落;赤风即心风,心主血脉,属火,心火亢盛,则血脉营血受扰,热为火之渐,热盛迫血妄行,外熏蒸肌肤而生疮;白风即肺风,鼻为肺之外候,肺气通于鼻,虫袭肺脏,其脏有热,则鼻气不和,津液壅塞,停结鼻内,可见鼻梁塌陷或变生息肉;黑风即肾风,肾为先天之本,藏五脏六腑之精,肾气调和,则耳闻而聪,虫袭肾脏,肾气不足,则可出现耳鸣如虫的细小叫声,或如车轮滚动、击雷打鼓之声;虫袭皮肤,则皮肤麻木,不知痛痒;虫袭筋,筋受风热则驰纵,出现四肢关节下垂,或肢节坠落。至于“恶风”的起因,多由患者用力过度、饮食失常、房事不节而致汗孔开泄引起脏器虚衰,加之气候失常,冷热交替,或湿地而卧,外邪流入五脏、通彻骨髓,诱发此病。体现“虫”之生成离不开“湿、热”邪之外部因素,此所谓“虚风因湿,和合生虫”。病理研究发现麻风杆菌主要侵犯人体皮肤及周围神经,严重者可累及深部组织及内脏器官[15]。这与孙思邈早年提出的麻风病起病多因感受“热与湿”之邪,“虫可食人五脏、皮、筋、甚者入骨髓”之理论相吻合,由此可见孙思邈对麻风病认知理论的先见性与可贵性。
4 论用药,杀虫祛风、清热除湿
孙思邈在治疗麻风病的过程中,主要以解毒杀虫、祛风、清热除湿法为主,代表方剂有阿魏雷丸散、苦参消石酒、岐伯神圣散、锻石酒、蛮夷酒等。同时辅以大白膏外涂改善顽痹,大黑膏外用治疗疮脓溃疡,浸汤法、洗浴法等促进疮口愈合、毛发再生。尤其重视松脂、苦参等药物的应用,苦参清热燥湿,“至神良”,炼松脂“绝谷治癞第一”,古籍中曾记载“病士入山,教服松脂,服至百日,须眉皆生”[14]。辽宁省麻风病院曾报导,苦参散(以苦参为主药)可以辅助治疗晚期良性麻风病及早期恶性麻风病体质较弱者[16]。福建省麻风病防治院曾使用松香散改善麻风病患者症状[17]。广东省高州县卫生防疫站用精制松香丸及15%精制松香注射液治疗14例麻风病患者(瘤型11例、结核型3例),结果7例显著进步、6例进步、1例恶化,有2例瘤型患者3个月后细菌转阴、未见明显副作用;青岛麻风病院用苦参丸治疗15例瘤型麻风病,1~2年后1例接近治愈、11例有效、3例无效[18]。现代医家也将松脂和苦参用于治疗其他皮肤病如银屑病、湿疹等[19-20]。由此可见,孙思邈的用药经验对后世麻风病乃至其他皮肤病的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5 论治疗,药物治疗为主,食疗为辅
孙思邈认为合适的饮食有助于药效的完全发挥,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服饵”篇详细论述了服药后饮食禁忌,如“凡服药,皆断生冷、醋滑、猪犬鸡鱼、油面、蒜及果实等”[14],并且在其他篇章论述疾病时详细记录了服药后所忌事项。
《千金方》记载“服阿魏雷散,则不得食五辛、猪肉、鸡、犬、秽食、臭恶之食,大嗔怒、房室,皆忌之”;“服苦参消食酒,第一忌房室、房室脉通,其虫得便,病即更加,大怒、大热,禁食黏食、五辛、生冷、大醋、酪、白酒、猪、鱼、鸡、犬、驴、马、牛、羊等肉,皆为大忌,其余不禁”[14]。此处“五辛”即小蒜、大蒜、韭菜、芸苔、胡荽,皆辛温之品,易发风、动气、助热,病热者应忌之[21]。猪、鱼、鸡、犬肉等笔者认为泛指一切肉类肥甘厚味之品,易伤及脾胃,脾胃失于运化,则湿热内生或食积生热,热邪易促进“虫邪”对机体的损害。“生冷”指冷饮、冷食、未加热煮熟之品,“黏食”大多指以糯米做成之品如汤圆、麻团、年糕等,“酪”指乳制品,此三味皆为黏滞不易消化之品,易伤中阳,阻碍脾胃运化,生痰湿、助邪热,使正气不能完全抗邪,延误病情。大醋,酸温偏涩,易滞涩阻气、壅塞气机、妨碍脏腑运化功能。“白酒”助邪热。“秽食、臭恶之食”指霉变,有臭恶气味的食物。这里主要体现了孙思邈讲究饮食卫生的思想。禁大怒,不良的情志因素会影响机体脏腑功能,阻碍疾病的康复。禁房事,因为房事使脉通,虫得其精液则使病情加重。
以上服药后禁忌,孙思邈多从麻风病的病因病机考虑,他认为麻风病的生成离不开“湿、热”两邪,而内伤饮食则生胃火,暴怒则生肝火,房劳则生肾火,内火炽盛,火动血热,挟风而为风火,挟湿则为湿热,熏腐肌肤,加重“虫”邪对脏腑的损害,因此服药后应忌之[22]。
6 论预防,首创隔离法
《千金方》收集了唐以前各医家“疫病”防治的理论思想,隋唐时期受佛教等宗教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将麻风病赋予“鬼神”学说,认为本病因鬼神或天命之惩罚所致,或是因为前世干了坏事,今世遭到报应;或者祖辈的恶行应在子孙身上所致,并未对麻风病的防治有科学的对待,使得麻风病患者甚至亲属,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和偏见,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缺乏认识有关。《备急千金要方·恶疾大风》所载:“余以贞观年中,将一病士入山”[14],孙思邈率先在山中设置麻风病床是防止麻风病传染的重要手段,类似现代的“隔离”法。“隔离”法的意义包括:一方面保证了远离世俗外界的偏见,体现一种避世的思想;另一方面,山中环境清新、无秽浊之气,可进一步防止麻风病的传染,有利于疾病的恢复;最后,孙思邈当时已经观察到有些麻风病患者“爱恋妻孥,系着心髓不能割舍,直望药力,未肯近求诸身”[14],而在山中治疗可绝其嗜欲,断其所好,有助于疾病的预后。总之,孙思邈当时已认识到环境隔离对疫病发生的关键作用,对目前中医药防疫思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价值。
7 小 结
麻风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染病,所涉及的不仅是医学问题,还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千金方》中孙思邈关于麻风病的病因学认识,以风、虫之邪为主,强调热和湿为致病重要因素;治疗方面,以苦参、松脂最为常用,重视药后调理;注意饮食宜忌,巧用单方、简易方,率先将麻风患者引山“隔离”治疗。当时因宗教的盛行,出现了大量寺院医学,各州府设立了诸多如“疠人坊”类的传染病院,为我国最早的隔离设施,而根据世界医学史记载,西方最早的麻风病院约建于十字军东征时,较孙思邈所处时期至少晚了4个世纪。由此可见孙思邈提出的“隔离”治疗思路对后世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意义。现代医家在临床上对《千金方》治疗麻风病方药的发挥较多,如松香散、扫风丸、苦参散等,治则上尤其重视解毒祛风、清热利湿。时至今日孙思邈治疗麻风病的治法、方药仍然为临床诊疗提供了理论及实践依据。
《千金方》中“疫病”病因病机学说、防治结合思想,得到了较多的借鉴与使用。孙思邈对于疫病病机和防治认识,广泛地影响着后世医家,并推动了现代中医疫病学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