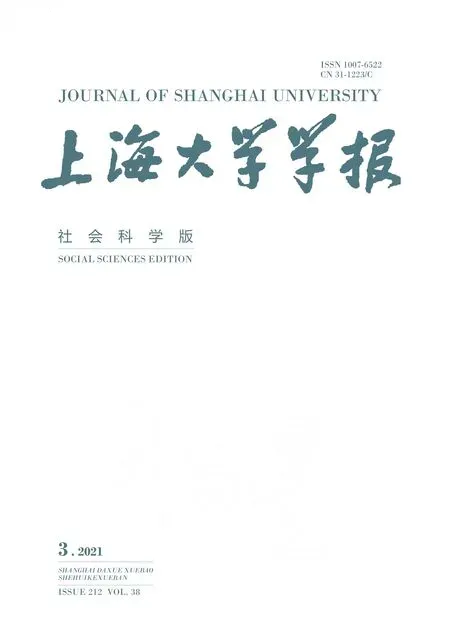现代权利理论争论程序性解决方案的贡献与缺憾
——与彭诚信程序性权利观商榷
2021-01-08张玉洁
张玉洁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现代权利理论肇始于西方启蒙时代,是以理性信念和个人主义为基础对权利现象作出的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1]由于两种理论将权利解释为不同的事物——意志理论解释为意志或选择,而利益理论解释为利益——因此两者之间的争论在西方近代法学理论史上一直持续不断。
关于在两种权利理论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在西方自这些理论产生之初就颇多争议。①除提出和传承两种权利理论的相关学者的著述外,对两种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2011);Peter Jones,Rights(St Martin’s Press,1994);Hillel Steiner,An Essay on Rights(Wiley,1994);S J Stoljar,An Analysis of Rights(Macmillan,1984);Brian Bix and Horacio Spector(ed),Rights:Concepts and Contexts(Ashgate,2012);R G Frey(ed),Utility and Right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就国内而言,夏勇于1992年出版的《人权概念起源》一书对两种理论进行介绍,之后,随着相关领域外文著作的翻译和理论资料的汇编逐渐增多,这两种理论逐渐为学界所熟知,同时,以两者为基础诠释权利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彭诚信所著《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彭诚信不仅对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产生背景、基本诉求和各自优劣进行了详尽梳理,更跳出它们在权利实体问题上的一贯纠缠,尝试以程序性权利观解决两者之间长久的争论。
在笔者看来,彭诚信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彭诚信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补足了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两者的超越;其二,以程序性问题为集中关注点研究权利问题,实现了权利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上的转变;其三,程序性权利观的提出使我们意识到现代权利理论所处的基本哲学定位。
当然,作为一种全新的权利理论,其提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争议和挑战,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权利领域发挥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作用。事实上,即便在促使学界以一种全新的哲学视角审视现代权利理论争论这一点上,彭诚信的观点及阐述也已经是功不可没了。
一、现代权利理论争论的哲学定位:实体性纠葛
彭诚信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使我们意识到,现代权利理论争论的核心在于什么是权利,即何种事物是我们通常所称之权利。[2]这种追问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权利本质抑或权利概念的实体性争论。由于这种实体性关涉,既有理论始终无法为权利现象提供全面可行的解释。
(一)现代权利理论概览
现代权利理论中的意志理论缘起于康德。在其哲学理论中,权利被界定为一种将定言命令的可普遍化要求外化为行为的意志。[3]20-24经由萨维尼、温德夏特等人的传承和发展,到20世纪末,康德的理论在哈特(H.L.A.Hart)那里形成了意志理论的另一重要分支——选择论。②温德夏特对康德意志论的传承和发展,可参见(法)莱翁·狄骥著《宪法论》之第一卷“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页。选择论认为,权利的本质应当是权利人对义务人义务履行行为的一种选择。[4][5]由于都强调个体意志在权利界定中的核心地位,康德和哈特的理论均被视为意志理论传统的组成部分。[6]239利益理论产生于比康德稍晚的边沁以及他们的后辈密尔。边沁和密尔均认为,权利并不必然与意志或选择相连,相反,他们将权利视为法律上认可的利益。[7][8]20世纪末,利益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渐精细化的过程——拉兹(Joseph Raz)、麦考密克(D.N.MacCormick)和大卫·里昂斯(David Lyons)等分别将能够成为权利的利益解释为足够将他人置于义务之下,在一般情况下为权利人带来好处,为法律所承认并旨在使权利人直接受益的利益。[9][10]149,152[11]国内的许多学者也认可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对权利的基本解释。①例如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彭诚信《现代权利理论: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集中关注的是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除此之外,现代权利理论争论还包括许多其他对权利的不同认识,例如源于格老秀斯并被麦克洛斯基(H.J.McCloskey)和米尔恩(Alan Milne)承袭的资格论,该理论将权利视为进行行为、要求、占有、所有和获取的资格。[12][13][14]资格论也为国内许多学者尤其是法学类教科书所采纳。②例如陈守一、张宏生:《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从古罗马时期受害人可以根据法律要求提出救济主张的实践中生发,于19世纪末期在英语世界广为流行并最终被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加以系统化的主张论,也是现代权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主张论认为,辨别一个事物是否是权利的关键,在于权利人能否提出主张。[16]此外,由于权利所涉面向众多,许多学者将诸多要素融合起来作为权利概念的界定,这一理论可以称为要素理论。最著名的要素理论推崇者当属霍费尔德(Wesley Hohfeld),[17]尝试将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结合在一起以解释权利现象的维纳(Leif Wenar)和斯威尼华申(Gopal Sreenivasan)也可以算作该理论流派的成员。[18][19]国内一些学者也持有此种观念。③例如葛洪义:《论法律权利的概念》,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1期;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545页。
(二)争论的实体性关涉
现代权利理论争论的哲学根基是关于权利实体性问题的不同认识。实体性问题与程序性问题相对,在权利问题上,前者关注的是何种事物是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权利,而不关注经由何种程序权利得以存在和实现;后者则恰好相反,权利的程序性问题所追问的是权利——尤其是法律权利——如何能够在法律体系内生成、实施并由个体所切实享有。程序性问题是彭诚信程序性权利理论构建的重点。事实上,正是彭诚信对程序性权利观的提出和论证,凸显了既有权利理论在实体性问题上的集中关注。前述意志理论、利益理论、资格理论、主张理论和要素理论等,关注点都在于一般权利观念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即几种理论分别将意志、选择、利益、资格、主张或多种要素融合作为认定权利的标准。对于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这些事物如何能够形成具体权利从而参与其中,并没有过多的论述。
2)中国8m3户用沼气池生命周期成本为3 082元,其中运行和维护费占户用沼气池的全生命周期成本的42.8%。
虽然关于权利本质或概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涉及程序性问题,但这并非现代权利理论的核心。例如关于权利究竟是意志、选择抑或利益的认识,会影响立法者和司法者在立法和裁判过程中对权利形式和归属的认定,进而影响相关主体对权利的享有。但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判断的标准仍然是实体性的,即通过权利与何种事物相连的观念对权利进行确认和分配,而确认与分配的程序在对权利本身的考虑之外。换句话说,在现代权利理论的视野中,权利的程序性问题是外在于权利的,关于权利本质或概念的探讨,并不经由其外部经验或要求决定。
(三)诸多权利现象无法解释
现代权利理论对实体性问题的集中关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法对既有权利现象做出全面有效的解释。这是导致迄今为止权利理论之间争论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彭诚信尝试从程序性问题切入权利现象的一个潜在考量。
一方面,现代权利理论主要是对私法权利本质的总结,无法实现对公法权利的有效解释。基于不同的考虑所提出的权利,其实体性问题的答案——或曰本质——必然有所不同;对一类权利实体性问题的关涉,可能无法对另一类权利予以解释。在区分公私法的理论中,公法权利的目标主要在于赋予个体以避免国家干扰或要求国家行为的能力,而私法权利则在于赋予个体以避免他人干扰或要求他人行为的能力。[20]现代权利理论的构建大多以私法权利为基础,例如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就均是以霍费尔德的主张为核心构建其基本理论体系的。[21]244-246那么,霍费尔德的其他权利要素可能就无法获得解释。例如,选择论就难以解释豁免——例如免受酷刑的权利——因为即便权利人放弃其权利,义务人(例如国家)也没有理由不履行其不得施加酷刑的义务,权利人对义务履行行为的选择无法体现。[22]这也正是利益理论认为意志理论解释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哈特后期提出不完整的选择仍然能够成为权利的理论补充,①关于这一补充理论,可参见H L A Hart,"Bentham on Legal Rights"in Jules L Coleman(ed),Rights and Their Foundations(Garland,1994)1,26。但是缺口一旦出现,选择论对权利现象的解释力就已经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现代权利理论往往注重对处于法律运行某个特定环节中权利现象的理解,对于该权利在其他环节中可能产生的不同观感经常缺乏解释力。一般认为,法律运行包括四个环节,即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权利在不同的环节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如果权利理论仅仅以其中一个环节为基准探求权利的本质,很可能无法适用于其他环节。例如选择论偏向于对守法环节权利现象的解释,即在法律将权利赋予某个主体之后,该主体所享有的是对义务人义务履行行为的支配能力。这一理论对权利在立法和司法等环节的解释力就偏弱,因为仅仅知道权利是主体的选择,几乎无法为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制定法律和解释条文过程中就权利如何确立与分配的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引。在彭诚信看来,利益理论也偏向于对守法环节中权利现象的解释,因为该理论将权利界定为法律承认的利益,强调个体所享有的权利在经由法律确立之后的状态。[23]173-174
但是笔者认为,利益理论的旨趣并不止于此,除此之外,对权利是利益的解释,也是对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应当将利益确立为权利的呼吁。换言之,不但权利是能够使他人处于义务之下,在一般情况下能够为主体带来好处并由法律所规定为主体直接受益的利益,而且在现实中如果出现了此类利益,立法者也应当将其纳入成为法律权利的一部分,抑或司法者也应当将享有这一利益的主体视为权利主体。[10]149当然,虽然利益理论有立法和司法的面向,其对守法环节的集中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对立法和司法环节中权利现象的解释能力,如利益理论始终无法回答为何许多利益一直未能为法律所认可并成为法律权利,以及为何某些法律确立的权利无法给权利人带来利益等问题。[21]244-246
二、解决权利理论争论的尝试:权利的程序性思维
为了解决现代权利理论的这些问题,彭诚信提出了程序性权利观。这一观点不仅实现了权利现象研究范式与视角从实体性问题到程序性问题的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体性关涉所导致的公法权利和立法、司法中权利现象无法解释的问题。
(一)从实体性权利观到程序性权利观的转变
彭诚信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是对阿列克西“作为程序体系的法律体系”这一观点在权利问题上的展开,其关注核心是权利在法律运作过程中应当如何获取和界定。程序性权利观的前提是主体参与,内容是主体利益,基本旨趣是构建在立法、司法、守法和执法过程中主体参与权利设计与分配的制度。[23]192-196程序性权利观意在通过程序的架构沟通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具体来说,就是以人人参与表达意志的程序为保障,实现对相关利益的评价和权利归属问题的判断。程序性权利观的提出和论证,实现了权利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的转变。彭诚信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可能认为自己的权利理论仍然处于现代权利理论的框架之内,是将两者融贯的一种尝试。但是在笔者看来,程序性权利观已经与以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权利理论在基本关注范式与视角上呈现出极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彭诚信的权利观已经从现代权利理论对权利现象与实体事物之间关系的集中关注,转向探究权利现象在法律运行过程中的境遇。
这一种转变,不仅仅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变化,更具有哲学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现代理性主义尝试用理论解决许多现象,但也因此倾向于——虽然并未有意如此——将个体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禁锢在既有理论的区域范围内,压制其他可能的思维方式和关注点;不仅如此,现代主义的话语方式还倾向于——同样可能并非有意如此——使我们忘却这种禁锢和压制,下意识地认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24]在这种情形下,如若不是主动地反思,往往只有新的研究视角和对象出现后,人们才会恍然意识到这些压制和禁锢,并进而发现曾经的认识和思维的局限。对权利现象的理论解释也是如此:现代权利理论将权利现象与实体事物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对权利的某种富有启发的解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思维也被限制在这种联系中,认为权利的界定就应当以其与实体事物之间的联系为基点来切入。只有在彭诚信提出程序性权利观之时,我们才意识到接近权利的方式已经被现代权利理论禁锢在实体性关涉层面上;也只有在意识到这一点之时,我们才能够跳出这种实体性联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审视权利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彭诚信的程序性权利观可以视为一种对现代权利理论的解构。
(二)私法权利观与公法权利观的融贯
以判例和习惯为主要法律渊源的不成文法国家,个体的参与也是私法权利观与公法权利观融贯的关键。虽然在不成文法传统中,宪法和法律规则并不是以民主机构进行立法的方式确立的,而是通过法官在具体裁判中予以宣告或行为主体在政治实践中反复遵循,但是个体的参与并不因此而失色。在私法——尤其是民商法——领域,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权利形式、内容和归属的判断并非以法官个人的喜好为依据,而是以经由每个个体反复参与形成的社会交往经验或习惯为依托;在公法——尤其是宪法和刑法——领域,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对压迫的反抗和对国家行为的要求,同样是个体权利的直接来源。只不过与成文法传统不同,在不成文法传统中,公民在权利确立方面的参与并不是以主动立法或选择代表进行立法为模式,而是以每个个体参与社会实践形成习惯进而形成规则为运作机理;尽管社会最后产生的规则及权利并不是每个个体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是就产生规则和权利的社会实践本身而言,个体的参与都是有意识的。当然,即便在不成文法国家,例如英国,某些权利——尤其是公法权利——也经常是通过代议机构以立法形式确立的,人人参与作为这些国家之内个人权利确立的正当性依据也同样成立。
融贯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人人参与这一基本程序预设,不仅仅体现在权利最初获得确立的过程中,也呈现于权利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例如,对于一个新兴的或新型的利益能否上升为私法权利,②新兴权利与新型权利不同,前者指新近出现的现象上升为一种新的权利类型,后者则指在新的时空场域下,某种既有权利在主体、客体、属性、权能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参见侯学宾、郑智航:《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提升与未来关注》,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在成文法国家就需要民众选举的代议机构进行抉择。如果在人人参与的机制中,多数人认为这一利益应当在法律中予以确认,那么该利益才能够成为法律权利。对于基本权利的判定也是如此,只是相较于法律权利的确立,宪法层面的权利对人人参与的范围要求更广,例如一些国家要求代表的绝对多数同意,另一些国家则要求全民公决。在不成文法传统中,新权利的确认则需要法官依循既有的实践及实践中行为主体的需要进行判断,如果实践中人们已经将某种利益视为一种独立的利益,那么将其纳入法律权利就是正当的;如果这种利益在实践中同时获得了对抗国家或要求国家行为的内涵,那么其也可以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存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私法权利还是公法权利的确立与革新中,以人人参与为程序保障对利益的公正评判而言都是必经的程序。在这个层面上,彭诚信的程序性权利观具有贯通私法权利和公法权利的巨大优势。
(三)立法、司法与守法过程权利观的统一
程序性权利观不仅能够融贯不同领域的权利现象,也能够统一解释同一权利在法律运行不同阶段所展现出的差异样貌。①通过程序性权利观关涉整个法律运作过程的目标,可参见彭诚信,《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191页。在程序性权利观的设想中,人人参与利益评判的程序不仅仅体现在立法过程,也应当体现在司法、执法与守法等法律运作的其他环节。首先,在立法程序中,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不成文法国家,公民参与规则的确立都是坚持民主原则这一现代国家的核心机制。其次,在司法环节中,不成文法传统中的司法同时也是规则寻找和确立的过程,因而也符合立法所要求的人人参与机制。在成文法国家,在法官仅仅依循既定法律规则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公民个体的参与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例如在关于权利相对应义务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履行的案件中,权利人所提供的义务存在证据及其对义务履行方式的要求,以及义务人所提供的义务已经履行、无法履行或不应当履行的抗辩证据与理由,都是判定这一案件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司法环节中保障公民的参与无疑也是权利能够得以正确分配和维护的关键。再次,在行政执法环节,公民个体的参与也是确保执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因素。例如行政机关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大型项目的审批许可,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作出对当事人相关权益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等,都需要进行听证,征求利害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②参见《价格法》第23条,《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许可法》第46、47条。听证就是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也规定:“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涉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对社会公众有重要影响等重大利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进行论证咨询。”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草案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或者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较大影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需要进行听证的,起草单位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③参见《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13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5、16条。此外,对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也是民众参与程序中的一环,因为备案审查就是将行政决策和执法环节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宪法和法律是以人人参与为基本程序的构建,因此,即便行政立法过程没有公民的直接参与,其也能够通过合法性和合宪性审查实现间接的监管。最后,在守法环节中,公民的参与更是毋庸置疑,所谓守法必然体现为公民个人及其形成的组织对法律及其中权利规定的遵循。不仅如此,守法环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为新权利的产生与既有权利的更新提供了现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人人参与这一程序性权利理论的前提预设,是统一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环节过程中权利现象的有效法门,也是程序性权利观能够成为整个法律运作过程中权利现象之统一解释的关键。
不过,尽管在融贯公法权利观与私法权利观和统一立法、司法、执法与守法等整个法律运作过程中的权利观念的层面上,彭诚信的程序性权利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为代表的现代权利理论,但是该理论却始终无法实现对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完全替代。
三、权利理论争论的无解:程序在实体问题上的缄默
程序性权利理论无法解决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之间的争论,是因为作为程序的权利无法完全摆脱对实体问题的追问,如此就必然回到意志与利益的纠葛之中。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深深植根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仅仅依靠程序上的共识或安排无法弥合两者之间的深刻裂痕。
(一)无奈回归的实体争论
关于权利现象本质的解释必然涉及实体问题。权利,在现代以来的人类观念中,一直被理解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概念,并且在语言中以特定的语词——例如中文的权利,英文的right等——进行表达,这意味着权利概念必定对应某种事物(无论是具体的事物还是抽象的事物),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过程存在,或者能够被化约为这一事物形成、确立和实施的过程。换句话说,权利既然是语词与概念上的一个独立部分,必然不等同于其成立、进入法律和产生实效的过程。尽管这些过程对权利的概念或本质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决定其概念或本质;但是在经过这些过程之后产生的或作为这些过程前提的权利,就形成一个与过程本身相分离的事物。这也是为何权利与权利的实施、权利的生成等具有表述上的区别。
在现实中,权利确立与实施的过程对实体性问题的追认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关于某个权利是否应当在立法和司法中予以承认,就需要首先确定这个权利所关涉的是个人自由意志还是利益,尤其在选择与利益可能相互冲突的情况下——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其利益的减损,例如安乐死——仅仅依靠人人参与的程序并无法给出究竟应当保护自由还是维护利益的建议。关于某个权利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中应当如何分配并进行保护的问题,也需要追问权利的实体性本质。因为只有知晓该权利是强调自由还是利益,才能够明确将其分配给哪一方更能够实现其旨趣,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保护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实现,仅仅加强当事人的参与无法直接获得这些结论。同样,在公民守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追问或在潜意识中将权利与实体事物联系在一起——因为权利所保障的究竟是意志还是利益,是个体正确行使权利的关键。仅仅赞同每个个体都应当尊重法律和权利,并无法回答权利对于个体有何意义以及权利行使的边界在哪里。有鉴于此,尽管彭诚信所引拉兹和阿列克西对无需实体共识就能够形成程序共识的论断在理论上是成立的,[23]187-188[25][26]但是在实践中,程序从来无法脱离实体而独自存在。仅仅构建一种具有较强贯通力的理论,是无法回应权利实践之需求的。这也是为何既有现代权利理论无一例外地选择以实体事物对应解释权利现象的一个潜在原因。
在《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一书中,尽管彭诚信提倡且坚持认为其程序性权利观较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具有更多优势,但也无法据此就规避对实体问题的回答。作者在书中也明确承认,“权利的程序理论最终亦需回答权利本质问题”。[23]204事实上,当程序性权利观在该书上篇被界定之后,整个下篇都是以对利益和意志的论述为基础而构建的:权利主体的界定,以意志理论对个体意志、自由与人性尊严的强调为基础而确立的人格理念为核心;权利的确立直接被解读为“从利益到权利的程序”,权利的生成因此就是利益成为权利的过程;权利的内容是对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各自范围及其之间关系的考察;权利的层次与体系是依据主体对利益需求的不同划分的基础性、辅助性和救济性三个层级;义务自愿性的界定是以履行义务是个体自由意志的表达为基本理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私法责任也是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主、兼顾当事人自由意志为考量进行构建的。在下编第一、三与五至八章中,虽然作者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在研究范式和哲学认知论上实现了对现代权利理论的反诘,但在真正以这一理论构建其权利制度之时,诉诸的却仍然是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事实上,彭诚信一开始就将程序性权利观的核心界定为利益,将其前提界定为人人通过表达意志的参与,[23]192-196这已然埋下了这一理论与权利实体性问题之间不断纠缠的种子。如果程序性权利观无法摆脱对实体性问题的追问,那么该书或许无法宣称其程序性权利理论能够实现对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替代。
(二)实体性争论的理论预设
彭诚信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无法取代或整合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并不奇怪。事实上,迄今为止,尝试融合或超越后两者的理论均以失败告终。在彭诚信之前,西方学界著名的尝试性理论是维纳的多功能理论和斯威尼华申的混合理论。①对于这两个理论的讨论,也可参见彭诚信:《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上编第六章。前者将权利解释为包括免除、裁量、权威、保护、供给和履行等六种功能中的一种或几种事物,以功能的全面罗列实现对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所能解释权利现象的广泛囊括。斯威尼华申则要么将意志和利益进行某种或然的简单组合,要么将利益作为意志目的的复杂组合的方式,试图实现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有机结合。但是,维纳的多功能理论在其旨趣和适用中更加倾向于利益理论。[21]244-246斯威尼华申的混合理论则无法避免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各自的劣势,甚至可能导致个体拥有与其毫无相关事物之权利的荒谬结论。[21]264,272
现有努力均无法调和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是因为这两种理论对权利本质解释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意志理论源于康德的理性主义和先验自然法,利益理论则产生于边沁和密尔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传统。[6]239,262不同的哲学理论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逻辑预设,导致以这些哲学为生长土壤的权利理论之间从未能有效彼此接纳。例如,在道德和法律规则与人类世界之关系问题上,先验主义认为,道德世界是外在于人类社会存在的,人类只能通过理性对道德要求进行“猜测”。[27][28]具体来说,个体运用其纯粹实践理性获得道德的产生规律——即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从这一规律中获得道德的直接要求,并运用其实践理性将这些要求外化于行为。[28]42-43,110-111将定言命令所要求的道德法则外化于行为的理性,抑或称之为意志,就成为康德的权利概念。[3]14,20-24权利因此与相信存在某个超越于经验的世界的先验主义哲学紧密相关。选择论虽然植根于哈特的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但也并未完全脱离先验主义哲学,因为个体在法律上拥有选择的哲学前提必然是个体的自由意志。
边沁和密尔虽然与康德同处于理性主义的传统中——两者同样赞成人类理性在理解自然世界和掌握道德法则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则不应当来源于先验世界,而应当源于经验世界。[29][30]246换句话说就是,经验主义哲学认为,道德和法则是内在于人类世界的。苦与乐是人类最重要的体验,因而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须在分析苦乐中进行。[31]168在边沁和密尔的观念中,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动机是避苦求乐,因而这一动机也应当成为个体行为的规范指引。[32]权利作为行为规则的一部分,其也应当以苦乐来解释,即权利应当是获得利益或免于失去利益的痛苦。[30]290在这个意义上,将权利界定为利益,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观一脉相承。拉兹、麦考密克和里昂斯虽然将权利解释为某种特殊的利益,但他们对权利的认识并没有脱离基本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框架,体现苦乐的利益仍然在他们的权利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在现代以来的哲学历史上,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来都无法完全调和,因此,深植于其中的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之间无法融通也早在它们产生之初即已经注定。
(三)程序性权利观的实体空缺
彭诚信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对实体性问题关注不足,因此无法有效解决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之间的争论:程序性权利观的理论旨趣在于对权利设立、分配与行使的程序进行构建,虽然不得不回归实体性问题,但这种回归仍然以对程序的完善为目标,未能就实体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正因为这样,程序性权利观也未能就意志和利益两种实体性事物所代表的深远哲学传统进行辨析。当作为程序的权利不可避免地涉及实体性问题之时,程序性权利观将仍然摇摆在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之间。
在彭诚信的理论中,程序性权利观将解决实体性问题的意志和利益分别作为其前提和核心。具体来说,人人参与是这一权利观的前提,而人人参与以每个个体表达意志为基础,因此程序性权利观注重每个人主观意志的表达;关于权利设立、分配与行使的程序,其所要考虑的是能够对利益进行公正的评判,利益因而是这一权利观的核心概念。彭诚信的这一处理,实质上是将意志作为利益化身为法律权利的手段和途径,将利益作为意志表达在权利问题上所要达至的目标。但是,如此处理仅仅是一种对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简单综合,无法解决在具体问题中先验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冲突。个体的自由意志完全有可能与其经验的利益相龃龉,例如个体可能毫无理由地自愿将生命置于他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其生命享有自由处置的先验权利,就无法与维持其生命对他有利的经验感受共存。究竟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当尊重作为手段的个体意志还是作为目标的个体利益,程序性权利观并无法给出答案。有鉴于此,分别将意志和利益设定为途径和目标的程序性权利观无法调和意志与利益之间的分歧。
彭诚信将利益解读为“欲求”,[23]239想要将“欲”之利益与“求”之意志结合在一起,在这里似乎倾向于支持个体的选择。可是,这一结论无疑与现代法律的规定相背离——即便个体自愿将生命置于他人之手,剥夺该个体生命的行为仍然侵犯生命权并成立故意杀人罪。在这个意义上,程序性权利观并不必然得出符合民众一般权利观念的结论。事实上,即便是利益理论,也拒绝将能够成为权利的利益与个体的“欲望”直接联系在一起,即利益不等于个体意志所欲求之事物。[10]149,152[33]因为正如这里的冲突所示,个体可能欲求伤害自身之事——在利益理论的观念中,这种欲求不应当被法律规定为权利。[31]161
程序性权利观对程序性共识的强调,也无法实现对实体问题背后哲学争论的调和。尽管如彭诚信所说,对权利持有不同观念的个体可能对设立该权利有共同的吁求,但是基于对权利实体问题的不同认识,个体可能持有对权利设立与分配程序的不同认识。将权利视为先验意志或经验利益的不同个体,可能在是否设立某权利以及如何设立该权利等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例如在法律是否应当规定安乐死权利的问题上,坚持意志理论的学者由于其先验主义哲学背景,可能认为答案取决于其能否与人类本质或宇宙本质相符。在康德看来,就是安乐死权是否符合可普遍化要求。因此,如果由支持意志理论的学者主导立法,那么在该权利设立的立法论证中将以哲学理论的论辩为主。而坚持利益理论并认为权利必须来源于个体经验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权利是否应当被实证法所承认的关键,在于个体诉诸安乐死的能力能否给个体带来愉悦或使其免受痛苦。因此,在利益理论主导的立法或司法过程中,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利弊考量就将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主要工作。如此看来,实体问题背后的哲学理论预设分歧很有可能会影响程序共识本身。如果程序性权利观无法调和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深层哲学分歧,那么其也无法完全超越或替代这两种理论。
四、结语
关于权利本质问题的现代权利理论争论,自启蒙时代开始至今已历经数百年。由于不同理论处于不同哲学背景之中——尤其是意志理论所处之先验主义与利益理论所处之功利主义——试图融合或超越既有理论的努力始终未能成功。彭诚信的程序性权利观也是此类未能成功的尝试之一。对程序性共识的强调,致使该权利观未能有效深入探究权利现象的实体问题,更加无法就意志与利益之间的哲学裂痕进行弥补。但是尽管如此,在提示我们跳出现代权利理论的实体性关涉并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视角解读权利现象的作用上,《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一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彭诚信对立法、司法、执法与守法过程中权利观的一体关注,以及其程序性权利观贯通解释公私法权利现象之能力,也为此后学者探索权利问题、创新权利理论提出了辐射范围上的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