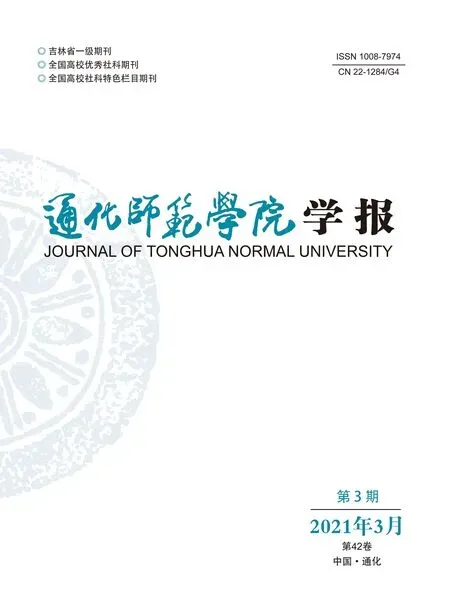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中介语语音系统发展路径初探
2021-01-07陈凤然边雅姚秀清
陈凤然,边雅,姚秀清
中介语语音系统(Interlanguage Sound System)作为外语学习者语言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遵循怎样的规律,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什么,外语教学又应如何把握这些因素和相互关系,从而达到更有效的教学和学习目标。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这些问题是应用语言学研究得到充分发展以来学者一直努力探索的话题,研究者分别从语言形式、功能、认知和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尝试找到满意的答案,但迄今为止,得到的答案似乎还很难达成一致。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LARSEN-FREEMAN于20世纪末提出把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eory-CDST)引入到应用语言学研究[1]。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尝试把认知和社会文化视角相结合,从更全面的角度解读学习者语言系统,是当今后现代社会大背景下对语言本质研究的又一重要转折[2-3]。CDST认为,外语学习者语言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其发展(Develop)过程(替代习得Acquire)具有非线性(Non-linear)、动态性(Dynamic)、非预测性(Non-Predictable)、自组织性(Self-Organizing)和对初始状态敏感性(Sensitive to Initial Conditions)等特点。外语学习者语言作为中介语系统,其发展没有终点[4]。在该理论框架下,外语学习者语言发展的过程受学习者个体(Individual)因素(如动机、情感、信念、学习策略等)、认知(Cognitive)因素(如记忆、资源、学能等)和社会文化(Social-Cultural)因素(如身份、权力、评价等)的综合影响,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因素之间始终通过学习者个体的能动(Agency)协同(Adapt)发挥作用,以涌现(Emerge)形式表现。因此,中介语系统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期间既有相对稳定的引子状态(Attractor),也有变异的斥子状态(Repeller)。外语学习者语言的研究应更关注对此动态过程和路径(Trajectory)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更好把握学习者语言作为复杂协同系统的本质[5-7]。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无疑为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又一发现语言动态发展过程的有益视角。本文在回顾中介语语音系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尝试发现中介语语音复杂系统发展的路径,描述各子系统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协同作用的关系,以期为构建国内良好外语教学生态提供参考。
一、中介语语音发展研究回顾
自SELINKER提出中介语理论起[8],从不同角度把中介语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开展的研究就一直在进行。在中介语语音发展模式及其过程解释方面,不同学者从语言迁移、认知、变异、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了不断摸索。
语言迁移理论(Language Transfer)由LADO提出,指的是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9]74。其后的几十年间,大批学者对二语习得中的迁移理论进行阐释,围绕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迁移的原因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10]57;[11]1;[12]217;[13]。迁移理论的提出影响了中介语语音各个层面的研究,它从语言整体习得出发,涉及语言本体、学习者认知、社会语境等多个层面,虽然很多学者随后对迁移理论进行了质疑和反驳,但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从学习者母语与目标语的类型学角度出发,ECKMAN提出标记性区别假说(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与结构一致性假说(Structural Conformity Hypothesis)[14],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中介语语音系统的标记性在语音习得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标记性越强,母语语音与目标语语音区别越大,习得越晚越困难;标记性越弱,母语语音越接近目标语,习得越早越容易。该假设的基础是语音对比分析,虽然在预测习得困难程度方面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15-17],但一些实证研究也给出了相反的证据[18-19]。ECKMAN承认标记性区别假设存在缺陷,于是又提出了结构一致性假说[20]。在这一假说中,ECKMAN认为中介语也是一种自然语言,其习得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受语言习得普遍规律的制约,而不是受母语标记性差异的限制。两个假说的提出和ECKMAN观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介语研究从单纯的语言对比分析向学习者语言普遍性观点过渡的转变。
在生成语言学不断发展和注重从认知角度探讨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的大背景下,尝试从认知角度解释中介语语音习得的模式不断涌现。FLLEDGE的话语学习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21]、BEST的母语同化模式(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22]和KUHL的母语磁效应假设(Native-Language Magnet Effect)[23]是其中典型代表。三个模式都认为母语语音在中介语的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话语学习模式从语音的范畴化解释母语与目标语语音的相似或区别,以判定学习者语音的范畴构建过程。母语同化模式中,母语语音与目标语语音的相似度会被同化到母语的音系范畴里,但目标语中缺失的语音或相似性差的语音对学习者的习得会造成困难。母语磁效应假设则从语音原型的角度解释中介语语音现象,母语语音的原型会对目标语语音进行范畴的吸引和同化,从而影响学习者感知。与此同时,运用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进行中介语习得的研究也相继出现[24]。在这一框架下,语言迁移依据限制性排序的原则起作用,同时标记性会起到关键作用。从语言普遍性角度综合研究中介语语音发展过程的还有MAJOR提出的个体群体发生模式(Ontogeny Phylogeny Model-OPM)[25]157。在该模式中,中介语包含了母语(L1 factor)、目标语(L2 factor)和普遍因素(U factor),各个因素在中介语语音发展过程的作用此消彼长。同时,母语、目标语和普遍因素与正式程度、标记性和相似性相互关联,决定了学习者语音发展的路径。MAJOR还从语言普遍性的角度提出中介语习得者作为群体可能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个体语言之间的接触与变化决定了过程,个体与群体发生模式既适用于中介语语音习得,也可以适用于语言其他层面的习得。这些模式的建立对中介语语音认知和感知(perception)方面的研究尤为重要。
在结合社会文化对中介语语音发展研究方面,GATBONTON的渐进扩散模式(Gradual Diffusion Model)[26]和TARONE提出的能力连续体假设(Capability Continuum)[27],关注学习者语音变体(Variability),是较早运用动态的观点对二语语音习得的过程进行解释的研究。GATBONTON认为:中介语语音习得是一个系统的、渐进的过程,语音的变化形式和语境相关,逐渐由非目的语的替代音发展为目的语语音。学习者语音变体的出现具有一定规律,与语境的类型有关,重语境(Heavy context)下先习得,轻语境(Light context)下后习得,两者之间是蕴含(Implicational)关系。TROFIMOVICH等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此模式进行了验证与补充,认为语音相似度与在词汇中出现的频率同时起作用[28]。在TARONE的语言能力连续体中,学习者的语音习得变异根据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语言任务(Task)发生系统变化。此外,ZUENGLER提出的话语协调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29]和MILROY L& MILROY J的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30]注重结合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学习者年龄、身份和目标语环境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选择使用什么样的目标语和如何使用目标语的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决定最终习得的程度,某个变量可能会对语音的习得产生重大影响。
综合以上探讨,中介语语音习得模式的构建为中介语理论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有学者认为,模式或理论本身不能解释中介语语音习得过程的变量,因为变量本身具有自然性,一些模式的建立并不能等同于我们需要的习得理论或真实能力的体现[31]。随着中介语研究的不断深入,原先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可能在中介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学习者语言变体、僵化、评价标准等的分析方法应有更开放和发展的态度,应结合学习者个体差异、认知、社会等各层面因素综合进行[32]。
中介语理论的发展经过了初期构建、验证、反驳或补充修订,依据的理论或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变化中,其变化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脉络相一致。相关研究从使用单一理论与方法逐渐过渡到多种研究方法和交叉理论的运用,从简单的语言对比发展到了关注发展过程的描述与解释,学习者个体、语言本体、语言认知和社会文化各层面的研究趋于融合。与此同时,中介语语音习得与影响因素相互作用、超音段音位发展、相关因素在外语教学运用过程中如何掌控的问题等,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二、中介语语音复杂协同系统发展的路径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外语学习者语言作为一个中介语系统,符合复杂系统的一系列特征。在此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间与系统内部变量具有全关联(All-Connetedness)特点和不可预测性,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线性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学习者个体差异作用随时空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33]。在此过程中,各子系统和变量之间是双向协同(Bidirectional Adaptation)互动的关系,学习者能动性(Agency)在综合各种资源促进语言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4]。因此,理清并确定学习者语言系统的相关维度(子系统)、各维度的构成因素及各维度、各因素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对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至关重要。
(一)国内外中介语习得模式构建
在中介语语音习得(发展)相关因素及其模式构建方面,国内外学者在近些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MOYER在对学习者年龄与非母语口音和学习体验的研究中发现,与学习者年龄相比,学习者其他个体因素如认知和心理因素起到的作用更大[35]146。在此期间,学习者与目标语社会互动的体验也会对学习者的动机、策略等起到促进或消减的作用。在DOUGLAS FIR Group团队构建的多语环境下的二语习得交叉学科模型(Transdisciplinary Framework)中,学习者处于多个同心圆的核心,从内向外与学习者互动的层次分别为核心层学习者与他人的互动、多语/双语环境下的互动、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包括学习者认知的机制与能力)、中间层面的社会群体和机构的影响、宏观社会层面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作用等。各层面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直在交互的过程中,一个层面的互动依赖或包含了其他层面的互动,每个层面都以连续的变化形式而存在[36]。戴运财和王同顺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建立了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二语习得模式[37]。在该模式中,学习者语言的互动维度有学习者、语言和环境。其中,学习者因素包括个体认知差异、个体情感差异和学习策略;语言因素包括语言距离、语言标记性和语言原型性;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学习环境和语言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间呈双向互动关系,共同作用于学习者语言的习得。崔刚等在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专门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时,把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分为两大类型:稳定变量(内隐变量)和易动变量。其中稳定变量包括语言学能和性格,易动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中介变量又分为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四种。直接变量包括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这八个变量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交互关系,有些是双向的相互影响,有些是单向影响,所有不同的变量组合关系都与学习环境有互动关系,共同作用于语言学习的最终结果[38]87。徐锦芬和雷鹏飞在探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外语课堂教学时,把外语课堂教学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语言维度、认知心理维度、社会文化维度和个体差异维度。各维度间都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通过课堂作为教学或互动的方式与途径,共同影响学习者语言的习得过程[39]。
(二)中介语语音系统构成因素及其互动关系
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中介语语音系统本身的特点,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中介语语音发展的动态系统总体应包含四个层面的因素/变量,即语言本体因素、学习者个体因素、心理认知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其中,语言本体因素既包括人类语言习得与发展的普遍因素,如语音的类型、习得的顺序、省力原则等,也包括学习者母语与目标语各自基于类型的语内标记性和语际标记性,如部分单音的差异与相似、超音段特征差异、音系规则差异等;学习者个体因素包括年龄、学能、性格、情感、动机和学习策略等,这些因素的形成与每个学习者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成长过程和经历等密切相关;心理认知因素包括认知能力、语言观、记忆、理解与表达、资源掌控等,该层面因素与个体因素密不可分,更多体现为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能力,如语音听辨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对不同口音的认可度、对支持或竞争资源的充分利用或适应能力等;社会文化因素可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类,其中宏观因素包括学习者所处社会的整体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结构等,微观因素包括语言资源(包括课堂内外)、群体与个人互动、身份、反馈与评价等。
各层面因素形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而且每个系统有各自的特点。语言本体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由于受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长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阶段性相对稳定状态,因此语言普遍性因素作用会比较明显。比如英语和汉语在音系规则和单音发音的差异性与相似性方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由于语内标记性和语际标记性对学习者语音发展造成的影响更趋向普遍性。但在学习者心理认知和个体因素层面,由于所处群体、学习环境等各方面条件随时发生变化,对学习者动机的持续性、情感、策略的选择、语言观甚至理解与表达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会体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比如在外语课堂上,如果教师不能构建很好的外语语音输入环境,为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多样化的、贴近实际生活的语言使用资源,学习者的动机可能受到影响,不利于学习者更好掌控资源并发挥能动性的作用。
划分出中介语语音发展的几个层面,是为了在研究中和教学中更好地区分和掌控各因素及其关系。但实际上各个子系统之间呈全关联关系,学习者语音系统发展的结果都是子系统间各因素动态互动过程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处于核心位置,通过能动性的判断和选择,以某种方式呈现,但语音呈现的形式和结果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各种资源之间又有相互支持或竞争的关系,因此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通过各因素不断协同互动并反复强化后,学习者语音的发展会出现相对稳定的引子状态,即通常所说的僵化。但如果环境条件或个体因素发生足以让学习者采取相应策略并持续,各子系统及其相关因素的组合状态将发生改变,学习者的语音表现可能进入另一个不稳定的发展过程。例如,中国学生在英语口语中经常表现出过度使用降调和重读,在了解英语是以重音为节奏基础的语言之后,对英语节奏的认知会提升。但是如果在学习材料中没有提供现实生活场景来展示重音、声调和节奏在真实话语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保持或提升学习者在超音段方面学习的动机和投入,也就不能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学习效果。
(三)基于有效教学生态的中介语语音动态发展路径
对于我国外语学习者而言,因为相对缺乏与母语者直接交流的语境,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外语教学生态对学习者语音发展至关重要。有效的教学生态应包含语言、学习者、心理认知和社会文化四个子系统,不仅涉及微观的课堂教学生态,也包括学习者所在的宏观社会大环境。既包括学习者个体,也应涵盖与学习者直接或间接使用目的语交流的教师、学习者和社会人员,还包括各类网络资源。宏观环境因素通过教学任务设置、个人参与、课堂展示等作用于课堂微观环境和学习者个人,学习者在课堂教学中体验互动、获取的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反过来也促进学习者参与社会应用的动机,形成各子系统因素间有效的良性互动循环。良好教学生态的建立,对学习者正确外语语言观念的形成、语音学习动机的保持、有效学习策略的使用和掌控学习资源能力的提高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无论在怎样的教学生态中,学习者个体始终是核心。在外语语音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学习者个体因素通过与其他子系统因素持续互动发挥作用,语音的发展结果以涌现的形式展示,以涌现结果为起始状态的又一轮互动同时发生,循环往复。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因素与其他各子系统因素间的协同互动持续作用于语音的动态发展,各因素间既有相互支持也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学习者自身掌控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和策略,即学习者能动性,始终是决定语音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教师,如何通过构建微观课堂生态并帮助学习者提高外部资源掌控和应用能力,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投入,从而使学习者能动性地充分发挥其在语音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师生协同共建的学习环境,是整个外语教学生态构建的重要环节。
总之,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框架内的中介语语音系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系统,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学习者的语音系统发展不是按照一个预定的轨迹无差别发展,而是各种因素时刻互动、学习者与外部因素动态协同的过程和结果。
三、外语教学启示
任何一个理论或观点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不断的质疑、验证等过程丰富并完善是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中介语语音系统发展的教学实践和相关研究,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不断深入。
在如何开展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方面,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MOYER在探讨学习者语音系统自动性(Autonomy)时提出,应尽量多给学习者提供获取真实语境话语的技术手段,让学习者接触更多目的语语音变体形式,以提高他们对目的语语音范畴和模式的识解能力;让学习者接触并讨论语音的地区差异、社会群体差异等在具体情境下的交际互动效应,从而提升他们评判与自我评价的能力;强调朗读与角色表演的作用。[40]徐锦芬、雷鹏飞[41]、LARSEN-FREEMAN[33]、郑咏滟[42]等指出在外语教学中应特别注重学习者个体能动性的培养和提升,并提出应结合良好教学生态建设、各层面因素互动关系研究、师生角色转变和强化实际情景下的语言运用等方面,抓住学习者语言多维度、时空情境性和体验为主的动态发展特点,为学习者培养和提高掌控学习资源和良性协同互动的能力。徐锦芬、龙在波在探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外语课堂教学时,建议教师在学习者语言自组织基础上设计课堂任务,尽可能创造联结性增长点,重视学生对自我状态的认知,强调重述/反复的作用,正确认识初始状态对语言发展的重要性等[43]。
综合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中介语语音发展研究和实践成果,并结合我国外语教学实践的实际状况,在国内外语语音教学方面应注重以下原则和实践方法:
(1)加强外语师资语音意识和能力。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学习者语言对初始状态具有敏感性,同时也是动态的。教师对学习者语音的关注程度、自身语音能力的提升等,对促进学习者形成积极的语音学习态度和动机,进而在学习者阶段性语音初始状态基础上培养积极有效的学习认知和策略都具有重要作用。
(2)重视语音教学的本土化策略。现有国内外有关语音发展的研究鲜有把二语与外语学习环境进行区分的,但在国内外语语音教学条件下,学习者很少能有机会与目的语为母语的人员沟通,甚至学了很多年都没有真正使用口语进行实地交流。因此,如何运用包括现代技术在内的各种音频、视频和社会资源,解决学习者没有更多像二语习得甚至其他日常应用比较频繁的社会文化语境的问题,是教师必须面对并根据实际情况实现语音教学本土化的重要课题。
(3)努力构建有效运行的语音教学生态。语言学习的多维性决定了语音学习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因此如何更好地整合课堂教学、课下自主学习和利用社会资源,包括建构有效的反馈和评价机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对于形成良好的语音教学生态至关重要。
(4)强调语音教学资源的多样化和情境性。任何语言的学习中语音的输出都是最直接、应用最广泛的方式,让学生更多地接触目的语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了解并创建更接近口语现实情境的效果,能让学习者更直接感受基于体验的互动过程,更有利于学习者语音发展。
(5)关注学习者语音系统的时空动态发展过程。教师在关注学习者群体学习效果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学习者个体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中语音选择和发展的过程,根据个体特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这个过程既是学习者态度、动机、观念、认知、策略等个体因素动态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作为指导者和语言学习协同互动重要角色转变的过程。
(6)注重学习者个体能动性培养和提升。语言学习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任何外部环境的作用都需要通过学习者个体的能动作用实现。因此,如何在调动外部资源为学习者提供充足有效的外部条件的同时,通过积极反馈、课堂活动和双向沟通等方式,充分调动学习者积极性,消除因为焦虑、动机减弱或策略不当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培养他们保持积极投入的态度、掌握利用多种外部资源、有效进行自我评估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学习策略,都是语音教学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
俗话说“教无定法”。在当代应用语言学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转型期,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如何根据学习者情况适时调整和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如何根据外部条件和资源变化充分发挥学习者自身能动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四、结语
在当今应用语言学界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努力探寻外语学习者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为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该路径没有终点,以外语教学的有效生态为基础,过程中学习者个体、语言本体、心理认知和社会文化各子系统及其相关因素始终进行着协同互动。学习者语音发展以涌现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又一互动发展过程的初始状态。学习者能动性决定了学习者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掌控和利用外部资源的策略和能力,形成师生协同的学习环境对构建有效的教学生态至关重要。该路径的确定对外语语音发展中如学习目的、动机、语言观、学习者及教师身份、课堂活动、社会互动等因素如何组合,对语音发展又起到何种作用,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学习者发挥能动性掌控资源,外语课堂如何构建促进和保持学习者动机并培养有效学习策略的外语教学生态等理论与实践方面提供了又一视角,希望能为业界同仁提供有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