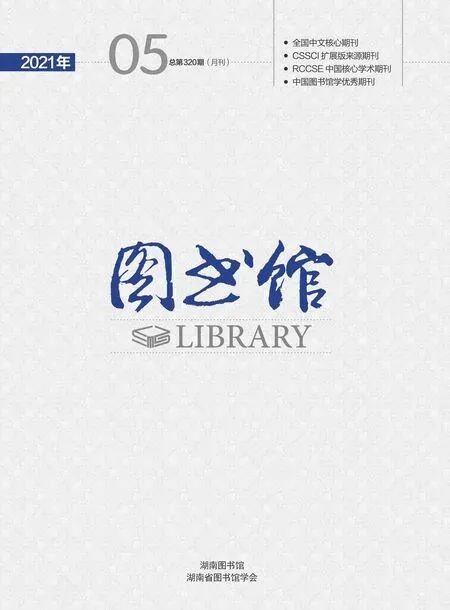王伯祥先生的藏书活动与图书管理思想研究
2021-01-07宗瑞冰
宗瑞冰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7)
王伯祥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史学者、编辑家,曾兼任开明书店的图书馆馆长,他痴迷于藏书,其藏书经历以及所撰写的藏书题记《庋榢偶识》,思想内涵丰富,值得我们挖掘、整理与总结。本文以王伯祥所撰写的读书题记《庋榢偶识》[1]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他坎坷多舛的藏书经历,挖掘他诚笃务实的藏书理念、海纳百川的聚书途径、藏以致用的利用观、注重适用的图书整理思想,以彰显近代学人对我国藏书事业、藏书思想史、图书馆发展史的贡献。
1 坎坷多舛的藏书经历
王伯祥(1890—1975),名钟麒,江苏苏州人,别号碧庄、容叟、巽斋、容安、容堂等,晚年目力衰减,一目失明后,曾自号畸叟、不翔等,曾任教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编辑十余年,1932年转任开明书店编辑。他在开明书店任编辑时受书店老板章锡琛先生之托,兼任图书馆馆长职务。由于深谙目录学并精通版本,他在经营图书馆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使开明书店的图书馆经过几年经营渐具规模,深受编辑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称道,该图书馆毁于1937年的“八一三”炮火中[2]。新中国成立后王伯祥应郑振铎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身)任研究员,出版专著有《我国三千年来地方制度的演变》《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春秋左传读本》《史记选》《开明初中国文读本参考书》《开明国文读本》等。
王伯祥的藏书生涯始于青少年时期。顾颉刚在《王伯祥先生〈书巢图卷〉后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与王伯祥、叶圣陶青少年时一起淘书的经历:“其时新书肆皆设观前街,而观内木棚数家,东廊下有华氏,西廊下有朱氏,皆售旧刻本。是时吴中学风已变,群视旧籍为无所用之,问津者寡,价因日贱,一册仅售铜元数枚。我辈以茗谈之便,日必趋之,视囊中钱多少,选购一二,挟至茶座,交互览之,兼施评判,以为人间至乐萃于是矣。”[3]叶圣陶也在《书巢记》中也写道:“书者,伯祥之偏嗜。一旦丧焉,怅惆几无以聊生。乃又徐徐致之,资不足则假之友好。如鹊运枝,如燕衔泥,不以为劳。”[4]这是王伯祥的两位至交好友对他一生爱书、藏书的准确写照。
由于对书目类书籍烂熟于心,王伯祥青年时期即有藏书家的风度。顾颉刚在文中还提到他们早期即烂熟《四库提要》《汇刻书目》《书目答问》等书,经常翻览,对于明、清人之书刻于何时何地,触目了然,因此虽在青年,但是宛然已有藏书家鉴赏的风度。王伯祥所藏之书,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前已达万卷:“积十年,所贮图书已盈一室,虽力棉务广,不能罗珍秘,而先人所遗乡塾读本及通用要籍,与夫考索所需之工具书,为卷殆将逾万”[1]。这些书籍,由于“一·二八”日寇的侵略,大都毁于战火,与涵芬楼藏书遭同一厄运,这也成为他心头第一大痛事。
劫后补偿性地重购收藏。对于已毁的书籍,王伯祥总是念念不忘,其后有机会总是设法重购收藏,并在题记中记下此书的前尘后事。如《庋榢偶识》卷一中有云:“《史汉商榷》二十八卷,残存四册,辛壬倭作,寓庐成烟,图籍灰飞。”卷三中云:“《书目长编二卷》戊辰正月,北京排印本,原二册今并装一册。箧中旧亦藏此,辛壬之变,同被浩劫,近日偶阅西泠印社目录,有此出售,乃走一力购取之,稍弥前失。”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搜罗一些广益书局、北新书局、大达社、世界书局等印行的质次价廉的书,他在卷一《窦存》一书的提要中写道:“丁丑秋冬,坐困衍福楼,日惟求遣于时行廉价印本之笔记,广益、新文化之书乃大集,此书其中之卓出者,每加翻㠾,翌年冬初重看时漫志,不无枨触,握管茫然。”因此他的藏书中,刻本以及珍稀本较少,多为近现代印行的书籍。从他坎坷多舛的藏书经历,吾辈可以想见近代学人藏书之难,从事学术研究之艰,不能不令人心生敬佩。
虽遭劫难,王伯祥的藏书依然颇丰。据其子王湜华言:“到1950年全家自沪迁京时,打制了十八个大木箱,才够装运他的全部藏书。……到家父去世时,藏书量已相当可观。家人将藏书捐给文研所,解放后的一般书籍不接受,还共捐了近两万册书。”[1]
王伯祥一生爱书如命,好藏书籍,嗜书成癖,书友颇多。他的藏书斋先后有“疾流云馆”(苏州通和坊老屋)、“曲斋”(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书巢”(1938年以后于法租界)等。王伯祥与郑振铎、叶圣陶、陈乃乾(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俞平伯、郭绍虞等学者过从甚密,经常相约一起选书、买书、评书。叶圣陶听说王伯祥新建了藏书之所——“书巢”,高兴地作了柏梁体长诗《书巢歌》与《书巢记》以示庆祝。其后王伯祥在1939年请画家蔡震渊画了一幅《书巢图》,并请钱石仙篆引首,将一文一诗与图一起装裱成《书巢图卷》,先后请贺昌群、施蛰存、郭绍虞题写。1966年顾颉刚为《书巢图卷》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后记长文,以记他们多年的友谊和坎坷多舛的藏书经历,该图卷及诗文遂成一段佳话。
王伯祥不仅好藏书,而且好读书,终日手不释卷,眼不离书,“每得佳书,往往喜于封面或扉页上题辞”[1]。这些题记最终汇集成《庋榢偶识》出版,其内容除“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外,还考辨版本、流传、得书经过、有关掌故、同类著作以及由此而生的议论、抒情等等,文笔近乎随笔,读来饶有兴味。从中我们抽绎出王伯祥诚笃务实的藏书思想、海纳百川的多元聚书途径、藏以致用的思想观念等,以见近现代学人好书之诚笃与积书之艰难。
2 诚笃务实的藏书思想
2.1 为爱而藏
王伯祥的藏书种类繁多,经、史、子、集、图录、碑帖等类皆有。但作为“嗜史若命”“喜史地书”[3]30-34的文史研究专家,他尤为笃诚地收藏史学类的书籍。诸如编年史、杂史、史表、史抄、史评、传记、地理、目录等类皆有所藏,如《明通鉴》《资治通鉴补》《南疆逸史》《中外纪年通表》《史汉商榷》《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一统志》《观古堂藏书目》等。史类书籍对于他的文史研究最为有益,因此他特别留意购买,种类也最齐全。如《文献通考详节》这本书就是出于对文史考索的兴趣而购置的:“民国二十二年岁在癸酉,季夏之朔,购自大庆里中国书店,出银一元为代价云(当旧藏尽毁时,渴于求书,对此类有助考索之籍特感兴趣)。”对于《历代统系录》这本书,王伯祥曾言:“予弱冠治史,即蓄此本为检览之资,南北旅行食,皆行箧自随。”无论行走坐卧吃饭等都随身携带该书,可见他对于此书的喜好之深。该书毁于日寇战火后,他又先后购买了两部,分别是鸿宝斋据三长物斋石印本和三长物斋原刻本,先购得鸿宝斋石印本,自叹“得此稍慰”,并对其中的讹字及沿传讳改诸字,随手改正。后有机会购得原刻本,遂将鸿宝斋石印本给了他的儿子,仍以三长物斋刻本庋架,还颇有合浦珠还之感,对失而复得的书倍加珍惜。
2.2 尤重实用
他购书藏书以实用为第一要务,并不以版本的珍稀程度为标准。如对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刊行的两大古典文献丛书《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和《四部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他尤为看中《备要》的实用性强。在《庋榢偶识》卷二之《又扫叶山房石印书目答问》的提要中,顺笔比较了这两套丛书的短长:“《丛刊》以广收古刻名椠,影印传真为号召;《备要》则多采注释名本,全用仿宋体聚珍版排印(大徐本《说文》仍用影印),以清晰悦目为标帜。两者互有短长,而《备要》较资实用。予遭燹求书,自以备类资用为亟,乃舍《丛刊》而取《备要》(后每遇《丛刊》零种为《备要》所无者,随购以补阙)。”对比两套书的选书取向和侧重、版式的区别等因素后,他选取了《备要》本,而以《丛刊》本的零种为补充,这样既满足了实用目的,又能弥补《备要》本所未收的缺憾。从这个取舍标准,我们可以看出他购书藏书多出于实用之需,而非沽名钓誉地以收藏珍稀版本为荣。
2.3 不尚珍秘
王伯祥与著名藏书家郑振铎相交五十年,在上海居住的三十年中,过从甚密,尤其是在涵芬楼共事十年,朝夕相晤,关系甚睦,经常一起访书、论书。但两人的藏书理念有所不同:郑振铎是“冷书孤本,尤所癖好”;而王伯祥则“喜泛览,不尚珍秘”[1],“决不为藏书而藏书,所置备之书,都为治学之所用,不矜持版本之古老,更不求孤、怪”[5]。两人藏书理念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藏书特色:郑振铎珍稀藏本较多;王伯祥的藏书种类繁多,珍稀刻本较少,近代书社出版的书籍较多。
2.4 好拾残简
对于喜爱的书籍,王伯祥不论品相如何,都收入囊中,因此有了“好收拾残简”的喜好。对此喜好,他曾在《庋榢偶识》卷二中自嘲曰:“越六十又五年庚子闰六月初六清晨,濬儿侍予就医阜外医院归,偶过朝内大街,见路北地摊上有此薄本,封帙已佚,底页亦多蠹损,斥人民币一角易归。剪旧信封前后夹护之,居然改观矣。”在他的影响下,其子王湜华先生也“染”上此好,并经常从冷摊旧书店中淘得好书,比如《庋榢偶识》卷一中乾隆刻本的《易义阐》就是如此得来:“我家自上海迁来京师后,湜儿就学于灯市口育英中学,挟书出入于冷摊旧肆间,颇喜检拾残册,归以呈予。”他还曾从小贩手中抢救出好书:“《双鱼罂斋古今集联》刻本,残存三册。此残本三册,为湜儿从估担上抢救所得。”
好拾残简的藏书爱好,也导致他经常自己动手修补残书。1964年9月与陈乃乾购于厂甸中国书店的《读史探骊录》一书,他于七十五岁高龄仍亲手修补:“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午后,阴森闷人,爱为检纸补缀(以脱线破烂故),仅及首册封面与尾册封底,非但材乏,目力亦不济也。”1964年9月29日他购买《月令粹编二十四卷》于厂甸中国书店,由于该书封面已烂,因此“越九日,觅旧纸糊之,且加线焉。平生结习,至老不忘,正堪自笑”。他对当时盛行的硬面西式本的书籍“终觉不能调洽,深用欿然”,终于还是“遂毁新装,仍还初服,手自经营,劳而弥欢”,亲手为该西式装束的书籍更换了封面,恢复线装书籍的传统装束。从他好收残简并动手修补之事,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择地、不择时、不择品相地收藏书籍的真正爱书之人。
3 海纳百川的聚书途径
王伯祥的访书途径很多,根据其题记所述,约归为以下四种。
3.1 淘买购置
他经常去书店、书肆、市场、书摊、废书堆中淘书。如《朱晦庵楚辞集注八卷》是他从上海古籍书店购得;《月令粹编二十四卷》乃于1964年购于厂甸中国书店;《经籍纂诂并补遗百六卷》购于来青阁;《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因遭劫灰,后重购一部于泰东书局,以弥前失;《正芳民歌集》购买于苏州卧龙街旧书摊;《历代纪元汇考八卷》得之于国子监中国书店。解放后调至北京,厂甸年市成为他每年必游览之处,每去则必购书一二册:“厂甸年市,数百年来向为京师岁首盛会。百货殷阜,人物熙攘,全国观瞻系焉。予每届年会,必往游览,游必择购一二书册,用资留念。”又如《新定说文古籀考》购于废书堆中:“解放后,开明书店依出版总署指示,合并于青年出版社,动议于一九五一年九月,酝酿至于五二年十一月始定议,十二月初,双方合流,因将积存杂件分别清理,出版科遂斥去多余样书,作废秤售。此书(周名辉撰,于吴清卿、丁佛言、强梦渔三家之说多有是正之处)予就废书中拯救以归。”从废书中抢救得书,使之免遭“熔炉之劫”,他视此为积了一件小小的功德。
王伯祥经常约同叶圣陶、顾颉刚、陈乃乾、柴德赓等一起访书。王伯祥与叶圣陶、顾颉刚在吴中求学期间即一起买书于书肆。由于战乱与两人远离,后多与陈乃乾一同访书,如《幼学故事琼林》就是二人一起购置的:“丙午燕九节前一日,与乃乾约,会晤于隆福寺街修绠堂,阅架得此。”同样购置的还有《古文辞通义二十卷》:“此书,三十年前予主开明图书馆时,即为馆罗致之,旋为周君振甫假去,辗转数四,竟未璧返,当时颇感懊惜。然沪坊未得再遇,盖书虽近出,流传不多,又未为时人所重,以致湮没耳。丙午燕九前一日,偶与乃乾约晤于隆福寺街修绠堂,阅架得此,殊有旧雨重逢之乐。驱斥资购归私藏,亦所以了此一段香火缘也。”对于他人借而不还的书,王伯祥除了懊惜之外,更是着力搜求,一旦得偿所愿,即有久旱逢甘露之喜。可见他对于书籍的搜求和收集,用情颇深。
3.2 路边偶遇
他的一些藏书也多为偶遇得来,如所购买《韩诗外传》即是如此:“戊寅仲春,商务印书馆设廉价部,将旧存底货贬值斥卖,往往有绝版旧籍错列其间。一日清晨偶过之(时稍晏即顾客盈门,徘徊拥塞,无从插足),瞥见此本,标价仅六分,予喜旧帙之重遇,因购以归。手自并装,合为一册。爰志始末,用留纪念。”他无意中瞥见已毁的书籍,而且价廉,仿若老友重逢,自然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再如《新华小学地图》,他有意购求而不得,却得之于路途中等车的间隙:“此图初出,见报即往城内新华书店及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购买,竟已售缺(此图上册为本国部分,下册为外国部分,编制新颖,册后均附地球仪图,读法用红绿眼镜),为之废然。十七日与滋儿游门头沟,归途在东辛房待车,适车站附近有新华北京分店京西矿区门市部,偶入闲翻,居然睹此于柜头,仅存二部,遂购其一以归。一以志望外之喜,一以微近日购置新书之难耳。”《文选古字通》乃王伯祥偶然得之于就医途中;《格致镜原》乃是戊寅仲春饭罢散步,偶过蟫隐庐而购;《南北史捃华》八卷是辛丑年腊月访问杭州期间,偶然路过湖滨古籍书店而购。诸如此类得之于路途之中、偶遇之下的书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他对于购书、藏书之殚精竭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得到好书的机会,并且慧眼独具,能从常人视若不见之处发现好书。这些对于现代访书工作而言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很有启迪意义,书不一定非要去书店柜台购置,所谓“处处留意有好书”。
3.3 故交旧友所赠
他的故交好友知其爱书藏书,常赠书于他。如《白雨斋词话》八卷乃是叶圣陶“自苏城冷摊所购赠”。《齐东野语》与《鹤林玉露》是开明书店所赠。《检字一贯三》是顾颉刚所赠:“曩在颉刚斋头见此,叹为精绝,求之四十年未尝遇。丙申之春,颉刚偶得之于冷摊,知予求之亟也,特携过见赠。彼能遇复,遂获分惠,我独无缘,竟未之见,因缘遇合,有若前定。铭感之徐,慨焉长喟已。”《十国春秋一百一十六卷》乃是郑振铎所赠:“民国癸未,倭难方殷,沪上百业敝,坊贾尤难于图存,乃以庋阁旧籍,捆载以赴纸商熔炉。西谛知之,亟出赀救之,便以此本及《水道提纲》见赠。”王伯祥与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等都是极爱书之士,将自己所得之书赠予老友,一见他们的情谊深厚,二见他们都深谙彼此的爱书之癖,互相成全,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爱书人之间的情谊。
3.4 抄书移录
王伯祥还爱抄录喜欢或未见过的书籍,并以此为乐。他八十以后,尽管右眼已眚,但对于抄书之事仍乐此不疲,多次在题记中言及自己的抄书之乐。如“病废以还,百事莫能为,而抄书自遣。遂为常课。”“老去无憀,以抄书自遣,数年以还,亦手抄不少。”其抄书之功,累年竟达几十册之多:“每择平生殊赏,或未见之籍,随兴移录,积年所得,不下二三十种,分缀成册,偶一抚摩,自谓此我山中白云也。”对于抄书亦颇有心得,认为“抄书之功,端在精勤,方其凝神对观,濡毫落纸,墨香四溢,百虑都蠲,其乐有难以语言形容者。”抄书之乐,他人或难以体会,而先生乐在其中。因此他的一些藏书,都是自己或家人所抄。如“《美术丛书》之合意者,几摘录殆尽”;《初月楼论书随笔》乃于“辛亥正月廿六七两日抄毕”;《吴歈百绝一卷》则是“翌晨即抄,廿四日抄毕”。抄书之勤奋可见一斑。《德清俞先生缪悠词》乃就着俞平伯手中所持的卷宗手录而成;《沈石田纪游卷题记》乃是辛亥长夏“赏其俊,遂移录之”。对于珍稀书籍,王伯祥更是不放弃机会抄出一副本,如清嘉道年间的顾禄著有《颐素堂诗文集》《题画诗》《桐桥倚棹录》《清嘉录》等书,由于太平军的战火,书版多毁失,所以他的书流传稀少。当王伯祥知道顾颉刚藏有《颐素堂集题画诗》及《桐桥倚棹录》,而后者已成枕秘孤本时,即从顾颉刚处借来该书,令其子王湜华抄录一本:“三儿湜华,业余颇耽抄书,遂乞诸颉老,假《倚棹录》归,偕其妇文修漏夜共抄之,此一珍秘孤本遂得录副储予籍。”对于心仪已久并且传世极少的书籍,能够抄录一本,其中的欣慰和喜悦之情可以想见。
4 藏以为用的利用观
王伯祥对图书的收藏和利用,主要是为治学而藏、藏以致用,具体表现在为校勘之用、以书证史诸方面。
他买书藏书多为校勘之用,如比较版本的异同和优劣,考订文字的异同。他在阅后所撰的题记中往往能切中肯綮,指摘版本的得失和优劣。如他购买了《明通鉴九十卷附记六卷》(清·夏燮撰)后,即与陈鹤本对勘,认为夏本“实胜陈氏《明纪》,其精窍处尤在自撰之《考异》”。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误字、讳改之字,即随手校正。如他在读《历代统系录》时“凡误字及讳改之字,随手校正”,只是对于这样的错误恨不能尽数校改。王伯祥对于当时重印古籍,并擅加错误标点以至误人之事,尤为痛恨。他在《天府广记》这本书的题记中说:“予向谓不明古籍真谛而滥施标点,贻害较白文更大,盖白文流传,尚可使读者玩索自得,即有舛错,亦可供学人思适之资,一加标点,即隐示准则,浅人凭以体会,不免导入迷途,识者获此,徒滋笑柄。又何苦而为此徒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之事哉。”他认为给古籍加了错误的标点还不如不加,纯属浪费,意见颇为中肯,也足以让学界同仁引以为戒。对此常年陪其淘书的王湜华感触最深,评价最为切合实际。他称王伯祥“决不为藏书而藏书,所置备之书,都为治学之所用,不矜持版本之古老,更不求孤、怪。如说在版本上亦有所追求的话,那就是力求校勘之精良和使用之方便而已。”[5]34-36
此外,王伯祥对于购买的用纸粗劣、名不副实的书籍,仍悉心收藏,持“以书证史”之用心。如他购买了1959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宋诗举要》后发现此书下册用纸粗糙,竟“以粗劣杂堵勉辏印播”。虽然初上手时感觉有点棘目难堪,但是他念及“国家当此颠沛,仍以崇文为亟,及时流播,不犹愈于废阁不行乎?它日于此得一艰苦之考验,不更为一大好纪念乎?”于是乐而识之,更加珍惜。又如他购买《正芳民歌集》,阅后发现该书多是神道设教麻醉民众之宣传品,而非民歌,但亦不鄙弃,存而用来见“旧书堆蕴毒之深”。书籍是一代社会历史的见证者,无论其好坏优劣,不因其鄙陋而毁之,任其作为一代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有意义的。
5 图书管理思想
王伯祥在任开明书店编辑时,曾兼任图书馆馆长职务,一手创建了开明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体系,对此他的孙女回忆说:“开明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在祖父经管时期已确定,分类体系亦由他一手创建,有一简明扼要的分类表。”[2]600王伯祥之子王润华于高中毕业后进入开明图书馆从事图书的分类和整理工作,王伯祥亲自指点他整理图书,以适用性为原则为图书分类:“为了追求书目的适用,祖父要求他将内容涉及宽泛的图书尽可能往上位类放。还记得,曾教他在大类之下相近的类目之间,可运用空行、星号等符号体系作为区别与分隔。”这些图书分类的经验,使王润华获益终身,对他在出版总署编辑《全国新书目》,在版本图书馆编辑《全国总书目》,乃至在北京图书馆负责编辑《民国时期总书目》帮助很大。
6 结语
上文梳理了王伯祥的藏书经历,探究了他的藏书思想,这些经历和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后代子孙的学术道路。如其子王润华先后在开明书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工作,先后编辑和主持了解放后大型书目《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居功甚伟;其子王湜华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其孙王绪芳主动选择图书馆学专业,从事图书馆工作多年。此可谓爱书藏书,家风绵长。
王伯祥的藏书经历和藏书思想对扩大我国近现代藏书家的研究范围、梳理近代图书出版史与图书馆史都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发展,我国近代图书出版业迎来史无前例的兴盛,也催生了更多的私人藏书家。他们的藏书经历以及藏书理念,由于新旧社会的更迭和动荡,必然更为曲折坎坷和丰富多姿。他们中的一些人兼具多种身份,有的虽并不以藏书家著称,但是其丰富的藏书经历和藏书思想,折射了近现代图书出版业的演进历程,传承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这样的学者型私人藏书家,值得我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