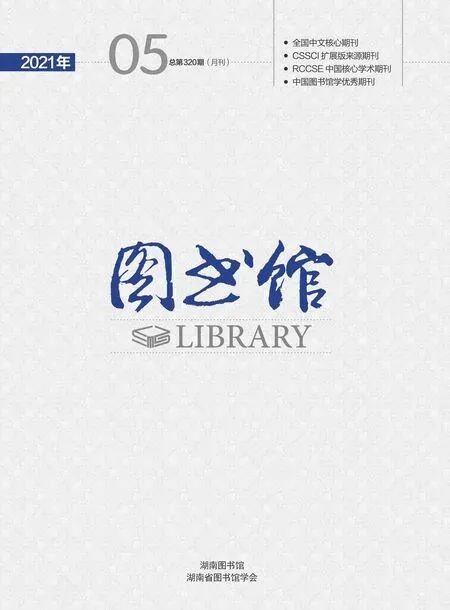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刍议*
2021-01-07路宽李伟
路 宽 李 伟
(1.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2.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1]要研究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历史,必须以该时期该领域的翔实史料为基础,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和结论[2]。同样,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研究社会主义中国传播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基础。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经由日本、苏联、欧洲、美国等渠道传入中国,产生了大量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历史文献,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头二十年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报纸杂志都谈论过社会主义,其中至少有二百多种报纸杂志刊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报道和文章。而这些年出版的有关书籍,也在百种左右。”[3]I这些文献,既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也有幸德秋水、河上肇、柯卡普、倍倍尔等外国理论家和学者著作的中译本,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和恽代英等中国理论家的相关著作;汉译本收藏地遍及中国(含香港和台湾),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有藏本存世。对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有利于追本溯源,考镜源流,摸清社会主义文献传入中国的种类和数量,揭橥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和信仰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书写系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本文所论述之“早期”主要涉及1871年至1927年间的50余年。使用“传播”一词,并非仅指域外社会主义文献在中国的译文译本,也指中国最初的翻译者、研究者和学习者受到域外社会主义文献影响后所撰写的相关论著。对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不仅有助于考察在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哪些域外文献传入了中国,亦有助于考察早期传播文献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何种影响,中国的传播者、学习者和研究者发挥了何种作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中的哪些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有助于考察域外社会主义文献在中国传播、被接受和发生影响的总过程。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早期传播的研究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早期传播的相关史料未被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没有新材料,难以产生新问题,早期传播也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主流。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近年来,学术界已着手系统收集和整理早期传播的相关史料,对早期传播及其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潮。
1 现状梳理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早期传播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取得了很大进步,梳理现有成果有利于明晰现有工作的边界和推进未来的工作。
1.1 专题性资料选辑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早期传播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198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代昭、潘国华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两册)。该书整理了19世纪末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基本史料和文献,主要包括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国人撰写的马克思传记、各种社会主义团体的会议记录和活动报道等。姜义华编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一书收录了1873—1924年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料,编者为每篇文章添加了富有学术性的按语。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一书,按时间顺序编辑了1899—1923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介绍和传播的史料。1985—1987年,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出版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一辑和第二辑,每辑分上、中、下三册,共6册,系从包含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和文章中节选而成,所收资料十分丰富,主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学说,列宁的生平和主张及俄国革命,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及德匈革命和各国共产党,巴黎公社、五一国际劳动节及各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之定义及内容,无政府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空想社会主义等内容。
1982—1984年,有三种关于无政府主义方面的资料选辑出版,分别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内部资料,1982),《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共3册,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这三套资料收录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史料。《“一大”前后》(共3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不仅选编了党在一大前后的相关文件,还收录了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觉悟》《劳动音》《劳动周刊》《先驱》等)的发刊词,以及与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的文章,除此之外,还选编了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如新民学会等)的内部通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传播的史料收集和整理陷入低潮。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又有新的重大进展。2015年,湘潭大学组织编纂了大型丛书《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该书主要收集了1915—1949年中共早期组织及其外围组织直接或间接组织创办的151种红色进步期刊,囊括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布尔什维克》《红旗周报》《群众》《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共产党》等重要刊物,其中很多期刊是1949年以来首次被收录并公开出版。这套丛书共428册,约3亿余字。《红藏》所收集的红色期刊多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2016年,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共3册,吕延勤主编.武汉:长江出版社)一书,按时间顺序编排了1917—1927年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相关的重要史料。2018年,湖北大学的田子渝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第一辑第1—3卷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1920—1927年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外国诠释本,马克思主义的国内诠释本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全书计划出版四编,主要包括《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价值价格及利润》《列宁经济学》《帝国主义浅说》《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等经典著作,内容涉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列宁关于东方社会革命的理论。2019年1月,北京大学编纂的《马藏》第一部第1—5卷出版。《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再呈现,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4]1。《马藏》分为中国编和国际编,目前编纂的是中国编。《马藏》中国编分为四部:第一部为著作(含译著)类文本;第二部为论文文章类文本;第三部为各类通讯报道,各种档案、笔记、书信等文本;第四部为中国共产党有关文献类文本。2019年11月,清华大学杨金海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的首批成果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项目旨在对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典著作的各种中文译本进行收集整理,并作适当的版本、文本考证,以此展现经典文献在中国传播的历程。首批成果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考释本。
1.2 档案资料
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很多国家的档案资料加快了公布进程,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很多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文献。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陆续在内部发行了“革命历史文件汇编”(如《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等),包含了很多中共早期历史资料和早期传播相关史料。90年代,俄罗斯档案管理机构开放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早期档案,比如,共产国际“二大”到“五大”的史料,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联络资料等。1989—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套资料起初是内部发行,后公开发行。1997—201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这套资料约3 600余篇,1 350余万字,含中央档案馆首次公开的300多篇文献。这些重要文件的公开、整理和出版为推进社会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3 著作选辑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翻译、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著述逐渐得到了收集和整理,以选集、文集等形式出版。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文集,如《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等。第二类是国民党相关理论家的著述。这主要指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的文集、选集,如《孙中山全集》(共11册,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等。第三类是中共早期理论家的论著。这主要指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恽代英等人的论著,如《守常文集》(北新书局,1950)、《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李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8)。2013—2014年,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高君宇、张太雷等中共先驱领袖人物的文集、选集等20种,共46册。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整理和出版了多部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相关的资料性丛书,此类丛书也包含有大量与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关的文献。比如,张枬、王忍之编写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1977)、高军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共2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6)、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共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桑兵主编的《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共45册,北京,香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万卷楼图书公司联合出版,2011),以及戴逸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共100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015)等中国近代重要人物的选集、文集等资料。
1.4 工具书
自晚清以降,国内学者开始编纂汉译西学的书目,这类工具书为社会主义文献的收集工作提供了指南和线索。
1896年刊行的《西学书目表》收集了三百余种明末以来译述的西学书目,书末还附以《读西学书法》(共3卷,附录1卷),“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西学书目表〉序例》)。1899年,由绍兴藏书家编辑的《东西学书录》(共2卷,附录1卷)刊行。1902年顾燮光对此书进行增补后以《增版东西学书录》之名刊行,该书扩为4卷、附录2卷,增加三百余条,约为原书之一倍。1904年,顾燮光“又读译籍约千余种”(《〈译书经眼录〉自序》),将1902年以来新出的书目编为《译书经眼录》(1935)。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一书对以上各书进行了汇总和整理。以上晚清新学书目工具书,对于查阅晚清时期的社会主义文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启动了相关工具书的编写工作。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写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1978)介绍了五四时期的重要期刊,其中包含众多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期刊。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一书收录了五四运动时期有进步性、代表性的期刊(如《每周评论》《新青年》《建设杂志》《星期评论》《新潮》《湘江评论》等)的发刊词,重要社团的宣言章程,以及中共成立后主要刊物的发刊词,革命出版机构史实与出版物目录等。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书。该书由上海图书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5至1985年间出版,共3卷,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1899,1900—1911,1912—1918,共收录期刊495种,对所收各种期刊均有概要性的介绍,并按各个期刊之卷期汇录全部篇名。尽管仍不够齐全,但该书为查找与社会主义早期传播相关的报刊文章提供了便利。
进入80年代,与早期传播相关的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迅速增加。《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对近代中国译日本书进行了编目和整理。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共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期刊。90年代后,也有一些工具书出版。《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共17册,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996)和《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共3册,吴永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此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济南:齐鲁书社,2002)、《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张晓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等工具书也为查找早期传播相关资料创造了有利条件。
1.5 电子资源
除了纸质资源外,日益兴盛的电子资源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目前最主要的电子资源形式是数据库。与早期传播文献相关的较为重要的数据库有“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晚清期刊(1833—1911)全文数据库”“中国近代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上海图书馆)”“晚清民国旧报刊数据库”“晚清民国大报库(爱如生)”“民国时期期刊(1911—1949)全文数据库”“民国旧报刊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1833—2017)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大成老旧刊数据库”“瀚文民国书库(1900—1949)”“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1850—1951)全文数据库”“字林西报数据库”“大陆报(1911—1949,英文)数据库”“大公报(1902—1949)数据库”“民国日报(1916—1949)数据库”“上海泰晤士报数据库”“申报数据库”“时报(1904—1939)数据库”“中国近代文献图库(1833—1949)”“中国近代影像数据库”“小报(1897—1949)数据库”“新闻报(1833—1949)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读秀”数据库等等。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早期传播史领域也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如《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黎澍.《历史研究》1954(3))、《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丁守和,殷叙彝.北京:三联书店,1979)、《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杨奎松,董士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唐宝林主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谈敏.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等。以上论著中对社会主义传播史的论述有助于深化对早期传播的整个历史脉络、主要阶段和思想特点的认识;一些作者使用了较多珍贵资料,这也为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提供了重要线索。
2 问题论析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间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属于古籍,但在书写和内容方面又不同于年代更为久远的古籍(如唐宋元明时期的古籍),具有自身的特点。“古籍整理非人人可为的简易机械工作。”[5]目前从事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者,除少数学者外,多数学者普遍缺乏古籍整理的经验,缺乏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和辨伪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尚处于探索之中,还未形成系统的规范和方法。在目前相关文献整理的热潮中,许多问题亟待有关研究者相互合作,共同解决。
2.1 资料收集的起点和范围
以往对社会主义早期传播起点的界定,往往是1917年、1919年或1921年,收集早期传播的史料也多是从这几个时间点开始。例如,现有很多资料的收集是从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一书收集文献的时间范围是“1917年11月至1921年12月”[6]。《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收集文献的时间范围是“1917年5月—1927年12月”[7]。有些资料则从1919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一书收集文献的时间范围是1919年8月至1927年7月。有的文献则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例如,《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一书所收集的资料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头20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的文献。《马藏》收集文献的起始时间是十九世纪末,编者认为:“在十九世纪后期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开始译介各种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中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端。”[4]i《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一书则将起始时间明确界定为19世纪70年代,该书称:“所选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一九〇七年前后有关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出版物上的反映的资料”[8]。
上述资料收集的时间起点不同,但均有其理论依据。如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共成立,这些时间节点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状况的确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但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早期传播的起点可以界定至1871年,是年3月,中国外交官张德彝见证巴黎公社运动并将其记录于日记(《三述奇》)中。巴黎公社结束40天后(1871年7月11日),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等也从欧洲报纸上摘译了“法京民变”的消息。从这时起,欧美社会主义文献逐渐涌入国内。以《马藏》为例,该书第1部第1—5卷,收录早期传播著作(含译著)28册(如《大同学》(1899)、《近世社会主义》(1903)、《社会主义神髓》(1903、1907、1912)、《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3)等),约 360 万字,而这仅是1894—1903年间的著作,还不包括该时期庞杂的报刊文章、通讯报道、书信、笔记等。因而,以1871年为收集相关文献的起点更能全面反映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原貌。
从资料选编的范围来说,相关学者应该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收集和整理与社会主义理论相关的历史文献。学术界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史,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也仅是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各种译本。这就极大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这并不符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客观历史进程。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直到1920年8月,国内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全译本,即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而在此之前,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载体几乎都是对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释著作,如幸德秋水、河上肇、福井准造、村井知至、柯卡普等人著作的汉译本,上述著作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使毛泽东“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三本书中,除了《共产党宣言》外,另外两本书——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均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释著作[9]。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汉译本当然是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重要载体,但不能据此排他性地否定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著作的汉译本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应运用大历史观的思维、视野和方法,从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出发来选择、收集和整理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历史文献,推进和深化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
2.2 资料选编和资料全编
早期传播文献的类别包括各类纸质文献。现有的纸质资料整理类型主要有资料选编和全编两种。
资料选编是选择某一个时期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献(著作、论文等),去粗取精,进行整理和出版。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即是“从一九一九年八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的一百七十四种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本中精选九十二种文本编纂出版”[10]。选择的标准则是文献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程度。一般来说,资料选编收录的是内容与社会主义理论联系较为紧密的各种文献,对于涉及相关内容较少的文献则不予收录。具体到某一文本,通常是摘录其中与社会主义理论联系较为紧密的内容,对于其他内容则并不收录。资料选编的优点是直接明了,通过这些被选择的文献,研究者能够直观地了解某一时期有哪些社会主义的文献和内容传入国内。有编者解释说:对于庞杂的早期传播文献,“不分良莠,不辨主次地把这些材料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提供给今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也未必明智。……精心的选材和适当的编排,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将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基本再现于今天的关键。”[3]I-II而选编的缺点是读者只能管中窥豹,无法了解节选内容在整个文本中的原貌和地位,无法了解原文本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旨。实际上,有些节选内容只是原文本中很小的一部分,也有些文献的中心主旨并非宣介社会主义。
资料全编是将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相关文献(著作、论文、报道、日记、广告等)悉数收集,并予以整理和出版。全编侧重于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编者试图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相关文献,且对于单个文本,不只是收录其中与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内容,而是收录整个单本。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时混杂于各种文献和思潮之中的状况,使研究者能够从整个思想史文献的视野中,考察早期传播的内容散布于何种文献之中,社会主义怎样逐渐从零散论述的状态转变为集中论述的状态,且最终如何在各种思潮中逐步壮大。缺点是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增加了文献收集与整理的难度和时间。采取这种方式编纂的成果主要是《马藏》。该书力求全面搜集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中文译本、国外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相关著述的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重要理论家的著述、中国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著述、报纸杂志等媒体的通讯报道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文本,如档案、日记、书信等”[4]iii。
2.3 影印出版和录排出版
早期传播相关文献的出版目前主要有影印出版和录排出版两种方式。
影印出版的优点是以原貌形式呈现第一手文献,比较准确,错讹较少,且整理出版的效率较高。《红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等即以影印形式出版。田子渝解释说:“原著影印出版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文本的原貌,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研究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和精神。”[10]
录排出版,则要对原貌进行更改,一般是将原来竖排文献改为横排排版;底本往往无断句,或有断句号,而无新式标点。按照古籍整理的规则,如是录排出版,则应重新断句和点校,对错讹予以纠正。但由于文献数量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团队又往往缺乏文字学、校勘学等专业知识和富有校勘经验的专业人才,因而大多数整理成果,并未进行重新断句和点校的工作。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一书《序言》中说:对于选自原始文本的文献,“标点符号一般不作改动”[6]。《马藏》在《凡例》中亦说明:“底本中以‘。’‘、’表示的句读,均保持原貌。”[4]ix只有少数文献整理者做了此类工作。如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一书“所选的资料,原文或无标点,或仅有旧式断句,今全部标点,并重新分段”[8]。无论是否重新标点,整理者一般会对底本中的排版、分段、引用等在录入排版时使用新式排版和标点规则予以表现。例如,《马藏》即是录排出版,原为竖排版的均改为横排版,底本中的竖排引号均改为横排引号;对于繁体字则“一仍其旧”[4]ix。录排出版的优点是,符合今人的阅读习惯,便于对史料中的错漏之处予以标注或更正,也便于添加校注和说明。当然,无论是影印还是录排,一般均以译本的第一版为底本,初版缺失的,再选择其他版本。
现有文献整理的编排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的以文献出版或发行的时间为序,采取此种方式的有《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等;有的以主题进行区分,对相同主题的内容集中编排,采取此种方式的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等,其将第一、二、三国际,巴黎公社,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不同主题的文献分别集中编排;有的以文本类型为序,采取此种方式的是《马藏》,其将著作,文章,通讯报道、档案、笔记、书信,文件等四类文本编为四部。这几种编排方式各有千秋,各有利弊,从读者阅读和查阅资料的角度看,以内容和主题编排,更有利于读者使用。对于整理者而言,面对巨量庞杂的资料,则以时间或文本类型编排更为便利。
影印出版或录排出版,并无优劣之分。影印出版一般需要克服对文献中文本内容、译本版次、专有名词、文本形成背景等注释和说明不足的弱点;录排出版一般需要克服校勘、断句以及字体转换过程中产生问题较多等弱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大型丛书可以制作相应的电子数据库,由于数据库容量较大,影印版和录排版可以一并展示,方便读者对照使用。这样,两种出版方式的优点便均可得到利用。
2.4 文本校注与文本说明
文本校注和文本说明撰写是目前相关文献整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容易产生问题之处。这里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底本文献信息不全。因年代久远,不少底本的出版时间、出版单位、作者、译者等信息不全。这就需要整理者收集该文本的不同版本,分辨初版本和再版本,对照不同版本,补齐相关信息。
二是译名不统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文本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机构、事件等并无统一的译名和规范,不同译者依据己见或音译、或意译,因而产生众多译名;且很多文献是由德文、法文或英文,译为英文、日文或俄文,再译为中文,经过多次翻译,译名与原名含义相差甚远,乃至往往面目全非,甚至在同一个译本中同一词语的译名就有两种以上。例如,在1903年广学会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恩格斯的译名至少有三种:“野契陆斯”[11](第二编4)、“意契陆斯”[11](第二编24)、“野科陆斯”[11](第四编3)。因而,考证文本中与现代通行翻译不同的人名、地名、国名、事件、机构名等,作出准确的学术性注释,是文献整理者需要处理的问题。
三是译本版本差别较大。早期传播过程中的经典论著往往会有多个译本和版本,这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各译本的书名差异很大,作者和译者署名也有很大差异。有的是全译,有的是节译,有的是添加了译者个人见解的译述本;有的是文言译本,有的是白话译本,也有将文言译本演为白话的译本;有的称是不同译本,实际上是同一个译本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本;有的称是不同版本,实际上是不同译本或是经过了译者的大幅重译或删改而形成了另一个译本……以上诸种问题,都是整理者需要悉心勘察的。
四是通假字、异体字、错别字较多。早期传播文献多属古籍,因语言习惯和印刷技术等问题,文中通假字、异体字或错别字较多,这需要整理者根据当下整理和出版规则予以处理。
五是文本的形成背景、思想要旨、历史地位和研究动态等有待挖掘。文本整理者需要对文本的此类信息予以探究,形成提要或文本说明,为读者提供文献的相关信息。
针对以上情况,各种已出版的相关资料所做的工作不尽相同。有的对原文中除文字之外的错误,基本保持原貌,不做改动。如《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一书《凡例》介绍:“原文中史实错误一般不做订正和说明。”“所录文字或有晦涩不通、词不达意之处,除个别较重要资料外,一般不予改动。”[3]IV有的对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重要人物、事件、机构等名词作了注释,对于文中的其他生僻专有名词则不作注释。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一书的处理是“由于译文、语境的时代性,不少人名(如马克思、恩格斯等)、地名(如彼得格勒等)、专用名词(如德谟克拉西、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在不同时段、不同著述中有不同的译文,本书稿尊重原文,不求统一,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用‘今译’加以说明。”[6]有的则对所收录文献中的所有生僻专有名词及错漏之处均作了注释,对文本相关状况撰写了文本说明。《马藏》的编纂即是如此。编者“以页下注释的方式,对原书中的误译、误写或误排之处,予以更正;对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著述、历史事件、组织机构和报刊等名词给予准确而简要的说明”,以“编者说明”的方式“对文本形成和流传情况作出描述,如介绍文本原貌及来源、作者、译者、历史背景、出版情况、不同译本和版本演变情况、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和史实、文本传播状况和研究状况、文本的思想倾向等问题”[4]iv。
关于文本校注,有不少问题有待学界同行共同解决。如繁体旧字形转换新字形、繁简体之间的转换等。目前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多是通过电脑完成,但是电脑处理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将较大篇幅的简体字的词组整体转换为繁体时,由于是中国台湾的词库,因而会自动转换为台湾用词。如信息(資訊)、网络(網路)、托马斯(湯瑪斯)、布尔战争(布林戰争)、对象(物件)、工程(專案)等。还有些简体字对应多个繁体字,用法也有差异,用电脑等设备将简体字转换为繁体字后也会出现不少错讹。如头发(頭發)、深谷(深穀)、皇后(皇後)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文献整理者梳理此类用词,列出词汇清单,供修正错误使用。
关于文本说明,有些整理者会对文本内容及其在社会主义传播史或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概括和评价。但有几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对文献内容的阐介不够准确。文本说明本是对文本背景信息和内容的介绍,是读者阅读的向导。但如果整理者的阐介较为随意,不够准确,反而会对读者造成误导。如对于出版时间较早的文献,整理者往往会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统计“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出现的次数,这往往会被读者用在各种研究成果中,但如果仔细查证,会发现很多统计数据并不准确。此类介绍导致的结果反而是以讹传讹。二是有些关于文本的说明,对文本内容的评价不当。这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用当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的中央编译局译本或当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标准去指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文献的内容,批评其翻译质量不高,内容不尽正确等,对这些文献的价值作出较低的评价,甚至认为其不值得整理。这种以今人的理解苛责前人、求全责备的做法,并非科学的态度。另一种情况是对文献的评价过高。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初期,其理论往往散布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著作中,且内容较少,在这部分著作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但不少文献整理者却对诸如此类的文献作出过高的评价,往往给予“最重要”“具有重大意义”等定性话语,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坚持历史主义的思路,将历史文献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从文献本身出发,分析其在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对文献进行介绍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3 前景展望
整理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文献的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文献收集工作,推动机构间的协同合作,培育学术共同体,优化文献整理成果的评价机制。
3.1 完善文献收集工作
第一,进一步挖掘和收集中文报纸杂志。清末民初,报纸杂志成为传播新知识的重要媒介。很多报纸杂志刊载了大量包括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学说的西方新知识,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旅欧知识分子创办的《新世纪》《旅欧教育》《赤光》《少年》等,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星期评论》等,均刊载了大量社会主义的相关信息,开阔了中国民众的视野,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例如,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终刊于1948年,是近代中国办刊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学术性杂志,有“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之称。该刊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话语平台。左翼作者如瞿秋白、陈望道、恽代英、吴恩裕、胡颂之、冯宾符、范寿康、邓初民、张明养等在该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挖掘和收集港台和海外相关文献。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文献分散于海内外,因而,收集文献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大陆,还应放眼海外。除了美国、日本、俄罗斯与欧洲各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也藏有大量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相关的历史文献,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至今仍未能够被系统地收集。例如,20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很多译书出版机构(如译书汇编社、闽学会等),刊发了很多新式著作(包括译著)和报纸杂志,通过这些机构和杂志,向国内宣介了包括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新知识。这些新式著作和报纸杂志很多收藏于日本各地的图书馆。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在论述社会主义早期传播史的著作中常会提到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有一个“蜀魂”译本,此译本经研究者在国内各地搜寻,均无结果。研究者通过日本学者,很快在日本的一个图书馆找到并复制了此译本(研究者后来发现,国内某图书馆也藏有此译本,但该馆以其是古籍为由,谢绝查阅)。
第三,挖掘和收集西文相关文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文献,不仅有汉文文献,还有大量西文文献有待挖掘和整理。从晚清至民国,来华西方人士和中国报人在中国创办了若干英文报刊,如《字林西报》 《上海泰晤士报》 《大美晚报》 《上海晚邮》 《中华快报》 《上海差报》 《北华捷报》 《密勒氏评论报》 《北京导报》 《广州时报》 《京津泰晤士报》等等。这些报纸的内容主要是时政新闻,以及中国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信息,其中包含了大量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相关的内容,对人们从各个侧面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被誉为“近代中国外文第一报”的《字林西报》曾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12]。该报的一些文章,如German Socialism in America[13]、Socialism in Germany[14]、Socialism in Japan[15]、What is Socialism?[16]等,对于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具有推动作用。因其经营者、编辑和记者多是西方人士和中国新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观察与记录常常不同于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因而,这些资料对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较为特殊的思想意义。
清末民初,国内机构或个人也通过各种方式直接从国外引进西文(主要是英文)文献,从外文文献直接获取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知识。例如,仅在1919年和1920年,北京大学就引进了涵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相关外文著作67种,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雇 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zur Judenfrage und andere Schriften aus der Frühzeit)、《 共 产 党 宣 言》(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反杜林论》(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考茨基著《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托马斯·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Socialism)、托落茨基著《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列宁与托落茨基著《俄国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等重要著作[17]。
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提供了很多近代日本的社会主义论著和文献,其馆藏的很多电子书资料可免费下载。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对于检索相关文献信息也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收集和利用电子文献。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为文献的收集和编纂提供了助力。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和电子资源使得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可以便捷地获得个人所需要的文献资料。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也涉及利用各地电子资源的问题。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建设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两所图书馆都对清末民初的部分文献进行了电子化加工,建立了不少非常实用的大型数据库。如上海图书馆打造的“中国近代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中国近代中文报纸全文数据库”,前者包括了《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大美晚报》等,后者包括《民国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以“民国日报数据库”为例,创办于1916年初的《民国日报》,是中华革命党宣传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曾风行全国,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曾在一个时期对欧美、日本等地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作了较多介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也作了积极的宣传,李达、瞿秋白、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等曾在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民国日报数据库”支持全文检索和下载,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3.2 推动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协同合作
近年来,国内已形成了早期传播文献整理的热潮。北京大学、湖北大学、湘潭大学、嘉兴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都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开展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尽管各单位收集文献的时间范围、内容侧重点以及整理和出版方式各异,但都围绕早期传播这个主题开展工作。这种新局面有利于推动学界关注早期传播文献,扩大文献收集范围,从整体上推进对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但是,目前的文献整理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早期传播文献因年代久远,底本数量往往十分有限,有些甚至是孤本,研究者通常要在世界各地搜寻,对于经过各种艰辛搜集到的文本自然会视之为珍宝,不肯轻易与人。这就造成各单位收集的文献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各单位出版的成果所收录的文献自然也有所不同,各有缺憾。
第二,重复收录和重复整理。由于文献整理工作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许多文献是各家都收录了的,因而出现较多的重复收录,其整理占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这无疑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因而,各单位在文献收集与整理方面应尽可能协同合作,一起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第三,缺乏统一的整理标准和规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普遍缺乏文字学和校勘学方面的编辑和专家,早期传播文献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古籍的特点,因而,早期传播文献的整理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制定整理规则。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对于同一文献的文字校勘、文本注释和文本说明撰写的标准各异,且重复整理,费时费力,质量又良莠不齐。
针对这些问题,各单位需要协同合作。一是资料收集方面尽量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资料收集工作本身耗时耗力,而资源共享,互通有无,能够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弥补各自收集文献的缺失。二是合作推进针对文献状况的调研工作。例如,哪些文献还未被收集和整理,哪些文献已经是被整理完成的,在已整理的文献中又有哪些是质量低劣需要重新整理的。只有完成此项工作,才能明确文献收集和整理的方向。三是共同制定早期传播文献整理的规则和标准。各单位协同整理文献,共同制定文献整理规则和标准,可以有效避免重复的低质量劳动,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
3.3 培育学术共同体,优化文献整理成果的评价机制
学术共同体的创立有利于明晰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有利于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深化对早期传播文献收集与整理的认识,推动对相关学术问题的共同探讨和交流,促进文献资料的共享和利用,有效避免重复研究和低效率研究。编纂相关文献的工作远非少数个体所能完成,必须联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者共同推进。文献收集和整理过程中,有条件的单位应积极创造平台,通过开设专业研究班、青年教师与博士生寒暑期研讨班、工作坊以及早期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相关课程等形式展开对相关问题的探究,强化早期传播的问题意识,明确研究思路,形成研究共识,推进研究创新,聚集一批有深厚根基和浓厚兴趣的青年研究人才,逐渐形成早期传播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共同推进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文献收集和整理成果在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并不算作学术成果,因而也不能列入学术评价体制。大多数文献收集和整理人员短期内可以抛却名利的考虑,投入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而,如果长期没有学术成果评价的激励,且受制于职称和福利待遇,年轻学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被调动。为鼓励广大学者从事早期传播文献收集和整理的工作,目前文献整理成果的评价机制亟待优化,应该推动高校等科研单位将文献整理成果纳入现有学术考评体系,将文献整理成果与其他学术成果同等看待,对优质的文献整理成果予以奖励和宣传,促进早期传播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开展。
傅斯年曾指出,“史学便是史料学”,“治史便是整理史料”。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特别重视质量,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和数量。由于相关文献数量巨大,广大研究者需要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制定文献收集和整理清单以及文献整理的规则和标准,推进早期传播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