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布堆绣造型及其心态文化
2021-01-07张继文
张继文
(西安工程大学 新媒体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0 引 言
延川布堆绣作为民间布艺刺绣,植根于黄土高原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是特定环境与社会背景下族群文化的载体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特定地域环境下生活的人类群体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极富特色的民间美术,延川布堆绣经民间艺术家之手,对特定的物象提炼、重组、选择造型,以特定的载体传达出该区域民众共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它既是心态文化的体现、文化内涵的核心,也是本文透过造型艺术去探究的重点。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以延川布堆绣为单独研究对象的学术性成果仍然较少。相关理论研究多集中在造型艺术、色彩与装饰、设计应用等方面[1-4]。文献[5-6]均是图片为主的作品集,鲜有文字说明。文献[7-8]主要从历史、发展现状入手,对布堆绣的结构形式、色彩表现、风格特征等展开论述,分析布堆绣蕴含的文化和审美特征,涉猎虽广但不够深入和系统。文献[9]从地理环境、文化历史、社会生活等因素分析布堆绣的色彩成因,探寻色彩寓意、情感特征,并探索其色彩呈现特征在当代设计中的创新表达。文献[10]在现有设计因子提取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布堆画牡丹花纹样因子提取模型,并探讨了纹样因子提取及应用方法的可行性。文献[11-12]对延川布堆绣的风格、特征进行归纳整理,并结合不同的设计实例探讨布堆绣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运用。文献[13]立足延川布堆绣,对民族化图形语言的信息传达做了初步研究,对民间艺术文化信息共享做了初步畅想。
现有理论研究中,对布堆绣造型观展开专项研究并深入剖析文化内涵的鲜有涉及。本文从该角度出发,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实物分析等方法,从延川布堆绣的源起、造型的形成入手,对布堆绣文字与图片资料进行全面梳理,针对样本展开定性分析,并提炼归类。最后透过其造型观探析布堆绣呈现的心态文化,洞悉其艺术特色和造型规律,为延川布堆绣的保护、传承提供理论基础。
1 陕北民间美术造型体系的承袭关系
任何艺术形式都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凝结,民间美术的创作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作者本身及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深层心理需求[14]。布堆绣艺术正是通过其独特的造型观,传递出当地族群文化的本源意识。陕北地区民间艺术造型和审美习惯的形成显然与其生存状态和生活实用、情感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处黄河流域的陕北地区,原始社会境内已有人类繁衍,古代曾是不同部落更迭和多民族融合汇聚的地方。陕北的地域文化形成于漫长的封建时代,经历了3个时期,首先是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是陕北地域文化的形成期[15],后又经历了魏晋至宋代的文化发展巅峰期和明清之后的文化发展稳定期[16]。明初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但退居漠北的蒙古仍时时威胁明朝,导致明中期陕北成为军旅繁盛之地,战乱和严峻的气候环境,形成了陕北较封闭的文化环境。一方面加速了陕北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封建没落时期的中原文化对陕北的浸淫,反而较完整地沿袭了封建社会上升期的汉代文化,包括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几千年来的山川巨变,人们历经迁徙往返,兵戎相戈,终八方移民在此地共筑基业,经过历代民族血脉融合,文化习俗相交渗透,逐渐形成了黄土文化,拥有了自己的艺术体系和造型观[17]。
原始艺术中对物像形体的表现往往是直观、自由的。陕北出土的大量的玉器、陶器、青铜器等,多来自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这些器物的纹样成为陕北民间美术中艺术造型的源头。加之与边疆接壤,北方民族的文化、审美以及彪悍粗犷的性格都为陕北民间美术个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氏族公社内蒙阴山岩画中的《倒照鹿》的造型,在今天陕北民间美术作品中常常能见到。秦汉以后,中原的集权组织加强了对陕北的管辖,筑长城、修直道,促进了陕北经济文化的发展,此时的中原艺术在陕北地区成为主流的艺术形态。今天陕北民间美术雅拙与粗犷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造型中仍可看到汉代画像石造型的特点,例如:陕北东汉墓画像石侧面奔马右刻却在面部显示出2只眼睛。这与陕北民间美术作品中常出现的造型一致,都是以本质代视觉直观现象[18]。从中不难看出孕育陕北民间美术的文化土壤和造型形成的承袭关系。作为民间艺术的延川布堆绣,其表现形态当然也概莫能外,在构图中也充分表现出这种文化承袭。
格罗塞曾提出,艺术形象最原始的形式,首先是表现于“人体装饰”,其次是“器具的装潢”[19]。从实用而来的布堆绣,逐渐从服装和日常生活用品中独立而来,以装饰画的形式呈现,更注重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作品古朴遒劲、构图夸张、轮廓洗练、色彩浓辣鲜明,表现出原始自然的人性,充分体现出陕北艺术的原生形态。
2 延川布堆绣的造型观
布堆绣的呈现形式有别于其他刺绣,它犹如将剪纸贴在布上,又似碎布层层堆叠,并在堆积的布块上施以各种针法,使得画面层次分明又浑实遒劲。作品呈现出的物象形态少了婉约柔情,多透出狰狞之气,这是由它的文化传承带来的,因为它一方面继承了原始巫术和图腾文化,另一方面深受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其审美和艺术表现的影响。图案廓形都简洁洗练,呈现出直观的外貌特征,透露出陕北民间美术蕴含的独特的造型观和哲学观。
2.1 时空观
布堆绣常常在平铺的画面中体现出了四维的时空感。其体现出的空间透视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美术构图中的“焦点透视”,也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散点透视”不同,靳之林先生认为“它是四度空间的多点透视”[20],常是以中国本源哲学观展开构图。布堆绣与汉画像石呈现的造型思维十分相似,都表现出一种原始思维的特征,即把要表现的事物按自身的理解进行摆放,而不是依照眼睛所观察到的事物或景象瞬间的状态进行刻画。常常把不同时空的多个事物围绕在一个主体物象周围,也喜欢将平视的立面与俯视的平面相结合,呈现混搭的空间表现形式。
如布堆绣作品经常会出现的劳作场景中,整个画面中人物、动物都是运用平视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构图,而作为劳作主体工具的磨盘在展现时却是正圆的形状,这是一个俯视的视觉透视,但磨盘的底座在构图中又回到平视视角,这一构图完全摒弃了通常美术作品统一视角的构图习惯,完全是根据主题需要或主体审美需要,以流动的视线,表现不断转换的空间。这种构图形式,既表现出正面,又表现出侧面,把不同的空间和时间观察到的物象、形态统一在一起,用的是一种观念性的语言艺术(见图1)。

图1 推磨(作者:郭如林)
2.2 意形观
陕北民间艺术家们在通过布堆绣作品展示个人审美和艺术理解时,主要是通过想表达的寓意来进行形体设计的。不同于学院派造型体系注重解剖,强调准确的透视关系,民间艺术造型体系中不讲透视、不懂解剖,看起来不科学的构图关系,正是人类艺术的本源。在布堆绣创作中,民间艺术家更愿意“以意舍形”,意是“理”,形是“自然的形态”。这里不是通过解剖学认知来表达事物,而是通过“哲理”传达对自然界的理解[21]。
布堆绣的作品呈现中往往特别重视眼睛的刻画,认为那是最传神的部分,所以眼睛表现得很大,黑白分明,显得炯炯有神。不仅如此,眼睛还会呈现各种形态,有花朵形状、鱼形状、果实形状等。例如抓髻娃娃的眼睛被表现为2个概括的石榴形状。石榴在民间艺术中有多子的寓意,是生殖繁衍的象征之一,而抓髻娃娃本身也表现的是繁衍之神,因此用石榴的变体呈现抓髻娃娃的五官,正是强化“意”的表现,而忽略形的准确。除此以外,无论人物、动物的面部是正面还是侧面,眼睛的形态都是完整的正面,眼珠大而圆,不会被眼皮遮挡,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模式,只为显出神采(见图2)。

图2 布堆绣中的眼睛
2.3 阴阳观
陕北民间美术保存了黄河流域以及黄土高原的早期文化信息,延川布堆绣也不例外的承袭了这些文化信息,其作品内容和造型上屡屡反映出了各种文化时期的文化原型遗存。例如鱼、鼠、莲、葡萄等多子的形象;“抓髻娃娃”“蛇盘兔”“鱼戏莲”等主题。
“抓髻娃娃”是陕北民间文化中表现频度最高的主题之一,“髻”为“鸡”的谐音,代表是阳性。女子成家后即要梳起双髻,也是生殖崇拜观的展现[22]。抓髻娃娃也有男、女之分,其中女性抓髻娃娃双手举鸡,而男性抓髻娃娃双手举莲花或石榴(见图3)。莲和石榴都代表阴性,石榴更寓意着多子。这种阴阳结合的造型,是陕北人传统的对生命企盼的表达,鲜明地反映出陕北一直以来的有关阴阳的文化认知。

图3 女性、男性抓髻娃娃
郭如林表现“推磨”主题的布堆绣作品中,圆形磨盘在上,而平直的磨盘底在下,以盘喻天,以底喻地,以磨盘喻天圆地方的宇宙母体,而它也恰恰是画面的主题。磨盘碾磨的粮食是生命延续之源,磨盘的中心是一副八卦图,阴阳平衡,化生万物,诠释了中国哲学观念的物质化形态构成,也正传达出中国传统的阴阳观。
2.4 情趣观
陕北民间艺人的创作往往不受任何绘画原理的约束,随心所欲,因为没受过系统的学院派的学习,反而没有框架的约束,不受客观物象形态、纹理的限制。他们展开艺术创作的原因简单而单纯,颜色的搭配,装饰纹理的取舍只有一个依据,就是自己觉得好看,就这样做了。生活的烦闷与简陋让他们更渴望在美术创作中充满情趣和装饰。“要有意思,要好看”成为了他们的口头禅,也成为创作中的审美核心。
布堆绣作品中的牛头,在表现牛鼻子时,不是按常理用简单的圆圈表示,而是将鼻孔比例放大,绣出2朵团花,并分出虚实4个层次,从中心向四周,由实至虚。不仅凸显了布堆绣特有的堆叠层次感,而且更具艺术感和趣味性,让牛的形象更亲和,更有喜感(见图4)。

图4 牛头
在郭如林的描绘劳作的场景中,夫妇俩正在打谷,为表现飞扬的成堆的谷子,创作者用放射的牡丹花瓣的形状来展现,虽不符合客观规律,画面却更加唯美,欢喜的场面更加突出,收获的满足与喜悦洋溢在作品中(见图5)。

图5 打谷子(作者:郭如林)
3 布堆绣造型观投射出的心态文化
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要将文化准确分类是很难的。对于文化结构的解剖最普遍的认识是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2个层面。至于文化结构的分层,一般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心态文化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本文透过布堆绣艺术探究的重点。
经过长期的历史沿革形成的群体文化,往往借助不同门类的艺术载体加以传递,延川布堆绣艺术作为区域文化的显性载体之一,将陕北人生活得到的经验、智慧,直觉的感受和对世界的认识透过作品传达出来。当地族群的“心态文化”透过布堆绣的造型,或含蓄或直接的传达出来。情趣观中不受客观形态束缚而形成的任意组合,展现出当地人乐观、豁达的性格和朴拙的价值观念;意形观中强化“意”而忽略“形”,追求“大”“满”的造型,正是其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布堆绣中的阴阳观表现出对生的理解和崇拜;时空观中不依自然规律呈现出的空间变化,一同展现出他们独特的“哲理性”的思维方式。
3.1 价值观念
价值观反映了人的认知和需求,也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和信念。西北黄土高原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使当地的生活资源并不充裕。生活的艰辛、物资的匮乏没有击倒陕北人,反倒成就了他们乐观豁达、踏实勤勉的性格。这种淳朴的认识和需求观念糅合中国传统思维,对布堆绣艺术主题的设定和造型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当地人通过布堆绣的艺术形式描绘心目中的理想生活,通过一些图像符号趋吉避凶,传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淳朴的陕北人认定辛勤的劳作是摆脱现实困境的方式,常常借用布堆绣造型艺术传达出对劳作与土地的敬仰。例如耕牛是传统劳作方式的重要劳动力,被陕北人视若“命根”。谈情趣观时曾提到用牡丹花造型装饰牛鼻、牛身,牡丹花是阳性的象征符号,装饰于耕牛既代表力量,又寓意着繁盛,这也是陕北延川人心目中的价值所在。田埂上仰天吹起的唢呐,四周环绕的凤凰、喜鹊、耕牛以及唢呐的喇叭口上装饰着的花卉都是传达欢乐、美满的符号因子,显示了对未来生活的期盼(见图6)。

图6 庆丰收
冯山云的作品“日月”中,女人站在黑色的背景下仰头向天,男人低头盘坐映衬于白色背景,一男一女、一阴一阳,表达了陕北人对现实的思考和未来的憧憬。陕北人常说:“仰头婆姨,低头汉”,仰头是婆姨们的果断和细心,是面对现实生活的智慧;低头是男人们的沉思、冷静、刚强,对未来的筹谋,这样人们才能更好的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生活的故事(见图7)[23]。这些作品都反映出陕北人对世界最本源的认知、判断,反射出其淳朴的价值观。

图7 日月(作者:冯山云)
3.2 审美观念
陕北地区因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造成的物资匮乏、发展滞后,使得丰沛富足成为大家的共同企盼。投射到审美中,形成了对“大”、“满”的造型的偏爱。在“大而美、满则富”的审美观念引导下,构图中往往舍去对自然形态的限定,不按事物的真实比例刻画,对于重要的、偏爱的物象便表现得大而丰满。构图追求饱满,顶天立地不留空隙。空白之处都要添上装饰和点缀。这也就出现了布堆绣造型中常将不同时空的事物刻画于一幅画面中的时空穿插的造型观。
在民间艺术家高凤莲老人的作品《黄河细折腰》中,牲口体态丰满硕大,家畜飞禽都集中在画面中,鱼飞跃于天空,花草飞鸟铺满河道与小径,构图饱和,而且完全不依天上地下的布局常理。摒弃常规的空间感和透视原理,屋里屋外的景象放入同一个构图中,看似纷乱却自有一套认知逻辑,整组造型视觉上丰满磅礴,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繁茂昌盛的生命之图(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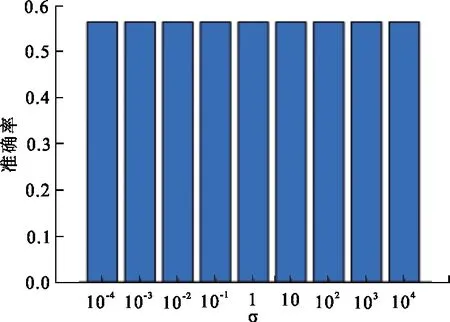
图8 黄河细折腰
3.3 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从现代信息科学的意义上说,是主体从外界获得信息、加工信息,从而形成新信息的途径和方法。布堆绣正是创作主体将生活中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后,以自己的理解用新的形式描绘出来的途径,充分地反映出群体认识世界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美术造型体系中崇尚对自然形态的模拟,或是对自然形态的直接变形,布堆绣的造型观更愿意表达意念的传递和变形,通过独特的时空造形观,呈现“哲理性”的思维方式,诠释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表达主观感受。
布堆绣虽是静态的作品,却在静中让人感受到“生”的力量。无论是人物还是、植物,造型上多呈现出向上伸展的状态。如抓髻娃娃中向上伸展的手臂,高高昂起脖颈的凤凰,藤蔓向上盘绕盛开的荷花,都传达出生命的蓬勃和创作者对“生”的渴望。这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人们,为对抗现实生活的困苦,祈求健康平安、富足长寿、子孙繁衍等精神需求的表达方式。
在物象造型的表现也非常独特,延川布堆画中的女娲,摒弃中国传统神话形象中的人身蛇尾,削弱了神秘感、距离感,被附上浓郁的“陕北”色彩,形象更接地气,如同生活中的陕北婆姨。四周缠绕着莲花、孩童,象征美满和旺盛的生育力,这也是陕北人传递信仰的表达[4]。
布堆绣图案造型中出现最多的符号就是牡丹、莲花、石榴、葫芦、鱼、蛙等象征阴阳和旺盛繁殖力的物象,创作者常用含蓄的类比方式来显现对“生”的渴望。虽然显性的因子为植物,但实则是以此喻彼。藤蔓枝桠往往象征男性生殖器,花叶象征女性生殖器,树枝和花叶的交错缠绕也象征男女欢爱。在公鸡、凤凰的脊梁上经常会出现一个“云钩”纹样,当地称为“胜”,代表第二性生殖器官,是阳性的象征。类似这样的象征性符号常常含蓄而隐秘的出现在作品中,向外界传达出本族群对生命繁衍的理解与崇拜(见图9)。

图9 云钩子
4 结 语
本文从陕北民间美术造型体系的承袭关系入手,对延川布堆绣文字性研究成果与图片资料进行全面梳理,筛选样本并对其造型呈现方式展开定性分析,得到时空观、意形观、阴阳观、情趣观4种造型观,并从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思维方式3个角度,结合其造型观探析布堆绣呈现的心态文化。探究延川布堆绣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既是对布堆绣专项理论研究中欠缺部分的补充,也为今后更深入的探究其艺术特色和造型规律提供参考。
延川布堆绣通过其独特的创作语言,用一种含蓄的借物言情的表现手法,向外界展示出本族群的文化认知,传达出族群共同的生命感悟。其造型及文化的深度探析对维护民间艺术生长的文化生态,传承工艺和图案,巩固族群的精神家园,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凝聚力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