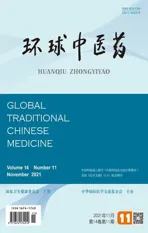从“营卫交会失和”谈不寐的辨证论治思路
2021-01-06张亚敏朱雪莲
张亚敏 朱雪莲
失眠,中医学称为“不寐”“目不瞑”,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种睡眠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寐而不酣,或醒后不能再次入睡,严重者彻夜不眠[1]。中国睡眠研究会经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率达38.2% ,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2]。中医学对不寐有着丰富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但由于医家流派繁多,对于不寐病因病机及分型各有见解。李鼎先生[3]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营卫是临床医学中“辨证施治的主要法则”,本文试从营卫角度对不寐的辨证方法提出新的思路,为临床分型论治提供参考。
1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入为寤寐之枢机
营卫之说从何而来?在《黄帝内经》成书时期,“营”主要指“军营”,有环绕而居的意思,“卫”则主要是行走的护卫,意思是围绕巡逻,由此产生保卫的含义。《黄帝内经》沿用了早期“营”具有的环绕而居之意,因此营气可以环绕循行于人体经脉,如环无端,周流不息。由此可见,营卫应该是共同组成抗邪系统而存在的,一旦一方过强或过弱,或两方配合不默契,即可出现问题。在营卫学说强调“营”对经脉的濡养、灌溉作用,突出了“营”的滋养内涵,对“卫”继续沿用“保卫,防护”之义。
1.1 营卫阴阳出入正常是睡眠的必要条件
《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又曰:“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白昼阳旺之时,属阳之卫气行于脉外,盛于体表,发挥其温煦及防御作用;而于夜晚阳气衰微之时滞于脉内,与营气同周游于五脏六腑。这里首次阐明了营卫的关系——营行脉中主内守,卫行脉外主外御,营卫之气的运行各有法度,营卫之气的阴阳出入正常是睡眠的必要条件。正如王冠英[4]说,天有昼夜,人有卧起,人之昼寤夜寐周期与天地昼夜日辰节律变化协调一致、周而复始,营卫循行、阴阳出入为寤寐之本质,“荣卫之行失其常”为不寐发病之机。
1.2 营卫至时而会失常则不寐
营卫盛衰有涨有落,营卫循行有离有合。卫气只有达到“至阳而起,至阴而止”,人体才得以“昼精而夜寐”。若营卫阴阳出入相会失和,则会导致不寐。
邪气从外侵入致卫气郁闭,或营阴内耗,致使卫强或营弱。营卫不调和,卫气浮越,夜间卫气不能入于阴分,则出现“夜不瞑”。白钟国[5]亦认为卫气运行失度是造成睡眠障碍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营卫运行的道路涩滞,经脉不通,使卫气独行其外,不得入于阴,交会失和,亦可使“目不瞑”。“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若使脉外之卫气顺利进入脉中,必须满足营卫相会之道路即经脉管壁通畅,若脉管有血瘀、痰湿阻滞,均可导致气道不通,营卫至时而会失常则不寐。如《临证指南医案·痰饮》记载一患者不寐,叶天士认为其病机是“痰饮日聚”,同时《叶天士医案存真·卷三》中亦指出:“痰饮乃阴浊所化,以渐有形,阻碍阳气,不得入于阴。”痰饮内聚,阻滞气机升降,阳不入阴,致使不寐。
可见,营卫之气的阴阳出入为寤寐之枢机。
2 不寐发生的根本病机为营卫交会失和,阳不入阴
2.1 营卫偏盛偏衰,阳不入阴
营卫偏盛偏衰,交会失和则阳不入阴。营卫失和致不寐,可以从卫强和营弱两个角度论治。卫强是卫气在表位过度郁滞,绝对充斥,需发散解表;营弱是在里的津血不足,营血亏虚,不能与卫气正常交合,故夜不暝。《景岳全书·不寐》曾对失眠病机有所论述:“不寐证虽病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尽矣……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
借鉴“中和”思想来理解:中和即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现营卫有一方偏盛偏衰,两方不能达到中和的境界,甚则背道而驰,卫气浮越于外,故不寐。
2.2 营卫通路阻滞,阳不入阴
《灵枢·营卫生会》云:“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暝”,说明年轻人气道通畅,营卫可以正常运行,此为昼精夜暝的基础。反之,若营卫通路阻滞,气道不通,卫气行于阳,独卫其外,不得入于内,阴阳交通不畅,则不寐。
《寿世保元》言:“血荣气卫,常相流通,何病之有。一窒碍焉,则百病由此而生。”营卫二者以气血之体作流通之用,常相流通则阴阳协调。卫气郁而不舒,营气涩而不行,营卫之行受阻则气机失和,气血郁滞,津液停聚。津液不得气化,失于布散,壅遏凝结成痰,痰浊日久易与血互结,或化热或成瘀,阻滞营卫交通运行之路,使营卫运行的道路涩滞,经脉不通,阳不入阴导致不寐。
3 明确致病原因是分型论治的关键
3.1 邪气扰之:卫强营阴相对不足
卫强即卫气在脉外过度郁滞。邪气客于人体则卫气奋而抗邪于外,不能入于阴分,形成卫气浮盛于体表、精气虚于内,神气不得内守,故而不得眠。患者多表现为睡眠时间短,易醒,醒后难以入睡,常伴有自汗,头痛头晕,肢体酸疼,纳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浮。此时需发散解表,同时使脏腑精气敛于内,神气得守而安眠。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桂枝汤加入龙骨、牡蛎两味中药,从而达到调和营卫的安神功效。其中桂枝为君,能够解肌散寒,有透营达卫之效,白芍为臣药,酸苦而寒,益阴敛营,桂枝与芍药一散一收,一阴一阳,互相配合达到调和营卫之目的;大枣味甘,补脾生津,生姜性温,助桂枝解肌,姜枣合为佐,补益脾胃以化生营卫;甘草担佐使药之责以助阴阳调和。龙骨、牡蛎性纯阴,借助甘草清阳之性入经,收敛浮越之卫阳,安脏腑之精气,故而达到安神之功效。
刘景源教授曾应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营卫不和型失眠疗效显著[6]。张秋明等[7]用甘麦大枣汤合此方治疗围绝经期失眠,取得明确临床疗效。陈平[8]对营卫不和型老年不寐患者予右佐匹克隆片和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进行治疗,结果显示调和营卫法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
3.2 营气不足:营弱(阴虚)
此类患者病机实质在于营气衰少而卫入失常。《灵枢·营卫生会》曰:“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现代社会进入快节奏时代,人们“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起居无节”而最终“欲竭其精,耗散其真”,导致营气衰少者不分年龄越来越多。日间卫气不能顺利出于阴分,羁留营间,导致日间容易困倦;夜间卫气不能按时入于阴分,往往夜不能寐。营气衰少,营血亏虚,不能与卫气正常交合,尤其当阴虚伴有火旺时,火性炎上,阻碍卫气与营气相合。
《灵枢·邪客》针对营气衰少提出了“补其不足”的治则。《景岳全书·不寐》将失眠分为有邪、无邪两种,无邪“总属真阴精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指出“无邪而不寐者……宜以养营、养气为主治”。由此可见,此时宜调补营血。营卫调和,卫与营交合,“阳入于阴”即可目瞑。
3.2.1 心阴虚 患者多失眠心烦,多梦易醒,心悸汗出,头晕耳鸣,咽干口燥,手足心热,大便干燥,舌红少津,少苔,脉细数。天王补心丹为临床常用方。甘寒之生地黄为君,入心能养血,入肾可滋阴。天冬、麦冬滋阴清热;酸枣仁、柏子仁取其养心安神之功;当归补血润燥,为臣药。人参补气以助生血,并能安神益智;茯苓、远志养心安神;五味子味酸,能敛心气,安心神;丹参清心活血,凉血宁神,使药力补而不滞,以上共为佐药。桔梗载药上行以俾药力上入心经,为使药。全方滋阴养血,补心安神。
3.2.2 肾阴虚 患者多见失眠健忘,心烦,耳鸣,腰酸,口干津少,男子可伴有遗精,舌红,少苔,脉细数。代表方剂黄连阿胶汤。患者多长期耗精劳神或房事伤精,易致营血不足,营血不足则不能收纳卫气,卫气不入营血,自然不寐。治疗需大补精血,另一方面清有余之心火,使得营卫平衡,水火既济。黄连阿胶汤中黄芩、黄连清火,白芍配合阿胶、鸡子黄养血益精,全方配伍可达到滋阴降火安神之功效。
3.2.3 肝阴虚 患者多见失眠心悸,虚烦不安,头目眩晕,眼睛干涩,舌红,脉弦细。酸枣仁汤为其代表方。酸枣仁有疏肝养心安神之功,《本草汇言》记载其可敛气安神,荣筋养髓。茯神甘淡平,《本草纲目》谓其可安魂魄, 养精神;知母苦甘寒,可清热泻火、滋阴润燥,既能清实热,又可退虚热,两者共为臣。肝脏体阴而用阳,肝阴不足易导致肝疏泄功能不利,故加入川芎辛香温燥,走而不守,与大量酸枣仁配伍,辛散与酸收并用,调肝血而疏肝气,补血与行血结合,具有养血调肝之妙。甘草和中缓急,调和诸药。熊微[9]对糖尿病伴失眠(阴虚内热型)患者在糖尿病基础治疗上配合酸枣仁汤加减治疗,发现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证候积分,改善睡眠质量。
3.3 痰湿
《医方论》曰:“多食浓厚则痰湿俱生。”嗜食辛辣油腻碍胃之品,影响脾胃运化,易酿湿生痰。而“酒为湿热之最”“过饮易生痰动火”,过量或长期饮酒,损伤脾胃,脾胃运化失常亦可积湿生痰。痰湿阻滞经脉,营卫运行道路受阻,使阳不入阴;痰湿日久易化热,痰热熏蒸于外,使卫气难以入营,均可导致不寐。此型患者多表现为失眠胸闷,心烦,泛恶,嗳气,头重头昏沉,口苦,舌淡红有齿痕,苔腻,脉滑。
《灵枢·邪客》提出了“通其道而祛其邪”的治则,邪去经通,阴阳得和,则失眠之证愈。“胃不和则卧不安”,饮食不节,过饱伤胃,过饥伤脾,最终导致脾胃运化失常,内酿痰湿,营卫运行道路受阻而不寐。半夏汤为最早的祛痰安神之代表方,由半夏、秫米组成,以长流水煎煮而成。半夏燥湿祛痰,秫米健运中枢,畅通阴阳交通之道路,长流水取其善行通滞之性。此汤方能祛痰化湿、调畅脾胃、疏通阴阳,有引阳入阴安神之功。
温胆汤为古今治疗痰热不寐之名方,此方源出自南北朝姚僧垣的《集验方》,由半夏二两、生姜四两、橘皮三两、竹茹二两、枳实二枚、甘草一两组成。方中半夏为君,燥湿化痰,交通阴阳,臣以竹茹、枳实清热化痰,佐以橘皮理气燥湿,生姜温阳化痰饮,甘草调和诸药为使。丁甘仁先生常以温胆汤合半夏汤治疗胃不和之夜不眠症。
3.4 瘀血
《伤寒论·辨脉法》云:“营卫不通,血凝不流”,而“久病入络”“久病必瘀”,营卫失和日久则会出现血脉不通,瘀血内生,阻滞营卫交通运行之路,使道路涩滞,阳难以入阴而致不寐。此型患者多失眠日久,躁扰不宁,夜多惊梦,夜寐不安,心悸怔仲,可伴面部色斑,唇暗或两目暗黑,胸痛、头痛日久不愈,痛如针刺而有定处,舌暗红或有瘀斑瘀点,脉弦涩。
清代吴澄认为寤时气血通畅,寐则气行无力,气血不通则不寐,开创了补气活血治疗不寐的先河。在前人的基础上,王清任进一步阐述了血瘀致病的广泛性,并在《医林改错》写到“不寐一证乃气血凝滞”,提出了不寐的病机为气血凝滞,制定活血化瘀治疗大法,并以血府逐瘀汤治疗顽固性失眠,为后人治疗不寐拓展了新的思路。
卞建峰[10]基于“久病必瘀”“百病兼痰”之说,辨治顽固性失眠从病理因素“痰瘀”着手,选用法半夏、丹参、胆星、川芎、石菖蒲、炒枣仁、龙骨、牡蛎、琥珀等药以化痰消瘀,疗效显著。邓铁涛认为血瘀既是长期失眠的结果,又是造成病情顽固不愈的重要因素,善用补气配合活血以消瘀散瘀[11]。
4 结语
古今中医学者对于不寐有着不同的辨证论治方法。《素问·宣明五气篇》提出五脏藏神理论,认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以此为依据,清代冯兆张提出“肺气虚,肺无以克肝,肺魄不能制肝魂,神魂飞扬,则不寐”。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谓:“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以上均为先辈对不寐的认识,多从五脏论治。现代学者亦对睡眠障碍病因病机进行了归纳总结,从阴阳失衡、营卫失度、五脏不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12]。有学者以脏腑及病理因素为分型要点,分别从肝、脾、肾、胆、瘀及痰等方面探讨引发失眠的理论基础[13]。还有医家认为该病或因心神失养、或因邪扰心神所致,其基本病机可分为阴阳失交与脏腑不和,辨证论治以脏腑分型为核心[14]。
纵观前人运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各种辨证方法辨治不寐,变换自如,但个别证型间不免重复。比如脏腑辨证从肝脾论治,肝气不畅则气机郁滞,肝郁克脾,脾运化水谷、水湿的功能失常,湿滞水停,痰湿内生,或湿郁化热,日久成瘀,湿热瘀同样能导致不寐,此时从脏腑辨证和从痰瘀论治不免有所交叉重复,所以选择切入点十分关键。
本文把不寐的病因病机归纳为两类,其一营卫偏盛偏衰,卫强或营弱,使营卫交会失和而不寐;其二营卫运行通路不畅,痰湿、瘀血等病理产物的产生阻滞营卫运行道路,使营卫交会失和,阳不入阴而不寐。此种辨证思路简单明了而形象,可供临床医生参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