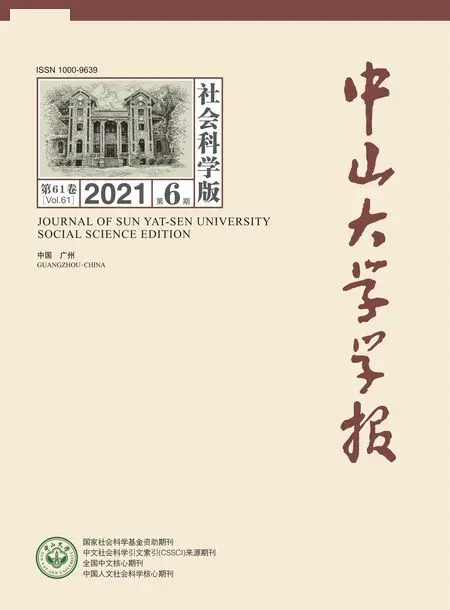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2021-01-04唐定坤
唐定坤
诗和赋是唐前文学的大宗,二体关系复杂而又交互影响,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页。的理论建构到“汉世为赋者多无诗”②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2页。的创作实情,下至魏晋的诗赋辨体,延续为赋的诗化及文体趋同,无不昭示了这一命题演进的繁复多变。今代学者或注重从文学史的进程研究二体的影响交融,或注重就时段性、代表作家来分体辨异。实际上二体的密切关系及分异趋同,在赋体发轫时就已兆其端。按刘勰折衷前人之说,虽称“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但在上承班固以来广为前人所认定的赋自《诗》出的文体源流时,又以“风归丽则,辞剪美稗”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4、136页。的论《诗》法则对之展开批评,遂使诗赋的源流叙事遮蔽了二者的立体分异,影响了后之论者的观察。如称荀赋为四言诗体赋而源出于《诗》,延及界定赋“亦诗亦文”而为“诗的别支”,便未注意到赋之初起实乃“变《诗》”而与之相疏离。揆其实情,荀赋的历史语境不仅反映了赋与《诗》的复杂关系,也在文本层面昭示了赋与诗的本质区别,并为赋体诗化提供了可能。文体的演变往往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内在局限、发展倾向等重要命题,这正是本文从赋的源起着手讨论二体分异趋同的根本原因。
一、赋自《诗》出的历史实情
从现存作品的文本形态来看,汉赋的起源约有三途:散体骋辞大赋承宋玉赋而敷衍为“京殿苑猎”类的宏大题材,以指呈“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136,134页。的大汉主题,是为赋国主流;骚体赋源自屈骚,承担了文人发摅情志的功能;四言咏物赋承自荀子,却因体例的“演而未畅”②姚华:《弗堂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30年,第29页。而最为后代轻视。马积高《赋史》分为文赋、骚体赋、诗体赋三类即本于此③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页。,而多为当代论者援用。本来三途并进而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东汉班固称“赋者古诗之流也”将赋的生成纳入了《诗》的流变,其主要策略则是通过“称《诗》谕志”的传统而强调屈赋和荀赋“恻隐古诗之义”④班固:《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56页。,伏下了赋自《诗》六义出之说,用以《诗》衡赋的功用性批评建构起大赋的经学源流体系,遂将多维化的分类演进转化为一维化的文体源流。此说呼应了西汉司马迁、扬雄以《诗》学讽谏来评价赋体的得失,具有经学时代的普遍性;至晋以下左思、皇甫谧、挚虞等皆承其说,而最终在刘勰“赋自《诗》出,分岐异派”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136,134页。的强调中形成明晰的源流定论,迄清末经学未解散之前一直未有质的改变。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普遍的文学写作来讲,任何人的文体书写都可看作一己情志的表达,班固标举屈、荀“恻隐古诗之义”的理由显然较为牵强,实不能作为赋源自《诗》的主要证据。从赋源的三途来看,散体大赋和骚体赋在本质上皆和楚骚是近亲而无关乎《诗》,只有四言咏物的荀赋才具有和《诗》纠葛不清的关系,所以赋自《诗》出的真相关键在于荀赋对《诗》的汲取实情,由此才能进窥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
现存荀赋主要是《赋篇》的咏物五章,篇末附有《佹诗》,与另一篇具文学意味的歌谣辞《成相》收在一卷。《汉书·艺文志》列荀赋二十五家,章太炎释为“孙聊效物”⑥章太炎:《国故论衡》,第90页。,刘师培释为“阐理之赋”⑦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效物”铺陈以“阐理”可以看作荀赋的基本特征。按刘勰谓荀、宋赋的“爰锡名号”,《赋篇》属首立赋体而初具规模之作;尽管荀宋赋作的先后已不可考,但相较于宋赋开散体的成熟文本形态,荀在宋前之说合乎文学演进的逻辑,他这组作品确实也呈现了早期《诗》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称名和传播两个方面来展开考察。先看前者,五章分赋礼、智、云、蚕、箴五物,为何最早是这组咏物的作品冠之为赋?尽管不乏论者认为这可能并非荀子本人题名,但即便是稍后的文人总撮五章而称《赋篇》,也存在着对这些作品体性的确认。从表面看,李善注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⑧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1页。承自刘勰“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即赋的称名从《诗》六义而来。而《毛诗序》中的六义显然有汉人建构的影子,仍需上推至《周礼》称大师教“六诗”⑨郑玄:《周礼郑注》,《十三经古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3页。之赋这一源头,考虑到周代用诗皆指向《诗》,庶几勉强可以称为赋体出自于《诗》六义的手法之“赋”。若从客观史料来考察则另有隐情。按赋义最初用为赋税赋敛,段玉裁发现上古“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传》曰:“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⑪孔安国:《尚书孔传》,《十三经古注》第1册,第93页。下引此书,不另出注。可知早期赋税内容皆为有价值的有形实物,这就推出了赋的“赋物义”⑫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7页。。赋敛赋物之义下转到《诗》中六义再到赋体,赋字与“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⑬王念孙:《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1页。是一以承之的,这样一来,赋体的“铺彩摛文,体物写志”⑭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136,134页。义承自《诗》六义之手法“铺陈”的近亲意味就弱化了,而毋宁说是与赋布、赋物一脉相承。返观荀子《赋篇》恰好又是分赋云、蚕等五物,且以铺陈直言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这就勾连起了一条以“赋物”为核心的文学演进理路,下至宋玉《风赋》取“物色”题材仍之。可见,说赋体源自《诗》六义殊为皮相,赋之“布、敷、铺”义所依附的赋物传统与之并无关系;这同时也合理解释了结尾抒情的《佹诗》部分并不列于五章之前为《赋篇》称名代表,歌谣辞《成相》在当时不归为赋的编集原因。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荀子造作《赋篇》(含《佹诗》)大致契合于《诗》赋在“行人之官”①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44页。的手中同源而分离的进程。春秋外交“赋《诗》言志”是用《诗》的主要方式,“赋”为动词,郑玄谓“或造篇,或诵古”②毛亨等:《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08页。,“诵古”为赋《诗》中成篇无疑。而《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③班固:《汉书》30,第1755页。章太炎释“登高”为“讲坛之上,揖让之时”,赋为“微言相感,歌诗必类”④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7,页。,指明行人之官在“诵古”的进程中发展出了即兴赋诵而类于《诗》的进谏文本,刘勰所称“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已经把这一过程清晰地描述了出来。行人之官的身份和职能决定了即兴的辞令必须要承担“微言相感”的交际目的,所以“感物”的赋辞必然要承担“写志”功能的赋义;交际的现场微妙性不仅决定了文辞不可能恣意展开,还决定了辞令“体物”之“显”和文义“微言”之“隐”。而荀子《佹诗》分别又被收入《战国策·楚策四》和《韩诗外传》卷4中,皆十四句,系“为书谢曰”之辞,称“因为赋曰”⑥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93页。,通合于行人之官注重以文章辞令来达到“微言相感”的大义这一临场赋诵的劝谏活动;又称赋为诗,则当为“诗与赋未离”⑦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7,页。的原始状态,只是即兴赋诵演变成了退而“造篇”的书信,便包涵了认真构思的可能。以此推之于五章咏物的明确称“赋”,不仅在于“赋物”本义的题材取用,其中君臣问答重赋物之“显”和赋义之“隐”、文辞考究而大似“谐隐”敷陈之“谜”,皆已不是游士说君的临场客观实录,而是深思精构的文本创作。所以据此行人之官的传播者身份以及“不歌而诵”的传播方式来看,赋的确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
然而这种功用层面的同源并不能证明文体的近亲关系,文体的特征主要取决于文本的构成形态。按荀子本是《诗》的重要传授者,关键在于《赋篇》“四言的分子也很多,常常有模拟的痕迹”⑧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此即学界所称荀赋是“变《诗》”而来。“模拟”《诗》之痕迹者,除了句式字数多相同外,部分遣辞亦有迹可寻。如《礼》中“爰有大物”,近于《诗·凯风》的“爰有寒泉”⑨毛亨等:《毛诗注疏》,第185页。下引《诗》作品皆出自该书,不再另注。;《云》中的“卬卬”,源自《诗·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又《蚕》的义理,杨倞注与《诗·瞻卬》的“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有关⑩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然并非全取自《诗》,《知》中“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源于《尚书·汤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可见遣辞并不排斥其他典籍。既用《诗》之四言,则牵涉到用韵,表现于《赋篇》各章的四言主体。只是如果进推先秦文本的实际情况,则上述四言体式、遣辞、用韵三者所指呈的关系,仍未必能确证赋自《诗》出。首先,四言为主并非《诗》所独有,比如《老子》就是以四言为主的语录体;其次,取辞在创作学上从属于“依经立义”的传统,任何后起文章的造作无不广援前代典籍;再次,诸子行文,若有四字句接连出现,便多用韵,这在《老子》及纵横家说辞的铺陈句式中俱不难见到。此外,从作者层面来看,诸子主要作文,鲜有作近于《诗》体的“歌”,如果仅凭四言体式的部分相同认定后者“模拟”了历经数百年而成熟的《诗》体,显然缺乏说服力。
二、从诗句到散句的体制分异
值得注意的是,《云》中的“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门”,让人想起《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3页。下引该书皆据此本,不再注。的“门”,以及第五十九章的“莫知其极,可以有国”,其间不惟有语辞取义的脱化痕迹,句式构造也是一脉相承的。后者可以启发我们从句式形态的组构角度去考察。按《赋篇》五章皆由谜面的描写和谜底的设辞议论两部分构成,前者以四言为主,后者变为杂言。兹以《云》为例: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钜,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参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㕁穴而不偪者与?行远疾速,而不可托讯者与?往来惛惫,而不可为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亿忌者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4—316,315,213页。下文所引《赋篇》内容皆出自该书,不再注。
本篇句式形态丰富,大致由形容词前置兮字句、二元合成句、语气词结尾的排比句、虚字连接的陈述句四种特殊句式和一般四字句所组成。形容词前置兮字句即第一段连续出现的“忽兮”“攭兮”“卬卬兮”三句。“忽”为迅速貌;“攭”,杨倞注“分判貌”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4—316,315,213页。下文所引《赋篇》内容皆出自该书,不再注。;“卬卬”,杨倞注“高貌”。“兮”字前的形容词或为一字,或为重叠两字。上溯这种句式,《老子》十五章便曾接连出现“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等七句,又二十章有两字重叠形容的“傫傫兮若无所归”。这是《诗》中所没有的。二元合成句由两个具有二元关系的句子共表一意组成,如“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钜”“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这在强调“反者道之冲”的《老子》中更为常见,如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七十七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但《易》中也不少,《诗》中则偶见。语气词结尾的排比句主要在谜底的设辞部分,文中连用了六个以语气词“与”结尾的疑问句。而《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为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以六个疑问语气词“乎”结尾的句式构成排比。尽管《云》用的语气词不同,但《礼》《蚕》用“与”、《箴》《知》用“邪”、《知》《云》包含《佹诗》还有以虚词“也”结尾的陈述排比句,最少指明了一条语气词结尾排比句的发展途径;荀子的三度变换为用,或许只是规避雷同,其源仍无关乎《诗》。虚字连接的陈述句,指向于以虚字充当散语结构中连接功能的句式。如“而”,《云》有“而大盈乎大寓”“德厚而不捐”“五彩备而成文”,《老子》则有“而人居其一焉”“繟然而善谋”“万物归焉而不为主”等。又“以”虽多用为介词,弱化则转为表连接功能的虚字,亦可资比较。《云》有“动则綦高以钜”,推及《智》有“以示下民”,《礼》有“生者以寿,死者以葬”,《老子》则有“或下以取”“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报德以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等。准之于它们所处字位和语法结构功能的对应比较,不难推出两者的句式性质如一。只是《赋篇》形式相对整饰化,或许是“不歌而诵”的表达要求所致。这二字在《诗》中当然也有所运用,但后者的虚字主要用为语辞而凑足四言,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就用为连接功能而言,出现的频率和比例要都低得多。
总结这四种特殊句式,皆与《老子》相关而去《诗》较远。《荀子·天论》称“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④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4—316,315,213页。下文所引《赋篇》内容皆出自该书,不再注。,又《荀子·解蔽》“虚一而静”之说便源自老子“致虚极,守静笃”和“涤除玄览”的虚静说,而其弟子韩非有《解老》《喻老》二篇,亦见师门对《老子》的重视,俱可证明荀赋句式构造取法《老子》的可能。有学者注意到荀赋句式来源不仅远绍《老子》,还分别见于《文子》、《管子》和《庄子》⑤李炳海:《荀子赋文本生成的多源性考论》,《诸子学刊》2017年第1期。。即是说,荀赋句式构造的取源不是《诗》句,而是从类于《老子》的散语句式系列发展而来的。散句的表达受日常生活叙事的时间线性逻辑支配,有着次第表述而从容不迫的意味,多以虚字连接散语,本质属文,当以文法论,这就同《诗》句拉开了距离。
只要对二者稍加比较申论,就能见出质的区别。《诗》最初亦由散句发展而来,其用四言或为合乐的需要,但正以四字一句的形式限定发展成为“雅润为本”的“正体”。刘勰称“四字密而不促”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7、571页。,陆时雍则谓“四言优而婉”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2页。,正可见出其构造的特点。现代西方语法学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任何完足的表意必须具备主谓宾三个句法主干成分,如果四字足一意,则几乎每一个字都具有指实的功能,此即其“密”处,如“将子无怒”。但《诗》因合乐咏歌的需要,必然要追求重章复沓、悠扬舒缓的抒情功效,四字成句不契于此,于是就形成了两句足一意的表达,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此即其“不促”处;其本质是由语辞虚字和叠字按照“足四原则”③何丹:《〈诗经〉四言体起源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23页。补足每句四言而构成的,正是这些虚字叠字,冲淡了“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④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页。的表达,获得“优而婉”的审美效果。要之,表意四字一句足矣,抒情却赖两句足意:于是《诗》中两类句式并存,二者张弛之际则诗意弥增;而以抒情“言志”为主的风诗则多两句足意的诗行,甚至以之为分章结构的标志。又从诵读的音律节奏讲,“发一字未足舒怀,至于二音,殆成句矣”⑤成伯玙:《毛诗指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单字无以成为节奏,必待二字组合,推之于《诗》四言则由2+2节奏组成。但一句足意的表达受句式空间的限定,必多用单字而不切合于口诵顿逗;反之,两句足意的抒情句式在按拍吟咏的过程中,极易走向追求双音节叠韵联绵词的出现和运用,以使其意义节奏符合按拍诵读的音律节奏,诗意的韵律和意味就此产生,有学者认为这正是使“四言脱离散文形态的基本要素”⑥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5页。,以此才促成了《诗》体之诗化。凡此可见《诗》句的独特形态,只要与荀赋造句稍加对比即可见出二者分野。如《云》中“有物于此”,其组构系虚字连接散语,其目的是为了引发“物”的铺陈——故不必如《诗》的两句足意,也不必考虑其表意符合诵读的顿逗与否,只以文法为据,从“居则周静致下”下至“莫知其门”这十六句,一顺而下,铺排云的状态、变化等,遂以此而构成了疏离《诗》四言的赋体。
赋以铺陈为要,自手法言乃“敷陈其事而直言之”⑦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页。,铺陈径取“直言”,直言当属散句,所以骋辞大赋也称“散体大赋”,这使得直言赋句一方面排斥“雅言”《诗》体的含蓄句式,另一方面亦不必受限于句式的多少和短长。从前者看,行人之官从即兴“赋《诗》言志”中分化出来的进谏文本,“不歌而诵”而欲以达到现场效果的旨趣容易引发一定的辞章整饬化追求,这是赋体初起即以古老的四言为主的重要原因,或许与流行的《诗》四言有一定关系;但直言既以表意为主,若取诗意蕴涵的《诗》语句式则有悖铺陈之效,所谓委婉劝谏也是就整体性而言的,细节势必不克雕饰。所以“变《诗》”是表象,毋宁说是疏离《诗》体句式,而取《老子》以下的散化四言。从后者看,铺陈并不受限于句式的多少,而只求目的的达成,这就造成了多句表达一个方面的内容,可谓多句一意;微观而言亦可谓一句承担一个细节内容,即是一句一意,悉皆拒绝前论《诗》句的诗意凝结表达。同时,铺陈直言的为文旨趣必然接纳杂言,所以荀赋虽多四言却杂有三言六言,这既是对四言的间破,亦何尝不可看作是赋体对《诗》体四言的疏离和分异。及至汉代散体大赋成为主流,更不纯以四言为主,即便在咏物小赋中,完全取用四言的情况亦为罕见。下至诗的兴起而形成诗赋二体的分异,其理仍同。按汉代乐府大兴,藉《古诗十九首》终演化为文人五言诗,下至七言诗的兴起,仍类同于《诗》体四言散句演化为诗意句的进程,盖以乐府叙事而仍取散句,定型为五言诗以后,直言散句成分亦不少,只是连并七言都在2+3(含2+2+1)或2+2+3(含2+2+2+1)的节奏轨范中走上了诗法化的道路。不仅形式的限定使得节拍同构起如联绵叠韵般的两字音组,其中单字一方面间破了二二诵读节奏,另一方面也成为锻炼用字和调整语序的关键,承担起了诗化的主要功能,使得五七言离散句越来越远,而最终判然分途为内涵句法功能和审美意味的“诗句”。显然,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已大不同于骚体用兮字的五七言句,更不适于铺陈直言,即所谓“五言七言,最坏赋体”①孙福轩辑:《历代赋论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三、从手法到特征的升格拓展
班固纳赋入《诗》的经学源流建构,不仅影响了赋的创作和批评纠结于《诗》“讽谏”的经学功用,还影响到了后代将《诗》之手法纳入赋学批评系统。如浦铣便称“赋中最多比体”②何新文:《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7页。,沈德潜称“(赋)导源于《三百篇》而广其声貌,合比兴而出之”③潘务正点校:《沈德潜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007页。,意味着赋之比兴承《诗》而如一。以此进推荀赋手法的“承《诗》”“效物”,却显扞格难通。实际上《诗》之三体三用历来在经学话语中都被予以了通合性的阐释,二者互为依赖。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④胡寅:《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6页。则三用都指向于《诗》吟咏情性的表达功能,其中暗涵了体用相关的学理逻辑。《诗》中之赋虽具有施之于一章的整体性,却要求契合于整首抒情的需要,即皎然《诗式》称“象事布文,以写情也”⑤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5页。。而毛公“独标兴体”⑥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01页。固当意识到兴的优越性,其抒情仍赖两句足意,意味着是以咏物兴发情事的两两表达模式,即朱熹称“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⑦朱熹:《诗集传》,第2页。;这里的物和情具有二元连类关系,存在着一个叙物和写情(事)的线性表达结构。比虽取类较为灵活,却仍和兴一样只有“随意性、暂时性、片断性”的功用。所以“《诗》的体制决定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⑧易闻晓:《中国诗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0、369页。,三用的表达也具有符合《诗》四言抒情的对应机制。
六义之赋“变成”赋体,赋体仍用赋法,三“赋”间的关联分异尤需辨析。六义之赋是以铺陈整体的一章节来抒情,赋体初起则以敷陈和赋物为中心,换言之赋体的核心在于铺陈的手法和赋物的题材,题材是最容易在文章造作中转换的,故有论者提出铺陈才是“立赋之体”⑨林纾:《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合订本,第49—50页。的关键,并由此形成赋最主要的体制特征,而不同于诗的形式立体。于是从六义之赋到赋体的赋法就形成了“手法上升为原则,原则开新出方法”的发展理路。即是说,当此前的表现手法升格为立体的原则时,文章的造作就会围绕此原则反过来发展出多样的铺陈方法,包含吸纳诸多表现手法及至文体要素以转换为铺陈之用,和对新方法的探索开新;正是这种内在的原则要求而不是外在的形式限定,给予了赋体强大的文体容纳空间和改造能力,终使其“蔚成大国”。先看以铺陈立体对《诗》用手法的吸纳,这稍有不同于赋体散句对《诗》体句式的疏离,其重心在于对诸手法进行积极的转换和改造,惟此才堪完成多角度铺陈题旨的任务。改造必有异于本来面目,徐师曾比较二者:“(荀子)所作五赋,工巧深刻,纯用隐语,若今人之揣谜,于诗六义,不啻天壤。”⑩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合订本,1962年,第101页。可谓卓识。首先《诗》主情而荀赋“阐理”表彰儒家经义,在文体功能上就别于泾渭,自然会影响到用的转换。“纯用隐语”指明与三用表达相异的原因,五赋的谜面是赋物的隐语,全为铺陈,其实谜底也可看作变换句式的铺陈,相对于《诗》中之赋的整体章节抒情,这里的表达完全不受章节形式的限制,通篇可用;比的情况则较为复杂,《云》《蚕》《箴》三篇藉咏物以言志,可以看作“通篇以赋为比”,但《礼》《智》二篇是直陈儒家经义,其中就有“片断性”的比,惟此略同于《诗》,这与比“取类不常”的特点有关;至于兴,则五篇皆不用,这是因为以物兴情不适于“阐理之作”。此外,五赋的谜面为铺陈赋法,亦可看作比法,谜底的交待则有“言志”的意味,在章法上就构成了“托物见意”①钱澄之:《田间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这倒是颇类同于先秦诸子叙事的托事言志方式,符合于诸子“以立意为宗”而虚饰本事的“文学发生学”②唐定坤:《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如果将之看作对此的承续,其文体源流的逻辑反而更加通融合理,不消说与三用手法更是“不啻霄壤”。即便看成对《诗》体三用的发展,亦必契合于赋以铺陈为原则所体现的强大吸纳改造力。当赋“蔚成大国”之后,大赋及骚体赋甚至将这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手法的升格拓展至为广博,与《诗》之三用所去更远。
再看《赋篇》在铺陈原则下的方法开新,可以从句式、用字、章法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考察,尤能见出荀赋立体初具规模“演而未畅”、而仍别于《诗》的文体特征。句式仍是重点,结合上节分析可概括为直陈一顺句、二元合成句、排比句、形容词前置兮字句四类,俱以铺陈体物为原则和宗旨。荀赋首先采用“爰有大物”“皇天隆物”“有物于此”的直陈式开头,表明通篇咏一物的主旨,开出一顺而下且内涵不同角度的“效物”铺陈,可称直陈一顺铺陈句。如《蚕》首起“有物于此”,下至四言结束的“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连用十六句分别围绕“此物”的形状、习性、生长过程等来加以陈说,表明开篇直陈所预设的空间具有无限展开的可能。只要对比《诗·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即可见出类似的开头在兴的两两规限中呈现出的明显分异。二元合成句和排比句已见前章所引。前者运用颇多,五篇计十余处,如《知》“桀纣以乱,汤武以贤”,《蚕》“下覆百姓,上饰帝王”。这虽不为荀赋独有,但《赋篇》的多次为用,显然意识到了骈偶二元具有合为整体一元的空间铺陈功效;只是两句即止,尚受制于“微言”语境规限而未及详细拓展,要下至汉赋变为以空间词作引,并在该维度内广加敷陈,才能见出空间的博阔和气势的恢弘。排比句用作铺陈也显系有意而为。前论“邪”“与”“也”三种语气词结尾的句式构成排比,五章使用如下:“邪”结尾,《知》连用五句、《箴》连用三句;“与”结尾,《礼》连用五句、《云》连用六句、《蚕》连用四句;“也”结尾,《知》连用五句、《云》连用三句。这种句式不受制于字数的多少,甚至有两句合表一意的杂言,但最少都是以三组比列而用,三复为言,间不容发,颇能达到排比铺陈以增气势的表达功效。如此密集地出现,是此前诸子文本中从未有过的,当然更不可能在受篇章形式限定的《诗》中接连出现,可视为成熟的典范。形容词前置兮字句用于铺陈,更见荀子首制赋的开新。按赋物必须见其形貌性质,方能查见本然;前置形容字强调物状,正赖“兮”的语气一顿,使读者形成先得物貌的强烈形容效果。如《蚕》“㒩㒩兮其状”,“㒩㒩”前置强调蚕的形貌,杨倞注“无毛羽之貌”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6页。;“兮”字后接“其状”,指明状物。又前引《云》的“忽兮”三句,不仅前置形容字,同时连用三句虚字“也”结尾构成了双重铺陈,俱见良苦用心。此外,并不咏物的《佹诗》也有“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功效如一,稍不同的是所状乃是情貌。这类仅以形容词和兮字为标志的散句大异于《诗》句,确然有着较强的铺陈功效,故而广为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赋家所承续发展。如宋玉《高唐赋》:“其始出也,㬣兮若松榯;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旗。”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65页。在“兮”字后复以形容,连成双重形容的铺陈,而接连使用,屡变句式,令人目不暇接,最见状物之效,已越荀赋草创的单一形容。
用字铺陈表现于物貌的描写形容而多取叠字和联绵字①易闻晓:《辞赋联绵字语用考述》,《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荀赋首开赋中“描写铺陈”,用叠字计六处,《礼》有“涽涽淑淑,皇皇穆穆”,“涽涽”,昏昧貌,杨倞注为“思虑昏乱也”;“淑淑”即踧踧,局促貌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4页。。此外《云》有“卬卬”,《蚕》有“㒩㒩”,如上节所引俱在形容。联绵字计有两处,《知》有“周流”,回环貌;《箴》有“赵缭”,杨倞注当为“掉缭”,即“长貌”。叠字联绵的描写在《诗》中亦偶见,如《诗·崧高》:“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朱熹传:“赋也……藐藐,深貌。蹻蹻,壮貌。濯濯,光明貌。”③朱熹:《诗集传》,第283页。《诗》中形容的用字受制于四言两句足意的表达,故叠字在一句中需和另外的表意实字组合;藉此对比荀赋“涽涽淑淑,皇皇穆穆”的两句连叠,已有其他句式分担表意功能,故能专事描写形容以为铺陈,拓展了铺陈的空间。只是荀赋的联绵叠字所用仍少,稍乏气势,要待汉代大赋的兴起,如枚乘《七发》:“纯驰皓蜺,前后络绎。顒顒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483页。变为了数句形容一顺而下的表达,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才堪获得淋漓尽致的铺陈功效。最后,简单讨论一下章法结构。五章咏物皆有意引猜谜的形式敷衍成篇,而设客(臣、弟子)问主(君、五泰、王)答,略有纵横家劝人主的形迹,系为“文”的逻辑架构,已然预设了一定的铺陈空间,较《诗·溱洧》的截取主客问答片断式抒情,显然具有了容纳诸方描写的可能。只是与其句式、用字的情况相近,悉有初具规模“演而未畅”的体貌特征,要待宋玉吸收楚辞演为明晰的散体大赋文章构架,才堪发展出宏博恣肆的铺陈体格。
四、从题材到功能的文体位移
赋虽以铺陈为确立文体的原则,但受其本义影响,铺陈的手法和赋物的题材实有合二为一、互为依赖的倾向,即是说,赋的铺陈手法已导引了相应的题材范围,正如《诗》中体用通合的表达机制。从班固的“感物造耑”,到六朝人称“物以赋显”“赋体物而浏亮”“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皆昭示了二者的统合关系,而以清人俞玚“赋家俱以体物为铺张”⑤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江苏: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367,175页。所称最切,即赋之铺张(铺陈)必施于物,赋之体物必赖于铺张。何以如此?《说文解字》:“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53页。王国维以为“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⑦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页。。指明物的代指始于大而复杂的具体实物,惟此才堪为赋。其后才推为抽象之物,亦即以物成事,故称物事、事物;随着主体性的介入析出深层的情理,或以物事相对有形可依,情理抽象难解,故论家每以对举。所以返观赋体的“赋物”传统,必以赋敛“实物”这一本义为先,荀赋的《云》《蚕》《箴》三章准此;《礼》《智》二章,虽以抽象之“理”为书写对象,但“爰有大物”“皇天隆物”的开篇表名乃是用“物事互指”的意涵。物既析言为四,则为赋的铺张效果有高下之别:由物及事皆具形象(实以赋实物为中心),可以“图貌”求工而“蔚似雕画”,故愈加铺陈而愈见汪秽博富;情与理之抽象,当以真挚和深思为上,虽可用为题材,而反复铺陈必易流于失真和枯燥。所以《礼》《智》二章的抽象说理不如另外三章实物铺写为佳,庶几“以议论为便,于是乖体物之本”⑧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江苏: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367,175页。,只以拟之于有形之物的描写而可堪为赋。
宋玉散体大赋的取材仍承此义。其《九辨》承自《离骚》,开篇以燕、蝉、雁、鹍鸡等名物接连铺陈渲染悲秋,已有变为赋物的迹象。至其《风赋》入《文选》“物色”类目,固属正格;而萧统编《高唐赋》《神女赋》等入“情”类,实本于“事”类,前者重在铺写高唐“朝云”之“大体”,后者重在铺写神女,皆可看作以骋辞赋物为中心。但由于缺乏实证,宋赋似尚不能全看作是对荀赋的承续扩张,而更可能是时代转向的文体造作——其中根本原因就是以隐体助推为赋,可与荀赋立体互参。按“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正是荀宋为赋进谏君上的相同背景。从主体的政治劝谏意图来看,隐则导向“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故而“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①刘勰著,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71页。;但从游戏功能来看,只有以物设譬的谐隐才堪娱乐的最大化,也易于为文的纵横逞辞,这正是隐体为赋而“以体物为铺张”的关键。荀子宗儒重礼,故不欲华辞;宋玉本好文辞而取法楚骚,据“王以为小臣”②习凿齿著,黄惠贤校:《校补襄阳耆旧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页。的身份可推其人戏嫚,符合“宋玉含才,颇亦负俗”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4页。的评价,以此宋赋才逞辞铺张大力发展隐体赋物的一面,其体广博的空间预设远大于荀赋的初具规模,有似于纵横家之恢张谲宇,而超越了隐体的回互其辞,故能成为一代汉大赋的开创者。所以汉代虽有抒情骚体赋和四言咏物小赋,皆地位不显,终不敌“京殿苑猎”类大赋的队伍庞大,其理即在于此。可以说,宋赋立体并下张赋域的关键,正在于隐体游戏娱乐成分的张扬和政治劝谏成分的弱化,这既对“演而未畅”的荀赋遥相呼应,同时昭示了赋体之长在于铺陈原则与物事题材的遇合发挥。
但荀赋立体所呈现的文本形态及所内涵的文学意蕴,同时也伏下了诗化的可能,其中隐含了消解铺陈手法和赋物题材的因素,终使赋体在后代不断的批评中,从以手法规限题材的立体转向注重功能的单一强调,形成了诗化的文体位移。从结构上看,《赋篇》的二元组构在新文体的内在趋动下涵有彼此消解的相悖性。本来五章的谜面描写与谜底说理,乃是基于隐体藉物劝谏以发挥政治功用的二元谋篇形构,在文体上却成为了后世“作赋以讽”赋体章法的滥觞。关键是荀赋劝谏意图严肃明显,庶几可看作政治应用文体,使得赋体初起就和《诗》一样具有政治功用品格;宋玉开散体大赋尽管大力发挥了赋物骋辞的一面,却仍未完全放弃这一点,赋终究没有发展成纯然的逞辞游戏之体。显然,赋体铺陈的辞章追求会“没其风谕之义”④班固:《汉书》卷30,第1756页。,从而引发讽谏失效的批评;反之,政治讽谏的功用要求会制衡赋向铺陈蹈厉一端的极度发展。这种赋体内部彼此对立、制约、消解的先天矛盾,正是其自身在后代广遭《诗》学功用性批评、产生诗化位移的本质原因。从表达上看,“托物见意”、赋物出理的二元表达隐含着凭藉外物来书写内心情志的同构机制,使得“物—理(志)”的结构书写极易演变为“物—情”的同构书写。这时作者赋物的运思就会从“分敷物理”的客观赋物发展成为“触兴致情”的主观体物,赋物题材这一重心就会在抒情传统中转向表面“体物”实则主“情”的功能性强调,庶几同于诗。从篇幅上看,荀赋五章都可当作独立的一篇赋,其容纳“作赋以讽”诸要素的短小篇幅为后世树立了“言省”“义正”而文质相称的赋体典范,伏下了消解赋体长篇巨制而导向诗化的可能。一旦铺陈蹈厉的赋物辞章追求引发讽谏失效的功用性苛评,必然会反向轨范篇幅导向内部二元的新平衡,后世扬雄“丽淫”“丽则”、刘勰“风归丽则,辞剪美稗”的批评即本于此,而以挚虞称“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⑤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9页。,最堪代表。站在《诗》学的立场,挚虞明确彰荀抑宋,“演而未畅”的荀赋竟然是“言省”而“义正”的赋体典范;这种批评当然会压缩“苞括宇宙,总揽古今”的赋物空间,对铺陈手法的运用形成制约和消解,从策略上讲就是刊删赋物之辞而张扬情义之本,导向篇幅的减损和抒情性的凸显。可以说,荀赋政治劝谏所流衍的功用性批评贯穿始终,不管是对《诗》学之“则”和“情义”的强调,还是对“物—情”结构中“情”的强调;而对于以铺陈原则赋物的客观事实,却多不为论家抉发表彰,这就形成了题材手法立体和功能批评的错位,当过度强调赋的表达功能时,也就预示着赋体将走向诗化和“消亡”。
这需要参之于赋的诗化史,大致反映为四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是骚体赋的形成拓展了赋可抒情的文体功能,使得抒情可以作为题材和功能兼而入赋。尽管从题材类型讲,它不敌赋物的散体大赋,但从表达功能上讲,则与之构成了文人言志的公私二域①赵敏俐:《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这就为赋的诗化准备了条件。第二阶段则经由《诗》学功用批评发展出了藉物抒情的小赋。汉大赋的兴起以逞辞铺张为要,在立体和功用间形成了“劝百讽一”的尴尬,于是不断遭到以《诗》之讽谏功能为原则的批判,扬雄之说可为代表;下迄三国,赋作的篇幅大为缩减,抒情小赋兴起,这固然与时序代变有关,但仍不应忽略赋在经学功能批评下的内在演进理路。从赋物题材的传统来看,两汉小赋或取荀子状物说理,或取状物比德,鲜有藉赋物以抒情者,与骚体赋之用于抒情不相杂越。汉魏之际的赋,则在篇幅减少的同时开始着意于抒情的功能表达,出现了大量藉物抒情、即事抒情甚至以情为题的小赋,如祢衡《鹦鹉赋》、曹丕《感物赋》、王粲《登楼赋》、曹植《愁思赋》等等。这些赋一面在结构上有欲达成“丽”“则”相兼的体势,另面在赋物的弱化和抒情的强调中开启了诗化之旅。第三阶段最为重要,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强调赋物题材到抒情功能的转变,文本的书写则因主体情绪的渗入而开出了物情一体的诗境。陆机明确提出“赋体物而浏亮”标举赋“体物”的体格,已明显不同于此前班固“感物造耑”的客观感察物貌,“体”字内涵了从玄学体物理到诗学体物情的逻辑进路,“浏亮”则内涵了玄学对铺陈“淫词”的消解和洗礼;这一从“论文辞”转向“论文心”②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的导向,使得他将许多“物”“事”题材体写成了“缘情”之赋,所以有论者认为其诗“缘情”和赋“体物”是互文③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而陆云《与兄平原书》竟然处处径以“情”本功能来论赋;其《岁暮赋》序称“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④严可均辑:《全晋文》,第1056页。,将最后一句改成“作诗以言情”,亦何尝不可,他强调的重心是主体“感”物之“改”和作文以言之“情”,“物”为机缘而“情”为旨趣,赋体对“万物”的题材规限意识和“铺张”原则悄然隐退,这就走上物情合一的诗境化道路了。及至刘勰总结咏物小赋: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页。
旗帜鲜明地指出赋“触兴致情”的创作实情,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置之于论诗何异!表面上是要在题材之“物”和主体之“情”两者间建立起新的平衡,另面也意味着极力突显赋体应具“抒情”之功能。第四阶段则表现于梁代以下二体的诗化趋同。此段赋篇多涵诗境,极为注重炼字炼句,篇幅短小,与诗仅有句式的差别。甚至沈约、萧氏父子、庾信等人,根据赋体的吸纳能力大量实验五七言诗句入赋,流风所至,不仅出现了如萧纲《采莲赋》、萧绎《荡妇秋思赋》、庾信和萧悫《春赋》等“诗体赋”,也出现了沈约八咏、谢庄《山夜忧吟》、任昉《静思堂秋竹》等名不题赋实则亦诗亦赋的作品。至此,赋家的兴趣全在于即物抒情的诗境体察和声律形式的技法探索,或许文学的创新是他们痴迷于新体探求的动力,但终究在以《诗》学讽谏和诗歌抒情为本位的功能性批评中,促使一代汉赋在发生了文体的位移后行将“消亡”,并遥远地回应了荀赋立体所孕育的种种内在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