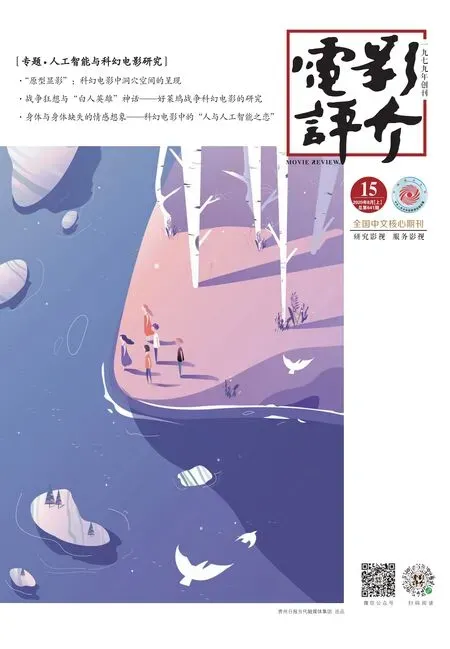《我不是药神》:从新闻到银幕的现实主义抒写
2020-12-30李俊
李 俊
2018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裹挟着现实主义高频新闻的共振强势上映,在同档期影片中一骑绝尘,斩获30亿元票房。影片题材来源于真实的深度新闻报道,以“昂贵的癌症药”“药品倒卖”“走私”“冲击医疗体制”等高聚焦词汇,强烈冲击观众的视觉神经,成为现实主义影视题材的最新经典。
该片的巨大成功,主要归功于电影题材在新闻社会效应周期内的实时表达,在人们对渐行渐远的新闻淡出之际,续以惊爆的影视语言拉回了观众对现实的切身关注。《我不是药神》对新闻题材的强势重刷,再次证明现实主义影片的强大生命力。
一、紧扣社会痛点的题材选择
故事的原型陆勇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因购买高价抗癌药“格列卫”治病而家徒四壁;当他接触到药效类似但价格便宜很多的仿制药“格列宁”时,便义无反顾走上了帮助一众白血病患者代购抗癌药的道路,因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继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新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影片适时而生,待影片成型,现实风波却以撤诉偃息。
现实主义影片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在艺术观念层面,按照客观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再现客观事物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典型性,即在艺术形象层面,注重创造典型形象;三是批判性,即从与现实的关系来说,大胆暴露社会问题,体现批判性。一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都是社会民生的难点和痛点,《我不是药神》在题材选择上,重叠社会痛点,关注社会民生矛盾,组合影视符号去抓住与观众息息相关的具象化表达,将新闻报道“陆勇事件”搬上银幕,将观影者带入角色中,让人身临其境,从而直击观众内心深处,达成共情、共振。
对比追求特效更多更强的高成本大片,《我不是药神》没有作高大上的特效技术处理,也没有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冲击和震撼的镜头,但现实主义的题材让观众拥有天然的代入感,与观众产生了更多切身的关联。如《桃姐》让人联想到自己勤劳慈爱、默默奉献一生的姥姥或奶奶;《狗十三》让人联想到自己跌跌撞撞、哭哭笑笑的少年时代;《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大学时代的点点滴滴……现实主义的脚踏实地,让代入感更加真切也更加深透。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年迈的父亲因血管瘤晕倒在疗养院,高昂的医药费让程勇束手无措,他将病中的老父亲安顿在面包车上拉回家时有一个脸部特写,愁眉苦脸的他此时内心一定万分煎熬。无奈之下,他只能铤而走险,冒着走私“假药”坐牢的风险接受老吕的提议——代购印度“格列宁”赚钱。“我不要做救世主,我要赚钱。”这是程勇为了父亲的医药费急需赚钱的真实呐喊。
电影巧妙地站在观众的角度推进故事情节,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当观者看到电影中憔悴不堪的病人,看到人满为患的医院,看到普通人为生计所迫的囧态,看到片中人物的生活一地鸡毛、情感分崩离析时,当然也就看到了自己、家人、朋友、邻居、亲戚等的生存之痛,共情与共鸣自然而生。
在影片后半部分,老吕去世之后,影片陡然走向高潮,程勇又开始卖药。异国药厂因诉讼被关闭,厂长以2000元的价格从零售店回购药品,程勇则以慈善的方式出售药品——500元卖给病人,自己补足1500元的差额,至此,程勇的人物形象发生了转变,变得高大伟岸了。老吕因张长林抬高药价而无药可吃病情恶化后,老吕的妻子走投无路求助程勇时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这一镜头冲击力十足刺破了观众的泪腺。
老吕、老刘、黄毛、老吕的妻子以及被带到警察局的病人老奶奶,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可以化身普通的观众,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是影片中的角色——病人、朋友、亲戚、父母、妻子、孩子亦或药商、警察、法官……各类角色都能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通过现实主义刻画,影片将社会民生的痛点展露无疑,让观众身临其境,感慨万千。
二、深刻披露现实的细节处理
现实主义题材的商业电影以较为理性的方式记录日常、发现生活、探寻并展示生活细节,于无声处感人至深。影片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程勇以及与他有关的抗癌病人的故事,并没有评价程勇的做法是对是错。从主要人物来看,程勇的各类细节刻画做到了入木三分。开始,他是一个付不起房租、付不起父亲手术费的穷困潦倒小商贩;但他又有十分暖心的举动,上有老下有小的他牵挂着父亲,贴心地喂父亲喝粥,他吃了儿子嫌弃的包子馅儿。自己穷困潦倒但当儿子要买鞋时却能慷慨解囊,在给儿子买鞋付钱时他犹豫了,其对自己能力的无奈以及对儿子无法庇佑的爱,都表现在点点滴滴的细节里。影片从多个侧面交代了程勇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其走私“格列宁”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铺垫;他顽固、傲慢、世俗小商贩的嘴脸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而这些人物形象塑造是服务于影片之后的人性升华的;观众在前半部分有多讨厌程勇这个角色,后半部分就有多喜欢、尊敬他。
老刘、黄毛、思慧等病人及患者家属形象在一幕幕感人的细节中成功地被塑造。牧师老刘作为高尚信仰的传播者,本不该做违法的事,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成为“五人卖药小组”的成员,将“格列宁”售卖给来教堂的信徒;黄毛为了不拖累家人,只身一人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上海独自生活,一个让人心疼的懂事青年形象呼之欲出;思慧带着微醺的“勇哥”回家,是一个单亲母亲对女儿救命恩人的无奈“感恩”之举。当程勇出门时说:“别吵醒孩子。”思慧关上门后嘴角上扬,她笑了;她感受到了程勇跟别的男人不一样的地方。在警察局里,病人老奶奶拉着曹警官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我吃了三年药,吃垮了房,吃垮了家人,可我还是想活,谁家还没个病人,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呢。”——这让在情与法之间两难的曹警官感触颇深。而曹警官,在黄毛因保护程勇引开查仿制药的警察发生意外车祸后,也以“愿意承担任何处分”为代价终止了仿制药事件的调查;甚至一直贩卖仿制药,最终因抬高抗癌药价格“被人点了”的“反派”张长林,最后也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当警察问他是谁依然在售卖仿制药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卖假药的是我。”“五人卖药小组”第一次“团建”去娱乐场所,领班为难思慧后,程勇三次将钱甩到桌上,暗示“我们有的是钱,叫你干啥你就干啥”,这是普通穷人对艰难而压抑的现实生活的无形反抗。思慧看着领班跳舞时眼里含泪,这是一个单亲妈妈对生活所带来的屈辱、无奈以及委屈的发泄。值得一提的是,病人戴着或摘下口罩在影片中有极强的暗示作用:程勇第一次与各院病友群群主交谈如何卖药时要求大家摘下口罩,病人们迫于无奈纷纷摘下口罩,但并不是自愿的,暗示大家出于无奈妥协于现实生活,当程勇知道病人害怕有菌环境时悄悄掐灭了烟;程勇从去世的老吕家出来时,走廊两旁的病人带着口罩表情严肃而冷漠;此处的口罩代表着大家对程勇的“不友好”;当程勇自掏腰包重新卖“格列宁”而被警察抓住锒铛入狱时,自发前来送他一程的病人们纷纷主动摘下口罩,暗示着大家已经完全接纳了他,并且尊敬、感激他为病人们所做的一切。纵观整部影片,创制者一直用简单的细节诠释平凡人的生活,诠释人性的伟大与爱的无私,让观众一次次被刺激,一次次被感动。

电影《我不是药神》海报
三、推动民生变革的社会效应
看完《我不是药神》,观众大多会流泪,哭过之后便陷入了沉思,有人开始深入了解医药背后的研发问题,有人则改变了对身边病人的看法,学会了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新闻和该片引发的舆论话题仍在不断蔓延。
究其原因,这与现实主义类型电影的题材选择密切相关。回想此前大火的国产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等,都是由真实事件改编,据专业人士分析,取材自深度新闻报道的现实主义电影勃兴将会是商业电影创作领域不可阻挡的趋势。深度新闻报道的责任是拓展读者和观众的认知,而由深度新闻报道改编的影视作品,则更能直观深入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吸引观众的目光,引发大众的思考。影片的播放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抗癌药物平民化的进程,这是优秀的影视作品发挥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
在《我不是药神》一次主创见面会上,导演文牧野说道:“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家应该立足国情,以积极的心态去探知不尽如人意的周边现实,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的多面性,复杂性和无奈,甚至无解,但是怎样去推进变革,是电影表达的应有之义。”
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创作中,《我不是药神》开掘现实的深度和类型优化的技巧,为当下国产电影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现实主义并不拒绝类型经验和戏剧冲突。中国的现实主义有着自身的优良传统,钟惦棐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这种情况有所体认和概括:“现实主义在文学艺术上不是作为流派而存在,而是作为文学艺术家对待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人民采取何种态度而存在”。可以说,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创作手段,其深层次更是一种社会观、民生观。树立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价值取向,关注国计民生尤其是民生疾苦,是现实主义电影的第一要义。
《我不是药神》成为爆款也表明,中国观众呼唤现实主义创作,真实的生活和现实主义创作都是有大量关联的。电影作为大众化艺术在直面现实生活矛盾的时候,也一定要给人以温暖和希望,以人性和正义之光点燃人们内心的善良。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当下新时代的中国电影,需要温暖的现实主义、积极的现实主义、建设性的现实主义、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在收获口碑的同时,影片现实主义的笔触,对人性之光和社会进步的展现,让不少观众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和温暖的正能量。如同片中程勇所说,我们批评性审视现实,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更美好,我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结语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将新闻事件转化为影视作品的现实主义佳作,其紧扣社会民生痛点,将目光对准癌症患者和他们离不开的昂贵救命药品,其中的社会深意不言而喻;影片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真实再现病患弱势群体的喜怒哀乐,呈现了影视作品推动日常生活变革的社会价值,达成了现实主义影片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