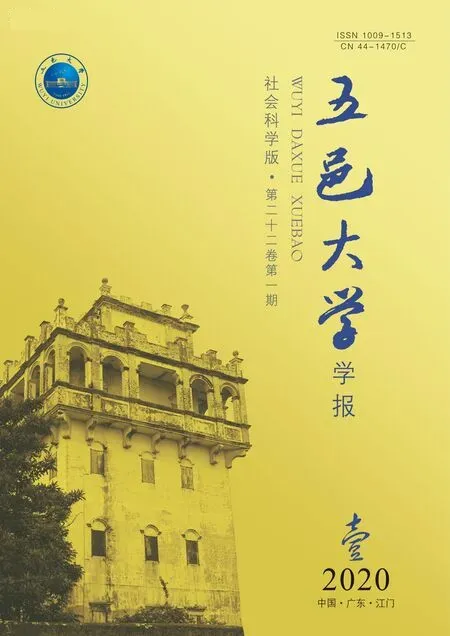丝蒂薇·史密斯诗歌中女性形象的伦理表达
2020-12-29陈彦华
陈彦华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丝蒂薇·史密斯(Stevie Smith)是战后英国一位重要的女诗人,一生著述颇丰,共出版《大家的愉快时光》(1937)、《只对一个人温柔》(1938)、《不是在招手而是溺水了》(1957)、《青蛙王子》(1966)等十余部诗集。国外学者主要研究她作品中的古典元素、笑声和创作背景,国内对她作品的研究较少。章燕认为,她的作品“写实与想象糅合,平淡中显见神话之魅力,幻想中透露现实生活的痛苦与无奈”[1]。 确实,她的诗歌创作采用迂回的笔触,融入神话元素,再现了圣经和神话故事当中的女性形象,如夏娃、圣母玛利亚、狄多、特洛伊的海伦、冥后帕尔塞福涅等,借以讽喻现实,表达对英国现代社会女性群体生存状况和情感心理的关注。
神话研究者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认为神话“具有编织新内涵和新形式的持续力量”[2]。当代女作家通过解构和重写神话,挑战传统意识,重构女性身份,表达新的生命体验和传达新的文化内涵。史密斯通过对经典神话和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再创作,描绘她们面临的伦理焦虑和困境,表达她们的伦理诉求和伦理选择。而这些女性的原型,大部分都能在史密斯的其他诗歌中描写的现代女性形象中找到对应和关照。尽管时移境迁,她笔下现实世界的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女士兵等,仍然与神话中的女主角经历着相似的伦理困境。史密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借古喻今,抨击父权社会伦理体系的虚伪性,为女性赋能,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描绘母系社会的伦理愿景。 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探讨、阐释史密斯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有助于读者理解诗人思想的深刻性。
一、 外在伦理角色规范下的女性形象
西方文学中存在两种女性的原型:代表原罪、堕落和死亡的堕落天使夏娃,以及代表圣洁、童贞和生命的女神圣母玛利亚。在父权制社会伦理秩序中,女性的最高价值是母亲身份的获得,而女性的身体和欲望则被看作是卑下的象征,是从属于男性的存在。
(一)顺从的妻子——夏娃
在史密斯的诗歌“How Cruel is the Story of Eve (夏娃的故事多么残酷)”中,她用第三人称的超然视角对妻子的传统伦理角色进行批判:“骗她嫁一个主人/她必须这么做,否则就会后悔莫及。/主说的。”[3]633男权社会对女性强加了卑下、从属的伦理角色。进入婚姻以后,女性接受了自己的伦理角色,学会了“生存之道”:“很快女人变得狡猾/掩饰她的智慧,/要不然他怎么会/带来食物和住所,杀死敌人?”[3]634诗人用简单直白的语言道出深刻而锐利的观察:父权制的伦理秩序使女性把自身和孩子的幸福都押在了男性身上,从而牺牲了自我,泯灭了个性。诗人在诗歌的结尾一针见血地指出:“Oh, falsity(哦,虚伪)”。女性对于父权社会赋予的传统伦理角色感到困惑和焦虑,由此可见一斑。
(二)坚强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美国女评论家芭芭拉·韦尔特在《真正女性气质的崇拜(1820-1860)》一文中把真正的女性气质归纳为四种品质:虔诚、贞洁、温顺、持家。[4]在男性眼里,女性应把尊贵的玛利亚作为行为的典范,以毕生的崇敬之情追随圣母玛利亚的荣光。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死亡来自夏娃,而生命来自玛利亚。”[5]在父权伦理秩序中,母亲是生命的源泉、尊贵的化身。
史密斯的对话体诗歌“A Dream of Comparison (对比的梦境)”,通过展现夏娃和圣母玛利亚之间进行的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体现了女性身上同时并存的两种伦理身份——卑下的妻子和伟大的母亲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女性获得救赎的一个必要途径是成为母亲。
她的另一首对话体诗歌代表作 “The Queen and the Young Princess (王后与小公主)”,通过王后与小公主的对话传达出一位母亲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小公主以天真无邪的口吻向王后提问,女性的成长是不是会伴随着快乐的缺失?王后的回答则体现了母亲对女儿的劝诫:“振作起来,孩子,振作起来,拥抱头疼和王冠 /有痛苦才有极乐,阴影使太阳变得更强烈。”[3]426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进入母亲的角色,承受人生的苦难,勇担责任,是一种加冕和重生。
因此,史密斯笔下的妻子和母亲履行着父权社会赋予她们的伦理责任和道德规范。要适应这种外在的伦理秩序,她们必须调整自身,把两个角色都扮演好。
二、 被“绑架”的女性内在的伦理困境和诉求
一战以后的30年期间,英国社会经历了非常剧烈的社会文化变革,原子弹和冷战的阴影挥之不去,加上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广,社会性别的伦理规范也在重塑之中。女性在适应外在伦理规范对其赋予的责任义务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价值追求和自我实现需要而产生了独立意识,与传统的伦理规范产生冲突。史密斯颠覆、解构了神话故事的主流叙事话语,通过经典故事中“被绑架”的女神的心理独白描写,隐喻现代英国社会女性面临的伦理困境,表达她们的伦理诉求。
(一)被战争“绑架”的女性的伦理困境
聂珍钊教授提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身份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6]263而伦理身份的错位导致伦理秩序的混乱:“伦理错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6]257根据古希腊神话的描述,海伦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的王后,因其美貌绝伦,被帕里斯掳走带到特洛伊,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违背了婚姻伦理中的忠诚原则。妻子和情人的两重身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海伦陷入了伦理困境当中。在神话的主流叙事中,对海伦“红颜祸水”的不道德的伦理标签是父权社会强加的。海伦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他者”地位。
史密斯的诗歌“I Had a Dream(我有一个梦)”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让海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话者通过梦境的形式代入了海伦的角色,对自己的真正身份和故事的不同版本提出了疑问:“我也不能设法让卡桑德拉说出来的是,/我是海伦的传说中的哪一个。/ 是她的幻影,而真正的海伦在埃及,/ 抑或是活生生的海伦 /墨涅拉奥斯会带回去斯巴达的那位。”[3]566她究竟是危险的情妇,还是贞烈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伦理身份感到困惑。王子赫克托耳指责海伦的“不虔诚会给特洛伊带来厄运”[3]567,把过错责任全部推给海伦,是典型的父权社会的霸权伦理思想。遭到误解的海伦心情非常沉重,自我解嘲道:“我笑了/但是我更想哭。”[3]567在男性伦理秩序主导的世界中,女性被剥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
因此,在诗歌的结尾处,海伦做出了自己的伦理价值判断,声明了自己的伦理选择:
我将永远不会成为
那位恶作剧的爱笑的海伦,与墨涅拉奥斯回国
在安静的宫殿里,做她的针线活,笑着
讲述她的故事,然后哭泣:哦,可耻的我。[3]567
海伦声明,她拒绝被传统伦理观绑架,不愿意被男性继续摆布和利用:回归妻子的角色,把自己谴责为“可耻的”情妇。史密斯通过海伦的叙述隐喻现代社会,女性的伦理角色往往是留在家里做家务,按照男权社会的主流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歪曲自己的形象,以满足男性的想象。而史密斯笔下的海伦有着独立精神、敢于挑战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是一个勇于追寻自我、捍卫自己人格和尊严的女性。
史密斯的另外一首诗“Come on, Come back(来吧,归来吧)”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在现代战乱中的女性发出的伦理思考和身份追寻。 海伦是被古代战争绑架并被父权制伦理体制用莫须有的罪名指控的女性的经典原型,在特洛伊的城墙上不断地追问自己的身份,拒绝当战争的替罪羊。同样地,这首诗中的女士兵也是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冠冕堂皇的现代战争的漩涡里,在战争中丧失了记忆,在小丘的石头上不断地追问自己被卷入战争的缘由:
人道灭绝者M.L.5.
她死里逃生
但是她的记忆已经永远消失。
独自坐在小丘的圆形扁平石头上,
她恐惧,她哭泣,
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3]452
现代战争是大国恃强凌弱的霸权行为,泯灭人性,冲破了一切道德底线和伦理平等,是男权思维的极致体现。父权社会的统治者们为追求权力和边界扩张发动战争,平民被剥夺了选择权和话语权。战争夺走了女兵的记忆,她被卷入了巨大的虚无之中,对自身身份和战争意义的追寻注定是徒劳、绝望的。史密斯借助女兵的视角,对现代战争的伦理进行反思,抨击了现代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传统伦理的毁灭,深刻地刻画出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处境。
(二)被丈夫“绑架”的女性的伦理诉求
女性在结婚以前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结婚以后就要受到父权社会家庭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制约。从女儿到妻子的伦理角色转变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要做出妥协和牺牲,适应的过程是艰难的。
史密斯通过 “Persephone(帕尔塞福涅)”一诗用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女性在伦理角色转变过程中的心理抗争。某日,帕尔塞福涅外出采花时,大地突然出现裂缝,冥王Hades(哈得斯) 骑着黑马,穿着黑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她掳走,带到冥界的黑暗深渊。诗中以帕尔塞福涅的第一人称视角说出了她的内心感受:“哦,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 我伸手去摘下一朵花,娃娃脸般可爱的白天 /突然响起了雷暴,转瞬变成了冬天?”[3]344这段话道出了她灾难般的感受。史密斯用重复、隐喻的修辞手法道出了丈夫哈得斯所代表的父权社会家庭伦理秩序对女性的绑架和束缚。
帕尔塞福涅深深地想念母亲: “但我的母亲,我爱她,却离开了她/她失去了一个好女儿,/悲伤撕裂了她的心。”[3]344帕尔塞福涅离开以后,谷物女神德墨忒尔无心管理人间的粮食庄稼。大地寸草不生,变成了冬季。在诗歌的最后,诗人对神话进行了戏仿,用反讽的手法迂回地控诉父权制伦理体系:”我的丈夫冥王他可知道?他能否猜出 /这样寒冷的冬天/正是我的快乐所在。”[3]345诗人孩子气的解嘲凸显现实的冷峻。
综上所述,史密斯笔下被战争掳走的海伦、女士兵,还有被丈夫掳走的帕尔塞福涅都是被父权制伦理体系约束的女性的缩影。史密斯用戏仿的手法将神话降格,颠覆主流叙事,让这些女性发出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表达她们的焦虑和困境,并道出女性内心的伦理诉求和对父权伦理的控诉。
三、 女性的伦理抉择
在史密斯成长的过程中,父亲长期缺席,也缺乏关系密切的男性亲属。因此,她在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父亲角色产生疏离感,甚至是敌意。她笔下的父权社会危机四伏。夫妻、父女之间的关系常常出现危机。例如,在她著名的“Not Waving but Drowning(不是在招手而是溺水了)”诗中,溺水之人就是她生命中父亲形象的象征。而在这首诗所配的插图中,溺水的是却是一位女性。有读者认为,画中人正是史密斯自己。 史密斯对她生命中父亲的缺席一直耿耿于怀,画中人的溺水象征她内心的殇恸以及父女之间沟通的缺席和情感的消亡。在“Papa Love Baby(爸爸爱宝宝)”一诗中,女儿对父亲没有爱,使得父亲伤心欲绝、远渡重洋;在“Precarious and Tenuous(危险的和柔弱的)”一诗中,她以负面的形容词命名家中所有的男性成员。这些诗作表达了诗人对父权制社会伦理秩序的质疑和厌恶。
史密斯某些诗作中的女性表现出鲜明的伦理价值取向,勇于与父权伦理秩序诀别;另外一些诗作则勾勒出理想的女性乌托邦。
(一) 女性与父权伦理秩序的诀别
史密斯的“Dido’s Farewell to Aeneas(狄多向埃涅阿斯告别)”,以狄多的第一人称视角写出了她的内心独白: “我一直跟随着命运之神的步伐,从不退缩,心甘情愿地追随他/而现在,并非毫无预兆,我走到了尽头。”[3]447狄多的一生都被操控,她的哥哥和埃涅阿斯使其陷入了“妹妹”和“妻子”的伦理结之中:哥哥夺走了她的丈夫,而她却要继续承担“妹妹”的伦理责任;埃涅阿斯背弃了她的爱情,使她失去了作为“妻子”的伦理角色。 她最后唯一能操控的就是呼唤死神,以刚烈决绝的方式与父权伦理秩序诀别。她的自杀是自身内部伦理身份矛盾激化并无法找到合理出路的极端行动。但是自杀并没有为她解开伦理结,在诗歌的结尾狄多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大仇未报,我将死去,她大哭道,但我将死于自己的选择。/来吧死神,你知道,虽然你是神,但是当你被召唤,/你必须来到我跟前。来这儿吧,来这儿吧,我呼唤你。”[3]447在诗歌的末尾,诗人使用顿呼(apostrophe)的修辞手法,通过想象力的渲染,与死神进行隔空对话,体现她对父权社会伦理体系的激烈控诉,表达与其诀别的坚定决心。
在另外一首诗“The Wedding Photograph(婚礼照片)”中,女性说话者告诉未婚夫,她将在婚礼结束后,把他带到丛林之中,让步履缓慢的老狮子吃掉他。她在诗中用第一人称视角和黑色幽默的语气道出了自己到丛林与丈夫同归于尽的惊人阴谋:“是死亡的念想点亮我美丽的眼睛/但是人们认为你很幸运能获得如此漂亮的战利品。/ 啊,虚弱的我只想独自徘徊 /然而,我不敢不结婚就离开家里。”[3]569在不经意的轻盈中,她道出了沉重、痛苦的思考:丛林象征着黑暗和死亡。她要把象征父权伦理秩序的统治者的丈夫带到山林里杀掉,然后自杀,与父权伦理秩序彻底了断。这是她逃离“妻子”的伦理身份并化解自身伦理困境的出路。在诗歌的最后,诗人把她对父权社会的仇恨揭露得极致:“啊,悲痛,让火焰燃烧,在眼睛的末梢燃烧吧,/让恐惧的火焰熊熊燃烧,让火焰随着哈利的呼吸熊熊燃烧。”[3]569诗人通过反复(repetition)的修辞,体现了梦魇般的仇恨如熊熊烈火般煎熬着她的内心,挥之不去。
(二)女性对母系社会乌托邦的伦理愿景
史密斯诗歌中的主人公经常借助想象的力量逃遁到一个图画世界中的理想之境,与现实世界形成反差,用以讽刺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制伦理体系。例如,在“The Lady of the Well-Spring(源泉女神)”中,小孩琼恩被雷诺阿的名画《源泉》深深吸引,遁入想象世界:
她听到了泉水噼噼啪啪叮叮咚咚嘶嘶作响
林中的鸟儿叽叽喳喳升起,
现在,当她奔跑时,她听见了
涓涓细流的潺潺流水声
水花四处溅起,那是水的源泉。
现在,琼的双脚踏在深深的苔藓中,看着
岸边有一位高大的皮肤白皙的女子躺在哪里
皮肤白皙光滑,肚子微微隆起,
丰满的乳房,细致的纤腰和修长的双腿[3]424-425
……
诗人用清新的文字,如“噼噼啪啪(clacking)”、“叮叮咚咚(croaking)”、“叽叽喳喳(chattering)”等拟声词,用丰富的韵律、意象和联想描绘出一个充满欢乐和青春气息、富有生命力的人间仙境,诗歌充满音乐感和画面感:琼恩仿佛进入了如伊甸园般的神仙世界,这位赤裸的女子就像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夏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诗人通过孩子的视角,为读者描绘出一幅脱离了父权社会森严伦理规范的母系社会乌托邦。孩子琼恩遁入乌托邦,隐喻女性回归母系社会的乐园,回到生命的本源,返璞归真,就如冥后帕尔塞福涅在冥界度过冬天以后,回到母亲的怀抱,人间便恢复了春天的气象,万物复苏。诗歌的节奏和色彩美使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交响曲余响不绝,隐喻母系社会的乌托邦充满了生命力,使女性获得自由,不再受到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
四、结 语
史密斯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锐利的视角和饱满的情感刻画了百变多彩的神话和现代女性形象,传达了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伦理寓意。在主流社会外在伦理规范的制约下,大部分女性一生当中都要在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之间取得平衡。而在战争肆虐、职场挑战和家庭结构变化等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道德伦理环境不断变化,女性因此产生了独立意识,陷入到一些伦理困境之中,产生了新的伦理诉求和选择。在伦理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她诗歌中对女性伦理观的发散思考和多元伦理选择无疑是有思考价值、借鉴意义和欣赏价值的。
道森和恩特威斯尔指出:“她诗作中的多元声音为反二元对立观念开辟新的路径,避免两性之间或其他分化群体为争夺统治权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中。”[7]
使用神话故事人物展现伦理价值观是史密斯的一大显著写作特色,构建神话般的虚构世界,用欢笑面对辛酸是重要的心灵治愈良方。正如她在诗歌“How do you see?(你怎么看?)”中所言,如果我们不借助魔幻的元素和美丽的神话故事教会孩子们善良的道理,那么现实世界的尔虞我诈将使我们无法承受,我们也会变得杀气重重。[3]667她为笔下的女性形象搭建了想象的舞台,让她们在舞台上自由驰骋,恣意自在地抒发内心的伦理诉求和构筑美好的伦理乌托邦,消解了经典神话的主流叙事。她借用神话所讽喻和折射的伦理寓意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价值体系相互关照,有助于启发人们对现实伦理价值体系的思考和重构。当人们的伦理价值观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时,能从她的诗歌世界中找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