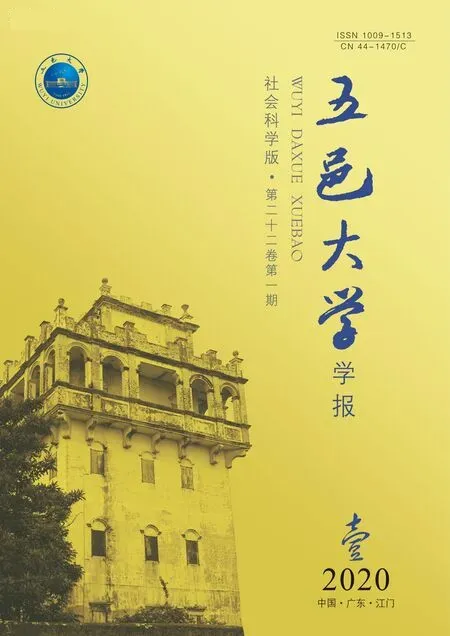《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
2020-12-29王凡
王 凡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反讽笔法展现了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1],书中涉及少数民族的汤镇台“平苗”情节也是别具意味。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系列公案小说《大唐狄公案》表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的传奇性故事,在呈现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之时,也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形象。学界对于《儒林外史》“平苗”情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本事、源流的考证,如何长风、邱宗功等学者合撰的《吴敬梓笔下黔东南少数民族起义考察》(《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探讨了该情节的艺术特色、考察了战争发生的真实地点。而李远达的《文人“兵”梦的虚与实:〈儒林外史〉萧云仙、汤镇台本事补证》(《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则在对萧云仙、汤镇台等书中人物的本事加以补充考证的同时,还对“平苗”情节前后将领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反映作品主旨进行了探究。相比之下,有关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的研究虽在近年成果频出,但书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却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为本文的比较性论析提供了某种研究契机。对两部作品中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比较有助于审视、探究不同时代与地区的作家、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形象的独特认知和阐释,这无论是在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在民族学研究领域都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
一、“番汉战争”情节的历史影射与艺术虚构
《大唐狄公案》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主要集中于《迷宫案》里。在这篇小说中,面对危局的狄仁杰巧施妙计肃清了城中内奸,俘获了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乌尔金,退外虏于城下。《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则表现了汤镇台以半途伏击和假扮鬼神之计全歼了以人质相要挟的野羊塘苗人。可以说,两部作品中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均重在展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政权之间的战争冲突,但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儒林外史》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历史原型,这也成为该书映照历史的方式之一。据李汉秋先生考证,汤镇台的历史原型即为清将杨凯,其征讨苗寨、善于用兵的特征,黾勉为国、却一生宦海沉浮的事迹都与书中汤镇台的经历逼似[2]。而从宏观历史层面来看,《儒林外史》中的汤镇台故事也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有着明显的指向性。明清时期,苗人被分为“生苗”“熟苗”两类,清代的龚柴曾对此作以区辨:
其已归王化者,为之熟苗,与内在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峒,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苗性刚倔,嗜杀。生男敛铁为贺,即长,治刀佩之,彍弩药矢,长矛鸟枪,出入与俱,以轻生善斗为尚,好寻旧恶,睚眦之隙,动至操戈,非及时排解消释,往往相寻不已。或强弱悬势,贫富不敌,蓄愤积怨,暂时不报,俟势力相敌,怂恿有人,遂纠众执械,拼命奋斗。[3]
可以说,龚柴在区分“生苗”“熟苗”的同时,也对苗人尤其是“生苗”的生活习俗乃至民族性格进行了论析。可以看出,“熟苗”是指“邻近汉区或与汉人比较接近,能讲汉语”亦即“被纳入版籍,被地方官吏直接管辖,遭受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剥削的苗族居民”,“生苗”则是指“居住在偏远山区,与汉人关系疏远,言语不通,与汉族生活习俗各异的苗民。”[4]作为文学家的吴敬梓也通过《儒林外史》对苗民这种与统治政权的亲疏关系作了区分:
我们这里生苗、熟苗两种,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从来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会闹起来。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带的苗子,尤其可恶。[5]
太守雷冀向汤镇台介绍当地“苗情”的上述这段话,虽然充斥着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口吻及对苗民的污蔑性语气,却也反映了苗民中的“生苗”“熟苗”之分及其与汉族政权迥异化的特殊关系:“熟苗”接受当地政府的封建统治,顺从于他们的管理乃至盘剥,而世居深山的“生苗”则不仅没有接受统治政权的统治,过着相对蒙昧原始的生活,还时常与统治当局发生冲突。清雍正时期开始实行的“改土归流”“开辟苗疆”虽在客观上有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强化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但这一带有强制推行汉文明色彩的政策的实施却受到苗族地区尤其是聚居于湘、黔等地的“生苗”的强烈拒斥,并由此引发了他们的暴动、起义。《儒林外史》中以清人杨凯事迹为素材所展现的汤镇台“平苗”情节,正反映了清代中期“苗族原生文明体对汉族君主专制制度下地主经济文明体向苗疆地区强烈扩展和传播的抗拒”[6]这一历史,并投射出以作者为代表的士人对此的认识和思考。
与《儒林外史》中的少数民族书写相比,《大唐狄公案》中有关少数民族的情节则没有十分明确的历史指向。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伴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军事冲突和文化融合:从犬戎袭取镐京致西周灭亡到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与和亲,再从“五胡乱华”到唐、宋两朝与突厥、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对峙,元、清两朝更是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主宰中华的统一王朝。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高罗佩从宏观把握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冲突、融合并进的特殊历史,兼以艺术虚构,杂糅成《迷宫案》的“番汉战争”情节,从而既令其成为书中的重要情节,又折射出一定的历史意蕴。值得注意的是,《迷宫案》中狄仁杰挫败“番酋”乌尔金的攻城图谋与《儒林外史》中汤镇台“平苗”虽都是以“番汉战争”来构成情节主体,但《儒林外史》中的这一情节由于摄取了清将杨凯的事迹,并影射了清代中期苗族与统治政权发生军事冲突的史实,故而表现出较为明确的历史实指色彩。与之相比,《迷宫案》的这一情节虽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古代的“夷夏”关系史,但其并非是直接裁取自某一朝代的某个将领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历史事迹,亦未以具体的某一少数民族作为表现对象,故同样是表现“番汉战争”,汤镇台“平苗”的情节比狄仁杰挫败乌尔金图谋的情节有着更为明确的历史实指性,甚至已有“直录史实”的些许色彩,而后者则是在相对模糊的历史指涉中,凸显的是作者在情节设计中更为显著的艺术虚构意识。
《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实际上与中国古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来观照社会历史的特殊意识不无关系,从杜甫的“诗史”意识到《金瓶梅》的“以宋写明”,中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映照了社会历史,这一创作理念无疑也影响到吴敬梓,其不仅将元明易代及明代的一些历史事件穿插其间,也从真实历史人物中汲取素材,影射若干史事,书中的“平苗”情节即是如此。然而,“援史入文”、“以文映史”却非高罗佩关注的焦点,其主要还是潜心于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素材来建构跌宕曲折的悬疑侦破情节。因此,狄仁杰擒获乌尔金、巧退少数民族入侵的情节虽投射了高氏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却没有明确的历史实指色彩,围绕这段情节所展现的“空城计”“诱敌计”都明晰表明他主要还是通过情节来铺设故事悬念、强化叙事节奏、增强作品可读性的创作出发点。这也是两部作品在“番酋战争”书写方面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番酋”形象塑造的审美差异
《儒林外史》在展现汤镇台“平苗”时,主要将笔墨集中于他如何依据敌情出奇制胜,以彰显其足智多谋,但被一次次赚入彀中的苗人形象则被完全旁置,小说仅以其愚蠢无谋、野蛮好战的形象来凸显汤镇台的用兵如神。由此可见,该书并未从艺术形象审美的层面对少数民族人物加以塑造。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高罗佩在《迷宫案》中展现少数民族首领乌尔金妄自尊大、狡狯机诈的反面形象时,也对这一人物的其他性格特征进行了刻画。在狄仁杰部下马荣前来诈降时,乌尔金曾言:
我自幼随父常出入兰坊,亦曾去长安经商数年,还到过京畿之外不少州县,故深知唐室官场中一向文恬武嬉,不乏尸位素餐之人。那些鲜衣怒马、峨冠博带的衮衮诸公,整日灯红酒绿,斗鸡角抵,声色犬马,逍遥行乐,早将国家安危置于脑后。再者,兰坊又是个边陲远镇,此城易手后,长安官家未必马上知晓。况且现在通西域之路改道,唐朝廷即使获知兰坊失陷,也无须担心我们会拦截西域诸国东进使臣,劫掠财礼,故不会立即发兵前来收复失地。待长安昏君醉臣大梦初醒,我们则早已在此站稳脚跟,立国称雄。到那时我们兵精粮足,以逸待劳,唐军纵有貔虎十万,又奈我何。[7]198
由乌尔金的上述言语可以看出,其希求里应外合、攻城割据的企图虽不乏以卵击石、痴人说梦的色彩,但其对中原汉族政权统治危机的认识以及据此制定的基本战略却并非没有合理之处,如若不是狄仁杰慧眼识奸、巧施妙计,那么乌尔金等人依计行事,则形势亦将难以预料。这不仅烘托了狄仁杰运筹帷幄、临机决策之能,也凸显出乌尔金虚妄狡诈、野心勃勃等负面特征,以及富于韬略、具有政治敏锐性等形象特质,而并非只是将其单纯塑造成为有勇无谋、残忍嗜杀的“蛮夷”形象。通过乌尔金这一具有丰富形象色调的“奸雄”人物,可以看到高罗佩规避善恶立见的人物塑造窠臼、努力塑造鲜活艺术形象的创作目的。
相比之下,《儒林外史》的少数民族人物仅是作为过场性的反面人物出现在情节中,而缺少对其复杂性格的刻画。该书的主要艺术成就之一便是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从严监生吝啬成性与顾惜亲情的复杂交融到匡超人亲孝淳朴与道德堕落的形象渐变,再到王玉辉劝女徇夫的内心情感变化,无一不是在直击人物灵魂深处。这些艺术形象生动鲜活、饱含人性意味,反映了吴敬梓小说人物塑造圆形化、丰满化的创作意识,但其却并未对书中的少数民族人物进行类似的深层化呈现,这其中潜隐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
西周末年,北方戎、狄等少数民族对周王室及各诸侯国产生了巨大威胁,“华夷之辨”的理念自此日渐凸显。管仲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呢,不可弃也。”[8]173而孔子的“内华夏而外诸夷”[9]之说则是儒家在这方面最集中的认识。“华夷之辨”对于华夏和四夷的区分是以礼仪、文化为标准的,主张彰显华夏文化的先进、秉持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而不应屈从于夷狄的文化和习俗,强调“用夏变夷”[10]。通过“华夷之辨”“华夷之争”,“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民族先后认同了华夏,而在接触与交流中,诸夏也吸收了其他民族大量的优秀文化成果。”[11]与此同时,古人对这一观念的强调实际上又放大了所谓的“夷夏之别”,以致形成“严华夷之防”这类具有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狭隘意识:一方面将“夷狄”视为猛兽、异类,正所谓“狄,豺狼之德也”[12]、“戎,禽兽也”[8]647;另一方面还认为“蛮夷”落后、野蛮,华夏高度文明,强调对其征伐、令其威服,故而有“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8]647的认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王韬就指出: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华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13]
但即便如此,这一狭隘观念仍影响深远,并投射于文学作品中。在《儒林外史》汤镇台“平苗”这一情节中,苗民的本真形象被彻底旁置,而被定位为愚蠢蒙昧、狂妄无知而又徒生事端、色厉内荏的反面人物,他们只有在以汉族为代表的统治政权的“威服”下才能安分守己。正如法国学者萨维纳在论及苗族历史时曾说的那样:“所有的苗族,在汉人心中都被妖魔化了,他们觉得苗族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反复无常、野蛮的民族,尤其他们都有小偷小摸的毛病。”[14]可以说,《儒林外史》对于少数民族客观真实形象的缺席化呈现、对其负面化的形象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华夷之辨”观念中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潜在影响。
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毕生精力探研中国文化,但其又能时时秉持一种西方理性思维和文化辨证精神来对中国文化加以客观审视与理性思考。因此,在创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高氏虽受到明清小说的影响,并通过改易明清公案小说情节来架构书中的情节,但在许多方面他仍然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理解与认知,对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书写即是如此,他并未受到传统“华夷”观念中偏狭、消极一面的影响而对少数民族进行贬抑、矮化,继而令自己书中出现汉“高”番“低”或汉“正”番“邪”的“番汉”关系形态,而是在将“番酋”乌尔金设置为反面人物的同时,又通过对其言行举止的细腻描摹、对其多面形象的鲜活塑造,使得以其代表的少数民族人物获得了一种在《儒林外史》中本该具有、却又付之阙如的平等“话语权”,从而反映了高氏对于传统“华夷”观念的理性思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接受。故此可以说,相比于《儒林外史》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贬抑化呈现,《大唐狄公案》对于乌尔金这类人物形象的独特刻画,是成功而有价值的。
三、少数民族文化描绘的丰富性差异
《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中叶西南地区苗族与统治政权的复杂矛盾冲突,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汤镇台在“平苗”前后的仕途际遇来揭示封建官场真实的一面。具体说来,小说一方面以汤镇台平乱贬官表现了忠臣为国效命却不为朝廷认可的传统悲剧,另一方面又展现了汤镇台在“平苗”期间与太守雷骥的暗中“角力”:汤镇台熟知兵法,而雷骥却更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因此,雷骥虽未亲涉“平苗”之役,却可分享战功,而汤镇台虽平乱擒敌,却被朝廷斥为“率意轻进”“好事贪功”。作者通过草蛇灰线的手法折射了封建官场中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残酷现实及封建官僚机制的腐朽。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虽然立意深刻、手法高妙,但其中的苗民形象仅是作品为了表现汤镇台的宦海沉浮、人生变幻而设置的,古代苗族的生存状态、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完全隐没于“番汉战争”的单纯描写中,这既与“严华夷之防”这一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观念存在一定关系,更和该情节思想立意的侧重点与倾向性有着内在关联。
与《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罗佩在《迷宫案》中不仅围绕着“番汉战争”情节塑造了“番酋”乌尔金的独特形象,而且还有意描绘了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异质文化。该小说对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北寮”妓馆进行了别具生趣的呈现,其先是通过马荣假扮嫖客、前赴“北寮”查访白兰迷踪,对城中这一特殊场所进行了总体刻描:
这北寮又自是一番景象,但见酒家茶肆之内多为胡人,身着异装,口操番语。[7]170
此后,小说又对北寮妓馆内的人之百态进行了细腻的描摹:
屋内既闷又热,一股羊骚臭直钻鼻观,中间地上支了一只火盆,四周矮凳上围坐了三男三女,一个个均袒胸露臂,手执铜扦,拨火烤肉。一嫖客已有三分醉意,一只胳膊搂了身边的女子,摇摇晃晃轻声哼起了下流小曲。另两人则清醒如常,以番话说这话儿。二人不算高大,却一身紧肉,不可小看。掌班将一小壶酒放在马荣面前,自回柜台。一女子起身,琴架上取了琵琶,倚墙自弹自唱起来,虽不成宫调,嗓音却佳,倒也别有风趣。[7]172-173
小说首先是通过酒馆、茶肆中胡人的着装、言语对“北寮”浓郁的胡番文化氛围进行了整体渲染,而后又细腻勾勒了胡客与胡妓的狎昵之行及歌妓胡女的形象特征,为读者展现了“北寮”的“青楼”文化。在呈现“番汉战争”情节时,亦通过勾栏瓦肆中的市井文化书写,描绘了古代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图景。
《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在情节内容上广泛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素材,运用的却是西方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和表述方式。西方侦探小说在构建悬念迭起的推理破案情节时,也常常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可以说是映照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则使读者分别领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尼罗河沿岸的秀美风光与中东地区的风土人情。而这一审美特征在《大唐狄公案》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如《朝云观》展现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铜钟案》再现了唐代佛教盛行以及僧侣横行不法的特殊历史,《黑狐狸》则呈现了古代中国繁荣璀璨的诗歌文化与文人雅士的生活意趣。但《大唐狄公案》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风俗民情、传统文化的辐射在反映的广泛性与丰富性方面都远胜于西方传统侦探小说,这无疑也投射出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通过文学作品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传输、展示中国文化的高度自觉意识。正因如此,《迷宫案》在利用有限篇幅展现“番汉战争”情节、塑造“番酋”乌尔金形象的同时,更饶有意趣地通过对“北寮”这一特殊场所的描写来反映一定地域、民族的市井文化,反映出高氏利用文学作品来传播、展示中国社会文化风貌的内在创作动机,体现了其力求把通俗性、可读性与文化性、思想性有机融合的文学创作理念。
结 语
《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虽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故事情节,但二者对于少数民族形象的文学阐释却存在着诸多差异。《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有着明确的历史指向性,而《大唐狄公案》的“番汉战争”情节则更多地源于作者的虚构;《儒林外史》对“番酋”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塑造基本忽视,《大唐狄公案》则相对立体地刻画了此类艺术形象;《儒林外史》以“平苗”之役为表层情节,在揭露封建官场时也把针对古代苗族真实生存状态的社会观照隐没其间,而《大唐狄公案》在表现“番汉战争”时,更对“青楼”文化和市井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细腻描摹。表面上看,两部作品在古代少数民族书写方面的差异性是由二者在创作时代、风格类型、题材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固有差异所决定的,但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与高罗佩在其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极呈现及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证接受相关,另一方面又和《儒林外史》影射历史的创作意识以及“华夷之辨”观念对于中国古代士人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少数民族书写对于认识、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思想主旨以及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