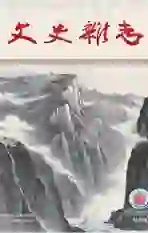陈寅恪:从“读书种子”到四大导师(下)
2020-12-28余灵均
余灵均
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有一点还须注意:即陈寅恪的比较研究虽然反映出较强的德国东方学传统,但在本质上却具有中国文化本位的坚定立场。这一点,是与包括德国东方学在内的欧美日东方学迥然不同的。西方的东方学皆视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文化为“他者”,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研究东方。陈寅恪则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看待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和其他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寻求彼此间的异同,从而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推动它的弘扬与发展。前引《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便代表了陈寅恪的立场。因此,我们与其说陈寅恪在治东方学,不如说他是以东方学为工具来研究中国文化。
换言之,陈寅恪是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驱动下来比较与研究中外文化之异同的。所以,他尽管十分熟悉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但其佛学的研究,仍以汉地文献为重点。他所关心的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国被中国文化改造的过程以及佛教对中国社会(主要在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非印度佛教本身。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是将蒙古、西藏以及以今新疆为中心的西域文化都归入中国文化来研究,认为这些文化自古就属于中国文化之一部分。他认为中古时代(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北方胡人南下,融入中华民族,给中国文化带来活力。他进而指出,作为中国中古文化高峰的唐代文化,就是中原周遭的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一些单篇史论中,从文物制度(礼乐、典章制度)、兵制、法律、建筑、工艺乃至财政各方面去论证北方与西方、东方胡族(包括居住在今天蒙古、新疆、西藏、东北地区的当时汉族以外的民族)对唐代文明、中华文明之形成和繁盛的杰出贡献。这种不以血缘而以文化论种族的“种族文化观”与德国著名哲学家、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1744—1803)的史学思想比较相似。
陈寅恪在欧美日游学十六载,系统学习了世界历史与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包括赫尔德、兰克、兰曼、吕德斯在内的欧洲近代思想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东方学家的著作,还有马克思《资本论》等,掌握了不少西学治学方法和十几二十余种语言文字,又接受了种族文化主义(或称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此间还系统学习了从十三经到二十四史的中国文化元典),使他从一个涉世不深的青涩访问生,成长为一位淹贯中西、学究天人的大学者。1931年5月,时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列的陈寅恪在题作《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文里写道:“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陈寅恪正是由于走出了国门,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并能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取世界先进知识,从而脑洞大开,思如泉涌;纵横捭阖,元气淋漓;知人论世,皆成一家之言!
1919年吴宓在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时,便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惊为天人,有“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之语。到了1934年夏,吴宓在《空轩诗话》里仍不改初衷,说:“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要知道吴宓说这话时,做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已三年,此前还主持过大名鼎鼎的《学衡》达十一年,担任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有六年,也是名扬海内的一代学人。其所语,当是那时学界的普遍认识,没有虚饰。
《吴宓日记》1961年8月30日有记说:“寅恪兄之思想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这是吴宓与陈寅恪最后一次面晤(在中山大学陈宅)时,对陈寅恪与之交心的感悟。“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自冯桂芬、孙家鼐直至张之洞、陈宝箴、陈三立一脉相袭的政治主张;到陈寅恪这里,则化为一种更具世界眼光的文化原则、思想方法,用以指导他十六年的游学生涯并及此后的治学道路。这种原则、方法被学者归纳为“中国文化本位”论。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在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即在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能动性的同时,亦倡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及创新性。这样来看,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并不完全等于“中体西用”论(吴宓的感悟并不确切),也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不小差距。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里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本根未死”“终必复振”——这就是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满满的自信。陈寅恪坚信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现虽至衰世,但根还在,一有机会,必将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陈寅恪为邓广铭作序之时,正是中国抗战处于最艰难之际(1943年1月,陈时羁泊西南桂林之一隅),但他却在艰难时刻看到了抗战的黎明,看到了中国文化复振的曙光。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精英麇集西南,克服艰难困苦而致力于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的情景,坚定并鼓舞了陈寅恪“为往圣继绝学”的决心及信心。但在如何振兴中国文化的方法论上,陈寅恪不尽然同意他的密友吴宓等的学衡派主张,也有异于同属其友人的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写了一段话,以道教、新儒家为例,阐明了他对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看法:
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
在这里,陈寅恪其实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命题:用开放精神凿通中西文化间壁,以达成西学中国化,继而融入世界先进学术朝流,推动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复振、创新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做的正是这件事。
陈寅恪游学西方十六年,虽未获得任何代表学位的文凭,但仍然取得学业上的大成绩、治学上的大收获。其根本原因,就是明确了自己的肩负的文化责任,能够始终抱着坚持、维护和弘扬、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宗旨,去有意识地、有区别地和大胆地吸收欧美先进思想文化而以融汇贯通,化为己用。他的最终目标、崇高理想,就是以文化兴民族,以学术救中国。这个目标、这个理想,亦被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认同;但论其践行,则以陈寅恪等为代表的少数人做得最好、最精细。他们在中国文化于近代以来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愈加深而渐趋颓势之际,用一腔忧患意识和一生睿智与辛勤去填海补天,追逐太阳,厥功至伟,感天动地!
举荐之趣和《与妹书》
陈寅恪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终止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一纸聘书。清华学校是依托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于辛亥革命前夕成立的。1906年初,在决定启动庚子赔款退还程序之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斯致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操纵中国领袖的方式。”“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更有力地支配美国在商业上持久地获利。”可见美国人所谓“退还”“庚子赔款”的“义举”纯属扯淡。首先,“庚子赔款”所依据的《辛丑条约》是一个羞辱中国的完完全全的不平等条约,条约本身就不义,何谈后续的“义举”?第二,连1904年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自己都向清朝驻美公使梁诚承认:“庚款原本就索要过多”(后梁诚报告:美国超收庚款达二千二百万美元之巨),所退部分,即此“索要过多部分”。第三,美国从来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其用“退款”办学纯粹是出于长远掌控中国之需;否则,强盗掠走财物,岂能甘愿退还?这不符合资本家或帝国主义的本性。美、英、法、日以及沙俄等掠走中国的敦煌文物、黑水文献退还过吗?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掠走的圆明园珍宝、紫禁城—中南海珍宝退还过吗?都没有!所以,脱离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去感念它的“好”,不是愚昧就是别有用心。美国政府正是出于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目的而实行“庚子退款”的。
1908年12月,美、中两国商定,在向美国派遣公费(用所“退”“赔款”充值)留学生同时,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称“游美肄业馆”。后来以该馆为基础,于1911年4月29日在北京花木扶疏、风光绮丽的西北郊正式成立“清华学堂”,翌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春设立大学部,同时筹办国学研究院。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当时(1925年2月初)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处主任是刚从东北大学赶来的陈寅恪挚友吴宓。他同时还兼清华大学筹备委员。要办好国学研究院,第一要务就是聘请教授,这一点吴宓是非常清楚的。他就任后,先后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三位为国学研究院教授。应该说,这三位教授在当时学术界都属领军式人物。梁启超、王国维是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自不必说,而那位赵教授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赵元任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当时的语言研究领域正如日中天。因此而言,吴宓聘任他们,在校方是给予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但是,当吴宓要聘任他的老朋友陈寅恪为第四位教授,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陈寅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既无学位又无著作,相比前三位教授,那火候相差实在不是一两个等级。可吴宓却不管不顾地一味向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教务长张彭春卖力地推荐尚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来研究院出任第四位教授,这自然遭到主事之一的张彭春拒绝,称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不应放松聘任标准。这吴宓急了说:“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按:实为十六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之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2]吴宓当时的心情,是焦急而悲怆的。这里《学衡〉杂志是时任南京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的吴宓与东南大学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等教授于1922年春共同创办的,主编是吴宓。陈寅恪在这个以“研究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刊物创办之初,曾给它捐过款,写过稿,但对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却保持一定距离,不属于学衡派阵营。那么,被吴宓拿来说项的、被他推崇备致的陈寅恪《与妹书》说了些啥呢?这里将《学衡》所刊节录本予以全文照录,以供赏析: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圆。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剛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结玄义)。好在天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明为伪造。达磨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3]
吴宓单拣出陈寅恪该文来说事,倒不是去夸耀陈氏的文采斐然,而在于向校方讲明有眼当识金镶玉的道理:你看那位正在世界学术中心——柏林大学深造的义门陈氏的后代,文化积累有多棒,学术功力有多深,雄心抱负有多大!今清华国学院开创伊始,正缺这方面的人才;而此处不用,则必为他处所用——沧海遗珠之憾,不该出在堂堂清华之身!据吴宓后来回忆,当吴宓举出陈氏《与妹书》后,又费了一番口舌,教务长张彭春仍不为所动。不得已,吴宓便转而向态度模棱两可的校长曹云祥再申前言,并以辞职相要挟。曹云祥被纠缠不过,只得点头应允。吴宓便趁势草拟一通学校聘书电稿,要曹签字;曹在无奈之中也签了。吴宓取得签字,如获至宝,连夜向万里之外的陈寅恪发出急电,以清华国学院名义召他回国,言“虚位以待,共襄盛举”云云。此时大致已是1925年2月中旬了。吴宓在不到半月时间里就完成了对“四大导师”的聘任,除了其对教育、对学术投入的满腔热情及巨大努力外,他那不可抗拒的人格(谦逊、无私、敦厚、真诚)魅力亦是助之成功的重要原因。冯友兰先生曾为之感慨道:“雨僧(吴宓字)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在负责文学院时建立了国学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聘到清华作导师。”
不过,对于陈寅恪如何受聘清华一事,又有说法称系蒙梁启超的推荐方果。陈哲三先生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述及此事: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罢,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罢!”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4]
这里有趣的是:梁启超亦搬出陈寅恪“寥寥数百字”的《与妹书》来亮牌晒宝,可见陈《书》在当时学界大腕中的冲击力非同小可,当谓举座皆惊,一片赞誉!只是陈氏到底是由吴宓荐举,还是梁启超举荐,至今难以厘清。或者二者均为陈氏之伯乐,合力举贤(或分先后),这才最终促成陈氏加入清华国学院之盛事吧!
艰难蜕变
1925年3月间,陈寅恪连续收到清华聘书电文及好友吴宓邀入清华的信,既兴奋又犹豫。之所以兴奋是多年异于常人的留学经历终于得到传统社会的认可,从此可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毫无牵挂地专心从事教学与治学;之所以犹豫是如果就此回国,就会中断在柏林大学的深造专研——他在柏林大学待得愈久,愈觉得学海无涯,需要补充的东西太多。
矛盾中的陈寅恪复信委婉地表达了想在德国继续读书两年的意思。4月下旬,吴宓接到来信,心急如焚,急忙又给陈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说信。陈寅恪感动之余,不再犹豫,决定接受聘请,不过却提出欲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采购图书的请求。吴宓接信后就和学校相关领导及部门反复沟通,不断协调,最后校长终于同意预支陈寅恪薪金二千元,预付购书款二千元,后又追加款项二千元……吴宓在等待陈寅恪清华就任一事上,可谓有求必应而仁至义尽了。
陈寅恪在德国收到款项后,让朋友傅斯年、罗家伦等朋友协助,为清华国学院购置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书籍。这些图书为陈以后的教学和治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这是后话。陈寅恪同吴宓一样,也是急公好义之人。他先后共收到吴宓寄来的六千元,除去购书,还慷慨地拿出一部分来接济经济上拮据的傅斯年、罗家伦等朋友。
这样又折腾好几个月,陈寅恪终于启程回国。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1926年2月,陈寅恪抵达上海。这次回国,他除了携带随身行李、所购书籍外,还顺便带回一个活泼乱跳的三岁小男孩,交给尚待闺中的二妹陈新午照顾。这小男孩便是表弟俞大维在柏林与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钢琴教师)同居所生之子俞扬。这俞扬长大后英俊潇洒,在1959年于美国与蒋经国爱女蒋孝章邂逅,迅速坠入爱河,于1960年完婚。他俩尔后育有一子,取名叫俞祖声,与全国政协前主席俞正声同辈,乃叔伯兄弟。而俞大维则于1929年夏天回国,不久便娶陈新午为妻。俞扬也便正南其北地唤新午为“姆妈”(上海话“妈妈”)。
离家虽七年(从1918年底赴美国算起),恍如换人间。此时的陈家已失去当年全家欢聚一堂的风光了:陈寅恪的母亲和长兄去世两年有余,年迈的父亲也患上尿闭症。五次出国,五次归国,显然此次家庭的变故最大,虽称不上是天翻地覆,却可说是沧海桑田。而在陈寅恪身上的变异是:此次归国的他已然成熟了,全然脱去早年的鲁莽和浮躁。
虽然当时学界对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寅恪做导师(按清华《研究院章程》,教授专任指导,即称导师)一事议论不断,但在后者那里,对于如何应对却自是心中有数。回国后,陈寅恪先回杭州悉心照顾生病的散原老人,一直到父亲的身体慢慢好转,才于1926年7月,从容赴北京报到。
陈寅恪到达北京后没有选择直接去清华,而是选择先入住西河沿新宾旅社,想来并不是旅途劳顿这个理由。吴宓则自然心领神会,竟一天中过来探望两次;又于第二天(7月8日)一早赶到旅社,陪陈寅恪到清华园报到。
至此,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终于齐聚清华园,开启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造奇迹之路。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了他们而光芒四射,创办两年后,便令清华学校的声望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北京大学(1898年)和北洋大学(1895年,1951年更名为天津大学)。
陈寅恪初到清华园时,一开始住在工字厅的西客厅,与好友吴宓为邻;9月间,又搬至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住所附近的南院二号。
1926年9月8日,陈寅恪正式开始在国学研究院开课。当时研究院学制为一年,此时已经是第二届了,这届学生有刘节、陆侃如、戴家祥、王力、谢国桢、吴其昌等三十六人。陈寅恪起初开设《金刚经》,后来陆陆续续开设“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课程。陈寅恪初入清华时,在国内大学中尚属“三无”教授(一无博士文凭、二无学术成果、三无任教资历及声望),所开课程和教授方法因冷僻、深奥、难懂,所以一开始选修他课程的学生很少。
所幸陈寅恪与刚刚结识不久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投缘。此时陈垣已经是颇有名声的史学大家,在北京文化圈威望很高。俗话说与德者为邻,品德自高;以尊者为友,必成大家。陈垣经常和陈寅恪通过交谈、通信形式切磋学术问题,并积极向外界推荐他。此外,陈垣还郑重地请陈寅恪为其三本新著写序,加之陈寅恪不断撰写学术文章发表,很快便声名鹊起,甚至可以说后来居上,开始与长他十岁的陈垣并驾齐驱,成为史学界有名的“二陈”。
随着时间的磨合,渐渐地陈寅恪的教学方法开始为学生所接受,他的课也开始越来越受学生欢迎。据他当时的学生姜亮夫回忆,陈老师讲课,会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譬如他讲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有不少话不符合印度原典精神;又说《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么讲法,这种语言怎么说的,那种语言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怎样,一说就能说近十种;并会说出哪些语言在哪些地方是正确的,哪些地方是错误的,哪些地方有出入等等问题,这是他的研究心得。他讲得兴致勃勃,听者则努力认真地听——他的讲话带着明显的长沙口音,需仔细分辨、领会。
与当初刚进清华园的饱受质疑相比,仅一两年之后,陈寅恪的“三无”帽子就已被甩掉了两个,另外一个(博士文凭)也自然遁去——没有人理会,更没有人计较。此时的陈寅恪已经是实至名归的四大导师之一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1928年春,北平(1928年北京改北平特别市)大学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系教授,专讲“佛经翻译文学”(秋季改授“《蒙古源流》研究”)。
随着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尽,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在北平协和医院驾鹤西去,1929年6月赵元任离开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中央研究院之后,尚在清华园的四大导师就仅剩陈寅恪一人了。
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改就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之后他一直在清华大学执教,直至1948年底从南苑机场登机赴沪。他在清华二十二年间,除了讲授佛经和中国西北边地民族文化之外,還独辟蹊径,把中国中古文化、中古文学纳为授课范围,实行了教学与治学上的重大转型。
从1902年至1926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用了整整二十四年时间完成了从“读书种子”到四大导师的艰难蜕变,开启了一代历史学大家辛苦的教书治学、著书立说之路。
1928年春,陈寅恪与一代才女唐筼(字晓莹)相识,7月15日于清华园南院二号订婚,8月31日完婚于上海。时陈寅恪三十九岁,唐筼三十一岁。婚后他俩先后育有三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流求、小彭寓指今中国领土台湾及附属澎湖列岛。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及澎湖等被强行割让给日本(1945年方复归祖国)。陈寅恪及唐筼念念不忘,以此纪侮。
注释:
[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84—285页。
[2]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9页。
[3]陈寅恪:《与妹书》,载《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
[4]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