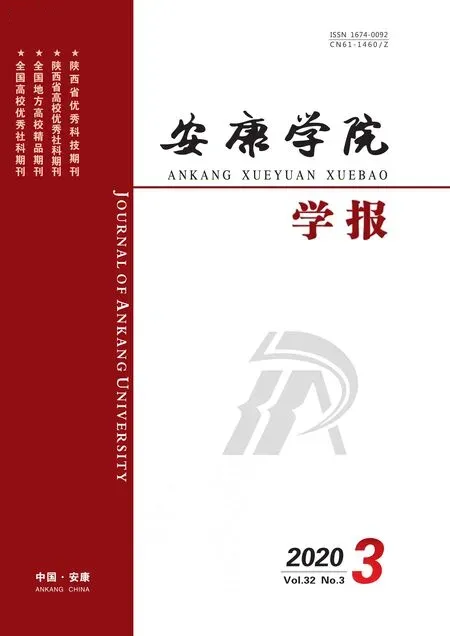“致良知”:从任物之心到即体之心
2020-12-26祁斌斌
祁斌斌
(1.大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8;2.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一、良知在人心
王阳明认为良知在人心上,也在事物上;在人心上求得的良知与在事物上做工夫求得的良知是同一个良知。天下万物、古今万世只一个良知。
(一)天下一个良知
王阳明认为天下只有一个良知。他说: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弊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为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1]168-169
这段话表达了王阳明的一个基本观念:天下万世只有一个良知。首先他认为尧舜之道是道在尧舜身上发端而成尧舜之道。尧舜之道也是孝悌之道;孝悌之道是就人之良知,是在最真切笃厚、不容弊昧处言说道,是尧舜之道。因此尧舜之道、孝悌之道是一个道或良知,只是就尧舜身上或就孝悌上言说道,因而是良知,且是同一个良知。王阳明进一步认为这一个良知无处不在。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举止动静等一切事物(也包括身、心、意、闻见等)上求的那个良知与事亲、从兄上求得的那个良知是同一个良知,只是针对不同的事物言说同一个良知而已。所以在千变万化,以至于不可穷尽的事物上求得的良知都与那事亲、从兄的良知是同一个良知,没有例外和遗漏。所以事亲、从兄的良知就是那尧舜之道,此外再没有其他良知。所以天下万物、古今万世只是那一个良知,这一个良知在人事的最切近处言之,就是事亲、从兄的那个良知,这出的良知最为真切笃实、人人都有、最不容弊昧。这个良知放之四海皆同,施之古今皆一。所以同一个良知在不同的事物上有不同的名称,其实皆是同一个良知。王阳明如是回答他学生关于一个良知的问题。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1]36-37
因此那一个良知在不同的事为上、在不同的境遇中有不同的名字。仁、义、礼、智只是同一个良知在不同事物上的不同的名字。同时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良知,良知又会有不同的称谓,如天、帝、命、性、心等,其实只是一性。这一性,在不同的事为上又有不同的名字。性、命、天、良知、帝等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不同称谓。
良知以心言谓之性,那么在人心上做工夫,会不会遗忘物理?对此,他在致顾璘的信中如是答复: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达之处。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1]95-96
在心上做工夫而遗弃物理,则失却本心,也不知本心为何物,所以“心即理”。外吾心而求物理,理将没有着落,不知理在何方,也不知所求者是什么,所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所在物上做工夫所求得的理即是在人心上做工夫所求得的理,所以“吾心即物理”。物理即是良知。良知以孝亲之心言谓之性;以孝亲之事言谓之理;性即理,皆是良知。心是身之主宰,这是人的最为切近、不应昧之处;就此处说良知,即是性;就事事物物上说良知,即是理。所以人心之理即是天下万物之理,人心实统乎万物之理,无心外之理。求本心而遗物理,不知在心上求个什么!性与理为一;心与理为一。王阳明反对将心与理分开。所以有孝亲之心,就有孝亲之意,就会有孝亲事,当然会有孝亲之理;反之,无孝亲之心,就无孝亲之意,就没有孝亲之事,当然也没有孝亲之理。王阳明认同:“身之主为心”“心是身之主宰”。身之理,即是心之理;心之理也即万事万物之理。理虽然散在万事万物上,实际与心之理为一。所以天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之理即性,以全体恻怛言,即是仁;以其事之宜言之,即是义;以其条理秩序言之就是理。心之理或良知是同一的。
(二)良知在人心
王阳明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在人心,不但圣人,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1]140-141王阳明主张良知在人心,其意图并非说良知在人心里面、良知是主观的且依赖人心而存在,或良知为人心所属;而是强调人心是人最切近、最笃实、最不能弊昧处,是身之主宰,人应该首先在人心上做工夫求良知,在一念发动处做工夫求良知。当人心无物欲牵蔽、不牵绊于私己之身,即是良知的发用流行。他进一步说:“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1]258意有善恶,人应该在意上做诚意格物的功夫,所以知善知恶是良知。“指心之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1]180从中可知,意为心之动,意是有善有恶的,知意之善恶即是意之灵明处或良知。这表明良知也在人心,人应该在人心上做工夫来求得良知。所以王阳明说“心即理也”。
1.良知在意、知、闻见、知觉等上面
意、知、闻见、知觉等是人心之动,良知在它们上面。王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269人心有知觉思虑,良知或“知”是心或知觉思虑的本体,合乎理智的视听闻见知觉活动都是良知的发用,良知也在它们上面。“人心之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著实用功。”[1]273良知离不开闻见知觉。
人心自然会知,自然知得是非,良知也在认知活动中存在。“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1]15-16良知落在见父上即是孝,人自然知得父当孝;落在见兄上即是弟,人自然知得兄当弟;落在思虑上即是知或思无邪,人心思虑自然要正,等等。
2.良知在人情上
陆澄曾就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这一观点问于王阳明,王阳明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1]36喜、怒、哀、乐等情感形式也是心感于物而动的表现,良知也在这些人情上面。《中庸》中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14这表明未发之中和已发之和皆落在人心上。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3]69恻隐、羞恶等是人情,仁义礼等就在它们上面发端显现或发用流行。
有人情就有良知在其上。王阳明在答学生书信中问题时否定了人情可以外于良知而存在。他说:
“来书云:‘尝试于心,喜、怒、忧、惧之感发也,虽动气之极,而吾心良知一觉,即罔然消阻,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后,然则良知常若居优间无事之地而为主,于喜、怒、忧、惧若不與焉者,何与?’
知此,则知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而有发而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谓‘良知常若居于忧间无事之地’,语尚有病。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1]134
这段问答中他的学生肯定了良知离不开喜、怒、忧、惧,但却怀疑在无事时,或无喜、怒、忧、惧时,良知与喜、怒、忧、惧没有关系了。这疑惑可理解为良知可以离开喜、怒、忧、惧。王阳明对此的回答是良知不滞于喜、怒、忧、惧,喜、怒、忧、惧也未曾离开良知,或外于良知。
二、良知未曾离却事物
良知在人心,良知工夫也在人心上。道心没有离开事事物物,“心外无物”。人不能外人心而求物理,也不能外物理而知人心。
(一)意之所在便是物
王阳明说“心外无物”。“物”自然成了心的活动内容,这一心的活动被王阳明称为“意”。心的活动的显现或外化即人的行为活动是心之所在,即可称为“物”“事”或“行”。心之所在即是物,无心外之物。正如王阳明所说:有孝亲之心,就有孝亲之意;有孝亲之意,就有孝亲之事;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意;无孝亲之意,即无孝亲之事。意必有物。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13-14
“意”的活动同时也是“行”的活动时,“意”之所在即是“行”的活动,行的活动便是“物”或“事”。如“意”落在君上,事君即是一物;意落在爱物、仁民等上面,爱物、仁民即是一事或一物。笼统言之,心的活动同时意味着的那个“行”的活动可以称为“物”。
(二)万物一体之仁
王阳明主张“万物一体之仁”。其宗旨是在工夫上说本体,即良知工夫离不开万物。人的最本己处、最真切笃实处,也是事物,人应当在这些最真实切己的事物上做工夫。仁即是人的最本己切近的事物之理,即孝亲之仁。万物非本体,但万物不离本体,本体不离万物,万物本体一也,万物一体。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之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执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1]230-231
仁是良知在事亲上而言的,事亲是良知的真切笃实处,是良知最本己之处。上面谈到天下一个良知,万物之理也只是一个仁。所谓万物一体之仁。它意在强调良知工夫离不开万事万物,人首先应当于最本己处做工夫,即在事亲上做工夫,在此处致得良知和在万事万物上致得良知是同一的。为了进一步强调万物一体,他补充说道: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执事非为体。”[1]232
耳目口鼻心非没有本体,王阳明认为人不应该只在一事一物上做工夫,应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让人在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不要离开万物而求本体,不要离开工夫而求本体。所以他曾说,万物无体,以心为体,心外无物。
面对“万物一体”的观念,有学生对它表示怀疑且问道:
“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
先生曰:“你只是在感应之机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1]277
王阳明批判了学生的看法,认为学生只是着心在具体的事物形态上看问题,所以万物个个不同,更不可能同体了。从求良知的角度看,人若不局限于在身上求良知,也可以在万事万物上求良知,那么将人心与物同体。他让学生在良知发用上、天理流行上看万事万物,万物自然与人同体。如果在良知发用上、在天理流行上看问题,岂但禽、兽、草、木与人同体,鬼神也与人同体了,万物一体之仁,无有例外。
三、人心任物
人心常常不好于道,而趋于物。《论语》中说:“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4]“意之所在即是物”也表明人心任物,“意”为任物之心,并且执迷于物。同样“心外无物”可以理解为心驰于物、人心在物。“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常人往往肆情纵欲,驰游于物,昧良知而行,不能合理中节,不求取良知,放其心而不知求,所谓心任物而行。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3]289-290人之所行所由本是有道的,但人放其心,驰游于物、恣情从欲,而不自归于良知。《中庸》说:“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2]17“罟擭陷阱”可以理解为人痴迷于情欲、陷溺其心于事事物物中,而不求取本心或良知。即使一时求得良知也不能持守住永固,结果还是放心于情欲、物欲之中,而不能知觉。总之人常陷溺其心于私欲、闻见、任心于物、从而失却本心。所以有学生问王阳明。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要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皆不得其职。”[1]51
王阳明认为心要像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持守良知天理,不使心著在物上或让心去逐物,这样才能心统五官,天下乃得治于人君。
任物之心不合于道。《中庸》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2]16道之不行在于人心有过与不及,即不合道理、任心于物、放心于情。“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2]6心逐于闻见知觉、声色货利,失道而不正。这必然会于视中不见道,于听中不见理,心流于物、逐于闻见。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有放失,留滞于情欲,任由情欲支配摆布,不归于正。
(一)人心任情肆欲
情感和欲望是人心的表现,但情欲往往会过度。王阳明说:“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1]41七情所过,即是人心任情肆欲。
人心昏蔽不明也是人心任物的一个结果或表现。王阳明说:“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1]130-131人心常常昏蔽于物欲,不能知觉良知之明,故须学以去人心之昏蔽,以复良知之明。
二程子分析人心逐物的原因,即流于私欲或囿于私心。“……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硛,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1]122-123人情所蔽,即人情所过,是人心流于私欲的表现;用智则人执物象,心著于影象,自然放心于物象,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总之不之于理而流于物,这是人心昏蔽的原因所在。
正如王阳明所说,天理之心本来是廓然大公、纯洁无私的,但人往往痴心于情,任情于己,自私用智,足己所欲,心驰于物,从而使天理之心遭受蒙蔽。《乐记》中的“人化物”也表达了人心任物的观念。
《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5]
从中可以看出,天理之心感于物是性之欲,人的欲望得到合理节制。但在好恶没有得到节制,任由人心驰游物上,从而暗蔽天理之心,所谓“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也就化为物了。
人心任由情感或外物驱使,将会昏蔽人心、掩盖天理,人将沦为禽兽,从而物至而人化为物。
(二)人心易逐名利
人心要逐物,好名、好色、好利等都是功利心,是人心逐外任物的表现。王阳明认为这些都是为学求良知的“大病”。这样的“大病”入人心之深,传播之广,且危害极大。“为学大病在好名。”[1]69“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1]18“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1]19所以一朋友问王阳明:
“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的人,过了十年,亦还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1]233
可见好名好色好货等功利心之深重,非一番彻骨工夫不能除“大病”。王阳明指出它们的根子在人心上,这些都是人心任物之表现。
王阳明说:“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1]163人心流于功名利禄,日甚一日,三代之道欲挽而难复,圣贤之学日益而道日亡,可见人放其心之甚。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书者有以启之。”[1]18-19人执于己见,囿于己闻,自私用智,执著于物,修词饰文,流心于物。
四、致良知:从任物之心到即体之心
王阳明在回答学生关于“生之谓性”的问题时说:“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1]209这表明,凡人任意行、任意言,仍是性中之事、道中之事,只是没有抓住头脑,因而依旧执著在物上。若能掌握头脑,任意行,任意言,任物之心仍旧是即体之心。所以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因此良知的工夫仍旧在任意的言行上面,若晓得头脑依良知出来,言行自然合理停当。没有言行举止等事物作为工夫,性就会空乏无实而不真切;没有头脑拟或良知,言行举止等就会任意行止,产生过差。良知未曾离却事物,应该于任物之心上做求良知的工夫,从而求取即体之心或良知。
孟子尝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254言下之意是人心常常放失于物。情欲、私意、人欲、闻见、执著于事物等等即是放心或任物之心的表现。要求良知存天理就要在放心上、在任物之心上做工夫,即求放心、从任于物之心走向即体之心。所以王阳明说:“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1]50人心是人最为本己、切近之处,即任物之心;于此处做求良知工夫,自然尽得天理。
良知工夫离不开人心和万物,在任物之心上做致良知的工夫即可求得即体之心。
(一)人要在事物上做工夫
王阳明说: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1]16
这表明要求良知或天理,人应该在事事物物上做求良知的工夫,事事物物即是良知发见处,人就在那上面学存天理。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1]152“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它们表明心、或意或知不在天理上、不在心之本体或良知上面,而流于良知发见上或流在“物”上。因此心首先是任物之心或“放心”,意首先是任物之意,知首先是任物之知,从而导致心不正,意不诚,知不知,故而在“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做求良知的工夫,即在任物之心上做求良知工夫。
所以阳明反对佛家和老子学说抛却事物、人伦和日用常行在而虚无空寂上做工夫。这样的结果会使心沉空守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3]167仁之实、义之实、智之实、礼之实、是仁义礼智的发用或见端处,当然也是人求仁义礼智的工夫所在,即致良知之所在。良知工夫在事事物物上。《中庸》也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2]19-20这表明,求子之道,在于事父;求臣之道在于事君;求弟之道,在于从兄;求朋友之道,在于先施,人需要在事物上致良知。
(二)人要在心上做工夫
人首先应该在心上做工夫。但人心上的工夫不只是个守静和心中无事的工夫。还应该在意、知、闻见、思虑等观念活动及情感上做工夫,甚至也要在闲思虑上做工夫。《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14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认识到,不睹、不闻、隐、微、未发、中、独等都是在心上言,人应该在心上做工夫求良知,所以君子要慎其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道不可须臾离于心。如果心离开道,即为物,成为任物之心而非道心。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问:“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弊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8
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人应该在心上做工夫求天理,不是要到心外求天理。因为无心外之理,也无心外之事。
1.在意上做工夫
“意之所在即是物”表明,“意”是任物之心,故而须要在“意”上做工夫求良知。王阳明说:“意未有悬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弊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工夫。”[1]180“意”必著事物,是指“意之所在即是物”。言下之意就是“意”也是任物之心,“意”会流于“物”,于是“‘诚意’者,诚其物之意”[1]152,这要求人应该在“物之意”上做工夫王阳明认为意是有善恶的,所谓“有善有恶意之动”。因为意可能会流向私欲,所以意有善恶。人应该在意之所著处,即在物上做诚意工夫。诚意就应该是无自欺的,心不著于己、不流于私,而廓然大公合于事理物宜。“意”有善恶的问题实质是“意”从己身出发还是从天理物宜出发。“意”如果从自己出发自然流于私意,诚意自然变成去除私意,之所以诚意为去除私意,是因为“意之所在即是物”,人心任物,故须格物诚意。
2.在情欲上做工夫
既言情,它往往是已经发了;既已发,情往往过而无不及,情也是任物之心的表现。情最好不要发;已发之情已经是有所偏颇了,但发要中节。所以古人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14因此情既已发,须要在其上做工夫,这工夫可以是未发的工夫,也可以是已发的工夫。总之,须要在情上做工夫。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著,七情有著,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弊,然才有著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弊去,复其本体矣。”[1]240
王阳明认为情为人心本有,但应该从情上认得良知明白,在情上做良知工夫。他用日譬喻良知,用云翳譬喻情欲;当云翳四塞时,蔽日无隙,不可谓良知是无,只是人心纵于情欲。当七情顺良知之自然时流行,它们即是良知的妙用。因此人不可以执著于情;人心执著于情,人心任情便会流于私情,便是欲,这样会暗蔽良知天理。当情欲遮蔽良知此时,人应该于情欲处复其良知本体,勿使情欲过当或不“中和”。所以王阳明说“‘正心’者,正其物之心”[1]152,即要求人在情欲上做工夫使人心归于中和、中正,以复其本体。
3.在知觉闻见上做工夫
王阳明说:“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著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落实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检防,而真性自不息。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1]273人应该在闻见知觉上做致良知的工夫,无法在不睹不闻做良知工夫,于有睹有闻上求其不睹不闻,这样做才能求得良知本体,不为闻见所累;否则工夫无法落实,人心仍旧任物、驱驰于闻见知觉而累其心。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弊,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1]272
这段话表明致良知应该在闻见知觉上做工夫,这样人才不为闻见知觉所累。人于闻见知觉上致得良知,闻见知觉亦是良知之流行发用。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任物之心和即体之心本是一心,只要人在日常行事作为中,念念不忘良知,以求意、知、欲、事等合于天理,无私意私欲间杂其间,任物之心即是即体之心,就如顿悟成佛一般,刹那间私欲殆尽即是良知。
五、结语
总之,王阳明说天下一个良知时是从本体说工夫,即要在万事万物身上做致良知工夫。良知在人心上,人离不开事和物,意之所在即是物,人心往往追逐物欲和情欲,因此做致良知工夫即是在意上做、在心上做,也即在物上做。心外无物,人须有格物诚意工夫才能求得良知。因此致良知即是在意、闻、知、见上做格物诚意功夫,即是从任物之心走向即体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