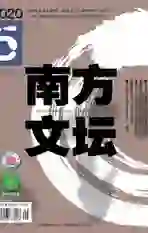田汉的桂林时间
2020-12-24黄伟林
根据张向华编《田汉年谱》,1939年4月20日,田汉率领平剧宣传队抵达桂林,这是田汉首次到桂林,这一次田汉在桂林停留了五个月,直到9月21日,才率领平剧宣传队离开桂林。1940年2月至3月,田汉有昆仑关之行,往返经过桂林,皆有短暂停留。1940年5月,田汉由长沙到重庆,19日途经桂林,当天离开。1941年8月23日,田汉携母亲、弟弟和女儿一起由衡阳到桂林,这次到桂林停留时间较长,超过三年,直至1944年9月上旬才根据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出的第二次疏散令,与安娥一起离开桂林。
严格说来,整个抗战时期,田汉虽然多次出入桂林,但在桂林停留的时间总共也就三年多。三年多时间对一个人的一生而言并不长,但桂林的三年多时间,在田汉的生命历程却格外重要。桂林时期,田汉创作了多部重要的戏曲作品,实现了从话剧到戏曲的战略转移;记录了大量抗战戏剧信史,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戏剧事业观念;从精神到物质上支持了多个戏剧团体,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戏剧领导人的地位。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对田汉的桂林时期进行论述。
一、从话剧到戏曲的战略转移
根据董健的研究,1937年开始,田汉在话剧创作上出现了颓势,在传统戏曲中找到了新的生路,启动了旧剧改革运动,开始了艺术上的战略转移①。董健统计田汉在抗战八年期间共写了14部戏曲,《明末遗恨》《杀宫》《土桥之战》《新雁门关》《旅伴》《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岳飞》《双忠记》《新会缘桥》《武松》《金钵记》《武则天》《情探》,其中《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双忠记》《新会缘桥》《武松》《金钵记》《武则天》七部皆在桂林所写②。董健认为,抗战时期田汉戏曲创作收获之大,为任何一位中国现代剧作家所不及。田汉本人1941年12月25日在写给漫铎的信中也表示,“近来于话剧工作外,仍以余力策动旧剧改革运动之复兴”。而田汉的工作当时就受到了同行的关注,漫铎的评价是:“看您的《新儿女英雄传》感到中国旧戏有一个新的前途。民族形式论争的结果,在京戏这一部门您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榜样。莎翁初期的剧作在您这里也嗅到同一的气息。”③
田汉不仅通过剧本创作策动“旧剧改革运动之复兴”,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精神上甚至物质支持上曾挑过一个重担”④,这个重担是什么?他自己说“担子的一边是由平剧宣传队一部旧队员编成的文艺歌剧团,一边是大体由抗剧各队同志陆续汇聚而成的新中国剧团”⑤。根据田汉的说法,文艺歌剧团在桂林曾有三个月的时间,其给养及其一切费用,皆由田汉这个清寒的文士独立支持。“每天早晨我常常在睡梦中就為着筹这团体的伙食而发抖。我自己为戏剧改革焦头烂额固属应该,连许多熟识的朋友如章东岩、张云乔诸兄都被我拖累不堪,那时还住在月牙山的巨赞法师也代我借过五百元,沫若兄由重庆寄来贺我母亲生日的五百元也给他们吃掉了。”⑥田汉这番话是1942年春天说的,事实上,桂林时期,他不仅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了平剧宣传队的后身文艺歌剧团,而且,他还支持了中兴湘剧团和四维平剧社。也就是说,桂林时期,田汉在精神和物质上共支持了三个戏曲团体。对此,董健在《田汉评传》中有详细记述⑦。
从侧重话剧创作到侧重戏曲创作,这是田汉戏剧生涯的“战略转移”。这个战略转移是在桂林时期完成的。董健探讨了促成这个战略转移的原因,他认为共有六点,大意为:第一,田汉从小受到传统戏曲的熏陶,他的艺术细胞中有很多传统戏曲的基因;第二,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传统戏曲包含着强烈的民族精神;第三,广大中国老百姓有着对戏曲的爱好和欣赏习惯;第四,田汉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柢;第五,田汉在话剧创作上出现了颓势,需要开辟戏剧创作新路;第六,战争为田汉重新组织旧艺人提供了机会⑧。这六点原因总结得很好,但有一点董健先生有所忽略,那就是进入全面抗战以后,田汉对中国传统戏曲形成了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与抗战的功利目的有关,而且与田汉的民族意识有关。如果说话剧是田汉等中国戏剧家20世纪引进中国的戏剧形式,那么,戏曲则是千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成出来的戏剧形式;如果说话剧对于20世纪的中国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和时代性,那么,戏曲对于20世纪的中国则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1942年4月1日、7日、13日,田汉在桂林《扫荡报》发表了题为《岩下纵谈——艺人的行路难》的连载文章,这篇文章的开头,出现了这样一段话:“地方戏剧艺术,小之代表一地方的文物,大之代表一国的神明,此类工作原应由地方政府或文化机关来主持。无奈今日戏剧的一般处境,维持其存在已经不容易,谈不到被提倡保护的话。”⑨这段话是针对九如湘剧团当时的情状而说的。如果换成今天的语言,可以这样表述:中国的地方戏曲,小的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物,大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它们必须得到保护和传承。将地方戏剧艺术(即戏曲)上升到地方文物和国家神明的高度,这是田汉戏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高度重视,而田汉在桂林已经对戏剧作为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客观地说,这种认识与当时田汉的身份也有关系,作为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掌管全国的艺术宣传,使田汉开始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思考戏剧艺术。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创作行为的转变,从此,田汉的戏剧生涯发生了如董健所说的战略转移,即从话剧创作为主转为戏曲创作为主,而且,这个转变并非局限于战争时期,而是延续田汉整个后半生。而田汉这个战略转移,确实是在桂林发生并实现的。
为什么田汉这个传统戏曲创作和改革的战略转移是在桂林发生并实现?首先,这与当时桂林浓郁的传统戏曲文化氛围有关。在田汉入桂之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马君武已经在桂林启动了桂剧改革,欧阳予倩也为桂剧改革提供了实验性作品,也就是说,田汉入桂前后,桂林已经营造了很好的传统戏曲改革环境。1939年4月,田汉带领平剧宣传队到达桂林,得到马君武的隆重欢迎。在桂林期间,平剧宣传队上演了田汉的《新雁门关》,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对田汉戏曲创作的重要激励。因此,在首次入桂的五个月中,田汉住在榕湖南岸五美园的一座小楼里,完成了两部大型京剧剧本《新儿女英雄传》和《江汉渔歌》,作为平剧宣传队桂林第二期公演的两台重头戏隆重推出,获得了热烈的演出反响。其次,桂林本身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经有过抗元、抗清的经历,特别是明末瞿式耜、张同敞力抗清兵身殉桂林的故事在桂林长期流传,这种历史文化积淀为田汉的戏曲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田汉曾就瞿张二公的事迹写了京剧《双忠记》。该剧由田汉支持的文艺歌剧团演出,得到桂林名宿以鹤笙、龙积之的赞扬,为文艺歌剧团带来了一点收入⑩。
二、记录抗战戏剧信史
1941年,还在南岳的时候,田汉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抗战戏剧运动应该留下一些精确的记录,为自己,为战友,为后继者”11。从而开始了《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的撰写。这是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应该是田汉在南岳的时候开始动笔的,文章有这样的文字:“我想趁这南岳侍养的期间,把这个报告整理一番,交给《戏剧春秋》广泛地圡教于贤明的公众。”12但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应该很大,田汉在南岳的时间是1941年上半年,文章内容写到了1942年,可见,该文后半部分的内容是1942年写的,而田汉1941年8月已经开始旅居桂林。这篇文章分三章:抗战戏剧组织工作的一个小段落、就剧运全般的五点建议和抗战话剧报告。这篇长文最初刊载于《戏剧春秋》第一卷第六期、第二卷第二期、第二卷第三期,只刊登了全文的一、二两章和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三章列有目录,共七节,这七节的标题分别是:1.从上海救亡演剧队说起;2.抗战演剧队之编成及其工作;3.抗敌宣传队的戏剧活动;4.儿童剧团的收编;5.关于各剧队生活教育改善及工作展开的几点要求;6.从抗敌演剧队到戏剧宣传队;7.对话剧工作者的五点请求。《戏剧春秋》只刊登了第一二节,第二节《抗战演剧队之编成及其工作》篇幅庞大,内容是对各个演剧队的介绍,目前已有的是抗敌演剧队第一队、抗敌演剧第三队、抗敌演剧第四队。按照这个内容,当时有十多个抗敌演剧队,田汉应该逐一介绍,仅此一节,至少还可以写几万字,但田汉后来并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构架,仅仅写到抗敌演剧第四队就中止了。
文章中,田汉写道:
兹将其分发后工作经过及其宝贵经验尽手边随时所能搜集之材料,或与各队队长及主要队员谈话之结果,列记于次。其中第六第十两队,以一在苏鲁战区,一久在河南,工作人员不易晤面,消息亦时断时结,语焉不详,殊为恨事。则望两队旧人及各队同志补充,使成抗战剧运信史。13
虽然田汉没有完成这篇足以写成一本书的长文,但哪怕就是这篇文章,也已经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抗战戏剧史料。比如,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表格,将十三个上海救亡演剧队的领导人、活动路线、经过概况一一作了精确的陈述,第二节则对抗敌演剧第一队、第三队、第四队的发展过程、工作历史作为详尽的叙述。可以想象,若不是田汉在1942年即发表了这篇长文,多年以来,哪怕是当事人,回忆这段历史时也会失去这样一个既提纲挈领又周详细致的参照系,而难以保持历史叙事的精准度。
诚如《田汉年表简编》所言,“《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抗战演剧队之编成及其工作》等文,均为现代戏剧史这重要文献”14。《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确实记录了极其珍贵的抗战戏剧历史。比如,为了描写演剧一、二队的发展过程,田汉回顾了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的工作史。仅这个演剧队名称的更换,就令人眼花缭乱,若不是田汉深度参与了这段戏剧历史,他也难以理清其中的脉络。
到桂林后,田汉不仅继续《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一文的撰写,而且投入了具体的戏剧活动,写剧本、带剧社,如其所说,从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推动桂林的戏剧活动,即使如此,田汉为抗战戏剧运动写信史的念头仍然没有消失,他虽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戏剧和话剧的创作,但在《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一文之外,他还是撰写了一批仍然可以称为“信史”的文章,如《双十节·戏剧节》《烽火里来的声音——介绍抗敌演剧队》《关于演剧七队及其新歌剧——他们是怎样战斗过来的》《希望与珍重——迎“新中国”诸同志》《抗战戏剧第七年——说几个故事》《戏剧节与西南剧展》《病與朋友》《枪毙“疏忽”来追悼保罗的死》《序〈愁城记〉》《岩下纵谈——艺人的行路难》《岩下纵谈——艺人的行路难(续)》,这批文章虽然不像《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那样系统,但组合起来,同样构成了抗战戏剧历史的记录。
《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重点记叙抗敌演剧第一队的历史,《关于演剧七队及其新歌剧——他们是怎样战斗过来的》重点记叙演剧七队的历史,演剧七队的前身是抗敌宣传第一队,隶属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由于工作成绩好,又正好在七战区工作,当原来的演剧第七队改编成后,抗敌宣传第一队就袭用了演剧七队的番号,武汉撤退时,该队到长沙,参与了长沙大火的救灾工作,于1938年12月18日到了桂林,曾在桂林中南路口出了一张大壁报,面积超过十八张普通报纸,每次观者如堵,1939年3月出发到南宁、防城、钦县、东兴等地进行宣传工作,步行两千多里,还参与了1939年11月桂南战事的战地宣传工作,桂南战事结束后,他们在湘桂铁路沿线做流动演出,回到桂林后,舞蹈家吴晓邦、戏剧家焦菊隐都曾为他们导演作品。15
值得注意的还有《岩下纵谈》系列散文。以《岩下纵谈》为标题,田汉共写了三篇文章:《艺人的行路难》《艺人的行路难(续)》《孩子的行路难》。其中《艺人的行路难》主要写了4个戏剧团队:九如湘剧团、华侨马戏团、文艺歌剧团和新中国剧社。
《艺人的行路难》,顾名思义,写的就是抗战时期艺术工作者的艰难岁月。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写了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吴绍芝、徐绍清、彭菊生、欧元霞、徐初云等人在桂林的生活。文章写道:“他们不仅没有菜吃,甚至两个礼拜不沾盐水。徐初云先生那样在湘剧净行可以说是湖南‘省宝的人手上长了一个疔疮,终日痛苦至于泪下,但找外科医生诊察的钱都没有。欧元霞、吴绍芝这些湖南代表的名角,每天也只能吃两顿稀饭。”16文章第二部分写的是华侨马戏团,在作者笔下,华侨马戏团表演的虽然名为马戏,但因为贫困,团队连一个匹马都没有了,演的都是人戏,这些人戏都是演员们多年训练的“绝活”,很精绝也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如表演《飞人》的女演员王陶英,就在练习时从钢丝上摔下死亡,以至于田汉发出如此感叹:“我们享受艺人的绝活为这惊奇骇目的时候,艺人们却每一秒钟都在拼着性命!”17文艺歌剧团是根据陈诚的嘱托组织的,有军方的支持,然而战争期间交通不便,也经常有断炊的时候,田汉写道:“他们从郑亦秋君起几个月拿不到最低的生活费,他们的儿女,啼饥号寒之外还疮疥满身。”18
田汉这些关注艺人疾苦的文章,不仅在今天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戏剧文献,而且在当时解决了相关团队暂时的无米之炊。比如《艺人的行路难》一文发表后,远在湖北恩施的演剧九队与平剧团看到了,就联合义演获得八千多元义款,全数寄给了新中国剧社,解除他们的艰困19。
在熟悉的各个戏剧团队中,田汉最欣赏的是新中国剧社。桂林时期,他写了《希望与珍重——迎“新中国”诸同志》,记述了新中国剧社在湖南的旅行公演,《艺人的行路难》虽然不是专门写中国剧社,但重点介绍了新中国剧社的情况,离开桂林后,他还写过《“新中国”是怎样奋斗出来的?——在昆明文协欢迎会的演词》等文。这些文章成为新中国剧社奋斗历程的完整叙述。
三、反思从事戏剧事业的初心
新中国剧社是原来国防艺术社社长李文钊发起成立的一个民间戏剧团体。成立之后,由于原来的股东撤出,李文钊倾尽家财,终于无法在经济上维持新中国剧社的运转,只好退出新中国剧社,新中国剧社因此成为一个由社员自主自理的职业剧团。
如前所述,田汉从精神到物质上支持了这个剧团。
正是在与新中国剧社相濡以沫的过程中,田汉发现了这样一个民间职业剧团的新的品质、新的性质。他认为,“新中国剧社是一个把中国戏剧文化启蒙运动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的团体”。“新中国剧社是唯一的人民剧团,介在军方和省方两大剧团之间,和人们维持着友好关系。”20
1943年,新中国剧社从湖南旅行演出回到桂林,田汉在与他们的深度交流中,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戏剧事业观念,在《希望与珍重——迎“新中国”诸同志》一文中做了初步的表述。
他提出了四点看法:一是强调要弄明白为什么从事戏剧事业;二是希望戏剧人以社会为学校,从社会找老师;三是主张戏剧和时代紧密结合,面向瞬息万变的现实,及时准确地反映现实;四是保障戏剧人的身体健康21。
他说:
我们为什么在干戏,为什么不怕饥寒,不畏艰苦困难地干戏?这就是我所谓“招魂”的问题。现在因为缺少这种灵魂才会在艰苦前低头,才会各顾私利,各逞物欲,破坏剧人应有之高尚品性和情操。唯一挽救颓风的方法是每天大家以志节自勉,大家来招魂,否则物质条件丰富也不可靠。少青团等的崩溃分裂、留桂剧人的挫败,演剧团队某些工作同志首先上的颠落,都是可怕的榜样。22
“招魂”是田汉于抗战后期乃至胜利之后反复提出的概念,在《抗战戏剧第七年——说几个故事》一文中,开篇小标题就是“先招一招武汉时代的魂”,为什么要招武汉时代的魂,因为武汉时代是全民抗战的时代,但到了抗战后期,那种宝贵的热情消歇了,田汉分析这种情形并提出招魂的解决办法:
今日戏剧界似乎又回到以前人自为战的时代。由于客观环境的困难,大都急急于自身利害的关心和枝节技术的追求,把抗战初期的宝贵的热情大部分消歇了,甚至艺术上一些应有的新认识也渐次把握不定了。应当说而不说,或争其所不必争,乌烟瘴气代之而兴。私心十分忧虑,也曾在一部戏剧工作者中提起招魂运动的口号,意思是大家重新振作起抗战初期的雄大旺盛的意气和企图心,然后剧运的发展才可重入正轨,技术上的某些成就才更有光辉和意义,戏剧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才结合得更紧。23
从当时的情况看,田汉的“招魂”主张并没有“一呼百应”,甚至有人泼冷水,认为人心已死,招魂谈何容易24。但田汉不是那种半途而废的人,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招魂”口号,而且在现实里发动“招魂”运动。事实上,几乎在他提出“招魂”口号的同时,他就参与了西南剧展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试图以西南剧展来重振剧人的士气。
甚至抗战胜利以后,田汉还写过以《招魂》为题的文章,文章中回忆了他提出“招魂”口号的情境,说明了招魂的内涵:
在桂林,我曾对戏剧工作同志们提出“招魂”的口号,那是因抗战进入后期,中国丑恶现实暴露日甚,常不免使志士寒心。抗战工作愈益艰苦,抗战情绪愈益低落,就在戏剧圈子里,抗战初期那种不顾一切效忠运动的高度热情已经不易看见,而开始着眼于物质待遇。剧目选择也准此而着重于商业价值,不必针对现实。这一种倾向原是政治低潮必然的现象。大的方面受了阻碍,势必驱使许多人钻小圈子。但这种逆流不加阻止又势必影响剧运发展,那是说戏剧工作曾经被认为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一翼,于今大家若把运动忘了,戏剧将从它正常的轨道颠落下来,而成为演剧工作者们单纯的生活手段,就是单指着戏剧吃饭。政治性教育性被忽视,技术性娱乐性被强调,戏剧将急遽地走向庸俗化商业化的道路,重复袁世凯称帝之后“文明新戏”变质的悲剧。这不是“忋人忧天”而是“势所必至”。所以我觉得该及时地来一个招魂运动。让我们把有过光辉历史的中国戏剧运动重复扶上正轨,一时一刻也不让它和现实脱节。这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把这口号向朋友们大声疾呼。今年戏剧节日在重庆,我也重复过这样的呼号,想把中国剧运史上忠勇坚贞、效忠民族解放、不屈于暴力及物欲的灵魂给招转来——魂兮归来,反故居些。25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招魂”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口号,田汉是从较长久的时间坐标、较宽广的观察视角,提出戏剧运动的“招魂”主张的。
田汉在桂林生活的时间大致为1939—1944年。这个时期,中国的全面抗战从最初的激情洋溢进入了相持的各种纠结,万众一心的场面也逐渐转变为各自为阵的局势。全面抗战期间,田汉经历了武汉时期的高亢、重庆时期的冷峻、南岳时期的疏离,恰恰是桂林时期,田汉在与多个新旧戏剧团队的共同奋斗过程中,形成了对戏剧事业新的认识,这里既有戏剧与时代结合、与社会结合的思考,也有戏剧人的生活保障、身体健康的关怀,这些都是戏剧事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在这种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之外,田汉也形成了一种较为超越的视角,正是因为建构了这种超越的视角,田汉才会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为抗战戏剧事业撰写信史,才会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戏剧的“招魂”运动。1944年,田汉与欧阳予倩、瞿白音等共同发起了西南剧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南剧展是一个包括戏剧展演、戏剧资料展览、戏剧工作者大会的大型戏剧活动,如果说戏剧展演是当时西南戏剧运动的现实呈现,那么,戏剧资料展览则是抗战十三年中国戏剧运动的历史呈现,戏剧工作者大会是中国戏剧工作者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思想激荡。西南剧展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这个创举,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田汉、欧阳予倩这些中国现代戏剧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们对中国现代戏剧历史的反思、现状的把握和未来的引领。
2019年8月于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
【注释】
①②⑦⑧24董健《田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405-411、438、439-447、406-408、450页。
③《致漫铎》,见《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90-91页。
④⑤⑥⑨16171819《岩下纵谈——艺人的行路难》,见《田汉全集》第1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77、577、578、571、571、576、579、585页。
⑩《新中国剧社的苦斗与西南剧运》,见《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18页。
11121315《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见《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81、381、395、457-461页。
14《田汉年表简编》,见《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99页。
20《“新中国”是怎样奋斗出来的?——在昆明文协欢迎会的演词》,见《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10页。
2122《希望与珍重——迎“新中国”诸同志》,见《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475-476、475页。
23《抗戰戏剧第七年——说几个故事》,见《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479页。
25《招魂》,见《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76-577页。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学编年史”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