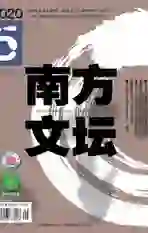理性之光:张爱玲与毛姆比较论
2020-12-24张龙云
张爱玲推崇天才论,论者也不断推举她为天才,但真要人相信她完全横空出世,这在21世纪的今天究竟难以服人。张爱玲究竟如何开启了自己的现代文学写作之路?她的现代写作资源究竟出自何处?因此值得深究。
张爱玲熟知中国古典文学,她的现代写作吸纳了某些古典写作资源,但整体而言这种古典资源并非决定性的:在时间和性质上,张爱玲的写作都只能是现代文学,而不是古典文学的延续——即便如此熟悉传统小说的鲁迅也坦然承认,自己是读了外来翻译的作品才开始(现代)小说写作的①。此外,张爱玲最初创作与其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关系亲密,周瘦鹃曾极力推举张爱玲。不过,这种貌似同路人的关系,起初大致是鸳蝴派作家满心欢喜的误认。在张爱玲这边,大概只是作为初入道者怀着应有的谦卑,且乐得接受这种误认。这也许正是主流文学史不得不将她置入“雅俗”模式中的难处所在:她有俗文学的某些特征,但俗文学却无法定义她。再次,张爱玲因为(在后来的主流文学史划定的时间意义上的)晚出,似乎理应在其时现代文学作家群中接受某种师承或认同某种风格。吊诡的是,晚出的张爱玲不是人生/社会现实派,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乡土中国,也不是主观抒情的自叙传,甚至不是都市新感觉派——虽然她多数时候身处都市。
总之,张爱玲需要一个新的参照物。
一、故事与技艺
英国作家毛姆正是这样一个新的参照物。
其实,将毛姆作为审视张爱玲写作的参照,不算什么新鲜的发现,这几乎可以追溯到张爱玲成名之初。早期鸳蝴派代表人物周瘦鹃读完《沉香屑》,当即感觉:“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m 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对此“心悦诚服”②。胞弟张子静更进一步佐证:“《红楼梦》跟Somerthet Maugham写的东西她顶爱看。”③直到1980年代,张爱玲致庄信正的信中还在表达这种喜爱:“收到毛姆传,来得正是时候,喜从天降,连照片都精彩,张张看了又看。”④后来夏志清也发现:如果《沉香屑》一开始用英文写就,“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毛姆(W.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作品。”⑤这是从张爱玲看毛姆。反过来,如果从毛姆看张爱玲,几乎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如此相近,以至于熟悉张爱玲写作的人,阅读毛姆英文小说原作比如The Painted Veil(中译名《面纱》)特别是小说前半部分时,恐怕也忍不住误认为是张爱玲手笔。
他们之间究竟哪里相似?最显眼因此最容易被论列的是写作技巧。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有关张爱玲与毛姆关系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毛姆和张爱玲都具备传统小说家的独特魅力:擅长故事。张爱玲认为:“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⑥这是张爱玲的小说观,也是她的故事观。她甚至能极端地执行这种小说观故事观:她的散文《爱》标题宏阔得甚至相当抽象和空洞,而文本又简短到不足三百字,情节、人物和语言均可谓极简,但丝毫不影响读后的刻骨铭心。毛姆是西方公认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讲故事是人之天性,我想短篇小说的由来大概是从前晚上,猎人们为了给吃饱喝足的同伴们消磨时间,于是就在山洞篝火边上讲起听来的传奇故事。”⑦不仅“讲故事”是人的天性,而且“听故事”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精神渴望。毛姆深谙此道。
具体而言,不妨比勘这两个故事高手的讲述,看看他们究竟在哪些方面相似。
首先,他们都充分遵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诗学传统,注重艺术的整体统一。毛姆明确指出,一个好的故事“应该像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一样,有开端、发展和结尾。……(情节)是引导读者兴趣的一条线索。”⑧张爱玲更是为了追求故事结构上的整一效果,往往在故事末尾設置一段与开头相近的场景描写,以便首尾照应。《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等都是读者最为熟知的例证,“咿咿呀呀拉着”的胡琴,至今还和着那苍凉的故事一遍遍地反复循环。
其次,叙述视角上他们小说的背后似乎一直隐藏着某个洞察万象又不断消失的叙述者,其叙述视角在全知与限知、聚焦与模糊之间了无痕迹地自由切换,可视的日常景象与不可视的微妙情感,惯常与变化的细节犹如生活本身一般历历在目。毛姆的小说《面纱》中,故事一开始叙述者以全知视角描述一对男女偷情画面,但很快,全知叙述者就在“他们小声交谈着,近乎耳语”的无言中消失不见,转而借小说人物受限视角来继续陈述:“他循着她的目光望去……一分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接着,鬼使神差似的,另一扇窗户的白色陶瓷旋钮也自动转了起来。”⑨此时,被看(唐生和凯蒂)转变成看者。透过受限视角,屋内场景逐一呈现。两人惊恐之情在凝望“白色陶瓷旋钮”的过程中淋漓尽现——门外究竟是否有人也因视角受限而成为悬念。张爱玲《封锁》同样从全知叙述视角开始,吕宗桢或吴翠远只是电车众生中的一员,但从吕宗桢“宣告调情计划”起,限知的叙述视角便开始不断地游走于吕、吴二人之间。正是在受限视角的选择与遮蔽下,这段不可思议的电车恋情才变得合情合理。从无所不知的全能叙述者退回到有限的“当事人”视角,反而赋予故事以逼真感,调动读者的好奇心。
再次,张爱玲和毛姆都有着高超的心理洞察能力,人物隐秘的内心情感在他们的笔下纤毫毕露。张爱玲对曹七巧的心理刻画早已为人熟知,而《红玫瑰和白玫瑰》描写一个既向往情欲自由又想保住社会名声的男人振保,在道德和情感之间徘徊的矛盾心理。当情感/情欲危及其社会地位时,他便立即退回到符合社会规范的“好人”位置,继续戴上清白孝顺、义气克己的面具。这与毛姆笔下的查理·唐生如出一辙。
最后,张爱玲和毛姆都具有极为敏锐的感官能力。他们对日常事物细节的精微摹写,犹如荷兰画派一般细致入微,给人以电影画面般真切的视知觉体验。比如,《刀锋》中那段著名的对聚会现场的描绘中⑩,叙述者借用小说人物伊莎贝儿的视角,漫不经心地扫视着聚会上各式各样的人,每个精挑细选的细节都被定格下来,通过电影特写式地放大,推到读者面前。这样的技法在张爱玲写作中同样娴熟。《茉莉香片》开篇即透过叙述者的画外音勾勒出一位听众茶馆听戏的场景。似乎有推拉镜头,由听戏全景向“茶烟缭绕”聚焦放大,随即由茶馆切换至香港的柏油山道,远远地一辆公共汽车慢慢驶向读者;忽而镜头从全景又切换成车内“杜鹃花”的特写,并随着杜鹃花的枝丫一直向窗外推远。忽而,镜头又从“红成一片”的远景跳跃回来,最终聚焦于车内“杜鹃花”后面的男孩11。通过对人物年龄、着装、姿势、面庞和神态的细致描写,成功地呈现出一个阴沉女性的男生形象。
这些都是张爱玲和毛姆在讲述故事时的共通技艺。这一定程度上担保了他们虽然写作(主题、题材、人物、环境等)不同的故事,却能风格“神似”。不过,这些相似很可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相对浅表的层面:作家与作家之间多少会存在技法上的相似。
二、文学观与世界观
将毛姆和张爱玲的写作联结起来并最终形如孪生的,除了故事的技艺之外,还有写作背后更深层的理念。
如果相信我们自己的阅读感觉,恍惚之间很可能将毛姆的《面纱》误认为张爱玲“沉香屑”式的写作。其实,这几个文本除了共有香港背景外,不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还是主题取向,并无“互文”关系。真正造成读者错觉的根由,并不在于具体故事情节,而在于更深处相似的人性描摹:对俗世普通人的呈现。
《面纱》里的凯蒂与唐生,似乎隐约呈现出葛薇龙和乔琪、白流苏和范柳原,振保和娇蕊,甚至曹七巧和姜季泽的某些影子。他们笔下人物之间的相似,不只是在中国读者这里得到了印证,在英语读者那里也令人吃惊地得到了确认。一位美国大学生读完《秧歌》,很困惑地问张爱玲:“怎么这些人都跟我们一样?”张爱玲听后觉得“被她一语道破了我用英文写作的症结,很有知己之感”12。这个问题以及张爱玲的感觉,可能正是揭示张爱玲写作价值的入手处,是张爱玲文学世界难以觉察的“天机”:张爱玲的文学写作不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不是鸳蝴派的,甚至也不是新文学传统的,而是世界的。
张爱玲想要描绘的,正是同(无论中外古今的)你我一样真实的普通人。她在《写什么》中提到:“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一辈子也写不完。”13张爱玲所眷恋的以及毛姆所钟爱的,正是这一类“普遍现象”的题材。较之纪念碑式的英雄谱写,不论毛姆还是张爱玲,都更倾向于小人物,偏爱于讲述些不彻底的“小事情”14,于凡俗的人情琐事中舒展人性。他们的作品也因此都被称为“通俗小说”。张爱玲曾坦言:“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5在张爱玲看来,革命或战争只是人生的“例外”,极端的病态或极端的觉悟也只是少数,而平凡的不彻底的普通人的生活——恋爱结婚,生老病死——才是人生的常态。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张爱玲根本没有看轻战争或革命这样的时代纪念碑式写作的意思,当然同时也丝毫没有看重它们的意思,而后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疑给她埋下了祸根。而在毛姆看来,伟人与恶人之间并无多大差别,因为“伟人也有软弱、浅薄、诡诈、自私、纵欲、虚荣或放纵的一面……所有人都是伟大和渺小、善良和邪恶、高贵和卑微的结合体”16 。由此,不管是科学殉道士瓦尔特,还是情场浪子范柳原,抑或是经过宗教洗礼的凯蒂,都不可能成为清壁坚绝的圣人,而只能是软弱中有坚强,虚伪中有真实的凡人而已。着意于对俗世凡人的日常摹写,其背后根植于两人极为相似的文学观乃至人生观世界观:较之轰轰烈烈且首尾一贯的英雄伟人,矛盾复杂的小人物(普通人)更为真实。用毛姆的话说,他们身上“蕴含着我们人人都很熟悉的普通人性”17。我们也因此能理解张爱玲对凡俗人世的真心喜欢,不是出自某种崇高意义而是来自脚踏实地的喜欢:对她而言,“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18。而对嘈杂纷乱的十里洋场上海,张爱玲却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19这近乎母亲对儿女无条件的接受和喜爱。
三、写作的理性逻辑
张爱玲究竟因何而特别服膺这种对普通人人性的特殊关照?很有可能,这得益于张爱玲的英语能力以及由此生发的西方理性思维。
张爱玲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接受西式教育,修习英文、绘画、钢琴等。小学就读被称为“美国现代教育的实验场”20的黄氏女学,中学则是美国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女中,该中学“全用英文课本,老师也大都是英美籍”21,最后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22,因战争原因最后改入香港大学,而香港大学同样是英式教育模式。
正是在这里,被研究者忽略但却特别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张爱玲其时所在香港大学文学院的“文学”,并非我们今天想当然地以为的“汉语言文学”,而是“英国语言文学”23,即:张爱玲的学习专业本身即是英国语言文学,其中尤其注重英语古典文学修养和英文写作训练。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期间几乎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独揽尼玛齐与何福两大奖学金,并有望免费去牛津大学读博士),英文学习能力相当突出。先天的语言天赋和后天的勤奋努力,张爱玲的英文思维得以充分训练,英文水平已经“达到了老道浑成,炉火纯青的水准”24。张爱玲对于英语文本的热爱,已经到了“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25的入迷程度。张爱玲不仅喜欢英语,还特别擅长英语写作。她在正式小说写作之前,已在《泰晤士报》《二十世纪》杂志发表过多篇英文随笔26。后期赴美更是直接用英文进行创作。《秧歌》《五四遗事》《少帅》等均先以英文写成,后译为中文,且毫无翻译痕迹。美国大学教授(夏济安和夏志清)都对其“随心所欲、中英文互译的本领很是钦佩”27。
以此观之,张爱玲不只是精通英语,而且深谙这种语言背后的逻辑理性——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更是思维方式本身。《二十世纪》报主编梅奈特曾说:“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28这种西式思维及西式表达方式,至少在语言思维层面上使得张爱玲与毛姆之间根本不存在中西之间的阻碍。
毛姆素以冷峻锐利著称,甚至被指为“愤世嫉俗、冷酷无情”。在毛姆的作品中,叙述者始终保持着客观理智的态度,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放置于放大镜下进行观察。毛姆的创作风格,同他早年行医经历息息相关,三年的行医经历令他看到了“原汁原味的生活”,体悟到“人类所能表達的每一种情感”,见识到被疾病恐惧击垮了防线后“赤裸裸的人性”29。他发现:“在人体解剖中,完全正常的情况才是罕见的。”30这显然启发了他对人性的理解:完全正常是一种理想,而真实的人性其实混杂着“自私和厚道、理想主义和肉欲、虚荣、羞涩、公正勇气、懒惰、紧张、顽固”31等诸多性格特征。这与他早年行医(自然科学)经验以及深受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尤其莫泊桑影响有关。
与毛姆一样,张爱玲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临水照花”“陌上探春”的超然态度,恪守作为“观察者”的客观中立态度,避免个人情感和价值立场对故事的直接干预,让故事人物各行其命。张爱玲的小说里,既不见旧小说惯有的善恶对立、神仙搭救、圆满结局,也不见新文学中常见的宏大主题和批判传统情怀。有人隐约感受到“张爱玲的《传奇》,有点像法国《红与黑》(Le Rouge et la Noire)小说中描写西洋高等社会细腻的趣味”,也有人评论者直言:“张女士真正用一个西洋旅客的眼光观赏着这个古旧的中国……她的手法并不新奇,她是把外国笔法介绍给我们。”32于是,她虽然用中国语言描写中国故事,却东西无碍:张爱玲文学技艺以及文学观的更深处,隐藏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叙述理性。因此,有人早就这样形容过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得如同数学”33。而“冷眼旁观”的真实含义,并非孤影自怜或凉薄无情,倒恰恰是应该理解成英语及西方世界带给她的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也可视为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西方文化一直以来对事实和真实的尊重。这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根本共识。只有在这种共识之下,才可能谈论(普通人的)普遍人性。
张爱玲写作中这个如此重要的特质,却一直被湮没在别的一些亮晶晶的饰物下,比如她中文小说里的古典韵味(语言层面)和她自身的女性(感性)形象,更不用说那些敏感的政治意识以及容易消费的情感八卦。最终,张爱玲写作中的理性精神,被“民国才女”的“冷眼一瞥”一笔带过。这绝对不应该仅仅只是张爱玲的悲哀。
总之,理性叙述是她与此前此时中国文学之间最值得关注的区别,也是张爱玲之所以是张爱玲的最独特之处。与毛姆一样,她既不是作为传道者或革命家也不是为了抒情泄愤或消遣娛情来进行文学创作,作品里流露着浓厚的法国现实主义痕迹。夏志清说:“她(张爱玲)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34“自然主义客观描写”,其实质即理性叙述,它主要源于包括毛姆在内的西方理性求真传统,而非载道或写意的中国抒情传统。这正是张爱玲行文的理性叙述底色。只不过,与理性到近乎冷酷的毛姆相比,张爱玲的写作少了几分锐利,多了几许“地母”式悲悯。这悲悯是在“懂得”和“慈悲”的限度内有所节制的情感表达。因此,张爱玲很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直接运用西方(英语)思维(不是西方意识或思想知识)进行文学写作,真正将西方理性思维和中国(古典和现代)语言完美融合的唯一现代作家。
四、余论
可能正因为如此,张爱玲与毛姆不仅风格神似,在文学史和阅读史上的命运也出人意料地类似:都面临着阅读史上“雅俗共赏”和文学史上“无处安放”的诡异境遇。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受欢迎、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英国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既被称为“英国的莫泊桑”,又被指为一个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作家。有评论者指出:“毛姆……是一个奇怪而又少见的文学现象,一个既糟糕又出色的作家。如果一部20世纪的短篇小说集中没有将毛姆作为代表,它就没有多大意义。”35大部分批评家倾向于把毛姆看作聪明、完美的技巧大师而不是艺术家: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思想深刻的作家。这既招致批评家们的不满,却又成功捍卫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听故事究竟是人类古老的传统。总之,毛姆在文学史上之所以无处安放,主要是因为他在一个现代主义艺术时尚中却仍然坚持古老的故事传统,保守着相对陈旧的现实主义手法。
张爱玲与毛姆有所不同。她在1940年代中期的上海曾名噪一时,无可争议的民国才女。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社会革命浪潮的兴起,旧爱的不良声誉,张爱玲避居海外,由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销声匿迹。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张爱玲重新进入民众视野,并再度掀起“张爱玲热”:于读者而言,张爱玲乃当之无愧的民国才女。与毛姆相似,张爱玲的作品之于中国文坛而言,同样不合时宜、无处安放。柯灵曾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36不过,她的不合时宜之处却不在固守传统写作手法,而在于超越时代的创新:她实现了西方理性思维和中国语言几乎完美的结合。
她的真正难题在别处:主流文学和意识形态话语感兴趣的,她偏偏不感兴趣。
【注释】
①鲁迅:《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25页。
②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见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22页。
③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见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4页。
④张爱玲、庄信正:《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第119页。
⑤李欧梵:《张爱玲在香港》,《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⑥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176页。
⑦[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观点》,夏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第128页。
⑧16293031[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毛姆自传——让灵魂舒服一点》,王敏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第210、52、62、67、67页。
⑨[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面纱》(中英文对照全译本),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17,第2页。
⑩[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刀锋》,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78页。
11张爱玲:《茉莉香片》,见《张爱玲文集》(卷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46页。
12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见《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332页。
13张爱玲:《写什么》,见《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134页。
141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175、175页。
17[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書与你》,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17,第6页。
18张爱玲:《诗与胡说》,见《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132页。
19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59页。
20祝淳翔:《黄氏小学:张爱玲的西式教育启蒙》,《档案春秋》2013年第9期。
2122242628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第19、27、31、53、54页。
23当时港大的文学院即英国语言文学专业,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含中史等)则属另一个学院:邓志昂中文学院,其遗址即今天的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这也从侧面解释了张爱玲从港大转学上海圣约翰时缘何遭遇国文不及格的尴尬处境。
25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见子通、亦清主编《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4页。
27宋淇:《私语张爱玲》,见子通、亦清主编《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132页。
32《〈传奇〉集评茶会记》,见子通、亦清主编《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79至81页。
33胡兰成:《民国女子》,见子通、亦清主编《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34页。
3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66页。
35Clare Hanson,Short Stories and Short Fictions,1880—1980. 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Ltd.,1985,p.49.
36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384页。
(张龙云,湖北大学文学院。本文为湖北省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2019年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