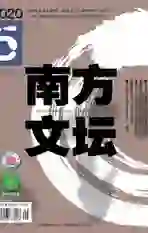汉语小说叙事文本抒情性渊源及其特征探析
2020-12-24孙仁歌
前言
所谓汉语小说,就是指那些应用汉语书面形态及其语法规范写作的小说文本,又被称之为叙事性作品。然而,这种貌似说事叙事的虚构之事,放在中国文学史上具体语境上去考察,也就不难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汉语小说的叙事发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滋生于叙事本身,而是与叙事性作品的前身抒情性作品的语境乃至文化渊源息息相关。
童庆炳在《中西文学观念差异论》一文中认为:“现在中国学者不少人摹仿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叙事学,这诚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看不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抒情特点,就没有找到中国叙事文学的根本所在。”①窃以为,童庆炳这一观点并非一家之言,对照一下中国文学史,可谓言之有据。
一、《诗经》以降,抒情始终
领唱中国古代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抒情文本总集,它的诞生及流行,便领唱中国古代文学两千年之久。即便期间出现了唐宋传奇、明清小说,但叙事的抒情“基因”的血统关系是不能因为叙事的崛起而改变。追溯中国文学的起源尤其抒情的起源,我们既不能否认鲁迅的“抬木头说”,如此,也就不能否认《诗经》的诞生与西周春秋时期民间狩猎、歌舞的关联。《诗经》本是儒家的经典,那么为儒家所崇尚的“制礼作乐”形成的独有的礼乐文化体系,无疑就是《诗经》的精魂所在。《礼记·乐记》中有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②这虽然不尽是《诗经》之理,却应该是左右《诗经》从萌芽到形成一种抒情模式并传唱开去的早期意识形态元素之一。虽不敢说《诗经》就是汉民族颂圣文化的开端,但可以说《诗经》以歌传诗的抒情模式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却是空前的且与时俱进,不仅是历代诗词发展的资源,也是叙事性文学悄然萌芽、发展乃至崛起的“酵母”。
且不说开篇《诗经》就是抒情的格调,就连《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上古文艺史话里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可见《诗经》也并非从历史的天空掉下来的“天赐馅饼”,也是从远古先贤那里传承下来的“文化种子”发芽开花并结果。尤其到了唐诗、宋词两个抒情巅峰,抒情为本的观念在中国文人墨客的写作审美尺度里就成了一种圭臬,恰如童庆炳所说:“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文学的观念从‘言志说转向陆机的‘缘情说,转向刘勰的‘物以情观说、‘情者文之经说,就把中国诗学的情感论作出了重新的理论阐述,凸显出中国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乃抒情之作品的性质。”③
即便是“诗言志”,“志”与“情”也不可分割,“情”乃是“志”的基础抑或前提,倘无“情生”,又何来“志向”?正因为如此,“诗言志”才会转向陆机的“缘情”说。唐诗中的意境说及其广泛应用,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后世叙事性作品的影响尤为难解难分。国画的写意观念也正是来自意境的文化渊源,意境的本质特征就是写意,写意的主要表达方式就是抒情,诗画一体。
当然,抒情毕竟不是文学的全部,后世发生并崛起的叙事性文学,即便是以抒情为目的,却也终究归属于叙事性文字,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另一半。
二、叙事是抒情的另一半,
也是文学的另一半
纵然抒情长期领唱中国文学尤其古代文学,但抒情终究是相对的,如果没有叙事形态的存在,抒情说也就缺少了支撑。有抒情就必有叙事,彼此相辅相成,尽管抒情孕育了叙事,但叙事毕竟构成文学的另一半。虽然抒情长期领唱中国文学,但抒情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叙事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元曲等抒情性文体,几乎都是抒情领唱叙事,物引情思,情动为志,因此,抒情必然离不开叙事,否则,抒情也不成为抒情了。所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直是抒情为本,叙事为辅,抒情离不开叙事,叙事更依赖于抒情的左右逢源。
说抒情孕育着叙事,叙事又坚挺着抒情,或许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语境形态吧?诗人之所以会抒情,首先是因为被外物感动了,可见,文学发生的情感说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曹文轩在谈及“感动文章”时说:“从前的小说理论基本是围绕‘感动这一核心单词而建立的,许多话题只是这一话题的旁出或延长。当小说家們进入构思过程时,盘桓于心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感动他人与后世。”④由此可见,中国的小说理论家谈及小说及其叙事时,也深受抒情观念的影响,强调小说构思必须从感动出发的重要性,但要感动他人与后世,首先是自我的感动乃至激情满怀,否则,还谈何感动他人与后世?
抒情与叙事既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与抒情性作品发展到某种非此即彼的关口,叙事性作品也就会很及时地应运而生。之所以会产生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乃至明清章回小说之文本,可能就在于长期贯穿抒情为本的文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及其人性日益复杂的内心表达的需要,更不能代替叙事性作品而独领风骚。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也涉及中国叙事学之于意象与抒情的渊源:“中国诗歌长于意象抒情,它所创造的闪光的意象,随时从这种处于文学正宗地位的文体向其它(他)文体的渗透。”⑤这里虽然提出的是“意象抒情”,其实也在证明“意象抒情”是奠基“叙事文本”抒情为本的发展脉络。
《世说新语》作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离抒情这棵大树的根脉最近,说它是小说还有点勉强,但把它视为叙事文本的萌芽倒也未尝不可。单从它的语言特色去考证,其精炼含蓄,隽永传神,简约真挚、恍然生动的语势,就与抒情性作品形神相融,血肉之躯难解难分,甚至可以把抒情喻之为皮,叙事喻之为毛,彼此的关系,单从表现形式上看似乎泾渭分明,但从内在关联上考察却又形影相随,皮毛紧密,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唐宋传奇中的代表作《柳毅传》,之所以全篇洋溢着浪漫主义基调,尤其语言方面体现出来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谁能把这种叙事的抒情性根脉一刀斩断呢?汉语小说自诞生以降至明清,无论短中长,差不多篇篇都离不开诗词歌赋的点缀与灵动,倘若把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歌赋都抽掉,那么剩下的文字就如同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再让这个人去讲故事,他肯定就丧失了生动性乃至灵性。故此,陈平原言之有理:“中国古典小说之引录大量诗词,自有其美学功能,不能一概抹煞。倘若吟诗者不得不吟,且吟得合乎人物性情禀赋,则不但不是赘疣,还有利于小说氛围的渲染与人物性格的刻画。”⑥
所以,有学者认为探寻汉语小说叙事的胚胎抑或根脉,都绕不开“诗强其里”这个事实。因为“小说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始终受着‘诗骚传统的影响,使小说思维呈现出诗化的流变态势,以致在唐代发现了可以追求诗意的传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更是产生了浪漫主义小说”⑦。的确,韩进廉的說法是符合中国文学乃至汉语小说发生发展实际的,作为汉语抒情性作品的源头“诗骚”就如同民族文化的一代代“疫苗”被不断注射到汉语小说的文脉里,后世小说无论把故事讲得多么好听,恐怕都割舍不了“诗骚”的干预乃至无意识作用其中。“诗赋虽然不是小说的直接源头,但它发于小说产生以致早在汉代就趋于鼎盛,它那虚构故事情节的叙事框架,对客体的精细描绘,不可能不对小说文体施加影响。”⑧此外,郭绍虞也持这一观点:“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⑨
当然,仅凭这点材料还不足以讲清叙事是抒情的另一半,也是文学史的另一半的话题,因为汉语小说的巅峰既不是六朝志怪,也不是唐宋传奇,无疑,明清章回体小说以及某些短篇白话小说等,被更多的学界同仁视为汉语小说的“黄金白银”。尤其《红楼梦》的诞生,理所当然成为汉语小说的一大标杆,它的抒情诗性特征更是有力地证明了汉语小说抒情为本的观念之无懈可击。
三、《红楼梦》是歌唱故事而非叙述故事
明清章回小说从文本而论是叙事的,即讲故事的,但扒扒它的皮,又不难发现抒情为本的真面目。
是的,打开《红楼梦》,全书抒情性描写抑或叙事比比皆是。一览《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几乎通篇描写都是诗意的、抒情的、充满朴素而又浪漫之叙事形态,可谓是抒情的故事,是故事的抒情。无论读到何处,隐含到叙事者,都在悄然地放大诗情画意的情境。为了营造“游幻境”,以下几段铺垫性的文字也不乏一种淡淡的抒情意味:
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来。
这段铺垫性文字是写宝黛关系与众不同,就因为关系亲密才会常常言语不合,动辄泪来悔往,阴晴不定。即便对日常琐碎之事的描写,作者似乎也极讲究语言的节奏感,简洁、明媚、诗意、抒情,悲剧的基调不知不觉中沉淀在叙事的字里行间。
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二人来面请。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顽,先茶后酒,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
铺垫性文字也在步步为营,继而引出园内梅花盛开,贾母携众人赏花游览,自然就离不开设宴吃酒、于是就借酒说梦,从而套出穿透全书主旨的纲领性故事“游幻境”。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最平常不过了,但只要你细细品尝一下,仍然能领悟到一种说事如歌的语势,起伏跌宕的节奏感始终如一。
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贾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来。贾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嬷嬷、姐姐们,请宝叔随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
到了这里,铺垫性文字越发入诗入情,于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物秦可卿便“清水出芙蓉”,继而引玉入寝,于是领衔全书企图的“游幻境”之“大戏”便由此展开。无疑,语感好的读者,读诵这一段文字,也同样会分享受到一种诗语般的节奏及韵律,可谓是“在音乐的胎盘中孕育着诗”,当然在接下来的浓墨重彩中,这种入诗入情的描写更是俯拾皆是。请看:
一语未了,只见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了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
无论是描写日常琐事、还是描写诗情画意,作者显然永远都是抒情家,用词造句总像是一位钢琴大师在满怀深情地弹奏着《秋日的私语》,描述中有奇境、有惊艳、也有“乐舞诗飞”的语感。诸如此类,《红楼梦》全书中不胜枚举。如果如此面面俱到,此文恐怕就要连篇累牍、跑题万里了。
《红楼梦》的确是抒情的、诗意浓浓,可见,童庆炳所阐释的中国文学观念是以抒情为主的审美形态说,并非无稽之谈。不仅《红楼梦》如此,中国戏曲如《牡丹亭》等也然。童庆炳认为:“《牡丹亭》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物,乃是根源于作者有情感郁积于心中,不得不发。……这就说明了中国戏曲以讲故事为表,以抒发情感为里。”⑩换一句话说,沉淀在汤显祖心底的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要释放艺术化了的情感,这也是构成创作动机的主观因素之首要内驱力。如该戏第十出 《惊梦》,可谓曲曲是叙事,曲曲又是抒情、是诗语,熔音乐美、画面美、意境美于一体。
【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行介)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贴)今日穿插的好。
戏曲作为叙事性文学,但它的叙事形态似乎与生俱来就是抒情的、诗意的,较之小说叙事的抒情性特征,戏曲的诗意化抒情更加彰显。无疑,它与小说是互通的,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渗透。以上这曲描写,如果从《牡丹亭》中抽出来独立成章,不就是一曲生动优美如泣如诉的长短句吗?然而它终究是戏曲中作用于起承转合功能的叙事性文字。
【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旦低问)那边去?(生)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低问)秀才,去怎的?(生低答)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这曲【山桃红】虽说多是对话,但开篇几句诗语便为对话营造了节奏,真乃抒情意味凸显,诗意盎然。与古典小说叙事形态同理,如果说“戏曲表面是讲故事,深层次仍然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11,那么以此类推,与戏剧相似的小说自然也在这一原理之中。应该说文学就是情感的载体。诗人、小说家一生都在悉心侍候自己的思想情感,情生于万物之诱惑,如此才有生命写作的诞生,情滞而文谢,情是妙文之源。纵然中西方文学观念有所差异,但在研究定论文学起源说中,却也有人主张文学起源于情感说,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代表。
以中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乐,律和声”的文化渊源为考,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的真正核心还是离不开一个“情”字,正如童庆炳所说,“明清以来,戏曲、小说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表面看,似乎离开了抒情传统,转向了叙事方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第一,明清两代抒情的诗仍属于正统,是高雅的标志;第二,就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作品而言,仍然贯穿着中国的独特的抒情传统”12。是的,摆一摆明清以来传世的每一部小说与戏曲,都是抒情与叙事兼并的“种子”,《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如此,此外,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各类小说与戏曲也莫不如此。
若以诗词曲赋的数量作为衡量一部名著抒情为本的事实,那么《红楼梦》也首当其冲。童庆炳不仅认为中国戏曲是以“讲故事为表,以抒发情感为里”13,还不容易置疑地认为“一部《红楼梦》不过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感叹生命的快乐与悲哀而已。……《红楼梦》是在歌唱故事,而不是一般的叙述故事”14。或许童庆炳是提出《红楼梦》“叙事如歌”的第一人,大凡认真读过《红楼梦》又深谙中国文学史的人,可能不会对这一说法持完全否定立场,《红楼梦》是叙事的,也是抒情的、诗意的、浪漫的,通篇诗词曲赋此起彼伏,构成了全书伤情悲世的基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红学研究者蔡义江曾编辑出版了《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一书,并在书中提出“按头制帽,诗即其人”的议题,同时也认可作者苦著《红楼梦》定“有传诗之意”,“传诗”说可谓就是抒情为本的另一种说法。该书共选入了三百六十余篇诗词曲赋和分析鉴赏,颇有可读性,假如你把这些诗词曲赋从《红楼梦》中全部抽掉,那么《红楼梦》可能就曲终歌罢,面目全非了。
正如关四平所述:“《红楼梦》的情感表现由多个层面构成,既有男女爱情,也有亲情、友情。无论是哪个层面的情感表现,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均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15这与童庆炳的《红楼梦》叙事观“歌唱故事”说如出一辙,悲剧的传播,有时就是一种感叹、一种哀号、一种泣血,一言以蔽之,就是抒情。
小说叙事得益于抒情的孕育,同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得益于诗评的发展与丰富。倘若没有诗评,又何来叙事理论的批评。“小说的评点自然是从对诗文的评点发展起来的,但它的盛世则要归功于李贽。”16即使现当代文学理论抑或批评研究,诗学批评虽然所占的比例锐减,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会公然否定汉语小说叙事的抒情基因,相反,不少专门从事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以及美学研究的当下学者,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有关这一点,陈世骧给予的论断更为明确:“中国文学注定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荣耀。……赋中若有些微的戏剧或小说的潜意向,这意向都会被转化,转化成抒情式的修辞。”17
四、即便现当代文学的叙事形态,
也不乏抒情与诗意的精彩
前面已经提及现当代文学中经典作家作品,诸如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沉沦》、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诸多短篇小说等,抒情与诗意的质地还是显而易见的。童庆炳认为《红楼梦》就是在歌唱故事,那么无论什么时候读一读鲁迅的《伤逝》,又何尝不是在歌唱故事甚或就是一曲悲歌呢?小说一开头就为整篇悲歌奠定了长歌当哭的基调: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有人把这种开头总结为基调式开头,即一句诗意的开头,就为全篇的思想定下了基调。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诗意的开头方式展开叙事,不排除潜意识里受到一种歌咏理念的驱使,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唱起了故事。有一个常识性的理论,诗句凝练而又高度概括,一句顶十句。尽管这个开头也不能说就是纯粹的诗句,但至少有几分散文诗的语势,抒情的意味还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正因为采取了这样一种诗意的开头,小说接下来的叙事都自然而然地顺应着抒情的笔调为子君而悲歌连连了。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这几句叙事对悲情故事承前启后,子君的死,让“我”顿悟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我们原来的爱都被这个黑暗的世界戏弄了,子君的死是悲哀的,“我”虽然还活着,完全是苟且偷生,极度的苦闷和绝望,生还不如死了好。全文始终如一的诗意的、抒情的又充满悲情的叙事,赋予子君以“挽歌”以“绝唱”,卒读全篇,恐怕多数读者都会领悟到一种悲剧的力量、诗的力量。虽说抒情的极致似乎只能属于优秀的诗篇,但欣赏《伤逝》到最后,也分享到了一种抒情的极致。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是的,读完《伤逝》这几句结尾,从至痛的抒情中,我们似乎已经窥视到了叙事者一颗伤痕累累的灵魂!无论这个叙事者多么隐含,我们都无法将作者与叙事者也包括小说中那个替身“涓生”,完全割裂开来。因为鲁迅本身就是20世纪最苦痛的“这一个”,否则,《伤逝》也就达不到如此撼人心魄的叙事效果。由此,我们又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抒情性文学传统的影响与渗透,小说的鲁迅还会不会采取抒情的笔法抒发“涓生与子君的”悲剧故事,这里也就不便定论了。《伤逝》的抒情笔法的确很精彩,虽不能说这种笔法就是“鲁迅笔法”,但是不是可以说汉语小说叙事文本抒情性渊源及其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种普遍性?
同样,就20世纪新文学的小说叙事文本而论,浪漫一族除了鲁迅,还有郁达夫、沈从文、废名等,精彩的抒情性叙事也是不胜枚举。郁达夫作为一个奉守自叙传写法的作家,但他却在他的自叙传的小说里注入了浓浓的浪漫而抒情的元素,无论是《沉沦》还是《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写法上虽是自叙传的,而在叙事策略上,似乎都又别具情种,几乎每一篇都与诗意的抒情性的叙事形态结下了“同盟关系”。尤以《沉沦》最具有代表性。
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较之鲁迅《伤逝》叙事语势丰姿夺目之抒情形态,郁达夫的《沉沦》中的文字就显得凝重、迟缓、犹豫了许多,不过这些异于他人的叙事方式,也并没有遮蔽全文抒情性特征的存在。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浪漫主义一度盛行,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叙事无不洋溢着与众不同的到浪漫情结与隐约抒情式讲故事的特征。上面这段文字是《沉沦》中开头铺垫性描述,从中不难捕捉到抒情的“蛛丝马迹”,这种塑造一个忧郁的、颓废而又浪漫的青年深层次的心理病象,任凭作者内心世界如何激情燃烧,而字面上的抒情总是克制的、内敛的,抒情始终受到叙事文本制约的尺度,在作者内在思维的把握中也恰到好处。
《沉沦》的抒情性特征不仅有别于鲁迅的《伤逝》,也有别于沈从文的《边城》。在小说叙事学研究领域,《边城》一向就被学人视为诗美、地域美、意境美的小说。全文诗意浓浓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叙事结构,让这个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广泛的美誉,除了结构被赋予了诗意美、地域美、意境美,还被赋予了奏鸣曲式的叙事、牧歌式的叙事,由此可见,《边城》简直就是诗化小说的典范。
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
随便从《边城》原文中攫取一段文字,就能分享到一种“乐园图式”的诗意境界,字里行间弥散着浓郁而典雅的古典审美情趣。独立欣赏这一段用于小说叙事层面的文字,作者营造的是诗一般的语言,有意有境,意扬境阔,很优美,也很好读。意境本来是评价中国抒情性作品诗歌的术语,一度成为中国古代诗人咏诗填词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境是中国文学审美的一个概念与定式,“指的是通过形象性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能够把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的空间的艺术境界”18。而到了后世小说家的叙事笔下,意境美又有了新的用场。到了现代,茅盾就把意境应用到了现代文学范畴,这种文学现象又进一步证明,中国抒情性文学领衔中国叙事性文学并对叙事性文学产生“传宗接代”级别的影响与渗透,已经成为一个无须争论的事实,可以确认本文的中心议题汉语小说叙事文本抒情性渊源及其特征考证种种也是顺理成章的。
此外,废名的小说也是文学史公认的“梦幻”叙事,熔人情美、意境美、精神美于一炉,其审美的抒情性特征几乎涵盖了废名小说的全部。周作人曾对废名的小说文字如是说:“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欢含蓄的古典趣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19 甚至有人干脆就把废名的小说当诗读、当画看,小说叙事的感觉常常被诗情画意冲淡了。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无意中呈示这种诗意的、抒情的小说叙事方式,从鲁迅到郁达夫到沈从文到废名再到何其芳到冯至到汪曾祺等,赓续连接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性小说的一条连贯的线索。
小结
总之,汉语小说叙事文本抒情性渊源及其特征探析,材料翔实而可信。也就是说,本文主旨汉语小说叙事文本抒情性渊源及其特征探析是充分的,观点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过,汉语小说叙事固然可以视为抒情的载体,但就创作动因及其目的而言,抒情为本也并非叙事性作品的唯一,就文学的社会功能而言,应该还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乃至传播某种思想等意图,单纯强调抒情为本抑或歌唱故事,难免显得简单而局限,因为抒情是与作者的创作思想、发挥某些社会功能乃至目的紧密挂钩的,有关抒情的思想层面、社会功能层面的意义也不容小觑,在强调汉语小说叙事抒情为本观点的同时,也当建立更为丰厚的理论资源。
随着社会现代性文化元素日益全方位注入,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叙事也会多元生变,比如小说的主观性色彩逐渐会被小说的客观性或未来某些不确定性所取代,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即中国文学的观念抒情说抑或叙事性作品的抒情性“文化渊源”研究,永远都是探析中国文学的真命题,不会因为未来文学发展可能出现的万花筒般的多姿嬗变的不确定性而被颠覆。
【注释】
①③⑩11121314童庆炳:《中西文学观念差异论》,《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②互联网百度百科网“礼乐”简介条。
④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2,第206页。
⑤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第277页。
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10页。
⑦⑧⑨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6、15、15-16页。
15关四平:《唐代小说文化意蕴探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437页。
16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25页。
17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三联书店,2015,第5页。
18赵则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第540页。
19吴晓东:《废名小说“文章之美”》,《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
(孙仁歌,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