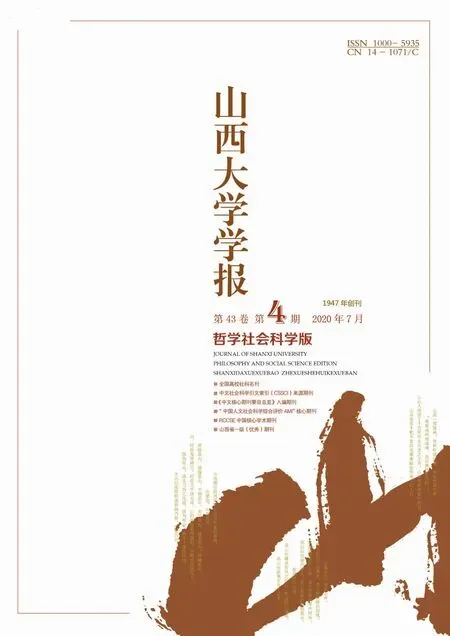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思考
2020-12-22常江
常 江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引言: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危机
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日趋深入的介入以及对新闻业形态的有力重塑,业已从基本概念和阐释框架等方面对新闻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革新的要求,使新闻学的研究陷入了“研究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1]。对此,国际新闻学界从2010年开始,以《数字新闻学》(Digital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Studies)和《新闻学》(Journalism)等期刊为平台,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讨论。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新闻学学者提出应在数字化的语境下,对新闻学进行重新概念化,[2]甚至认为“数字新闻学”是新闻学自新闻规范理论、经验主义新闻学、新闻社会学和全球比较新闻学之后的“第五大范式”。[3]在中国学界,对于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新理论体系或理论范式的讨论还不多见,但也有探索性研究指出,数字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应在价值内核、核心概念、研究实践和批判理论四个维度上展开,并呼吁不同视角下的理论化路径的共同参与[4]。
然而,与数字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相比,对于这一新范式的研究方法论的探索目前仍较为少见。尽管《数字新闻学》期刊于2016年曾推出一期特刊专门讨论数字新闻研究的方法问题,但其收录的文章大多局限于具体的“研究方法”(methods)层面,几乎未曾触及更加本质的“方法论”(methodology)问题。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既然数字技术导致的是新闻学的本体论(ontological)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必然要求研究者进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革新,以实现对新的新闻本体的准确理解。[5]因此,对于数字新闻学来说,危机存在于方法论层面,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而现有关于数字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仍主要集中于如何采用更高级、更复杂的手段(主要是计算机辅助手段)去采集新形态的新闻文体的相关数据,始终未曾脱离经验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传统。这种回避方法论问题,仅从提升效能的角度进行的具体研究方法“更新”,显然不能与数字新闻学在当下的理论内涵与理论期望相匹配,致令数字新闻学在研究实践层面上始终脱离对于作为“生态”的数字技术的准确理解[6]。
不过,在现有关于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的讨论中,还是有学者提出应当着眼于数字新闻生态自身的规律,而不仅仅是增大数据容量、拓展可供分析的内容类型等具体效益需求。例如,比利时学者Ike Picone就指出,就具体的研究实践而言,数字新闻学关注的核心概念应该是“数字新闻用户”(digital news user)而不是新闻的内容,这是数字新闻有别于传统新闻的关键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数字时代新闻的内容无关宏旨,而是意在强调“用户”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数字新闻的本体而言更加“切题”。他进而提出了数字新闻学进行方法论革新的三个方向:第一,建立一种总体性的(holistic)研究路径以把握数字用户的新闻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复杂纹理,并在这些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媒介实践之间建立关联;第二,对研究方法的设计应该更多指向数字新闻用户“使用”新闻的情境(contexts)而非它们所接受的具体内容(content);第三,数字新闻学研究应当将与新闻活动有关的个体视为媒介的使用者而非传者或受众,进而将重点放在对人们的“新闻经验”(news experiences)的解释上。[7]上述观点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数字新闻学方法论创新的实质:改变将新闻生产、新闻内容和新闻接受相割裂的传统新闻学研究思路,围绕“作为经验”甚至“作为生活方式”的新闻活动,探索一种总体性、阐释性的新闻研究方法论。
在克里斯·安德森(C. W. Anderson)等学者对数字新闻的理论化工作,以及Picone对数字新闻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设想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并在90年代完成国际化和主流化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具备成为数字新闻学主流研究方法论的潜能。对于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方法论的可能性和适用性的讨论,既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有深刻的当下意义。
二、新闻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运用于新闻学研究的实践,其实从新闻确立自身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那一天起,就从未间断过。[8]这种分析视角将新闻视作通过符号、故事和仪式为世界提供多维度意义、多元世界观的文化拼盘。[9]在美国,这一传统主要由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开创,并由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克里斯·安德森等人发扬传承,他们用“新闻生产的社会学”“阐释社群”“新闻生态”等概念,来强调以文化的思维来理解新闻过程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新闻学研究的文化路径,其实更多取法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而非文化研究,这一路径将新闻业的文化视为一种有明确边界的、近似于部落式的文化,却并不十分关注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问题。不过,从源于英国的正统文化研究自身学科发展历史看,新闻也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们就十分关注新闻的生产机制和接受实践问题,他们基于对电视新闻的研究,产出了包括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模型,以及对《举国上下》(Nationwide)等现象级新闻节目的案例研究在内的大量杰出成果,这些研究目前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经典理论的一部分。用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的话来说,正是因为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对新闻的关注,才使的新闻在欧洲乃至后来在美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值得被重视的严肃议题。[10]
新闻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这种天然的亲缘性,源于两个学科在基本价值层面的相似性。对此,哈特利做出了两个方面的归纳。第一,新闻学和文化研究都关注技术在复杂社会形态下对意义的中介化过程,只不过前者主张通过新闻选择与报道的专业化实践达成这一目标,后者则主要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生产实践的探析来实现这一点。第二,新闻学和文化研究都有明确的民主价值取向,区别之处在于前者的整个实践体系建立在对平等的知情权的追求之上,后者则期望通过考察有关身份、权力和再现的各种斗争来追求文化平等。[11]39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学科又在理解和表述上述两种价值追求的认识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新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一系列“不言自明”的核心概念的常识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芭比·泽利泽看来,这些概念包括事实(facts)、真实(truth)和现实(reality)等等;而文化研究的认识论则是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经济的,反对不假思索地承认任何“常识”的合法性。换言之,文化研究的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决定了其研究实践十分注重对语境化(contextualized)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性(agency)的强调,主张通过个体对常识、权威和规范提出质疑的方式来推动理论进步,这就跟新闻学的客观主义专业意识形态有了巨大的冲突。[12]
新闻学和文化研究的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在两个学科的“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学术实践,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由热到冷再到热的演变过程。不过,今天来看,文化研究最初对新闻学的热切关注,不过是将新闻视为理解文化权力、文化生产以及文化的社会影响的一个“强度案例”而已。这种研究由于并不注重对新闻自身的规律的探讨,而只注重解释新闻与社会、文化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而最终导致了两者的“决裂”。也就是说,在文化研究几乎无所不包的研究视野中,新闻根本不具备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机制,与好莱坞电影、通俗小说和流行广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新闻作为拥有自己类型学和叙事传统的公共文化档案所具备的理论潜能,也很快就在密集而程式化的文化研究实践中消耗殆尽。这不能不说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理论发展初期的傲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新闻学”还是“新闻”都几乎在文化研究的学术建制中销声匿迹,新闻消融于“媒介文化”。[13]用泽利泽的话来说,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新闻学失去了其单数形式”。[12]而在90年代,新闻学界(尤其是新闻教育界)更是出现了旨在批判、抵制文化研究影响的激烈论证,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发生于9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的“媒介战争”(media wars)。在这场新闻学和文化研究的著名冲突中,以Keith Windschuttle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新闻学学者措辞严厉地指出文化研究令新闻学,尤其是新闻教育陷入了毫无希望的相对主义,甚至提出应当将一些当时有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清除出新闻教育界。[14]新闻学者Martin Hirst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指名道姓地点出在澳大利亚新闻学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称自己“简直想要扼住哈特利的喉咙,像摇晃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摇晃他”。[15]这种近乎人身攻击的敌视令Graeme Turner感慨:“文化研究到底对新闻学做了什么,竟招致这样巨大的愤怒?”[16]
对于学术史上这场新闻学向文化研究“发难”的著名“战争”所体现出的情绪化和个人化色彩,我们暂且不予置评。这一冲突之所以发生在澳大利亚而不是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较高的地位与较大的话语权。但“战争”之所以会发生这件事本身,揭示了新闻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的认识论分歧,其实关系到了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作为公认的“学术性不够”的弱势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简单来说,若如文化研究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所示,否定“真实”“客观”等概念的“不言自明性”,则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将不复拥有自便士报传统以降形成的专业理念内核,新闻生产不再是为专业人士所共享的知识体系,新闻从业者也不再是被特定技能所界定的职业身份。在新闻传播的技术和新闻业的形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除非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之间天然、牢固的纽带不复存在,否则文化研究的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始终都会是主流新闻学所警惕的认识论、方法论。
对于主流新闻学界的指控和批判,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抗辩——尽管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的。约翰·哈特利即指出,文化研究之所以可以作为新闻学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新闻学的发展背弃了其最初的民主化承诺。他认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建立在新闻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基础上,但新闻职业化的历史进程却受制于传播技术的发展,且始终以机构的形式存在。例如,电视新闻职业的形成依托于电视媒介的传播技术,可这种技术既十分昂贵,又有极高的准入门槛,那么电视新闻职业就必然要以“电视台”这样的机构为形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若只关注新闻自身的选择标准、从业规范、操作方法和专业主义,并坚称新闻为追求公民知情权和个体信息自由而存在,却忽视电视台作为机构的利益诉求和“企业文化”,岂非自欺欺人?所以,新闻学期望不借助“外力”而实现的“自足式发展”,不过是为了将新闻业塑造为一个排他的“族群”(ethnicity)而已。新闻学界长期无视机构媒体(及其背后的资本和权力)的利益,通过大量琐碎的研究去不厌其烦地区分新闻业的“内部人”和“外部人”,这种过度的职业化学术生产策略已让新闻学走上了反民主的道路。[11]39-51用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话来说,新闻学总是用“看门狗”“第四权”这样的隐喻来彰显自己作为民主过程的“代议者”的身份,但在机构化的形态下,“代议”的新闻学就像“代议”的议会政治一样,已在很大程度演变为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话语。[17]哈特利进而提出了“作为人权的新闻学”(journalism as a human right)的口号,其意在表明新闻学的发展始终不应背离其民主价值初衷。
而在美国,新闻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泽利泽则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促进新闻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其实对于文化研究走出自身的“舒适区”、实现理论范式的突破也有重要意义。她认为“新闻学或许是一个可以帮助文化研究以优雅和宽容的姿态迈入成熟期的研究领域”,[12]盖因新闻学对“真实性”近乎顽固不化的坚持,可以促使文化研究对其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认识论近乎顽固不化的坚持进行反思。而事实上,文化研究路径下的新闻研究也从未否定过“真实性”的客观存在。将文化研究概括为一种纯粹的建构论,其实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语境论”(contextualism),即主张研究者关注包括真实性在内的各种不言自明的“真理”被界定和理解的社会条件。
三、数字化对新闻学研究方法论提出的新要求
我们在前文深入辨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新闻学方法论的历史脉络、观念基础,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的认识论冲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文化研究和主流新闻学关于新闻的认识论存在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关于新闻活动主体的身份的。简单来说,文化研究不赞同主流新闻学的“职业化”研究取向,认为这一取向在区隔“新闻职业”和“非新闻职业”的同时,也默许了一部分人理应拥有排他性的信息生产权和传播权的现状,这与新闻学的价值根基相矛盾。一如Hargreaves所说的:“民主就该让每一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传播一个事实或一种观点的权利,无论这事实多么琐碎,这观点多么丑陋。”[18]第二个矛盾则体现在新闻业的媒体机构属性上。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下,主流新闻学对专业主义、新闻价值、新闻生产、新闻伦理的讨论,其实都建立在默许新闻媒体机构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之上,这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认可了机构力量(及其背后的资本和权力)界定、规训乃至垄断信息权的合法性。在传统媒体时代,上述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毕竟新闻学没有能力改变支撑其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也绝不愿意通过拥抱建构论而否定自身的历史。而正是由于无法在逻辑上澄清自身体系的内在冲突,新闻学长期在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居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如哈特利所描述的:“如果你读新闻学的著作,会发现里面写的大部分都是政治的内容;而如果你读政治学的著作,则会发现书里对新闻的描述无比粗糙,透着满满的轻视……新闻学成了认识论领域的无主之地。”[19]
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新闻业的普及打破了这种僵局。一方面,尽管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数字技术”拥有很多类型,其对新闻内容和新闻活动的影响也各有差异,但在生态的(ecological)层面上,新闻的多种数字化路径其实共同指向了一种在形式上更加民主的、空间式的(spatial)传播结构: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受众的边界的模糊、新闻机构的层级结构日渐瓦解、新闻类型与文体的多样化、新闻标准的多元化等等。[20]这些新的结构特征,无不在破坏传统新闻学为自身所设立的认知边界和专业传统,令建立在真实性和客观主义基础上的规范性观念系统出现严重动摇。对于新闻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语境化的特点,甚至有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新闻生产研究的动态学”,以探索在变动不息的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的方法。[21]另一方面,专业主义的瓦解和传统新闻机构人文导向的专业文化的退场,也令数字新闻的文化日益附丽于主导数字技术发展的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话语,并呈现出价值极化(polarization)和民粹主义(populism)的倾向。由于传统新闻学理论话语的匮乏,新闻学者只能在缺乏总体性研究框架的情况下,将这种破坏性的新闻文化从字面上解读为一种微观形态的“直接民主”。[22]这显然是在忽视数字信息环境与宏观全球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做出的非语境化的、与现实完全脱节的错误结论。传统新闻学的方法论危机,在数字新闻时代变得更加紧迫了。
总体而言,新闻生产的去媒体(机构)化、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受众边界的消解,以及数字技术的生态性影响带来的价值极化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危机。从数字新闻业发展的种种当下特征来看,有两个任务迫切需要新闻学的研究实践来完成。第一,对数字生态下的新闻生产、流通、接受的状况做出准确的描述和解释。这项工作是一切新闻理论建构的基础,但实际上远未完成。如前文所述,由于数字技术导致了新闻业身份边界的消解和机构文化的退场,原本泾渭分明的“5W”框架已不再有意义,如何以一种新的学术话语体系来“再现”新闻和新闻业,是新闻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这表明Picone对新闻学方法论革新方向的判断是正确的: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应该是总体性的、解释性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到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具体情境中,通过观察与互动等手段,对新闻和新闻业的生态做出原生态的记录。第二,在理论的维度上,探索具体的新闻活动与特定的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如果说传统新闻学对于学术体系与民主价值追求严重脱节的状况“视而不见”,尚属为捍卫自身(本已脆弱)的学理价值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那么在当代新闻业于数字技术的价值虚无偏向的影响下全面呈现出极化、民粹主义、反公共性特征的情况下,新闻学的研究便绝无理由再回避对自身所终极追求的民主价值的界定和申明。毕竟失去了旧的研究操作性传统的新闻学仍然可以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建立新传统,但放弃了温和的、公共性民主价值追求的新闻学则将彻底丧失自身在社会和思想进程中(原本就处在危机中)的独特地位。
不难发现,数字新闻学要践行上述两个使命,除对理论体系(本体论)的建构外,也需要方法论(认识论)的革新。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追求对日常生活中的指意实践进行总体性理解,对支配观念和行为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反思,同时有着对于温和文化民主的明确价值追求的“祛魅式”研究路径,也就迎来了参与新闻学学术体系发展的新契机。简单来说,以文化研究为方法论的新闻研究实践可以以如下三种方式进行:以民族志(ethnographic)的探析方式描摹并解读新闻活动中用户/能动者的意义生产与交换行为,进而在总体上把握数字化的新闻网络(news network)的运作机制;在对新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和观念的解读实践之中,不断自下而上地归纳数字新闻学的基本观念,建构数字新闻学的概念框架;通过对文化政治与文化经济的结构分析,探索数字新闻学的批判理论维度。
接下来,本文就从笔者用大约两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项针对数字新闻从业者和数字新闻用户的系列访谈研究出发,尝试通过对自身的研究经验的归纳与反思,来探讨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方法论的适用性(applicability)问题。
四、数字新闻学的文化研究实践
从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间,笔者针对数字新闻学的不同研究议题,对美国、英国和瑞士三个国家共106位数字新闻机构员工(84位)和数字新闻用户(22位)进行了共8项半结构或无结构的深度访谈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主要服务于笔者对“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进行建构的意图。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对这一系列研究的具体过程进行介绍,而仅从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方法论的适用性的角度,对研究的经验做出归纳。
首先,文化研究主张“穿上他人鞋子”的参与式甚至介入式的研究方式,令笔者有效地完成了数字新闻学体系建构的理论扎根(theoretical grounding)工作,从而自下而上地归纳出对数字新闻学进行理论化的六个主范畴概念,包括生态、内容生产、责任、情感、价值、重建,以及四种话语构型,亦即未来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维度:数字技术、新闻生产主体、新闻情感网络、新闻业的价值追求。由于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这些经扎根理论得出的本土概念,完全源于对新闻活动主体(包括有机构身份的新闻从业者和普通新闻用户)的新闻活动、新闻观念和新闻认知的解读。这种由不同类型的新闻行为主体协同生产出新闻学基本概念框架的理论化方式,与数字新闻业日益扁平的信息传播结构是相匹配的。简单来说,由于非机构的新闻用户在新闻生产与新闻意义解读的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因此他们的“数字新闻经验”对于未来新闻学的理论建设来说,也就是不可或缺的。同理,在这一逻辑下,新闻伦理也不再仅仅是对机构新闻从业者的排他性要求,而是成为所有新闻活动主体的行为准则,一如哈特利所指出的:当我们将新闻视为一种“人权”而不是一个职业,所谓的“新闻伦理”也就变成了一项公民素养[11]43。拥有深厚的“参与式生活经验研究”的文化研究方法,是我们在传统的、职业精英化的新闻概念框架被数字技术破坏以后进行新闻学术体系重建的有效工具。
其次,文化研究方法追求对结构分析和身份研究的兼顾,而这两者恰是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亟待革新的主要原因。传统新闻学固然没有忽视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如新闻社会学便在新闻机构研究和新闻从业者身份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但这种考察始终无法完全摆脱信息论的功能主义色彩,更倾向于将个体身份与机构文化视为有互动关系的两个系统,而非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观念共同体。在这项系列研究中,为了厘清数字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笔者对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和新闻网站在内的多种新闻机构的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借助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认同理论,最终提炼出包括“作为技能的职业认同”“基于媒介形态的职业认同”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职业认同”三个分析维度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客观/专业主义”和“自由/自主性”话语向“责任/公共服务使命”和“克制/道德标准”话语的转型过程[23]。这种将机构文化和个体行为的互动过程置于考察中心的研究路径,避免了割裂式地谈论新闻媒体的变迁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其目的依然在于提供一种对新闻业进行理论化的总体路径。
最后,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从未追求过纯粹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文化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价值导向的,因而也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数字新闻学理论对价值极化进行反思的需求,和对民主价值观重建的追求。这是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新闻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前提。正如Graeme Turner所指出的:新闻学和文化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那就是对民主化的公民身份的建设”。[16]而哈特利则以一种更有修辞效果的方式称:新闻学和文化研究都对人类生活的阴暗面,以及人类为了所谓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有共同的兴趣。[24]只不过,传统新闻学对民主价值的追求集中在程式研究(如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和规范研究(如新闻伦理与规制)上,当这种程序和规范与新闻的民主追求之间形式上的关联被数字技术摧毁,新闻学便不得不面对没有价值根基的程序民主不过是伪装的价值虚无主义这一事实。因此,长期致力于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标准的各类合法性程序进行政治祛魅的文化研究路径,就拥有了介入新闻学体系建设的认识论基础。正是在使用文化研究方法对新闻活动主体的共享价值观和价值期待进行了深入解读后,笔者才提出了以“价值重建”作为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宗旨的理论化路径[25],这将为新的数字新闻学体系补充在传统新闻学里长期缺失的批判理论面向。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本文通过对新闻学和文化研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关系的辨析,以及对文化研究作为研究路径介入新闻学学术体系的历史的考察,首先从观念层面厘清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的可能性问题。紧接着,本文又对笔者用近两年时间围绕“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展开的、包括106个研究对象的系列访谈研究经验进行归纳,探讨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方法论的适用性问题。
经分析,本文认为,在数字技术冲击传统新闻体系、为新闻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的当下,将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一种能够兼顾新闻研究价值取向和可操作性的学术发展策略。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既是可能的,也是适用的。这种可能性和适用性既源于文化研究和新闻学在本体论上所共享的一系列基本观念,也建基于新闻业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所面临的重重认识论危机(当然也可能是转机)。
本文的分析表明,文化研究的相对主义思路并不必然以解构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为研究手段,而更多是主张对塑造了“真实”和“客观”概念的历史条件进行总体性的考察。文化研究与新闻学都属于有着明确的民主价值导向的规范理论体系,而新闻学原本职业化、精英化的理论化方式让很多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这就在方法论意义上导致了新闻学的理论贫困。传统新闻学的诸种“元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渐失合理性的现实,为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重新介入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它完全有可能在质疑濒临破产的客观主义(不是“客观”概念本身)认识论的基础上,令未来的数字新闻学的理论体系更好地实现逻辑自洽,以更加有力的方式为人在数字时代的信息生活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