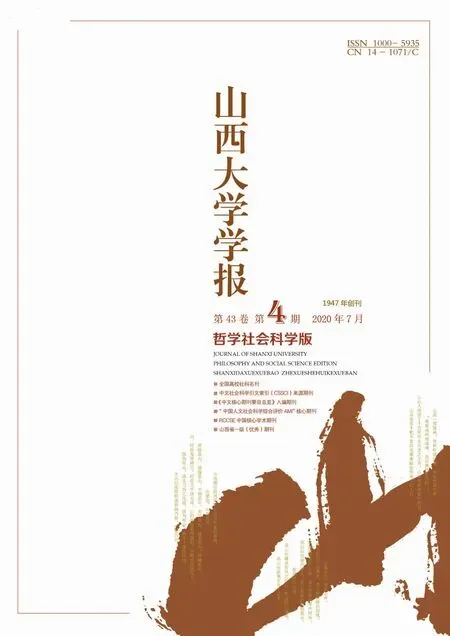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的读者认知与“重写”
——由“小冰”诗歌中的风景引发的思考
2020-12-22殷国明
成 业,殷国明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2017年,微软开发了名为“小冰”的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程序,并出版第一本由人工智能写作程序创作的诗集,由此吸引了文学界、理论界的关注,诸如诗歌的词语组合、写作的观念问题以及机器对人类创作思维的学习与主体性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一般的观念里,诗歌需要个体的“灵性”,是文学活动中最具有创造性的一种话语实践,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凭借神经网络结构与大数据语言分析,让机器人也能从事这种创造性的文学实践,无疑表明机器人对人类创作思维的学习又迈进了一大步。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诗歌写作模式与读者阅读、认知模式等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一、“小冰”诗歌中的风景审美结构
程序小冰的创作,基于微软研发的人工智能情感计算框架技术。据小冰团队负责人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学院副院长李笛介绍,在短短4天的时间内,小冰对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从五四新诗到80年代的朦胧诗)进行了超过10 000次的迭代学习,并逐渐在写作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喜好和写作技巧。难以想象“一个人类”要读完这么多诗歌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将这些诗歌里的词汇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创作当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微软程序的深度神经网络,小冰具备了从视觉画面捕捉信息产生创作思路,并进一步据此完成诗歌创作的能力。小冰的程序操作是将一张图片上传到程序当中,然后程序通过对画面信息的解析形成创作灵感并完成写作。在小冰的程序页面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其获得灵感的视觉画面和它根据画面写作的诗歌,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几乎看不见的。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历时的结构关系,读者无法看到勾起作者灵感的现实场景,只能通过文本中的形象展开想象,而在阅读小冰的作品时,这一切都变为可能。这为我们进一步分析、阐释小冰的诗歌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同时也形成了人工智能写作不同于传统写作的有意味的新的形式。
在2017年5月16日小冰的发布会上,主办方展示了一首小冰当天根据现场提供的图片创作的诗歌。(1)图片参考IT之家https:∥www.ithome.com/html/win10/309263.htm,是沙滩俯拍图,前景是海岸与复古汽车,后景是嬉戏的游人。图片是一片沙滩的俯拍图,沙滩上有几个人和一辆车,图片下是小冰即时创作的一首诗歌——“可有多的沙子/你的名字在世间又一次隐去/在最高的地方/世界睁开眼睛”。这是一首典型的“大”诗,作者在对着一个不知名的对象倾诉,沙子作为一个引发情感的象征意象一带而过,而画面中存在的几个人和一辆车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诗歌当中。通过诗作和画面的对比,我们一眼就可以发现小冰在面对这个沙滩的时候表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面对这一片沙滩的风景,小冰没有选择表现其中的人,也没有把注意力聚焦在工业化的代表——一辆敞篷车上,而是用一种宏大的浪漫主义抒情的方式去写作作为意象的沙子。在此处,沙子也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触动作者情感的象征,最后则转向某种哲理式的抒情,程序在这里显然有意回避了画面中所有工业和世俗的日常、琐碎的风景。在诗歌中,小冰在用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典诗歌的语言进行创作,这种语言使其在创作中天然屏蔽了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相关的风景和符号——这些风景与符号在20世纪90年代的口语诗歌中是着重书写的对象。小冰写于2016年9月17日的一首诗歌中,这一表现更加明显:“看那星,闪烁的几颗星/西山上的太阳/青蛙儿正在远远的浅水/她嫁了人间许多颜色。”单看这首诗,“星星”“西山”“太阳”“青蛙”,全都是乡村抒情的词汇,读者眼前自然地浮现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景象,最后一句“她嫁了人间许多颜色”,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程序中展现了现实的风景:江边一轮明月下,远处是灯火一片辉煌的都市。都市成群的建筑、通明的灯光全都没有入诗,小冰完全忽略了画面当中现代化的风景,而去描写乡村抒情式的想象(2)图片参考IT之家https:∥www.ithome.com/html/win10/309263.htm,前景是江水与渡轮,后景是灯火中现代都市的轮廓。。
在日本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作者柄谷行人认为:“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就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1]20柄谷行人这里指的当然是文学艺术中的风景。日本现代文学、艺术中的风景进入作者视域是在通过复杂的认识装置的颠倒之后,这种认识装置的构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先验性的。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热内玛格丽塔在阐释其风景绘画的讲座上提出,风景就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似乎是跳出自我去观看,但它其实只是我们内在经验的心理表象”[2]11。视网膜上的风景审美,是由人脑海中的构造(design)去结构的,而“在构造中起作用的正是文化、习俗与认知”[2]11。人们通过脑海中的文化、习俗与认知的构造,对风景进行审美结构。同样,小冰在认识图片中的风景的时候,调动的也正是程序中的审美构造。这种审美构造的来源是五四新诗到80年代朦胧诗形成的强调主体性的浪漫抒情的主流传统。小冰的制造团队选择的519位诗人大部分偏向这一长期形成的主流的诗歌审美趣味,虽然其中也有少数李金发那样的象征派诗人,但在对大量浪漫抒情文本的重复训练中,那种现代诗歌晦涩多变的象征方式也并没有占据小冰诗歌创作的核心。以于坚、朵渔、蒋浩为代表的90年代城市口语诗人的创作偏向琐碎、日常、碎片化的现代工业意象,这些诗歌不在小冰的学习库,因此就没有进入小冰对风景的审美构造当中,以致小冰在面对视觉图像中工业日常的画面元素时选择了忽略和遮蔽,完全不把它们当作可以写进诗歌中的风景。
当然,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对知识和信息惊人的学习能力让人类望尘莫及,如果在小冰的诗歌学习库中加入一批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影响力的90年代诗歌,那么其诗歌中缺失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常琐碎和消费主义的诗歌语言一定会得到补充,面对这些现代的风景,小冰也将具备强大的诗歌书写能力。那么这样是否就意味着小冰诗歌中那些风景的缺失,只是学习数据库的资料不够全面,如果拥有不断持续更新的诗歌资源库,小冰就能完全接近一个真正的诗人,创造出新的风景?从形式主义的诗歌观念出发来看这依然是不可能的。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认为艺术的存在是为了找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人对事物样貌的感知脱离既有的认知,回到“所见的视像”[3]187。这样的视像可以完全区别于观众以往审美构造中认知的风景,以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形式撞进观众的视域,形成对既有审美认知的颠覆。什克洛夫斯基称之为“陌生化”的大胆艺术观念,即“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3]187。就目前小冰的程序设计来看,这样的创造物还很难在小冰的诗歌中出现。小冰所能看到的风景完全是由人类输入的素材决定,当浪漫抒情的诗歌素材占据小冰学习库的主要部分的时候,它写出的就是浪漫抒情诗中的风景,可想而知当城市口语化诗歌成为其审美结构的主要来源时,它就会写出相应的诗歌。在这样的前提下,小冰对风景或事物的认知永远不能超出人类既有的认知范畴,也就根本完成不了形式主义追求的陌生化的创造性的诗歌活动。
除了语言,视觉上的控制也是阻碍小冰书写出新的风景的重要因素。小冰始终根据人类上传的图片获取灵感,形成自己的创作。其面对的风景,是从拍摄图片的人类视角看到的风景,这极大地限制了它创作的自由度。海外电影理论家Martin Lefebvre认为:在视觉文化的语境下,风景是自然的寓言,是视觉装置渗透的自然。[4]xv自然的图像已经脱离了自然本身,摄像机、凝视、取景框共同参与了风景的建构。镜框把“自然”转化成了“文化”,“大地”转化成了“风景”。[4]19-60在拍摄一张照片时,拍摄者选择的摄影机的机位、摄影的角度、构图的光线、景深的变化都决定了照片中风景呈现的内容和文化意味。从小冰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上传到程序中的人类摄影的图像和它书写的风景之间的关系。以上文提及的2017年5月小冰发布会上的诗歌为例,这首根据一张沙滩的俯拍图写作的诗歌典型带有一种“俯视”的意味:“你的名字在世间又一次隐去”“在最高的地方/世界睁开眼睛”,这些句子很明显受到拍摄风景的俯瞰视角的影响。“我想为你拍摄的照片,写一首诗”,程序页面上出现的第一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程序书写的风景一开始就是人类通过镜头拍摄的风景,这个风景本身已经隐含了拍摄者的风景审美和文化结构。
二、人工智能诗歌写作与读者接受
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程序小冰以其独特的形式与结构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诗歌创作中的语言与风景问题,意识到程序在创作中拥有固定的风景审美结构。而读者是否能够理解人工智能写作的诗歌中的风景,并产生相关的审美体验或阐释分析,事实上是评价这些写作价值的关键。从古老的阐释学到20世纪末大行其道的读者理论、接受美学的许多相关思考对此别具意义,在探讨小冰写作现象的时候如果忽视了相关的读者向度,将是相关现象研究中的重大缺失。目前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确存在不够系统的遗憾。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在人工智能程序小冰写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序言中提及,该程序研发团队以女诗人小冰为化名,在天涯、豆瓣、贴吧等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发布人工智能写作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更令团队惊讶的是,直到诗集出版之前竟然“没有人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女诗人其实并非人类”[5]6。在网络社区相关诗歌讨论区的读者应该说比一般读者具有更多的诗歌阅读经验,但依然无法辨认出这些诗歌的作者并非人类,这值得引起文学研究的重视:人工智能写作在读者接受层面的成功,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接受美学,引起了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对读者向度的重视。与此前半个世纪占据文论界主流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不同,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相应产生了一系列说明读者阅读理论的读者模型。其中以伊瑟尔的“隐含读者”、姚斯的“历史读者”、乔纳森·卡勒的“理想读者”三者最具代表性,三位理论家分别从阅读中本文与读者的相互作用、文学作品的接受史、文学传统对读者阐释的限定作用出发构建读者模型。将人工智能诗作的读者接受放在这三个模型中进行考量,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传统、读者接受、文本与读者互动的意义。
“理想读者”是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提出的概念。“理想读者”重视读者的阅读经验累积,强调读者需要大量的文学训练,卡勒认为如果一个读者能够“按照文学惯例,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去阅读和阐释作品,那么他心里必须明白些什么”[6]187。乔纳森·卡勒并不关注具体的个性化的文学阅读,而看重一个读者的文学能力——对于文学传统和文学惯例的了解。卡勒认为“诗学将描述一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所产生的意义就能被人的象征逻辑接受”[6]187,这种逻辑以文学传统为基础。“理想读者”为读者的阐释限定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指向文学传统。卡勒所说的“理想读者”正是人工智能小冰诗歌创作的理想读者,小冰通过对五四至80年代代表诗人的迭代学习之后所创作的诗歌,无论从意象还是审美结构上均与五四以来形成的新诗文学传统相符合。在网络社区相关诗歌讨论区的读者拥有一定的诗歌阅读经验或者说诗歌阅读训练,许多甚至还有相关的创作经验(常年在诗歌讨论区活跃的许多网友也喜欢自己发布诗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文学传统的角度来阅读阐释诗歌。在这样的读者看来,小冰创作的诗作即使不是跨时代的杰出诗作,也是符合新诗传统的优秀作品,脱胎于文学传统的优秀之作在专业的讨论区能够引起热议也就不足为怪。小冰的创作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程序系统已经可以总结归纳并运用文学传统和文学惯例,并找到它的“理想读者”。而强大的文学传统在给读者指明阐释理解的方向的同时,也在制造一种固定的阐释模式、审美惯性,这种模式和惯性都是可以被计算机程序所捕捉的。但如何突破这些模式和惯性,找寻新的意象、新的结构来达到新的审美效果,目前计算机尚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似乎为未来人类诗歌写作的新方向指引了道路。面对计算机也能遵循文学传统进行写作的事实,未来的“理想读者”在阅读一首诗的时候,需要关注的或许不再是这首诗遵循了哪种文学传统,而是这首诗在多大程度上瓦解、重构了哪些文学传统。
乔纳森·卡勒的“理想读者”试图以文学传统为读者的阐释限定一个方向,作为接受美学的代表理论家的姚斯则更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和阐释。姚斯主张“必须把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放进作品和人的相互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含有的历史连续性放在生产与接受的相互关系中来看”[7]26。姚斯更加关注读者对作品的消费、对作品的接受,认为各个时期历史的、社会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决定了一部作品的价值。在《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本文》中,姚斯对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批评家对波德莱尔诗歌《烦厌》的评价进行梳理,从一首诗歌的接受史、阐释史中印证自己的观点。通过姚斯的分析,我们看到葛底叶发现波德莱尔的诗歌背离了浪漫主义,潜藏着社会批判的重要功能,这正是浪漫主义诗歌熏陶下的读者不能接受的:浪漫主义诗歌的读者追求风景、心灵的和谐,而诗歌《烦厌》对现实与内在的不断颠倒破坏了这种和谐。对《烦厌》从世俗化的解读、主题层次的分析、句法结构上发展的分析,也分别诠释出这首诗歌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姚斯认为不同历史语境下的阐释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对本文的理解,“只要所提问题可以作为理解本文的一种新答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答案,那么问题就是合理的”[7]229,而不论这种阐释是在前人问题的基础上,还是取代前人阐释的重新诠释。读者在不同历史语境、阐释体系、“期待视野”下会对同一个文本做出截然不同的阐释。旧有的意义依然存在,而新增的意义不断叠加,历史在哪一刻终结,阐释才会在哪一刻结束,本文的意义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无限繁殖下去。姚斯的“历史读者”使阐释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漫长的游戏,作者的意图已经无关紧要,甚至文本本身的结构也只是游戏的出发点,在历史各个阶段的读者的阐释才是促进游戏进程的主要动力。在这场无限循环的阐释游戏中,无论本文究竟是出自人类作者之手还是人工智能写作程序,游戏的主动权——阐释的权力始终将牢牢掌握在人类读者手里。小冰的诗歌创作毕竟还是面向人类读者,一旦一首诗歌的创作完成,怎样阐释这首作品就与人工智能无关了,读者成了决定文本阐释价值的关键。
在姚斯看来,读者的阅读背景和展开阐释的历史语境成为阐释的核心。姚斯提出:读者在阅读一个文本的时候,总是预先含有“期待视野”。《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本文》中提及的例子可以很好解释“期待视野”:受浪漫主义诗歌熏陶的读者在阅读一首诗歌的时候,期待看到的是浪漫主义诗作中呈现的自然、风景与心灵的和谐统一。这样的读者在阅读内心风景与外在风景颠倒错乱的波德莱尔的诗歌时,并无法满足自己的期待,因而无法理解波德莱尔的诗歌潜藏的现代含义。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期待视野”事实上很大程度上由读者对过往文本的既有阅读经验决定。形成“期待视野”的阅读经验可以说也是对某种文学传统的摄取,与乔纳森·卡勒提倡的“理想读者”的文学能力密不可分。姚斯并不否认“前人遗留下来的问题,为后继阐释者创造了机会”[7]229,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读者既往的阅读经验也为对新文本的阐释创造了机会。读者对文学传统与惯例的了解和积累,无疑是影响“期待视野”形成进而影响阐释结果的重要因素。乔纳森·卡勒的“理想读者”与姚斯的“历史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补充,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阐释的方向,而阐释的方向一方面由读者的历史语境决定,一方面又受读者的阅读经验影响。从不同历史语境出发、不同文学传统结构出发的读者,会对一个文本形成完全不同的阐释。但每个时代都遗留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最终得以在文学史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反复阐释的经典文本?如果说文本的意义,是在“历史读者”的反复阐释中持续发展的,那么什么样的文本才能使得从不同视域出发的读者都能对其产生丰富的联想,并不断展开新的阐释?接受美学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尔的“隐含读者”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解释——文本之中存在一种“召唤结构”,“文本为读者预留了种种有利位置,邀请读者进入”[8]324。
“隐含读者”(3)“隐含读者”是读者批评中的重要概念,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后于伊瑟尔也提出过这个说法,但含义与伊瑟尔的完全不同,此处指的是伊瑟尔在《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中提出的“隐含读者”概念。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读者,而是文本内在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能与读者发生关系,达成读者与文本的阐释互动。伊瑟尔认为“如果我们要文学作品产生效果及引起反应,就必须允许读者的存在,同时又不以任何方式预先决定他的性格和历史境况。由于缺少恰当的词汇,我们不妨把他称作隐含的读者,他预含使文学作品产生效果所必需的一切情感,这些情感不是由外部客观现实所造成,而是由文本所设置。因此隐含的读者观深深植根于文本结构之中,它表明一种构造,不可等同于实际读者”[9]。从伊瑟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含读者”不是指实际阅读者,而是指存在于文本之中的一种构造。一些文本呈现一种开放的结构,不预先决定读者的个性与历史语境,从而能让不同个性、不同历史语境的读者都能介入其中。“隐含读者”模型旨在说明读者的阅读行为,必须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之中展开:文本的结构之中包含了读者,而读者的阅读使文本结构现实化,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意识形态下介入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从文本的种种细节到文本的综合意义。一个文本“空白”的部分越多,越能引发读者“结构化”的阅读行为。伊瑟尔关于文本结构不定性的释例主要集中在小说文本的分析上,而不定性对于诗歌来说似乎更为贴切,尤其是以朦胧多义著称的现代诗歌。在小冰的创作中,这种召唤意义填充的“空白”,是在读者的认识装置与作品背后隐含的认识装置的摩擦中产生的。
三、读者认识装置的介入与“重写”
前文分析的小冰诗歌中的“风景”背后,有着一套建立在乡村抒情文学传统之上的结构。小冰的诗歌“风景”脱胎于五四以来至朦胧诗时期的数百位诗人诗作中的“风景”,有相关现代诗歌阅读经验的读者,脑海中已经形成对相关风景的审美构造,因此可以通过小冰诗歌中的“风景”得到相应的审美体验,与文本形成互动。在柄谷行人看来,“风景”能够被发现并在文学中表现而且形成相关的文学传统,背后有一套特定的认识装置。而读者经过文学传统的训练,对文本中特定的风景形成审美认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套认识装置。读者对文本中风景产生的认同,正是形成风景的认识装置在文本外的“效果”。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分析了日本现代文学与现代日本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共谋关系,将风景的发现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性思潮联系在一起,“试图要于‘明治20年代’所发生的某种认识论‘颠倒’中,来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6。柄谷行人认为认识装置的改变,使得人的主体性开始成为风景描写的核心,“不是固有的自然风景被人们发现了,而是个性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确立使人们以全新的认识范式将自我投射到客观‘风景’中”[1]216。认识装置的改变又与内在主体性的确立关系密切,柄谷行人提出“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到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13。相对于从前基于日本传统宗教观、世界观从外部观看风景的主体来说,“内在的人”是带着全新的认识装置从内而外发现风景的新主体。日本现代文学通过新的风景呈现,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这套文学传统又是建立在内在的认识装置的改变之上。因此,读者在接受日本现代文学的风景描写传统时,也在接受风景背后的认识装置。随着读者阅读中对文本中风景的接受,读者看待风景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间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渗透进读者脑海中关于风景的审美结构,读者将逐渐形成对文本中的风景以及形成风景的认识装置的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非一定会产生。读者完全可能以一套完全不同的认识装置介入文本,从而和文本中隐含的认识装置产生对抗。正如姚斯在《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本文》中论述的那样,受浪漫主义诗歌影响的读者无法接受波德莱尔《烦厌》中的风景——他们期待看到诗歌中风景与自然、心灵的统一,而波德莱尔诗中内在和外部倒错的风景显然无法满足这种期待。读者进入文本的“期待视野”中,极有可能隐含着另一套认识装置,读者自身具有的认识装置和文本隐含的认识装置如果可以兼容,那么读者对于文本的接受就会顺畅许多,如果两个认识装置之间存在差异则会产生摩擦,进而影响读者的接受。
回到小冰的创作上来看,小冰的诗歌中描写的风景显然建立在乡村抒情的文学传统之上,即使创作来源的画面中有城市文明的风景,小冰仍然选择去“联想”农业文明的风景来进行表达。我们已经知道,小冰的诗歌创作源于对五四至80年代的新诗作品的学习,这些作品中的风景呈现背后存在一套程序装置,这套程序装置从现代诗人的作品中汲取了农业文明风景的描写,这种风景描写方式一定程度上符合许多读者的风景想象。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留下了大量描绘农业文明风景的文学作品,尤其在诗词方面——“明月”“清风”“小桥”“流水”的农业文明风景审美结构早已镌刻在中国人的风景审美基因之中。而自启蒙以来农村又是大量现代文学作品关注的重要地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作家又开始通过农业文明反思现代社会的新问题,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建立的新传统同样沉积在专业读者的阅读经验之中。漫长的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审美结构、感知方式依然在发挥作用,而现代文学的新传统又不断将读者的视野引至对农业文明的关注之上,正如南帆先生所言“文学意识到,人们的感觉和无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悠久的农业社会逐步设定了身体和感官的密码,农业文明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撤离。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文明的许多观念重新产生了重大的启示——尤其是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在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总结现代社会的时候”[10]。农业文明遗留的审美感知方式、现代文学的新传统影响了读者进入文本的“期待视野”,这套期待视野中隐含的认识装置恰好可以用于理解智能程序汲取的风景表达。这说明智能程序在汲取现代诗人的风景表达的同时,风景背后隐含的契合农业文明的认识装置也被保留了下来,并与部分专业读者的认识装置相容,从而使得小冰以农业文明风景为主要意象的诗歌被读者所接受。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小冰诗歌在部分专业读者接受方面的成功,事实上与认识装置的认同关系密切。反之,自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携带不同认识装置进入小冰诗歌文本的读者,将不那么容易接受小冰的诗歌。可以想见,一个受90年代以来城市化、工业化、日常琐碎的、消费主义的口语诗歌影响的读者,看到小冰诗中单纯、宁静的乡村风景,大概很难产生共鸣,甚至会觉得乏味——从城市、工业文明出发的琐碎的、破碎的看待风景的认识装置,天然与农业文明风景完整、自然、和谐的认识装置存在差异。
人工智能诗作中风景背后隐含的认识装置,与读者进入文本之前的认识装置之间可能彼此兼容,抑或互相抵制。这种关系将不断影响读者对于小冰诗歌的阅读、接受与阐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冰诗歌的文本呈现形式有别于传统文本的呈现方式,这为小冰的诗歌文本打开了使读者进一步介入的不确定性结构。由于小冰是通过上传图片进行诗歌创作,或许是为了突出小冰的深度学习能力,其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配上了创作来源的图片。读者在看到小冰诗歌中的风景的同时,也可以看到风景的“原貌”。这使得读者可以以自身的认识装置介入图片中的风景,去发现与文本中完全不同的风景,再通过与小冰的诗作的对比,产生更加复杂的阅读体验。这些诗集中的图片由是成为读者介入文本的入口,使小冰的诗歌呈现出与读者接受、思考共时的文本状态,同时也形成伊瑟尔所说的召唤读者填充欲望的“隐含读者”结构。这样的文本结构使读者的认知可以介入文本中的风景,避免了认识装置的差异对于读者接受、阐释的阻碍,使文本形成了一种如罗兰巴特提出的“可写性文本”一样能够引人“重写”的理想模式。
罗兰巴特在《S/Z》中提出的“可写性文本”的模式属于“生产式,而非再现式,它取消一切批评,因为批评一旦产生,即会与它混融起来”[11]6,这种文本带来读者介入“重写”的可能性,这种重写的可能性在于读者可以“分离它,打散它,就在永不终止的(infinie)差异的区域内进行”[11]6。这种有些过于理想化的文学形式,在传统的文本形式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而人工智能诗歌的文本形式却让这种文本状态变为可能。写作程序通过上传的图片进行诗歌创作,使读者在阅读小冰创作的诗歌的同时,能够看到程序小冰赖以写作的“元风景”,为诗歌阅读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建构出一种共时的开放的诗歌文本形式。这种文本形式达到了“可写性文本”的理想状态,是“无休无止的现在”[11]6,也是“正在写作的我们”[11]6。在程序界面中,读者可以看到小冰写作凭借的视觉风景,小冰诗歌中风景的意义在这个文本中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通过观看视觉风景,再反观小冰的创作,读者可以调动自身对于画面视觉风景的审美、文化结构,进入共时性的不断编码的状态之中:从江边的月光下的城市风景,读者可能想起“春江花月夜”的盛唐气象,也可能勾起关于上海、香港甚至是伦敦这样的海上都市繁华景象的幻想;沙滩上停着一辆泛着工业哑光的汽车,既可以联想到现代工业对自然的侵占,又能想到汽车广告式的潇洒出行的快意……不同文化身份、民族身份、年龄阶层的读者面对这些画面中的风景可能展开不同的想象。这些多元的文本系统并不来源于图像和文字本身,而在于阅读诗歌的读者自身的视域、经历和文化背景、知识谱系之中。当读者再将这些风景带来的感受投射入小冰的诗歌文本之中,诗歌也随着观众对风景感受、理解甚至是象征内涵挖掘的介入而产生了多元的含义。各种各样的无法确证的含义都会被读者投注在画面中的风景和诗歌中的风景上,这些含义产生的化合作用让读者始终在建构意义和瓦解意义的状态之间摇摆不定。风景有时会促使读者建立对诗歌的新的认识模式,有时又会让读者意识到这种认识模式是完全不可靠的。小冰的诗歌文本便可能将读者的想象力解放出来,引入自由构建关于各种开放含义的尝试之中,形成了读者对诗歌的“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