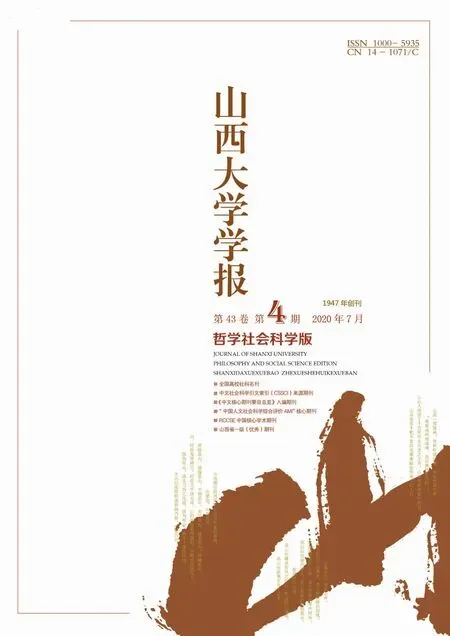赋 经 典 以 文 学 权 力
——论文学自觉精神与传统风规之学理关联
2020-12-22尹变英
尹变英,郭 鹏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文学自觉”之说,最早由铃木虎雄于1920年在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中提出。(1)见〔日〕铃木虎雄著,《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译者序中提及,提出“文学自觉”是此书的主体之一《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见此书第二章第37页)。此文最早发表于1920年的日本《艺文》杂志(见此书第2页)。1927年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在论述建安文学时,即以“文学自觉”来论定文学的独立价值,以“为艺术而艺术”来诠释文学独立的审美追求与气质禀赋。[1]“文学自觉”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它是对古代文学发展演化过程中节点性问题的重要概括。“文学自觉”命题的提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对“文学自觉”的认识,在大多数的使用语境中,偏重于叙说以辞藻华美为艺术追求目标,强调摅写个体情感,表达一己心怀的创作潮流与风气。其间似乎暗含着认为“文学自觉”是纯粹追求审美完善的潜在用意,也知会着以文学形式的精美和作者才华的超拔为精神气质的理论阈值。“缘情绮靡”成为文学自觉的注脚,“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2]成为“文学自觉”的独特气质。多数情况下在运用到“文学自觉”这样的措辞时,其学理内涵中所携带的认知逻辑也往往以类似惯性作用力的方式完成了对“自觉”前文学传统具有非文学性的、不够“自觉”的论定。那么,“文学自觉”作为观照文学史的一个带有节点性作用的论题,其前后的文学,围绕着“自觉”应如何审视呢?是否真的直到“自觉”的发生,文学才获取了稳定存在并独立发展的内在能力?是否“自觉”所带来的“独立”,才真的是古代文学得以瓜瓞绵延、代有特色的真正依据?是否“独立”存在的文学,只是支持追求形式华美、才能特异存在于文学苑囿?是否“文学自觉”之后,随着“自觉”程度的加深,随着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文学就找到了自己决定自己关注什么、反映什么与表达什么的专属领地?“自觉”之后,获得了“独立”的文学,从此不再受制于其他文化学术部类,足以按自己的学理逻辑不断丰富与持续演进?……这一系列由“文学自觉”引申出的问题,是我们在总体对待古代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时应予以深思,并给出合逻辑、合规律的解读的。
一、召唤与遥感:传统风规的权力场域与远程控制
“自觉”是个开端,它开启的道路究竟如何?在整体文学史镜像之中,“自觉”本身及其文学史效应该如何评说——我们须要延展视界,综合贯穿“自觉”及以后的文学发展演化问题,再回到“自觉”本身,以俾更好地把握其观念内涵、作用与价值。由建安至魏晋,文学开始注重“缘情绮靡”,也同时强调对审美价值实现的各种实践努力与理论思索,注重对文体的分类甄别以及专门研究。由此而后,重视抒发作者个性化人生情怀而非伦理道德层次的逻辑概括与表述成为普遍认可的文学要素。而日益重视艺术形式之美,也成为“自觉”后诗文领域的主要潮流。“自觉”作为节点,它的出现,转变了“自觉”前的文学风貌,也转变了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文学自觉”甄陶而成的“艺术精神”,是“自觉”及以后时代一直绵延的主流思想与核心价值观,正是它充斥着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各个方面,激扬着时代的格调与文学的气魄。但随着“自觉”程度的不断加深与范畴的不断延展,文弊亦随之涌现,固有传统与“自觉”间的关系就需要在新的文坛视镜中予以观照。
因“文学”萌蘖脱胎于经、史与诸子之学共构而成的学术文化,虽经“自觉”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与追求文章辞藻之美的主体权力,但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觉”前的固有传统并不会杳然无迹,反而会通过各种方式,在各种层面上对“独立”的文学发出遥感信号,从作者主体修养与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乃至事类、语汇或可资取用的篇章结构、章法安排和风格气度等“文学”绕不开的角度对“文学”产生作用。我们可以将固有传统的这种作用称之为“传统风规”。“传统风规”是“文学自觉”前古代文学在孕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文学的一些质朴见解与要求,其间也包含着对文学与经典间关系的理论认识。经、史与诸子之学,尤其是经学对文学的存在与发展一直都有着规范与约束的作用,这种作用也一直影响着文学领域内部对文学的认识评价——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与学术在已经“自觉”了的文学观念中一直都存在,也一直都在发挥作用,其权力场域仍然涵盖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化部类。
“传统风规”的作用基础,源自传统学术文化自身的影响力。其实在“自觉”之前,关于文学的意见已然众多,其合理性也并不因是否实现了“自觉”而被取消。从《尚书·尧典》“诗言志”开始,到《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到《史记·太史公自序》“发愤著书”;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到《法言·吾子》“足言足容,德之藻也”[3]60;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4]到《论衡·超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5]……关于文学应有的伦理情感内涵与外在艺术特征的认识,已经日益清晰与全面。这一系列的认识与理解,来自经、史、诸子之学中蕴含着的与人本身的性情修养和语言文采相关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见解。这些见解与古人对“文学”的理解紧密结合在一处,形成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势,对文学的存在与发展产生恒久的示范与规约作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产生的稳定见解,并未因“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而宣告离席。且因古代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一直都是一种相对传统文化学术统摄一切的话语表达。也就是说,“自觉”前的,来自经、史、诸子之学的各种对文学的理解,蕴含在稳定的学术文化思维之中,对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约束与规范的作用。及至“文学自觉”,这种作用力暂时退让。虽然关于文学独立存在价值与形式美追求的意见迸放,传统文学观念的规约作用却未尝夐然无踪——尤其是传统学术中的“宗经”式思维,因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正统思想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其影响依然巨大。它可以暂时沉默,但未尝消散,其作用的权力场域并没有隔绝于“独立”的文学领域之外。考察“宗经”观念和“宗经”式思维在“自觉”前后的起伏变换,颇能说明传统风规的显隐起伏与作用态势。
“宗经”是古代儒家学术文化的鲜明特点。《礼记·中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6]是儒家建立自己学术观点的逻辑前提。儒家本身就注重从历代典籍中寻绎人文社会传统的有益经验,也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其体系既是学术体系,也是知识系统,并且由此生发为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行动措施,因而也是思想理念与实践行动兼具的体系。而“宗经”,即向传统典籍寻绎合理内容以规约思想、指导实践,便成为儒家思想言说的话语起点与逻辑基础。较早对“宗经”问题阐说得较为深刻细致的是荀子。《荀子·儒效》有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7]133荀子之论,就蕴含着以儒家经典统摄一切文化与学术之意。荀子《正论》所谓“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7]342同时确定了“圣人”与经典共同具有的思想示范与道德规约意义——儒家之“道”、儒家认可的“圣人”与承载“道”与“圣”综合理念的“经”就是文化学术至高无上的典范,它们对后世来讲,是不应被撼动的绝对权威。西汉扬雄继承了荀子的观点,对儒家圣人的文化作用极为强调:“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对于圣人的文化作用与其在道德判断上的规约意义做出明示,“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3]82圣人在思想道德批判方面的权威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样,扬雄的宗经思想也承荀子之说而来,扬雄认为,圣人之道,流布在儒家经典之中,成为具有统摄力与约束作用的思想行为规范,在《法言·吾子》中,扬雄说:“不合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3]63其“先王之法”,即是就儒家圣人之道的规约作用而言的。在《法言·寡见》中,扬雄说:“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3]215意在突出儒家经典的文化作用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就文学来讲,扬雄是有条件的崇文,其条件就是经典的规约作用落到实处而形成的德性内涵:“玉不彫,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3]221但其对“言之文”的肯定,依附于对经典之文的合理性论定之上。比如扬雄对楚汉间骚体赋持抵斥态度:“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3]49便是从认定辞赋之作在儒家认可的德性层面上有缺失而言的。所谓“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3]60就是进一步提出的对文学情感伦理内涵与外在形式美显现的协调性要求。总之,荀子、扬雄所确立的“宗经”式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觉”前传统风规发挥作用的枢辖所在,其作用力本身,则须要通过对后世文化文学的遥感控制来实现。
从西晋时期开始,文风逐渐趋于华艳,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谓“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就是针对这种崇尚华艳的风气而言的。至刘宋时期,则“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8]67“穷力而追新”的风尚与追求华艳的专力驰骛,都与传统理念相悖。于是,在儒学、史学以至诸子领域,就会出现反对意见。在当时的北方,就有儒学色彩浓厚的苏绰改革,其锋芒所向,也旁及浮艳文风。与刘勰大体同时的裴子野,鉴于宋明帝之后的文坛浮华浇伪,“天下向风,人自藻饰”的现象,特撰《雕虫论》予以严厉批评,其文有云: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圣人不作,雅正谁分。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传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而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庭,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9]3262
裴子野的言语十分激烈,他所深为不满者,就是“兴浮”“志弱”的文坛风气,而这种风气,本是固有传统所绝对不容的。季札对郑卫之音的鄙弃,孔子过庭之训,都不会容许徒有“繁华蕴藻”而少“君子之志”的文章出现。《梁书·裴子野传》在评裴子野文时说他:“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10]可知当时流行的文风以“丽靡”为特色,这对于崇尚典实,为文法古的裴子野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裴子野对时文的批评,意味着对儒家重新介入文坛的召唤,是在弊病靡漫的文学时代,对儒家重获文学权力的期许。此际,刘勰与钟嵘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风规有所遥应,也能从打通古今的角度,对时文风气予以指斥。但崇尚华缛新奇,作品缺乏精神力量的现象并未随之改变。及至隋代统一,任治书侍御史的李谔即鉴于当时浮伪浇薄之风仍炽上《革文华书》,对南朝梁陈以来“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风气提出批评,并对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的做派极为不满,主张“弃绝华绮”,恢复以“《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11]的传统。如果不审视当时文风的实际问题,仅读李谔此文,或许会认为他有些偏颇。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偏颇”,实际缘于“自觉”后很长时期文坛弥漫着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谓“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8]136的实际情形。李谔的批评意旨,实际上也是对固有传统风规的一种召唤,是对儒家思想典籍重新获取文学权力的深切希冀。
“文学自觉”的精神核心是“独立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对辞藻华美的追求。在情感表达上,也有着蔑弃固有传统价值标准的意味,偏重表达一己之情,不再将伦理道德教化作为摅情写意的目的。但是,文学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是专就它成为可以区别于传统经、史与诸子之学的部类而言的。此部类可探研文体,也可参究形式规则与修辞技巧;可以讲求韵味,可以专究调遣驾驭辞藻的才华;当然也可以研究作为专门部类的“文学”的存在价值与发展演变规律,甚至还可以容许作者借这种专门部类以跻攀“不朽”的境界。但是,文学是人学,它始终离不开人的实践与人所存在于其中的实践关系。于是,即便是“自觉”了的文学研究,也无法规避去研究与“文学”有关的人的思想、性情、气质、修养,同样也无法度越人的道德属性去专门计较“不朽”的问题。从“文以气为主”到《世说新语》对才情的重视;从分析铨品人的才能高下到评判人的驭文能力与水准;从考量人的作品成就到评判人的知识素养……随着“自觉”程度的加深,文学研究的主体——人,成为牵动“自觉”精神,也牵动召唤传统呼声的缰索。于是,刘勰就提出人为“五行之秀”,且与文同为“天地之心”。[8]1又因为一切文章,都通过人的书写成为实在。于是,钟嵘遂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2]人,到底是文学存在的前提,是文学所依附的情实与根株。
当经学在汉代成为正统学术,其权威性与合法性就不可能不对此后的学术文化产生影响,人们也不可能因为“文学”成为“专门”的部类去绕越经学,以及史学与诸子而不学,去专门以从事“文学”自居。在当时的学术文化序列中,毕竟文学的地位与权力还不能与经史相拟,因此,所谓“独立”,只能是相对的。在作者实现李泽厚所谓“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之“人的觉醒”[13]时,他的学术素养也不可能绝缘于自己的创作活动。固有文化的“宗经”式思维还会作用于作者,作用于其创作活动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
因此,就有人看出了“文学独立”的现实状况,认识到要维护这种“独立”,就要提升“文学”作为专门部类的地位与权力:刘勰将各种文体的产生溯源至儒家经典也好,钟嵘“深从六义溯流别”[14]也罢,在他们话语阐述的背后,无不睒睗着将文学归入经典序列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维护,或许说成“保护”更为合理一些的主观意旨。即便是裴子野、李谔等人,概莫不以高高在上的儒家经典的角度论列文学,指摘文弊——固有传统的作用如此强大,刚刚“自觉”,刚刚脱离母体的“文学”,实在难以真正地去享用它的“独立”,更不用提去与经史较量高下了。纯粹“独立”的、与固有传统无涉的华胥胜境并不存在。然而,即便胜境不到,也因“文学独立”的发生,使得文学具有,且一直具有了获取其“独立性”并按自身规律与逻辑发展的权力。这种权力使文学得以保持其与传统学术的区别与差异,并要求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则进行创作、批评和研究。不过,经典作为文学得以体现其“独立性”,且滋养了前“自觉”时期文学发展传统的“母体”,并未绝对地拒斥文学获取其“独立性”与独立价值的期许,它始终牵挂,并试图涵毓着文学的每一步成长。即便是文学出现弊端,传统学术也不离不弃,更无意去扼杀“文学”以及文学的“独立性”,它会像刘勰、钟嵘那样去包容去忍让。虽然也有裴子野、李谔等人的严厉斥责,但文学已然获取了其“独立性”,并且具有了保持其“独立性”并追求形式华美的权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固有传统的规约作用与“文学自觉”的精神取向之间,形成了一种关切、援引、劝导与匡范并存;指斥、轻慢、批驳与控驭兼具的张力结构——在此结构中,经典与“自觉”了的文学之间竟如同母子关系一般,是挂念,也是叛逆;是控驭,也是挣脱。它们可以有远近,也可以有扞格,但无法彻底分离,也无法像秋蓬脱离茎干似的飘然无踪。文学始终在文化之中,也始终受到传统风规的惦念和牵挂。“自觉”了的文学终于有所成就,终于在自己的逻辑脉络中“独立”地取得了硕果,这就是《文选》。但是,弊病也随之喷涌,在充满生机的“独立”苑囿中,也奇卉丛生,异草错杂,可谓混乱与生机并存,迷离与希望兼具。“自觉”至此,“文学”在攀折了壮硕果实的同时,也蹙迫无路,前方、前程都不知如何平章。
在这样的景况中,对“自觉”前后的文学予以观照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学术对于文学可以容让“独立”,但却不容许迷失。于是,从苏绰、裴子野到刘勰、钟嵘,都出于为“文学”寻访出路的目的来干预文坛。终于,国家归于统一,新的时代文化召唤与之相应的文学精神。李谔、王通的主张遂应运而生,更进一步地发出传统对“自觉”的回归召唤。其后唐初的王勃、杨炯等人都沿着李、王的思路对“自觉”以来的文弊进行抨击。(2)参见:王通之说,主要见其《中说·事君》;王勃与杨炯的意见分别见《上吏部裴侍郎启》与《王子安集序》。传统对“文学”的召唤日渐强烈,其风规进入新文学秩序构建并玉成新文学精神的时代契机已然出现。及至陈子昂,通过对“文章道弊”的反思,通过对“自觉”后的齐梁文学之“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做派进行抵斥,明确提出了规复风雅比兴传统的要求[15]——经过苏绰、刘勰、钟嵘、裴子野、李谔、王通等人的持久努力,“文学自觉”以经典重获文学权力,经典精神与“自觉”精神融漾激扬为一体的新文学品格样态的出现而收声,对“旧有传统”的背离,也终于在否定之否定的文学理论演进过程中,向经典回归了。而“文学自觉”作为一个文学史的坚实命题,其作用区畛便覆盖在建安至初唐的整个过程之中。
二、回归与融漾:涵纳“自觉”话语诉求的新文学秩序与权力擘画
“文学自觉”促使人们深入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更深入地认识固有传统和传统经典的存在价值。“自觉”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掘进,也逐渐触碰到了“自觉”伊始人们尚无暇顾及的许多问题。“自觉”的程度在加深,“自觉”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我们过去总是在强调“自觉”激发了“人”的活力,却多少忽略了它也在新的语境之中激发了传统经典的活力。传统经典在“自觉”之初,几乎被取消了在文学方面的权力,然而,文学在其自身“专门”领域中的权力布局因“文学”本身处于“独立”之初的幼弱状态,使得“文学”在整个文化部类中的权力地位尚不足以比拟经、史,且在自己的领域内,也无法确立各种文体间的权力分配关系。“自觉”带来的并不是各文体间井然有序的,能凸显“自觉”成果的文体秩序,也没有带来相应的文体间合理的权力分配秩序。诗、赋间关系如何?诗、赋与其他应用文体的关系如何?可以纳入文学苑囿的其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6]3的篇籍与诗、赋以及其自身间关系又如何?这些文体秩序与文体权力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也使得“自觉”之后的文坛找不到合理方向,难以在清楚明白的轨迹上维护“自觉”成果,并进一步激扬气魄抖擞精神,创造新的文坛景致。这时的文学,须要一股“外力”的介入,这种“外力”,应该能赋予“文学”以更高的地位以及相应的存在权力,并且能促使文学内部的各种权力归于有序,并总体上形成能够吞吐万类、自我更生的合力。从这个角度观照,刘勰的观点与主张实际上就暗含着继承“自觉”精神,并援入传统经典风规的意旨。
刘勰之述理,一直都有着赋予儒家经典以文学权力的用意。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继而又指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其语势即由人文向文学性阐说推进。进而,刘勰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认为举凡天地间之有文者,均可纳入视阈之内。《原道》又谓:“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圣人连通天人,后人之文应向圣人讨其宗途。因此,道、圣、经交织成的文,是天地间最美之文,在刘勰看来,也最具文学权力。故《原道》接下来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8]1道有其文,人有其文,记述圣人言语者亦有其文,文学权力之获取,盖源于此。刘勰认为,圣人将道传布于人文社会。其传布的方式亦非仅在文章领域,而是通过圣人之文以实现对人性情的塑造:“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而刘勰之所谓“文”,涵盖面极广,他通过认定“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表述,将“文”的重要性与道、圣紧密贴合到了一起。所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之类的叙述,就是将圣人在文学领域中的权力以文学的方式予以表达:“若徵圣立言,则文其庶矣。”这就确定了圣人的文学权力。而所谓“徵之周孔,则文有师矣”,[8]15-16则将文学能够连续发展的内力归因于师法周孔而得以之构成文运气脉。在“道”“圣”“文”三者之间,“文”的存在与传播形态就是“经”。圣人之道对文学发挥直接作用就是通过儒家经典实施的,学者在思想性情上应该以经典为范式,遵从经典应有的,对文学进行规约的权力。刘勰认为,经典可以“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能够在人的性情最深处影响人本身,也能在文章各层次发挥典范作用。而经典又具有永恒的楷范作用,所谓“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后人若能“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可以在性情与文章方面“正末归本”。作为“性灵熔匠,文章奥府”的经典,刘勰将其纳入文学领域,将其援引至“自觉”之后的文学苑囿中来,意欲使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发展发挥持久的作用。在刘勰的理论中,“正末归本”的思想基础,就是经典具有在文体以及文体范式方面对后世的恒久影响力。他指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8]21-23经过这样的论定,刘勰就将儒家经典纳入文学之中,重新赋予它们以文学的权力,冀望于它们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持久永恒地发挥范式作用。
此外,刘勰在论述史学与诸子时也都认为它们在文章之美方面足以供学者采撷。在论述各种文体时,刘勰也极重视各种文体在创作时如何能结合文体本身的形式要求,创作出美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这些都是刘勰调适“自觉”精神与传统风规的理论努力与实践表达。“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孚甲新意,雕画其辞”,[8]514就是统合一切具有文章之美的艺术要素的努力。无论是“自觉”了的独立的“文学”,还是传统的经、史与诸子篇籍的所谓“文章”,一切有助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8]134的为文要素,学者都应更为积极地予以汲取。再譬如刘勰之于楚辞、谶纬等文献,能以开放态度予以包容,所注重的,就是它们业已具有的对当下的巨大影响力。刘勰以之为例,通过对楚辞“取熔经义,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和对谶纬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和“有助文章”的赞誉,重申了它们具有的文学权力,并且将它们纳入文学发展的洪流之中。这样,刘勰在理论上周密、完整地表述了自己既重视自觉精神,又注重以经典风规改造,甚至是再造当下文坛的努力。有了“宗经”这种援引经典入文学领域并赋予其文学权力的理论擘画,再去统合“自觉”的精神成果,“望今制奇,参古定法”[8]52的新文学秩序就能够生成并得以确立了。
“文学自觉”的集大成者是《文选》,萧统对文学的见解集中表现在其《文选序》中。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就是文章篇籍不断趋于华美的过程:“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文学不会一成不变,“变改”是绝对的,而变改的方向,则是“增华”。而文学本身对人的召唤作用也是文学得以合理存在的原因。萧统自述他对文学的喜爱是因文学可带来“入耳之娱”与“悦目之玩”的感官愉悦,也并非出自儒家式的以文养德、以言语砥砺志节的伦理愿望。萧统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表现,也很看重文学所蕴蓄的使人沉浸其中,涵茹品味的审美韵味,也就是萧统说自己之所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赏,移晷忘倦”的文学审美特性之所在。萧统十分珍视文学蕴含的这种审美特性,甚至认为,经史之篇籍,无须去课求此种特性之有无。关于诸子之文章,萧统认为它们“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史书之作“盖乃事美一时,流芳千载,概早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所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于是在《文选》中不予收录。将经史篇籍在文学中的权力以“不能文”和“事异篇章”为因由,巧妙地剥夺了。至于儒家经典,萧统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说,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16]1-3在看似无可辩驳的推举之后,以难以芟夷剪裁为借口,褫夺了儒家经典在文学领域的作用权力——经、史与诸子就这样在“崇敬”中失去了在文学领域发挥作用的权威与权力。而其《文选》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名义,将文学的词采之美与愉悦性情的价值予以强化,从而自然而然地将经、史与诸子“请”出文学府苑。(3)除了《文选》,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统又择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今萧统集中有《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或疑《诗苑英华》即本传中所说的《文章英华》。所以,专门选取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诗文予以裒辑,是萧统表达其文学主张与审美理想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对文学自觉中注重审美呈现与个性表达理念的一种落实。
与萧统相较,萧纲则更进一步。比如对向经典致敬的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8]614的用典做法,萧纲十分不满,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指出: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9]3011
对于以掎摭典实为指归的创作,萧纲是反对的,认为“吟咏情性”者,本不须攀比经诰。萧纲还将问题置于古今对立的层面上予以观照:“若以今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在其所谓“今”“古”,即自觉精神与传统风规间出现龃龉甚至抵牾时,萧纲从他所推许的审美角度,肯定了“今”,对崇古表达了不满:
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9]3011
萧纲推崇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反对过于规摹经典。这也正是对“自觉”精神的一种珍视。尤其是还能认可声律论,并对诗文创作不去“精讨锱铢,核量文质”表示不满,而所谓“精讨锱铢,核量文质”其实就是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形式美规律的探究,这一点与萧纲反对古今间“俱为盍各”的态度一样,都是他对自觉成果与自觉精神的重视与维护。至于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所说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9]3010则属一种强调主体个性的情绪式表达,不足为意。
至如徐陵所编《玉台新咏》,或是由萧纲授意。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即云:“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17]萧纲强调文辞华美,重视吟咏性情,其理念的逻辑延伸最起码逗引了宫体诗格调的出现。刘肃所载,可备一说。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专就其所选诗作的审美向度与艺术格调做了铺排渲染,谓其诗“无怡情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所谓“新诗”,徐陵亦不避讳,至以“艳歌”称之,并谓其诗“曾无忝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18]“无忝雅颂”,实则未必,“靡滥于风人”,则契于厥旨。要之,萧纲、徐陵在重视诗文形式华美,强调诗文摅写一己性情上,并不背离“文学自觉”的精神。然过度张扬,完全蔑弃固有传统的规约作用,任由诗文千篇一律的去华美,去摅写几无现实关切的一己情怀,则又背离了艺术本身具有的真善诉求,反而出离了自觉精神,更与传统风规渐行渐远了。
由王充、葛洪及至萧统,对文学发展创新持支持的态度,这种态度与文学自觉的精神相契。由陆机、潘岳等人的创作实践而至萧统、萧纲的相关主张,对文风华采的态度也十分显豁。这种尊重文学发展,珍视文学形式美期许的见解,都源自文学自觉的命题要求与精神旨归。虽然当时的诗文风气有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对自觉精神甚至产生了“反噬”的作用,但它们对自觉精神本身的诠释与发挥,是自觉本身的题中之意。有了屋宇,才能讲求装饰布置,装饰布置过于华缛,可以改变,但若连屋宇堂室都没有,什么都无从谈起。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中,刘勰、钟嵘、裴子野等人能够将固有传统援入文学苑囿,使之获取新的作用权力,并将这种权力用以擘画新的文学秩序。刘勰之纲领毛目与钟嵘的六义为本,其实都是对新的文学权力与秩序的理论设计与具体安排。这样整合融漾传统与现实的努力,就有了文体序列与权力整合方面的实效形态——但是我们在论述“文学自觉”时长期都将其忽略了。
三、结语
结合文学史,尤其是“文学自觉”前后在发展演化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与演进轨迹,我们可知,所谓“文学自觉”,在部类独立方面,终有所成。自此,文学遂成为可与经、史与诸子之学相比类的专门领域。不过,这种专门化并非与后者完全绝缘,而是声气相通,精神相济,“独立”的是形式门类,而非精神学理。同时,“文学自觉”的成果还表现在“独立性”的获取和自觉按照自己规律演进并持续发展的权力被承认。文学在“自觉”后有了自己在知识谱系与学术文化序列中的地位与权力,但此地位与权力虽有“为文不朽”说的振臂鼓荡,还不足以去充实“独立”了的专门部类,使其气雄力沉,足以傲岸经史,比况诸子。再者,“文学自觉”创设了一条专门讲求文章辞藻形式之美的路途并形成强大的氛围和气势,也因之催生了种种弊端,种种看似合理,实际上会凋伤艺术精神的做派和风气——这种因“自觉”而释放生机,又因生机勃发而出现弊病的文学史存在,是“自觉”成果的另一面。因此,“文学自觉”的确使文学有了自己的开始,却并未开启出一条使文学可以长久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自觉”释放了“艺术精神”,但并不能充分颐养并持续供给这种“艺术精神”。那么,除了“独立性”和专门地位的获取以及按照自身逻辑演进的权力的获得以外,文学的出路与未来命运并未能得到明示,“自觉”的理论能量与“自觉”了的文学局面并不能有效匹配并形成稳健演进的内力。因此,重新邀约固有传统,重新将固有传统的精神风规援引入文学领域与文学思维之中,就成为提高文学地位,增强文学权力的合理思路。通过对“宗经”式思维的强调,通过“深从六艺溯流别”的理论阐释,重新赋予经典以文学的权力,同时抬高文学,使文学得以在传统学术文化的卵翼之下增强权力,获得更有权威,也更合法化的腾挪空间,就成为“自觉”出现了问题时革除弊病,整肃风气的有效手段。这种针对文学前程而设计出的思路,至初唐时期,终于得以实施并真正解决了问题,也为以后文学的发展寻明了方向,找到了路途。至韩愈、柳宗元以及周敦颐等人对“文”“道”关系做出论断并渐次形成文学史共识,古代文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理路及其与其他部类间关系问题就有了稳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