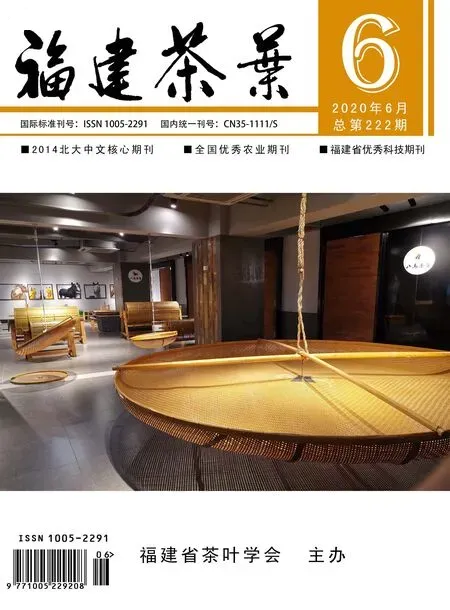“致富”路上的“同情”伦理关切
——基于茶文化的视角
2020-12-22吴珍
吴 珍
(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四川内江 641100)
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在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社会经济飞速进步发展的今天,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法律是冷冰冰的,而道德是主动的充满温暖的。事实上,早在17世纪时,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已经给了我们指导,那就是通过社会善良的价值取向,约束个人的利己,形成道德行为准则,为社会成员所尊重和遵守。
1 《道德情操论》的伦理维度
《道德情操论》全书共分为七卷,洋洋洒洒近40万字。斯密继承和运用了休谟的“同情理论”,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博爱、责任、赞许、正义、良心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开篇即谈“同情”,认为同情心是人类天赋的本性之一。斯密通过分析个人道德情感的本质和社会道德评价原则,指出利己主义的人应该如何调控自己的情感与行为,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揭示了在构建良序合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1.1 同情——斯密伦理体系起点
作为亚当·斯密伦理体系的主要阐述载体,《道德情操论》是严谨而广泛的。同情是斯密伦理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同情是人的本性、社会行为及美德等一切的基础,是所有人类良好道德和情感的基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斯密的同情观与中国古代的儒家先贤主“仁爱”、扬“五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更与孟子“恻隐之心”高度统一而共生。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同情”一词解释为:在移情基础上对他人的苦难处境或不幸遭遇产生关怀和理解的情感反应;给予物质帮助的态度和行为体现;对别人的言语行为、立场观点表示赞成和肯定。事实上,同情意味着我们会乐他人之乐,悲他人之悲。正如斯密所言,包括同情或情感共鸣在内的伦理中的原始性情,并非只存在于有德行的人身上,罪恶的流氓与犯罪分子也有同于他人的痛点和点,这是使他并未完全丧失同情感的内在心理机制。
“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情感,我们希望朋友同情自己的怨恨的急切心情,甚至要求他们接受自己友谊的心情。”在一定意义上,爱是同情的一种特殊表现。斯密举例说,当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象或真切地看到受难者正被击打腿或手臂时,我们会本能地收缩抚摸自己的腿或手臂,似乎错觉以为自己正在被击打。当我们看到舞台上轻歌曼舞的的表演者时,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随声哼唱或舞动身体。甚或路边看到盲人,我们会不禁感慨眼睛的重要性,或是想象自己如果处在一片黑暗的世界怎么办。因此,同情是在认识和理解到了他人言行观点并与他人言行观点和合之后,才滋生的相似的共通的情感。“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愤恨来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方法来判断它们。”因有同情感,我们会理解、在意和关注他人的情感体验,并在道义上或物质上给予帮助。因有同情感,我们会调控自己的言行以及情感,避免自私或私利的行为,追求言行的道德化。
斯密的同情观认为,我们审视他人行为时,会运用想象把自己分成审查者与被审查者两体。这样,我们既以旁观者的立场和比较公正的态度评价他人的言行,又能置身事外的想象自己评判自己的言行,这样可以让不同的人在相同或近似的处境下产生相同或近似的情感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流与评价,从而衍生出为大多数人接受和共鸣的社会一般伦理准则。
1.2 合宜性——行为的伦理标尺
“合宜性”贯穿于《道德情操论》始终,亚当·斯密明确定义“合宜性”,其内蕴在于社会之于众人言行的道德评价标准。当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场时,我们会根据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理解导致他人行为的情绪和动机来决定我们是否同意这种行为。如果我们与旁观者有共通的情感体验,我们就会认为旁观者的是正确的,于我们而言是合宜的;反之,则是不合宜的、不被理解甚至冲突的。斯密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合宜性”,认为利害关系本身并不能单独作为人们言行的伦理评判依据,而要与言行的心理机制、效果机制结合成为“合宜性”。在“合宜性”这个伦理标尺上,斯密认为谨慎、自制、正义、善良、仁慈等才是符合的尽善尽美的姿态。
同情原理之下的“合宜”行为,烙上了美德印记,表达着一个美好伦理愿景。诚然,斯密将“合宜性”作为社会大众的言行的基本要求,既是一种道德标尺,也是一种社会言行姿态,对促进社会和谐完善有重要导向意义。“正确的合宜性需要遵守一切诺言,比如对公共利益负有的责任,对那些出于感激、亲情或善心而要赡养和抚养的人应负有的责任。”社会人充斥着社会责任与角色,并非“单向度”的人,不能也不可能一切“为己”、“利己”。亚当·斯密强调人际交往中的信义与责任感,认为物质利益的追求要受制于社会道德,不做伤害他人的事,而要努力去“利他”。可以说,一个成熟的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社会大众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社会大众的言行有“克己利他”的本能或习惯性倾向。
2 “致富”与“行德”的规约制衡
众所周知,《道德情操论》前后出版了六次,期间又交替创作《国富论》,足见两部著作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分别架构起斯密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学思想,并共同构成斯密整个学术体系。前者谈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指出个体要行德,做有道德的人。后者又谈热衷于追逐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引导个体经济致富。《道德情操论》把思想行为归结为同情,而《国富论》却把思想行为归结为自私,是看似矛盾的对立统一。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伦理原理基础。斯密认为,社会人不可能单纯只有利他之心,也不会单纯只有利己之心。有人曾经说过“不读《国富论》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如前所述,即便是那些一心追求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也会受制于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情感因素,也有其道德依托与道德角色,比如家庭关爱、自尊和慈善等等。
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其丰富。我们一边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一边又忧虑于传统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抵制的现状。物质生活的精致华贵遮掩不了精神生活的饥饿单薄;宽敞豪华的住宅填充不了心灵的漂泊无依。加之近些年的诸如“扶不扶老人”的敏感新闻事件,频频叩击与呼唤社会大众的良知和德性。人们在“致富”之路上越走越远,在伦理德性的道上也渐行渐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扭带因物质交易关系导致一定程度的断裂,甚而被物质利益或快餐式的情感所取代,“私心”“利欲”频频蒙蔽了仁慈、善良的双眼。在虚荣、自私、妒忌、贪腐、忘恩负义等黑暗情感因素的包围下,急需重锤塑造个体的同情、责任心、公正、善良、仁慈等伦理关切,更多地展现自己的“利他”之心,捍卫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
3 茶文化视角下“致富”路上的伦理关切
根据斯密“合宜性”的标准,应建立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框架,成就“致富”与“行德”的统一。平衡自己与他人的利益点,限制私利帮助他利,以善良仁慈的作为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点和茶文化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
3.1 培育在经济领域的经济道德
重拾斯密伦理观,培育在经济领域的经济道德。谋求利益的“取”是我们的行为趋向,而我们“取”的行为也要遵循一定的“道”即伦理准则。而茶文化的“精行俭德”也对人们有类似的要求。“精行”是指行事而言,茶人应该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行事,不逾轨;而“俭德”是就立德而说,茶人应该时刻恪守传统道德精神,不懈怠。同样,在经济领域里,企业有自身社会责任,不是也不能完全谋取利益,这样是不可能长期发展的。企业必须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在自己担负成本的基础上经营获利的同时兼顾他人与社会公利,使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才是合宜的、慈善的企业,也才是利己利他的高尚经济道德主体。
3.2 斯密伦理观与茶文化的互相促进发展
伦理道德是触类旁通的,斯密伦理观与茶德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然而茶德“重理论轻实践”“追求个人精神理念”的倾向,在引导个人践履道德规范上还不。因此,积极吸收斯密伦理观中正义、仁慈、克己等合理内核,对促进我国茶德及其经济文化交流新发展,提高人们文化素养有积极作用。
3.3 重塑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秩序
人人都有同情心,每个人都应将自私的情感控制在合宜的范围内,弘扬发展“责任文化”。以自己的道德情感影响周围的价值认同,引领培育社会美德和公德,进而建构起注重德性的社会道德实践关系,为重塑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秩序提供思想基础。届时,不再以监督监视来迫使人们工作,人们自觉尽职敬业,树立起岗位的道德情操,营造生活与工作中的强大责任氛围。
总之,重拾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依托“同情”、“合宜”“善良”“责任”等合理伦理内核,茶文化作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一起,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一种善良美好的道德情感,引领人们穿越昏暗的私欲丛林,让伟大的思想照进现实社会。因为唯一比阳光还要灿烂的,只有道德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