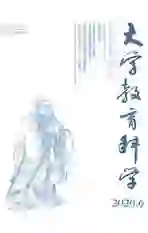英国教育史研究的传记叙事模式述评
2020-12-21武翠红
摘要: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起源于对教育大师的历史赞歌。20世纪50年代至今,它在自身发展历程中,随着理论基础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研究取向的新教育传记叙事模式。其主要有三类研究取向:社会史取向的教育者个人传记研究,架起了个人-教育-社会之间的桥梁;社会文化史取向的女性主义教育传记叙事研究,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教育历史联系起来,呈现教育发展中女性的声音;情感取向的教育主体传记研究,分析维度从“语言结构”转向“情感经验”。英国学者通过三类研究取向的传记研究,引入私人化史料叙述传主的故事,明确传记阐释教育历史的“叙述限度”,彰显了传记叙事的价值维度,实现了教育史研究的视域转换。
关键词: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情感经验;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649.5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6-0102-09
英国教育史学兴起之初,传记叙事就是其主要编纂方式。传记叙事起源于对教育大师的历史赞歌。20世纪50年代至今,英国教育史学传记叙事模式主要有三类研究取向——社会史取向的教育者个人传记研究、社会文化史取向的女性主义教育传记叙事研究和情感取向的教育主体传记研究。英国学者通过这三类研究取向的传记研究,将大师个人传记研究扩展至社会群众、普通教育者、劳工阶层和女性的叙事上。同时,他们还引入私人化史料叙述传主的故事,明确传记阐释教育历史的“叙述限度”,彰显了传记叙事的价值维度,实现了教育史研究的视域转换,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传记转向”[1]。本文拟对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兴起和发展状况进行回顾,深入分析不同取向的教育传记叙事模式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读英国教育史学者如何在“传记”和“教育历史”之间实现平衡,以进一步剖析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背后的史学意义。
一、 伊始之处:教育大师的个人传记及其历史赞歌
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传记一直都是历史编纂的主要方法之一[2]。而在英国教育史学发展历史中,传记研究可以追溯至1868年奎克(R.H.Quick)的《教育改革家评论》(Essays on Educational Reformers)一书。奎克采用传记编纂方法对西方教育改革家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研究。在奎克看来,教育改革家能够传递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教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和主要力量;教师通过对他们传记的阅读能够激发其传播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热情和激情。1881年,在《教育理论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ies)一书中,布朗宁(O.Browning)提出教育史研究不应只是教育改革家的生平和实践活动,而应是教育理论演化的历史,因此应关注教育家的理论思想研究。在《教育理论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ies)一书中,布朗宁以传记形式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教育家的教育理论思想进行阐释。之后,亚当森(J.W.Adamson)在奎克研究的基础上,将17世纪现代教育先驱培根、夸美纽斯等人的教育思想以传记形式介绍给读者。
1911年,科林伍德(W.G.Collingwood)的《约翰·拉斯金传》(The Life of John Ruskin)出版。作为拉斯金的学生,科林伍德用传记的形式呈现了拉斯金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本书是在拉斯金在世时着手写的,他看到了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得到了拉斯金的认可”[3]。在传记的最后一部分,科林伍德叙述了拉斯金1870~1900年在牛津大学任讲座教授及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校长的经历。在科林伍德的笔下,个人传记就是一部个人思想史,在介绍拉斯金的生平中呈现拉斯金教育和教学思想,同时兼顾涉及的历史事实,尝试平衡“传记”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以“传记”引出“历史”。科林伍德的史学思想影响了教育史学界,学者们对传记题材的教育历史研究较之前的兴趣有所增加,并且更加注重在轶事和细节中记录和辨析史实,注重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伪。
除了在教育史以及历史著作中以传记形式介绍教育历史上传递民族精神的大师的生平和教育理论、思想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教育家、教育改革家的传记研究,如《洛克传》(The Life of John Locke)、《约翰·弥尔顿传》(The Life of John Milton)等。这类关于教育历史上的大师——教育政策制定者、打破现有模式的教育管理者、推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家的历史赞歌式传记研究,形成了英国教育史研究叙事模式中“传统的个人传记研究”[4](P609)。传统传记叙事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坚守教育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即通过叙述教育历史上传递民族精神的大师思想、实践、活动、理论,探讨教育史自身的发展变化。这种传记叙事仅仅是停留在教育史研究的本身来叙述过去教育者的故事,不涉及教育发展和教育者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其次,书写英雄史观视域下教育者的历史赞歌。在这些传记里,多是记录英雄人物、名人的生平和德性,将教育者视为民族文化、精神的傳递者和教育发展的推动者,进而赋予教师职业神圣的光环,以此来激发和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正如沃森(F.Watson)所说:“教师应该细查教育历史中的‘大师表……”[5](P59)。再次,带有文学色彩的个人传记。受传统史学的影响,传统教育史学家将教育史学视为一门艺术,“教育史家的综合和解释工作与艺术工作相近,必须包含想象和直觉能力”[6]。学者们将教育者参与的教育事件故事排列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一部关于教育者生命历程的历史作品,目的在于为人们树立榜样,提供参照,重视叙述的宣传和借鉴功能。因此,这样的历史作品需要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能够激发和推动读者,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叙述以便呈现鲜活的具有影响力的教育者形象。最后,这些传记中很少涉及传主不好的地方,多是高歌赞扬,对其性格、思想中好的地方加以宣传,注意力放在大师身上高贵的品质和有利于推动当前教育发展的思想和实践活动方面,将历史知识固定在传记写作者的道德选择上。
二、批判与创新:引入“外在理路”的英国新教育传记叙事模式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界发起重新阐释英国教育历史的呼声,传统教育大师的个人传记研究受到批判。学者们认为早期的教育大师个人传记研究只遵循了教育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即仅是就教育谈教育,忽视了教育史研究的“外在理路”。所谓教育史研究的“外在理路”即教育发展变化与社会变迁、相邻学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教育史研究应关注教育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随着教育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文化史转向、语言学转向和全球化转向,教育史研究的传记叙事模式进入了新教育传记叙事阶段。随着关注焦点和理论基础不同,新教育传记叙事模式内部出现了两类不同取向的传记研究。
(一)架起个人-教育-社会之间的桥梁:教育者个人传记研究的社会史取向
1959年,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批判传统学术研究的僵化界限——割裂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呼吁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社会学的想象力指“能够捕捉到从远隔千山万水到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7]。米尔斯认为研究者应具备将个人经历与历史知识联系起来、并能将个人问题与社会公共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的能力。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思想影响了西方教育史学者,他们开始在教育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教育者的个人故事与社会结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由此,传记的叙事模式呈现了社会史的取向,开始考察传主的职业生涯、社会背景、交往圈如何影响教育发展。在《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一个局外人的旅行》(James Kay Shuttleworth:Journey of An outsider)一书中,理查德·塞拉克(Richard Selleck) 引入了传记研究的“外在理路”,成功地将传主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作为一位新兴中产阶级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在理查德·塞拉克看来,沙特尔沃思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希望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认可和接受,并融入这一阶级的生活”[8](Pxiv),然而,他“最终成为努力捍卫社会结构的受害者”[8](Pxiv),依旧是城市的“局外人”。在叙事内容和叙事取向上,理查德·塞拉克重视社会阶层因素对沙特尔沃思历史叙事的影响,巧妙地将沙特尔沃思个人经历与当时社会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呈现了一个圆形的人物形象——“残酷时代的典型缩影”[8](Pxiv)。该书被称为一本值得看的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传记,“采用了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9](P4)。
而在英国,加里·麦卡洛克教授的西里尔·诺伍德传记研究,完美地阐释了教育史研究中如何运用传记方法,以传记形式清晰地呈现了19世纪末至二战时期英国中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画面。在这本传记里,加里·麦卡洛克教授对西里尔·诺伍德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将诺伍德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其生活、教育、职业生涯联系起来,深入分析了诺伍德的教育、社会和政治理念,探索了中等教育理念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加里·麦卡洛克教授还清晰地呈现了中产阶级在中等教育发展中的态度和作用、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情感和形象,以及公学与现代文法中学之间的矛盾,深刻剖析了中等教育改革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麦卡洛克教授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理论依据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9](P3)
与传统的传记研究不同,受社会学影响的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更关注事件背后意涵的建构过程,在叙事内容、叙事对象、叙事方法上均呈现不同的特点。一是在叙事内容上,重视讨论社会结构与个人事件之间的关系,将传主涉及的教育事件和实践活动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的政治文化分析和整体的历史经验叙事,涉及阶级形象、阶层意识以及社会角色的分析。在教育历史事实的逻辑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学者们试图探索教育实践、课程改革、教育政策制定与颁布、教育改革等问题的制度根源。二是在叙事对象上,学者们对教育历史上被忽视的、争议较大的教育者进行叙述研究,分析传主的政治信仰、教育思想以及历史意识,以全面呈现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三是在叙事方法上,学者们以《社会学的想象力》为理论依据,实质上是建立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引入跨学科方法,从多维度、多重视角对传主一生的经历进行综合阐释。
(二)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女性主义教育传记叙事的社会文化史取向
随着女性主义史学叙事的兴起与发展,学者们倡导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在对女性教育改革者、女教师及女校长进行研究时,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在教育改革中的缺席及失声等归因于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提倡重新认识私人领域的家庭劳动价值,依据新的价值观描绘女性在教育历史中的形象。琼·西蒙——“英国第一位反传统习俗的教育史学家”[10]依据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的工作分工,开始重新阐释英国教育经验。1955年,她撰写了《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1860~1931) 与英国保育学校》(Margaret McMillan (1860~1931) and the English Nursery School)一文,力求通过英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麦克米伦一生的职业生涯,叙述其在英国保育学校创立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琼·西蒙尽管认可社会学对传统史学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但她“认为真正地理解教育,应主动掌握教育发展的历史知识遗产,不能被动接受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制约和影响”[11]。因此,琼·西蒙的社会史取向传记叙事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特色。
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已让学者们认识到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具有政治意义。伴随着英国新史学的社会文化史转向,英国教育史研究视线下移,除了研究精英人士之外还关注普通民众,不仅叙述他们的教育故事,还注重解释和说明教育故事背后的研究意义所在。正如戴豪斯(C.Dyhouse)所说:“教育是女性取得地位和权威的公共舞台,在公共舞台上,可以探讨性别政治的社会史以及性和性别史。”[12]因此,女性主义者要建立关于教育的合法化解釋框架,搜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变得尤为重要。1977年,在《孝顺的女儿们:女性谈论自己的生活》(Dutiful Daughters:Women Talk about Their Lives)一书中,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n)和迈克林德(Jean McCrindle)运用丰富的口述资料呈现了不同生存环境下女性群体意识的考察。女性主义史学叙事开始从个体转向群体的研究,注重历史个体与历史群体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理解女性群体的共同教育经历提供了历史解释的路径和方法。在《英国教育史上四位杰出的女性》(Four Exceptional Women in British Education)一文中,哈罗德(F.Harold)和海伦(F.Helen)认为四位杰出的女性已经发现学校不再是教孩子识字和加减法的地方,而是她们所处时代生活的一部分[13]。1981年,戴豪斯叙述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女孩群体社会化的过程,既把教育如何固化了女性传统形象的故事叙述好,又解释和分析了教育事件背后青少年女孩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呈现了女权主义和女孩教育之间的关系[14]。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教育传记叙事运用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经济、政治制度,同时也关注性别观念和文化意识。正如卡罗琳·斯特德曼(Caroline Steedman)所呈现的女性主义教育传记叙事框架那样,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社会关心的教育问题或事件的过往具象,这需要史学家通过多种路径创建融合个体历史经验与整体历史视野的叙事范式。英国女性教育史学家古德曼(J.Goodman)将“教育传记研究置于性别假设的批判中,以便将莎拉·奥斯汀(Sarah Austin)融入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为国家普及教育体制而开设的英语运动故事中”[15]。在《女性和教育,1800~1980》(Women and Education,1800~1980)一书中,古德曼和马丁(J.Martin)明确了“传记研究有助于探索个人生活和公共世界的联系”[16],通过分析女性个人生活与教育公共问题之间的关系和交叉,叙述了1800年至1980年间女性教育改革者的历史故事。此外,为了进一步回应女性主义教育史研究的最新趋势,马丁还“以公立学校一对夫妇的传记为案例剖析了传记方法如何研究1900年至1960年伦敦的阶层政治和女权运动,进一步阐释了传记与历史之间的交叉、生活经验与历史经验的差异、代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重要问题”[17](P515)。同时,马丁还明确了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传记方法主要关注的七大问题:“(1)主流/支流/边缘之间的关系;(2)个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3)个体与集体实践的关系;(4)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5)性别与社会资本的关系;(6)‘不同的定位——积极的、消极的、肯定的以及力量的来源?(7)主体间性理论化: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17](P519)
女性主义教育传记的叙事研究重塑女性形象,叙述对象既有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谢娜·西蒙等历史人物及其女性主义教育观念,也有普通女性群体的个人教育经历和生活状态,既关注女性个人教育历史记忆,也关注女性集体教育历史记忆,从女性的视角研究教育历史上教学、课程、教师、学校环境等重要主题。在叙述内容表达和逻辑形式上,女性主义教育传记的叙事研究突破了传统传记研究范式,引入了性别分析范畴、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畴、布迪厄的文化理论,揭示了性别形象与教育制度、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之间的关联,将生物性别化的个体和社会性别化的整体联系起来,强调女性作为教育历史主体的独立自我意识,辩证地理解女性与教育改革、教育事件的关系,带有强烈的现实意识、政治化与实用取向,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传主所处时代的历史具象、教育环境和意识形态,解读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女性的心理和心态,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取向。
三、从“语言结构”到“情感经验”: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情感取向
21世纪以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开始转向情感经验。它萌芽于性别研究,成为女性主义发展新趋向,迅速扩展至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情感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代表了史学的“崭新方向”[18]。随着史学领域情感转向的发展,英国教育史研究也开始关注情感。罗伊·洛(R. Lowe)、麦卡洛克等在担任英国教育史学会会长的主题发言中,都运用自传形式呈现了自己的学术历史。这些学术记忆里包括英国教育史学者的教育情感。马丁以此为切入点——遵循从特殊个体到一般的思路,深入分析了“英国教育史研究的传记转向”[19](P88)。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史研究不仅要包括教育历史人物理性层面的思考和行动,还应包括传主的感性和情感因素,这样的教育传记叙事解释才能完整。但是,在情感转向的同时,英国学术界还立足于传记研究的历史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对教育史研究的传记叙事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讨论,进一步探寻了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创新方向和路径。教育史研究的分析维度从“语言结构”开始转向“情感经验”。
(一)在传统与新教育传记的辩论中,明确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
2002年,罗伊·洛指出:“随着历史学家对女性教育的研究,教育史上的‘精英男性學校正逐渐被‘精英女性学校所取代。”[20]“长期以来,很多人对女性主义教育研究领域的传记研究持保留态度,将其视为学术史上不太合适的流派。”[19](P92)正是在这样的质疑背景下,学者们对传记方法究竟如何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如何在传记和历史之间实现平衡、如何更好地阐释教育史,进行了再思考和讨论。加纳德(P. Gardner)分析了新旧教育传记之间的不同,认为“传统教育传记研究主要关注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打破现有模式的教育管理者;20世纪后期,传记研究转向了社会学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对精英的教育经验和激情抱负的书写已经转向了对社会群体、劳工和妇女的关注,尤其关注教师、学生和家长”[4](P609)。加纳德认为传统与新教育传记方法建立了政策和实践的分析维度,赋予了它们超乎本身意义的重要性。但还有另一种研究模式,学者们关注这些历史人物——他们既不是传统的精英人物或新教育传记中的劳工阶层、女性和社会群体,也不是政策制定者或教育实践者,而是处于精英和下层社会两者之间、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之外的历史人物。因此,加纳德以一种新的形式阐释了被史学家忽视了的萨甘特(E.B. Sargant)在1884年至1905年所参与的教育改革,明确了其在教育发展中的历史贡献。马丁回顾并分析了传记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教育史研究的传记叙事是阐述思想起源的一种体裁,是分析社会选择和替代可能的工具,是观察社会变迁本质的窗口,是阐释人类思想与社会结构之间交叉的方式”[19](P98)。马丁呼吁未来教育传记叙事研究应“从生活史研究中学习理论和知识以丰富对‘人民教育史的理解……要关注教室里所有人的经历及其意义,确保进步的思想以及为进步思想所奋斗的故事不被遗忘”[19](P102)。不难看出,加纳德和马丁尝试在新旧教育传记叙事模式之外探索教育传记的新方向,即通过关注新旧史学所忽视的群体,以传主的生活史研究管窥教育的历史变革。
(二)关注情感经验: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新走向
在西方,身心二元论依旧占据一定的地位。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身心是相互联系并交织在一起的”[21]。正是在身心二元論的批判声中,英国学者们开始关注情感、心理等因素。“2010年以来,教育史学者已经像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将情感视为后天养成的习惯。从长远来看,这种习惯像其他社会和文化实践一样,可以被控制、学习和遗忘。”[22](P690)学者们开始分析“维多利亚情感主义”“民族爱国主义”“斯拉夫人的爱”等情感,并把学校视为情感习惯培养和发挥作用的场所[23]。这打破了传统的将“理性”和“感性”割裂的史学观念,学者们开始关注人类情感生活的社会性和感知性。
首先,学者们扩展了教育的定义。情感取向的教育传记叙事模式要求对教育生活的本质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也就是对教育进行重新界定。学者们认为只有重新界定教育,才能真正改变教育史的编纂方式。“教育史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批判视角从正规的学习环境扩展至非正规教育,包括青年组织、大众媒体和社会运动”[24]。对教育的重新界定,既包括教育史研究视角的转变,也涵盖了教育史学研究范围的延展。
其次,反思社会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研究。新教育史学家虽然有时会记录教育历史人物的情感波动,但没有进一步描述情感波动对教育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在关于土著居民抵制殖民者文化中,马修·尼尔(M.Kneale)“从殖民地的抵制到寻找一种自救方法到最后打败殖民者的思路,论证了土著居民对殖民者的影响”[5](P178)。在这里,马修·尼尔将殖民地的民族情感对教育、文化的影响呈现了出来。坦尼娅·菲茨杰拉德以新西兰两名传教士为例叙述了1820年至1830年的教育网络图,描述了传教士科尔达姆·威廉姆斯(M.C.Williams)和简·纳尔逊·威廉姆斯(J.N.Williams)在施教过程中的情感。不难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思考:情感是否影响了教育发展?如果影响了,其地位怎样?这样的反思进一步推动了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的情感转向。
再次,引入情感经验的分析以考察教育历史的多面性。2010年以来,英国学者对情感理论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情感理论为思考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方法,还为书写特定时刻提供了理论工具。它加强了对个体、日常、短暂时刻和意外的研究。”[22](P694)在《教育史学——教育史研究的斗争历程》(The Struggl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一书中,加里·麦卡洛克用了“斗争”(Struggle)一词,其含义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将教育史研究视为斗争的领域,学者们围绕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展开争论和博弈;二是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状态及学者们为其奋斗的历程;三是加里·麦卡洛克本人的教育史研究奋斗历程。正如加里·麦卡洛克所说:“此书是我个人教育史研究的经历,回忆了过去,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加入教育史学会,寻找有助于新西兰教育史研究发展的路径以及寻求解决当代教育政策困境的出路。”[25]在阐述这一奋斗过程时,他用了“尴尬”“麻烦”“焦虑”“高兴”等词来表达教育史学人为教育史研究辩论和斗争时的情感。在《西里尔·诺伍德与中等教育理念》(Cyril Norwood and the Ideal of Secondary Education)一书中,加里·麦卡洛克清晰地呈现了诺伍德对父亲、妻子、中等教育及阶层的情感,深入分析了具有争议色彩的诺伍德的焦虑、不安和害怕的阶层心理,叙述了每一次参与教育改革时诺伍德本人的感受和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以此案例来阐明“教育史中个人传记、职业生活、政治变化之间的联系,以推进对中等教育更深层次的理解”[9](P13)。
综上所述,自21世纪以来,英国学者围绕教育管理者、教师、家长、学生的情绪、心态、焦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增多。英国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和国际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Paedagogica Historica)刊发了数篇英国学者关于情感研究的论文,刊发的数量也有增加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教育史学者对情感研究的重视。另外,英国还出版了《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期刊,成立了情感研究中心——牛津大学情感研究中心,多个学科从事情感研究的专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共同探讨情感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英国人文学科情感研究兴盛的大环境,也进一步推动了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情感转向。英国学者找到了阐释教育历史的一把钥匙——研究传主的教育情感。学者们透过对传主教育情感的分析,进一步剖析教育发展和改革背后的社会阶层关系、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对教育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入。
四、传记叙事何以能阐释教育史——对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追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教育学者从社会史、女性主义、新文化史、情感史的角度审视传记叙事模式,倡导跨学科的教育传记叙事研究,从多个角度阐释着教育史以呈现完整的教育历史故事,提升了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彰显了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史学意义。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传记叙事能否有效阐释教育历史?或许通过对英国教育史研究传记叙事模式的追问,能够进一步理解教育传记叙事阐释教育历史的合法性。这是教育史编纂学理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彰显传记叙事的价值维度,实现教育史研究视域的转换
通过对英国教育史研究叙事模式发展过程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教育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变化,已满足了科恩(S.Cohen)的“历史重新阐释的三个合法条件——新史料的发现;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学科的影响;关于新旧历史资料的各种问题的解答”[26]。早在2004年,古德曼和马丁接任英国《教育史》期刊编辑时,就发现“该期刊对传记方法的重视”[27]。十几年过去,《教育史》期刊依旧关注“教育与特殊群体之间的关系”,传记叙事类文章数量仍有增加的趋势。这些文章不仅运用传记叙事方法研究教育史,而且也开始关注传记理论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教育传记研究史的回顾和梳理。学者们立足于传记叙事的价值维度及其对教育史研究的“修正”“改造”和“重构”,旨在从反思教育史是什么或教育历史的基本维度出发,重新理解和解读教育史研究,并尝试探索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创新方向和变革路径。
英国教育史学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时,站在一定的主体立场并遵循一定的主体标准,追问“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等之类的问题,提供传主在政策制定、教育實践等过程中的具体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呈现传主生活实践活动的原则、动机、方向和目标,以此彰显传记叙事模式的价值维度。“传记像棱镜一样,透过它能够看到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复杂层面,能够从特殊看到一般,反之亦然,是评价性格、动机、行为和意图的方法。对于愿意深挖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尤其研究下层社会的历史时,传记是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历史研究方式。也就是说,教育传记的价值在于不仅要叙述主流和精英的故事和生活,还要关注边缘个体和教育环境的故事。”[19](P101)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透过传记这一“棱镜”让我们看到教育历史天空中的点点繁星,实现了英国教育史研究视域的三次转换:一是教育史研究的话语核心从社会背景、社会环境、社会结构转向教育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思考;二是从个人理性思考转向个人日常生活、心态、语言结构等,让教育历史不仅是关于“他”的教育历史,也还有“她”的故事;三是教育史研究不仅关注人的理性,还应关注人的情感经验,对情感经验背后的历史意义进行分析,通过个体情感经验的表达来解读社会阶层关系和教育改革背后的故事。
(二)引入私人化史料来叙述传主的故事,在史料变革中重构教育历史
在进行传记叙事研究时,教育史学家如何了解传主内心的感受与情感体验?英国学者既解读公共化史料,还重视挖掘私人化史料,通过对日记、信件、自传、口述资料、记忆等对传主的生活、心理、情感进行勾勒,更好地呈现传主真实性情的私人形象,以此来补正以往教育史研究中传主的公众形象,从这些充满矛盾或者跌宕起伏的人生写照中,管窥到时代变化和社会变革,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传主与现实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发展之间复杂微妙的多重关系。但研究者如何判断这些资料里表达的观念、思想和情感是传主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呢?英国学者通过论证私人语言,让私人化史料和公共化史料一起来重新叙述传主的故事,在史料变革中重构教育历史。
学者们认为传主的教育意识源于生活变迁的现场。在诺伍德的传记研究中,麦卡洛克指出:“虽然去利兹文法学校做一名教师不能完全展现他的才能,但是诺伍德得到了一次追随父亲塞缪尔的机会——从事教育工作……不断变化的家庭状况与诺伍德决定去利兹文法学校有关。”[9](P50-51)麦卡洛克将诺伍德在利兹文法学校的教育改革动力或原因与其生活变迁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诺伍德父亲的失败、家族社会地位的衰落及妻子凯瑟琳的支持和爱成就了他在利兹文法学校的改革。正如麦卡洛克所说:“这些学校的案例研究以及与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家族史呈现了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理念的主要特征。”[9](P58)
在新传记研究中,学者们关于传主的选择,已经从成功的精英人士转移到被忽视的参与者以及草根上。由于对被忽视者和草根的公共化史料较少或者记载偏颇,那就需要新的史料来补充或纠正以往的观点。在涉及教育变迁问题时,女性主义者按照草根-日常-文化-教育的逻辑,深入草根文化和视野之中,在边缘女性的行为、态度中看到了教育历史文化因素在长时段英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变迁中的“活力”。马丁运用传记的方法证明了女性不只是历史的受害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她以女性教育者亚当斯(M.B. Adams)为例,探究其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交织关系。“生活并不是以线性叙述的形式呈现,以‘老年结束,而‘社会职业一词的提出,表明了传记写作中的重要发展——出现了脱离生命历程方法的纪年;人生的故事还包括职业生涯,以及相关的逆转、过渡和胜利。”[28]传记研究给政治化进程和政治化运动中的性别动力提供了分析框架,“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人们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联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9](P232)。
人们可能会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采用传记叙事模式的教育史学者会不屑于公共化史料。实际上,他们不是不屑于公共化史料,而是缺乏公共化史料。正因如此,学者们为了全面诠释教育历史,才会不断地挖掘新的史料,并不断地重新解读原有史料。这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白“历史资料能够就内容加以解读,而且还能作为一种深入到制作这些资料的人和社会思想-心态(mentality)中的一种路径”[30]。
(三)在尊重客观性中合理表达主观性,明确传记阐释教育历史的“叙述限度”
教育史研究不仅仅是叙述,还需要历史阐释。要让教育史研究能够科学健康地发展,必须保持教育历史阐释的严肃性和客观性。那么,如何进行教育历史叙事,直接影响着教育历史阐释的成效。教育叙事不能随意地演绎、想象、虚构,必须尊重教育历史的客观事实,不能以研究者的“教育史史实”来取代客观的“教育史史实”,叙事的逻辑必须呈现教育历史的客观逻辑,在社会大背景中来把握和分析教育历史事件。换句话说,传记叙事和书写的教育史史实,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教育历史史实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是衡量传记类教育史作品是否科学的标志。鉴于此,英国学者在尊重教育历史史实客观性的基础上合理表达主观性,明确了传记阐释教育历史的“叙述限度”。
英国学者认为传记叙事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是传记阐释教育历史的“叙述限度”。学者们依据大量材料和事实的分析和研究,叙述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传主的生活、思想、情感和理念。传记叙事模式遵循两条路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路径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路径。这两条路径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内容是相互贯通的——即建立在研究方法之上的叙述,以此来实现科学的教育史学方法与个体化的传记叙述方法的有机融合,在尊重教育史史实客观性的基础上保持传记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同时,英国学者还强调教育历史的“自我批判”,认为这是保证教育传记叙事科学性的前提。正如马丁所说:“对于传记研究者来说,在研究过程中是需要自我批判,要承认传记叙述受讲故事的文化习俗影响。”[29](P220)
综上所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英国教育史研究的传记叙事模式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在传记叙事的价值、史料选择和运用、叙述和阐释的限度等问题上,学者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以更广阔的空间、更多元的史料、更复杂的联系研究教育史,不仅与教育形态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相吻合,也是教育史学者立足史学对这种演进的回应。英国学者对传记叙事模式的深入研究,无疑对于我们研究教育历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Rustin M.Reflections on the Biographic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in the Turn to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Comparative Issues and Examples[M].by Chamberlayne P.Bornat J.&Wengraf 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2] Momigliano A.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Biography[M].Expanded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
[3] Collingwood W.G.The life of John Ruskin[M].London:DoDo Press,1911:Preface.
[4] Gardner P.‘There and Not Seen:E.B.Sarga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1884-1905[J].History of Education,2004(06).
[5] 武翠红.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Watson F.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in Peter Gordon and Richard Szreter,History of Education: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M].London:The Woburn Press,1989:19-20.
[7] Mills C.,W.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7.
[8] Selleck R.James Kay Shuttleworth:Journey of An Outsider[M].London:Woburn,1994.
[9] [英]加里·麥卡洛克.西里尔·诺伍德与中等教育理念[M].武翠红,赵丹.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10] Simon B.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1980s[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1982(01):87.
[11] Simon J.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the ‘NewSocial History.History of Education Review[J].1983(12):11-12.
[12] Dyhouse C.Miss Buss and Miss Beale:Gender and Authority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in Lessons for Life:The Schooling of Girls and Women,1850-1950[M].Edited by F.Hu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23.
[13] Harold F.&Helen F.Four Exceptional Women in British Education[J].Equity & Excellence in Education,1977(04):10-17.
[14] Dyhouse C.Girls Growing up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M].London:Routledge,1981.
[15] Goodman J.A Historiography of Founding Fathers? Sarah Austin(1793-1867)and English Comparative Education[J].History of Education,2002(05):425-435.
[16] Goodman J.&Martin J.Women and Education,1800-1980[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4:6.
[17] Martin J.Thinking Education Histories Differently:Bi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Class Politics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London,1900s to 1960s[J].History of Education,2007(04-05).
[18] Plummer G B.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A Literature Review[J].History Teacher,2005(03):385-400.
[19] Martin J.Interpreting B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Past and Present?[J].History of Education,2012(01).
[20] Lowe R.Do We Still Need History of Education:Is It Central or Peripheral[J].History of Education,2002(06):492-493.
[21] Clever I.& Ruberg W.Beyond Cultural History? The Material Turn,Praxiography,and Body History[J].Humanities,2014(03):546-566.
[22] Sobe W.N.Researching Emotion and Affect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J].History of Education,2012(05).
[23] Sobe W.N.Slavic Emotion and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Yugoslav Travels to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20s and 1930s,in Turizm:Th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Tourist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Gorsuch E.A.& Koenker P.D.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82-96.
[24] Olsen S.Juvenile Nation:Youth,Emotio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ritish Citizen 1880-1914[M].London:Bloomsbury,2014:8.
[25] [英]加里·麥卡洛克.教育史学:教育史研究的斗争历程[M].武翠红,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III.
[26] Cohen S.New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1960-1970[J].History of Education,1973(01):87.
[27] Goodman J.& Martin J.Editorial:History of Education-Defining a Field[J].History of Education,2004(01):1-10.
[28] Martin J.Reflections on Writing a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Woman Educator Activist[J].History of Education,2001(02):163.
[29] Martin J.The Hope of Biography:the Historical Recovery of Women Educator Activists[J].History of Education,2003(02).
[30] [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