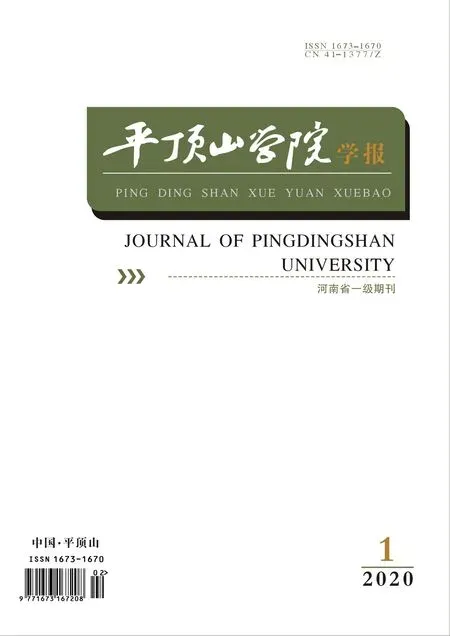论都市日常生活视域下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2020-12-19赵鹏
赵 鹏
(平顶山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平顶山467036)
唯美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无论是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还是《狮吼》《金屋》作家群纵情声色的唯美主义狂欢,都体现了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坛的广泛传播。而在都市日常生活领域,唯美主义思潮同样影响巨大。唯美主义“为艺术而生活”的主张,佩特关于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刹那间美感享受的观点,都成了唯美主义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拒斥世俗生活的依据。资产阶级的兴起导致功利主义哲学大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艺术领域的庸俗化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实用化上。因此,唯美主义者将审美无功利的态度拓展到日常生活,都市社会中任何领域都被纳入审美的范畴,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一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外在形式的美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而中国唯美主义思潮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主要体现在自我形象塑造、书籍装饰艺术、电影画报以及社会改造等领域。
一、自我形象的塑造
服装是唯美主义者表达自我审美理念的重要道具。王尔德就是以奇装异服的打扮来展现自我对于美的信条的传达:“他身穿带有花边的天鹅绒大氅,齐膝短裤,黑色丝袜以及领口下榻的宽松衬衫,还系着一条硕大的领带,这毫无疑问一定会激起人们的好奇甚至愠怒。”[1]王尔德还经常手持唯美主义的标志——百合花或向日葵——在广场散步,以此来塑造自己美学青年的形象,进而扩大唯美主义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唯美主义思潮中,邵洵美、叶灵凤、林微音等人都有意模仿王尔德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实践审美改造生活的理念。邵洵美长相俊美,其异国情人项美丽在文章中多次赞叹他俊美的外貌:
他(云龙)的头发柔滑如丝,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头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不笑不语时,那张象牙色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他的面孔近乎苍白,在那双飞翅似的面目下张扬。塑造云龙面孔的那位雕塑家,一定施展出了他的绝技,他从高挺的鼻梁处起刀,然后在眼窝处轻轻一扫,就出来一副古埃及雕塑似的造型。下巴却是尖削出来的,一抹古拙的颊髭比照出嘴唇的柔软和嘴角的峭厉。下巴上那一撮小胡子,则好像是对青春少俊的一个俏皮嘲讽。静止不动时,这张面孔纯真得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少静止不动。[2]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回忆中开玩笑地说邵洵美的面容和笔直的高鼻梁甚至多次激起雕塑家江小鹣、画家徐悲鸿等艺术家创作的欲望,可见其自身形象的完美。邵洵美曾经发表过一篇《从时代说到装饰》的文章,认为装饰就是表现我们身体的艺术与本能,他从衣饰服装的设计谈到鞋子的式样袜子的团,从女子的敷粉谈到香水的用法,充分体现出对身体享受的熟稔与重视。叶灵凤小说《禁地》中的主人公可谓是邵洵美这种审美改造生活理念的实践者:他身穿黑色的夹袍,黄色薄绸的衬里,“从这一件夹袍和脚上的一双胶底的赭色皮鞋上,可以看出它的主人公对于衣饰的色彩配置和调和,已有了相当的研究”,主人公的房间“最令人注意的是衣柜上的一列化妆品”“镜子的左方排着五个参差的香水瓶……镜子的右方第一件是一盒面粉,牌子与那瓶淡绿色的香水一样,再过去也是面粉,这一瓶便是青年适才用……衣柜右方最后的一件是一个黑色方形扁盒,镶着两道银红色的边缘,这是修饰指甲的Cutex。Cutex盒上另外还有一小盒Nail Polish”[3]。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邵洵美、叶灵凤等人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自我形象的塑造上追求审美性,恰恰体现了审美对1930年代上海文人生活领域的渗透。
二、书籍装饰艺术中的“比亚兹莱风”
中国唯美文人对美的实践显然不仅仅局限于自我,书籍的装帧和插画作为文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场景同样成为其唯美表达的试验田。比亚兹莱是英国唯美主义画家,曾经为王尔德的代表作《莎乐美》画插图,他的装饰绘画作品通过简单的黑白线条的运用传递人物的质感和物体的层次,充满了颓废和怪诞之美。自唯美主义引进中国后,比亚兹莱的装饰艺术也迅速被国内文艺界所接受并模仿。
最早介绍比亚兹莱的田汉在创办《南国周刊》的时候,就多次引用比亚兹莱的作品,而且还为比亚兹莱提供了一个颇有诗意的译名“琵亚词侣”。鲁迅也非常喜欢比亚兹莱的作品,曾出版有《比亚兹莱画选》,称赞他是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并认为“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4]356。除鲁迅外,田汉、郁达夫、梁实秋、邵洵美等都曾经为比亚兹莱的装饰艺术所心折,不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叶灵凤。
叶灵凤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所学校曾经被誉为西方唯美主义的讲习所,不仅培养了滕固、倪贻德、叶灵凤等大批唯美主义人才,更是首创将裸体模特引进人体素描教学。叶灵凤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对比亚兹莱有着浓厚的兴趣,据他自己在《比亚兹莱的画》一文中回忆,当他在美术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比亚兹莱的画,并模仿过很多比亚兹莱风格的插画。后来创造社的刊物《创造月刊》等许多书籍的封面和装饰插图都出自叶灵凤之手,他还获得了“东方比亚兹莱”的称号。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叶灵凤的这种自我吹捧,加上“革命文学”论争中对鲁迅的挖苦,使得鲁迅对叶灵凤模仿比亚兹莱颇为不屑,讥之为“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4]169。叶灵凤的插画从形式上看确实与比亚兹莱非常相似,都用纤细优美的黑白线条勾勒而成,都经常出现女性身体等意象,都带有强烈的颓废和色情意味。他和鲁迅对比亚兹莱的关注点不同,鲁迅虽然也看到了“恶魔的美”,但更多是强调比亚兹莱“罪恶的自觉”;而叶灵凤则欣赏比亚兹莱身上唯美主义式的颓废和享乐主义式的肉感。叶灵凤对比亚兹莱的模仿和提倡伴随了他的一生,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到后来创办幻社,出版《幻洲》半月刊,他设计的许多刊物的封面和插图都带有比亚兹莱风格,1930年代更是设计了一套比亚兹莱风格的藏书票,其文学创作也同时糅进了比亚兹莱式的描写技法,为其创作增添了不少唯美色彩。
三、电影和画报等视觉性的唯美传达
视觉文化的发达,是都市现代性的标志之一。电影、画报等视觉文本以独特的符号展现城市生活,很快赢得了都市男女的喜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娱乐休闲活动之一,鲁迅就是其中一个。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上海的九年间观看电影次数多达142场。电影行业的发展刺激了社会对视觉影像的需要,随着摄影和印刷技术的普及,画报以其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占领了文化市场,涌现出《良友》《时代》等印刷精美、设计讲究的画报,图像传播成为1930年代的新趋势之一。据统计,到1930年代仅上海一地,电影院的数量已达到40多家,画报则多达27种。不论是电影抑或是画报,都展现出现代都市文化从满足需要为主的普通消费向满足欲望为主的消费艺术的转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电影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电影观念和理论充斥着电影市场,其中既有以张石川、郑正秋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电影,也有以但杜宇、史东山、汪煦昌等为代表的提倡形式美、讲究艺术性的唯美主义电影。1933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之一《春蚕》被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改编为电影,由于电影观念以及对电影的评价不同,引发了“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之争。“软性电影”论的提倡者刘呐鸥、穆时英主张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这种以审美和享乐态度观照电影的理念颇有唯美主义的色彩。不过当时占据电影市场多数的还是从美国好莱坞引进的影片。据调查,在1933年上海放映的567部电影中,国产电影仅占据20%左右,而美国影片则占一半以上。好莱坞电影注重声色刺激和感官享受的特点与“软性电影”论者一脉相承,而电影市场中不断涌现出的女明星如嘉宝(Greta Garbo)、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等因其完美的身姿和面庞成为大众观照与消费的对象,即使存在些许女性意识的表达也被淹没在消费文化的狂欢中。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都是电影院的常客。据施蛰存回忆,他和刘呐鸥、戴望舒等人每天“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5]。以他们为代表的都市新感觉派的创作就是好莱坞电影这一特征的体现,无论是刘呐鸥《游戏》中有着“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鼻子”和“高耸起来的胸脯”的女主人公,还是穆时英《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的女人,都是都市现代性的产物。她们穿着时髦,生活方式摩登,是现代都市催生出的敢于消费一切,但又同时被男性所消费的物质女性形象。她们毫无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充满诱惑的身体在都市中追求感官享受,同时也将自己物化,在她们的身上闪现着迷人而又颓废的唯美主义色彩。正如穆时英所谈到的那样:“好莱坞王国里那些银色的维纳斯们有一种共同的、愉快的东西,这就是在她们的身上被强调了的,特征化了的女性魅力。就是这魅力使她们成为全世界男子的憧憬,成为危险的存在。”[6]电影,无论在唯美主义者的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女性魅力在画报中同样有所体现。《良友》《万象》《大众》等画报和电影一起,用图片诠释都市体验,营造出一种商业化、大众化的都市文化潮流。《良友》画报从1926年创刊起就以装帧精美而著称。首期杂志封面用大篇幅刊登了影星胡蝶的半身玉照,从此之后,《良友》的封面就成为展示都市现代时尚生活的T台,摩登女郎、电影明星成为杂志封面的常客。据统计,《良友》画报出版的172期刊物中,有161期都有封面女郎的形象。尤其是1930年代的上海,商业文化的氛围和唯美主义的理念完美融合在《良友》画报上。例如第69期的封面女郎手持网球拍,身穿短袖的运动服和短裤,显得活力动人。这在当时相对保守的时代氛围里无疑会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却营造出一种健康自然的都市生活方式和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理想。
四、社会改造领域的唯美主义实践
中国唯美主义思潮在社会改造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张竞生身上。张竞生是民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曾经在1912年至1919年间先后在法国、英国留学。英法两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唯美主义风尚对张竞生影响颇深,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就是关于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卢梭的研究。而对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也不陌生,他在专著《浪漫派概论》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张竞生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不但延续了唯美主义在艺术领域对美的重视,更将美的重要性拓展到社会领域,提倡美的人生观,施行美的社会组织法,并最终建立美的政府,创造一个“美的乌托邦”。
张竞生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925年出版的《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之中。《美的人生观》一书共分为两章,第一章是用美的标准去分析衣食住、体育、职业、科学、艺术、性育以及娱乐七项内容;第二章则是用哲学的眼光去研究美的思想以及美的精神生活。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第一节“美的衣食住(附坟墓和道路)”为例,张竞生细致地剖析了人类的衣服、食物、居住甚至坟墓和道路如何达到美的标准。他认为穿衣服不仅仅是为了需要,更多是为了美观。传统服饰有着种种弊病,因此他对自己心目中美丽的男装和女装都做了仔细分析,尤其是对女装还运用了插图予以说明。总之,张竞生指出“故美能统摄善与真,而善与真必要以美为根底而后可。由此来说,可见美是一切人生行为的根源了,这是我对于美的人生观上提倡‘唯美主义’的理由”[7],这无疑是对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理念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发展。而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张竞生则主张从美的、艺术的与情感的方面去组织社会。例如他认为应该把社会事业分开,男子担任一切粗重丑臭的工作,女子则担任各种美趣的事业,如艺术、慈善、教育、装饰等事业。在现实生活中张竞生也确实实践过这些理念,他在上海创办美的书店,招收年轻女子担任店员,为此还曾经被鲁迅批评以女色招揽顾客。这当然是鲁迅对张竞生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张竞生非常重视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甚至提出了新女性中心论,认为只有以女性为社会的中心,才能成为一个以情爱、美趣以及牺牲精神为主的“美的社会”。张竞生最有争议性的则是他在性育方面的观点,就连颇赞同他的观点的周作人也认为“美的性育”一节中的所谓神交法甚是“古怪”。而张竞生之所以在社会上留下“性欲博士”的骂名,也正是因为他在性知识传播上的大胆和激进。1926年北京光华书局出版的《性史》一书,尽管他自己一再声称是“科学与艺术的书”,但其间对个人性史的露骨描述确实与当时社会伦理道德不符。不过,联想到唯美主义非道德化的倾向以及对感官享乐的推崇,张竞生的这些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中国唯美主义思潮在社会改造领域的影响因张竞生而显得颇为突出。
邵洵美、叶灵凤、林微音、张竞生等唯美文人游走于电影院、咖啡馆、豪华公寓、茶社、新式书店等都市文化空间,筑造着他们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想象,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书籍装饰艺术、电影画报以及社会改造等各个领域实践着他们对于“美”的想象。唯美主义从诞生起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理念,艺术至上、反抗庸俗的精英立场只是其中一面,而另一张面孔则是贴近生活、创造时尚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中国唯美主义思潮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风生水起,极大促进了这一思潮的普及。不过,也正是因为唯美主义和都市日常生活之间这种难以割舍的密切联系,迫使其走上了一条从反抗救赎到物化、泛化的道路。从对工业社会中庸俗市侩风气的反叛,到都市商业文明中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唯美主义和都市文化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艺术的理想终究难以离开现实生活的渗透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