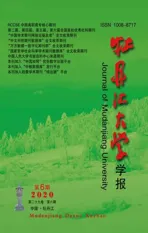殖民语境下女性的自我救赎
——论哈萨克斯坦长篇小说《阿荷碧蕾克》
2020-12-19热宛波拉提
热宛·波拉提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朱苏普别克·阿依玛乌托夫是哈萨克斯坦长篇小说《阿荷碧蕾克》的作者,是哈萨克斯坦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翻译家。1889生于今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州巴彦阿吾勒县。1931年去世。著有长篇小说《卡尔特霍家》《阿荷碧蕾克》,中篇小说《昆妮凯之罪》,剧作《人民的堡垒》《追名逐利的人们》《热比哈》等。此外,朱苏普别克还曾将莎士比亚、果戈里、莫泊桑、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译至哈萨克语介绍给本国人民。《阿荷碧蕾克》发表于1927年,是首部以哈萨克女性命运为基底,再现革命时期哈萨克斯坦乡村社会变化进程的小说之一。小说的时间线选在20世纪初哈萨克斯坦新旧社会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经历了战火、殖民、饥荒等多重蹂躏,可以说“苦难”曾是整个哈萨克民族之殇。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现实主义成为大量哈萨克斯坦作家反击殖民压迫的重要表现形式。他们大多通过真实刻画受压迫者的苦难——特别是殖民语境下的女性悲剧命运,对黑暗社会加以抨击。首度将这类主题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哈萨克斯坦作家有穆尔加合甫·杜拉托夫,苏里坦马合木提·托尔艾戈洛夫,斯潘迪亚尔·库别耶夫,朱苏普别克·阿依玛乌托夫,穆赫塔尔·艾乌佐夫,别依姆别特·马依林等。然而,朱苏普别克·阿依玛乌托夫在创作旨归上与上述作家的创伤叙事有着根本的差异。在朱苏普别克笔下,女主人公的幸福与自由不仅仅局限于嫁给心爱之人的个人婚姻幸福,更在于女性获得社会意义上的精神解放。因此,作者在小说中所再现的社会矛盾、历史事件等,均对女主人公阿荷碧蕾克的命运造成了直接影响,所有的时代变迁以及乡村文化景观的变化,都与主人公的流难生命密切扣合。马克思说过:“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准地衡量。”[1]朱苏普别克·阿依玛乌托夫即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矛盾、各大历史事件、阶级斗争重重交织,人民备受压迫的社会境况下,将女性的个人遭际与民族的历史命运交织在一起,再现了哈萨克斯坦封建部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图景以及哈萨克斯坦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真实的生存状况。小说揭露了卫国战争临近结束,白卫军①因战败于红卫军逃往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对沿途哈萨克村落犯下的种种罪行。
一、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的牺牲品
小说从全篇的核心事件阿荷碧蕾克被掳写起。作者一开始将聚光灯投向阿尔泰山麓玛尔喀湖岸边的哈萨克斯坦乡村的自然风光:玛尔喀湖的水如蜜。饮过玛尔喀水的母马的乳房流出的是乳汁,不,不是乳汁,是福光,满溢着一个个奶桶……②小说开篇即描画了一幅丰饶祥和的哈萨克乡村图像。然而接下来就以一场混乱的殖民兵匪的侵袭戳破这个美好图景,前后情节的高度反差成功地营造出小说的冲突感。白军逃、红军追,民族解放起义的硝烟已经弥漫到了哈萨克斯坦边境乡村,深居山沟深处的玛木尔巴依的部落也遭到了白军匪兵们的袭击。匪兵们杀死其妻,掳走了其未满十五岁的女儿阿荷碧蕾克。主人公阿荷碧蕾克被赋予哈萨克民间传统审美意义上的美丽与教养,作者借助其未婚夫别克波拉提回忆第一次遇见她时的心理活动侧面呈现出阿荷碧蕾克的芳容:
额头圆挺,天鹅脖颈儿,水灵灵的双眸,娇美的樱桃小嘴,宛若新生的幼茎!柳条般的身形没有一丝瑕疵,犹如鲜嫩的须茎!发饰叮铃铃作响,起身时膝盖轻轻抚触过白裙,迈出母马般骄人的步伐;和嫂子絮语时,笑声宛如银铃般清脆……道别时,瞳仁里闪着光芒,微微颔首,而后默默凝望,一切的一切都浮现在别克波拉提眼前。
作者用优美的比喻与细节描绘,将阿荷碧蕾克的柔美、纤细与雅致写了出来。她的名气甚至吸引来了白军匪兵。阿荷碧蕾克被掳走后,她的悲剧就此开始:从未直视过男性的天真少女,变成了一个逃兵、强盗,甚至连名字也无从知晓的白军军官——“黑胡子”的玩物。作者对被俘后的阿荷碧蕾克内心痛苦焦灼的状态做出了大量描写:
她神色迷惘,扶着帐篷沿钻了出来,想起昨晚的事情,泪水就如泉眼般扑簌簌地滚下来。从厚厚的毡子里探出身,即使阳光直直地照在阿荷碧蕾克的脸上,也没有替她拭干那无尽的泪水;裹挟住内心的黑暗使她迫切地渴望光明,心知自己只有永远地闭上双眼才能解脱之后,便只想从这兵匪窝儿里稍稍溜开身,最起码去看看外面。
……
四周群山连绵,林海茫茫,山顶上振翅翱翔的雄鹰,朝山上徐徐攀沿、形如蚁身的马匹,帐篷外那沿河边生长的灌木丛都没有在阿荷碧蕾克的眼里稍作停留,就那么匆匆滑过,她的目光在地灶上的哈萨克人的水壶、木盆,裂缝的舀子上停了下来。落入俄罗斯人手里的也不知道是谁的舀子?可怜的舀子!我们同病相怜。
这段细节描写看似庸常琐碎,然而对被强掳异乡、失去家园依靠的阿荷碧蕾克来说,这些从家乡掠夺来的物件是她唯一熟悉的东西,同样暗示着主人公未来的命运跟这些掠夺来的物件一样,处于被支配、无自由的境遇。
小说在阿荷碧蕾克被劫走后到返回家乡的这一部分也有三个可讨论之处:
其一,小说中白军迫于形势欲再度逃亡时,阿荷碧蕾克不愿跟随匪兵们一起逃走,黑胡子军官临行前遂欲开枪打死她:“阿荷碧蕾克突然朝瞄准自己的枪口冲了过去。黑胡子的手抖了一下。左轮手枪掉到了地下。”主人公就这样勇敢地从枪口下救了自己。作者在这里再次亮出了黑胡子军官殖民者的身份,只是这时候的阿荷碧蕾克由最开始对噩运的被动承受转向了奋起抗争,人物的主体性逐渐明晰起来。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阿荷碧蕾克从初入“狼穴”时完全不懂殖民者的语言,在殖民者中间成了无声失语和无自由的代名词,再到年深月久,慢慢主动开口说一些俄语词以便能发出那么一点可怜的声音,同样表现出阿荷碧蕾克在困境中隐微的主体性。
其次,坚决留下的阿荷碧蕾克孤身面对寒夜里的荒野,又遭到狼袭,主人公与围在帐篷外的狼群殊死搏斗的情节使全篇小说发展到了高潮,所幸阿荷碧蕾克聪慧过人,关键时刻点明火保住了性命。阿荷碧蕾克接连两次为了求生而奋起抗争并取得胜利,说明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已逐渐复还主体能动性。
其三,身心遭到重创的阿荷碧蕾克,内心深处对未来仍怀有一线希望,她不惜一切地想要回到家乡。在行路人的指引下终于临近家乡时,内心强烈的耻辱感与负罪感使她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负面认同,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越是接近自己家乡的山石,脚踩干净的地面,越是羞愧难耐,倒不如被一枪死了算了,她反倒为自己从黑胡子的枪下脱险而后悔起来:被狗舔过的碗似的,觉得自己的身体、甚至呼吸都是肮脏的……
在传统的父权文化中,贞洁被看作是女性首要的道德规范。失去贞洁的女性被看作是肮脏而堕落的女人,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惩罚。阿荷碧蕾克作为一个自幼在哈萨克传统父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一直无法摆脱被殖民者剥夺贞洁的心理阴影。然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哈萨克封建部落内部的利益冲突(穆卡西因阿荷碧蕾克的兄长托列根没有满足他当伯鲁思③的贪欲,亲手把阿荷碧蕾克送到俄罗斯匪兵手里以解私恨),于此阿荷碧蕾克不幸充当了这一恩怨的 “替罪羊”。无独有偶,匪兵们本打算“平分”阿荷碧蕾克,黑胡子军官则对阿荷碧蕾克表达了爱意,表示如果阿荷碧蕾克肯跟了他,他就能让她免于被众匪兵蹂躏的下场,阿荷碧蕾克权衡后选择默默屈从。在一场匪兵们的较量中,“黑胡子”军官拼死赢得了阿荷碧蕾克专作自己女人的特权。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哪一个空间(“敌”抑或“我”),阿荷碧蕾克都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在父权制下只能作为被男性抢夺的物件,毫无自由可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既是哈萨克封建部落社会内部利益斗争的牺牲品,也是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牺牲品。小说这一部分所呈现的阿荷碧蕾克是殖民时期千千万万哈萨克乡土女性的代表,更是俄罗斯帝国主义行径下殖民地万千女性的缩影。
二、与家园的协商与逃离
创伤书写作为殖民活动所遗留在罹受苦难的殖民对象身上的一种表述方式,展现出了战时殖民行径的残酷,作为战时受到戕害和侮辱的女性而言,她们的身体和灵魂遭受了无尽的创伤,与这些创伤相较,更为难以消除的是同胞族民的冷漠和怀疑,幸存者所遭受的二次精神伤害。[2]小说中费尽艰难终于回到家乡的阿荷碧蕾克,对家园本抱以协商的态度,希望乡人重新接纳自己,等来的却是来自同胞族民的侮辱与耻笑,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对她避而不见。
(一 )父亲的无视
小说成功塑造了哈萨克传统部落家庭长老——马木尔巴依内心清高,自尊心极强的父亲形象。我们可以从事发前后父亲对阿荷碧蕾克态度的转变窥见一二。小说开头形容阿荷碧蕾克是“玛木尔巴依的阿荷碧蕾克”:“玛木尔巴依的阿荷碧蕾克,年幼的闺女阿荷碧蕾克,珍贵无比的美丽少女,金耳环摇曳着、银发饰铃铃作响。”阿荷碧蕾克俨然是在父亲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富贵娇女。事发之后父亲的态度则有了极大的转变:
阿荷碧蕾克为父亲从未单独找自己说过话而懊恼。她的父亲甚至不愿意与阿荷碧蕾克独处。父亲与她之间的亲情纽带就好像被陡然切断,阿荷碧蕾克清晰地感觉到一道隔阂形成了。父亲的眉头什么时候能舒展开来,什么时候可以温柔地看我,什么时候会找我说话?……好像父亲看她一眼,悲伤就能减轻一些,会变得幸福一些似的,即便如此,父亲也不去看她一眼。现在对阿荷碧蕾克来说,这比母亲的逝世更让她感到煎熬。
小说中描写玛木尔巴依细腻的心理变化,也足见作者对心理描写驾驭的功力:
嫉妒、羞耻、懊悔、同情、愤怒、痛苦——所有的情绪一齐延伸,她的生还成了他眼里的沙子,令他悔恨交加,怒火中烧。但是难道要让自己去砍自己的手?朝自己的肚子捅刀子吗?像只咽下毒药的狼般痛苦不安,满腔恨意,拖着骨头架子挪步。有时候老人家孤身一人的时候会陷入沉思:“可怜的孩子有什么罪呢”,动起恻隐之心时,想起她遭遇过的事情,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胸口强烈地拒斥着阿荷碧蕾克,不让她接近自己似的。有时候甚至会生发这样的念头:“早点儿甩开她如何?”
得知阿荷碧蕾克怀了白军匪兵的孩子后,父亲对阿荷碧蕾克的态度更是由先前的躲避转向了极度的愤怒:“父亲玛木尔巴依几乎恨起了阿荷碧蕾克。甚至命令后妻:让她滚。”阿荷碧蕾克面对父亲的冷漠与疏离,内心经历了由不解到伤心,再到绝望的边缘:“如果我那唯一的、亲爱的父亲都恨我,那谁还容得下我?”
(二 )未婚夫的抛弃
未婚夫别克波拉提在得知阿荷碧蕾克生还后,即使对阿荷碧蕾克遭遇过的事情心知肚明,心底里仍然割舍不下旧爱,几经内心挣扎,决定不计较阿荷碧蕾克的过去,与她再续前缘。阿荷碧蕾克也努力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终于鼓足了勇气,慢慢向别克波拉提靠近:
孩子们都睡下后,阿荷碧蕾克穿着新裙子,干净的褂子,散着香气,身披外衣,谨慎地迈开步子,小心地开门,关节处微微发颤,轻轻跨过了门槛。月光明亮。积雪如银箔般闪烁。星星夺目耀眼。两家之间的小径隐显出来。这条路——仿佛是通往天堂的路。通过这条路好像就可以敲开美好幸福的人生之门。越是靠近,幸福之门就越近在眼前。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时,阿荷碧蕾克却怀孕了,当然是俄罗斯军官的孩子。阿荷碧蕾克彻底心灰意冷,她想尽办法流产。患有不育症的嫂子乌尔克娅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在村里散布开来。阿荷碧蕾克在嫂子的毡房附近——库尔肯姆拜婆婆的家里生下了儿子,阿荷碧蕾克请求老婆婆不要留下这个孩子,老人家把孩子送到了尝尽无子之苦的乌尔克娅嫂子那里,在村里宣布乌尔克娅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叶斯肯德尔。只是此时阿荷碧蕾克对自己孩子的态度仍然是极度拒斥的,人物内心深处依然对经历过的创伤怀有强烈的耻辱感,呈现出主人公持续“自责”的精神构图。
(三 )乡人的凝视
返乡的阿荷碧蕾克被同乡人无情地贴上了“俄罗斯人吃剩的”,“俄罗斯人糟蹋过的姑娘”标签。作者甚至在小说里讥讽波孜格出于好奇心,急于去看从俄罗斯人手里生还的阿荷碧蕾克:
俄罗斯人也到过她们村里,姑娘妇女们都藏进了山石间,她自己也落入过三个士兵的手里,经历了命运该经历的。小房里的姑娘自从那以后便患上了淋病,整日躺在家里。即便如此,她的好奇心难道会消退吗!
别克波拉提知道阿荷碧蕾克怀孕后,再也没有勇气去兑现彼时的陈诺,弃她而去。父亲玛木尔巴依的再婚,后母乌茹克冷酷的性情,再加上自己怀了俄罗斯军官的孩子,此时的阿荷碧蕾克失去了一切,她的纯真、贞操,应有的地位。主人公甚至再度有了轻生的念头:
过去那种“要是死了就好了”的想法再次浮出。对这个世界来说自己是无用的、多余的人,就好像被人群抛弃的肮脏的小野狗,脚下甚至没有一块能站稳、依靠的巴掌大的地方,心脏堵到嗓子眼里,眼里的泪水汇聚在一起不停地流着,流着……
小说对主人公返乡后这一部分描写,反映出殖民地女性在遭到殖民者一方的极大羞辱后,再次经历来自族群内部被压抑、被驱逐、被边缘化的命运,被部落集体凝视、评价。在家乡无法被接纳的阿荷碧蕾克只好追随哥哥托列根一同离开,去往城市。“出走这一行为,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形态和精神欲求,它并不简单是背井离乡这一浅层的意义,更包括个体在精神上对原有文化、文明的反叛、逃离、重新审视与重新建构。”[3]阿荷碧蕾克在体验过丧失、空虚、绝望之后,无奈之下只能以一种逃离的姿态来反抗现实。作者在这里揭露了殖民时期哈萨克妇女曾沦为俄罗斯匪兵玩物的这一历史悲剧,控诉了殖民历史给女性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灾难,特别是给殖民地女性带去的巨大伤痛。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尝试描写女性化的身心经验,特别是对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情欲心理层面用心颇深。譬如小说前半部分阿荷碧蕾克与黑胡子军官的亲密描写:
黑胡子几乎对阿荷碧蕾克寸步不离……仔仔细细地拍打过被褥后,亲自铺在帐篷里侧。他用自己的灰色毛外套紧紧把阿荷碧蕾克揽在怀里睡,仿佛要把她的嘴唇吞下去似的长久地亲吻,用力抱紧她,伸出手去咯吱她时,阿荷碧蕾克的心脏堵到嗓子眼,脉搏加快,要燃起来似的,全身颤抖,她闭住眼睛,忘记了自我,浑身瘫软,呼吸变得急促……之后发生得一切她自己也不清楚……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作者对女性性爱心理的描写含蓄、自然。主人公由一开始对军官身体的极度憎恶,到特定场景中内心产生了微妙变化:“阿荷碧蕾克回乡后,独处时常常想起与军官在一起的时候:然而痛苦的回忆都消失了,浮在眼前的竟然都是温馨的时刻。”作者对女性矛盾心理的细致探索,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
三、城市新女性——自我救赎之途
(一 )城市生活
在小说的这一部分,作者安排城市哈萨克知识分子登场,增加了不少相关人物与情节,将城市生活与哈萨克乡村现实联系在一起。例如,哈萨克乡村中逐渐出现有远见的人家把孩子送到城市接受教育的情况。得益于这批人,在黑暗中度日的哈萨克斯坦民众眼前有了一丝光亮。小说中反映此类社会现实的情节还有:玛木尔巴依把儿子托列根送去城市上学,别克波拉提在托列根的帮助下在城市就医,之后在托列根家中与城市中的哈萨克知识分子阿克巴拉、巴勒塔西、多尕,卓尔尕别克等人相识等。小说中描写聚会席间的一幕则再现了苏维埃政府初年,弥漫在哈萨克斯坦社会的政治氛围,包括哈萨克知识分子之间的意见矛盾,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展望等等。作者通过叙写这些插曲,展现出这一时期诞生的哈萨克斯坦新型现代化城市的特点以及城市新兴群体的面貌。小说中,我们可以从阿荷碧蕾克来到城市后所经历的种种事件获得有关哈萨克传统乡土女性逐渐走向城市、接受教育,观念得到转变的信息。阿荷碧蕾克在奥伦堡求学时,作者对当时的教育条件作出了直观描写:
大概有五百来孩子。屋子里很挤。柴火少。时烧时不烧。屋里面脏乱,臭烘烘的。这么多孩子肯定会弄臭啊。打开洞会进来寒气,使人生病。不开的话就快要窒息了。再加上食物也不足。正是闹大饥荒的年份。相互争抢,每天也只有半磅的面包,没有肉沫的土豆汤能喝。
小说的核心人物虽是阿荷碧蕾克,但作者的写作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其个人经历。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成长、生活过的各种环境,相联系的种种人物,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城乡现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由衷地尊重、赞美人们赖以栖居的大自然和本民族优秀的传统;同时,又犀利地批评弥漫在哈萨克乡村中的陈旧的部落分裂主义,以及哈萨克底层民众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目光短浅的缺陷。此外,同样讽刺了那些在城市里习得知识、技能,却逐渐偏离哈萨克民族传统美德的行为——嗜酒、纵欲、无耻以及奴性心理。
(二 )收获爱情
来到城市后,阿荷碧蕾克在奥伦堡的工农速成中学与城市青年阿克巴拉、巴勒塔西相识,他们两位都对阿荷碧蕾克倾心,并来信表达了爱意。一开始阿荷碧蕾克对阿克巴拉萌生了好感,巴勒塔西怀疑阿克巴拉对阿荷碧蕾克的真心,私自把阿克巴拉的日记拿给阿荷碧蕾克看(阿克巴拉在日记里表达了对另一个女孩库兰的爱慕之心)。阿荷碧蕾克认为巴勒塔西是出于对阿克巴拉的嫉妒才这么做,对巴勒塔西的行为感到愤怒的阿荷碧蕾克一气之下把自己的过去统统告诉了巴勒塔西。阿荷碧蕾克也知道自己的事情会立即被阿克巴拉知道,果不其然,阿克巴拉立即与阿荷碧蕾克划清了界限。巴勒塔西则通过这件事从心底里肯定了阿克碧蕾克的人品,不在乎她的过去,再次向她示爱。阿荷碧蕾克这次没有拒绝巴勒塔西,与他携手步入了婚姻:
每天下班后,阿荷碧蕾克都会把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告诉巴勒塔西,告诉他有谁都说了些什么。两人互相交流思想。有时候巴勒塔西写报告、特写时,阿荷碧蕾克会跟着抄写。有时候阿荷碧蕾克忙起来的时候,巴勒塔西也会买饭回家。他们互相体恤着彼此,依靠着彼此。他们觉得如果不是两具身体,他们其实是一个人。
这是旧社会中哈萨克男女之间不曾有过的景观。新的社会生活让女性地位得以提高,在新时代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得以走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成为与男性社会地位平等的公民,有了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的勇气。小说结尾,阿荷碧蕾克随兄嫂,与巴勒塔西携手一同返乡,这时候的主人公面貌焕然一新:
阿荷碧蕾克不像从前,她变了,有了本领,变得成熟精干,成了村里女人们的楷模。过去阿荷碧蕾克身上那种内敛、阴郁,羞涩的气质已消失不见。部落里的长老们看见阿荷碧蕾克的举止都惊叹道:“她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城市有什么魔力?以前本是个老实害羞的孩子啊?”无论如何,阿荷碧蕾克现在是全新的,是有技艺的。她不再只是长辈们的孩子,而是大家伙的孩子。现在长辈们也从心底里尊敬她了。
小说中见证过阿荷碧蕾克苦难的阿尔泰山曾经让她觉得:“身子像是被电闪雷鸣的黑云紧紧压住。”如今则是:“思想,身体都站起来了……晚风亲吻着她的脸颊。”小说结尾,阿荷碧蕾克与自己的亲生孩子和解,宣示着主人公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地和解了。她终于可以放下,从内心深处原谅自己,接纳自己,安顿自身了。阿荷碧蕾克的结局宣誓着在新的时代下、在旧观念面前,知识女性的精神胜利。正是经过城市的洗礼,阿荷碧蕾克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才走出了创伤阴霾,获得了自救与得救的阶梯。不可否认,现代性对于女性的自我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个曾经面对困境勇敢坚强,却又卑屈退缩的女性主体是逐步发展、逐步丰满的,这其间充满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自我冲突、自我辩证,以及内外协商的过程。
四、结语
小说作者朱苏普别克·阿依玛乌托夫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却真实再现了俄罗斯帝国统治下殖民地女性在夹缝下求存的生命历程。作者一方面突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及其内心的痛苦迷惘,对殖民地女性所经历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无限悲悯;一方面勇于直面残酷的殖民地现实,用现实主义手法实时揭露帝国的殖民行径,与殖民主义进行对抗斗争,成功塑造了主人公阿荷碧蕾克为追求平等、自由,走向城市接受教育,为实现自我奋起抗争的哈萨克知识女性形象。借助阿荷碧蕾克这一形象,作者充分肯定女性为僭越封建内囿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鼓励更多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积极追求自身的幸福,展现出作者对女性美好未来的信心与期望。《阿荷碧蕾克》作为哈萨克斯坦小说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作品,在我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值得更多的学者去关注、研究。
(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教研室教授Aygul Uysen对笔者的写作给予了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白卫军:简称白军,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的一支武装力量。白军以保皇党派为基础,主要将领有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人。1921年初被苏俄红军消灭。
②中选文皆由笔者经哈萨克文原文翻译至中文,后文不再单另作注。
③文伯鲁思:旧时听命于俄罗斯帝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掌管各部落事务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