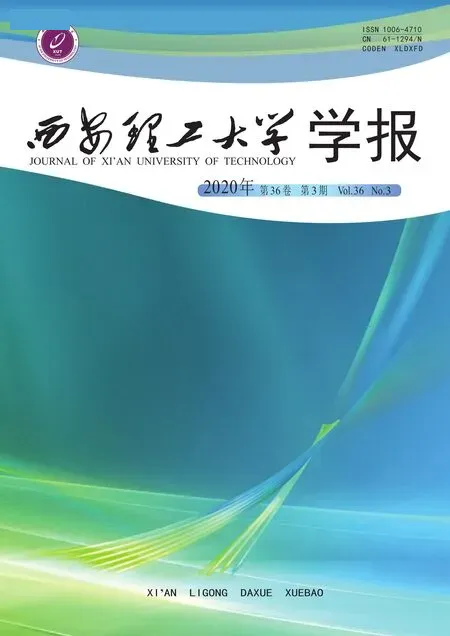基于产权性质差异的管理层能力与上市公司避税行为实证研究
2020-12-15陈淑芳白珂瑞
张 静,陈淑芳,白珂瑞
(1.西安财经大学 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2.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是否成功,除了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技术条件等原因外,管理层能力在经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Demerjian等[1]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税收问题作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2008年1月1日生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在2017年2月22日进行了正式推行后的首次修订,伴随着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税收规避问题。
Scholes等[2]研究发现,通过避税行为可以给企业带来大量的税收节约,从而增加公司的价值。Desai和Dharmapala[3]提出在企业采用税收规避减少支出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存在避税的成本,比如税收筹划成本、代理成本等。Dyreng等[4]的研究表明,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其通过制定方案做出决策给公司定下基调,从而对避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如何衡量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并采取相应的避税行为是管理层在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但是,正如Slemrod等[5]所指出的,两权分离为企业避税带来了新的问题,即避税行为一旦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效益,那么所有者就会通过一定的措施鼓励企业的管理者采取避税行为。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避税行为对企业股东来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尤其是学者Desai等[6]在其研究中发现企业的管理层所做出的避税决策和管理寻租之间正向相关,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实行避税决策。国内学者也对避税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进行了探讨。王跃堂等[7]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为了减少应交所得税而去操控非应税项目的损益,进行避税决策,从而增加企业利润。曹越等[8]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社会信任仅对非国有企业的避税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从公司外部环境角度出发,曾亚敏和张俊生[9]通过研究税务部门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发现税务部门监管力度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李春玲[10]研究表明在管理者权力较大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股票期权激励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避税程度。吴联生[11]从内部股权情况剖析了避税行为研究发现公司股权中,国有股权的比例与实际税率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公司的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其实际税率也越高。这些研究虽未将企业避税问题放在首位,但其研究成果拓宽了我国税收问题研究的范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刘行和叶康涛[12]通过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增加企业价值的同时,也可能面临企业声誉受损风险、政治风险等问题。管理者的能力越强,其选择避税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避税活动所带来的企业利润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减少。因此,避税行为的实施与管理者密不可分。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管理层的能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上,弥补了我国关于该领域实证研究的不足。同时加入所有权性质这一因素进行考量,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研究管理层能力在所有权性质不同的公司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探讨,得到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管理层能力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结论。本文深入研究了避税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并探讨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期能够为合理进行税收规避和遏制激进避税行为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管理层能力是指管理层的管理能力。管理层能力不仅体现在整合资源、制定战略、执行决策等方面,还体现在管理层处理人际关系、自身人格特质等方面。站在企业整体的角度而言,企业需要以既定的资本投入获得产出,管理层的作用不可或缺。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即DEA-Tobit二阶段回归模型来衡量管理层能力。Demerjian等[1]提出该量化方法,首先通过DEA模型构造公司资源利用的效率前沿,之后将效率值进行分割,剔除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之后,剩下部分定义为管理层能力。避税行为同其他投资行为一样,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避税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税收节约从而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能力较强的管理层更有可能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活动之中,而避税活动正是可以提高企业利润的活动。企业的所有者从增加收益这一角度出发,是希望企业管理层可以进行税收规避活动从而减少所缴纳税款的。另一方面,避税活动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包括税收筹划成本、诉讼成本、公司声誉的损失、公司面临的核查风险等。吴祖光等[13]发现代理成本在市场化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管理层在制定税收规避的决策时,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委托人诉求、企业外部环境等综合考虑税收规避的成本和所带来的收益。正如Park等[14]的研究结果表明,避税活动对能力强的管理层吸引力会下降,管理层会更偏好于其他可以带来较大收益的投资活动。同时,管理者在对公司内外部环境和资源进行评定时,也会考虑税收规避活动对自身的影响。能力强的管理层往往有较好的声誉,其也更关心自己的声誉是否受到负面影响,比如合理避税游走在法律边缘,其与偷税漏税往往难以把握,进行避税存在较大的风险。若避税行为激进,超越法律界线,企业和管理层的声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而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样本为我国上市公司,避税行为对管理层和企业声誉的影响更大。然而站在管理层的角度,能力较强的管理层本身就可以通过日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等获得较好的业绩,且受自身认知水平的影响,能力强的管理层会更加珍惜自身声誉,对避税活动产生的风险容忍度较低。因此,能力越强的管理层越不可能通过避税来减少税收负担以达到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综上所述,避税活动存在风险和成本,对于能力强的管理层,采取避税活动并不是最优选择。管理层的能力越强,其越不可能采取激进的避税行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管理层能力同企业避税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1.2 所有权性质对管理层能力与避税关系的影响
纳税人进行避税行为以减少自身税负从而降低了国家税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从而影响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对产权性质的划分中,目前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控股股东的性质进行区分,另一种是按照实际控制人的性质进行区分。参考现有研究管理层能力的文献,吴联生等[15]指出“国有股权问题是我国公司治理的重中之重”,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存在差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政府是以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文雯等[16]认为相比于国有企业,学者型CEO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高层次CEO的学术经历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曾姝[17]指出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大时,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账税一致避税”这一隐蔽性更强的避税手段。除此之外,刘华等[18]认为,国有控股企业面临的所有者缺位等问题使得其治理结构和决策方式等更为复杂,进而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在所有权性质不同的公司中,其避税程度会存在差异。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所有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力度更弱。在国有控股企业中,税收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等方式对企业进行税收监督和检查,所以国有企业受到的监管强度和监管力度均要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强度较大的监管力度之下,管理层进行避税活动的成本和难度也相对较大;从税收角度考虑,由于税收收入作为政府的一大收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国有控股企业承担着较大责任,因此通过税收规避减少纳税金额并不是可取的行为;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在进行避税行为时,还需要考虑政治成本和声誉风险。综上可以看出,相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能力越强的管理层,越不可能进行激进的避税活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管理层能力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不同,一般而言对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类企业和保险业公司;②剔除ST、PT以及审计师出具拒绝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样本;③剔除当期所得税费用不为正的样本;④剔除商誉为零的企业;⑤剔除研发费用总额为零的企业:⑥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共获得2 405个研究样本。本文选取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以及统计分析均通过SPSS和Stata统计软件实现。
2.2 变量定义
2.2.1解释变量的定义
管理层能力与企业价值密不可分,利用同等的资源,管理层能力越强,产出越多,企业价值就越大。学术界在对管理层能力进行定量时,多采用DEA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来构造公司效率前沿,从而测定管理层能力。本文同样借鉴Demerjian等[19]研究结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研究方式,具体计算过程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1) 使用DEA模型的分析软件DEAP进行各公司运营效率的分析。具体计算公式为如下:
(1)
式中:MAXθ表示i公司所在行业最优资源利用效率值;Sale代表唯一的产出变量-营业收入,位于上述模型的分子;六个投入变量位于分母,分别为营业成本COGS、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SGA、固定资产净额PPE、无形资产净额INTAN、净研发支出RD、商誉GW;v1~v6表示各变量的影响系数。把每一个企业作为一个决策单元(DMU),输入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选择投入导向,观察在同一产出情况下,各企业的投入情况是否需要增减以达到最优。
2) 通过第一步的结果,利用Tobit回归对管理层能力MA进行估计。本文在此处排除了公司其他层面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在此处分行业、分年度进行回归分析。参考现有研究,将运营效率中的公司特征对运营效率的影响这一部分剔除,所得残差即为本文解释变量管理层能力MA的数值。本文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θ=α0+α1SIZE+α2MS+α3FCF+α4AGE+YEAR+ε
(2)
式中:θ代表公司资源利用效率值;SIZE代表企业的规模;MS代表市场份额,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当年同行业所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和的比重表示;FCF为公司自由现金流水平的虚拟变量,正值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AGE为公司上市年限;YEAR为整个行业的年度固定效应(所有企业的求和结果);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为各变量对θ的影响系数;所得残差ε即为本文的解释变量企业管理层能力,用MA表示。
2.2.2被解释变量的定义
本文将参考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式,选用会计-税收差异这一指标进行衡量企业避税程度。会计-税收差异是用会计上的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二者之间的差额来权衡企业的避税水平,差异越大,则说明企业进行避税的程度越大。
BTDi,t=β1TACCi,t+μi+εi,t
(3)
式中:BTDi,t代表公司i在年份t的避税程度,一般而言,避税程度BTD的数值越大,表明公司避税越激进,避税程度=税负差异/资产总额,税负差异=税前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名义税率);TACCi,t为公司i在年份t的应计利润,TACC=(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资产总额;β1为应计利润对避税程度的影响系数;μi表示公司i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εi,t表示公司i在年份t的残差与公司i平均残差μi的偏离度。
2.2.3控制变量的定义
1) 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用企业年末的总资产自然对数表示。通常情况下,公司规模越大,其进行避税活动的成本也相应改变。因此本文选择控制公司规模对管理层能力与避税行为的影响。
2) 盈利能力ROA:盈利能力用净利润比资产总额表示。企业盈利能力强弱会影响企业规模,从而影响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选择。因此,本文选用盈利能力作为控制变量。
3) 资产负债率LEV:即企业财务杠杆,用企业年末负债总额比资产总额表示。
4) 产权性质SOE:若为国有企业,则以1表示,否则取0来表示。
5) 固定资产比率PPE:用固定资产净额比资产总额表示。前文提到,会计-税收差异中,有一部分差异是由于会计核算和税法规定之间存在差异导致的,比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折旧方法、残值等存在差异。这为企业管理层的避税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本文在此处加入了固定资产比率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6) 无形资产比率INTAN:用无形资产净额比资产总额表示。与固定资产类似,无形资产在核算时,由于税法和会计计量之间存在差异,为管理者进行税收规避提供了便利。因此此处将无形资产比率作为控制变量。
7) 成长性GROWTH: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衡量。营业收入增长率越大,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越好,企业通过避税行为提升价值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越大,则企业越少进行税收规避行为。
8) 上市年限AGE:用上市年限加1后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上市年限不同,公司在不同时期面对的外部环境也会有差异,税收规避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将上市年限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9) 现金流量OCF:用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净额比期末资产总额表示。
在验证假设H1之后,再按产权性质的分类进行研究,将样本数据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两部分,探讨假设H2。
2.3 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Dyreng等[4]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采用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管理层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个体影响。在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控制了时间层面的年份效应,控制了公司层面上的平均差异,控制了影响企业避税程度BTD的影响因素。为验证式(1)的假设,设计如下实证模型:
BTDi,t=α0+α1YEAR+α2FIRM+
∑kαkCONTROLk+α3MA
(4)
式中:BTDi,t为公司i在年份t的避税程度;YEAR为年份t固定效应;FIRM为公司i固定效应;CONTROLk表示第k个影响公司i在年份t避税程度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是会影响避税程度的其他财务指标;MA为公司i管理层能力,是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k为各变量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系数。表1为各个变量的定义和解释。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对筛选整理后的2 405个有效样本(其中,国有控股企业825个样本,非国有控股企业1 580个样本),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本文研究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衡量会计-税收差异的被解释变量BTD的平均值较小,最大值为0.449 018 8,最小值为-0.184 637,可见我国企业在避税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国有控股企业均值为-0.000 525 1,非国有控股企业均值为0.000 341 1,说明非国有企业的避税程度大于国有控股企业。
管理层能力MA经过DEA效率前沿量化之后,又经过Tobit回归,最终通过残差表示,因此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的数字并不大,均接近于0。但国有控股企业的均值为0.004 405 7,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0.000 456 6,但在最值方面,国有控股企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且标准差也小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说明非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整体的管理层能力存在差距,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能力差距。
从控制变量上看,企业规模SIZE最大值为27.961 7,最小值为19.205 8,且标准差为1.376 006,可见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存在着差距,且差距较大。国企规模均值大于非国企规模均值,也与我国国企规模大的实际情况相符。
盈利能力ROA均值仅为0.058 525 8,数额较小,最大值为1.181 861,最小值为-0.151 369,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国企均值为0.044 623 1,小于非国企的均值0.065 785 1,说明较之国企,非国企的经营效率较好一些。
财务杠杆LEV均值为0.471 865 1,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可能与行业有关或是由于不同的管理层对待财务杠杆的态度不同所引起的。国企的均值为0.584 686 3大于非国企的0.412 955 3,非国企的债务融资受到较多约束,因此财务杠杆数值较小。
固定资产比率PPE和无形资产比率INTAN二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重固定资产,轻无形资产投资的偏好。
从成长性GROWTH我们可以看出,最大值为5.076 488,最小值为-0.618 269,但基本存在上涨趋势。国企的均值为0.089 735远远小于非国企的均值0.205 347 5,根据营业收入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出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情况更加乐观。

3.2 相关系数分析
表3为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从下表可以看出企业避税程度和管理层能力之间相关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这证明管理层能力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该结论只能初步论证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管理层能力和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更进一步的论证需要下文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同时,观察表3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小,最大的盈利能力与现金流量的相关系数为0.555,这表明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和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

表3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Tab.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results
3.3 回归分析
3.3.1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相关性研究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表4显示企业管理层能力的变量MA与表示企业避税程度的变量BTD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23 868 2且显著,说明企业管理层能力越高,则避税程度越小,管理层能力较强的管理者越不倾向采取避税的方式。这也说明,在我国对于投资者来说,避税行为较为负面,能力强的管理者会将资源投资在可以提高企业利润的其他投资、经营活动之中,而不是进行税收规避。

表4 回归分析t值及相关系数统计Tab.4 t value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tatistics by regression analysis
此外关注控制变量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如下结果。财务杠杆LEV与企业避税水平正向相关,系数为0.008 419 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产负债率LEV同企业避税程度BTD之间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ROA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相关系数为0.220 071 9且显著,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与避税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现金流量OCF与企业避税程度BTD之间相关系数为0.043 532 9,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现金流量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SIZE与公司避税程度BTD的相关性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上市年限AGE与公司避税程度BTD的相关性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固定资产比率PPE与企业避税水平显著为负,系数为-0.002 264 2。企业的无形资产比率INTAN、成长性GROWTH与企业避税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认为假设H1成立,即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负相关。
3.3.2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
本文将产权性质作为分类依据,研究所有权不同的企业其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从表5回归分析结果,首先可以得出结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其管理层的能力均与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P值分别为0.035和0.001,其相关性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这也验证了上文的假设和回归分析结论。其次,通过分析数据可知,管理层能力对避税程度的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行为相关系数为-0.025 325,即管理层能力每上升一个点,企业避税行为下降0.025 325个点。这一相关系数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相关系数-0.024 985,即管理层能力每上升一个点,企业避税行为下降0.024 985个点。通过比较二者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即国有控股的企业管理层较之非国有控股企业越可能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因为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并不能很好的对公司实际管理者实施监督和约束,高层管理者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自己对问题的评估进行判断和制定决策,在企业避税方面也相应更具有话语权。而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管理层不仅需要考虑企业避税的显性成本,还需要考虑隐性成本,例如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等;尤其是能力较强的管理者,其政治成本更高,因此在政治风险方面也更谨慎,考虑的因素更多,管理者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力更强,因此制定决策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避税能力和避税动机更强,因此管理层能力对避税活动的影响作用会被其削弱。这也验证了假设H2成立。

表5 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回归分析Tab.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tate-owned holding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holding enterprises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再次验证上述假设H1和假设H2的正确性和本文结论的准确性,通过变量替换检验和变量滞后检验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3.4.1变量替换检验
1) 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相关性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经过上文的回归分析验证,可以得到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之间存在相关性关系的结论。为了消除统计偏误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现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在进行企业避税时采取的衡量标准是会计-税收差异,因此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将采取另一种企业避税衡量方式,即有效税率衡量,有效税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的税收规避水平越低。本文采用的有效税率ETR公式如下:
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税前利润总额
(5)
改变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方式并不影响实证结果。回归分析显示说明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可见前文的研究假设在稳健性测试中依然获得了验证。
2) 产权性质差异对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关系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H2,现同样利用ETR衡量企业避税程度,并验证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能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可以得到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程度大。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利用会计-税收差异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结果一致,再一次论证了上文的研究假设和实证分析。
3.4.2变量滞后检验
一般来说,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存在滞后性,具体而言,本期投入的各项资源转换为实际产出不一定会在本期得以体现,管理层的能力可能作用于未来期间的产出。因此,考虑到管理层能力滞后性,参考孔文泰等[20]在进行稳健性研究时的方法,将解释变量管理层能力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再次检验是否与上述回归分析得到相一致的结论。
1) 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相关性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管理层能力滞后一期进行回归,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行为负向相关。说明管理层的能力越高,企业越不可能实施税收规避行为。这与上文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之前的研究结论。
2) 所有权性质对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关系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在验证了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之后,同样考虑产权性质存在差异时,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关系是否也存在差异。研究中可以发现,在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管理层能力和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相关关系仍为负相关。其中,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的相关系数,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相关系数,该稳健性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回归分析结论。可见企业产权性质不同,管理层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也不相同,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更显著。
4 结论及建议
管理层能力越强,越会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产权性质不同,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在考虑避税活动增加企业价值的同时,避税活动产生的成本同样不容忽视。而成本的核算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要求管理层在进行税收规避时,需要考虑避税成本和收益,因此,冒险避税并不是管理层的首要选择。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为特殊,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因此这也造成了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进行避税行为时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较高。非国有控股公司自身避税能力和避税动机更强,管理层能力的提升对避税活动的减少作用会受影响,会被企业自身避税动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个人效应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较弱。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掌控着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避税行为只是增加企业利润的一种方式,但存在较大风险和不利后果,并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也可以通过加大对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抑制管理层采取避税行为。
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在进行人才选拔时均存在问题。企业的员工缺乏对管理层的监督和考察,因此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制度对企业日常经营显得愈来愈重要。同时政府税收部门需培养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提高税收流向的透明度,真正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此提高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纳税行为的责任感。作为监管部门,要完善法律体系,加大税收部门的征管力度,深入开展检查工作,对企业所得税税收工作严格把关,针对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管理层能力对避税行为影响程度不同问题,可以加大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税收监管力度,从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