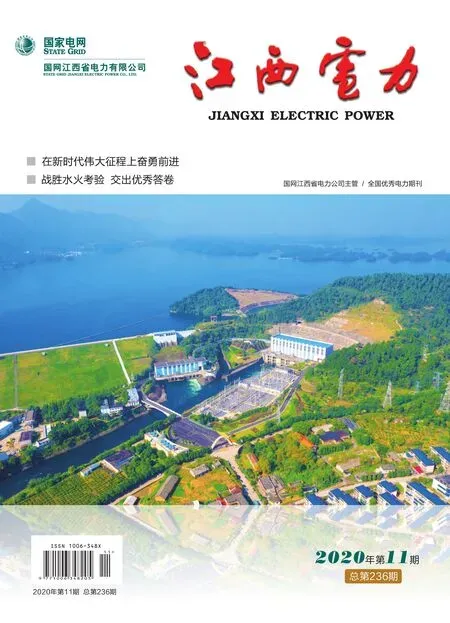橘子皮儿
2020-12-14文_余盼
文_余 盼

自小知道,橘子皮是一味药,治感冒咳嗽。只要着了凉,背上稍稍有点凉,尚未咳出来,母亲就嚷着,踢被子了吧,衣服穿厚实一点!临吃饭,临睡觉,将一个搪瓷大罐端出来,让我走到罐前,头上罩一块毛巾,将我的头摁近罐盖,把盖子打开,一股腾腾的热气蒸上来。“先蒸,再把汤喝了!”
待热气慢慢消散下去,我端起杯子,将里面的料儿都吃个一干二净。里面有啥?橘子皮,生姜,放点红糖。每天都这么来一下,居然也不用吃药,感冒就渐渐好了!
因此,我也继承了这个习惯。后来,寻医问药方便了,也不用再拿橘子皮儿当药吃,但仍然晒干,用来做香料泡茶烧菜,却是一种老传统,老习惯。
橘皮经放,越放越香。老家做辣豆腐,豆腐里面掺进虾米、腊肉、辣椒和橘子皮末儿,放在火上烤,喷香。橘子皮炖肉烧鱼,那是常料儿。有橘子皮炖的肉,跟没橘子皮炖的肉,就少那么一点特有的香味儿。
素常,我在桂花树下拾掇点橘红的、金黄的丹桂银桂儿,晒晒干,再弄点老枇杷叶,剪碎了,晒晒干,再将橘子皮晒晒干,放一点蜂蜜——一杯自制的桂花止咳茶就泡好了!除了老家送来的土蜂蜜,其它都自己拾掇,不花钱。泡在玻璃大壶里,有黄有绿,养眼。
橘子皮儿,也就是陈皮。中国的陈皮,要数广东新会的最闻名。淘宝上点开了看,哇,一百多块一斤。中国茶博会在杭州开,正好在会场,逢着新会县城的陈皮商人,看到橘子皮儿一剥三瓣儿,伺弄得跟朵花似的,一叠叠码起来,扎好捆好,盛在特制的透明器皿里。价格按照年份,好似建德五加皮、绍兴花雕,几年陈,几年陈,放得黑黑的,三百多块一斤!
亚洲的土壤,大概特别适合产橘。越南橘子运到杭州,十块钱三斤。浙江各地都产橘,柑橘多,便宜,黄岩蜜桔一斤也要将近五块。要我说,再把多下来的橘子皮做陈皮,做香料,那用处就大了!
书上写,以前的贵妇住的是“椒房”,就是夯土的泥筑,加进了“椒”这样的香料,除湿,透香,不知道有没橘枝儿。读古书,就知道,古代的人并不落后,生活里头有大讲究,精美着呢。要我说,其实这些我们看上去随意扔的东西,古人都用得好好的,比我们有心呢!
橘子,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水果,在古代却不是寻常之物。看屈原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橘子,可是皇宫里的稀有果味儿,且,不是容易迁徙的品种,有着坚定不移的高洁品质。因此,古人有将自己比作丹橘而自荐的,譬如张九龄,“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岁有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亦有刘伯温《卖柑者言》,虽然只是买到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橘子,但因此引发的时政之感,却也有一番质朴的治国道理。
自然,橘子皮儿还能做灯,冰心的小橘灯,守着童年,守着纯真,守着对未来的祝福与希冀!
夏秋,橘子上市的季节,我少不得买上几袋,吃完橘子,将橘子皮放太阳底下晒。有一天,回家迟了,大概橘子皮干儿剪得一瓣一瓣的,太阳底下,透香,橙黄,招眼儿,居然还招了顺手牵羊的主儿。
如今,吃完橘子,我还是将皮儿到处晾,车上也是,桌上也是。这都是外婆身上传下来的习惯,可惜如今的年轻人不懂得,不时兴了。我想,眼里看到的,会成为记忆,看似不经意,却储存着,到了哪天,孩子独立过生活了,这些习惯就会重新呈现出来。这就叫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