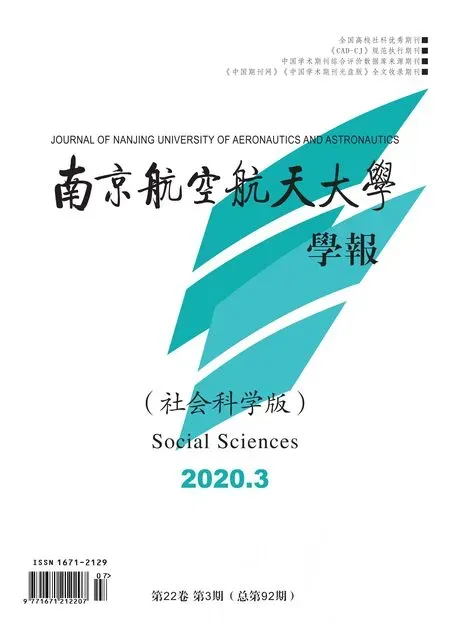论《京华烟云》听觉叙事的模式及听觉空间的建构
2020-12-14陈智淦
陈智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福建漳州363105)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林语堂小说三部曲之一《京华烟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哲学思想、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译本的翻译策略等,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京华烟云》却相对匮乏。刘锋杰指出,林语堂在小说中重视家族作为意义传达的叙事功能,他采用家族叙事模式展现家族衰亡;[1]赖勤芳则研究该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2]陈智淦、张秀燕从旅人的行踪作为小说的线索分析其旅行叙事。[3]上述研究均属视觉叙事的范畴。在叙事学领域,与视觉叙事相比,听觉叙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听觉叙事研究指向文学的感性层面,这一层面貌似浅薄实则内蕴丰厚……听觉叙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断发出声响的动态世界……这个世界似乎更为感性和立体,更具连续性与真实性。”[4]实际上,《京华烟云》拥有丰富的听觉意象和声音资源。小说中蕴藏丰富的听觉叙事,即听觉感知叙事或声音叙事,不仅包括物理层面的声音景观(声景或音景),也包括作者对声音的意识,以及把声音当作感知对象的强烈感觉,如傅修延所言:“诉诸听觉的讲故事行为本是人类最早从事的文学活动,从‘听’的角度重读文学艺术作品,有助于扭转视觉霸权造成的感知失衡。”[5]林语堂在小说中对声音的复制与扩大表现出强烈的想象力,即便是旧派人物代表姚思安对声音也曾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我们,声音就是声音而已。一道光线,也就是光而已。但是洋鬼子却把声光发展成一门学问。而制造出留声机、照相机、电话机。我还听说有电影,不过还没看见过,要学这个新世界的新东西,忘了我们的历史吧。”[6]263他表示要关注西方世界制造出的留声机、电话机、电影和照相机等,这番有关现代技术化声音的言论让新式人物孔立夫都为之敬佩和感动。声音或听觉感知行为也是小说独特的叙事焦点,尤其是女性角色对声音持有天生的敏锐感觉,无论多么细微的声音都能听见,莫愁甚至“睡着了也能听见东西”[6]575。
叙事学理论中的“视角”“观察”“聚焦”“焦点”等文论术语偏重视觉,与“谁看”的视点不同,叙述声音“控制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叙述与被叙之间的关系。尽管常常与视点相混合或混淆,但与人称相比,声音有更广的外延。”[7]换言之,“谁说”的“声音”更倚重耳朵、嘴巴等接受或传递信息,而且比视觉器官还清晰。国内叙事学研究学者傅修延在听觉叙事研究中“创建和移植一批适宜运用的概念术语”[8]中首推“聆察”“聆察者”等研究话语工具。其实,“聆听”“聆听者”等术语更为准确。此后,国内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听觉模式对文学作品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研究,呼吁重视和恢复听觉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9]听觉叙事研究潜力巨大,听觉叙事研究首先离不开听觉空间的建构模式。“听觉空间的建构取决于有意识地听或无意识地 听 ,不 仅 诉 诸 于‘ 实 听 ’‘ 虚 听 ’‘ 共 听 ’‘ 独 听 ’‘ 偷听(有意或无意)’等等,不同种类的听会建构出不同的听觉空间。”[10]根据听觉叙事所依靠的听觉空间大小和声音来源的不同,《京华烟云》中听觉叙事的模式大体分为独听、共听和偷听等。其中,独听和共听有时可以彼此相互转化。听觉叙事的模式及听觉空间的建构研究既可以拓展该小说的叙事研究视野,也可以为林语堂其他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通过听觉感知或声学的阐释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声音事件的重要性,从而发现理解小说叙事意义的新方式。
一、独听模式
小说中不乏描绘发自多个声源、分布在空间各处的声音,但只通过一个聆听者来聆听,这是一种多个声源单个聆听者的独听模式。
在第12章,林语堂在描绘北京城这一人间福地时,他借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姚木兰之耳独听城市空间里的声音。“有街巷小贩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走街串巷的理发匠的钢叉震动悦耳的响声,还有串到各家收买旧货的清脆的打鼓声,卖冰镇酸梅汤的一双小铜盘子的敲振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妙。”[6]163在古都北京这一城市空间里,客观存在的城市声音和林语堂主观上对听觉感知的兴趣构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即听觉主体)叙事描写的背景。变戏法、马戏团、戏棚子、街巷小贩的叫卖声等人声和钢叉震动声、打鼓声、铜盘敲振声等市声是古都北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常模式,这些声音所发出的时间和位置各不同,但聆听者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对不同时间发出的不同声源进行重组之后的独听叙事支撑起北京古都所特有的一片音景。
其实,这个聆听者姚木兰隐含的听觉主体是林语堂本人。声音作为古都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地烙印在林语堂的记忆中。林语堂在1961年出版《辉煌的北京》一书,他在这部地方志式的著作里以一名游客的身份置身于帝都北京的多个角落,向国外读者层层讲述北京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剖析北京文化的各个层面。充斥小巷的各种小贩叫卖声也是北京民众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声音“轻柔,低沉,远远地拉着长腔……那是一种独特的、平静的、睡眠时不可或缺的声音。”[11]21林语堂定居海外数十载后依然记得街头小贩制造的种种声响,包括给孩子理发的大音钗所发出的震响、卖酸梅汤用铜盘和瓷勺敲碗所发出的叮当声、叫卖冻柿子时的吆喝声等人声和市声。
由于小说的大部分故事都置于北京,帝都北京所发出的晨钟暮鼓声庄严地回荡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林语堂还以聆听者曼娘的角度描述北京这一标志性的声音,曼娘与木兰一样,在院子里听见街巷里小贩在清晨时所发的叫卖声。“可是她也有女人长居深闺中发展出来的听闻的敏感。听到的声音也是新奇而美妙的……她听得见鼓楼的暮鼓,听得见钟楼的晨钟。虽然钟鼓二楼离曾家有一里之遥,但是震荡之声半城都能听见。”[6]165曼娘在夜里不眠时所听到的打更声音其实就是鼓声。这个声景也是典型的独听模式,晨钟暮鼓声成了曼娘敏锐听觉的刺激物。于曼娘而言,北京城巷子里的叫卖声也融入到城市的标志音中;于林语堂而言,即便在他离开北京35年之后,他也依然清晰记得自己居住北京时聆听到的替代钟声的梆子声和叫卖声。“古时候,钟鼓楼传出的钟声充当着守夜人,这职能现已被城市雇佣的守夜人所代替。他们走街串巷,用木锤击着梆子,午夜击三下,破晓时击五下。”[11]21曼娘对晨钟暮鼓声的独听足以说明,林语堂对北京古城特有的标志音的怀旧心理非常强烈。
同样,小说中风景描写的视觉叙事和湖上、河上等场景中船夫、船娘发出的歌声、箫声的听觉叙事也非常突出。比如,小说的视觉叙事体现在林语堂描绘荪亚、木兰带着儿子从徽州回杭州的行船过程中的风景,“在河面船上过夜,明月高高在山上,微风自河面吹来,其美真是无法描绘”。[6]748而听觉叙事的画面则更是不胜枚举,比如,木兰和荪亚等人同游杭州西湖时,“他们乘小舟徜徉于湖面,享受湖面轻柔的微风,听远处船上青年男女的歌唱。”[6]466再如,木兰一家探访定居苏州的立夫和莫愁一家,雇船“往乡间去,河道渐宽,岸上陆地宽阔,在月光之下,一片恬静。一个船娘会吹箫。”[6]649其实,小说中的这些视觉叙事和听觉叙事都是林语堂挪用了童年记忆片段的体现。
1905年,林语堂就与其兄长乘小船经过小溪、西溪到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小学读书。在《林语堂自传》(1936)第1章《少之时》中,林语堂如痴如醉的描绘了30多年之前从家乡坂仔到漳州的行船夜景,除了江中行船三日的沿途风景极具诗意之外,“……[船上]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着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12]10林语堂在童年时亲历的这些风景与声景共同构成的充满美感的良夜美景永远镂刻在他的记忆中。时隔40年后,林语堂在《八十自叙》(1975)第2章《童年》中依然清晰的再现了儿时求学途中行船码头的夜景以及船工的夜间生活,他回忆说:“有时,我们听见别的船上飘来的幽怨悦耳的箫声。音乐在水上,上帝在天宫。在我那童稚的岁月,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12]63
可见,小说中独听模式的声源分布在听觉空间的各个角落,该模式的听觉空间范围相对较大。林语堂在离开北京数十年之后依然能够如此清晰的回忆北京城内的各种声音,“与林语堂在北京近6年(1916-1919年,1923-1926年)的生活足迹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经历密切相关。”[13]51他甚至认为,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孩童时期以及灵敏的感觉是“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12]6。林语堂从小就表现出对听觉感知的强烈兴趣及其对声音敏锐的感受能力,他在两部自传中记载的童年记忆与小说中木兰在湖上、河上等各种听觉空间里的听觉叙事具有惊人的相似。
二、共听模式
小说中建构的听觉空间不仅诉诸独听模式,也再现了发自一个固定声源但却向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多个聆听者扩散的声音,这是一种单个声源而多个聆听者的共听模式。
在第26章,林语堂描写姚家迁入新居后举行盛宴时意外请进的打把式卖艺表演。表演者是一家父母姐弟等老小四人,分两组相向站立。父亲打鼓后四人同时载歌载舞,唱短歌时用“得而——拉他飘一飘”的重复收尾句。“可想而知的是,这两个重复尾句若是由一个好合唱队唱,会是很美的小调儿……倒是那个姑娘和她弟弟的声音在春天的空气之中,畅快可喜,听着蛮好。”[6]393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或庭院空间中的听觉叙事。卖艺人在歌唱完毕之后,这个小姑娘及其父亲与弟弟分别在姚家府内表演了两个杂技节目。林语堂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同样记载北京城普通百姓种类繁多的娱乐活动,除了在茶馆或小酒店里谈天说地之外,“出名的娱乐场所多的是,如前门外的天桥,歌曲、音乐、女人、拳术和杂技,应有尽有。戏院通常是露天的或坐落在院子里。”[13]235林语堂对京戏表演非常熟悉,他不仅长篇介绍京戏表演者的程式动作、唱腔、台步、笑法等各种表演技巧,还详细介绍公共娱乐场所的秦腔、陕西梆子等西北风格的乐曲、主题以及京剧唱词的发声、昆曲剧种等。
在这一章中,牛怀瑜的声音同样多次回荡在此次家庭盛宴上,他当众对孔立夫恭维的话语既滑稽可笑,又让参加盛宴的人尴尬不已。立夫听到牛怀瑜嘴里吐出的空泛词句“像连珠炮般爆发出来,就像学校毕业典礼时政客的讲演,实在听之熟矣。”[6]400之后,他在餐桌上对政界的大发议论更是引发所有人的强烈不满,“怀瑜一边说话,一边不断清嗓子,唾沫星子乱飞,声音之高,使邻桌的妇女,有时会停下谈话来听他,好像大家都要准备听了不起的政治秘闻一样,连仆人都觉得他们伺候的必是一桌子内阁大员。”[6]400林语堂以幽默式的方式描绘这幅共听盛宴,把怀瑜口中的石油统制政策、新公债等比喻成宴席上丰富的一道道菜。大厅里的所有听者都不敢言语,但怀瑜一番拥护新元首、报效国家的言论在饭快吃完时却直接遭到立夫的公开驳斥和猛烈攻击,宴席最终草草收场。
在第45章,林语堂描写姚木兰迁居杭州后参与小教堂的祷告活动,“木兰在城中城隍山的家里,在圣诞节,听得见天主教修道院的歌唱……修女的特别的诵经声和纯白的脸,非常感动她,她的眼睛湿湿的,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永恒。”[6]766-767这是小说中唯一的教堂空间的听觉叙事,木兰在观看教堂中新奇的典礼以及修道院院长的动作时联想到家中刚遭遇的变故而感慨万千。她此时复杂的心情完全与她身处教堂的听觉空间中所感知的声音密切相关。同样,教堂里的听觉记忆伴随着林语堂的一生。他在孩童时期因为家庭信仰的缘故就与教堂活动的音乐结缘,在《八十自叙》中仍记有童年时在教堂做礼拜时对教堂钟鸣的回忆,自己在做礼拜时在空中飘荡的钟声在会众耳中犹如神圣的音乐。他在教堂中对西洋音乐耳濡目染,教会的赞美诗和歌声就是其童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潜移默化的音乐熏陶让他成为音乐的信众。
此后,林语堂在鼓浪屿的求学阶段(1905-1911年)更让他从此与西方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02年,鼓浪屿就沦为公共租界,外国传教士也随之来到鼓浪屿建立教堂并开始传道,他们“在教堂举行宗教活动,总伴有唱诗节目,教会兴办的学校也都开设唱圣诗的课程。随着年代的推移,弹唱西方音乐蔚然成风”。[14]20世纪初,现代钢琴传入厦门,在鼓浪屿求学的林语堂也深受音乐的熏陶,“走在山上小道可以听到从洋房里传来的贝多芬或肖邦的钢琴曲,或从教堂里传来的《圣母颂》”。[15]在《八十自叙》(1975)年,林语堂承认他在鼓浪屿求学时期所听到的传教士的合唱音乐对自己的影响:“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12]80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阿苔)描绘林语堂赴美后与家人在纽约第五街散步时甚至走进回教徒的教堂,尽管林语堂并非回教徒,但他表示“‘要去听音乐,不是听他的布道。’我们走了进去。但乐队已停止奏乐,我们只坐了五分钟便出来。”[16]换言之,与其说林语堂为教堂的音乐所吸引,不如说他对音乐与生俱来持有一种本能的敏锐感知能力。
总之,小说中共听模式的声源描写主要来自于听觉空间里的某一个角落,如庭院、餐厅、教堂等。如果聆听者离声源位置太远,即不处在同一个听觉空间中,就不可能听到声源。因此,共听模式的听觉空间范围相对较小。
三、独听和共听的共存模式
首先,当听觉空间的界限模糊或无法断定聆听者为何人时,独听与共听模式的区别不明显而难以确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特别明确的界限。
在第20章,林语堂刻画木兰思念立夫之情时穿插了木兰在晨间花前或夜晚月下迷恋诵读或唱相思诗词的情节。林语堂除了一句话交代木兰精读李清照的词集《漱玉词》之外,他还完整地引用木兰诵读李清照《声声慢》这一首词,小说提到该词的“开头用七对相同的字,用入声,最后以‘了得’结尾,就如梧桐滴雨,点点滴在她的芳心上。”[6]274在这一情节里,读者完全无法判断小说中的“她”是指李清照或是姚木兰。读者同样无法判断现场的聆听者是谁或处在声音空间的何处,甚至作者也不一定清楚地意识到此时木兰发出的声音是“独听”还是“共听”,但他在小说中完整展现木兰吟唱或默诵李清照的这首词用意令人深思,词中凄清的音乐性语言(包括平仄的节奏和重复的格律)尽显木兰莫名其妙的伤感与愁绪。尤其是词中起句的七组叠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结尾句的两组叠词(点点滴滴)极富音乐美,李清照的低声倾诉和忧伤的愁绪也是木兰当时心情的写照,词人复杂的思绪、凄凉孤独和惆怅茫然借助风声、雁声、落花声、雨声等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第36章,林语堂描绘木兰的女儿曾阿满参与的学生游行活动,当孔立夫从私人方面得知段祺瑞政府要对示威者采取行动后急忙骑车前去寻找阿满。他挤进总理衙门的入口时听见尖锐的来复枪声、学生的尖叫声。段祺瑞的卫兵从埋伏的各处角落跳出,拿刀带枪地向学生连劈带砍。“他看见一个魁梧高大的卫兵,脱去了上衣,一边挥舞铁鞭,一边发狂般大笑……那条铁链子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打上了他的右踝骨,他想他的右脚一定打断了。但是他还往前挤,脚下踩着了一个躺在地下的人……只有那个使钢鞭的人,不显疲劳……他用有节奏的吼叫配合着钢鞭的响声,再找人逞凶。”[6]582如果从聆听者的角度看,对于示威者和镇压者而言,他们身边的声源都是共听模式,而对于在游行队伍中寻找阿满的立夫而言,周围远近的一切声源都是独听模式。同样,枪声、学生的喊叫声和卫兵的厮杀声是整个游行事件背景的定调音,而突出在前景位置的铁鞭、铁链、钢鞭的响声则是信号音。可见,在这起爱国学生的游行活动中,定调音和信号音同时共存于一个混乱不堪的音景画面里。这一听觉叙事的写实全景同样是林语堂在自传中两次回忆自己参与和目击“三·一八”惨案的经历。林语堂借助声音画面有力地控诉军阀政府的暴行。
在第39章,阿非和宝芬在北京饭店邀请姚、曾两家的人聚餐。在这所洋饭店舞池里,中外男女老少杂沓共舞,嘈杂的舞曲声是定调音,而曼娘因为第一次看到女人、洋人跳舞而手脚忙乱,她手中的叉子掉盘子上时发出老鼠般的尖叫声。尽管饭店舞池的声音能压倒读者对个别声音的注意,但画面中叉子掉盘子上发出的呛啷声和曼娘老鼠般的尖叫声与舞曲声不协调,更能引起现场周围人群的注意,洋女人的瞪眼相看与曼娘战战兢兢的神情形成鲜明对照。曼娘首次进舞厅的尴尬与《红楼梦》中第六回写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好奇如出一辙。虽然这些看似不协调的信号音与周围舞曲声的定调音显得格格不入,但也同样共存于饭店空间的音景画面中。这是聆听者所捕捉到的更加复杂的双重听觉感知,即同时感知到个别声音和集体声音的存在。
其次,当聆听者置身于战场屠杀难民的听觉空间里,枪炮声的巨大声响导致声波延长和听觉流异化,距离聆听者非常遥远的声音都能吸引其注意,这种听觉空间范围非常大。
在第45章,林语堂描写木兰、荪亚、肖夫等人在一个青年副官指引下驱车穿过战区,昼夜可闻的爆炸声、大炮响声、机关枪声音等就是听觉空间范围大的共听模式。同样,林语堂描绘木兰和家人西迁逃难过程中经过松江火车站遭遇日本侵略者空袭屠杀时的听觉叙事也是如此。
不久,外面喊声又起,飞机的嗡嗡声又回来了。
荪亚蹲在中间通道的边上,阿眉和木兰几乎在座位下平伏,阿眉吓得直哭。他们把衣箱拉到头上遮挡。这时有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全车都震动了,一定是前头或是后头中了炸弹。然后是天空机关枪嗒嗒的声音凶猛地响。外面的难民自上空遭受屠杀,犹如猪狗一般。[6]761
难民鬼哭神号的尖叫哭喊声、飞机的嗡嗡声、炸弹响声、天空中机关枪咯咯乱响声等各种声响混乱地交织在日本侵略者残酷屠杀难民里。在这幅由各种震耳欲聋的混杂声音画面里,因个别声音和集体声音共存,聆听者听觉感知变化迅速,声音来源复杂,听觉场面混乱不堪,共听或独听的听觉叙事模式模糊难辨。任何一个听觉敏锐的聆听者如果处在这样一种多结构声音网络的“环绕音响”的空间位置里,都会受到多种非常规的攻击性声音的刺激而丧失其原有的正常听觉认知能力。林语堂在小说中以精彩的听觉叙事画面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性。
实际上,林语堂在创作该小说前虽然没有亲历战场,但身在海外的林语堂时刻关注国内的抗战情况,他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每天都到《纽约时报》大厦前的广场,关注最新抗战消息。巧合的是,志在为抗战出力的林语堂于1940年5月携全家取道菲律宾,辗转香港回到重庆。他在回国后居住北碚,甚至搬至缙云山一座庙宇,以躲避日机的狂轰滥炸,亲身经历日本侵略者给重庆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野蛮轰炸。
可见,独听或共听模式所建构的听觉空间范围大小是相对的,二者因听觉空间界限模糊、听觉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或在场聆听者身份的模糊性而难以辨认,因此彼此并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
四、偷听模式
偷听,即偶听,是一种叙事文学作品中不确定的听觉感知。偷听与幻听、灵听是叙事学领域中“不可靠叙述”的三种常见的听觉叙事手法,“听者多在不经意间接受到触动自己的听觉讯息,因此,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被卷入行为,听者最初并无获取相关讯息的主观意愿,当然也就不可能预先为此作什么准备。”[17]相比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独听或共听的听觉叙事模式,林语堂在小说中虽然不乏简略描写的偷听事件,比如第35章,曾府丫鬟雪花听到经亚与其父亲曾文璞、曾太太和姨太太的对话中商量经亚与暗香的婚事,但小说中描写最为详细并为故事的发展、转折提供动力的偷听事件却只发生在冯红玉身上。在第33章,林语堂详细描写冯红玉一次无心偷听阿非与美国小姐董娜秀的对话。
红玉回去时,大家已经往忠敏堂去了。她正要转回,听见阿非的声音,也看见环儿的头在忠敏堂内,然后又听见美国小姐的声音。
她正往里走,在台阶儿上,听见阿非说订婚的事。她就躲在假山后偷听。阿非刚才是说巴固要和素丹结婚,是因为不忍心教素丹做卖煤球儿的生意,但是说话的声音低,她只能听见说话的片段。
她听见阿非说:“男人就是那个样子。为自己心爱的小姐怎么样都可以。我也是那样儿。”
环儿说:“我听说她有个痨病根儿。”
美国小姐问:“痨病是什么?”
阿非很严肃地说:“就是tuberculosis。”
“那么你还娶她吗?”
“我当然还要娶她。男人就是那样儿……由于怜香惜玉……宁愿伺候她一辈子……她好美,就是任性。”[6]514-515
在上述林语堂描绘的忠敏堂这个听觉空间里,就对话双方最近的聆听者孔环儿而言,她是唯一一位与说话双方作近距离正面交流的正常听者,能够如实还原对话的全部信息,“[阿非与董娜秀的对话]是关于素丹订婚的事。我们说她有肺痨病,阿非说巴固娶她是由于怜香惜玉的一番爱心。四妹可能听见我们说话,也许以为阿非说的是她自己。”[6]523而红玉的听是一次介于“无心”和“有意”之间的偷听事件。偷听者红玉躲在假山的后面,而且说话者阿非声音的低沉,她只能听见对话双方的片段。阿非的话语中间的三个省略号表明,他说的话受到假山的阻隔等因素的影响并未能如实的传入到红玉的耳朵。“他们走去之后,她才摇摇摆摆走到洄水榭去,瘫软在椅子上,她的两颊一会儿气得苍白,一会儿羞得通红。她的自尊受到了破坏,她的爱情受到了创伤。他爱她,可是……事实是……他那么说了……可是他会娶了她,由于怜香惜玉而伺候她一辈子……他爱宝芬不?她该怎么办才好呢?”[6]515这段红玉心理描写里的四个省略号说明,红玉拼凑偷听到的碎片化信息既不清晰也不完整,因此,他在这起偷听事件后的想法乱作一团,既有羞愧和自责,也有出于自尊的心理做好牺牲的打算。总之,她偷听到的信息彻底背离了原对话双方的真实信息,误认为对话者谈论的对象是她和阿非,最终引发了红玉自杀的悲剧。
可见,红玉自身因为受到体弱多病和多疑多虑、易怒等性格的限制,她对自己无意中听到的信息反应过度,无法在短时间内运用理性思维对偷听到的信息碎片进行拼凑还原,紧接着就留下遗书而跳池自尽身亡。如傅修延、易丽君所言:“偷听者要将听到的碎片状话语编织成可以理解的信息,就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将其‘二次叙述’……由于无法实现彻底的‘还原’或‘归化’,二次叙述与‘事件的原始形态’之间总会形成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也为叙述平添了许多意趣与悬念。”[18]红玉的偷听事件对整个故事的演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语堂通过偷听模式的听觉叙事意在制造一种叙事张力,为故事增添悬念。
五、结语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曾强调声音层面的重要性,“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19]尽管声音在《京华烟云》中作为核心事件或非核心事件有时很难断定,但它是小说产生意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林语堂在小说中的叙事焦点绝不仅限于视觉范围所描绘的风景,声音层面是构成小说作品审美效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以城市、湖上、水上、庭院、教堂、饭店舞池、战场等不同听觉空间所回荡的各种声音与听觉体验来表现清末民初长达四十年中国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以此扩展小说听觉叙事的天地。林语堂通过听觉叙事积极建构独听、共听、独听与共听共存以及偷听等多种听觉叙事模式,与其从小对听觉感知的强烈兴趣和对声音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密切关联。总之,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展现的声音资源、听觉意象和听觉叙事情境说明,他与声音(包括音乐)结下的情缘及其丰富的听觉想象贯穿其生命的始终。林语堂在其他文学作品创作中有意或无意设计的声音与事件之间的隐秘联系、听觉元素与事件的关联性,以及他强调聆听的重要性、对听觉的敏感性和对声音产生反应的内在冲动的复杂根源,并以声音为媒介建构丰富虚构世界时所传递的独特叙事特色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展开详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