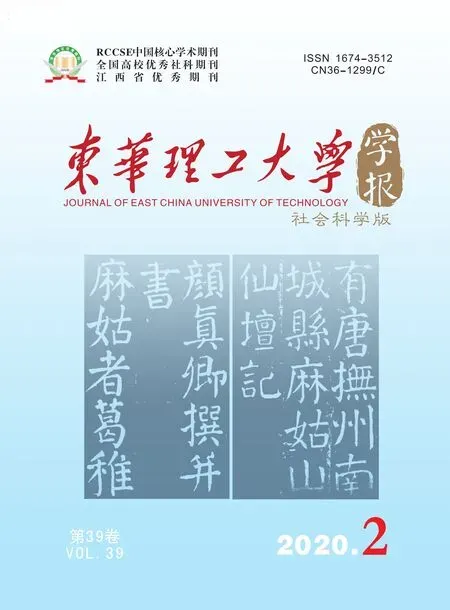从“声乐跨界”现象看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趋势
2020-12-13颜铁军曹正钰
颜铁军, 曹正钰
(吉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声乐跨界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艺术现象,已成为一个音乐研究领域的学术词汇。2020年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词“声乐跨界”显示共有170篇相关文献。我国关于声乐跨界研究自2005年以来,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2016年形成高峰,之后研究稍有所下降,但仍是备受关注的学术问题。鉴于笔者在声乐演唱与教学中的体验,结合观众接受美学的考虑,有必要对声乐跨界现象进行再探讨,并对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趋势作以研判。
1 跨界的词源分析
跨界,英文为Crossover,也可译为“Crossover Music”。《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中将 Crossover 一词解释为“多领域或多风格的成功,尤指音乐”;《韦氏新世界音乐词典》对 Crossover 有这样的定义:“原本是为某一类观众准备的音乐,表演者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风格演奏,在另一类观众那里获得高度成功的现象。”[1]跨界并不是音乐专有词汇,摄影、美术、服装等艺术领域,甚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经常用这个词汇。所以说,跨界是一个很宽泛的、包容性很强的、涉猎范围很广的词汇。跨界是由“跨”“界”两个语义非常清晰的字构成的动宾结构词。“界”是不同范围、范畴的分水岭,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事项被纳入到同一范畴,性质相异的事项被界隔为另一范畴。“界”使各个不同范畴保存着自己的本质属性、功能、特色。但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它事物或受其它事物影响。“界”的形成除了事物的内在属性的同一性特征外,不排除人的主观划分。事物的属性往往具有几个,其中最为核心的属性成了它所在范围、范畴的主宰,所以任何范畴不是单一的属性和性质,在本质上不具备排他性,其它被压制的属性依然在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为“跨”,即事物的转化提供了动力。“跨”的词性为动词,实质是打破范畴的“界”。某一范畴使另一范畴的性质发生转化或者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彼此融合,产生新的事物。事物之间跨界既有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政治、文化)的外在影响,也有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跨界的实质就是事物的联系,跨界生成的逻辑顺序应为游移、突破、转化、融合、再生这一完整的过程。通过对跨界的词源分析,可以看出跨界是事物间的联系。事物间相互转化融合并形成新的事物,是一个古今中外较为普遍的现象。换句话说,跨界是联系、融合、创新的代名词,只是具有了一个更为新潮的名字罢了。
声乐跨界是跨界现象在声乐艺术中的一种艺术形态和表现形式。原始时期人们祭祀与歌舞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萨满歌舞艺术。周代把祭祀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中世纪的欧洲把合唱用到基督教会的各种仪式中,产生了圣咏、弥撒、众赞歌、受难乐等音乐艺术。音乐跨入到宗教领域,丰富了音乐品类,产生了特殊的审美形态。不同的音乐冲破界限产生新的音乐体裁,是音乐发展历史的重要事项。我国的京剧就是西皮和二黄相融合的产物。陕北民歌与蒙古族民歌融合,形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的蛮汉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民族声乐基础上吸收西洋演唱技法,形成了我国早期的民族声乐学派。如此种种,都是跨界的结果。
唯物主义发展观认为,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从量变演化成质变。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的积累助推质的变化。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会产生社会革命或变革。声乐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同样积蓄了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应在学术界与广大听众对声乐艺术的审美标准的差异,而声乐的跨界恰恰是艺术审美心理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矛盾如何产生及如何来理解这种文化现象,现在有必要对我国现代以来声乐的“界”形成作以简要回顾。
2 我国声乐跨界的百年历史回顾
当代声乐跨界主要是指声乐演唱中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的相互借鉴融合发展。近百年来,三种唱法经历了自发发展、自觉发展、自由发展三个历史时期。
自发发展时期(1918-1949年)。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可谓自古有之,唯有美声唱法纯属舶来品。五四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出现了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变革。西方文化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城市音乐教育。音乐家王光祈、赵元任、黄自等到德国、美国留学,声乐教育家、歌唱家周小燕到法国留学,沈湘到意大利留学。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还聘请了苏联的石苏林先生教授声乐。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声乐人才流动现象对美声唱法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声唱法主要运用在北京、上海专业音乐院校的声乐教学中。民族唱法在这个时期仍处于原生的自发状态中,普遍存在于我国广大乡村及城市平民阶级之中。通俗唱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等大城市中盛行。黎锦辉、周旋等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
自觉发展时期(1949-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文化艺术界围绕着唱法的“土”“洋”问题展开了对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大讨论。经过多学派严谨周密的讨论,且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争论、分歧下,最后形成了创建民族声乐学派的创想。讨论达成共识后,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院校开始设置民族声乐专业的热潮,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民族声乐歌唱家,开创了民族声乐的新局面[2]。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民族声乐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并已自成体系[3]。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歌曲不断发展,尤其是通俗歌曲在青年人中倍受欢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至今已举办十五届,历经30载,在此平台上诞生了许多歌唱家。尤其是最终确立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三种唱法,对我国声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第一届青歌赛上,除民族唱法三等奖一人获奖外,美声唱法中几乎包揽了一等、二等、三等奖,而通俗获奖数为零。虽然三种唱法存在着技术难度上的差别,但从审美主体和艺术主体来看,三种唱法风格不同,不能以技术难度作为评价标准。鉴于第一届青歌赛的争议,1986年的第二届青歌赛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两组,每组又分成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三种唱法。清晰地划分了三种风格流派,对每个风格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直到21世纪初,很多人还在强调民味、美味、通俗味的纯粹性,欣赏习惯中三种唱法的界限泾渭分明,甚至排斥唱法的跨界混搭。最近几年,由于主流媒体的不断推介,使更多人认知、习惯了声乐跨界,对跨界的吐槽已全然退出审美视界。尽管后来又提出了原生态唱法、组合等,但三种唱法仍是歌唱风格体系的核心。
自由发展时期(2000—至今)。三种唱法虽然表现出风格的明显差异性,但在实践中,过多分裂三种唱法有机联系,人为制造界限、划清界限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艺术发展规律的。声乐跨界由一种唱法引向另一唱法,由一些人带动更多人的尝试,使唱法的僵化状态转为灵活,单一性转为多样性,进而引发了三种唱法自身内部的裂变,纯的或权威的提法慢慢淡然,更多的富于个性的声音为声乐跨界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个性声音的本质是融合、是跨界、是创新,是在原有唱法基础上产生的新质声乐艺术。
3 我国声乐艺术的跨界表现
3.1 音乐文学的双边走向
在我国传唱的外国歌曲,爱情题材所占比例较大,如《阿玛丽丽》《我亲爱的》《尼娜》《我的太阳》及《小夜曲》等。而我国较长一段时期的歌曲创作中,比较注重利用美歌宽厚、高亢音色,往往把歌颂祖国、赞美家乡等较为严肃的内容有意识地用西洋音调和唱法来表达。这种风格的歌曲如《黄河怨》《黄河颂》《我爱你中国》《跟你走》《中国的土地》等。新时期,美声唱法涉猎爱情题材歌曲有所增加,如《天边》《我的深情为你守候》《蓝色爱情海》等。美声类歌曲内容的爱情取向在艺术与观众之间架起了更为贴近生活的桥梁,对美声唱法的通俗化、大众化起到一定作用,细腻情感的表达也是对歌唱者长期讴歌主旋律的演艺模式的突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李谷一、朱明瑛、崔健为代表的歌手演唱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歌曲内容和品类较为丰富。而在港台地区歌曲影响不断深入之后,歌唱爱情基本充斥着通俗歌曲的歌词文学,通俗歌曲有着音域适中、曲调上口、内容贴近生活等易于流行的基因。但情感表述集中表现在男女情爱上,过于单一,缺乏对社会、祖国等更多维度的关注,久而久之形成畸形发展,即通常所说的“无病呻吟”。在批判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当代在通俗歌曲新的曙光,比如文风和古风的萌芽(不能说是兴起,还没有形成一个较有强势的创作群体或流派)。方文山的“旧瓶装新酒”,极大地提高了周杰伦作品的艺术品位。一些影视剧的通俗歌曲,在内容上基本能够反应剧情,表达真情实感。表达父母亲情、朋友真情的歌词文学也不断增多,这都让我们看到了通俗歌曲的新希望。
3.2 演唱方法的情感倾向
“诗咏志,歌咏情”,声乐艺术的核心功能就是情感的表现。以往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机械地运用歌唱技术演唱歌曲的现象,尤其是声乐教学中时至今日,也存在只重技术不重音乐的问题,通过青歌赛中一些青年歌手的表现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事实上,情感的表达应走在声乐技术训练之前,它既能激发歌唱的表现欲望,同时有利于歌唱发散性思维的开发及歌唱技术的解决。诸多的歌唱家在情感的表现方面是比较到位的,部分歌曲家对自己的代表作品也形成文字材料,谈了歌唱的体会。如孔令华著《让歌声更动人:中外声乐名曲练唱指导》[4]。以戴玉强、廖昌永、谭晶为代表的歌唱家,近年来对激情风格和柔情风格做了更为入木三分的情感阐释,主要体现在规范歌唱基础上对歌唱技术的突破,运用适度的白声哼唱、气息强烈撞击声门、局部共鸣的探索等以往非常规性的歌唱方法实现情感表述的艺术真实与夸张。
3.3 不同唱法之间的合作
以王宏伟为代表的歌唱家,实现了真声区与假声区的合理过渡,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高音唱法,挑战了男性高音演唱极限,提高了声乐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艺术家李玉刚塑造了一人双性、一人双角等演唱变体与艺术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人的好奇心。无论唱法如何区分,就嗓音机理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嗓音特质。美歌、民歌、流行歌、原生态歌曲的个性更为明显,将几种唱法的演员组合在一起演唱,无疑是一种艺术享受,犹如一个水果拼盘,同样的消费满足了几种口味。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推出的吴雁泽、戴玉强、阿宝合作的《草原上生气不落的太阳》之后,其他场合和节目效仿之风日盛。
3.4 不同艺术之间的融合
声乐除了自身发展外,也注重对京剧唱腔、黄梅戏唱腔、二人转唱腔等的吸收。比如李谷一演唱的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充分运用京腔,极具京剧韵味。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也是京味十足的一例。有些歌手就是京剧演员出身,他们的风格受到京剧唱腔的影响。比如屠洪刚对京剧板眼的关注,刘斌歌唱中鼻腔共鸣的追求,都隐藏着京剧的遗风。青年歌手王庆爽最近几年演唱的《千古绝唱》就是京剧唱腔与民族唱法结合的典范。还有一类就是前几年出现的《故乡是北京》等通俗唱法演唱,植入京剧念白、伴奏、歌唱北京歌词等元素的京歌,形成了一类题材。运用典型的舞蹈节奏,形成具有一定舞曲风格的歌曲是比较常见的艺术融合,《酒醉的探戈》《春天的芭蕾》《节日欢歌》等。龚琳娜的歌曲《忐忑》吸收了萨满神歌元素、流行音乐的时尚元素与声乐的快速、音区较高的技术解决能力结合,在新音乐风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声乐艺术的融合是艺术碰撞的火花,不同音乐材料的结合,是一个音乐转化与融合的过程,也是听众欣赏与检验的过程。当歌曲历经创作、演绎、得到认可之时,一种乐风即已成熟与扎根。
4 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趋势
声乐是最为古老的艺术,也是充满着青春朝气的时代艺术,声乐发展的历史预见着声乐的未来发展趋向。当前国家对于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思想、政策不断推进,教育领域对于艺术教育的关注等都为声乐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机制。唱法的分界虽然逐渐淡化,但在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各种唱法符合时代潮流、顺应欣赏群体审美需求是我国声乐发展的必然趋向。
4.1 美声唱法民族化
美声唱法源于意大利,是“belcando”的汉语通译,而它的确切翻译应为优美的歌唱或美歌。如果说“美声唱法”这一词汇在我国已经约定俗成,姑且在名称上倒不必过多口舌,但有必要重申美声的国际化问题及其民族化问题。美声唱法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欧洲、美洲、亚洲多个国家都有它的艺术身影,这是一种在世界上具有普遍影响的声乐艺术,所以是具有相对统一标准的国际化声音。美声唱法发展过程中,在意大利美声学派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德国声乐学派、法国声乐学派、俄罗斯声乐学派,这是美声唱法民族化的过程。美声唱法的民族化,不仅是歌唱语言的民族化、题材的民族化,还是音乐材料的民族化、音乐思维的民族化、审美情趣的民族化。我国近年来排演的一些新创歌剧没有脱离西洋歌剧的调性、和声、配器等音乐思维,歌唱的语言及宣叙调运用更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审美意向。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白毛女》《苍原》等以其较为突出的民族特性,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美声唱法是美妙的歌唱,帕瓦罗蒂、巴托莉等很多歌唱家能够运用美声演绎出极为细腻的情感。长期以来,在我国美声似乎成了思想严肃、审美庄重、技巧高超的代名词,不能以一种鲜活的、打动人心的演唱进行演绎。歌唱家廖昌永演绎的一些新作及对老歌的深情演绎,体现了美声唱法在中国民族化的一个典范。我们在借鉴美声唱法在歌唱技术系统性、科学性经验基础上,还要在唱法方面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而不是教导国人如何欣赏美声。“咽音”是意大利传统美声唱法中的重要演唱技巧,在我国声乐教学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借鉴与运用,把“咽音”理论民族化,应用到民族声乐教学中,必将对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促进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有十分积极的意义[7]。美声唱法民族化即是一个发展趋势,也是最后的归宿。
4.2 民族唱法个性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混居、杂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由于语言、习俗、气候、地理、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歌唱艺术上也形成了不同审美习惯、不同演唱方式方法。各种民族艺术充满特色,很难用一般的声乐审美标准来衡量他们的高下。蒙古族长调悠远辽阔,侗族大歌声音明亮协调,新疆民歌热情奔放,藏族民歌响彻云霄,云南情歌情感真挚等,整体看来民族声乐艺术个性化较为明显。在我国,音乐艺术院系培养出的歌唱人才可谓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各类声乐艺术都有其演唱方法,有其符合演唱机理的科学性。与其说美声唱法是科学的,不如说其具有较为完备的演唱体系、教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是指导集体创造的最佳方法,所以在产品上就容易出现成才快、数量多、品质高等特征。大量的歌手在美声唱法的指导下演唱民族歌曲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由于师承关系单一,出现“千人一声”缺乏个性的问题。艺术的美没有最高的标准,而特色是美的重要元素,这就是作品个性的魅力。艺术作品的同质化、模式化大大削弱了作品本身的竞争力。艺术的跨界发展使不同领域的作品相互映衬和相互诠释,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由表层进入纵深、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认可,由视觉、听觉的实践体验到联想的转变,进而做到了创作者、受众和市场的更好地融合[6]。民族唱法的发展在于更多地借鉴我国传统声乐艺术与民间声乐艺术,而不是以西方发声方法为圭臬,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发展的瓶颈。同时,加大民间唱法(原生态唱法)的传承与发展,在多元语境中得到更多展示的空间,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唱法格局,这样才会凸显民族声乐的个性,推进民族唱法的个性化发展进程。
4.3 通俗歌曲品味化
通俗歌曲由城市小调演变而来。就历史而言,通俗的即是大众的,是为某一区域多数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艺术形式。当代通俗歌曲过多渲染城市的男女爱情,尤其以爱的生死离别为甚,题材过于单一。针对流行歌曲尤其一些网络歌曲的庸俗化,中国音乐家协会曾做过讨论,批判了很多通俗歌曲“无痛呻吟”的问题。以流行歌曲为主的流行音乐从意识形态来看,其本质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它淡化了音乐的教育功能,而强调音乐娱乐功能[7]。在《中国好声音》比赛中推出了新唱风,《中国好歌曲》比赛推出了新曲风。这些新的变化给通俗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歌曲内涵的提升。如2013年《中国好歌曲》中的《卷珠帘》透露着古风古韵;2014年央视春晚的《时间去哪了》对人生充满着思考。这样有内涵的歌曲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可以设想,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以及优秀文化的传承,通俗歌曲也会趋于品味化。任何好听的、健康的、有艺术性的音乐都是高雅音乐,这也是他让古典音乐走近听众、走向市场的又一次积极尝试[8]。
综上所述,声乐跨界是纵贯古今横跨环宇的历史现象,是多地域广泛存在的艺术现象。“声乐跨界”在当代发展成一个新的语汇,有着时代性的文化印记,除了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音乐理念,一种创作方法,一种审美风格。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地域文化不断破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势必生成众多的新质文化。声乐跨界就是一种新质文化,它是突破传统,创造声乐新风格的结果。同时,更多人把跨界作为一种手段,塑造自己的声音特点、拓宽自己的演唱风格,客观上推动我国声乐向着更为丰富多样的趋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