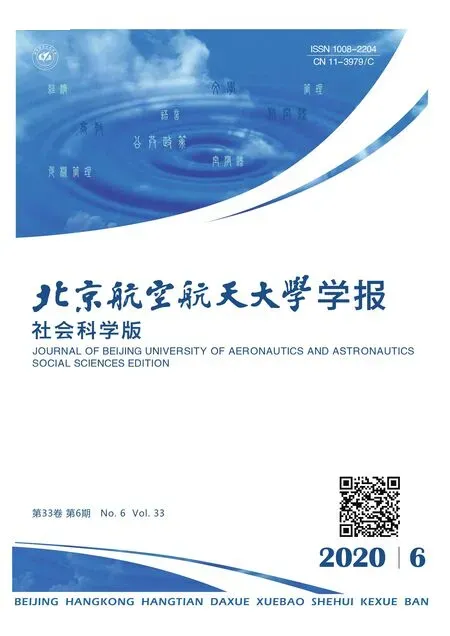朱熹序定《四书》过程探析
2020-12-12李丽珠
李丽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083)
朱熹通过诠释经典建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宏大理论体系,章句注疏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诸经之中,朱熹于《四书》用力尤深,《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耗时多年。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四书》,根据经典内容展开的不同,朱熹对其有不同定位,因而为学次序、为学方法皆有不同。朱熹一生勤奋著述,《四书》序定过程中不断修改自己的注疏,一步步清晰找到自己的立场,逐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把握朱熹序定《四书》的动态过程,有助于重现朱熹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全面性。
一、《论孟集注》成书
《四书》之中,朱熹于《论语》《孟子》二书耗费心神最多。朱熹曾曰:“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1]655朱熹少年时即随其父读《论语》,至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成书,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三岁时《孟子要略》成,其用心于《论语》《孟子》何止四十余年。之所以如此,朱熹曾曰:“《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有余家。”[2]51《论语》《孟子》二书乃学者求道之关键,所以古今为二书作说者不下百余家,众说纷纭,朱熹年轻时曾出入诸家,迷惑于此,这可以说是朱熹理会《论语》《孟子》耗时多年的原因之一。
根据王懋竑《朱熹年谱》看朱熹对《论语》《孟子》的注解过程,其三十四岁时,作《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据《年谱》载:“熹年十三四时,受二程先生《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诵习既久,益以迷眩。晚亲有道,窃有所闻,乃慨然发愤,尽删余说,独取二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補辑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2]24朱熹少年时从其父朱松学二程先生《论语》,惜其学未成时其父已逝。之后朱熹遍求诸儒《论语》之说,众说纷纭,无有头绪。至朱熹从学李侗,乃慨然发愤,独取二程先生及门人朋友之说解《论语》,编成《论语要义》一书。后又通训诂,正音读,删录以编成《论语训蒙口义》作为童子启蒙之书。四十三岁时作《论孟精义》(又名《要义》《集义》),仍是推崇二程先生之说:“宋兴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间尝搜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名曰《论孟精义》。”[2]51二程先生传承孔孟之道,朱熹取二先生之言以及有同于二先生之诸儒者之言,成《论孟精义》。至朱熹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或问》成。“先生既编次《论孟集义》,又作《训蒙口义》。既而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2]76《论孟集注》是在《论语要义》《论孟精义》的基础上约其精粹而得,《论孟精义》既然是取二程先生及学有同于二先生者之言而成,在此书基础上取其精粹而成之《论孟集注》也应是主要取二程之说。根据钱穆先生的统计,《论语集注》虽将二程与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董仲舒、韩愈同尊称为“子”,但据统计,“其义理方面,论其征引条说之多寡,二程及程门,仍占三分二以上”[3]。
通过对朱熹注解《论语》《孟子》过程的梳理,可见其《论语》《孟子》解主要取二程之说。《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通过《论语》阐述了何为仁以及如何行仁。在伊川的《论语解》中,他以“理”说“仁”。在解“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句时,伊川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4]1136“仁”为天下之正理,失此正理则天下失序,礼乐不兴。“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概念,明道曾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424理是万物之根源根据,“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4]33。理是最高本体,无有亏欠,独立自存,“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4]31。二程以“理”解《论语》的核心概念“仁”,朱熹的《论孟集注》既然主要取二程之说,其是否也如二程一般以一理贯穿注解始终呢?以下详细分析。
《论孟集注》中,朱熹以理为最高本体,万物之根据,理为天理,以理解道。解《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时曰:“不惑,则知事物当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当然之理,必有所从来。知天命,是知其所从来也。”[1]816“四十而不惑”,所谓“不惑”是知道事物当然之理则,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等具体的人伦道理。知道这些道理,还应知道这些道理之来处,这就是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5]75,天道流行赋予万物,万物得之以为正理,天道就是事事物物当然之理则的来源,是万物之根据,最高本体。关于这个“天道”,朱熹曰:“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①[5]103朱熹以理解道,最高的根源、根据——天道——即天理之本体。朱熹以天理为最高本体,天道流行赋予万物,朱熹亦以理来解人之心、性。朱熹极称赞伊川“性即理”一句,认为:“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6]1889伊川以“理”解“性”被朱熹所继承,“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6]103。天理流行落实到人身上为人之性,所以,可以说人性与天道其实是一理。在朱熹看来,性即是理,而心则包万理,而对于完满禀受天理的圣人来说,圣人之心则纯是浑然一理。“圣人之心浑然一理。盖他心里尽包这万理,所以散出于万物万事,无不各当其理”[7]974,圣人之心中无人欲之杂,浑然纯是一个天理,所以其遇事而动时也无不当理。《孟子集注·公孙丑章句上》中称赞的仁者亦是此种形象:“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5]291仁者本心全具天理。与圣人、仁者不同,普通人心中难免私欲夹杂,需要日用常行间作工夫,去私欲,存天理。修身之工夫亦是一理贯穿其中。“‘洒扫应对’是小学事,‘精义入神’是大学事”[7]1668,“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7]1666。人之修身工夫皆有所以然之理,所以小学工夫、大学工夫皆是一理贯之。若是人能通过修养工夫克去私欲,则可以见得日用常行之间,无非是天理流行之妙用。
朱熹曾问弟子陈淳《论语》应如何看,陈淳答曰:“见得圣人言行,极天理之实而无一毫之妄。学者之用工,尤当极其实而不容有一毫之妄。”[1]652朱熹以为陈淳此语得《论语》之大纲。《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教人切实作工夫处,圣人之言行无不当理而无妄,学者以圣人为榜样,其一言一行也应合于天理。事实上,通过对朱熹《论孟集注》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不光以天理规范学者日用常行,从万事万物之本原、根据到人之心性,再到人之修养工夫,这些在朱熹看来无不是一个天理贯穿其中。
二、《学庸章句》成书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正式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二书定著已久,犹时加篡改不辍。至是以稳洽于心而始序之”[2]198。二书成书已久,朱熹不断加以修改,至1189年正式序定二书。先说《中庸章句》,“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5]31。朱熹年轻时即读《中庸》,多年反复思索。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草成《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成,寄张栻、吕祖谦讨论”[8]。至1189年正式序定此书之前,朱熹不断与张栻、吕祖谦等讨论二书的内容。
朱熹注解《中庸》推崇的是二程对《中庸》的理解。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曾曰:“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5]30子思推本尧舜之意,作《中庸》,以昭后学,后孟子得之,以承先圣之统。之后异端四起,佛老大盛,幸有二程兄弟传《中庸》,续道统。朱熹在与吕祖谦、张栻讨论《中庸》文本的时候,多以二程思想为依归,以下略举两例。朱熹曾在写予吕祖谦的信中提到张九成《中庸说》的不妥之处:“往年见汪丈举张子韶语明道‘至诚无内外’之句,以为‘至诚’二字有病,不若只下个‘中’字。大抵近世一种似是而非之说,皆是此个意见,惟恐说得不鹘突。真是谩人自谩、误人自误。”[9]1426针对张九成对明道“至诚”之说的质疑,朱熹斥其为似是而非,维护明道之说。与张栻讨论《中庸章句》时亦曾曰:“‘执其两端’,熹说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过巧之病。如来谕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过巧。”[9]1346朱熹与张栻二人对《中庸》的理解是以程子之《中庸》说为依归,以是否符合程子之意为基准。以下具体分析朱熹对《中庸》的理解。
朱熹在《中庸章句》之始引明道之言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5]32所以可以说在程明道看来,《中庸》从始至终是言一个理。二程《中庸解》不传于世,《二程集》中所收《中庸解》据朱熹考证为吕大临所作。朱熹对二程门人之说颇有不满:“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5]30朱熹作《中庸章句》,接续二程道统,但对二程门人佛老好高之弊颇为不满,朱熹强调《中庸》为实学,他从明道那里接续“一理”,同时强调“一理”之分殊。曾有人问明道“始言一理”之说,朱熹答曰:“如何说晓得一理了,万事都在里面?天下万事万物都要你逐一理会过,方得……所谓‘中散为万事’,便是《中庸》中所说许多事,如智仁勇,许多为学底道理,与‘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与祭祀鬼神许多事。圣人经书所以好看,中间无些子罅隙,句句是实理,无些子空缺处。”[6]2015-2016晓得“一理”,更要晓得此“一理”散入万事中,《中庸》中为学道理、治国方略、祭祀之事,皆是“一理”贯穿。
《中庸》首句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熹解释这两句,“‘天命之谓性’,是专言理,虽气亦包在其中,然说理意较多”“率性者,只是说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许多道理。性是个浑沦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条理。循性之所有,其许多分派条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6]2018。天理流行赋予万物,人物禀受谓之性,性即理。此理一同,但物物皆有气禀差异,天命浑沦之性通于人物,则牛有牛之性,马有马之性,只要循其本然之性,则自有道理。天理流行发动通于人物为性,未通人物之前则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庸》以“中”为“天下之大本”。朱熹以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5]33,此句中的“理”“道”指天理散于人物之后为万理,“天命之性”则为天理,万事万物之理皆自天理而出。虽未发前为天理,已发散为万理,但朱熹强调已发、未发不可截然二分。“‘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只是思虑未萌,无纤毫私欲,自然无所偏倚。所谓‘寂然不动’,此之谓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块然之谓。”[6]2039“未发之前,万理备具。才涉思,即是已发动;而应事接物,虽万变不同,能省察得皆合于理处。盖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6]2038未发时是无私欲之天理,发动应接事物仍应合于理,已发、未发不可截然二分,皆一理贯之。
《中庸》的核心概念是“诚”,将诚深化为一个极具天人之学内涵的哲学范畴,朱熹以“理”解《中庸》之“诚”。“‘诚者,天之道。’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实其实理,则是勉而为之者也。”[6]2107诚是天理,真实无妄,诚之者则是说人通过修养工夫欲为真实无妄,实有其理于身。《中庸》中的修养工夫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朱熹认为此工夫主要为“存天理之本然”[6]2031。人物之性得自天理,可以说无这理便无人物。朱熹解“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曰:“有是理,则有是物;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彻头彻尾,皆是此理所为。未有无此理而有此物也。无是理,则虽有是物,若无是物矣。”[6]2126有实理,则有天下之物,若无实理,虽有物,但无实理之物便似无物,这便如相对二人说话不说实话犹如未说一般。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庸》中一个实理包括,从大本达道到修养工夫皆是实理贯穿。天理之大本无纤毫私欲,赋予人物为性,无这实理,便无万物,人因气禀私欲阻隔,作一系列修养工夫目的是为了复天理之本然。
朱熹于乾道八年(1172年)草成《大学章句》,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式序定《大学章句》,这之间朱熹不断与师友如张栻、吕祖谦讨论并修改,正式序定后仍不断修改,至朱熹去世前几日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朱熹表彰二程编次《大学》之功:“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5]14二程表彰《大学》,又编次此书,使圣贤之旨复昌明于世。朱熹学二程之《大学》,后又“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5]14,取二程之言,加入自己意思,补格物致知之传,成《大学章句》。
关于《大学》一书,朱熹曰:“《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1]420《大学》是说明古人为学纲目,从修身到治人的次第,所以朱熹以为《四书》之中应先读《大学》,懂得为学先后次第,之后再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所讲的这个为学纲目即“三纲八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此为“三纲”。“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此为“八目”[5]16-17。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明明德之事,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亲民之事。朱熹以为:“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5]16明明德、新民皆应止于至善之处,若能到此地步,则是人欲尽去全是天理。所谓“止于至善”之“至”者,即“天理人心之极致”[1]447。朱熹以为,古人为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便是人欲尽去天理流行的境界,想要到达这一境界需要通过《大学》之“八目”一步步实现。人们需要从格物、致知一步步做起,是因为“人本有此理,但为气禀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来,七颠八倒”[1]456。人人本有天理于身,但为气禀物欲遮蔽而不显,所以需要“八目”之工夫一步步重新使得天理彰显出来,天理贯穿作工夫的始终。
朱熹据程子之意,为“八目”之中格物、致知一章增补其传,朱熹增补其传的行为多有争议,但从增补的内容正可看出朱熹对一贯之理的强调。“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5]20格物就是即天下之物而穷其理,用功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天下事物之理无有不知,则可谓致知。朱熹增补的内容是据程子之意而来,《二程遗书》中曾收录一段程氏与其他人的答问如下:“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生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4]188可见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即是推本程子之意而来。格物是欲穷此理,致知是知此理,八目中其他工夫亦是围绕此理展开。“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1]496穷理、知理以至于将此理推广于天下国家。
朱熹于《四书》多所用心,以其为学者求道之关键。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朱熹对《四书》的理解受二程影响甚深,二程之学的核心概念“天理”被朱熹吸收运用到对《四书》的注解中。《四书》中涉及的多是人事之修齐治平等日用常行之事,天理、道体表现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随事发见的。朱熹以“理”解《论语》的核心概念“仁”,以“实理”解《中庸》的核心概念“诚”,以“穷理”解《大学》的“格物”,在《四书》的注解中始终强调一理贯之。
三、由《四书》及六经的为学次序
“四子,六经之阶梯”②[10]3450。《四书》中阐明人事修齐治平之道理准则,人人可得而学之。六经之《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是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学之不易。因此,朱熹认为,学者为学应先读《四书》,之后及于六经。“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6]2226。《四书》是熟饭,功夫少,得效多;六经则是需人去打禾为饭,功夫多,得效少。所以朱熹教人先看《四书》,后及六经。六经之中,朱熹专门为之注解者有《诗经》《仪礼》及《周易》。《周易》因其深厚的天人之学内涵,一直受到学者关注。实际上,儒学发展到两宋,其核心经典已由《五经》转向了《四书》,但《周易》的重要性仍在,所以杨儒宾曾言宋明理学的核心经典是“新《五经》”,即《四书》加《周易》[11]。伊川曾作《程氏易传》,朱熹对伊川之注解不甚满意,故而自己作《周易本义》。以下就以朱熹对《周易》的注解为例,分析朱熹对《四书》与六经的不同态度,这直接决定了《四书》先于六经的为学次序。
朱熹以为看《周易》应经、传相分,作三等看。“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6]2190-2191伏羲观物取象画卦,只是要教人卜得吉则行事,凶则止。文王、周公推演六十四卦,作卦辞、爻辞系于卦后,教人占得此卦则据此卦爻辞判断吉凶,文王易虽仍是做卜筮用,但已与伏羲易不同。孔子作《易传》,是就事上说理,侧重于从卜筮中发明出许多道理来。“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6]2191朱熹认为,伏羲为教民卜筮而作之易最为自然,是《易》之本义,《易》为卜筮之书。文王易不如伏羲易,孔子易则不如文王易。
朱熹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所以有不同于其他经典的言说方式——稽实待虚。朱熹曾在《周易本义》中讲到“读《易》之法”时提到:“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10]167曾有门人以此句问朱熹,朱子解之曰:“圣人作《易》,只是说一个理,都未曾有许多事,却待他什么事来揍。所谓‘事来尚虚’,盖谓事之方来,尚虚而未有;若论其理,则先自定,固已实矣。‘用应始有’,谓理之用实,故有。‘体该本无’,谓理之体该万事万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见,故无。下面云,稽考实理,以待事物之来;存此理之体,以应无穷之用。”[6]2224《易》中之理是实理,但采取虚说方式,不局限在具体事上。这个理包含万事万物,但又无形迹可见。“若《易》,只则是个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预先说是理,故包得尽许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正因为《易》虚说一个实理,不局限在具体事务上,所以人们用《易》卜筮才能随占而应,不管占问何事都能得到答案。
以上,朱熹认为《易经》本为卜筮之书。上古之时,民风淳朴,民智未开,伏羲观物取象以画卦,文王周公作卦辞、爻辞系于卦后,教人占得此卦则据此卦爻辞判断吉凶。“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6]2212与《四书》直接阐述价值准则、为学纲领不同,《易经》虚说一个理,以期卜筮之时随占而应。这也就决定了《易经》并非易读之书,先用力于《四书》,掌握圣贤传授的道理准则,学有余力后及于六经。这是朱熹基于经典内容的不同,推荐学者为学的不同次序。
朱熹通过诠释圣贤经典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对《四书》用力尤深,《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耗时多年。朱熹自述,其于《论语》《孟子》,“四十余年理会”;对于《大学》,至去世前几日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朱熹对《四书》的理解受二程影响甚深,二程之学的核心概念“天理”被朱熹吸收运用到对《四书》的注解中。《四书》中直接阐明了人事修齐治平之道理准则,人人可得而学之。六经则是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学之不易。所以朱熹以为,学者为学,应先读《四书》,之后及于六经。
注释:
① 《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中亦曾有类似之言:“道者,天理之自然。”
② 关于“四子”是指《四书》,还是指周、张、二程四子,历来有所争议。笔者以为“四子”指《四书》。因为朱熹在《语类》中讲到读书顺序时曾多次提到,应先读《四书》,后读六经。“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参见:《读易之法》,《朱子语类》卷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