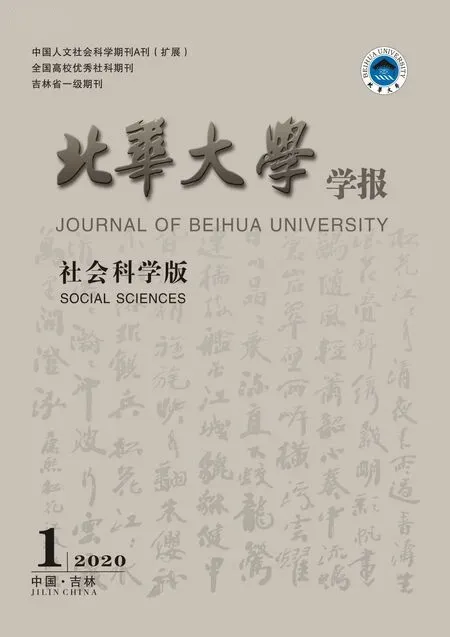东北抗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
——以罗登贤对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为例
2020-12-12王颖
王 颖
1934年6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刊物《红色中华》发表了《纪念罗登贤同志》一文。文章指出:“罗登贤同志献身革命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光荣的模范。”[1]罗登贤是中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和东北抗日武装的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初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代表党中央,进驻东三省。在抗日烽火的斗争岁月里,他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组织和领导东北民众在血雨腥风、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组建了抗日联合战线,创建了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为东北抗日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登贤在为东北人民求生存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崇高道德风范令人震撼,给人启迪,他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今天缅怀罗登贤对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既是弘扬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的纪念之意。
一、勇赴国难,坚定东北抗日的决心意志
伴随日寇的入侵,“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党组织内外交困,革命形势异常严峻。为了加强东北党组织的革命力量,1931年春,罗登贤被中央派到沈阳协助“满洲”省委开展工作。来到沈阳后,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马上着手指导省委在东北各大城市广泛发动工人运动,组织领导东北地下党的斗争。
1931年9月19日,罗登贤与省委书记张应龙一起主持召开了“满洲”省委紧急会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共同讨论确定了省委以后的斗争策略并制定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其中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的政策。”[2]这就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计划以较为通俗的方式呈现给普通东北民众,既为他们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东北面临的严峻国情,为后来省委提出联合起来、一致抵抗外来侵略的主张奠定了理论宣传基础,也为中央及时了解掌握东北战事,确定反日战略决策提供了主要依据。《宣言》还发出东北工农兵劳苦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3]2“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3]3等号召。该宣言既从东北党组织的角度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野心,又号召东北各界民众以不同方式紧急行动起来,联合反抗已经到来的侵略战争。实践证明,该《宣言》的主旨精神与随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精神完全吻合,这无不反映出罗登贤与“满洲”省委班子能够站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做出了符合国情的东北抗日决策和部署。罗登贤本人极富政治敏感性,精明强干且能主动思考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尚未接到中央具体指示时,罗登贤就在哈尔滨召集了“北满”特委高级干部会议,与参会同志一起分析政治局势的新变化,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展开斗争等策略问题。他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敌人在那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那里和广大人民一起,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4]94他郑重声明:“不驱除日寇,我们决不罢休;不驱除日寇,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人如果要提出这样的要求,谁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4]94他铿锵有力的话语震撼着在座的每一位共产党人,既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誓与东北人民共同抗战的紧迫性,也再一次坚定了东北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坚定决心。
1931年10月,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对东北反日斗争领导的指示精神,也出于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村存在权力真空的客观形势考虑,身为“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确定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派遣大批的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5]的方针,明确要求东北各地党组织要创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并派出干部加强对基层工作的具体指导。鉴于当时“东满”地区异常尖锐的斗争形势,加之当地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名得力干将去领导掌舵等实际情况,11月,罗登贤将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派到了“东满”任特委书记。临行前,他意味深长地对童长荣交待道,“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6],而不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此后,“满洲”省委的部分干部在罗登贤的组织安排下陆续被派往地方基层战斗一线。例如,杨君武、杨林被罗登贤相继派到“南满”磐石建立抗日武装,下派同志到基层一线后,立即着手在先前底子上筹建新的工农武装,将红色游击队扩充到800多人。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的前身;1932年春,省委委员周保中被罗登贤派往宁安,强化吉东地区的反日武装斗争和党对地方的领导。这些同志在上任前,罗登贤都要与他们一一谈话,交流思想,提醒他们认清抗日形势,灵活运用工作方法,鼓励他们在具体工作执行中完成东北抗战使命。任前谈话不但充分说明了罗登贤对派出同志的高度重视和满心期待,也体现出他在东北抗战期间所遵循的基本工作准则。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出于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出于中国共产党人固有的党性意识,罗登贤同志毅然决然地来到东北,在与东北民众一起抵御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对东北社会形势做出了客观、准确的判断,既坚定了东北民众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也显示出其爱国主义精神的战斗锋芒和深厚伟力,对推动“九·一八”初期抗战做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
二、临危受命,整顿东北各地党组织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激起了“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怒潮,省委坚决抗日的严正立场以及对东北民众的组织动员,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促使他们对“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沈阳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管控。为确保东北党组织的安全和各项抗日工作的顺利推进,1931年10月27日,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向中央请示,建议迁移“满洲”省委机关,即从革命形势严峻恶劣的沈阳迁往日军军事力量尚未能及、汉奸势力未公开附敌、敌人统治比较薄弱、革命形势相对缓和有利的哈尔滨。但由于当时沈阳政治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在“满洲”省委尚未接到中央回信指示时,11月下旬,“满洲”省委的廖如愿(时任军委书记)和杨先泽(时任宣传部秘书)被日本宪兵抓捕,随后张应龙(时任省委书记)和赵毅敏(时任宣传部长)也陆续被抓捕,“满洲”省委遭遇重创。为了迅速带领东北人民投入反日斗争,罗登贤勇往直前,积极担负起省委使命,代理书记职务并恢复中共‘北满’特委。直至12月,中央任命正在协助“满洲”省委开展工作的中央驻东北特派员罗登贤为书记,委派他组建新一届的“满洲”省委。此后,罗登贤肩负起了领导东北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重任。
在罗登贤的领导下,“满洲”省委的党团员都信心百倍地投身火热的反日斗争中,完成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首先,主持完成“满洲”省委的组建和机关迁移工作,明晰了省委的工作重点。鉴于“满洲”省委先前向中央发出的请示,经中央同意,1931年底在罗登贤主持下,“满洲”省委安全完成了办公地点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的工作。与此同时,组建完成了罗登贤届省委班子,除他本人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外,詹大权同志担当秘书长,何成湘同志担当宣传部长,杨林同志担任军委书记。罗登贤被派到东北时正值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期间。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后,“左”倾冒险主义依旧要求各地党组织继续进行土地革命,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立苏维埃政权。该路线虽然对“满洲”省委也有明显影响,但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从实际出发,在作出的《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的决议》中再次明确了省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不是继续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虽然这一正确主张是完全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但却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在1932年6月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不仅东北党组织因此受到攻击和批判,被扣上“北方落后论”和 “满洲特殊论”的帽子,而且罗登贤本人也被撤了省委书记职务。其次,恢复和建构东北党组织,捋顺组织职能。截至1931年12月,整个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员2 132人,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异常困难。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实现党对反日斗争的领导,罗登贤指示“满洲”省委班子成员立即着手恢复、调整党组织架构,除设两个特委(“东满”、奉天),一个市委(哈尔滨)外,还指导伊通县委、汤原中心县委等近十个基层党组织的反日斗争,进而加强了党的建设,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日游击战的重点区域。再次,团结动员民众,深入基层开展反日爱国宣传。1932年2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为了扩大反日宣传的地域范围,在罗登贤的直接领导下,省委其他同志也积极投身于东北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奔走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和农村,针对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对东北民众讲述着反日反帝的必要性,使民众切实感受到抗日迫在眉睫,并动员学生、工人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反日爱国运动。哈尔滨电业、沈阳兵工等企业工人诚恳地将农民动员起来,共同协作组成了当地抗日武装;在辽沈中间的小堡,中国共产党员在由抗日救国的劳苦大众组成的党的外围组织——农民大同盟内部以三五人的小会形式,互相串联,利用庙会、集市等地人多热闹的机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同时在农民中教唱革命歌曲等,以上宣传对唤起广大农民群众觉醒,动员他们参加反日斗争起到积极作用。在“东满”的延吉和清原,吉东的宁安,“北满”的阿城和珠河,“南满”的磐石和海龙等地,都陆续展开了工农反日武装斗争。此外,党组织还在许多工厂中秘密发行小报、传单,鼓舞工人群众反日斗争情绪。通过以上党组织的发动,民众被广泛调动起来,一时间东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奉命于外侵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从以上罗登贤组织领导东北民众抗战的历史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家时局危亡的关键时刻,罗登贤临危受命,只身奔赴东北,这种在危难之际依旧与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无私奉献精神指引着他不仅及时完成了“满洲”省委机关的迁移及组建工作,而且促使他上任后立即着手恢复和整顿东北各地党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党组织任务,及时将省委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进而全面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武装反日,罗登贤的这个重要战略性举措为后来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三、志存高远,探索建立民众的反日联合
“九·一八”事变后,“左”倾冒险主义未能及时认识到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大资产阶级已经逐渐转变立场,发展为抗日群体一部分的现实,依旧否认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教条思想肆虐到仍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的程度,主张以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所谓妥协的反革命派,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这些主张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有具体体现,明确了全党目前的工作使命是“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7]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罗登贤届“满洲”省委于1月15日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第三次宣言》,其中提出了诸如没收日本的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及一切企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没收一切英法美在华投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等11条行动原则,这些脱离东北实际的原则,显然很难在具体工作中贯彻执行下去。1月17日,“满洲”省委在号召扩大全东北工农兵统一战线的同时,再次强调推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由此可见,从领导层级上讲罗登贤领导下的“满洲”省委在指导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整体工作部署不可能不受到中央的制约。
罗登贤身处东北抗日斗争工作的第一线,他头脑冷静,能在具体工作中客观分析社会形势,对上级指示做了因地制宜的部分调整,进而推进了“满洲”抗日斗争的步伐。首先,高度重视抗日义勇军,尝试实现对他们的领导。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关于驱逐日本侵略者、坚决抗日的主张,获得了东北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支持和拥护,救国军、反日总队、自卫军等各种抗日武装应运而生。罗登贤和“满洲”省委高度重视这些抗日武装,经过分析研判,他指出义勇军“完全缺乏党的正确领导”,“义勇军目前显然的有两个前途:一则是在胡子头、军官、豪绅地主的领导下走到一时的挫折失败;一则是党能够打入义勇军中去树立党的领导,开始游击战争”,于是提出“应该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加强政治军事的领导”[8]347,为组建东北反日联合组织奠定基础。罗登贤还亲自指导省委同志以不同方式强化与义勇军的沟通联系,或选派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的骨干力量,或派遣党团员到义勇军中开展活动,或动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加入义勇军,或动员社会人士开展支持义勇军的募捐活动。在他任职书记期间,近百名的党团员和进步团体骨干被指派到军中工作。此外,罗登贤还经常到基层巡视,督查基层工作指导情况。其次,将东北的朝鲜民众持续归入反日联合战线。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1931年9月20日)中,“满洲”省委明确指出了全满的朝鲜劳苦群众,从朝鲜到“满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非人的压迫和掠夺,……由此动员朝鲜民众,今后在党的组织和带领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的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手起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9],打倒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在此基础上,罗登贤还协助“满洲”省委组织成立了中韩反日会、反帝同盟会等组织,吸纳更多的朝鲜民众加入其中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据周保中回忆,“1932年的坚强的‘东满’游击队和1933年强大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朝鲜同志和革命的朝鲜群众创造起来的,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10]再次,争取伪军反正,充实反日力量。1932年1月30日,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就发出了《告士兵群众书》,号召士兵“自动进攻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新工具独立政府一切武装”[8]104;在伪满洲国建国后的一个月,又公布了《告日本帝国主义新工具“独立政府”下的士兵书》,劝告士兵“倒转你们的枪回头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独立政府’瞄准,同武装民众联合一起扩大反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政府’。”[8]104随后,罗登贤委派干部在伪军部队中建立各类党团组织,并推动组建了伪军反日会,以此策动伪军变节反正。磐石中心县委在驻伊通营城子伪军第五旅第二营第七连中发展了5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了哗变;珠海县委在驻苇河的伪军中建立党支部,共产党员李启东、金策策动了120名伪军哗变。由于各地党员的努力和民众抗日斗争的影响,小到3—5人,大到成排成连甚至整团的伪军反正事件连连发生。但由于中央“左”倾关门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哗变队伍未能被发展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心系国家强。从1931年春来到东北,罗登贤出于对国家革命事业的强烈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东北战况的现实出发,尽自己最大努力,科学制定战略策略,始终将反日列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日力量,大胆尝试与党外人士合作,创新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组织对义勇军、农民、工人、“满洲”境内的朝鲜人、日本士兵等群体的联合,这就为后来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和实现积累了经验。即使在1932年7月到12月间,罗登贤也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意志消沉,而是竭力争取留在东北,为抗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罗登贤满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孤悬敌后、浴血苦战,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四、因势制宜,创建东北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是“满洲”要“组织‘北满’军队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1]据此,《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1年9月19日)、《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1931年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紧急决议》(1931年9月23日)四个宣言决议陆续出台,其主旨均为号召、动员东北民众武装起来,发动游击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这就表明在中央的指示下,罗登贤协助指导的“满洲”省委已经开始谋划建立民众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了。10月12日,临时中央再次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民游击队。11月中旬,罗登贤和“满洲”省委领导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中央有关组织游击战的工作指示,并做出了诸如培训游击骨干、派出巡视员、创办刊物等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加强党组织领导等各项决定。11月底,因“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除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被派到“东满”参加反日救亡外,省委无法开展其他工作,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也因此搁置。直到12月,以罗登贤为书记的省委组成后再次把创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列为省委的中心任务重新布置落实。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罗登贤协助指导的“满洲”省委着手创建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一方面源于要落实中央关于具体抗日行动的工作指示,另一方面则是由东北地区的实际战况所必需。在抵御日寇的过程中,虽然各地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迟滞了东北沦陷的脚步,但随着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人数的增加,其组织弊端也不断显现,如成分极其庞杂,组织混乱等。有的队伍还在国民党直接控制和影响之下,因此各地抗日义勇军不久就出现了分化和瓦解现象。该情况的出现也促使新组建的罗登贤届“满洲”省委意识到,只有迅速创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才能顺利开展东北反日游击战。进入到1932年,罗登贤届省委班子集体学习了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期间撰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一文,经过分析讨论,为切实落实文中强调的要广泛动员以工农为主的受欺压劳苦大众精神,省委拟定出台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其中指出要实现反日斗争的完全胜利,就必须武装民众,实现党对人民武装的领导。[4]96该文件为“满洲”省委力图创建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继续开展创建游击队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满洲”省委又发出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指导东北各地党组织创建抗日游击队工作。2月20日,省委指示“东满”党组织,明确了“东满”特委其时的重点职责为“坚决地去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发动与领导游击战争。”[12]3月31日,罗登贤届“满洲”省委再度提醒东北基层党组织,“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义勇军组织”[13],将号召东北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广泛团结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列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这点可从“满洲”省委向党中央提交的《满洲目前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斗争与党在群众中的工作》(1932年4月22日)汇报内容中获知,“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切近、最实际的战斗任务。”[14]在“满洲”省委和罗登贤的领导和号召下,东北各地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党组织创建抗日游击队的工作,从1932年初开始,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基层社会,积极开展了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武装和发动游击战的工作。例如,赵尚志被派到巴彦,冯仲云被派到汤原等,这些干部与当地农村党组织紧密配合,在反日斗争中逐渐强大武装自己。两年后,在东北大地上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磐石反日游击队、和龙反日游击队等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播下了东北抗日武装的星星之火,为后来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日寇烽火照东北,唯有应变不囿物。上述内容表明,虽然罗登贤届“满洲”省委不能摆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但罗登贤努力把开展和领导反日民族战争作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组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后来东北反日联合战线的确立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武装基础。
总之,回望历史,通过罗登贤勇赴国难,坚定东北抗日的决心意志;临危受命,整顿东北各地党组织;高瞻远瞩,探索建立民众的反日联合;因势制宜,创建东北抗日武装等,率领东北民众反击日寇,保家卫国的经历看,罗登贤主持“满洲”省委工作后,首先实现了省委工作中心从城市走向乡村,建立了基层武装力量。其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完成了斗争指向由国民党为主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正是具备了胸怀信仰、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才引领了罗登贤的东北求索之路,激发了他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努力寻求反日救国之路的信心,在反日实践的征程中发出了不做畏难者,争做搏击者的抗日救国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