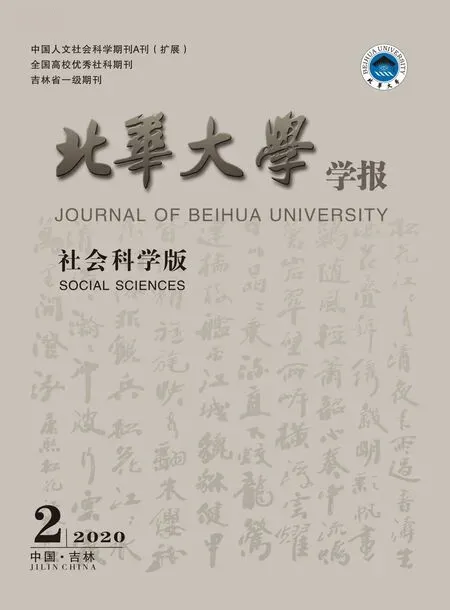战败前日本的“种族主义”及其特征
——与纳粹德国相比较
2020-12-12许赛锋
许赛锋
引 言
通常认为,20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外大规模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和德国,都曾主张“暴力扩张”“国家至上”“自身种族优秀”等理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表现出了诸多的相似之处。[1]然而,就如尽管日德都被称为“法西斯国家”,但两者的“法西斯性”却大不相同那样,(1)如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则会发现当时日本相较于德国,缺少“拥有绝对权利的政治领袖”这一关键因素(参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 国际中文版》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对于战败前的日本是否可以定义为“法西斯国家”,日本等国的一些学者也存在不同意见(参见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东京:未來社,1964年),但本文仍依据中国学界主流,认为战败前的日本具有法西斯性质。相较于德国,日本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行为不仅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在一些方面甚至还与德国产生了分歧和背离。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与开展较多的德国种族主义研究相比,专门研究日本种族主义的论著却非常匮乏。(2)先行研究中,马俊毅的《论二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分析了二战中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实质,指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安善花的《近代日本侵略中朝思想中的民族优越论分析》(《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1期)认为,以近代化成功为依托,日本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及种族优越感,逐渐演变为“挽救”东亚的救世心态和充当亚洲领袖的霸主意识,从而构造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最直接的思想基础;日本学者石田勇治的《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对目前关于二战日德种族屠杀罪行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述。通过对比二战前日德两国种族主义的共性与差异,进一步考察日本种族主义的相关具体实态,力求能从心理动因层面,为剖析近代日本侵略扩张的思想本质提供更多参考。
一、日德种族主义的共性
(一)鼓吹自我人种属性优秀
如众所知,“种族主义”是指对“遗传体质特征与个性、智力或文化的高低优劣有必然因果关系”深信不疑的一种思想。[2]在近代日德两国的侵略扩张思想理论中,过度迷信和赞美本民族的起源与血统,鼓吹自身在生物属性上的“至高优越”,是两者最为突出的一个共同特征。(3)需要说明的是,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早期对“种族、人种”(race)和“民族”(nation)的内涵区分并不明晰,几词常出现夹杂或交替使用的情况。同样,在东亚等地,像日本近代人类学创始人坪井正五郎就称:“将人种简称为人群之集合并无大碍,……世间常用之日本人种、大和人种、天降人种等人种之语,于人种学上并非有一定之意义,但在方便上亦可保留。”(参见坪井正五郎《通俗講話人類学大意(続)》,明治26年7月第88号;日本人類学会《東京人類学会雑誌》第八卷,东京:第一書房,1981年,第427页)因此,本文对于引用资料中的“人种”“种族”“民族”等表述,也更注重其在政治语境中的“人群划分”含义。
德国方面,法国人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以及英国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19世纪的基石》等宣扬人种贵贱有别的论著,对德国近代种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3]像张伯伦就认为,“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4]纳粹头子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后,进一步将“雅利安人优秀论”渲染发挥,宣称有着高贵血统的德国人,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他在其声名远扬的“大作”《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出,“人类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基本人种因素”,“各种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劣者和弱者应按照支配宇宙上的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服从优者和强者”。“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类文化、艺术、科学和技术成果,几乎全都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正是这一事实使人们得出这个并非没有根据的推论:只有雅利安人才是更高尚的人性的缔造者,因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这个字的原型……如果将人类分成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占有者、文化的破坏者三种人,那就只有雅利安人才有可能是第一种人的代表,人类一切创造的根基和围墙都来自雅利安人。”[5]
近代日本的种族主义思想,虽然不像德国那样有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同样具有“本国或本民族至上主义”“由天然的优越者进行统治”等明显的等级差别意识。[6]81特别是在长期存在的“神国观念”影响下,日本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更是坚信,“与神灵紧密相连”的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生优越者”。被称为日本近代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就曾宣称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优秀种族。[7]而伴随着日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连续的对外胜利,这种宣扬日本是“神国”,日本人是“神族后裔”的理论,逐渐成为其对外侵略与狂妄自大意识膨胀的重要思想根源。[8]
相应地,在近代日本许多侵略主义分子或团体的言论中,都可以找到“日本种族优秀论”的痕迹。如日本法西斯思想代表人物大川周明就声称,“吾等深信日本帝国被上天委以新世界领导者之大命”,“吾等之任务在于拯救受西欧虐待之国民,……使其获得人类最宝贵之自由权利,不受任何外部不当压迫,发扬其本来文化。”[9]其他一些重要的法西斯性质团体,如对外侵略干涉活动频繁的“黑龙会”,其纲领中就提出,日本要“阐扬东方文化之大道,进而图东西文明之浑合,以期充任亚细亚民族之领导者”[6]96。激进主张“建设新日本”的“犹存社”也放言表示,“吾日本民族必当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漩涡中心……,日本国家乃是使我们世界革命思想形成之绝对者。”[6]85从根本上说,近代日德两国的侵略主义者们,正是靠着不断宣扬自身优于他人的“差异”(difference)和“实力”(power),为“对待异己提供了动机和理性”[10]。
(二)实施种族主义暴行
在近代日德两国的对外武力扩张中,血腥暴力行为如影随形。就种族主义暴行的实施而言,纳粹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歧视和消灭犹太人、驱逐和迫害其他欧洲弱小民族的罪恶行径已经是世人皆知。据现有资料估计,二战期间死于纳粹屠杀的人数大约在l 200万到l 400万之间,其中仅犹太血统者就有560—570万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南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近300万苏联战俘以及200万波兰和苏联地区的平民,死于纳粹的集体枪杀、选择性饥饿政策以及针对游击队的所谓“剿匪行动”[11]19。
随着1930年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逐步扩大,其犯下的各类暴行亦是罄竹难书。如在侵华战争期间,仅以大屠杀暴行而言,粗略统计就有几百万中国人受其残害。[12]而其中,种族主义思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煽动作用。许多日本兵承认,“日本人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在人种上优于中国人。”[13]一名叫阿贺惠的日本兵,反省自己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武器的罪行时说,“我当时明明知道,这种毒气武器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杀人武器,但是,我还以‘这是日本侵略军独有的武器,对手是中国人’为理由而加以使用了。……我是荒谬地怀着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蔑视,就忘乎所以地蹂躏了人道主义,无视国际法,干出这种惨无人道勾当的。”[14]曾在中国山西作战的日本兵近藤一,2003年11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法庭上对过去的罪行做了反省,称其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因此怎样对待那些“劣等”的中国人都不为过,“杀中国人如同杀猪杀鸡一样,是没有罪的。杀他们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国家”[15]。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对所谓“血统”“遗传”等因素重要性的过度迷信,日德两国政府都出台了强行干预民众生育活动的法律政策。德国纳粹掌权后,先后颁布了《遗传病后代预防法》《婚姻卫生法》等法令,剥夺疾病患者的结婚权利,并且对患有遗传疾病的人员,如先天性弱智者、精神分裂症者、遗传癫痫症者等,实行了强制性的人工绝育措施。[16]同样,日本也于1940年出台了《国民优生法》,对那些患有恶性遗传性疾病等“不健全者”实施优生节育手术,旨在“防止及遏制有恶性遗传性疾病人数增长,增加健康者人数,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加强国民素质和净化民族血统。[17]尽管由于战争后期兵源紧张,日本政府放松了对相关法案的执行力度,(4)有统计指出,该法律颁布后的1941—1948年间,实施不孕手术的事例总共只有538件,所规定的“强制断种”案例1件也没有出现。参见園井ゆり《優生思想の社会史序説:明治以降の日本社会を例に》(《人間科学共生社会学》4,2004年2月,第43-59页)。但从种族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思想意识”“种族主义偏见”“种族主义行为”这三点要素来看,[18]日本的种族主义思想仍与德国纳粹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二、日德种族主义的差异
(一)关于日本“灭绝种族罪”的界定
一方面,学界大部分观点认为,二战期间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动充满了种族主义暴力。如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Gavan McCormack),就认为日本的行径符合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定义的“灭绝种族罪”标准,即“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19]。德国法学教授克劳斯·马克思(Klaus Marxen)等人指出,虽然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方式和范围”上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有系统、有计划的”[11]23。即便是日本人自己,对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发生原因,也有人认为那的确是由于日军的军纪败坏、种族沙文主义以及强烈的报复心理所造成的。[20]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战争时期日本的种族暴力行为和纳粹德国有所不同,其对于其他种族的排斥和迫害,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国家性的公开政策。像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就认为,关于二战中德国纳粹的暴行,确实没有什么辩解的余地,其大量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实无法推翻。与之相对,虽然日本当时在亚洲各国也不乏暴行,但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对一个民族进行有系统、有计划,并且冷酷无比的杀戮”[21]。日本学者石田勇治指出,尽管“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对外侵略期间所犯屠杀罪行的一种典型表现,但其并非出自于“参谋本部或国家的命令”,而是“现场指挥官的意愿和普通日本人的个人行为”[22]。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也曾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很明显,南京大屠杀是无数小规模屠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但是这种大开杀戒的背后并没有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支持。”[23]
以法律视角看,在二战后对德日两国进行的战争罪行审判中,“纽伦堡审判”注重反人道罪即种族灭绝政策的追究,“东京审判”则注重破坏和平罪即侵略战争罪的追究。由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所以反人道的种族灭绝罪成为其战争罪行的重要特征,而日本虽然也犯有“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重大战争罪行,但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在发生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在判决时反人道罪没有被单列,而是与一般违反战争法规罪放在了一起。[24]如英国陆军第八战争犯罪调查组的一名上尉,就曾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作证表示,诸如当年日军对南亚加里曼丹岛地区苏鲁克人的大规模杀戮,属于日本宪兵队镇压反抗时的过激行为,“而非日本官方有灭绝这个种族的意图”[25]。此外,由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因自身的战略利益需要放松了对日惩罚力度,最终像日军731部队进行人体细菌武器试验等罪行都未被列入审判程序,从而导致“东京审判”本身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不彻底性,事实上也间接影响了日本种族主义相关罪行的裁定,这些都成为部分人对日本“灭绝种族罪”产生界定分歧的原因。
(二)日德种族主义的相互背离
受“黄祸论”(Yellow Peril)(5)意指黄种人的发展可能会给白种人带来威胁和灾祸。这一论调最初所针对的是清末人口众多的中国,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势力不断增强,其逐渐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参见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20-227页)。等学说以及自身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纳粹党首希特勒在内心深处对“黄皮肤”的日本人抱有本能的厌恶和偏见。希特勒坚持认为,雅利安人创造了世界文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无论何时他的最聪明的前额都会迸发出神圣的火花”。而日本人作为“二流人种”,如果缺乏雅利安人持续的影响力,其文化就会“变得呆板,退却到在雅利安文化浪潮推动下才刚起步的休眠状态中去”[26]。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里面大量充斥着针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内容,以致该书后来在日本译刊时,日本官方还不得不对其进行了大幅删改。[27]237
希特勒早期的此类对日种族评价,显然不利于后来德日同盟关系的构建。1934年,纳粹文人约翰·里尔斯(Johann von Leers)向政府高层提交备忘录称,“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政治盟友都是蓝眼睛和黄头发。政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大众的利益,与种族思想的关系并不大。”他援引一些德国学者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声称9.3%的日本人的眼珠为半褐色,82%的日本人发色不是黑色而是深棕色,日本的军政要人多具有“小脸”“高鼻梁”等显著的欧洲民族特征,试图以此说明日本人与北欧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28]对希特勒等人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更是直接表示,“扮演白人种族理论家和思想家的角色,对我们毫无益处……我们决不要这个角色。在政治学领域,没有种族偏见的容身之地。”[29]
事实上,随着后期日本的对外行动逐渐有利于德国,希特勒的对日评价也开始有所变化。例如希特勒后来虽仍认为,日本人“就种族而言是缺乏创造力的民族”,但同时又称赞日本人“毕竟很聪明”。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动,一度受到德国自由派报刊的抨击,但希特勒却夸奖那才是日本人的优点。[30]希特勒还授予1万名居住在德国的日本人“荣誉雅利安人”头衔,宣布他们的待遇远高于其他“非雅利安人”[27]242。当然,希特勒对日种族评价的变化更多是策略性的,正如其所言,与黄种的日本结盟,并不违背德国的种族主义理念,“在眼下事关生死的战争期间,重要的是胜利。甚至为此可以不惜与恶魔联手”[27]245。
日本方面其实对此也心知肚明。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前夕,作为政府智库的“昭和研究会”,在一份名为《三国同盟问题对策》的报告中,归纳了日本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同德国的“巨大差别”:“日本基于皇道的对外政策是以光照道义的八纮为理想,与德国霸道的行动有质的不同。”“我民族政策是东洋民族主义,有接纳异民族的宽阔胸怀;德意的民族政策是雅利安人的民族主义,有强烈的征服异民族的倾向。”[3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招牌下,日本有关机构甚至还对日本国内、伪满洲国、上海租界等地区的犹太人多加庇护,意在抢占舆论道德高点和获取犹太人资金支持,这些都明显与德国的种族主义方针大相径庭。[27]246
双方思想意识里的这种貌合神离,更被随后各自的实际行动所佐证。例如,虽然德日两国都敌视苏联、英国和美国,但在不同时期将谁作为主要敌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1938年前,德国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希望日本能参与对苏作战,而日本虽然也想吞并苏联远东地区,但由于正全力侵略中国,最终无力顾及对苏作战;1938年后,希特勒为避免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令当时意图两面夹击苏联的日本大失所望;再后来,当德国占领北欧诸国、再度准备进攻苏联时,日本却在政策上放弃“北上”选择“南进”,于1941年3月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将主要敌人锁定为英国和美国。从1933年到二战结束,尽管日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结成了名义上的政治、军事同盟,但事实上却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配合。(6)参见工藤章,田嶋信雄《日独関係史2 枢軸形成の多元的力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1章)。在上述背景下,两国的种族意识因各自具体利益差异而产生背离,自然是可以预料之事。
(三)日本的“种族屈辱感”及逆反
如前所述,在德国种族主义者眼里,只有身材俊美、白肤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才有资格处于人类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是世界上最卓越优秀的人种,而除其以外的其他人种,都属于“低级或劣等”。在这一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德国纳粹分子掌权后,出于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以及文化、情感上固有的厌恶,其除了对“黑种”“黄种”等有色人种实施“常规性”的人种歧视外,还将种族主义政策的攻击矛头重点指向了犹太人、斯拉夫人、吉卜赛人等广义上的“白色人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整个社会开始全面西化,宣扬白种人至高优越的“白种优秀论”一时间成为日本人信奉的真理。毋庸多言,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连续对外侵略战争的得逞,对于渐成世界强国的日本来说,亚洲人等有色人种“理所当然地”沦为了其贬低和歧视的对象。但颇为讽刺的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论调盛行的时代环境下,日本人自身也同样难以摆脱来自欧美列强的人种歧视。一战后巴黎和会日本提出“人种差别废除议案”被否决、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等事件,都清楚地表明了西方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态度。[32]像在二战期间,虽然德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敌国,但在众多美国人的眼里,德国人只是纳粹独裁下的受害者,或者至少是与自己一样的同类,而日本人却纯粹属于毫无人性可言的“异端种族”[33]147。充满人种歧视性的“患黄疸病的狒狒”“猿”“猿人”等词语,是一些美国媒体贬低日本人形象时的常用描述。[34]
日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人在西方长期歧视下形成的人种自卑和愤恨,转而以排斥、仇视白种人的形式爆发出来。尤其在战场上,为了发泄人种屈辱和憎恨,日军甚至会对金发白肤的英美战俘专门进行折磨和残害。[33]150受此影响,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关押下的美国战俘有将近40%死亡,而与之相比,死于德国纳粹之手的美国战俘只占1%左右。[35]2当时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日本人的心理和文化“似乎是在征服欲和面对西方国家的自卑情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33]147。
日本人这种因被种族歧视而产生的逆反心理,还体现在对白种战俘的“征服展示”上。俘获英美士兵后,日军有意识地将其分散到各地的战俘营进行关押和劳役,借此炫耀日本帝国不可战胜的“英武形象”。1942年,日本驻朝鲜军参谋长要求将东南亚战场上俘获的2 000名英美战俘移送至朝鲜关押,“借此扫除对英美人之崇拜,确立必胜信念”,“令朝鲜人从现实中认识到帝国之实力”[36]。同年4月,日本东京战俘信息统计署发电称,“我们将要把战俘作为劳工使用,……另一方面也要把战俘作为教育和指导当地民众的反面教材。”一份由日本神奈川县知事发给大藏大臣和内务大臣的电报,更清晰地表露了日本的报复和炫耀意图:(民众)“知道这些外国人是战俘后,将会感受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因为原来高高在上的英国人、美国人竟然被皇军捉到日本工厂里来劳动……这会让我们的国民认识到,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35]45
著名学者桥川文三指出,诸如美国对日移民排斥等种族歧视行为,变相地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法西斯主义加速发展的催化剂。在当时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加重,对外扩张受到压制(如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限制)的大背景下,日本社会普遍表示出了对美英等白种列强既有统治权的不满和抗拒。在种族意识上,“日本出现了某种超越人类理性的恶灵。对于纳粹来说,那是一种出自于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神圣信仰,但对于日本来说,反倒更像是被白种人事实上的优越感所刺激,在累积到几近绝望的压抑感中,产生出的一种错乱信念”[37]。可以说,与德国纳粹自始至终坚持的自我种族优越意识不同,部分日本人面对亚洲有色人种时的“自大”与“狂妄”,面对西方白色人种时的“崇拜”、“自卑”与“憎恨”,一直是其种族主义意识中无法克服的矛盾样态。
(四)日本种族意识的投机性
正是由于日本面对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时有着不同的心态和目的,造成二战期间日本的种族主义相关行动也充满了强烈的投机色彩。例如,针对亚洲人等有色人种,除了武力侵略统治和奴役压迫之外,根据不同的政治局面需要而进行拉拢和利用,也是其种族意识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像日军占领中国大部分地区后,为在统治上达到软硬兼施的效果,劝诱中国民众妥协投降的“中日同文同种”“黄种提携联合”等口号,是其维护和加强控制的常用宣传内容。在东南亚战场上,为了鼓动印度人的反英情绪,首相东条英机在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就宣称,“拥有数千年历史及光辉文化传统的印度,如今也处在挣脱英国暴虐压制而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绝好时机”,日本将竭力对同处亚洲的印度施以援助,使其脱离白色人种的殖民桎梏。[38]
日本种族意识里的投机性,甚至还部分体现在针对苏联的外交表述上。尽管日本一直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洪水猛兽,对其抱有深深的戒备和敌意,但是随着后期战争局势的变动,日本官方的对苏评价也开始有了很大改变。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署后,日方代表公开称赞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道德肮脏”的种族歧视。当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劣势后,日本甚至开始冀望利用苏联与西方的矛盾以及“泛亚主义”思想来扭转战局。一些重要的上层领导人,像东久迩宫稔彦王,就多次强调日苏同是“亚洲成员”,因此要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英美的入侵。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员,这样苏联就永远不会站到白人那一边。”[39]
日本方面也深知,对外不当的种族意识表述和行动,有可能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1941年11月5日,在最终决定对美英开战的第七次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与首相东条英机的对答,就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对种族意识影响的顾虑。原嘉道担心日本参战后,作为白种的德、英、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产生变化,由于“德国未曾对美直接宣战,希特勒亦认为日本人是二流人种,故日本对美开战后,一旦德国与英美之间因人种喜恶而达成一致,则日本很有可能陷于孤立。此种敌意,若因厌恶黄色人种之故而由德国转向日本,则日本有被全体雅利安人种包围之危险”。对此,东条英机也表示认同:“正在考虑不让开战之结果成为人种战争。努力利用东南亚武力战斗成果诱导德意两国,避免德英、德美讲和。……无论如何一定注意避免使之成为人种战争。”[40]
职是之故,在具体的操作中,尽管“反抗白种殖民压迫”之类的口号,对于日军的攻占统治仍有实际利用价值,但日本官方则在口径上始终保持谨慎,严格控制着舆论对战争性质的宣传。对美开战伊始,日本在《日英美战争情报宣传方策大纲》中着重强调,“为针对敌国进行谋略战,确保与轴心国齐心协力,必须排除暗示此次战争是民族战争,特别是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间战争的各类言行。”[41]1942年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发令,要求各兵团“应明确认识,此次战争并非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而是驱逐近百年来侵略东亚的美英势力以解放东亚的圣战,要粉碎敌方离间日德意轴心国的阴谋”[42]。
概言之,相较于德国这样的西方传统强国,由于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后起性,造成其在对外思想认识和行动模式方面,受到了更多现实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在对外扩张侵略上,限于实力不济和战略需要,日本一方面暗自利用所谓人种上的“同一性”,极力以“有色人种联合反抗白种殖民统治”之类的口号,来欺骗和裹挟亚洲其他国家受其奴化、与其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又非常惧怕由此引发美、德等白色人种国家对其的集体敌视,进而陷入战略上的孤立与被动。其种族意识里希望左右逢源、唯利是图的两面性,在上述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中充分展现出来。
结 语
战前日本的种族主义思想,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其他思想理论掺杂在一起,成为其对内强化统治、对外发动侵略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从这一层面来说,日德两国侵略扩张思想中的种族主义,无疑在作用与影响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然而如上所述,相比之下,属于“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又因不同的历史条件、心理背景、政治考量,在种族主义的表现及相关应对运作上,与纳粹德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其中的“同”与“不同”,都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观察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思想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日本战争分子恃强凌弱、残暴狡诈的本质。
二战结束至今,虽然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思想整体日渐衰微,但在少数国家和人群中依然拥有一定市场。像在德国,以敌视移民为主要内容的“新种族主义”,日渐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即便是在号称“国民全体平等”的现代日本,作为少数群体的“阿依努人”和一些“部落民”(7)指世代从事“屠宰”“丧葬”等被视为“下贱、不洁”职业的人群。,仍长期在就业、住房、养老等方面遭受着差别待遇。[43]此外,就如部分日本人口中的“第三国人”(8)主要指自殖民时期就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和台湾籍的中国人。一词所示,居日的朝鲜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一些低收入外国移民,也常是其歧视的对象。日本人较为同质的民族特性,以及长期沿袭下来的对外来人群的戒备感与排斥感,都使得种族主义及其变种思想并未在日本完全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与二战后德国对纳粹分子的严厉打击不同,由于日本对历史责任的反省并不彻底,近些年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不断加剧,像前首相森喜郎“日本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44]之类的声音屡有出现。部分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分子,也纷纷通过鼓吹各式“日本人种优秀论”,试图从生物属性上抬高自我,进而达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美化侵略战争罪行、重塑日本帝国形象的目的。[45]日本此类种族意识的不断延续与翻版再现,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