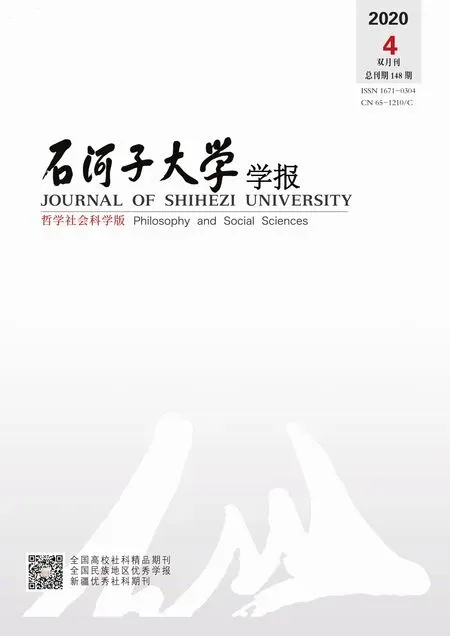国际伦理发展趋势探究
——一种以国际法为基准线的国际伦理研究视角
2020-12-09姜丽萍
姜丽萍,曹 兴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102488;2.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8)
国家伦理如以国家内外关系为坐标,可分为国内伦理和国际伦理。本文研究的是国际伦理的发展规律,首次提出国际伦理发展规律是从无到有、从敌对伦理发展为竞争伦理再发展为合作伦理的规律。其中,发展的轴心以国际法为基准线①所谓国际法,通常是指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规则总体,是若干国家参与制定或者国际公认的、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国际法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相对而言,国际法不仅是国际伦理的硬性指标、底线(下限)和中轴线,当国际伦理水准低于国际法标准时,说明人类伦理已经失去文明的水准进入野蛮区域;反之,当国际伦理水准高于国际法时,说明人类伦理已经离开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区域。
一、初民社会:伦理从无到有的节点
早期人类是从动物界向人类的过渡群体,处于半人半兽的发展阶段。据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研究,认为文明起源于宗教。宗教是原始社会包括万象的文化母体。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基于劳动、语言、宗教把人提升为文明的人,是告别类人猿的根本原因。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点在于人能够系统地制造工具、运用抽象思维的语言和宗教信仰[1]389。因此不难断定,人猿揖别的根本区别离不开宗教信仰。
然而,在笔者看来,与其说人类文明起源于宗教,倒不如说文明起源于伦理。因为,所有的宗教规范都是伦理。伦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宗教作为人的行为能够有别于动物的行为规范,就是伦理,或者说伦理才是宗教的本质。因为,抽出伦理文明属性,宗教什么都不是。人类发展只有到了构建伦理规范(包含在宗教之中)的时代,才标志着人类成为真正意义或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才真正告别了动物界。这是人猿揖别的软件标志。此外,硬件或经济标志是农业文明的出现,人由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的转变。考古学显示,“370万到1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已经开始了从猿到人的过渡,猿人开始使用工具,体质逐渐变化。到170万年(或15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于地球……约一万年前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农耕和畜牧,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为食物的生产者……”[2]19不难断定,远古时代以前的人类还处在半人半兽时代,甚至可称为文明史前时代,是考古人类学所说的旧石器时代。那是一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的时代。
如果说文化的历史至少有几百万年,而文明史最多不到一万年,多数民族只有几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素有五千年之说②一般都认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确切说炎黄是汉人的先民。。据著名中国史学家王桐龄考证,“距今四千余年前,汉族滋生于黄河流域,以耕耘为业”③王桐龄:《中国史》,《自序·历代各民族之盛衰兴亡》,第13页。王桐龄(1878—1953)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号峄山,河北任丘人,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才产生了伦理。因此,人类伦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伦理是与文明同时产生的。人类历史远远长于文明的历史。氏族社会是伦理从无到有的节点,从而绽放了文明的曙光。
文明诞生前的世代,人类大致经历过四次革命性的飞跃。第一次革命是从猿进化为类人猿,标志是直立行走,大约是250万年左右。第二次革命是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标志是人能够制造工具、协作劳动,有了群体交流,约为20万年前。第三次革命是从采集狩猎经济转向为农业经济,标志是村落的产生,人类进入到氏族社会,宗教有了长足的发展等等,大约在1万年前。伦理就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第四次革命是“大约6000年前,土地开垦和集约农业的新技术,使一些处于丰饶地域的群体,通过锄耕向犁耕的转化,得以显著地提高了产出”[3]15。据史学家研究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有先后之差。埃及和两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即跨入文明,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爱琴地区稍晚一些,大约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进入文明,中南美洲则更晚一些,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进入文明。”[4]20
氏族共同体是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高级状态,国家是躁动于氏族共同体之母腹的婴儿。学者时常称之为“初民时代”。其实,初民时代不是猿人时代,而是氏族时代。“初民”是指初步进入文明的人类。产生伦理规范人们的行为是文明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类人猿、智人是没有社会伦理规范的。人类基于伦理规范才把野蛮人提升为文明人。氏族社会产生了最初的社会伦理,告别了类人猿的野蛮状态。类人猿和智人是野蛮状态的人类,很多契约论哲学家、国际法学家称之为“自然状态”的人类。这也是无国际法发展的状态。
第一,伦理是共同劳动的需要。氏族社会之前的原始人所结成的“群体是靠单纯的本能聚合起来的群体,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采集、共同抵御毒虫猛兽的侵袭等等几乎仍然靠的是动物的合群本能。这种本能,我们从许多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动物那里可以发现其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5]38共同劳动中产生了原始共产主义伦理。
第二,伦理的产生是群体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产物和需要。人类的群体性是从自然或天然本能的群体性提升为社会群体性的。据人类学家考察,由于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初具规模的社会,因此最初的社会群体规模都是很小的。氏族社会最少数量是30至100人组成一个部落①Christopher R.Decorse,Anthropology:a Global Perspective,Third Edition,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1998.p118.。“一个氏族集团的成员不会很大,据一些人类学资料,一般不超过一百余人。”[6]768很显然,百余人不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家族。家族是氏族部落的最初表现形态。家族的力量极大地克服了个体力量的不足,增强了战胜自然、抵抗其他大动物袭击的能力。
第三,伦理的基础是婚姻家庭伦理。家庭伦理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一个根本性环节。在人类早期的几百万年中间,人们所过的男女生活,群婚而居,没有家庭,毫无伦理可言。为此古人说,“古者未有夫妇匹配之合,野处群居”②《管子》。,“男女杂游,不媒不聘”③《列子》。。那个时代还没有乱伦的禁忌。故马克思说,“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7]32然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性交方式不仅产生了伦理观念,而且终于产生了近亲不婚,后来到了中国周代(国家产生后)演变为更为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度④同姓不婚始于中国西周初期,是周人实行族外婚时遗留下的规定。春秋时,人们对同姓婚配会造成后代畸型及不育已有进一步认识,但同姓婚配仍在贵族中时有发生。。
家庭伦理是中华伦理最为发达的伦理元素。中华文明早在远古时代就诞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约在六千年前,逐渐摆脱采集和狩猎经济,进入到以种植为主的原始农耕经济。大约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中国人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⑤参见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中国远古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中,缔造了父权家长制,进而塑造了宗法制伦理。在西方社会从血缘社会到国家社会的转型中,血缘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所代替。在中国则相反,从三皇到五帝,再到夏商周,不断强化了血缘关系,因此从宗法制伦理走向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无论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所形成的父权家长制,还是此后逐步联结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至形成国家,人们的血缘关系不但没有松动、解体,而且恰恰相反,逐渐被打上阶级烙印,越来越牢固”[8]10。在笔者看来,两者具有某种因果关系。宗法制伦理塑造了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宗法制伦理是造就家国一体社会体制的原因,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是宗法制伦理的必然结果⑥参见曹兴《缘何走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悖论》,载于《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
此外,初民的产生就是人类文明产生的主体标志。把初民凝聚在一起的文明纽带和伦理规范是什么?考古成果惊异地告诉我们这个最初的文明纽带是宗教。氏族社会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其中氏族伦理是氏族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宗教禁忌则是氏族伦理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主体发展经历了多次质的飞跃,人类宗教和伦理的发展形态也相应发生大的飞跃。把初民凝聚在一起的文明纽带是多种标识的,在物质文明形态上是城市,甚至包括文字,而在精神文明标识上则是宗教。
第四,在研究宗教和伦理的关系时发现,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宗教伦理滋养了早期人类伦理。或者确切地说,早期人类伦理是从宗教伦理发源的。从此意义上讲,伦理与宗教是共生的①参见曹兴《全球伦理二象性理论结构》,载于《扬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在国家伦理产生之前,支撑人类精神文明的是氏族宗教,早期宗教成为早期人类一切文化的母体或文化起源。从伦理发生学意义上讲,没有早期人类的宗教禁忌,就不会产生前国家伦理和后来的国家伦理。早期人类的宗教戒条远比国家伦理产生的要早得多。很多宗教伦理的合理成分成为人类伦理的必需的内容,这具有很大的共性。如中国传统宗法制的忠孝,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摩西十戒中的后六条即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陷害他人和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以及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各大宗教中都含有大爱精神,包容了世界各族伦理的最大共性,都是人类伦理的来源。
二、从敌对伦理到抗争伦理再到合作伦理
氏族社会之后,人类发展的每一次主体提升都会引发新一轮伦理的提升。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古代国家社会,氏族伦理提升为古代国家伦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结束了古代伦理,催生了近代国家伦理;全球化时代则把全球伦理推向人类伦理的前台。因此,人类伦理是从无到有、从氏族伦理发展到古代国家伦理,再发展到近代国家伦理,最后发展为全球伦理与现代国家伦理并存的过程。全球伦理开启了地球人的“类伦理”。全球伦理是伴随人类群体性向上攀升而在伦理规范向前发展的过程。
文明之初,族内社会成员,相互视为同胞,遵守族内或国内伦理。一方面,不同民族伦理有着不同的民族伦理特色。中华民族走上的是一条“‘人本’而非‘神本’、以家庭为核心而非以个人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发展道路”[9]2。为此,追求忠孝伦理的宗法制成为中国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文化伦理轴心。古希腊社会,对于限于贵族的公民范围,推行正义、公正,正义成为古希腊政治发展、学者学术发展的中轴。因此,以追求正义为轴心的自然法特别发达。另一方面,各民族的伦理具有共通性,如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是各族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
人类发展产生伦理虽然意味着文明的开始。但是,文明的适用范围率先开始于族内或国内伦理,而在族际或国际关系方面仍处于野蛮状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戒条仅仅适用于族内或国内——在战争中必须杀死对方,自己才能获取胜利。战争状态中,族际或国际关系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②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9页。。在学界把这种状态称为是霍布斯文化或者霍布斯自然状态。人类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产生了共同的国际意识形态,即敌对的国际关系③氏族社会还没有产生国家,因此没有国际关系,但有的却是族际关系,即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温特提出,“自然选择可以解释霍布斯身份在3000年前的出现”[10]317。
自从国家产生之后,国家内部呈现一片伦理的绿洲,人人都享有国家伦理不同程度上的保护。而国际社会则处于无政府状态,野蛮的成分远大于文明的成分。很多人误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也就意味着无秩序状态,甚至意味着无伦理状态。然而,无政府状态并不等于无秩序、无伦理状态。无政府状态并不等同于无秩序状态,两者没有必然联系。秩序源于伦理,或者秩序就是规则或伦理方式。共同生活方式产生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共同的伦理方式。秩序源于伦理,有了伦理才有秩序。族内或国内伦理秩序是良性的,而族际及国际伦理秩序则是恶性的。国家内部是有政府有秩序,而国际上则是无政府有秩序。第一种国际伦理形态是霍布斯伦理文化,那是一种最糟糕的秩序或者是最坏的秩序,相互之间充满敌意,表现为冲突、对抗、敌对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战争状态。
我们提出疑问,初民时代族际关系都是战争状态吗?难道没有和平状态吗?和平年代是常态,还是战争状态是常态?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显然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这种猜测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状态。因为,霍布斯年代,人类考古学还不很发达,许多关于远古时代和上古时代社会状态,都是一片空白。为此,笔者借助于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摒弃近代哲学家自然状态的猜想,而根据后来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证实是相反的画面。
根据霍布斯伦理之后的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在人类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人口少而土地多,族际之间很少发动战争。新石器时代后期,爆发战争是因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造成的。根据英国史学家尼尔·福克纳研究,“起初,世界上并没有战争。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250万年里,小群的原始人在大陆上游荡,通过捕猎、采集和清除来寻找食物。不同的群落很少相遇,任何形式的冲突就更加罕见。只是到了后期,随着地球上人数的增加,出现了争夺资源的偶然冲突。……战争是对立的群体之间大规模的、持久的、有组织的暴力冲突。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开始的农业革命之前,没有发生战争的证据”[3]15。“早期的农业是浪费的,土地被清理、耕作、耗尽,然后放弃。使土地保持‘好的质量’的休耕和施肥,在当时还不是普遍做法。而当人口膨胀之时,土地的易接近性和可耕作性都开始耗尽。早期新石器时代经济的这些矛盾,促发了战争。”[3]14有一项考古成果证实了普遍的战争促发于新石器时代。德国西南塔尔海姆死亡坑揭露了公元前5000年早期新石器的战争痕迹:“34具尸体,其中一半为孩子,被倾倒在一条3米的深坑里。两个成年人被箭射中头部。其他20个人,包括孩子,是被棒子打死的。人类学家丝毫不怀疑,这是一个屠杀的地点。……人类已经开始从事战争。”[3]15随着人口增多和土地的冲突,战争不断升级。据考证,“在公元前3700年到公元前3400年,一种基于土地控制、部落联盟、大规模祭礼和战争的新秩序,在不列颠建立起来了”[3]18。
因此,不难断定,战争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战争从旧石器时代偶尔发生的非常态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时常发生的常态,但后者战争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积累,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战争中的俘虏从原先被杀害而变为奴隶。因此,使部落之间的战争由血亲复仇变为掠夺财富的战争。……以掠夺财产和奴隶为目的的战争日益经常发生”[4]19。族际之间的战争,把俘虏变为奴隶,由此族际之间的伦理演变为社会内部阶级伦理——奴隶主奴役奴隶的伦理。于是,国家及其早期国家伦理也就诞生了。
从上述考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人口数量与土地森林等资源的比例看,人类从少到多,相对人口增加资源则从多到少,转折点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代,之前族际之间很少发动战争,在那之后族际之间开始战争,解决资源问题。起初战争只是发生在族际之间,而不是族内。因此,战争伦理发生在新石器时代。
在中国远古(五帝)时代,“礼”是约束本族人的行为规范,是为对内伦理;“兵”发生于不同部落之间,成为族际之间相互惩罚的行为规范,是为族际伦理。中国三皇五帝时代,战事之多,世间罕见,因此关于兵的规则很发达[8]12。究其原因,尤其特殊的人文地理,天然屏障少,农业条件好,人口众多,需要争夺生存地盘。
国际伦理从霍布斯伦理发展为洛克伦理再发展为康德伦理都有一定的时间节点。根据国际关系学界分析,霍布斯伦理大约经历了四千多年,即公元前3000年到1648年。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温特提出,“霍布斯身份在3000年前的出现……”[10]317他认为洛克文化开始于17世纪的欧洲:“17世纪欧洲国家建立了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相互承认主权的做法限制了冲突。这种文化最终成为全球的文化,虽然在有些地方是通过霍布斯式的殖民主义进程建立的。”[10]309他还提出,“当无政府体系初始之时,自然选择更易于产生自助文化,而不是助他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发生过的假设被罗伯特卡内罗的研究所证实,他估计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有60万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今天只剩下约200个”[10]316-317。从霍布斯伦理转向洛克伦理的时间标志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建立,从洛克伦理转向康德伦理的时间标志是1945年后联合国的建立。
为什么霍布斯伦理向洛克伦理的转折点是1648年?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以国家利益为追求的工业文明时代所产生的国际关系取得了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1648年颁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果在于,法国和瑞典联军阻止了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宣布了帝国称霸的失败。后来这种阻止称霸的历史典故还很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61—1714)企图称霸,但被英国荷兰联军阻止了;拿破仑(1795—1815)企图称霸,被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四国阻止了。希特勒(1939—1945)企图称霸,被美国、苏联与英国阻止了。对此,温特明确提出,“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虽然战争频繁,权力分配不均,但是国家的死亡率却大大降低。小国发展起来,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看起来似乎是‘自杀性’的大国也得到了‘改造’。海湾战争是二战以后很少的几个这样的例子中的一个,当一个国家出于被另一个国家夺去‘生命’的危险境地,侵略者(伊拉克)也会被来自全球的国家联盟所打败,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科威特并没有什么自我利益。”[10]317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法律文件,是把国家主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重要文件。
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世界大战中觉醒了,开始构建合作伦理并萌芽全球伦理,以期待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伦理体系或者洛克伦理文化。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时称之为“康德文化”,笔者称之为“康德伦理模式”。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及实现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已经具有了全球伦理的意义。联合国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全球性事务的开始,而且意味着全球伦理、全球治理的萌芽,尽管当时还没有产生全球伦理、全球治理的理念。联合国的议事规则和提倡的伦理规则已经是潜在的全球伦理了。可以说,联合国的诞生叩开了全球伦理、全球治理的大门。《联合国宪章》的出现标志着国际伦理的法律化,开启了国际伦理提升为国际法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如果说霍布斯伦理的本质是铸就国际间的敌对关系,那么洛克伦理的本质是打造国际间的竞争关系,康德伦理的本质则是营造国际间的合作关系。
三、历史加厚发展观及现代三重伦理并存观
笔者在研究人类伦理发展中发现一个规律,即人类从无伦理时代的类人猿、智人发展阶段提升到产生氏族的氏族社会时代,之后伦理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古代伦理发展到近代伦理再发展到现代伦理。具体来说,是从古代文明的王族伦理(中国)或贵族伦理(古希腊古罗马)发展到近代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伦理再发展到现代的全球伦理;国际伦理则从敌对性伦理发展到竞争性伦理再发展到合作性伦理。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温特和布尔把国际关系类型或世界无政府状态分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温特)或格劳秀斯文化(布尔)和康德文化,主旨分别为敌对、竞争和合作。温特和布尔两人思想中存在一个根本性错误,那是理论方法论的错误,他们都认为三种文化状态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流转替换”或“替代”,这有如黑格尔批判过的,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杀死一个的古战场。其实历史发展绝不是替代发展的。历史方法论的错误必然导致观点、结论和路径预测等方面的错误。
笔者改用一种历史增厚发展方法论,扬弃温特和布尔的流转替换发展观。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不会沿着温特和布尔所理解的那样,由霍布斯文化转换为洛克文化再转换为康德文化,不会是沿着由他们规划好的路线发展下去,而是以自己固有的路径发展下去:世界共同体或国际体系不仅不会消灭国家体系(即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而且还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巩固国家体系或改变原来的国家体系,同时还兼备发展出一些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如联合国)或半全球性组织,与国家间国际体系进行多重交合、对立统一,形成一种路径向前走下去。
当然,温特和布尔的理论只是部分错误的,其中也包含有合理成分。笔者将继承并吸收二人的合理性,同时克服并批判二人的缺陷,提出一套有别于温特和布尔的新的理解,他们都认为历史是轮流替换的,笔者则认为历史是增厚发展:历史沉淀到现实中,现实沉淀在未来中,不断加厚发展下去。因此历史不是轮流替换,历史不是古战场,不是一个杀死一个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向前发展;而是传宗接代,不断加厚,现实能够看到过去历史的影子,未来能够看到过去和现在的双重影子。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三种伦理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尽量避免敌对的霍布斯伦理文化和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洛克伦理文化,倡导提速人类进入合作共赢的康德伦理文化的实践进度,使得无政府状态的发展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世界各国被整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前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发生了两次质变,即国际关系由敌对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再转变为合作关系,或由敌人转变为对手再转变为朋友。当今世界虽然已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时代,但是根据西方理念依然有很多国家间关系停留在敌对状态和对手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直接穿越霍布斯伦理,进入康德伦理但不否定洛克伦理,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非凡意义:以合作为轴心避免战争,营造和平、发展局面。
当今世界,国际伦理出现两种发展潮流,一种是逆流,即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伦理发展态势,表现为美国推出各类国际组织的“退群”即“退全球化”,还表现为英国的“退欧”,呈现出从全球伦理状态下的国际伦理倒退为民粹主义的民族伦理为轴心的国际伦理,简言之,是从以全球利益为核心的国际伦理倒退为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国际伦理。因此,导致合作共赢的全球伦理被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的敌对性伦理的回潮。所以,它是一种国际伦理发展的逆流。美国与英国“退群”标志着“国际法”发展的脆弱与不成熟。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联合国的所有法律文件的实施或落实都需要责任国的同意或许可,否则相应的国际法律文件就成为无效的文件。另一种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的“公助性”国际伦理,这才代表着人类国际伦理发展的主流。这两股国际潮流的碰撞,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国际伦理的主流仍是主权竞争性伦理,在很多方面仍包含敌对性伦理。因此,不要幼稚地认为,敌对伦理已成历史,已经再现了敌对伦理的回潮。追求合作共赢伦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还很漫长。
基于方法论的不同,本文最后的结论是:自人类产生文明以来,国际伦理从古代伦理发展到近代伦理再发展到现代伦理的规律,就是从自助的敌对伦理(霍布斯伦理)发展到自助互助兼顾的竞争性伦理(洛克伦理),再发展到合作共助的伦理状态(康德伦理)。然而,历史发展并不是简单替代地发展演变,而是不断增厚宛如滚雪球向前发展或者盘旋上升。因此,现代国际伦理虽然已经发展到全球伦理时代,但那只是全球伦理的萌芽,国际伦理的主流仍然是以主权竞争性伦理(洛克伦理),甚至在很多时候仍然包括霍布斯伦理的敌对关系。因此,合作共助、和平发展成为21世纪以后的时代精神追求,还要谨防从属于战争伦理的敌对关系的出现。追求合作共赢伦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可谓任重而道远[11]452!中国和美国、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及其国际伦理也必然包含冲突、竞争与合作的三重关系。基于上述理论自信,认为中国面对其他强国的战略应该是,不挑事、不怕事、当自强;不怕成为敌人,敢于成为对手,最好成为朋友!但不必一味追求朋友关系。